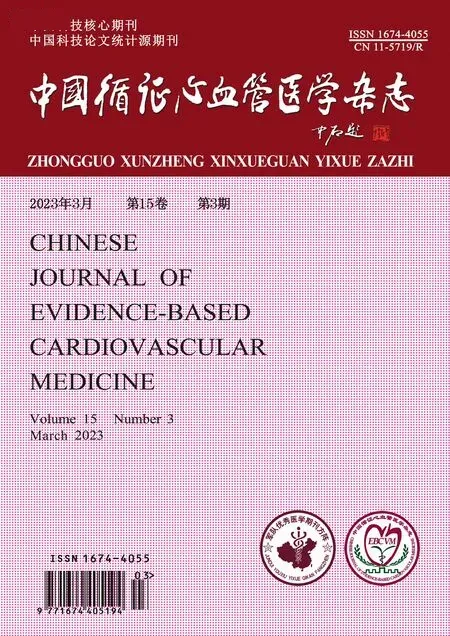高血压早期识别干预的肠道微生态学思路研究进展
赵栩进,李海文,杨志明
高血压是以体循环动脉压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心血管综合征[1]。《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2]显示,我国18岁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23.2%,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51.6%、45.8%、16.8%,根据报告推算,我国高血压现患病人数约2.45亿,而18岁以上人群血压正常高值检出率为41.3%,提示高血压前期人群基数可能更大。目前疾病三级预防观念逐渐普及化、生活方式干预及降压药物治疗方案进一步科学化,高血压知晓率及治疗率已有显著增加,但不可忽视的是,高血压患病率及血压正常高值检出率仍呈现上升态势,且高血压治疗控制率仅为37.5%[2],提使我们现行的高血压防治理念仍存在不足。
原发性高血压是遗传因素和包括饮食、精神应激、吸烟、体重、胰岛素抵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等在内的环境因素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神经机制、肾脏机制、激素机制、血管机制等或独立或交叉地影响机体血压水平及调节[1]。近来诸多研究提示,肠道微生态改变可能是众多高血压致病因素及机制中的一个环节[3-8],为我们思考如何扭转这种基本上升态势及如何改善治疗控制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高血压肠道微生态改变
肠道微生态系统由肠道正常微生物群落及其所生活的环境(即肠道生理结构)共同构成,肠道微生物种类繁多,包括细菌、古生菌/古细菌、真菌和病毒等,细菌群落是其核心部分,而肠黏膜是肠道微生态系统发挥生理作用的结构基础。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及肠道生理结构均发生改变。
1.1 肠道菌群失调成人肠道菌群非常多样化,主要由四个菌门组成:Firmicutes(厚壁菌门)、Bacteroidetes(拟杆菌门)、Actinobacteria(放线菌门)和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其中以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为主,常用的实验动物模型的肠道菌群结构也具有类似特点[9]。
1.1.1 肠道微生态整体评价指标改变Yang等[10]的研究显示,正常血压Wistar-Kyoto(WKY)大鼠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的构成比依次为78.56%、18.30%、2.50%和0.094%,而在以年龄配对的成年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中,构成比依次为94.78%、4.21%、0.26%和0.094%,两组间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的相对丰度存在显著差异。Mell等[11]的研究也表明,Dahl盐敏感(Dahl salt-sensitive,S)大鼠肠道中各菌门相对丰度与Dahl耐盐(Dahl salt-resistant,R)大鼠有显著差异。由厚壁菌门增加和/或拟杆菌门减少引起的Firmicutes(厚壁菌门)与Bacteroidetes(拟杆菌门)比值即F/B比值升高被视为肠道菌群失调的标志,可能是机体病理状态的一种潜在生物标志,而比值减低则被认为是机体处于健康状态的标志。SHR大鼠F/B比值较WKY大鼠显著增加,AngⅡ诱导高血压大鼠F/B比值同样显著增加[10,12]。细菌群落状态的整体评价通常主要通过三个生态参数来实现:Chao1丰富度(评价同一目标生物属在给定群体中的总数)、Pielou均匀度(评价不同目标生物属在给定群体中的相互数量关系)和Shannon多样性(基于属层面的丰富度和均匀度的组合评价参数)。SHR大鼠的肠道微生物丰富度、均匀度和多样性较WKY大鼠均显著下降,AngⅡ诱导高血压大鼠同样显示出类似改变[10,12]。
针对高血压人群的研究显示出了与实验动物模型类似的结果。Dan等[13]的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肠道中厚壁菌门显著增加,拟杆菌门显著减少,F/B比值显著增加,Yan等[14]的研究同样表明,高血压患者肠道中各菌门相对丰度与非高血压对照组人群有显著差异,Mushtaq等[15]也发现高血压病3级患者F/B比值显著增加。与高血压实验动物模型研究结果相一致,诸多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13,14]、收缩压升高患者[10]肠道微生物Chao1丰富度、Pielou均匀度和Shannon多样性较血压正常对照组、收缩压正常对照组有下降趋势。Sun等[16]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血压值与肠道微生物丰富度及多样性呈负相关。有学者将肠型的概念引入,以进一步阐释高血压个体肠道菌群失调状态。共生于人体的微生物所组成的微生物生态组具有个体差异性,但这些微生物并非随机组合,而是具有一定的构成模式,以肠道微生物生态组为例,通过优势菌属命名可分为Bacteroides(拟杆菌型)、Prevotella(普氏菌型)和Ruminococcus(瘤胃球菌型)等不同肠型。高血压患者中普氏菌肠型个体比例相对较高,而对照组中拟杆菌肠型比例相对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7],此结果表明,普氏菌肠型可能与血压升高相关,而拟杆菌肠型可能是血压正常人群更常具有的肠道菌群构成模式。
1.1.2 具体菌群改变SHR大鼠肠道中Streptococcaceae(链球菌科,归于厚壁菌门、Bacilli芽孢杆菌纲、Lactobacillales乳杆菌目)增加,特别是科内Streptococcus(链球菌属)显著增加[10,12]。链球菌属在肠道中酵解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终产物为乳酸,乳酸有助于调节肠道和循环的免疫功能[18]。SHR大鼠肠道中Bifidobacteriaceae(双歧杆菌科,归于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放线菌纲、Actinobacteridae放线菌亚纲、Bifidobacteriales双歧杆菌目)减少,特别是科内Bifidobacterium(双歧杆菌属)显著减少[12]。双歧杆菌属具有益生特性,是维持肠道稳态所必需的重要益生菌,在免疫系统的成熟和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19],同时可调节肠道内代谢[20],可通过产生乙酸盐(即醋酸盐)来改善肠道上皮细胞介导的肠道防御,减少宿主肠道致病菌感染几率[21]。肥胖等原发性高血压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已被证实与双歧杆菌减少相关[22]。而在WKY大鼠肠道中则富集大量产丁酸盐细菌,包括Coprococcus(粪球菌属)和Pseudobutyrivibrio(假丁酸弧菌属)[10]。肠道菌群代谢产生的丁酸盐对宿主具有多种益生作用,如减少肠道炎症[23]、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24]、刺激调节性T细胞产生[25]等。在SHR大鼠中,产乙酸盐和丁酸盐细菌分别减少约3倍和2倍,而产乳酸细菌则明显增加,与SHR大鼠一致,AngⅡ诱导高血压大鼠肠道中产乙酸盐和丁酸盐细菌减少,产乳酸细菌增加[10,12]。有学者[10,26]进一步表述:“高血压相关肠道菌群失调的特征是特定细菌群落及其相应代谢物的失衡,具体表现为产乳酸细菌增加和产乙酸盐、丁酸盐细菌减少”。
高血压患者肠道中Actinomyces(放线菌属)、Bacteroides(拟杆菌属)、Barnesiella(厌氧杆菌属)、Clostridium(梭菌属)、Klebsiella(克雷伯氏菌属)、Megasphaera(巨球菌属)、Prevotella(普雷沃氏菌属)、Salmonella(沙门氏菌属)、Streptococcus(链球菌属)等显著增加[14,15]。许多高血压人群富集菌群与肠道炎症和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相关[27]。而正常血压对照组肠道中则更多富集Anaerotruncus(厌氧棒状菌属)、Bifidobacterium(双歧杆菌属)、Butyrivibrio(丁酸弧菌属)、Coprococcus(粪球菌属)、Enterococcus(肠球菌属)、Enterorhabdus(肠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粪杆菌属)、Lactobacillus(乳杆菌属)、Roseburia(罗斯氏菌属)、Ruminococcus(瘤胃球菌属)等[13,14]。粪杆菌属和罗斯氏菌属等菌属是肠道产丁酸盐细菌,此外,许多正常血压对照组富集菌群拥有大量降解糖等碳水化合物的酶[27],糖的微生物酵解产物可以刺激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包括甲酸、乙酸、丙酸、异丁酸、丁酸等)的产生[28]。Kim等[27]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高血压患者粪便样本中,产丁酸盐细菌的丰度包括Butyricicoccus(丁酸梭菌)、Coprococcus(粪球菌属)、Faecalibacterium(粪杆菌属)、Fusobacterium(梭杆菌属)、Roseburia(罗斯氏菌属)与正常血压对照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人类肠道中主要的产丁酸盐菌之一E.rectale在高血压患者肠道中显著减少。在菌种水平上,Mushtaq等[15]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丁酸盐细菌F.prausnitzii(普氏粪杆菌)、R.inulinivorans、A.hadrus在高血压病3级患者肠道中显著减少。普氏粪杆菌是人类肠道中最常见的细菌之一,在健康个体肠道菌群中占比超10%,也是主要的产丁酸盐细菌之一,具有抗炎等益生作用[15]。在揭示门、科、属、种等生物分类水平上高血压人群肠道菌群结构显著变化这一现象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就特定菌群丰度与血压变化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Adnan等[26]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乳酸细菌Lactobacillus(乳杆菌属)与收缩压显著正相关,产乙酸盐细菌Holdemania(霍尔德曼氏菌属)、Coprobacillus(粪芽孢菌属)与收缩压显著负相关,产丁酸盐细菌Clostridiaceae与收缩压显著负相关。Dan[13]、Kim等[27]也分别在研究中得到了类似结论。
1.1.3 分子水平改变如前述,高血压相关肠道菌群失调的特征是特定细菌群落及其相应代谢物的失衡,具体表现为产乳酸细菌增加和产乙酸盐、丁酸盐细菌减少,有学者尝试进一步在分子水平验证这种特征的存在。Kim等[27]测定了高血压患者粪便样本中产丁酸盐相关酶(乙酸-辅酶a转移酶、丁酸盐激酶)水平,结果显示与正常血压对照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高血压患者血浆丁酸盐浓度显著降低。Huart等[29]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高血压患者粪便样本中的短链脂肪酸水平与正常血压对照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1.2 肠道生理结构及功能改变与前述肠道菌群失调相对应的是,SHR大鼠小肠纤维化面积增加、肌层增厚、杯状细胞数量减少、小肠绒毛缩短,小肠和近端结肠肠壁弹性度下降、硬度增加,肠道上皮屏障完整性下降、通透性增加,小肠和近端结肠紧密连接蛋白,包括Ocln、Tjp1、Cldn4水平降低[12]。在AngⅡ诱导高血压大鼠中同样观察到肠道通透性增加和紧密连接蛋白减少,同时基本复现了上述肠道病理改变[12]。Yang等[10]的研究也表明,AngⅡ诱导高血压大鼠结肠黏膜扣带蛋白减少,结肠黏膜扣带蛋白同样是一种紧密连接蛋白,其水平的降低与肠道屏障功能障碍有关,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可导致肠道炎症增加。Santisteban等[12]在SHR大鼠肠道固有层中还观察到Th17细胞显著增加,表明高血压个体肠道炎症增加,同时SHR大鼠肠道血流灌注减低。此外,在AngⅡ诱导高血压C57Bl6小鼠肠道中观察到丁酸盐的膜转运蛋白(MCT4)减少,这可能与高血压实验动物模型肠道中产丁酸盐细菌减少的变化是相伴随和匹配的[3]。
高血压患者肠道上皮健康生物标志物包括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FABP)、脂多糖(LPS)和连蛋白(zonulin)水平显著增加,尤以作为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重要调节因子的连蛋白的增加最为显著[27]。
2 高血压早期识别、早期干预的肠道微生态学思路
高血压诊断主要根据诊室测量的血压值,简便易行,但诊断标准和手段简便易行的意义仅在于快速识别患病人群,而扭转高血压患病率及血压正常高值检出率的基本上升态势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血压值改变前准确地“提前诊断”,即识别个体日后进展为高血压的风险性以及基于“提前诊断”的进一步完善高血压一级预防策略。
2.1 早期识别目前公认的与高血压发病有关的因素包括不可变的遗传因素和可变的饮食、精神应激、吸烟等环境因素及体重、药物、胰岛素抵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等其他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态改变可能是其潜在的危险因素,对高血压具有预测价值。Li等[17]的研究显示,与正常血压对照组相比,高血压前期组(125 mmHg<收缩压≤139 mmHg和/或80 mmHg<舒张压≤89 mmHg,1 mmHg=0.133kPa)肠道菌群Shannon多样性显著降低,普氏菌肠型个体比例显著增加,进一步针对高血压前期组和高血压组的共丰度分析显示,两组肠道菌群结构相似。上述证据表明,高血压前期人群的肠道微生态特征与高血压人群更加相似而非正常血压人群,提示肠道微生态改变可能是高血压易患个体在血压值发生改变之前“提前诊断”的良好预测变量。高血压风险预测模型对于识别具有高血压进展风险的人群有重要价值,该群体可能从及早的干预措施中获益。Echouffo等[30]选取了15种不同的高血压风险预测模型进行研究,年龄、性别、体质指数、糖尿病状况、吸烟、体育活动状况和家族史等是这些模型中最常见的预测变量。研究表明所有纳入模型的c统计量均在0.70~0.80之间,表明这些模型具有较好的鉴别能力。而Yan等[14]以高血压患者和正常血压对照组人群间差异菌群为鉴别标志建立的高血压识别随机森林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95%CI:0.73~0.82)。Li等[17]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鉴别标志从单纯差异菌群扩展至联合差异代谢产物时,模型识别高血压前期及高血压人群的能效显著提升,AUC可达0.91(95%CI:0.75~1.00)。以肠道微生态改变为预测变量的模型与Echouffo等综述的基于人群表型的各模型的预测能力几乎处于同一水平,表明肠道微生态改变在识别和预测个体日后进展为高血压的风险性方面显示出不错的潜力。此外,Kim等[27]还通过对肠道微生物数据和血液中的肠道来源健康标志物的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收缩压预测模型,预测因子包括肠道产丁酸盐细菌丰度及与收缩压具有最强正相关性的血浆连蛋白浓度,该模型的R2为0.554,利用该模型计算的收缩压值与实测值具有不错的拟合度。
2.2 早期干预目前高血压一级预防主要针对饮食、精神应激、吸烟、体重、药物、胰岛素抵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等可变危险因素,预防的主要内容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控制体重等。其中补充肠道微生态学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高血压患病率及改善治疗控制率。肠道微生态学的干预措施主要为微生态制剂(包括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元),此外还有膳食结构调整、粪菌移植等。近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上述干预措施在控制血压、恢复高血压患者肠道微生态、改善高血压靶器官损害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27,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