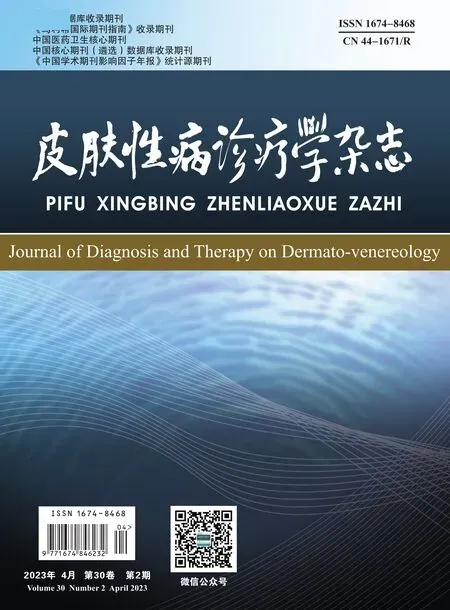瘢痕疙瘩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贾坤朋, 周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皮肤科,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瘢痕疙瘩是皮肤创伤或炎症后,在修复过程中发生的瘢痕异常增生,其特点是超出原伤口范围侵犯正常皮肤[1],常见于耳垂、前胸及肩背部等部位,可持续很长时间,难以自行消退,在有色人种中较易发病。瘢痕疙瘩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医学问题,传统治疗方法效果不理想,且都有很高的复发率,给患者身心带来巨大负担[2]。目前关于瘢痕疙瘩的发病机制尚有很多争议,大量研究表明在瘢痕疙瘩发生中,炎症反应、机械力及表观遗传修饰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进一步揭示瘢痕疙瘩发生的相关病理生理机制,本文就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炎症反应在瘢痕疙瘩中的作用
皮肤遭受破坏后,伤口愈合经历五个阶段:止血、炎症、增殖、再上皮化和重塑[3]。止血阶段,出现血小板堵塞和血栓形成等一系列反应。受损组织与激活的血小板一起,通过招募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引起炎症反应。当炎症消退后,新的血管和结缔组织出现,标志着增殖阶段的开始,此时,伤口区域也因伤口收缩而收缩。增殖阶段,角质形成细胞迁移驱动再上皮化。之后,新生血管消退、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重建,形成组织化的胶原纤维,完成重塑[4]。
然而,炎症反应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募集免疫和修复细胞启动炎症反应、促进创伤愈合,另一方面导致成纤维细胞(fibroblast,Fb)过度增殖、胶原蛋白等细胞外基质异常沉积[5],引起伤口异常愈合。
1.1 炎症细胞
典型伤口愈合过程的炎症阶段,免疫细胞主要与阻止病原微生物的入侵有关。免疫细胞失调情况下,伤口愈合过程改变,导致瘢痕形成。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淋巴细胞等炎症细胞均被报道参与了瘢痕的发展[4]。
1.1.1 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是最早到达受伤地点的白细胞,也是防止微生物扩散的关键细胞,不仅可以在伤口愈合的炎症阶段发挥作用,也可以持续存在,导致炎症阶段的延长[6]。一般情况下,当中性粒细胞持续浸润24 h后,逐渐凋亡,并被巨噬细胞吞噬清除,或者反向迁移离开创面[3]。若中性粒细胞凋亡或在去除其凋亡残余时发生障碍,可导致慢性炎症[6]。中性粒细胞的持续存在可能是瘢痕疙瘩慢性炎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其在瘢痕疙瘩中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行深入的探讨。
1.1.2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是损伤后组织重塑的主要参与者,主要分为M1型和M2型[7]。目前认为,在炎症阶段,M1型大多存在于伤口周围的组织中,它们会分泌大量促炎细胞因子,具有促炎和抗菌作用;相反,在增殖、再上皮化和重塑阶段的后期,伤口周围的组织主要包含M2型,它们具有抗炎作用,并参与ECM的合成,促进血管生成和胶原蛋白沉积[4]。巨噬细胞在创面的促炎与抗炎中表现出相反的作用,其具体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此外,不同细胞因子和创面微环境可促进巨噬细胞向 M1型或 M2型分化同时两种巨噬细胞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分化。在创伤后期,通过调节巨噬细胞的活动,在不影响创面愈合的同时调节慢性炎症反应,有望进一步改善瘢痕增生情况[8]。
1.1.3 肥大细胞 研究发现瘢痕疙瘩中肥大细胞数量明显增加、功能明显提升,通过释放组胺,分泌类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等促进皮肤纤维化[9],肥大细胞的数量和激活状态与瘢痕的程度呈正相关。为解释这些机制,Komi等[10]进行了共培养实验,证明肥大细胞可以通过释放IL-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刺激成纤维细胞增殖,导致Ⅰ型胶原蛋白的合成增加。这种胶原蛋白表达上调的效果可以通过阻断肥大细胞中的PI-3K/AkT信号通路而被取消。因此,肥大细胞和异常瘢痕形成之间存在着联系。
1.1.4 T淋巴细胞 由于T细胞亚群的多样性,目前研究认为T细胞在瘢痕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复杂,其中以辅助性T细胞(Th)和调节性T细胞(Treg)更为重要[11]。 Th 具有促炎作用,可分泌多种细胞因子;根据细胞因子的不同,将Th介导的炎症反应分为Th1型和Th2型。
研究认为,Th1细胞通过分泌IFN-γ,能够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下调Ⅰ、Ⅲ型胶原蛋白基因的表达,从而减轻组织纤维化Th2细胞分泌的IL-4和IL-13可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和代谢,导致网状纤维蛋白的沉积[12]。 众所周知,Treg能够抑制其他效应T细胞并维持外周的免疫耐受。此外,Treg 还可通过分泌 IL-10、PGE2 等,对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和浸润产生直接抑制,进而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来抑制纤维化[13]。如果Th过度增殖或Treg功能受损,将会导致这两种细胞之间的失衡,进而引起局部过度炎症反应[8]。
1.2 炎症因子
皮肤创伤后,组织细胞分泌多种炎症因子参与组织修复。在修复的任何阶段,发挥作用的炎症因子失衡都可能引起异常瘢痕的产生[4]。其中常见引起瘢痕疙瘩的主要炎症因子有白介素-6(IL-6)、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
1.2.1 白介素-6(IL-6) 当组织发生损伤时,IL-6可以通过与IL-6受体和跨膜蛋白Gp130结合形成复合物,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凋亡及发挥促炎作用[14]。此外,IL-6也可与可溶性白细胞介素-6受体(sIL-6R)通过IL-6反式信号传导来激活该信号通路并发生一系列级联反应[15]。Azza等[16]通过对瘢痕疙瘩患者和对照组的血清IL-6表达水平进行对比,发现患者血清IL-6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因此,通过干预IL-6及其相关受体有望成为治疗瘢痕疙瘩的有效措施。
1.2.2 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TGF-β在哺乳动物中发现了3种亚型,分別为TGF-β1、β2、β3。这些亚型几乎存在于所有正常组织中,通过Ⅰ、Ⅱ、Ⅲ型特异表面受体,以自分泌、旁分泌和内分泌机制发挥调节作用[17]。其中TGF-β1和TGF-β2被认为是促纤维化因子,其中TGF-β1所占比例最高(>90%),活性最强,生物体内TGF-β1激活Smad依赖和非依赖途径产生其生物学效应[17]。Hu等[18]研究发现,瘢痕疙瘩中诱导早期基因1表达明显升高,使其负反馈调节因子Smad7表达降低,TGF-β/Smad信号通路激活,导致细胞增殖活性、胶原分泌功能等增强。该通路被认为与瘢痕疙瘩的形成关系最为密切[1]。TGF-β3的特点是调节表皮和真皮细胞的运动,促进伤口愈合而不形成纤维化的瘢痕。重组人TGF-β3(计划商标为Juvista)在Ⅰ/Ⅱ期临床试验中显示了成功的结果,但在Ⅲ期临床试验中失败[19]。
1.2.3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TNF-α可能在瘢痕疙瘩的形成和增殖中起重要作用,因为它与各种纤维性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20]。TNF-α通过与其跨膜受体结合后,又与TNF受体1型相关死亡结构域蛋白(TRADD)结合,进而表现出强大的促炎、促凋亡等生物学效应[20]。
卿勇等[21]研究发现,TNF-α在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中具有双重作用。低浓度TNF-α通过活化NF-κB通路、JNK/SAPK通路、p38/MAPK通路,促进细胞增殖;高浓度TNF-α明显增强Caspase通路活化,且降低上述三条通路的活化,其促增殖作用消失。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中,TNF-α轻微活化NF-κB通路、JNK/SAPK通路,具有较弱的促增殖作用。TNF-α单抗Infliximab注射裸鼠荷瘤瘢痕疙瘩后,与未使用药物治疗的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瘢痕疙瘩中Ⅰ、Ⅲ型胶原蛋白的表达明显降低,Ki67阳性率减少,成纤维细胞凋亡增加。因此,通过调控TNF-α及其相关受体可能成为治疗瘢痕疙瘩的有效靶点。
1.2.4 其他炎症因子 研究发现IL-10可通过使P-Smad2/3表达下调, Smad-7表达上调,导致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生长受到明显抑制,Ⅰ型和Ⅱ型胶原显著减少[22]。IL-4和IL-13可以激活巨噬细胞,并产生一系列生长因子不同程度地参与创面愈合与瘢痕形成。此外, IL-17、 IL-37、外源性干扰素-γ(IFN-γ)等也不同程度的参与瘢痕疙瘩的形成[23-25]。
2 机械力
皮肤在人的一生中不断与各种机械力打交道,机械力的影响在不同解剖位置上是不同的。机械刺激影响伤口愈合进程,并导致身体特定区域过度瘢痕形成的易感性增加,机械传感器将机械信号传递给与ECM结合的细胞,并触发进一步的信号级联反应[26]。
2.1 整合素信号通路
整合素是一种重要的机械感受器,是细胞表面的跨膜受体分子,连接了细胞质与细胞外基质,是生物化学和机械信号转导的双向通道。整合素包含α亚基和β亚基[27]。当机械力作用于ECM后,激活细胞表面的整合素受体并使其聚集,与ECM特异性配体结合,整合素的β亚基在胞质内侧的尾部与肌动蛋白结合,形成黏着斑。整合素激活黏着斑激酶使其发生自身磷酸化,进而激活黏着斑处其他成分。黏着斑成熟后生成大量应力纤维,应力纤维将力学信号传入细胞内,使细胞对外界机械刺激作出反应,调节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分化及胶原收缩等[28]。因此,通过对整合素信号通路的调节可能成为治疗瘢痕疙瘩的潜在靶点。
2.2 TGF-β/Smad信号通路
TGF-β是促纤维化的关键可溶性因子,TGF-β1诱导肌成纤维细胞激活。被激活的肌成纤维细胞分泌TGF-β,形成正反馈回路,促使Fb增殖分化,ECM过度沉积[29]。在细胞中合成与分泌的TGF-β是无活性的,活化后才能表现出生物学活性。机械应力对TGF-β的活化有重要作用[30]。在处于稳态时,TGF-β在ECM中以潜在复合体(LLC)的形式处于潜伏状态,包括潜伏相关性多肽和潜伏TGF-β结合蛋白。机械应力使细胞外基质纤维拉伸,进而促进TGF-β结合蛋白与整合素结合,引起TGF-β从LLC释放且TGF-β的激活也依赖于细胞黏附和整合素的作用[30]。
机械应力作用于细胞后,可通过LINC复合体发挥对Smad蛋白的调节作用。LINC复合体定位在核膜上,由Nesprin和SUN两组结构蛋白构成,是机械应力在细胞核膜上进行信号传输的重要通道。在TGF-β/Smad信号通路中,TGF-β首先与Ⅱ型跨膜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受体结合,接着通过磷酸化Ⅰ型受体磷酸化并激活Smads及其下游分子通路,调节靶基因转录,从而影响瘢痕疙瘩形成[27]。此外,TGF-β/Smad信号通路还可与其他信号通路如通过smad4与Wnt/β-catenin相互作用,参与瘢痕疙瘩的形成与发展。因此,通过调控该信号通路有望起到防治瘢痕疙瘩的作用。
2.3 Rho-GTP酶
Rho-GTP酶是细胞内的蛋白质,在整合素和细胞骨架之间起中介作用,通过调节细胞张力、细胞内力、运动性和粘附性对机械力做出反应[26]。Rho-GTP酶被黏着斑中整合素的张力以及可溶性因素(如生长因子)所激活。RhoA、Rac1和Cdc42通过Rho激酶(ROCK)的刺激协调肌球蛋白Ⅱ的活性产生收缩力并促进肌动蛋白丝的组装,增加伤口收缩和纤维化的情况。Bond等[31]使用Fasudil,一种Rho相关激酶抑制剂,来阻碍大鼠模型中成纤维细胞的收缩性并防止瘢痕的过度形成。与对照组相比,使用Fasudil的患者的伤口挛缩降低。 因此,未来对Rho信号通路抑制剂的研究可能成为防止伤口纤维化和挛缩的一种有效选择。
2.4 YAP/TAZ
Yes-相关蛋白(YAP)和具有PDZ结合基序的转录辅助因子(TAZ)是两个主要的下游调节器,作为机械转换器对细胞骨架的硬度和排列作出反应。当细胞不受外界机械力影响时,YAP/TAZ在细胞质内持续处于非活性状态,该状态受上游机械力的调节[26]。机械力通过整合素细胞质结构域的变构调节传入细胞内。整合素细胞质尾部的构象变化触发信号转导通路如RhoA- ROCK信号通路,该通路由一些蛋白组成,包括纤维肌动蛋白。肌动蛋白丝上产生的张力触发了YAP向细胞核的转移,在细胞核中诱导En1谱系阴性成纤维细胞向En1谱系阳性成纤维细胞转变。然后En1谱系阳性成纤维细胞启动纤维化反应(包括α-平滑肌肌动蛋白的表达),从而产生更多的牵引力和更多的胶原沉积。这个过程是细胞质和细胞外基质之间双向互动的一个正反馈循环。Mascharak等利用小鼠模型表明,这种正反馈循环驱动着纤维化反应。研究者通过使用verteporfin在遗传学和药理学上阻断了YAP信号传导,并消除了纤维化反应,但verteporfin能否在人类身上治疗成功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5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
Wnt信号激活了许多细胞内的转导途径以控制细胞的命运。由Wnt激活的两条主要途径是经典Wnt途径(cWnt)或Wnt/β-catenin依赖途径和非经典(ncWnt)或β-catenin非依赖途径[33]。Wnt/β-catenin信号传导已被证实在皮肤的自我更新能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典Wnt途径对通过其表面受体将细胞外机械信号传入细胞内至关重要[26]。β-catenin是上皮细胞中粘附连结的结构成分,调节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机械力的作用下,附着在各自卷曲受体上的Wnt分子更加容易将β-catenin分子释放到细胞质中,在细胞质中它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其他信号传导途径,并可以前往细胞核,发挥上游调节器的作用[26]。
与正常组织相比,纤维化组织细胞核中的β-catenin基因活性增加诱导真皮成纤维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产生过多的ECM,从而导致皮肤纤维化[33-34]。此外,由于β-catenin诱导TGF-β在人类皮肤中诱导成纤维细胞活动,Wnt/β-catenin途径亦与TGF-β信号传导有关。Wnt/β-catenin信号通过对机械信号的上下调控,改变伤口愈合和瘢痕反应[26]。因此,对Wnt/β-catenin途径的研究可能为瘢痕疙瘩的防治提供一种新思路。
3 其他
3.1 瘢痕疙瘩表观遗传修饰
多项研究表明在瘢痕疙瘩中存在表观遗传失调,主要有 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 RNA(non-coding RNA,ncRNAs),它们在瘢痕疙瘩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影响瘢痕疙瘩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验证[35]。
3.2 脂联素
许多研究已经阐明脂联素对炎症和组织纤维化有负面影响,脂联素可能通过激活AMPK信号通路在抑制瘢痕疙瘩纤维化和炎症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脂联素可能成为瘢痕疙瘩发病机制的治疗靶点[36]。
4 总结与展望
瘢痕疙瘩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T淋巴细胞等炎症细胞,白介素-6(IL-6)、TGF-β、TNF-α等炎症因子,整合素信号通路、TGF-β/Smad信号通路、Rho-GTP酶、YAP/TAZ、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等机械力因素以及表观遗传修饰、脂联素均与瘢痕疙瘩的形成有关,对上述因素的干预有望成为治疗瘢痕疙瘩的新思路。本文对上述因素作用于瘢痕疙瘩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但未能阐明这些因素引起的一系列信号转导通路变化对瘢痕疙瘩进展的影响以及信号转导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为今后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