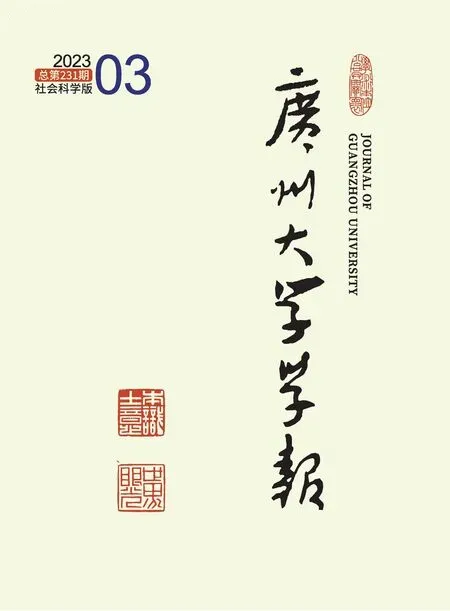探寻内隐集体记忆的隐藏力量①
阿斯特莉特·埃尔 著,田源辉 译
(1.法兰克福大学 现代语言学院,德国 法兰克福 60323;2.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重庆 400031)
一、不同于一般的角度:从不被纪念到内隐记忆
“把那些不同寻常的角度统统集中起来!”这既是韦雷德·维尼茨基·塞鲁西(Vered Vinitzky-Seroussi)[1]对记忆研究提出的明确建议,同时也是本文的出发点。“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的一般角度所涉及到的,通常是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是外显的,其参与者是有意识的,大多是官方的,且具有身份建构的作用。这就涉及到记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内的内容显而易见,而且已被多次讨论。不过这一范畴仍远未总结出记忆、社会环境和媒介传播间可能的全部关联。将记忆研究仅仅视为与纪念相关的研究使人多少想到——正如迈克尔·舒德森曾提到过的——一个仅在路灯的光束下寻找车钥匙的醉汉的例子。[2]
对于内隐记忆那些未被路灯照射的领域,传播学具有特殊的接入口。传播学的载体严格意义上并不涉及承载记忆的媒介,而是关于所谓的“当下提供者”(purveyors of the present)。[3]因此,舒德森在其有关将新闻媒体作为集体记忆媒介的思考中强调说:“并不是所有被社会记住的东西,都是通过或者联系有意识或有目的的纪念活动来完成的。相反,过往经常被掺杂到当下中,这一过程并不以纪念为目的。”[4]舒德森在此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即一方面是特定形式的“纪念性记忆”(commemorative memory),这种记忆往往是外显的,具有“集体自传的”(kollektiv-autobiographisch)性质并与身份建构相关;另一方面是被纳入“非纪念性记忆”(non-commemorative memory)的多种其他形式的集体记忆。
对于跨学科记忆研究而言,涉及到“非纪念性记忆”的形式,要注意到的是两个维度。首先是社会语境下的一种“外显”(explizit)记忆。从记忆参与者的角度看,这些外显记忆是一种社会语境中被符号化了的记忆,它们和时间或者和过去并不相关,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和身份直接相关。②简言之,记忆研究能够而且也应当运用其丰富的“跨学科工具箱”(interdisziplinäre Toolbox)来处理知识文化及其历史。其次,记忆研究仍尚未真正开始对内隐记忆具有的张力展开研究。这种张力虽往往是隐性的,却又十分有用。这也正是本文的焦点所在。因此在下文中将论及媒介传播在无意识的记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什么是内隐记忆?从心理学的视角说起
在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下,内隐记忆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个体无意识的记忆过程。认知心理学从不同的记忆系统出发,主张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明显不同。外显记忆使得有意识地(积极而伴有意图地)唤醒记忆成为可能,自托尔文(Tulving)[5]开始,外显记忆进一步被区分为符号记忆(“知道某事”)(wissen dass)和情景记忆。与此相反,从比如系鞋带、骑自行车这样的程序记忆(“知道如何”)(wissen wie),到感性层面和理性层面的铺垫效果,这些无意识的记忆形式被纳入到内隐记忆的范畴之中。纵览如今广泛细分的研究方向,内隐记忆所涉及的总是过去经验对当下想法、感觉和行为无意识施加的影响。③
铺垫(Priming)是心理学在实验室条件下使内隐记忆可被观察的一种方法。这一实验给受试者展示某些文字或图像,这些预先被展示的内容使受试者更容易记起之后类似的信息。且在这一过程中,受试者自己并未意识到预先展示的内容和其后所记起的内容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奇(John A. Bargh)[6]著名的“佛罗里达实验”中,受试者会被展示和年老相关的词汇,比如“健忘的”“秃顶”或者干脆就是“佛罗里达”,因为佛罗里达正好是许多美国退休者的定居地。他在这些接受测试的青年学生穿过房间的过程中发现,和预先被展示了年轻相关词汇的对照组受试者相比,前者比对照组受试者的行动要更缓慢一些。
对于跨学科记忆研究来说,“单纯曝光效果”(mere exposure effects)和“真相错觉效果”(illusory truth effect)④的铺垫效果尤其重要。就是说,不断重复听到的和看到的,因熟悉而显得可信,甚至会直接被认为是真实的。对此,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解释道:“反复重复是使人相信不实说法的可靠方式,因为‘熟悉’不容易和‘真实’区分开来。”铺垫效果也能通过对性别和种族的刻板印象而导致一种“精神强迫”(mentaler Kontamination)⑤或无意识的剽窃行为⑥。
造成上述这些效应的原因之一是,内隐记忆总是伴随着相关来源的缺失。因为信息的来源及来源的状况(亲身经历还是道听途说,可靠还是不可靠,虚构还是事实),看起来在被无意图唤醒的记忆中似乎并不起作用,而发挥作用的是那些看似熟悉、舒适、无拘束和真实的回忆内容。甚至自己所经历的过去,也能够被附上主观的、“间插性的”(episodische)特点。⑦
卡尼曼在其《快思慢想》(SchnellesDenken,LangsamesDenken)中强调,内隐记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一台能自动“快思”的机器。在心理学“双系统模式”(double process model)下,人类处理信息的过程被区分为被控制的(即有意识的)和自动发生的(即无意识的,无须认知参与的)。对巴奇来说,自动认知的过程具有四个特点:“缺乏意识、缺乏意图、缺乏控制和高效率(不依赖于认知资源)(nonreliance on cognitive resources)。”[7]
高效率是内隐记忆的核心特征,因为这些内隐记忆是无意识、无意图和不受控的。它虽有效而且快速,但对记忆者来说却是完全被忽视了的。难怪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Schacter)在《我们就是记忆》(WirsindErinnerung)一书中会有“被遗忘的内隐记忆的世界”(verborgene Welt des impliziten Gedächtnisses)这一说法。考虑到本文主要涉及无意识的集体记忆,且讨论的重点是其对未来的推动和塑造作用,因此就有必要在下文提到“内隐的集体记忆所具有的被隐藏力量”(verborgene Kraft impliziter kollektiver Erinnerung)。
三、隐藏力量:内隐记忆作为集体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将内隐记忆视为一种集体现象呢?对此,首先得再次明确的是,“记忆”(Erinnern)和“遗忘”(Vergessen)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不再是单纯地从个体心理层面来观察这些过程(普遍意义上记忆的作用),而是将其视为生物、精神、社会、文化以及物质元素的聚合物时,那么记忆在这种扩展形式下被视为一种“记忆生态学”(Ökologie des Gedächtnisses)[我(指作者)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明晰并保持哈布瓦赫所提出的,奠定了记忆研究基础的“集体记忆”(kollektives Gedächtnis)的传统]。在这一范围中,又产生出各组成部分的“共生”(Sympoiesis)和“动态共构”(dynamische Ko-konstruktion)。
“集体记忆”(kollektives Erinnern)并不是说在所有个体的头脑中都有一致的再现,而更多是说社会群体在回顾过去的话语、媒介和行为时所使用的特定视角总是反复被激活,而且与其他主题充分结合在一起。正是如此,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和盖伊·贝纳(Guy Beiner)才有以下论断:“集体遗忘”(kollektives Vergessen)并不是说过去的某个事件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而仅仅意味着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缺乏对此事件的记忆活动。[8]比如回避某些事件,使其被禁声,避免或禁止公众对其进行回忆,从而使得这些事件似乎难以被激活。只不过这些事件仍继续被保留在家庭或地方的记忆中,或者在科学话语中被符号化(类似于西班牙大流感中的情况)。⑧集体记忆的逻辑所隐含的——用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的话——便是“在不同的社群、团体、个人中记忆和忘却的分布并不均匀”。[9]
此逻辑亦适用于“内隐的集体记忆”(implizite kollektive Erinnerung)。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意识自主发生之事,诸如刻板的文化印象、未经加工的过去的事件、狂热的政权以及无意识的宏大叙事等,在某些观察者的眼里却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确实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却又很少被关注到,或者只有当内隐的集体记忆侵入到意识中才被部分人所注意到,比如刚接触到某一文化的“新人”(Neuankömmlinge)或者科学研究者,以及批评性的观察机构。此外,某些使用框架理论的记者和引经据典的政治家等记忆参与者,也能够有意识地使用内隐的集体记忆。这也正好说明,尤其是评论媒体、艺术以及文学,有能力使内隐记忆的能量展现在人们面前(例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⑨
从实用性角度考虑,内隐记忆因其所具有的功能性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在社会群体中,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不仅是集体记忆发挥功能和作用的方式,而且也是记忆系统不可拆分的组成部分(存在于不同脑区域中的这一系统具有的不可拆分性仍有待讨论)。⑩这是说特定的媒介可以既是官方性的外显记忆的载体,同时又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存在于后殖民社会当中,和殖民主义有关的纪念物,或者有关种族的概念都是很好的有关内隐的集体记忆形式的例子。只要还存在例如参加“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这类活动的活跃人士,那些内隐形式所具有的、能够在无意识中对记忆起稳定作用的力量就仍然能得以再现。
内隐的集体记忆用以形容那些在生物层面的、精神上的、社会文化以及物质方面的事实共同影响下而产生出的记忆的形式。它们对大部分的记忆参与者来说是既无意图也是无意识的。在内隐的集体记忆中,最为有效的部分涉及的是那些已经固定下来的纪念模式,例如类似于图示、叙事、价值观、刻板印象、世界模型或者特定的行为方式。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些模式常常被无意识但又活跃地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播和继承。在此过程中,广泛意义上的媒介具有核心的作用:内隐的集体记忆可以通过姿势、表情这类“原初的媒介”(Primärmedien)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媒介,或者通过模拟和电子化媒介来传播。
人类学家詹姆斯·维特奇(James Wertsch)在其著作《国家如何记忆》(HowNationsRemember)中所研究的国家叙事,是关于内隐记忆所蕴含力量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在与认知心理学家跨学科的合作下,他讨论了俄罗斯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在有关二战的国家叙事上,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在一项实验中,人们从11个国家各找出了100多名的测试者,询问他们认为哪10件事是二战中最重要的。[10]实验结果使人大吃一惊,因为甚至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受试者,对于二战持有的却是一个美国视角下的“记忆滤镜”。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件是珍珠港事件、诺曼底登陆(D-Day)和大屠杀(Holocaust)。而在俄罗斯,实验结果却截然不同:异常高比例的俄罗斯受试者都提到以下事件: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莫斯科战役(1941年冬至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冬至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1944年6月)、第二战线的开辟(即D-Day)以及柏林战役(1945年春)。
那么这一差异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又是什么将这些记忆中的事件整合在一起的呢?维特奇对此论证道:造成这一差异的基础因素是一种将俄罗斯描述为反复遭受外敌入侵的“受害者话语”(Opfererzählung)。这种话语实际上是一种大部分受试者都未意识到的叙事样本。但它却引导了人们对记忆中历史事件的选择,也因此提前形塑了人们对未来事件的看法。维特奇还指出,对普京而言,这种由国家建构的受害者话语还是快速而有效地控制认知的工具:“这种叙事已然沦为一种工具,而且几乎可以说这一工具已为普京所用,成为完成他意图的传声筒。”此外,维特奇的书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冲突的数月前出版,这其实很好地说明了,记忆研究有益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内隐的记忆素材是如何被政治策略有目的地利用的。
那么不可见的历史叙事又是以何种方式在社会群体中得以流传的呢?在俄罗斯,维特奇看到了一种国家意志:一种贯穿所有社会领域和传播媒体(家庭教育、教科书、新闻)的模板叙事。而且跨国的历史叙事传播同样受到内隐的集体记忆影响:在美国、意大利和德国,大部分人对于他们为何选择回忆珍珠港事件,而非库尔斯克战役,很可能都没有进行过有意识的思考。不过至少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是世界媒体对美国历史叙事的传播。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2001年迈克贝导演的好莱坞电影《珍珠港》。而内隐记忆作为“起源记忆缺失”(sozialen Quellenamnesie)的结果,对历史观产生的巨大影响,却常常被低估了。
同样,大部分受试者对自身历史事件选择所包含的片段、叙事、观点都没有意识。叙事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曾指出:“叙事并不是可以观察过去事实的透明全景窗,而更多的像是给复杂现实以特定形式的‘饼干模具’。”在此基础上,维特奇强调说:“叙事工具常常下意识地发挥作用,它给我们一个印象,仿佛我们能直接看到事实一样。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注意到的是,我们在过去或者在当下成功使用过的这些直接能接触到的、已经经过塑造的形式,促使我们在未来更有可能接着再次使用这些形式。这其实便是内隐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动力。”
四、社会学和传播学视角:框架和铺垫
在探寻内隐的集体记忆所蕴藏的力量时,研究者引入了有关传播和叙事的知识。社会学领域中有关框架(Framing)和铺垫(Priming)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与铺垫和心理学研究发生勾连相比,框架理论自身有着社会学传统。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接着到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再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1]如今框架(Rahmen)和框架构建(Rahmung)这些比喻被更广泛地使用:在传播学上有“媒体框架”(Medien-Frames),在政治哲学上有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战争框架”(frames of war),而在记忆研究中,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中的“社会框架”(cadres sociaux)的论断,直至今日依然是核心概念。
对于高夫曼这位社会框架分析理论的奠基人而言,框架是指“对于经验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12]框架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模式:“观察者主动将他参考的框架应用到其直接生活的世界中。”[12]通过构建框架来制造现实是一个主动的、但不一定伴有意识的过程。相反,其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恰恰取决于这一过程是自动进行的。
为了解释电视新闻报道能“生产”现实的力量,在媒体社会学中也参考过高夫曼的观点。对此,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解释说“是媒体框架使世界得以超越直接经验且看起来又十分自然”。[13]媒体框架指那些“筛选、强调和展示的原则”,它由更小的有关于存在什么、发生了什么以及什么重要的“隐性理论”(tacit theories)组成。“隐性”理论指框架是以内隐的、暗示性的知识为基础的。
这些角度始终和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cadres sociaux)概念相切合。通过“社会主力”(sozialen Kader),也就是通过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获得了所谓的“精神框架”(mentale ,,Rahmen“)。这些框架使我们有可能分享到集体记忆,并以此铸造我们的记忆,引导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处理新的经验。社会框架的概念对哈布瓦赫而言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关于这一概念他写了一本完整的书(《记忆的社会思维框架》)。此外,哈布瓦赫还认为精神框架的力量也处于隐藏状态中:“社会的思潮通常如同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是不可见的。在平常生活中,人们仅仅是在同其对抗时,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虽然社会学家通常聚焦于记忆的社会层面,但哈布瓦赫却以个例说明了媒介记忆研究一再强调的东西。这个例子所涉及的,是他一段著名的有关虚构在伦敦散步的趣闻轶事。社会框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介框架”(cadres médiaux)来传播的。这不仅对记忆而言是关键的,而且它具有很强的预加工能力:在哈布瓦赫列举的趣事中,媒介就是如同建筑师朋友曾说过的话或者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这些影响了他当时有关伦敦市貌的经验。[14]
就传播学而言,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M. Entman)大力推广并普及了框架的概念,在此过程中,他也借鉴了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根据恩特曼的观点,对于内容的筛选以及对某些内容保持沉默也属于框架的重要运行机制。沉默(Salienz)这一概念概括了可接受性、重要性和可回忆性:“这也就是说,要让某一信息对受众而言更引人注目,更显得重要或更有纪念价值。”[15]传播学的框架概念使人们关注到有意识、有策略性地利用内隐的集体记忆的可能性。
框架和铺垫是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它们可以使隐藏现象显现出来,不过二者在此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却不相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概念都和比喻相关。约翰·多雷(John Sonnett)发现,框架以空间和视觉的比喻为基础,而铺垫则是以时间和顺序的比喻为基础:只有当某个信息先出现后,才会起到特定的作用。[16]因此和框架相关的研究更面向于“如何交流”(,,Wie“ der Kommunikation)的问题,相反,关于铺垫的研究则更关注“交流什么”(,,Was“ der Kommunikation) 的问题。
铺垫更多是一种无意识下已有内容的自动激活,框架则更多是一种通过媒介塑造或者改变受众信念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关键的是对于“适用性”(applicability)和“易用性”(accessibility)的区分,这一观点由文森特·普赖斯(Vincent Price)和大卫·图克斯伯里(David Tewksbury)提出。[17]适用性更多是指某个框架的符号学作用(“如何?”)(Wie?),易用性则是指某个铺垫有时限的被激活的可能(“什么?”“何时?”)(Was? Wann?)。
五、“长时段”(Longue Durée)条件下媒介的(预)塑性
心理学和传播学中,关于框架和铺垫的研究之所以能和记忆研究结合起来,这和时间问题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当媒介的“预塑效应”[Effekte der (Vor-)Formung]能够长时间发挥作用时,这种效应才能影响集体记忆,并使之发生变化。而时间的稳定性,实际上也正是传播学感兴趣的范畴。克里斯蒂安·巴登(Christian Baden)和索菲莱·切勒(Sophie Lecheler)强调,只有框架能持续发挥作用,才变得对社会重要起来。因此产生了用以分析框架持续时间的理论模型。[18]
大部分认知心理学中关于框架和铺垫的实验都以分钟或者小时来计时。与此相反,传播学的研究则更关注框架经过长时间而变得稳定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称为一种“持续的适用性”(chronic accessibility)。对此“频繁的铺垫”(frequent priming)或者“重复的框架”(repetitive framing)都能有所贡献。[19]虽然在这一关联下,谢尔(Schemer)将框架效应能起作用的时间称之为“一定程度的半衰期”(eine gewisse Halbwertszeit),但在实践中,框架效应能持续发挥作用的时间,仅仅是10至20天。[20]
从记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听起来让人清醒,因为这里涉及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时间范围。为了弄清为什么某些媒介超过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其仍能发挥预塑形的作用(经过数代仍能起作用)。例如在数个世纪中,奥德赛或者出埃及记以及“圣母怜子”(Pietà)的叙事,和反犹主义的固有模板总显得是适用的。为了使这里所介绍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概念能长时间促进集体记忆的研究,必须将哪些元素联系起来呢?
首先,从荷马神话,到基督教圣像学,直到阴谋论这些例子都表明,这些“长期的铺垫和框架”(Langzeit-Primes und -Frames)总是由“多个媒介”(plurimedial)构成的。这些跨媒介的现象,超过所有已有媒介的界限,总是被再媒介化(以此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文化)。除了这些多媒介提供的动力外,那些使得内隐的集体记忆成为可能的框架,同时也具有社会层面的基础。然而认知心理学关于内隐记忆的研究集中于个体的记忆能力,并不关注框架如何构建,以及所构建的框架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对象这些问题。
内隐记忆通常是“长时段内”(longue durée)在复杂社会和媒介中被生成和稳定下来的。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这个能持续产生很强媒介塑形效应的文化领域又是如何被构建的呢?哪些类型的媒介是有权威性的?机构化、经典化、教育政策以及市场的哪些形式使得特定文化的铺垫和框架能够长期保持其适用性?这些问题指出了媒介文化史的方法论。此方法论在下文中将借助“记忆预媒介化”(mnemonischer Prämedialisierung)的张力来进行描述。
六、媒介文化史视角:“叛乱!”新闻学和预媒介化
当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将新闻学研究放到2008年记忆研究会议议程中,她的用词已经清楚表明,新闻学已经成为推动内隐的集体记忆的一种动力。关于记者,她写道:“作为当下的传播者,作为记忆的‘机构’,实际上因为其未固定下来的角色,他们倾向于同时展现显而易见的和被忽视的东西。”[3]新闻学这个“高度重要的记忆参与者”(hoch relevanter Erinnerungs-Akteur),看起来仿佛只能用内隐记忆的语汇来对其进行描述,即遗忘、无关紧要、难以言说。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新闻成了记忆的前提。[21]从18世纪开始新闻报道仍属于“前媒体”(erste Medien),历史事件被记录其中,提供了卡罗琳·基奇(Carolyn Kitch)所说的“历史的初稿”(the first draft of history)。[22]和作为明显属于储存媒介的编年史档案不同,新闻报道是无意识发挥储存效应的传播媒介(这大大早于出版文献和数字档案)。这种存储功能是一种内隐集体记忆的现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无意识的。
首先新闻报道是“历史被创造那一刻”(instant history making)的媒介,记录和传播是它最重要的运行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是指向现实的。不过偶尔当过去的新闻报道再次出现时,伴随而来的还有那时的框架。对于信息的筛选、强调以及遣词和叙事结构等框架,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依然还能察觉到。
比如英国对有关1857年到1858年间印度北部“叛乱”的报道就是这种情况。这场起义将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士兵、农民以及王室团结在一起,几乎让英国人丢失其殖民地。在对帝国中心公众的报道中,它被称作“印度叛乱”(这就是“叛乱的框架”)(Frame der ,,Meuterei“)。《伦敦时报》(TheLondonTimes)最早有关这场印度起义的新闻大多数是真正的或自称是目击者的报道,但这些新闻构建出一个十分片面的框架:起义被描述成一场针对英国合法殖民统治的密谋叛乱,参与这场叛乱的是一群忘恩负义又冷血残酷的宗教狂徒。这些报道中,不仅特别强调针对英国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而且还将其描述得特别野蛮。不过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暴行往往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虽然卡尔·马克思(Karl Max)早已经揭露出这些残暴的故事都是谎言,但英国早期媒体的框架还是进入了帝国的历史叙事中,分散到了英国19世纪的小说、戏剧、电影以及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后殖民历史书写中。
2005年,宝莱坞一部关于这次起义的电影《抗暴英雄》(MangalPandey:TheRising)引发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上面提到的框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每日邮报》(DailyMail)直接批评这部电影,称其为狂热的反英举动。而这恰恰是150多年来,用以形容抵抗英国殖民活动的标准话语。一次将19世纪的反叛活动改编为电影的尝试,如此再次成为了21世纪的一次新的反叛活动。再次媒介化的张力在此只能简略概括为:历史事件在新的媒介中重新转录时,总是伴随有旧媒介中的痕迹(Erll und Rigney)。因此,再媒介化也是更复杂且更具活力的多媒介形式的一部分。这种多媒介的形式是在众多记忆事件当中建立起来的。久而久之,再媒介化就会导致前媒介化:通过再媒介化稳定下来的框架会越来越完整,并且会黏附在新的经验上,直至最终将新的经验完全覆盖。之前提到的21世纪那场关于电影的争论就是这种情况。1919年的阿姆利则·马萨塞事件(Amritsar Massaker)或许也属于内置了叛乱话语的事件。相关调查委员会已经查明,在下令向非武装人员射击之前,负责的将领雷吉纳德·戴尔使用了“叛乱”“兵变”“1857”这类模板(汤普森将此称为“被遗传的想法”)。而这些模板对加利诺拉巴格公民举行的和平游行示威活动本不适用。通过回顾不难发现,19世纪新闻中的框架,直至150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当然,这些事情自身就是长达百年的前媒介化的事件。因为自18世纪开始,印度的农民起义就已经被英国人框架化为宗教狂热的叛乱。
在集体层面的“内隐”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知道。或许这个或者那个历史学家会有意做些隐喻,或许一些记者会有目的地在档案里找到过去的时报文章,或许甚至已经有些人意识到了被多媒介化了的记忆并且了解“叛乱模板”(Ausstechform Mutiny)的逻辑。不过更为普遍的情况还是,记忆文化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没有意识到有再媒介化的“链条”(Ketten)的存在[或者更好地说成“串联”(Kaskaden)]。因此用“狂热的”来描述反殖民的抵抗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合乎逻辑的。在此意义上看,内隐记忆又是“真实”的。这涉及在集体层面,长时段内被构建出的自动触发和“真相错觉效应”(Vertrautheitseffekte)。
新闻框架所具有的预媒介化作用仍未受到关注。新闻框架虽然持续发挥作用,但此过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仍是无意图和无意识的。在早期事件被媒体报道时,对特定的用于解释的模式已经出现了“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23]而这种不易被看见却又长期有效的影响力,恰恰是一种“社会失忆症”的基础。和被泽利泽称作“命名新闻”(naming journalism)[3]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内隐的集体记忆的形式。对于媒介文化史视角下的记忆研究来说,框架理论和铺垫效应至始至终都是重要的概念。它们只能在复杂的记忆生态中才能被翻译:“再媒介化”(Remedialisierung)(作为长时段内多媒介中重复的框架形式)和“预媒介化”(Prämedialisierung)(作为长时段内媒介铺垫的形式)。记忆的预媒介化,一方面是说在集体认知的层面,框架(包括刻板印象或模板叙事)的快速运用和调整;另一方面是说此过程自身也能作为媒介被观察,即当特定的框架在流变到新主题的过程中被辨认出来时,将其作为一种“媒介效应”(medialer Effekt)来观察。
七、记忆研究中的视角
那探寻内隐的集体记忆中所潜藏的力量对于跨学科的记忆研究来说有什么影响呢?内隐记忆当然仍然是不可见的,虽然它能影响人们的想法和行为。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一作用并不引人关注。此外,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内隐记忆,其差异有时是巨大的,但是这些巨大的差异同样也并不引人关注。研究内隐记忆就是为了让这些不被关注的东西能够从一束路灯中走出来最终被看见。与外显记忆相比,内隐记忆会更多地被预先塑形,并且内隐记忆具有一种向前的推动力,因而它更多指向未来。心理学家在有关铺垫的研究中同样也会强调过去经验对之后行为的影响,并且从媒介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新的经验和行为决策常常也是被内隐记忆预媒介化了的,或者换句话说往往是被我们参与其中的集体记忆预先塑形过了的。内隐的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最后还涉及在社会文化中“记忆-想象系统”(Remembering-Imagining-System)的媒介视角,而这一视角往往并不是在所有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意识的。[24]
那么在以如此的方式观察历史时,已有的官方纪念性的外显记忆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当然,首先这些外显记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社会层面,无意识的记忆能长期有效的前提,恰恰是通过经典化、机构化、再媒介化和重复纪念而产生的记忆文化。这也就难怪那些最为有效的长期框架恰恰来自于圣经、民族神话以及经典的好莱坞电影。在此意义上,正是外显记忆给内隐记忆提供了资源。
凭借内隐的集体记忆,记忆这一概念获得了一个现象级的跨学科范畴。因此也使得集合来自不同学科的方法和传统来解决问题成为可能。这些学科指的并不仅仅是已经提到的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和铺垫效应、人类学中关于“民族叙事”(nationalen Narrativen)的研究以及媒介文化史关于“再媒介化”(Remedialisierung)和“预媒介化”(Prämedialisierung)的研究。此外,运动研究[25]、新媒体理论(the digital unconscious)[26]、阴谋论动力研究(van Prooijen und Douglas)[27]、新历史哲学有关在当下再现过去的讨论(Bevernage und Lorenz)以及例如殖民者留下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持续影响力等问题所涉及的后殖民及去殖民的有关争论(imperial durabilities),都与内隐的集体记忆相关。
在记忆研究自身的领域内,有关内隐记忆形式的思考同样具有很长的传统。或许这一传统甚至比纪念性记忆的还要长。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有关“记忆诱发的象征”(erinnerungsauslösende Symbolik)和有意识地去回顾古典模型是完全不同的。“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Maurice Halbwachs’cadres sociaux)如同空气般不能被看见。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及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等作为“格式塔理论”(Gestalttheorie)的代表,在他们关于接受和记忆的研究中,也关注到了内隐的记忆过程。[28]
毫无疑问,无意识的概念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Sigmund Freuds Massenpsychologie)以及卡尔·荣格(C.G. Jung)存有非议的“群体无意识”(kollektives Unbewusstes)概念。在记忆研究中,对无意识的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张力进行描述时,从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关于法西斯主义遗存的思考,到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将“后记忆”(Postmemory)作为创伤记忆的一种非刻意的、跨代际的转写形式,心理分析所使用的思维方式等都具有核心作用。
那为何内隐的集体记忆并不是所谓的社会无意识呢?“内隐的”这一概念是参考心理学和认知学的研究后的选择。但这一选择将焦点放在了从记忆研究和认知学关于无意识的最新研究间的对话中产生出一种“新无意识”(neues Unbewussten)的可能性。并且在转向后人类的研究中,这一概念使得在“生物科技方法的合作”(die biologisch-technologische Koproduktionen)下去研究无意识的记忆者成为可能。
内隐记忆这一概念自身的优势更多是在范式上。丹尼尔·夏克特强调指出:“内隐记忆涉及的无意识世界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有着巨大的差别,它向我们揭开了认知神经学的面纱。”与弗洛伊德富于变化的热闹相比,内隐记忆中的无意识世界作为例如接受、理解、行动这些自然行为的结果就“平淡了很多”(weit prosaischer)。造成这一差异的因素,不仅和关于记忆力最常见的理解有关,而且和在最日常中、自动发生的记忆过程中隐藏的力量有关,此外还和社会和媒介维度的因素有关。当然,这里并不是要用认知科学的方法去和其他的学科比如心理学的方法相对抗,而是要将记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记忆文化中的日常现象里去:扩展到在弗洛伊德体系中还不曾涉及到的特殊角度。将重点放到无意识的认知心理学上更多是一种设定。这一设定尤其符合传播学中有关记忆研究的情况。因为传播学凭借有关框架和铺垫的研究能够在其对媒介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一个在记忆研究领域很强势的传统地位。
而探寻内隐的集体记忆的最大挑战还是方法论上的。因为人们要如何能将“隐秘之物”变得清晰可见呢?或许首先要做的是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除了记忆研究已经涉及到的学科外,不管是实验性的还是抽象性的工具,从媒介文化史研究到“数字人类”(Digital Humanities),都是新的可能性。此外,这样做的理由还在于,这么多学科的交叉给跨学科的合作提供了空间。
【注释】
① 本文选自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托马斯·伯克纳(Thomas Birkner)等合编的论文集《传播学中的记忆研究》(Handbuch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Erinnerungsforschung),2023年由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出版。本文获得作者授权译发。
② 参考:Erll,Astrid.KollektivesGedächtnisundErinnerungskulturen.EineEinführung3.A.Stuttgart:Metzler,2017a[2005]:104。——原注
③ 参考:Carlston,Don.,,Model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ntal Representation“.HandbookofImplicitSocialCognition:Measurement,Theory,andApplications.Hg.Bertram Gawronski,und B.Keith Payne.New York:Guilford Press,2010:4。 ——原注
④ 参考:Renner,C.Hackett.,,Validity Effect“.CognitiveIllusions:IntriguingPhenomenainThinking,JudgmentandMemory.Hg.Rüdiger F.Pohl.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7:201-213。 ——原注
⑤ mentaler Kontamination这一概念来源于心理学,字面翻译应为“精神污染”,指因遭受虐待或者受刻板偏见影响,而对某人、某群体、某物或者某地等有厌恶感并且想与之保持距离的心理状况。为了和中文语境下的“精神污染”做出区分,故此处试将其翻译为“精神强迫”。 ——译注
⑥ 参考:Schacter,Daniel L.TheSevenSinsofMemory:HowtheMindForgetsandRemembers.Boston,Mass: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107。 ——原注
⑦ 参考:Whittlesea,Bruce W.A.,Larry L.Jacoby,und Krista Girard.,,Illusions of Immediate Memory:Evidence of an Attributional Basis for Feelings of Familiarity and Perceptual Quality“.JournalofMemoryandLanguage,1990 (29):716。 ——原注
⑧ 参考:Beiner,Guy (Hg.).PandemicRe-Awakening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 ——原注
⑨ 参考:Erll,Astrid:,,Homer,Turko,Little Harry:Cultural Memory and the Ethics of Premediation in James Joyce’s Ulysses“.PartialAnswers,2019 (17):227-253。 ——原注
——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