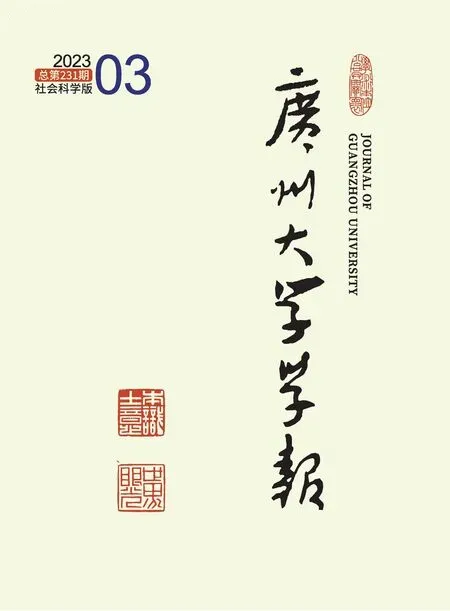期待视域之外
——疫情与集体记忆①
阿斯特莉特·埃尔著,刘 艺译
(1.法兰克福大学 现代语言学院,德国 法兰克福 60323; 2.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重庆 400031)
在大流行病肆虐期间,记忆研究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因为目前我们仍身处其中,然而,对过去大流行病的回忆或遗忘严重影响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体验。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历史的回忆、归档、纪念等等实践活动证明了自身作为重要社会资源的价值,并且新型冠状病毒最终也会成为被回忆的对象,从而影响社会的未来。因此,我将在文中探讨在新冠疫情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的集体记忆(kollektives Gedächtnis)。
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始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这一概念,他强调记忆始终“处在社会框架中”②。当前记忆研究是在跨学科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范畴内进行的③,集体记忆被认为是一个囊括了生物、心理、社会、媒介、文化和物质层面的复杂过程,不断重置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个体”和“集体”不再是相对概念,而是记忆研究领域中的不同研究视角:心理学研究个体的记忆能力,而社会学更倾向于观察其在社会及国际范围内发生的过程。集体记忆与历史也不是相对概念,在这里,历史事件是记忆的对象,历史书写则是集体记忆的方式。④
一、疫情之前的集体记忆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欧洲人在全球性疫情面前毫无准备,而我们本该预料到它的到来的。过去的一百年内就发生过多次流行病:亚洲流感(Asiatische Grippe)(1957—1958年)、香港流感(Hongkong Grippe)(1968—1970年)、俄罗斯流感(Russische Grippe)(1977—1978年)、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艾滋病毒或艾滋病(HIV/AIDS)、非典(2002—2003年,也就是SARS冠状病毒)、禽流感(Vogelgrippe)(2004年),猪流感(Schweinegrippe)(2009—2010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5年)、寨卡病毒(Zikavirus)(2015—2016年)、埃博拉(Ebola)(2014—2016年)。
可见,大流行病总是有规律地反复出现。早在2019年,医学历史学家弗兰克·M·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就将埃博拉和非典病毒看作是21世纪下一场大流行病的“预演”[1]466。然而,大多数欧洲人似乎都忽视了流行病,因为他们对流行病的想象总是投射在“它者”(das Andere)身上——要么是前现代的欧洲人(黑死病),要么是文化或地理上的它者。埃博拉似乎是专属西非的疾病,20世纪初的“亚洲流感”(正如它的名称错误地暗示那样)则是亚洲人的事情。
(一)被遗忘的西班牙流感(Spanische Grippe)
如果那些近期发生的流行病还不够令人难忘,那么1918—1919年有着惊人死亡数量的大流感(即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应该在人们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从1918年春季至1919年春季,西班牙流感共出现了三次高峰期。医学史上对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5000万至1亿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2.5%至5%。
《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是一部非常值得阅读的作品,它全面地讲述了西班牙流感史。据作者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所言,这场流行病是“自中世纪黑死病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甚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流行病”,死亡人数“超过了一战(1700万)以及二战死亡人数(6000万),甚至可能比两者加起来的总死亡人数还要多”。[2]12西班牙流感是当时所有流行病的源头,通过病毒变异,多次掀起较小的流感潮,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欧洲,它却完全被遗忘了。
(二)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
2020年初,对于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流行病并不属于莱因哈特·科赛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说的“经验空间”[3]。在文化中所感知、体验和记忆的东西会对未来的想象产生影响,这便是“期待视域”。2018年,西班牙流感一百周年之际,西班牙流感在欧洲获得了很多关注,但它既不属于纪念文化活动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学校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内容。
正因为如此,新冠疫情彻底破坏了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之间的关系。欧洲人自认为曾经所知道的或曾经所想的(关于呼吸系统疾病的危险、在民主社会中实行封控措施和临时立法的可能性、义务教育、经济稳定性以及佩戴医用口罩等问题)在短短几周内尽数失效。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新体验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超出了期待视域。正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2020年4月23日的政府声明中所言,新型冠状病毒很快就会变成“一种苛求”⑤,这一苛求不仅是对民主而言,而且也是对通过集体记忆承载的关于时间节奏和变化的社会想象而言。
然而,各地人们对同一时间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件却并非都有相同的感知。原因便在于集体记忆的形式不同:例如韩国对新冠疫情就有所准备,这或许是因为曾经历了严重的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西非人在2020年春季对于新冠疫情的到来似乎也并不惊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仍记得埃博拉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此外,各地的知识秩序和习惯记忆也各不相同:亚洲大部分地区习惯使用医用口罩,这种习惯似乎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流感;而在2020年春季的欧洲,关于医用口罩的有用性和适用性却带来了长时间争论。
(三)预媒介化(Prämedialiserung)
我想使用“预媒介化”这一概念来描述集体记忆如何塑造未来,即群体和社会以何种方式预测、解释和应对新事件。但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听上去有些别扭的概念呢?从手势、口头交流到书籍、电视和互联网——记忆需要表达和实现社会共享的媒介。集体记忆建立在媒介化之上,因此集体期待始终是由媒介预成型的,也就是预媒介化的。
西班牙流感就是例子:在欧洲,西班牙流感没有被充分媒介化以及再媒介化,从而也就未能使其成为新冠疫情的预媒介化动力⑥。欧洲缺少关于西班牙流感的当代著名的回忆录、绘画和小说,没有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圣像画或叙事,以及能够由此形成的社会性集体记忆。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SelbstporträtmitderSpanischenGrippe, 1919)或埃贡·什勒(Egon Schiele)的《蹲着的夫妇(家庭)》[KauerndesMenschenpaar(DieFamilie), 1918]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不属于艺术家的核心作品,也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圣像画流传下来。而对中世纪瘟疫的深刻集体记忆恰恰基于一些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比如今天还可以在教堂里找到的关于死亡之舞的绘画或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Dekameron,约1349—1353年)这样的迄今都属于欧洲社会的经典作品。
(四)回忆(Erinnerbarkeit)
各种原因导致了西班牙流感的低度可回忆性。第一,它作为历史事件,其建构不明确。H1NI流感病毒在当时还不可见且传播迅速,通常在短短三天内就能致人死亡。它无法被检测到是因为当时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还不可见(20世纪30年代开始可在电子显微镜下观测到病毒),所以它与当时肆虐的其他流行病病毒如结核病病毒混在一起,此外还有战争和饥饿夺走人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当时的人们很难将西班牙流感视作单独事件,从而将其与其他事件区分开来。
第二,西班牙流感缺少叙事潜力,即不太可能从混乱的历史事件中创造出完整的故事,因为要是不清楚事件的真实情况,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地点、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那么故事就不能展开。
第三,西班牙流感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士兵们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战死并被英雄化。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流感死亡的“可叙述性”更低,也就是说新闻价值更低。
第四,记忆文化倾向于成为规范。“历史教训”更容易从战争、种族灭绝和恐怖行动等事件中被总结出来,因为从这些事件中人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罪责和责任。面对气候变化和人类世(Anthropozän),人们才慢慢意识到洪水和流行病等自然灾害是由人类(共同)造成的,人类应对此负责。
第五,可回忆性同时也是存档问题。就像西班牙流感一样,这类在当时语境下没有被明确定义为单独事件的历史事件,缺少某种特定的动力,使人去分享其间的经验并流传至后代[在历史学中,这被称作“传统”(Tradition),它是“残余”(Überrest),即无意中留下的原材料的反义词]。
(五)什么叫作集体记忆和遗忘?
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范围内都留下了痕迹,也就是说留下了西班牙流感的残余,其中主要包括病毒学和在过去几十年内增多的医学史研究所使用的医学和统计学数据。就病毒学而言,在20世纪期间已灭绝的H1N1流感病毒是一个典型事件,在2005年出于研究目的被用于基因改造。[2]221在科学系统中一直保留着对西班牙流感的记忆,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是家庭记忆,它的传承从未中断,正如盖·班纳(Guy Beiner)等人在《大流行再觉醒》(PandemicRe-Awakenings, 2021)中写到,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家庭记得他们的祖先曾死于西班牙流感。[4]
集体记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头脑中都有相同的表征符号,而是指在社会群体中,过去的特定事件通过话语、媒介和实践被不断更新并与其他主题关联在一起。同样,集体遗忘并不意味过去事件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而仅仅指在特定的社会框架中记忆行为的缺失。这样一来,公众记忆中的事件才能被回避、压抑、禁止或难以言说。但记忆(例如西班牙流感)往往会继续在家庭或地区范围内——再或者在科学的专业话语中——继续存在。
二、疫情期间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发挥了什么作用?疫情经历触发了哪些回忆?哪些应对策略被挖掘了出来?在疫情期间可以观察到哪些记忆文化实践?
(一)历史类比(Historische Analogien)
充满矛盾的是,这样一种跨越国界的病毒却导致了包括在记忆领域中的重新民族化:为了理解疫情现状并使政治行动合法化,民族记忆中的历史类比通通被搜罗了出来。首先是记忆文化中的“惯常嫌疑”(die üblichen Verdächtigen)被激活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回忆了二战期间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和社会凝聚力;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其首次就新冠问题的全国演讲中曾六次重复了“我们正处在战争状态”(nous sommes en guerre);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2020年5月开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和珍珠港事件进行类比(暗示“亚洲人”的偷袭),明确宣告病毒是一场“战斗”。⑦将新冠疫情和二战进行类比的方式在曾经的同盟国中有一定的集合和动员作用,这是形成集体身份认知的记忆模板(当时和现在都是“我们”对抗“他们/它们”⑧,更确切地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对抗的是“它”)。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88年在其论文集《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undseineMetaphern)中所说的那样,“战争”大多被用于隐喻紧急情况和巨大社会牺牲的合法化。⑨
对新冠疫情的体验也导致了对历史上的大流行病的回顾:一百年以来,西班牙流感首次受到了广泛关注;瘟疫和艾滋病也成了公众的焦点;出版了多部关于流行病历史的比较研究作品,如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的《大瘟疫世纪》(DasJahrhundertderPandemien, 2021);关于流行病主题的经典文学作品——从薄伽丘的《十日谈》、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DiePestzuLondon, 1722),到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DiePest, 1947)——出人意料地再次成为畅销书籍,被重新阅读和讨论。
(二)(坏的)思维习惯(Denkgewohnheiten)
疫情重新激发了陈旧的刻板印象。用传染、疾病和堕落等表达方式来掩饰对它者的恐惧,这一习惯由来已久。早在中世纪,犹太人和妓女就被认为是淋巴腺鼠疫的源头。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能长达数千年的负面刻板印象和替罪羊思维突然重新出现。甚至包括那些人们认为早已被摒弃的思想,重新回归的刻板印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2020年春季在维基百科上发布的“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相关排外及种族主义”(Xenophobie und Rassismus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COVID-19 Pandemie)⑩列表证明了这一事实,它列出来数百项条目,从尼日利亚的恐华症到德国的反日歧视,再到美国的反犹主义等等。刻板印象是内隐的文化模板和思维习惯,通过代际记忆和媒介文化得到传播,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
在政治领域,人们战略性地使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刻板印象,在疫情期间就预设了未来的集体记忆。对于流行病名称的争论并非是新鲜事物: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仅仅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立国西班牙是首个公开承认受到流感袭击的国家,而战争强国的审查机制掩盖了受到流感袭击这一事实。尽管这一名称是不恰当的,但它仍然被保留在集体记忆中,以致形成了某种历史假象。为了防止“前瞻性回忆策略”(prospektive Erinnerungspolitik)此类做法,自2015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避免对流行病进行污名化或者误导性命名,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这一名称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当前的危机是集体记忆的检索标记。这些更新了的记忆涵盖了对历史类比的梳理,似乎被遗忘的刻板印象的再度出场以及刻板印象的战略性功能化。
(三)档案和纪念
目前可以看出,历史类比思维是业已结束定位和应对疫情的第一阶段,对特定历史事件的搜寻暗含了一种历史循环观。随着2020年秋季第二波疫情的到来,整个社会似乎已经处在了疫情的全盛期,作为历史事件的新冠疫情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已经显现出来。现在,集体记忆不再以过去而是逐渐以未来为导向。
新冠疫情档案馆的成立就是证明。在德国,最著名的此类档案馆是在线新冠疫情档案馆(Onlineportal Coronarchiv),该档案馆共收录4000多篇稿件,其中收录了“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经历、思考、媒体和回忆”。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数百场活动,目的在于将疫情危机下的经历记录下来。许多博物馆已经开始创建自己的新冠疫情陈列馆。所有这些活动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类社会正处在历史性的时刻,而导致其出现的源头应该让后代了解和铭记。
文学和艺术也试图描写和刻画疫情肆虐的当下,以保存下来留给未来。由苏格兰诗人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发起的“在我们现在的位置去书写”(Write where are we Now)项目已经发展成为大型国际诗歌集,收录了在疫情期间创作的诗歌。新冠疫情漫画也属于世界范围内以新冠疫情为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朱莉·泽(Juli Zeh)的《关于人》(ÜberMensch)和西娅·多恩(Thea Dorn)的《慰藉——给马克斯的信》(Trost.BriefeanMax)是德国首批关于疫情的小说,这种将生活经历加工成文学内容的速度令人惊叹,尤其是当人们将它与一战后的文学作比较时会发现,直到一战结束十年后才开始出现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又或者人们可以回忆一下,德国等待它的“转折小说”(Wenderoman)究竟等待了多长时间。
人们在疫情期间就已经开始以各种方式开展对疫情的回忆。疫情持续至一周年时,人们举办了首次正式的纪念仪式:2021年3月18日(意大利新冠受难者国家纪念日),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贝尔加莫为死难者献上了花圈;德国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 Walter Steinmeier)在2021年4月18日主持了新冠受难者纪念仪式。对逝者的纪念[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是文化记忆的“原初场景”(Ur-Szene)[5]],不在事件结束后才进行,而是在其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恰好是在国家层面上具有象征含义的第一年结束时)。除了这种公共的、具有传统性质的国家纪念活动,还有草根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在泰晤士河旁未经授权的国家新冠疫情纪念墙,人们在墙上画下数千颗红心并写下了多个疫情纪念网址。
三、疫情之后的集体记忆
疫情之后,人们会记住什么?面对现状,人们不禁想说: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记忆文化以自我反省为特征,因而我们能够强烈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历史时刻之中,对新冠疫情的特殊的历史化也无处不在。西班牙流感时期,人们没有设立疫情期间真实经历的档案。而新冠疫情时期的每秒钟的经历似乎都被储存在数字媒体中,这也正是新冠疫情的特点。这是世界上首次经历和记载下的数字化的疫情,是新媒体时代全球记忆生产的测试性案例。但问题是,在未来将有哪些媒介化了的经验、观点和叙事将被储存在主流记忆文化中?毕竟集体记忆具有高度选择性。一方面,集体记忆的产生和维持取决于自上而下的纪念行为。问题在于:会引入(国家以及国际性的)新冠疫情纪念活动吗?会建立疫情博物馆吗(或许会在现有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之上)?学习流行病相关知识会成为学校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吗?另一方面,集体记忆还有其他形式,也就是以共有的、深刻感受的经验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动态记忆,代际记忆(Generationsgedächtnisse)便是其中的一例。
(一)代际和记忆
新冠疫情期间很可能会产生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说的“一代人”(Generation),即一个在形成期受特殊经历深刻影响的(从而定义自己或被他人定义)、年龄大致相同的群体。通常认为,“形成期”(formativperiode)或“关键期”(kritische Jahre)介于17岁至24岁之间。社会学研究表明,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事件极容易影响其政治信念。认知心理学研究以自传体记忆中的记忆突点(reminiscence bump)为出发点:我们记得最清楚的事就发生在形成期。
尤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疫情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中小学和大学都暂停教学,人们不能参加大型聚会、出国或者举行庆典仪式(例如毕业派对),而在这一地区,正是这些活动决定了青少年和成年早期阶段。因此,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新冠疫情将作为代际记忆被保存下来。“疫情岁月”(Corona-Jahre)的经历是否会跨过代际的界线,这个问题将取决于我们在回顾疫情时是否会把它视作变革性事件(它不仅仅是重大事件,而且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和社会)。
(二)大流行叙事
集体记忆的基础是选择——选择要记忆的元素(由于大脑容量的关系能被记忆的东西非常少)——以及叙事结构化,即以连贯叙事的方式排列记忆要素。那么,新冠疫情在未来将被如何讲述?叙事结构是集体记忆的基础,因为每次经历和每件历史事件都会被追溯到它的开始、经过和结局。对历史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来说,“通过叙事结构化来进行解释(情节化)”(Erklärung durch narrative Struktur)是讲述历史的开始[6],因此,叙事和叙事结构都是无法避免的。但问题是,现如今反事实叙事与被肆无忌惮简化了的、虚假的阴谋神话,在和基于事实进行的(没有那么令人兴奋的)叙事争夺进入集体记忆的机会。为了把复杂事件和在疫情期间的不同经历尽可能准确而有效地转化到集体记忆中,需要哪些叙事结构呢?
与所有的流行病一样,新冠疫情也提出了特殊叙事挑战。流行病是自然灾害,而自然灾害很难被讲述——至少在我们现代记忆文化框架内是这样,因为它正是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世界大战、大屠杀、国家恐怖主义、专制政权以及全球恐怖组织等事件后成型的。这些叙事(有充分的理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规范性的,它们强调个人和社会的过失、罪责和责任。
但是在一场由RNA序列引起的灾难中,谁是“肇事者”?该如何重新定义“英雄”?“受害者”又是谁?什么是“历史教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未来的记忆文化必须学会以“隐含主体”(impliziertes Subjekt)的思维模式在后人类框架中更有力地运作[7-8],此时需要的不是前现代或现代的记忆方式,而是我认为的“相互关联”(relational)的回忆方式,而这又指的是什么呢?
(三)相互关联的回忆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风险社会”(Weltrisikogesellschaft)中,灾难在许多人的共同协作下发生,而个人却没意识到自己的罪责。[9]“隐含主体”[7]这一概念,指的是导致灾难的系统中的能动部分。在社会的不公、种族主义、饥饿、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等情况下,尽管不容易定义罪责和犯罪者,甚至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在西方)作为隐含主体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在后人类框架中接受这一思维模式意味着承认我们与非人类主体如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共同处于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称之为“共生”(sympoiesis), 简·贝内特(Jane Bennett)则称之为“分配代理”(distributive agency)]。[10-11]在新冠疫情中,病毒的RNA出现变异和跨物种传播的趋势,这一现象伴随着人类入侵野生动物栖息地,正是这种入侵使得病毒的“跳跃”——流行病的开端——成为可能。疫情大流行几乎不能归因于明确的原因或确定的肇事者,如斯诺登写的那样,它们“并不是随机事件[……]它们随着环境破坏、人口过剩和贫困而蔓延”[1]505。
2021年,我们同时经历了一场全球流行病、洪灾、火灾以及极地冰川融化,因此人们可以认为,新冠疫情将在集体记忆中与气候变化相关事件联系在一起。将来,人们回忆起新冠疫情时是否会把它当作气候历史上的转折点或者临界点,这个问题只能在数年后才能得到解答。
【注释】
① 原文出自Astrid Erll,PandemieundKollektivesGedächtnis.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GeschichteundErinnerung. APuZ, 2021年10月4日, 本文获得作者授权译发。 摘要、 关键词为译者所加。——译注
② 参见: Maurice Halbwachs,DasGedächtnisundseinesozialenBedingungen, Frankfurt/M. 1985 (1925); ders.:DaskollektiveGedächtnis, Frankfurt/M., 1991 (1950)。 ——原注
③ “记忆研究协会”于2016年成立。 参见: www.memorystudiesassociation.org。 ——原注
④ 参见: Astrid Erll,KollektivesGedächtnisundErinnerungskulturen, Stuttgart, 2017。 ——原注
⑤ 参见: www.bundeskanzlerin.de/bkin-de/aktuelles/regierungserklaerung-von-bundeskanzlerin-merkel-1746554。 ——原注
⑥ 再媒介化作为集体记忆的动力。 参见: Astrid Erll/Ann Rigney (Hrsg.),Mediation,remediation,andthedynamicsofculturalmemory, Berlin, 2009。——原注
⑦ 2020年3月16日, 特朗普推特发文明确提到“中国病毒”。 国内外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20日对此进行回应, 具体可参考网页: 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2088541.html。——译注
⑧ 德语中的“他们”、 “她们”和“它们”都是“sie”, 此处既指法西斯联盟又指新冠病毒。——译注
⑨ 参见: Susan Sontag,KrankheitalsMetapher/AidsundseineMetaphern, Frankfurt/M., 2012 (1988)。 ——原注
⑩ 参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ncidents_of_xenophobia_and_racism_related_to_the_COVID-19_pandemic#cite_note-dw52862599-3。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