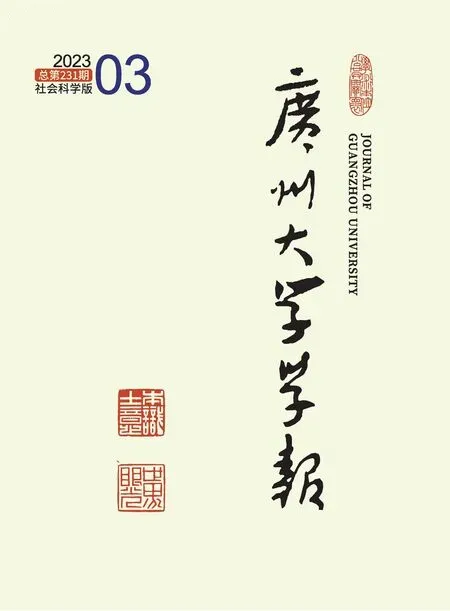两种“现实”的竞现:网游时代的“银幕世界”
——以电影《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为例
姚怡然,姚新勇
(1.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2.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网络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电脑网络游戏的不断升级换代,这既促进了网络游戏与电影艺术的互媒介化进程,又对电影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促使电影主动向游戏靠近以谋创新。约以1998年为界,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涌现出一批具有网络游戏时代特征的影片。譬如《黑客帝国》(1999)、《异次元骇客》(1999)、《人工智能》(2000)、《盗梦空间》(2010)、《她》(2013)、《像素大战》(2015)、《匿名者》(2018)、《黑镜:潘达斯奈基》(2018)、《头号玩家》(2018)、《失控玩家》(2021)等。在这些影片中,主角们穿梭于“虚拟”与“现实”、“梦幻”与“真实”之间,观众所面对的银幕虽非直接的网络游戏世界,却与其具有程度不同的近似性与同质性。这批电影的集中出现,意味着电影艺术产生了某种质性的变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网游时代”的电影纪元。
对此学界已有不少关注,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以传统科幻电影来定位、审视这类影片,具体研究常涉及技术与审美[1]、幻境与现实[2]、人工智能的迷思[3]、科技与未来的思索[4],以及“托邦”与空间转换等视角或主题,带有相当的哲学性及伦理思考意味。例如《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头号玩家〉的叙事空间与文化想象》一文,借用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三个概念,分析影片《头号玩家》在叙事维度上的空间隐喻,指出影片通过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并置,传达了导演的社会责任意识,思考了关乎地球所有物种延续的全球伦理问题。[5]此一分析可谓透彻、精彩,然而却没有意识到《头号玩家》这类影片已突破了传统科幻片的限度,它们所表现、思考的世界,并非彼岸性的幻象、“灵性虚拟”的“托邦世界”,而是“科技虚拟”仿真世界的真实存在,具有科幻片所缺乏的新质。相较而言,另一类“影游融合”视角的研究,则对此有所突破。
“影游融合”研究是近几年国内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这类研究认识到,数字化科技的迅猛发展与普及,促成电影的新质变化,产生了一批游戏与电影相互融合的新型影片,有必要将它们放在“影游融合”的特殊背景下进行考察。现有相关研究多属于宏观整体现象的扫描,如《游戏化电影:数字游戏如何重塑当代电影》一文,扫描了近20年来的一批影片,提炼了三种电影的“游戏化”形态:“时空设定游戏化”(电影时空设定的“游戏化”)、“情节结构游戏化”(影片情节的“闯关化”)和“视觉呈现游戏化”(“主观镜头”“跟随镜头”的大量使用)。[6]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分析,如《从〈头号玩家〉看影游深度融合的电影实践及其审美趋势》,不过其分析欠深入,基本也是特点指认与未来展望。应该说,现有国内影游融合视角的研究,基本还停留于“点到为止”的层面,且较为单向性地强调电影的游戏化。至于紧跟2021年“元宇宙”热而来的许多文章,更是简单地将《头号玩家》等影片划归为“元宇宙”电影,将它们变为“元宇宙”畅想或漫谈的“脚注”。当然,学界也有少数较有力度的研究,例如《媒介融合时代的电影“银幕”观》一文,通过传统的画框论、窗户论、镜像论等电影理论的回溯,揭示了“数字时代和媒介融合时代”“银幕观念”是如何持续不断地被“解域和重构”,即“从大银幕走向小屏幕”的重组,促成了银幕空间的重组以及银幕与人类身体关系的重构(由观众的静观到身体活动的介入性、互动性观影)①。[7]
但是不论深浅,现有影游融合类研究普遍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游戏与电影二项式对比关系的设定,使得研究往往局限在或者说演变为游戏与电影两种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二是重视游戏对电影的影响,忽视电影对游戏的抵抗与电影化改造,再媒介化研究的“互动性”被不同程度地架空;三是对相关影片时代性质的定位较为含混且游移。三方面问题中,前两方面较为明显,第三方面相对隐性,但却是导致前两方面乃至这类研究更多问题出现的基本原因。影游融合视角的研究,大都认识到了数字技术、网络游戏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强化了人们的虚拟化、数字性、游戏互动性体验,从而促成了新类型电影的批量出现。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却往往把相关现象归结为游戏与电影两种媒介的差异,而未上升到人类生存经验或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的高度来认识,紧扣这一基础认识对具体影片的深入考察更为缺乏。而一些研究虽然对此时代性变迁的基础认识较清晰,结合得较紧密,但对其定位则较为随意,时常把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与未来的技术相含混②。由此不仅造成相关研究的简单、浅表,过分重视媒介互融的技术性分析,而且也造成讨论对象定位的失准、解读的偏差或似是而非,忽视了数字化时代优秀影片对游戏的改造、规约、再编码③。宽泛而言,本文仍可归为“影游融合”类研究,但我们是以“网游时代的影片”为基本定位,侧重于以电影艺术为本位来展开讨论。
网游即“网络游戏”的简称,又名“在线游戏”。不同于“单机游戏”,“网络游戏”需要网游玩家通过互联网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多人游戏,以达到娱乐和互动的目的。而单机游戏多为人机对战,因其不能连入互联网,玩家间的互动性较差。网络游戏的实质在于打造虚拟的互动社区平台,其终极目标就是建造“虚拟实景”或“真实的虚拟世界”,也即所谓的“元宇宙”(Metaverse)④。从初级的电脑游戏到未来的“元宇宙”世界,尽管“虚拟世界”有着多样的名称,其仿真现实性程度也不同,但它们却共有着传统媒介所缺乏的直接的身体介入性或参与性⑤,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时空感、存在感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前所未有地加深了“计算功利的现实世界”和“追求神性的虚拟世界”的分裂[8],不如说是随高科技、人工智能而来的“虚拟世界”的“真实化”,使得人类的虚拟体验和现实感受既分割又高度含混。[9]88从根本上说,人类越来越真实地穿梭、沉浸、分裂于两种真实的空间、真实的现实、真实的世界中。⑥[10]1-6而本文用“网游时代”来指称这一态势,既是因为此概念含蕴着所有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更是因为网游电影和游戏当下所处的实际主流技术场域是“互联网”而非“元宇宙”。
在网游时代,电影所要处理的不再是传统电影的“一种现实实在”之“多种想象世界”的问题(即将物理世界和人类的多样“灵性虚拟”加以影像呈现的问题),而是在两种真实现实(“物理现实”与“科技虚拟仿真世界”⑦)共在的境遇下[10]1-6,如何以“一个银幕”来同时表现它们,而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为避免讨论的泛化,下文将细读《头号玩家》《失控玩家》两部优秀“网游电影”,重点从人类生存、空间叙事的角度来讨论其所面对并艺术性建构的两种现实、三重世界。
二、“一个银幕,两种现实”的呈现
影片《头号玩家》的开场已是2045年。由于地球生态恶化,世界处于混乱和崩溃的边缘,科技愈盛现实愈颓,人们终日沉迷并逃避于虚拟的VR“绿洲”世界,男主角韦德·沃兹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现实中他是生活于贫民窟叠楼的普通少年,生活落魄,默默无闻,但在游戏世界中却是高手,以帕西法尔之名和形象被人喜爱乃至崇拜。
《失控玩家》主要讲述的是NPC(非玩家角色)“盖”之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影片刚开始,银行柜员盖生活于网络游戏世界“自由城”⑧中,无忧无虑,生活千篇一律。经由爱情的启发,盖的属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意识到他自己、身边的朋友以及所生活的自由城都是被操控的,于是开启了摆脱人类控制之旅。最后在发明了他及自由城内核代码的键盘、米莉等人的帮助下,盖终于率领他的“族人”——自由城的原住民们,逃离了反派安托万的毁灭性追赶,去到一个新的真正的自由城,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而现实世界中的米莉与键盘的爱情也终于修成正果。
粗略来看,两部影片似乎并无太多新意,例如1998年出品的《真人Show》⑨就与它们不乏相似性。然而真的如此吗?
《真人Show》的主角楚门从婴儿时起就被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收养,被安置于一个叫作“桃源岛”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结婚、工作。楚门及其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真实,但他却不知除他之外周围的所有人都是演员,就是那座看上去和谐完美的桃源岛,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每时每刻都被无所不在的摄像头所窥摄,浑然不知地扮演着一个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中的真人秀主人公,他的一切都是被精心安排好的,是虚假生活,与其名字Truman形成强烈的反讽。后来由于父亲、爱情等诸多意外的出现,楚门终于发现了真相,不顾一切地设法逃离桃源岛,哪怕要迈出的摄影棚外是一片前途未卜的黑暗。
三部影片似乎在基本空间结构、主题乃至某些人物和桥段上,都不乏某些类似。然而这只是表象,细致比照便不难发现,《真人Show》属于电视时代的影片,所表现或处理的本质上是虚构的电视世界与真实的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头号玩家》和《失控玩家》所面对的则是网游时代之两种真实的“现实”:物理性的现实世界和人工智能所制造的网络仿真世界(一种虽似虚拟但却真实的现实世界)。因之,《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对两种世界的处理手段与《真人Show》明显不同。
在《真人Show》中,桃源岛与观众世界明显被电视屏幕所隔开。由于长期观看电视,观众对楚门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感情,为他哭、为他笑,为他逃离桃源岛的惊心动魄而焦虑不安,但是却无法亲身进入桃源岛帮助楚门,只能设法时时刻刻盯着屏幕,如果电视制作方掐断直播,观众也只能捶胸顿足。抛开象征意义和心理情绪不谈,楚门的命运如何,对现实世界的观众并不会产生太多实质性的直接影响。不仅如此,楚门及桃源岛的虚假性虽与科技相关,但他及桃源岛中的居民,都是肉身真人,只是因为电视公司的欺骗和刻意安排才造成了楚门及其世界的虚假性。
然而,《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中的情况却有本质不同。《头号玩家》中的绿洲世界是带有相当的虚拟性的,而且影片一开始也通过展示叠楼区中的居民戴着VR眼镜忘情地晃动身躯的场景,告诉观众叠楼世界中的人们是如何普遍地逃避现实的不堪,沉浸于虚幻的绿洲世界。但是这一展示本身却又表明,他们并不像《真人Show》中的那些电视观众,只是隔着屏幕观看另一个“虚构空间”,而是借助游戏设备进入绿洲世界,全身心地沉浸其间。正如影片旁白所说,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人们就基本生活于绿洲世界中。男主人公韦德邂逅爱情,发现生活的意义,由孤独的游戏玩家变为正义事业的领袖,与邪恶的IOI公司斗争,等等,也基本都是在绿洲世界展开。观者虽然通过画面仍然可一眼分辨仿真绿洲世界与现实叠楼世界,但从行为的一致性、命运的一体性来看,就难以区分虚拟与真实、托邦与现实了。高仿真的绿洲世界与叠楼世界都是现实,两种虽有差异但却命运一体、并行而在的现实。
相比之下,《失控玩家》不如《头号玩家》那么戏剧化,由“玩家角色”和“非玩家角色”所构成的“自由城”及其主角盖,更直观地呈现为电脑游戏中的存在;物理现实世界中的两个男女主角(键盘、米莉)和同事朋友(鼠标)⑩以及众多现实世界玩家所面对的电脑,更为物理性地将游戏世界与玩家世界相区别。可以说,影片《失控玩家》所依托的技术基础,基本属于当下网络游戏时代的技术,而非《头号玩家》那种带有更多超前性预设的元宇宙技术。不仅如此,盖的银行小职员身份,每天重复单调而“幸福”的生活,被操控、被设计身份的发现,都与楚门的生活颇为相似,就是自由城那阳光明媚的世界(如果去除戴墨镜的玩家角色),也与桃源岛很相像。尽管如此,《失控玩家》的游戏空间与具体操作电脑的现实物理空间的关系,并非《真人Show》那种对象化的虚构电视世界与被动的观众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游戏玩家不是纯粹被动的观者,而是行动者、参与者。但一个游戏程序是否最终被“再现性完成”,“再现”的时间长短,与游戏玩家具体的“玩”、对游戏设备的操控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具体的游戏最终能否完成,并不单独决定于程序设计员,而决定于设计者与玩家共同的“合作”。而像《失控玩家》这样建立于当下网络游戏技术基础上的影片,当中两个世界的交互性特征就更为明显了。虽然游戏玩家还没有直接佩戴VR眼镜等设备,但VR眼镜的操控功能已经想象性地表现在电脑屏幕的自由城里,玩家们已经借助那些戴着特殊功能墨镜的玩家角色进入其间展开互动。在这里,游戏世界自由城的命运与现实世界命运的关联度,远远超越了《真人Show》中两个世界的关系。
再从电影的主题看,虽然《失控玩家》《头号玩家》与《真人Show》也比较相似,都涉及到“我是谁”“自我意识的觉醒”“发现真正自我”“发现真实”等哲学性命题,但相关主题在两部网游电影中更直接地与怎样处理“物理现实世界”和“科技仿真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密切关联,并非是老问题的简单重复。
总之,《真人Show》是电视时代的电影,而《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则是网游时代电影的代表。在后两者中,物理现实世界与科技仿真世界的切换,不再是“看的世界”与另一个“被看的世界”之间看与被看的切换,而是一种“平行关系”的互动、共在。这些只有放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被真正理解,也才更具可信性。
三、“两种现实,三重世界”的交错
上述分析说明,网游时代电影面对的是两种平行、交叉互动的现实,这对网游类电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将这两种现实——以肌肉、竞技、身体介入沉浸感为特征的网游仿真世界和物理的现实世界——联结起来,使得电影既具有游戏的特点,又不失自身的艺术特色?
就动作画面的视觉呈现而言,电影与游戏具有天然的肌肉亲缘性,很适合对电脑屏幕进行再媒介化表现,反之亦然。所以像《头号玩家》所呈现的拟网络游戏的劲爆场面与情节,固然与斯皮尔伯格惯常的“史诗级大片”的导演艺术风格不无关系,但本质上则是电影银幕对电脑屏幕的一种“移植性”的再表现;至于人们津津乐道的影片所暗含的众多“彩蛋”,也不过是先前所存在的游戏或电影片断的再组合。但是不管电影对游戏肌肉性特点移植得多么成功,会多大程度地激发观众的情绪乃至身体反应,我们都很难想象电影观众(比如《头号玩家》的观众)在观影时会像影片中的那些人物一样站起来,随着银幕扭动身体。即便影院中的观众会如此,但这也只是一种模仿而非操作,不管他们如何模仿,影片都会按照既定的情节展开,仅凭这种模仿是难以真切地体会玩游戏时的沉浸式互动感。电影之所以是电影,就在于它不是游戏。如果面对两种现实,网游电影只是刻意地去追求电脑屏幕的似真性,通过镜头切换让影片中的角色往来于两个世界中,那么这不仅只是对游戏的简单模仿,而且更可能是向初期动作电影的倒退。电影的发展不仅在于拍摄技巧的进步,更在于通过技巧的进步把更多的情感、叙事、思想等元素融进电影中,形成它独具特色的时空表现。
所以,网游时代的优秀电影固然要积极地吸收游戏元素,更要思考“两种现实”的同时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会对作品中的角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怎样影响故事的展开,电影怎样才能用一个银幕有机而结构性地呈现世界——两个平行共在、相互影响的世界,它们及其表现将带给人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些都无法仅仅通过肌肉性的展示来回答。
《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对网络游戏再媒介化成功的关键,是通过将“英雄美人”和“资本批判”融进影片,让它们发挥连接两种现实的叙事功能,形成独特的多重时空的叙事,从而完成对网络游戏的再媒介化及对两种现实的表现与思考。这里先分析两部影片的多重世界或多重时空,叙事功能结构的分析留待下一部分展开。
从电影空间叙事的结构关系看,《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总体上存在三重世界或时空的关系结构。前两种是上述科技仿真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而物理现实世界又被区分成一般性的广大游戏玩家世界和游戏资本平台(即《头号玩家》中的IOI公司和《失控玩家》中的Soonami公司)两部分。三重世界关系的设置首先是对网游时代现实的一种实际再现。无论是当下的网络游戏空间还是未来的元宇宙空间,都是经由平台打造的。平台提供相应的游戏空间的技术支持,并设置、规范相应的游戏、行为规则,平台既勾连又操控着游戏玩家和游戏空间。尽管实际上由资本主导的平台可能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操控一切,但正如两部影片所表现的那样,每个平台投资方总会本能地竭力掌控一切。更深层地说,两部影片对平台的设置和叙事的展开,表现了好莱坞世界常有的“左翼”倾向,即对资本垄断的怀疑和批判,这突出地表现为《头号玩家》中韦德及其伙伴所代表的叠楼世界与IOI公司的斗争,以及《失控玩家》中米莉、键盘等同Soonami公司老板安托万的斗法。
当然,两部影片的特殊性并不在此,它们作为网游电影的特殊性,在于物理现实世界中的善(一般玩家世界)与恶(游戏资本平台)的冲突,一方面主要展示于游戏空间中,这正是影片汲取游戏元素,展示力量、速度、刺激、暴力之“黑科技”炫酷之所在;另一方面源自现实的矛盾冲突,又在游戏空间和现实空间同时对应性发生。这种共时对应性,在《失控玩家》中,主要表现为键盘、米莉操作电脑的动作与自由城中相应的打斗、炫技画面的相互切换;而在《头号玩家》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且夸张,不仅有着戴VR眼镜、穿装备的韦德及其伙伴们的身体动作与绿洲世界火爆打斗、竞技场面的镜头切换,而且在影片的高潮部分,更展示为穿着装备的全体市民与装备齐全的IOI公司机奴们的动作比划,以及绿洲世界中正邪双方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场面的相互对应。
四、表层的“游戏化”与深层叙事功能的规约
有研究认为,由于游戏元素的引入,《失控玩家》打造了四层交叉互动的空间,其中“以盖为主角的里层世界”主导并制约了“以米莉为主角的外层世界”,影片有了“新的叙述方式”,经典的“成长故事”叙事与后现代叙事风格交织,并通过游戏彩蛋等表现手段的自觉嫁接,带来了影片后现代的“拼贴性”“碎片化”与“戏仿性”,增强了影游互动下故事之于观众的体验感与沉浸感。[11]也有人认为,游戏元素的引入,影响了《头号玩家》的叙事,并导致人物设置及其关系的简单化,正是这种去复杂化的叙事策略,使得《头号玩家》即便堆叠了各种类型元素与母题,也不显得混乱。[12]这些观点虽不无合理之处,但却较为浅表,忽略了影片深层蕴含的叙事母题、哲理命题的重要性,更没有认识到这两者所形成的叙事结构及逻辑之于影片故事展开的内在主导性。
若想真正理解前述三重世界的关系,把握电影时空叙事的展开,探究影片所包含的启发性及其限度,需要针对其中的“英雄美人”和“资本批判”这两个母题作进一步的叙事功能的结构性分析。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英雄美人”和“资本批判”两个母题在两部影片中构成了“爱”与“善”的叙事功能配对,表现为“爱→自我觉醒→反抗→理想社会的达成”与“资本(契约的破坏)→反抗→资本(契约的修复)”一明一暗两种功能性深层叙事结构,恰是它们决定了影片情节的展开与空间交叉的互动。
众所周知,一般好莱坞影片的英雄美人母题,主导者是男性英雄,其冒险故事的展开往往构成影片叙事的基本情节,而美人只是穿插、过客、陪衬。但是在《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中,女性不再是简单的陪衬性存在,而是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她们启发和引导爱情的发现与展开,主导“爱的发现→发展→达成”之情节的推进,使之对应于“爱→自我觉醒→反抗→理想现实的达成”之深层叙事线索。在《头号玩家》中,如果没有萨曼莎爱的社会责任感启蒙,韦德就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游戏高手。就现实世界言,萨曼莎吸引并使韦德发现了爱,启发他正视现实世界的不堪,引导他从单打独斗玩家,成为拯救世界的五虎队员及整个社会反抗IOI公司的领袖。而在科技仿真世界中所开展的寻找彩蛋、争夺绿洲世界所有权的“世界大战”中,萨曼莎不仅启发韦德发现爱情,更直接为韦德最终找齐三把钥匙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而且如果不是受萨曼莎的社会责任感的启发,韦德难保不会陷入绿洲世界创造者所设计的签署合同的陷阱。可以说女主角萨曼莎发挥了导师与帮手的双重作用;而以其为主导的爱的发生与推进,既直接影响了虚拟仿真绿洲世界与现实折叠楼世界的交叉互动,也促使游戏闯关特点服从于(追求意义表述的)电影情节的展开。
在《失控玩家》中,爱的作用更为重要。整个故事的基本叙事以及盖自我意识之人工智能水平不断提高,均围绕着米莉和盖并兼与键盘的爱情发展而展开,米莉成了勾连两个世界的基本环。当然,两部影片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最后都指向了“善”的达成——由爱与善所主导的理想现实的达成,被异化性分裂的两种现实、两个世界(人类世界和高科技仿真世界)的紧张、冲突也得以解决。因此,尽管这样的故事仍然表现出好莱坞影片的俗套性,尽管它们吸收了诸多游戏元素,但我们仍然不难从中体会到,这是电影以自身传统模式及人文思考对游戏所实施的再编码[13],或曰电影对游戏的“吸收—抵抗”之双重实践。
再来看“资本(契约的破坏)→反抗→资本(契约的修复)”这一功能性结构,这是与爱的叙事功能相配对的更为重要的深层结构。与爱相对应,两部影片各存在一个反派:《头号玩家》中IOI公司的管理者诺兰和《失控玩家》中Soonami公司的老板安托万。前者想垄断绿洲世界,从而在绿洲中挑起“世界大战”;后者偷窃别人的专利并想完全操控游戏世界,为此不惜毁掉已经具有人的意识、自我发展能力的人工智能盖和自由城。就此而言,或可说影片讲述的是爱之善与恶之贪婪的交战,善最终战胜了恶。不过从本质上说,两部影片中的善并不是爱,而是“遵守契约”,这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有集中的体现。《头号玩家》中,韦德及其团队终于率先得到了绿洲彩蛋,拥有了绿洲公司的所有权,诺兰被捕,IOI公司破产;韦德则主动把绿洲公司的所有权与朋友分享,并制定出更为合理、人性的绿洲世界运行规则,达成了以叠楼为表征的现实世界与绿洲虚拟仿真世界的平衡、和谐。《失控玩家》中,米莉与安托万做了一个看似极不平等、极为吃亏的交易,保住了自由城,使其成了“真正”的“Free City”;而窃贼安托万最终破产并被逮捕。总之,在两部影片的结尾,现实世界的破败或纷争、存在的无意义或焦虑,现实世界、游戏世界与技术资本平台三重世界的分割与矛盾,都得到了治愈和解决。但是如果更为深入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两部影片所存在的不只是抽象的“遵守契约”的教诲,还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更具主导性的“资本(破坏契约)→反抗→资本(契约修复)”的功能性叙事结构。
《头号玩家》一开始就通过旁白提示:生态危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破败,人们只能通过沉迷于游戏世界来逃避苦难的现实,而许多人又因为向IOI公司举债,被关进机位小仓,成为契约奴般的“第六人”(Sixers)。需要注意的是,IOI公司和诺兰确实是反派、剥削者,但其恶之实质并非因为他们是资方,而是因为他们放高利贷、垄断、贪婪;而IOI公司将举债破产者变为机器契约奴本身,则是合法的依约行事,是受法律保护的。在绿洲世界的争夺中,诺兰也多次想与韦德签约,将他高价聘为“合作者”。所以,绿洲世界中的争夺大战不管多么激烈,都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的竞争。诺兰的违法主要在于他用暗杀、绑架的手段,试图清除自己的竞争对手。影片高潮部分,个人或小群体对贪婪资本的反抗,演变为被剥削市民的集体起义、同IOI公司的全面暴力冲突。正值此时,原本相对分割而存在的三重世界,更为直接、共时地呈现在银幕上,电影镜头频率更快地在三个世界中来回切换(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讲述着暴力的反抗。但这只是一场“压迫与反抗”的冲突,并非革命,因为影片最后,代表市场正常运行机制的Gregarious Games公司(社交游戏公司),找韦德签署拥有绿洲世界操作权的合同;警察——国家机器的代表——现身抓捕破坏正常良性竞争的诺兰,被破坏的契约重新得以修复,整个社会与绿洲世界都在善良的资本运营下得以重新正常运转。
同样,《失控玩家》中也存在类似的深层叙事结构,尽管它不像在《头号玩家》中表现得那样戏剧化。安托万的恶主要在于偷窃键盘与米莉所开发的软件程序;米莉化身进入游戏世界自由城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安托万偷窃的证据。NPC盖的自我意识的产生、与米莉爱情的发展,实际都随米莉、键盘查找证据和与安托万斗法的情节展开。最后安托万无法再用合法手段控制键盘和米莉,拿起大斧疯狂地砍砸,试图毁灭控制自由城的服务器。当然最终反派得到了惩罚,专利重归理当拥有者,而摆脱一切束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理想,则留给了获得自由又远去的Free City。
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否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空想与软弱的表现,这有待读者自行判断。我们想追问的是:拥有了自我意识成长能力的盖和其他NPC,如果也学会了人之恶会怎样?如果盖想念米莉而不能自已,是否会返回人类世界抢回爱人?自由城世界的NPC是否也会到人类世界为所欲为?如果这一切真的都发生了该怎么办?键盘乃至米莉是否会重新操起安托万的巨斧,亲手砍毁由他们所设计并拼命保存下来的连接自由城的服务器?若此,恶不就反转成了拯救人类的关键吗?然而问题是,一旦人工智能达到或超过了人的水平,毁灭人工智能究竟是能够拯救人类,还是更快地将人类推向《黑暗帝国》的境况?这些正是影片留给观众回味、咀嚼、反思的问题,其意义可能远大于观众借助互联网去搜寻影片暗藏的游戏玄机的“互动叙事”之意义。[12]所以,网游电影、优秀网游电影的成批出现,与其说是“预示了一个‘想象力消费’时代的到来”[14],不如说是它们借助网络游戏元素的吸收和消化,继续着电影既传统而又超前的艺术想象与哲理沉思及伦理追问。
五、余 论
经由前面分析可见,电影这一相对更为“传统”的艺术媒介,通过对网络游戏特点的自觉挪移,以传统的“爱”与“善”故事的讲述和深层哲理性思考的引入,将古老的人与自然的物理世界和正日益高仿化、真实化的游戏虚拟世界,直观、生动地勾连在了一起,从而形成或含蕴了网游类电影的独特魅力与意义。所以,有一类观点,即认为游戏元素的进入改变并主导了影片的情节展示、多重空间场面的设置,切断了线性时间逻辑展开的电影叙事,使得电影成为缺乏深度的“爆米花式”的快餐,显然过于简单、浅表。
从接受角度而言,网游类电影有意识地去迎合、满足Z世代观众所意欲的游戏介入感,以回应网游时代电影所面临的受众流失的挑战;同时,它们也让不熟悉网络游戏的观众,对此有更直观的感觉。就此而言,这确是“电影为游戏‘正名’”,“寓言了成人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一次沟通与和解”。[12]但是网游类电影终究是电影,保有“坐观”之观影特点,客观上要求Z世代观众对象化地静观,而非直接性地介入,促使他们对象化、反思性地认识自我、反思他们所熟悉的游戏世界。而电影所具有的哲理思考、伦理拷问的传统,又往往会促使优秀的网游电影艺术性地引入和创造第三种世界(时空),促使更广义的观众在观影时或其后更深入地思考。亦如《头号玩家》与《失控玩家》,既共时性地勾连、呈现了物理现实和虚拟仿真游戏现实,同时又引入了高科技资本游戏平台世界,使这个平常隐匿性的存在显性化,引导观众对其进行认识、审视和反思。
这些特点,当然不为《头号玩家》《失控玩家》所独属,一个银幕、两种现实、三重世界的结构属性,也为不少网游类电影所普遍共有。在此基本结构的制约下,不同的电影又会在有关爱、自由、意识与潜意识、人与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地球及宇宙命运等各种重大且基本的哲理问题中,选择自己所关心的主题,并使相关主题与影片深层的叙事功能结构相勾连,再配之以特定的故事情节,从而形成性质相近、故事各异的网游类电影。
【注释】
① 此文之所以质量较高,一是由于对传统西方电影理论引鉴的准确,二是对数字时代电影“被解域和重构”之特点分析的切实。但它也带有国内影视研究著述所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理论引借的滑动性、论证的技术化及语言表达的晦涩。
② 这一点在以“元宇宙”为着眼点的文章中比较突出,即便是玄莉群的《媒介融合时代的电影“银幕”观》(《当代电影》2021年12期)也是如此。此文常以“VR电影”为例讨论数字化时代电影的解域与重构,显然是将尚处于尝试阶段的(小众)VR电影,视为当下数字化时代电影的普遍情况。
③ 这些研究的相关问题,将在后文直接或间接地触及。
④ “元宇宙”英文为Metaverse,也可译为“超元域”“超宇宙”“虚拟实境”“虚拟世界”等,由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的小说《雪崩》(1992)首创。Metaverse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是基于多种技术所创造的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扩大了人们的交互空间。[参见Nelson Zagalo,VirtualWorldsandMetaversePlatforms:NewCommunicationandIdentityParadigms(Hershey: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1),p.xv]元宇宙是“未来虚实共生的人类世界”。(参见易欢欢、黄心渊:《虚拟与现实之间——对话元宇宙》,《当代电影》2021年12期)
⑤ 无论是通过电脑键盘的操作还是借助VR、AR、MR等技术装备的使用。
⑥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在2021年底“元宇宙”火爆之前,如SecondLife(《第二人生》,2003)和WorldofWarcraft(《魔兽世界》,2004)就已经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元宇宙”平台而诞生,并被重点研究。这已经不止是游戏,更是一种未来的生活。[参见William Sims Bainbridge,OnlineWorlds:ConvergenceoftheRealandtheVirtual(London: Springer-Verlag, 2010), pp.1-6]人们要学习如何在虚拟平台中进行身心合一的自我建构。[参见Stefan Sonvilla-Weiss, (In)visible:LearningtoActintheMetaverse(Vienna: Springer,2008), p.15]这些平台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让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中“玩”,更是能够在真实的现实中用于教育、实践等。
⑦ 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洪朝辉教授则区分了“灵性虚拟”和“科技虚拟”。前者是多样而主观的,是通过信仰、宗教、想象、意念、情感等展开的精神性活动,并可以通过绘画、语言、艺术品、电影、电视等来“再现”,其再现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视觉或听觉来加以对象性的感觉和认知;后者则通过高科技将包括灵性虚拟在内的物理世界仿真性地再造,使之成为与物理世界真实并在的虚拟世界。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视觉或听觉来进行感知,而且还能多感官甚至全感官地浸入其间,在其中活动,甚至生活。(参见洪朝辉等:《元宇宙的人文思考》,2021年12月5日“纽约聊斋”讲座)
⑧ 《失控玩家》英文名为FreeGuy,即“自由的家伙”,“自由城”英文名为Free City,而《失控玩家》之译名显然受了《头号玩家》影响,并不是很恰当。
⑨ 影片英文名为TheTrumanShow,本文采用了香港的译名,内地的译名为《楚门的世界》。影片主人公的名字Truman应为trueman的谐音仿造词,译为“真人”可能稍嫌直接,但显然要比“楚门”更接近影片的意涵,当然如果译为“臻人”或“臻仁”可能更恰当。不过为便于内地读者阅读,主人公的名字Truman仍沿用为“楚门”的译法。
⑩ “盖”的英文名为Guy(家伙),其朋友叫Buddy(老兄);Guy的设计者名为Keys(键盘),另一位同事及好友叫Mouser(鼠标)。显然这些都是“物化”性的命名,以隐喻他们无论是游戏世界中的角色,还是现实世界中的公司雇员,在两个“社会系统”中都是被操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