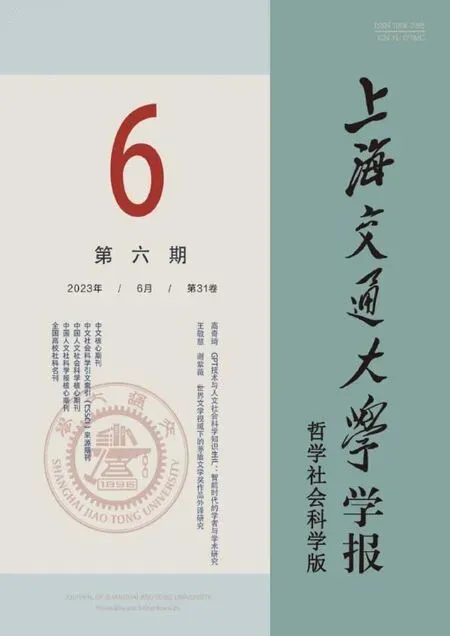必要的消失: 论劳动者的离线权
王 健
(中南大学法学院,长沙 410083)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拜以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平板电脑等为主要形式的数字通信设备的普及所赐,沟通的成本及时间大幅降低、缩短。与此同时,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用人单位通过视频、电话、短信和邮件等数字化方式在非工作时间与劳动者交流工作,甚至直接给劳动者安排工作,从而要求劳动者“变相加班”的情况屡见不鲜。前程无忧发布的《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显示,加班已成为我国职场常态,62.9%的受访职场人表示需要偶尔加班(1—2天/周),28.7%的表示需要经常加班(3—5天/周)。近六成受访职场人表示自身处于“灵活机动加班”机制中,他们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并不分明,84.7%的人在下班后,仍会关注工作相关信息。(1)《拒绝加班,到底有多难?》,2023年4月18日,https://news.sina.com.cn/zx/2023-04-18/doc-imyquezs8736001.shtml,2023年4月26日。在英国,根据“工会繁荣”(Trade Union Prospect)2021年4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来,35%的在家工作的上班族表示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所下降,其中超过40%的人认为这一问题与无法停止工作有关,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在工作时间之外查看电子邮件。(2)Umberto Bacchi, “Right to Disconnect Gains Ground as Pandemic Brings Work Home,”April 29, 2021, https://news.trust.org/item/20210429025351-xotsy, March 3, 202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4月14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危机期间及之后的远程工作安排》(Teleworking Arrangements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and beyond),全球有1/4的劳动者说自己必须在休息时间工作以应付额外的任务,而在疫情流行之前,这一比例在欧盟国家仅为5%。(3)Luiza Lungo, “The Right to Disconnect—A Necessary Demarc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Private Life,” Conferinta Internationala de Drept, Studii Europene si Relatii Internationale, vol.20, no.1 (March 2021), pp.176-181.可见,一方面,受惠于数字通信设备的瞬时性和便捷性,如今劳动者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拘束,从而获得平衡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自主性,摆脱办公室文化的羁绊;然而另一方面,正如法国立法委员会成员内努瓦·哈蒙(Benoit Hamon)所言:“劳动者离开了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离开工作……短信、消息、电子邮件,它们殖民了个人的生活,直到让人崩溃为止。”(4)Tyler Jochman, “Effects on Employees’ Compensation under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Marquette Benefits &Social Welfare Law Review, vol.22, no.2(Spring 2021), pp.209-224.用人单位利用数字通信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劳动者处理工作事务,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长期性甚至永久性的“待命”员工。为因应劳动者难以从工作中离线的现象,域外发达国家在立法和实践中逐渐重视对劳动者离线权的保护,它是指在非工作时间不从事与工作相关活动的权利。由于离线权的产生与数字通信活动有关,因此其内涵更多的是脱离数字通信的权利。据此,本文以文献分析的方式,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1) 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到底会对劳动者产生怎样的影响?(2) 离线权的提出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3) 域外国家是如何通过赋予劳动者离线权来应对数字化工作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4) 基于本土状况和域外经验,我国劳动立法是否应当及如何规定离线权?
一、 “难以从工作中离线”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与离线权的提出
(一) “难以从工作中离线”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
现代社会工业发达,分工极细,工作程序变得简单,工作不仅单调,且非常紧张,如工作时间不予限制,被雇者的身体及精神将因长期劳动而过度疲劳,道德与智识亦将受其影响而日渐衰落。(5)马超俊、余长河: 《比较劳动政策》,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70页。随着数字通信设备的普及和远程工作的兴起,“难以从工作中离线”的现象日渐突出,劳动者在任何时间段和任何地点都需要与用人单位和同事保持联系。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我国大量劳动者开启居家远程工作模式(6)疫情期间的2020年2月3日当天,我国有上千万家企业、近两亿人开启在家远程办公模式。参见王鹏: 《远程办公不误工》,《人民日报》 2020年2月11日,第5版。,但却由于难以从数字通信设备中离线,居家办公时,工作与生活并没有边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难以与工作时间断开的紧张状态会对劳动者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第一,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延长。理论上,科技的进步及普及和工作时间的缩短成正比。科技的进步与普及会提升人类整体的工作生产效率,通过将大量繁杂的重复性的工作交给机器来完成,可以使得人们有更多的私人生活时间。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7)以赛亚·柏林: 《卡尔·马克思: 生平与环境》,李寅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信息化时代的通信设备也包含着自己的反面: 一方面,数字通信设备的发展提高了工作安排的灵活性,从而有助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正是拜数字通信设备所赐,在劳动者下班后的私人生活时间中,如今也充满了如微信工作小组交流、邮件传递等与工作相关的各种活动,导致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其私人生活时间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工作时间在数字通信设备中从未真正结束,工作逐渐单向度地变成了生活的代名词。
第二,用人单位劳务指挥权的强化。在劳动合同中,劳动者有提供劳动力的义务,相应的用人单位则有提供劳动报酬的义务。然而,在劳动合同成立之际,合同双方对于劳动者究竟如何具体地提供劳务往往未必有明确的合意,而有待用人单位的指示。因此,用人单位拥有所谓的劳务指挥权作为其固有的权限。换言之,劳动关系乃是一种以劳动力为对象的继续性债之关系,用人单位基于人事管理、产品或服务品质管理及财产保全等目的,势必要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通过劳务指挥权对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进行指导和监管。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机器的生产力,资本正在开始新一轮的时空修复和剥夺性积累: 高度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不仅使得工作场所变得不再固定,也使得工作时间变得更加弹性化。(8)黄再胜: 《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危机、资本应对与数字劳动反抗》,《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5期,第124—131页。这些变化进一步强化而非减弱了用人单位的劳务指挥权: 一方面,在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工作场所不再囿于那些沉重的用墙壁围起来的工厂中,有智能手机和电脑的地方就是工作场所。数字通信设备交流的“瞬时性”意味着空间的贬值(9)成素梅: 《智能社会的变革与展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8卷第4期,第9—13页。,逼仄的工厂空间不再对劳动者的行动及其绩效产生约束,劳动者不仅可以在家中工作,也可以在旅途和假期中工作。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原本只出现在工厂中的劳务指挥权不仅可以出现在劳动者的家中,也可以出现在劳动者的旅途和假期中。另一方面,在传统的福特主义工作模式下,劳动者必须在用人单位规定的固定时间点上下班,并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完成一定量的工作。然而,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中,以往的工作时间的计算逐渐变得模糊,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越来越杂糅,这也意味着用人单位劳务指挥权越来越出现在劳动者的生活时间中。用人单位通过数字通信设备在下班后联系劳动者,无论是以强迫性的语言,还是商讨性的语言,即使在劳动者有空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都会使劳动者承受巨大的继续工作的压力。
第三,有损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借助数字通信设备,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下班后继续安排工作任务,虽然便于即时解决问题,但会导致“工作场所的电子压力”,即劳动者在下班时间无法充分休息,难以恢复自己所消耗的与工作相关的资源,给劳动者情绪状态、身心状态造成不利影响(如压力感、疲惫感、负面情绪、血压升高等),甚至可能导致劳动者难以从前一天的疲倦状态中恢复,进而更可能使得工作压力状态持续恶化,造成胃痛、头痛、睡眠障碍、抑郁等症状。(10)纪乃文、蔡宜衿: 《主管下班别LINE我: 探讨下班后用通信软件交办困难工作对员工后续负向心情、压力状态及任务绩效的影响》,《管理学报》2018年第3期,第307—331页。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之前的众多研究表明,持续工作文化是精神和身体不健康的主要原因和加速器。研究显示,晚上9点后回复工作信息的人睡眠质量较差,第二天的工作参与度较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截至2020年底),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劳动者中的精神困扰病率比2017—2019年期间高出49%,并且在除了农业、林业和采矿业以外的所有主要行业中都有所增加。(11)A. Valcelaru, “The Psychosocial Risks Encountered by Employe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ight to Disconnect,”Analele Stiintifice Ale Universitatii Alexandru Ioan Cuza Din Iasi Stiinte Juridice, vol.67, no.2(October 2021), pp.231-250.越来越清楚的是,在数字工作中过度使用技术设备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增加技术依赖,剥夺睡眠时间,导致情绪低落、焦虑和极度疲劳等现象。如果放任用人单位在下班后仍可随时联系劳动者,的确会对劳动者造成潜在的、持续的精神压迫和心理压力,从而给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造成显著影响。
第四,劳动者下班后的工作行为难以被认定为加班。传统劳动立法,包括加班时间的认定,很难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对劳动关系所带来的冲击,“现有立法是以传统的、一般的、典型的劳动关系为规制对象而诞生和发展起来,面对当代社会发展中呈现的就业和用工的多元化、灵活化趋势,显得力不从心”(12)石美遐: 《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研究》,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年,第25页。。相比之下,在网络信息技术助推下的信息化时代,劳动法所受到的冲击较以往更加特殊和具有颠覆性。(13)田野: 《劳动法遭遇人工智能: 挑战与因应》,《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57—64页。我国现行《劳动法》第36条规定了每天不超过8小时的工时制度,第41—44条则分别规定了加班的条件、加班的限制和加班费的给付。2010年9月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2020年12月最高法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4条进一步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然而,这些法律规定却难以解决下班后用人单位通过数字通信设备要求劳动者额外工作的问题。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劳动者在数字通信设备中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是否能认定为加班,存在较大的分歧。
在刘艳与上海湛盛贸易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14)参见(2020)沪0118民初437号。中,原告刘艳的第4项诉讼请求为,下班后被告在聊天软件上和其聊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属于加班。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被告确实存在于法定工作时间外安排原告工作的情形,因而酌情认定原告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3日期间存在10小时的延时加班。2019年6月23日后不认定存在加班情形,是因为2019年6月24日后被告实行钉钉考勤,加班需在系统中进行申请,原告并未申请。在中国地图出版社与孟慧丹劳动争议一案(15)参见(2019)京02民终5125号。中,原告孟慧丹为证明存在2017年9月26日延时加班,向法院提交微信截屏。微信截屏显示在2017年9月26日21时36分至22时14分之间,在名称为“群聊(5)”的微信群中,发送了大量与工作相关的内容信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当晚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其为完成工作任务延时加班6小时的主张,该出版社应支付孟慧丹9月26日延时加班工资,具体数额由该院依法核算。在晏金逃与金华市康源鞋服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16)参见(2020)浙0703民初1811号。中,原告晏金逃提交了周六、周日、节假日,晚上6点到10点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拟证明周六、周日持续的聊天记录都是工作内容,晚上、周六、周日、节假日有加班的事实。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虽存在部分下班后、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有关工作的内容,但聊天记录中涉及语音聊天的内容缺失,现有证据不足以直接证实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可见,由于法律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的,自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用人单位存在加班申请制度时,如果劳动者没有申请,即使劳动者为完成用人单位下班后通过微信等即时通信软件交代的工作而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也难以被认定为加班时间。显然,数字通信的即时性、隐蔽性和模糊性,导致劳动者事实上难以通过用人单位的加班申请,从而使得劳动者工作时间被“变相”延长的同时难以获得加班费。
(二) 劳动者离线权的提出及其社会意义
因为用人单位越来越频繁地通过数字化方式在非工作时间向劳动者在线发布工作指示,近年来一些国家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离线权,这一权利通常也被称为“不被联系的权利”或者“失联权”。具体来看,离线权的核心权利诉求包括两点: 一方面,保障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不受用人单位打扰的权利,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收到用人单位信息的可以不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劳动者不回应在非工作时间收到的用人单位发来的信息后,用人单位不能对劳动者做出不利的处罚。法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来保障劳动者离线权的国家,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了关于劳动者离线权的辩论。(17)离线权的概念最早来自法国最高法院劳工庭的一个决定,该决定(2001年10月2日作出)认为:“雇员没有义务接受在家工作,也没有义务将资料和工作所需的工具带回家中。”2004年法国最高法院支持了这一决定,并裁定:“(员工)在非工作时间无法通过手机联系不能被视为员工的不当行为。”随后,于2016年8月修改劳动法典,正式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离线权。不得不说,如此明确地在立法中规定劳动者离线权,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一,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正义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是测量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尺标。作为法律秩序的重要一环,劳动法所标榜的,就是一个清晰的正义价值秩序决定: 基于结构上劣势的劳动者之保护,直接通过国家公权力限制强势用人单位的支配、指挥和监督权。为确保劳动者拥有最起码的合乎社会正义的自由、平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权利,世界各国纷纷将休息权明确纳入宪法之中予以确认和保护。与此同时,劳动者休息权也逐渐在国际法律领域中获得广泛的认可。我国《宪法》第43条同样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然而,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中,劳动者的休息权无可避免地被随时在线的数字通信设备所侵犯。离线权益让劳动者在白天高速运转之后,晚上在家里获得充分的休息,重新“加满油箱”,以便第二天的工作。因此,劳动者离线权提出的实质目的就在于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将用人单位“脱嵌”的经济行为,重新纳入劳动法的规制范围,以改变互联网时代中强势资本压榨弱势劳动者的“弱肉强食”现象。
第二,有助于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劳动者通过在一定工作时间内付出自己的劳务来换取一定的工资固然重要,但是能保留给自己以及家人一定的生活时间也同样重要。工时过短,不但影响整体生产力,劳动者也可能无法维持生活;工时过长,劳动者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变得十分有限。(18)黄越钦: 《劳动法新论》,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我国劳动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似乎更多的仅仅是一种吸引人的学理概念,大量用人单位通过数字通信设备以过多的加班时间或持续性的压力破坏了劳动者的私人生活。正如相关学者在论述人与科技的关系时所提到的那样,“人工智能增强了人的理性力量,而高度发达的理性很可能会牺牲人的情感和灵性,从而使人单向度发展,使人性失去平衡”(19)於兴中: 《人与科技: 从智能间的平衡到人性的平衡》,《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55—64页。。在数字通信设备等科技产品大量使用的情况下,劳动者似乎被企业看作是一台可以连续、重复运转的工作机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者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工作机器。对劳动者来说,只有在工作活动停止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20)卡尔·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页。。因此,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只有在整个社会为了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共同福利而把人们拥有满足工作内和工作外生活需要当作一种规范性权利时才能够实现。赋予劳动者离线权,就是让劳动者通过断开网络、关闭电源以减少工作时间对生活时间的捆绑。
第三,有助于转变用人单位的观念。无论是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还是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其实现的前提都需要用人单位转变观念,即用人单位不将自己视为劳动者工作与生活中的最高权威,而是将自己视为鼓励健康生活、健康工作方式的可靠伙伴(21)崔聪聪、许智鑫: 《机器学习算法的法律规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8卷第2期,第35—47页。。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职业健康: 工作场所中的压力》(Occupational Health: Stress at the Workplace),该报告指出,为了创造健康的工作环境,企业必须有大量的促进健康的条件,其中一个关于促进健康的条件的例子就是实施下班后的沟通政策(after-hours communication),以使劳动者越来越沉重的工作压力有所减轻。以德国为例,大众、宝马和彪马等企业均对主管何时可以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向劳动者发送电子邮件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尤其是大众汽车公司规定下班30分钟后不得给劳动者发送任何电子邮件。因此,劳动者离线权的提出,有助于改变用人单位的观念,重塑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得用人单位在追求“物的生产”和超额利润的同时也注重“人的再生产”。
二、 域外经验: 劳动者离线权的具体建构模式及其利弊分析
随着数字通信设备在工作领域的普遍运用,欧盟国家的劳动者在休息时间仍在继续工作的比例也在逐渐上升。尽管自1995年以来许多欧盟国家周日工作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自2005年以来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周日在工作的劳动者比例却由27.5%上升至2015年的30%。(22)朱晓峰: 《数字时代劳动者权利保护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0卷第1期,第37—55页。尤其是,2020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迫使大量公司和组织转向远程工作。Eurofound2020年4月的调查显示,37%的受访者选择了居家办公。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在家完成工作的人平均每周加班6小时,而从未在家工作的人平均每周加班3小时。(23)Luiza Lungo, “The Right to Disconnect—A Necessary Demarc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Private Life,”Conferinta Internationala de Drept, Studii Europene si Relatii Internationale, vol.20, no.1(March 2021), pp.176-181.在德国,由于数字化的居家工作,56%的员工的工作量增加了,33%的员工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24)Olga Chesalina, “The Legal Nature and the Place of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in European and in Russian Labour Law,”Russian Law Journal, vol.9, no.3(June 2021), pp.36-59.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2016年)、意大利(2017年)、西班牙(2018年)、比利时(2018年)、斯洛伐克(2021年)、希腊(2021年)、葡萄牙(2021年)、爱尔兰(2021年)等国家开始采取积极措施,以规范工作领域中数字通信设备的使用,从而为劳动者平衡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提供保护。
(一) 法国: 不分类别的立法模式
在所有保障劳动者下班后享有不受雇主打扰权利的国家中,法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法国劳动部部长米莉雅姆·埃尔-库姆里(Myriam E-Khomri)在广泛听取专家关于正在兴起的数字时代报告意见后,着手对劳动法典进行修改。在这些报告中,由布鲁诺·梅特林(Bruno Mettling)起草的名为《数字化转型与工作生活》(Transformation Numérique et Vie au Travai)的报告,特别关注和论述了劳动者的离线权。(25)Matteo Avogaro, “Right to Disconnect: French and Italian Proposals for a Global Issue,”Law Journal of Social and Labor Relations, vol.4, no.3(September/December 2018),pp.110-129.在这样的基础上,2016年8月法国正式修改了劳动法典,并获得议会通过。修改后的劳动法典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由此法国大多数企业将在大部分情况下不被允许下班后联系劳动者。
修改后的法国劳动法典在集体劳动关系部分对离线权做出了规定,因此离线权的规定属于“团体协商”(第L2211-1至L2283-2条)中的“强制谈判范畴”(第L2241-1至L2243-2条)。(26)邱羽凡: 《当前劳工离线权之理念与实务——以欧盟国家之发展为参考》,《月旦裁判时报》2022年第8期,第88—99页。根据这些规定,劳动者可以行使他们的离线权(droitla déconnexion),企业应当有关于规范数字工具使用的制度,以确保尊重劳动者的休息休假、个人和家庭生活。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企业应当与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协商起草相关章程。该章程应当规定劳动者行使离线权的方式,并进一步规定对劳动者、企业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相关意识。对于法国这一开创性的法律规定,仍有进一步说明之必要。第一,小企业不适用此条规定,它只对拥有50名以上劳动者的企业有效,人数少于50人的企业可以向劳动者发布概述离线权相关规定的文件。第二,允许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和企业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年度强制谈判协议),这项“良好行为章程”(charters of good conduct)协议应当详细说明员工不希望通过数字通信设备与雇主联系的时间,脱离电子办公工具的时间,以及对非法行为的制裁,从而加强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规制远程工作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第三,为了体现现实中的各种不同情况,立法者只做出了一项一般性的规定,将离线权的详细规则交给雇主和工会或者员工代表来协商制定,以实际确定雇员如何行使离线权,如果没有达成具体协议,雇主必须执行离线权政策,包括培训计划,告诉雇员在工作时间之外合理使用数字设备,并监测离线权的遵守情况。第四,法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对不遵守以上规定的公司进行制裁,但当劳动者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受法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立法模式来明确保障所有劳动者的离线权。2018年比利时出台了《关于加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的法案》,其中第15—17条规定了离线权。根据该法案,与离线权相关的工作场所中的数字通信问题应当在预防和保护委员会内讨论,该委员会是一个员工代表机构,其必须在员工人数超过50人的企业中选举产生。为了确保劳动者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该法案进一步规定,年休假和其他非工作时间必须得到尊重,为此雇主应当定期应预防和保护委员会的要求就离线权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2018年12月6日,西班牙颁布《数据保护法》,其第88条规定了离线权并且明确这一权利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劳动者和所有类型的工作活动。2021年4月,爱尔兰成为在立法中明确离线权的国家,该国立法对离线权的权利主体同样采取的是不分类别的模式。(27)Luiza Lungo, “The Right to Disconnect—A Necessary Demarc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Private Life,” Conferinta Internationala de Drept, Studii Europene si Relatii Internationale, vol.20, no.1(March 2021), pp.176-181.
(二) 意大利: 特定类别的立法模式
受法国的影响,意大利关于智能工人(smart workers)离线权的立法辩论开始于2016年,其监管的趋势是通过集体谈判和公司惯例来予以规制。2016年意大利政府提出了两项关于智能工作纪律框架的建议,即第2229号和第2233号法案。(28)Matteo Avogaro, “Right to Disconnect: French and Italian Proposals for a Global Issue,” Law Journal of Social and Labor Relations, vol.4, no.3(September/December 2018), pp. 110-129.其中,第2229号法案第3条第7款明确承认了离线权,以表明雇员有权在下班后断开与数字通信设备的联系,而不用承担任何不利后果。第2229号法案第16条进一步规定,离线权只涉及智能工作领域中的雇员与雇主之间签订的强制性协议,对协议双方而言,有义务说明相关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以确保员工下班后有权与数字通信技术设备断开联系。随后在2017年5月10日通过的第81/2017号法案中,第19条规定必须规范工人可以在工厂外进行的活动、实现公司绩效所需的电子仪器和设备以及雇主在这些仪器和设备中行使其指示权的方式。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了智能工人其他相关的一系列权利,如第21条的限制雇主控制权,第22条健康和安全的权利,以及第23条的对工伤和职业病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延伸适用于工厂外进行的工作活动。(29)Matteo Avogaro, “Right to Disconnect: French and Italian Proposals for a Global Issue,” Law Journal of Social and Labor Relations, vol.4, no.3(September/December 2018), pp.110-129.
与意大利的立法类似,智利也只规定特定类别的劳动者享有离线权。根据智利的立法,如果远程工作人员制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那么雇主必须尊重他们的离线权,保证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不必回复工作消息。此外,阿根廷和斯洛伐克也同样只规定了远程劳动者才享有离线权。根据斯洛伐克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劳动法(修正案)》的规定,从事远程工作的劳动者享有离线权,雇主不能认为他们在离线期间拒接工作属于违反劳动合同。(30)Alexandra-Georgiana Vlc elaru, “The Psychosocial Risks Encountered by Employe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Analele Stiintifice Ale Universitatii Alexandru Ioan Cuza Din Iasi Stiinte Juridice, vol.67, no.2(October 2021), pp.231-250.可见,意大利等国家虽然部分效仿了法国的立法模式,但是这些国家立法中离线权的权利主体限定为特定类别的劳动者。这主要是因为离线权对传统工作时间较为固定的员工而言并无多大实质意义,他们往往和雇主有明确固定的工作时间约定,不管法律是否规定离线权,依据现有法律雇主通常不能在雇员下班后向其发出工作指示,相反,智能工人、远程工作人员等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劳资双方常常对于工作时间没有明确的约定,雇主可以随时通过数字通信设备联系员工。
(三) 德国: 自我规制模式
德国在保障劳动者下班后不受用人单位打扰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德国就业部部长Andrea Nahles自2014年起就一直呼吁制定“反压力法”(anti-stress law)。(31)Rich Haridy,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The New Laws Banning After-hours Work Emails,” August 14, 2018, https://newatlas.com/right-to-disconnect-after-hours-work-emails/55879/, April 16, 2023.不过,与法国采取立法模式不同的是,德国企业可以选择参加非强制性的自我规制政策,以使得这些政策尽可能地符合个人或行业的需求。具体来说,德国并未在法律中规定离线权,但是雇主协会可以与工会、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合作,制定适合特定雇员和雇主需求的政策。德国联邦政府认为,员工下班后天然地不负有为雇主服务的义务,因此也就没必要通过立法来明确规定离线权,(32)谢增毅: 《远程工作的立法理念与制度建构》,《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248—268页。采取这种集体协议的方式而非单独立法的方式来对工作场所进行监管更为合适,更能平衡劳动者的利益与雇主的需求。早在2012年大众汽车就率先在德国规定,下班后(晚上6点15分至次日早上7点之间)关闭公司的电邮服务器,以限制员工下班后利用即时通信设备工作的情形。2014年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Daimler)公司规定,个人在休假期间可以删除所有收到的电子邮件。这样做的目的,乃在于保证员工假期不被中断,同时可以使员工假期结束后自信地返回工作岗位,不会因为工作邮件被塞满而过于忙碌。除了像大众汽车公司和戴姆勒公司这样的规章协议外,德国劳工部在2013年8月30日也制定了公司下班后的沟通政策,以鼓励其他企业效仿。劳工部的该政策禁止企业在工作时间以外与员工进行任何工作交流,但紧急情况除外。比大众汽车等企业的规章协议更全面的一点是,该政策还规定了不允许企业经理对因下班后关闭数字通信设备而未能回复信息的员工采取不利的处分。
(四) 域外模式的利弊分析
首先,总体来看,各国对劳动者离线权的建构模式仍在起步阶段,且实践差异较大。2021年1月21日,欧洲议会达成了一项关于离线权的决议,鉴于各成员国实践的差异,该决议对离线权的界定、监管水平(立法或集体协议)和使用范围没有使用统一的办法。事实上,目前将离线权明确规定在立法中的国家仍为少数,大多数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等认为现行法律规范可以解决企业下班后让劳动者变相加班的问题,或者即使不能解决,也由于离线权的复杂性,而采取“让子弹飞一会”的消极不管理态度。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则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均认为需要采取积极行动来减轻数字化工作方式给劳动者带来的持续的工作压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各国相关措施均在起步阶段,仍有诸多不成熟之处,比如这些国家大多都没有试图确定劳动者享有离线权的确切时间。对此,“法国经济人联盟”主席米歇尔·德拉·福斯就曾表示:“我们必须测出数字时代的工作时间。我们承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加班,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必须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和短暂休息,避免总是在工作。”(33)林海: 《法国:“下班后的时光是神圣的”》,《检察风云》 2014年第18期,第54—55页。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4月14日,西班牙工会诉德意志银行一案,欧盟法院判决认为,有必要记录员工的工作时间,以便适当适用单个工作时间限制。没有一个能够衡量每个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短的制度,就不可能客观和可靠地确定工作时数和完成工作的时间,也不可能确定加班时数。See Federacian de Servicios de Comisiones Obreras (CCOO) v. Deutsche Bank (ECJ C-55/18).值得肯定是,无论是何种模式,各国均认识到了不同行业的差别,比如对于某些类型的行业,其本质上要求员工与雇主合作,需要经常在下班后保持工作联系。以法国为例,其做法主要是,在立法中做原则性的规定,为雇主制定适合各自行业的政策留下了灵活的空间,但这一做法却由于未能充分谴责违反法律的雇主而备受批评,即如果雇主选择不就离线权与员工进行谈判,法律也不会对雇主做出实质性惩罚(34)谢智菲: 《信息化办公时代劳动者的离线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0年第34卷第2期,第91—97页。。
其次,特定类别的立法模式与不分类别的立法模式相比,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离线权的主体是否做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不分类别的立法模式而言,无论从事何种性质的工作,只要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便都享有离线权。然而,有疑议的是,对于那些适用传统标准工作时间的劳动者而言,欧盟劳工法(或相应国家的劳工法)已经明确规定并保证了最长的工作时间,雇主在下班后要求这些员工工作的情况,直接认定为加班即可,为何还需要引入离线权?如果雇主以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不回复短信为由将其辞退,构成违法解雇,以及如果要求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通过通信软件或在线执行工作任务,应认定为加班,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规定这类劳动者享有离线权?这主要因为: 一方面,劳动者可以明确有权拒绝在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者可以实现权利的自我保护;另一方面,规定所有劳动者享有离线权是一种补救措施,通过法律的规定,雇主不仅应当履行在非工作时间不打扰劳动者的消极义务,更应当履行采取适当措施来为劳动者行使其离线权提供便利的积极义务,从而可以防止雇主滥用权力。(35)Olga Chesalina, “The Legal Nature and the Place of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in European and in Russian Labour Law,” Russian Law Journal, vol.9, no.3(June 2021), pp.36-59.因此,如果仅仅规定某些特殊类别的劳动者享有离线权,将传统标准工时的劳动者排除在离线权之外,就意味着雇主对这些劳动者没有相应的积极义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最后,德国虽然没有在法律方面明确劳动者享有离线权,但却提倡雇主采取自律的方式允许工会与相关社会协会或政府部门进行协商讨论,以制定符合各方需求的行业规则。不过,德国这种自我规制模式的风险在于,雇主会制定表面上有利于劳动者的规制,但却对劳动者起不到实质性的保护作用。此外,由于并没有法律要求雇主对劳动者离线权进行自我规制,因而虽然有一些雇主,如大众、宝马和彪马等企业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但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在德国,雇主与劳动者下班后的工作交流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不仅如此,直接从公司服务器关闭网络的做法,并无法减轻劳动者的工作量,甚至可能导致劳动者更多的焦虑,因为第二天上班时可能收到大量的邮件,反而形成更多的工作负担。
三、 本土建构: 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保护路径
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进程来看,有关劳动者工作与生活平衡、劳动者休息权保障的问题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注定会成为全球性问题。尤其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引起的大量劳动者突然开启的居家远程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数字通信设备在工作场所中的普及和使用,加剧了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二者界限的模糊程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尝试通过保障劳动者的离线权来破解此一新型问题。从域外的立法实践来看,发达国家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适时针对劳动者离线权进行了改革创新,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数字化时代中,我国较为缺乏从保障离线权的理念出发来解决劳动者私人生活与工作时间的冲突。在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方面,我国劳动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暴露出结构性缺陷。为更好地保障弱势劳动者在数字化时代中免于被用人单位过度榨取,我国也应当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者的离线权。
(一) 我国劳动者的离线权宜通过立法模式予以保护
目前,欧盟各国对通过立法规定劳动者离线权的必要性还缺乏共识,在欧盟层面尚未规定劳动者的离线权,但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部分成员国已通过法律规定了此项权利,从而可能导致欧盟内部的不公平竞争。(36)张伟栋、伯瑞儿·哈尔: 《欧盟工作时间规制的历史发展与法律构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1期,第58—68页。德国之所以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离线权,主要是因为德国联邦政府认为本国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则比较完善,集体协商机制较为发达,法律是否规定劳动者享有离线权并不重要。(37)谢增毅: 《远程工作的立法理念与制度建构》,《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248—268页。然而,近年来,由于自我规制模式下所制定的行业规则并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实质性的保护,德国学者要求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离线权的呼声也在逐渐增多。就我国而言,由于集体协商机制相对欠发达,通过立法明确劳动者的离线权,并要求用人单位与工会或劳动者代表就劳动者离线权做出具体的规则安排,对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平衡劳动者工作与生活、转变用人单位观念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此外,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第1033条明确了对公民私人生活安宁权的规定,即“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 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生活安宁……”应当说,《民法典》的这一规定也为劳动法确立离线权提供了一定的指引和参考。
(二) 我国离线权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从域外的经验来看,有关离线权的讨论基本上与远程工作密切相关。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远程工作人数在疫情期间比以前增加了数倍。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学界在远程工作立法方面虽然已有较多研究,但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因此更不用说研究成果尚较少的离线权,其立法方面的共识在我国仍然相当薄弱。不仅如此,离线权的产生背景是数字科技融入新的工作方式,但数字科技的运用是否已经改变了包括传统产业、行业在内的所有工作组织形式,以至于如果不通过设置一般性的离线权,无法摆脱当前的现实困境?以及即使必须通过立法来摆脱数字化工作带来的困境,但我国应当具体采取不分类别的立法模式,还是特定类别的立法模式?这些问题尚缺乏全面性的评估与研究。
此外,在考量我国离线权立法的可行性问题时,还应当注意,通过立法推行劳动权往往容易造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推行相关立法时应当采取一种共同协作的态度: 强调既是雇主与劳工的权利也是责任,而因应这种新诠释的劳资关系,则需要提供一种使用数字科技的新形式的教育方式,让劳资双方因了解数字科技滥用所造成的风险,而意愿从行为层面去改变使用习惯。(38)刘黄丽娟: 《数位科技对工作世界的挑战: 以法国对于工时规范之讨论为例》,《劳动关系论丛》 2018年第1期,第62—78页。进言之,离线权的有效实施不仅取决于法律要求,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如企业文化,雇佣关系类型(标准关系还是非标准关系),是否在不同的时区工作,工作强度,衡量工作时间的方式,能否通过劳动检查对侵犯这项权利加以有效制裁。(39)Olga Chesalina, “The Legal Nature and the Place of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in European and in Russian Labour Law,”Russian Law Journal, vol.9, no.3(June 2021), pp. 36-59.因此,通过立法来建构我国劳动者离线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即能完成的事业。然而,因用人单位下班后通过数字通信设备交付工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我国也应当尽早通过立法来保障劳动者的离线权,以平衡劳动者的工作生活与私人生活。
(三) 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基本立法框架
未来应当如何建构我国劳动者离线权的基本立法规则?相关的立法细节应当如何展开?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劳动者的离线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休息权,可以规定在休息权条款中。离线权并不是一项初始权利,而是一项派生性权利,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休息的一项权利。(40)谢增毅: 《离线权的法律属性与规则建构》,《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11期,第35—49页。我国《劳动法》第4章第36—45条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些规定表明,在劳动关系中,虽然时间是劳动者义务计算的单位,通过市场选择,劳动者以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的方式将自己劳动力使用的机会让渡给了用人单位,这就是工作时间,但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应当属于劳动者的休息时间。(41)沈建峰: 《劳动法上休假的法学构造与谱系》,《法学》 2021年第10期,第154—166页。因此,为解决信息化时代中我国劳动者“永远在线”的问题,立法者可以在《劳动法》第4章增加一条劳动者离线权的规定,即“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中享有离线权,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在约定的工作时间之外回复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或在线执行工作任务”。
第二,在对劳动者离线权做出明确规定后,还应当意识到,某些类型的行业及相关工作岗位本质上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下班后仍保持高频率的联系,比如那些在不同时区工作或需要国际旅行的劳动者。因此立法不宜规定得过于僵化,应当允许一定的例外,而这样的例外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当事人的自治能力,交由行业协会和工会、政府部门等组织和机构一起协商决定,促使劳动者离线权的保障更加弹性以符合多样的现实。毕竟,通过立法规定劳动者享有离线权看上去很美,但要真正落实劳动者离线权却不容易,各国的经验均是宜粗不宜细,详细的规则则交由企业与各方一起协商落实,以具体确定什么是正常工作时间以及非工作时间。质言之,离线权应当是灵活动态的,允许某些用人单位选择退出,但这一应对是例外规则,希望选择退出的用人单位必须充分说明不应施行离线权政策的理由。
第三,在协商落实具体规则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劳动者真实的意思表示,避免制定的规则实质上有损劳动者权利的保障。换言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某类行业的用人单位确实有下班后与劳动者保持联系之必要,否则难以行使其劳务指挥权,但是劳动者不愿意用人单位频繁通过数字通信设备联系自己,应当如何处理?笔者以为,对于这些特殊的行业或岗位,让劳动者提前知道自己的工作需要什么,是平衡其工作和生活的关键。这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应当在相关的规章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并在招聘时向劳动者予以充分说明并取得劳动者的同意。对于不同意的劳动者,用人单位自然可以基于雇用自由原则,对其不予录用。
第四,设置反用人单位报复的条款,如此劳动者才可以向政府自由地提出有关下班后用人单位给自己安排工作的投诉,而不必受到惩罚。域外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离线权的一个关键特征就在于,如果劳动者行使离线权,他们将受到保护,免受惩罚。具体而言,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下班后的沟通交流政策,其中明确规定不允许用人单位对因下班后关闭数字通信设备而未能回复信息的劳动者采取不利的处分(例如不考虑晋升、加薪等报复行为)。如果劳动者认为,一旦抱怨下班后过度的电子工作信息,他们会被用人单位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进而在工作场所被孤立和疏远,并有可能被降级,甚至被辞退,那么无论怎么通过立法来规定劳动者享有离线权都不会有实质效果。(42)Paul M. Secunda, “The Employee Right to Disconnect,” Notre Da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vol.9, no.1(February 2019), pp.1-39.
(四) 鼓励用人单位制定下班后的交流政策
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增加人的自由。在下班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数字通信设备交流工作这样看似新颖的问题中,往往还存在旧式的不平等,即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支配和控制。用人单位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利用自身的强势优势,通过数字通信设备变相让劳动者无形加班,不仅会导致劳动者工作效率低下,更会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与社会发展的应然趋势相悖离。(43)贺丹: 《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8卷第4期,第23—26页。由于劳动关系具有隶属性,用人单位会借助强势地位直接或间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取最大利益,甚至置劳动者的生理极限而不顾。(44)李炳安: 《我国劳动工时和休息休假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制度完善》,《社会科学研究》 2017年第5期,第103—109页。因此,政府应当指导和鼓励用人单位制定下班后的交流政策,尤其是针对那些下班后沟通交流特别频繁的行业,如互联网行业、医疗行业、法律行业等,以推动用人单位转变观念,制约用人单位的恣意行为。具体做法可以包括: 首先,政府可以采取激励政策,对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用工企业颁发荣誉证书,进行税收减免(45)周湖勇、钱伟: 《互联网时代劳动者离线权保障探究》,《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1卷第5期,第3—10页。;其次,对那些社会责任感较差的企业进行训诫教育,必要时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监督;最后,对于制定下班后交流政策的用人单位,政府还应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培训,以增加各方相关的法律意识,避免或减少下班后通过数字通信设备交流工作的事情发生。
(五) 加班规则与工作时间的认定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是,在用人单位通过数字通信设备要求劳动者变相加班的诉讼中,由于我国加班规则的滞后性,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无偿加班,难以获得加班费。为此,在离线权诉讼中可以适当翻转劳动者主张加班费应当由劳动者举证的规定,并对相关的电子数据进行专门化的分析。在数字通信设备中明显存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加班,劳动者也存在事实上的加班时,应当认定为加班,如上文中提到的中国地图出版社与孟慧丹劳动争议一案,法院并未考量劳动是否需要经过申请加班程序,而是直接以劳动者提供的微信消息认定了劳动者存在加班的事实。尤其是,在特殊行业和特殊岗位中加班规则更应当做有利于劳动者的调整。在此类纠纷案件中,对于加班规则的认定,对应当由主张加班费的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则可作适当调整,即依据个案的情况,由用人单位就举证不充分承担不利后果责任,如此才能更好地达到劳动者离线权和用人单位劳务指示权的平衡。
在数字化的工作方式背景下,下班后通过数字通信设备完成工作任务却难以被认定为加班的本质问题在于,数字科技在工作场所的运用使得从属关系从工作场所延伸到私人空间,从法定的工作时间延伸到生活时间。因此,如何限制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工作,如何妥善处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私人生活时间之间界限的模糊化,以及如何解决限制未记录工作时间的问题,是未来工时立法的重点。为此,有学者提出引入“第三时间”的概念,即既不是工作时间也不是休息时间,或者换句话说,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间的中间类别。(46)Olga Chesalina, “The Legal Nature and the Place of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in European and in Russian Labour Law,” Russian Law Journal, vol.9, no.3(June 2021), pp.36-59.然而“第三时间”的引入会打破传统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视为互相排斥的做法,即生活时间是指非工作时间以外的任何时间。因此在离线权诉讼中加班规则认定的关键措施仍然是测量工作时间的制度规定。为了更有效地实施离线权,有必要配套要求用人单位建立一个客观、可靠和可访问的系统,以测量每个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47)欧盟法院有两个典型案例对支持劳动者离线权而言意义重大,即在案件C-518/15的判决中,欧盟法院认为必须在短期内回复雇主电话的工人在家的待命时间应当被视为“工作时间”(2018年2月21日);在案件C-55/18的判决中,欧盟法院提出欧盟成员国必须要求雇主建立一个系统,以测量每日工作时间的持续时间(2019年5月14日)。
结 语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数字通信设备使得在线交流变得无时无处不在,不仅导致了劳动者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增加了劳动者的倦怠感。忙碌的生活早已使越来越多的弱势劳动者沦为失去自我、失去灵魂的“契约奴隶”或机器: 每个人都有大量的时间工作,但却没有时间进行家庭或休闲活动,更没有时间对自己、他人乃至整体社会进行反思性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劳动者离线权的规定和保障成为这个时代必要且迫切的事项。为此,我国可以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离线权,以使得劳动者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工作更具体面性和自主性,劳动者能真正因为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所包含的人性化的、解放性的潜力而受益,而不是毫无尊严地被数字技术甚至人工智能所奴役、取代和抛弃(48)吴汉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28—136页。。有鉴于数字通信设备对工作领域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方面的影响,未来我国劳动立法应当进行必要的变革,以更具深刻性和远见性的制度设计来全方面地保障劳动者的离线权。应当说,通过立法明确保障劳动者的离线权并不是平衡数字化时代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最终解决办法。相反,这只是我国为促进弱势劳动者权利保障以及平衡劳动者工作与私人时间而必须采取的众多步骤之一。因此,通过立法保障离线权不应当在真空中进行,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如加大政府部门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离线权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等,也应当一并跟进,如此才能真正落实劳动者离线权的保障,才能以离线权为杠杆,撬动和实现全社会更大范围的工作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