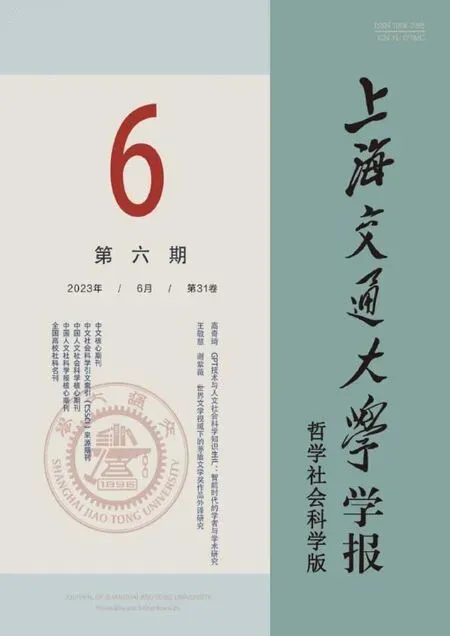数字人文与数字艺术史: 理论、论争及启示
李 斌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 610106)
1979年,法国艺术家埃尔维·费舍尔(Hervé Fischer)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一场演出中宣称艺术史已死。他指出,历史进程的“线性”概念已经结束,艺术和历史一样已经消亡,人类社会进入“元艺术”时代。现在,人类正处于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技术变革时代,互联网革命在各个领域不断创造新发展机遇。数字信息塑造了新的信息获取和解读方式,促成了新的思维与认知,凸显“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性。在信息技术影响下,新学术理念、分析工具和媒介载体等影响了学术界对于艺术史的认知。因此,费舍尔的“前卫性”宣言也揭示了艺术史研究需要转变理念、创新发展的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数字艺术史似乎成为了“艺术”和“时代”的双重选择。
在艺术史研究中,比较研究、视觉相似性研究等一直是基本操作之一。这些视觉联系对于研究艺术起源、传播、接受和流派史等至关重要。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记忆女神图集》(MnemosyneAtlas)由一系列不同主题的“图版”(150厘米×200厘米覆盖黑布的木板)构成,每张图版上都有与主题相关的各种黑白图像(照片)。他通过在图版上增删图像来研究象征符号的历史演变,向学术界展示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视觉连续性,将艺术史塑造成为可视化视觉轨迹,实现艺术史由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突破。
相较于瓦尔堡的传统方法,在数字人文理念影响下,数字数据、可视化技术和计算机算法等数字技术实现了艺术史的数字显示、视觉运行与自动关联等,使艺术史研究摆脱时空限制,拓展研究范畴,创造新的学术认知。本文将基于数字人文理念下的数字艺术史研究实践,分析数字艺术史概念、论争、书写策略以及未来发展等。
一、 数字人文与数字艺术史: 定义、论争与启示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一直致力于利用数字工具对大型历史、文学等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代表性研究团体包括由弗兰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领导的斯坦福文学实验室(Stanford Literary Lab)和由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领导的麦吉尔大学“.txtlab”等。数字人文的价值往往体现为“计算”。《牛津英语词典》将“数字人文”解释为“将计算工具和方法用于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和哲学)的学术领域”。(1)“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digital_humanitie, April 21, 2023.我国学者王宁也曾指出“数字人文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科技与人文结合而产生出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大学的计算机学科与人文学科交叉融合而产生出的一个交叉分支学科”(2)彭青龙: 《反思全球化、数字人文与国际传播——访谈欧洲科学院院士王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0卷第2期,第1—12页。,凸显了数字人文的技术属性和交叉学科特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数字人文研究主要基于数字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计算分析等,致力于充分挖掘数字数据的学术潜力和表达能力,开辟诸多学术研究新领域,其中就包括数字艺术史研究。
在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人文理念影响下,图像收集、计算方法等凭借广泛的适用性正在不断为人文艺术科学领域建构新的研究范式和交流方式。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数据网络的不断建立以及图像访问过程的不断简化,人文艺术科学研究已经开始全面进入数字化新阶段。例如,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学者可以在论文中使用数字图像佐证论点,可以放大查看图像细节或打破时空限制将不同时期的艺术品置于同一个文档中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等。
一直以来,基于文本、数据库等的计算过程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前沿,包括数据挖掘、主题建模、情感分析和网络创建等。但艺术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更关心历史记录和批评话语等要素,这导致数字人文与艺术史研究的结合相对较晚。那么,到底什么是“数字艺术史”?克莱尔·毕夏普(Claire Bishop)等学者认为数字艺术史是“由新技术激发的计算性方法论(Computational Methodologies)和分析技术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3)克莱尔·毕夏普: 《方法与途径——“数字艺术史”批判》,冯白帆译,《美术》2018年第7期,第128—131页。主要包括数据可视化、网络分析、主题建模、仿真技术、模式识别等领域。学者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则主张区分“数字化艺术史”和“数字艺术史”。(4)Johanna Drucker, “Is There a ‘Digital’ Art History?” Visual Resources, vol.29, no.1-2 (2013), pp.5-13.其中,“数字化艺术史”主要基于数字图像采集技术,是艺术史研究对于数字图像的简单运用;“数字艺术史”则包括对于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文本研究等计算方法的使用。我国学者周宪也指出:“数字艺术史的核心部分乃是将计算技术引入传统的艺术史研究的关键问题。”(5)周宪: 《数字艺术史的当下召唤》,《美术大观》2021年第12期,第107—109页。从学术界对于数字艺术史的定义可以看出,该领域具有很强的“数字人文”特征,凸显技术属性和交叉学科属性。其中,前者体现为数字技术、计算方法等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运用;后者则体现了数字艺术史的学科特征。
事实上,在“艺术史”前冠以“数字”之名本身就彰显“数字艺术史”与传统艺术史之间的差异性。就学科建设而言,数字艺术史符合“新文科”理念,是艺术史领域交叉学科建设的典范。随着数字人文与艺术史研究的联系越发紧密,围绕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显著增加。学者方维规就曾指出“数字人文和可视化技术(Visualization Techniques)对人文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认为“数字人文技术的优势是能整体计算出所有语言线索”。(6)彭青龙: 《概念史与比较文学中的思想和方法——访谈欧洲科学院院士方维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0卷第6期,第1—13页。目前,除了基础的目标访问、搜索、分类外,视觉分析、图像重构、计算分析、深度学习等不断为数字艺术史研究带来新活力,建构新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认知。不过,面对数字艺术史的快速发展,部分学者表达了质疑和担忧。例如,毕夏普等就曾从两个方面表达了对于数字艺术史研究的质疑。一是数字艺术史的简单化策略是否可行。这部分学者认为:“数字艺术史的实践者们极少能够意识到艺术史内部存在着批判性的论争。”(7)克莱尔·毕夏普: 《方法与途径——“数字艺术史”批判》,冯白帆译,《美术》2018年第7期,第128—131页。数字艺术史研究往往践行“数据中心主义”,推崇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热衷于数据挖掘、统计学分析以及数据的视觉化呈现等,试图利用数据的“客观性”和表达能力代替艺术史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但这些所谓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人类历经千年积累而成的艺术情感和主观判断。二是“艺术”分析是否能够被“客观量化”。例如,毕夏普质疑“美”这类主观判断能否成为量化测量的客体。为此,她列举了一个面部识别软件的例子,该软件数字化了13世纪到20世纪的1.2万幅肖像进行定量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 20世纪“美”减少了。毕夏普认为,这项研究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为了结论而结论。研究者并没有讨论“美”为何会减少。更何况,这项研究所获得的“结论”似乎是一个“常识”。另一方面,缺乏说服力。研究者并没有考虑“美”的主观性,也没有说明研究样本以及所选数据库的客观性等。
实际上,数字人文理念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提出多少“惊世骇俗”的结论,而是基于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改变现有知识与方法论体系。目前,数字艺术史研究正试图超越传统“艺术史”研究范畴,用数字化手段开辟艺术史研究新阶段。那么,这种“改变”是否合理?艺术史是否会完全适应定量分析?在数字人文研究过程中,传统艺术史批评对于正义、权力、真理、意识形态等理念的思考与批评不得不让位于定量分析、数据统计、计算机算法等。相比于艺术批评的主观性,数字数据的客观性尚未发声便已经充斥着“优越感”,似乎彰显着科学分析时代的到来。但是,我们不禁要问: 这些所谓的计算机实证主义方式是否真的能够增强人文艺术学科的理解力与解释力,是否真的能够推动人文艺术学科的创新发展?毕夏普坦言: 在数字艺术史研究中,“关键性的学理问题被数据所碾轧而变得异常扁平化”。(8)克莱尔·毕夏普: 《方法与途径——“数字艺术史”批判》,冯白帆译,《美术》2018年第7期,第128—131页。学者米里亚姆·金勒(Miriam Kienle)也认为: 虽然计算机技术使艺术史研究实现定量分析,但却错过了放大研究。(9)Miriam Kienle, “Digital Art History ‘Beyond the Digitized Slide Library’: An Interview with Johanna Drucker and Miriam Posner,” Artl@s Bulletin, vol.6, no.3(2017), pp.121-125.显然,如果只是为了“数据”而“数据”,那么数字人文与数字艺术史研究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质疑”而否定数字艺术史研究的价值。整体看来,数字人文影响下的艺术史研究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虽然艺术史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数字图像,但查看和呈现数字图像的方法仍然与传统方法相似。学术研究内容也相对单一,如比较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异同,或者专注于一个艺术群体、艺术流派,以发现与其他艺术家群体之间的关联性等。不可否认,随着新技术的介入,传统艺术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突破。但必须认识到,传统艺术研究方法和理念无法充分发挥数字数据的功能与潜力,尤其是艺术的特定性与可能性。因此,艺术史研究需要更复杂的数据模型与统计,以及新的可视化技术和数字表达模式等,需要利用真正的计算方法评估数字数据,开辟新的研究方法与策略。
二、 数字人文与数字艺术史书写: 方法、策略与创新
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趋势,数字人文与艺术史研究的结合正在逐步引起重视。正如上文所言,数字人文的价值往往体现为“计算”。而这也构成了数字艺术史书写的主要方法和策略。目前,计算机视觉研究已经实现多项功能: 使用计算方法分析和访问图像、视频等大型数据集;通过可视化技术或自动搜索等功能快速访问一个甚至多个数字图像集,在数千幅图像之间建立联系,以执行目标检测、查找视觉相似性等任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计算方法应用于艺术史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将图像中的信息转化为新知识?就研究方法和策略而言,数字艺术史研究可以利用图像模拟、数字数据、计算方法、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数字技术,对数字数据实施自动化、规模化分类和分析,以创建新的艺术关联性,实现艺术形式、内容、风格等动态变化的数字显示,发现纵向时间轴中艺术家创作主题或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等,生成艺术史研究新视角。
(一) 数据模型与数据分类: 基础、缺陷与突破
在数字艺术史研究领域,基于数据库的准确、高效、合理分类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诸如印刷品、照片或书籍之类的模拟数据通常存储在特定的系统中,按照类别(如流派、技术或主题等)或其他数据模型进行架构和组织。这些特定的存储数据库和模型主要包括网络模型、关系模型、实体集模型以及层次模型等。前三者通常被视为实体关系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简称ER模型)的基础,包含关于现实世界的重要语义信息。而层次模型则以树状结构组织数据,记录更具体的类别,如时代、风格、艺术家和主题等。一般情况下,数据模型的选择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集成数据的数据库、数据的主题和格式、后续功能或使用数据的规程等,其目的是简化数据存储、检索和交换。同时,为了让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课题的学者都能够访问数据,数据库还必须兼具灵活性、动态性和开放性。
在传统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尽管研究者已经尽最大努力进行编目和创建语料库,但是手动浏览的物理极限依然限制了研究范围。目前,计算机程序和算法已经能够快速处理和访问数以千计的图像,并考虑数字数据的特殊属性。在这种技术支撑下,研究者可以在图像之间建立新联系,从而在特定主题、艺术风格或艺术交流等层面获得新见解。例如,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Alex Krizhevsky)等学者将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应用于物体识别,基于ImageNet(10)ImageNet是一个计算机视觉系统识别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图像识别数据库。的一个子集对数千幅图像进行自动分类(11)Alex Krizhevsky, Ilya Sutskever, Geoffrey E. Hint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12, pp.1097-1105.,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
不过,现有数据模型建构依然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数据模型需要在固定空间中运行,限制了数据的检索以及不同系统或用户之间的数据交换等,影响了数字数据的灵活性和可用性,违背了数据分析的本意,也没有真正发挥数据的功能。此外,研究模型与研究数据的脱节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数字人文研究往往经历一个过程: 首先开发一套方法或者模型(或者利用现有的方法与模型),然后参考数据的特殊性。此类方法存在一个弊端,即在开发阶段不考虑数字数据的特殊性(如可复制性、可修改性等),限制了数字数据的学术潜力和价值。数字人文与艺术史的结合依然没能摆脱这一缺陷。作为交叉学科,数字艺术史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人文艺术、计算机科学等。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下,制作数据分析模型的学者不了解艺术史,艺术史学家又不懂技术,两个学科之间缺乏有效交流。正如萨宾·朗(Sabine Lang)和比约恩·奥默(Björn Ommer)提出的那样: 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数字数据的特殊性和相关要求,然后创建相应的方法。(12)Sabine Lang, Björn Ommer, “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into Knowledge: How Computational Methods Reshape Art History,”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vol.15, no.3 (2021). http: //digitalhumanities.org: 8081/dhq/vol/15/3/000560/000560.html, April 28, 2023.数字艺术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数字数据和计算方法产生新认知。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艺术史学者能够使用计算机方法和工具。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缺陷”?对于数字艺术史而言,未来的工作重点应该聚焦于以下两点: 一是必须减少对计算方法的怀疑,进一步减少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二是要强调艺术史学科自身工作的价值,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而这些“愿景”的实现,需要强化交叉学科建设,促使计算机科学家与艺术史学家密切配合。例如,要使艺术史学家熟悉了解图像处理过程,以便其能够发现图像分类等方面存在的错误、不足等,并向计算机科学家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从而改进计算方法,实现对数据模型的及时修正,使艺术史研究变得更加准确、高效。埃米莉·斯普拉特(Emily L. Spratt)和艾哈迈德·埃尔加马尔(Ahmed Elgammal)等学者的调查也证明,艺术史学家普遍希望“更多地了解人工智能进入人文学科的运动,或者计算机科学家对艺术史的关注”,而部分计算机科学学者也表示“有兴趣在开发计算机视觉技术新应用时从艺术史学家那里获得直接反馈”。(13)Emily L. Spratt, Ahmed Elgammal, “The Digital Humanities Unveiled: Perceptions Held by Art Historians and Computer Scientists about Computer Vision Technology,” arXiv: 1411.6714 (Nov. 2014), pp.18-19. https://arxiv.org/abs/1411.6714, April 28, 2023.这些客观需求体现出进一步推动计算机技术和艺术史研究者之间进行多维度合作的必要性。
显然,这种“合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艺术史研究者需要提高技术素养。例如,在大学艺术史课程体系中开设计算方法、数据模型等课程,使学生了解基本操作流程,加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强化重点实验室的引领作用。例如,艺术史学科与计算机学科加强合作,共同成立数字艺术史研究实验室,为该领域研究提供稳定的学术平台、艺术素养和技术支持。总而言之,通过教授数字技术或者开展合作研究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人与技术之间的隔阂,也有利于培养新一代交叉学科人才,为数字艺术史研究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撑。
(二) 数据科学与计算分析: 优势、不足与发展
根据定义可以看出,数字人文研究视“计算”为核心。但学者刘毅却认为,在数字艺术史领域,“信息数据”的作用要远大于“计算方法”。他指出: 就艺术史学科而言,计算的价值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其意义远远低于数字人文的另一大特性,即信息数据。(14)刘毅: 《透明的图像: 数字人文与艺术史的跨媒介叙事》,《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22—129页。“数据科学”源自经典统计学分析,融合统计学、信息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致力于发挥“数据”揭示现象、提供见解等功能,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在数字人文和计算机技术影响下,数据科学已经在模式识别、信息检索、信息可视化、数据挖掘等领域广泛运用。其中,通过相似颜色、笔触、物体或构图等要素鉴定艺术品相似性的视觉可视化研究一直是数字艺术史的重要差异化特征。传统艺术史中的视觉相似性研究往往受到时空限制,只能依靠艺术史学家视觉比对,研究范围较小且主观性较强。数字化策略则实现了艺术品的数字可视化,“数字数据”的运用打破时空限制,使视觉相似性在更广阔的平台进行充分比较研究,凸显数字艺术史研究的优势。
目前,数字艺术史领域的数据“数字化”主要依赖两条路径: 一是图像模拟,即将研究对象通过拍摄、扫描等方式“数字化”为模拟图像。例如,艾哈迈德·埃尔加马尔等学者将7.7万幅绘画进行“数据化”和风格分类,并将可视分组与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的艺术史五大对比原则相关联,(15)Ahmed Elgammal, Marian Mazzone, Binghchen Liu, et al., “The Shape of Art History in the Eyes of the Machine,” Thirty-Second AAAI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32, no.1 (2018), pp.2183-2191.提高了研究效率和准确度。二是数字模拟,即将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数值”化,利用传感器将二维图像转换为数字表示。例如,利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生成文本、图像、视频等大型数据存储库。
那么,数字数据对于艺术史研究到底有何作用?基于现有的数字艺术史研究可以看出,相比于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数字数据”拥有以下优势:
一是数字数据为艺术元素的表达与呈现提供新方式。例如,通过扫描技术实现图像的数字化,即将图像的艺术元素和特征呈现为具体“数值”,使构图、颜色以及图形之间的空间关系等内容可以进行有效评估、统计和分析,实现数据可视化。这种变化使艺术分析的重点从图像视觉分析转移到图像处理技术,为数字艺术史研究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解决了数字艺术史研究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同时,这些分析结果的直观性有助于为艺术史研究提供更加客观且具有差异化的描述,使研究者通过查看相关图像的分析数据即可研究一幅作品的流行程度、创作者对构图模型的依赖程度或者某一种颜色的产生、发展与流行等。
二是数字数据的“共享性”契合数字时代的特征。由于以数字数据的形式进行存储和使用,数字图像可以轻松复制。这些数字副本代表了数字时代真实艺术品的特殊复制品,形成特殊的数字ID,而不是计算机生成的具体图像。同时,数字图像的在线可用性带来诸多便利,如扩大图像受众、比较不同空间的艺术品等。这些数字数据(如艺术品或其他文物的复制品)也可以在博物馆网站等在线数据库中收集和发布,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共享。总体看来,鉴于数字数据对于艺术品的再现具有可传输且易于分发的特点,数字图像副本可以共享或同时用于多个项目,有助于建立全球艺术史研究网络,使艺术史研究跨越国界和学派,成为国际化和动态化领域。
三是数字数据的“可编辑性”拓展艺术史研究空间。数字图像的再现性和可复制性等特征允许在不改变实际艺术品的情况下修改图像,使图像编辑成为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能够更改颜色、饱和度、亮度、对比度等形式特征,也可以通过图像编辑比较数字图像的细节,研究色彩等元素对艺术品的重要性等。例如,里昂·盖蒂斯(Leon A. Gatys)等学者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系统,将图像解构为内容和样式两个部分,并进行任意重组,完成图像风格迁移,为创建艺术图像提供了一种神经算法。(16)Leno A. Gatys, Alexander S. Ecker, Matthias Bethge, “A Neural Algorithm of Artistic Style,” arXiv: 1508.06576, https://arxiv.org/abs/1508.06576, April 28, 2023.在这一过程中,一种风格的视觉特征,如颜色、形状、纹理和笔触等甚至能够被编辑到真实图像上,使风格化图像产生新的研究视角。
当然,虽然图像的复制和数字化显示为艺术史研究提供巨大支撑,但这种“数字数据”也存在不足。例如,由于图像的复制质量不同,数据的客观真实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这就使得数字图像中的颜色、清晰度、对比度等信息经常被误传,并用以伪造原始艺术品的外观。这种不确定性和非真实性使数字艺术史研究的说服力大打折扣。同时,在开发或阐释计算方法时研究者必须充分考虑视觉变化,如错误的色彩再现可能会导致违背真实图像的视觉相似性,模糊的图像会隐藏部分细节等。此外,艺术品的数字复制也引发了学术界有关原创性、独特性和真实性的讨论。基于德国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有关艺术品复制的观点,艺术品的功能、作用以及物理属性无法通过数字数据解读。
虽然数字数据存在争议,但基于数字人文研究的计算特性,数字数据显然已经成为数字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它推动了新艺术分析视角和方法的开发利用,使艺术史分析的重点从图像视觉分析转移到数据处理,从主观认知过渡到定量分析,为数字艺术史研究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解决了数字艺术史研究过程中的时空限制等实际问题。此外,数字数据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更广泛的运用,如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有助于扩大受众群体。
(三)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创新、质疑与启示
数字艺术史对于传统艺术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是扩大研究范围,提高研究的效率,如对于视觉相似性研究的影响等;二是利用新技术开辟艺术史研究新思路。相比于后者,前者除了为艺术史研究获取更多差异化信息外,还有助于开辟艺术史研究新篇章。自2015年以来,计算机深度学习发展迅速,类似人脑的卷积神经网络已经运用于计算机视觉分析以执行目标分类、目标检测等任务。基于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实现了以新的方式对数据库进行大规模分析,包括访问、链接和编辑数字图像等。例如,约瑟夫·雷德蒙(Joseph Redmon)等学者开发了YOLO模型(You Only Look Once),即一种单级目标检测网络,非常接近人类的行为模式。这个模型的特点在于能够快速定位图片中的物体、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等。通过神经网络系统,该模型能够根据图像信息一次性提供分类标签,如人、狗、马等。(17)Joseph Redmon, Santosh Divvala, Ross Girshick, et al.,“You Only Look Once: Unified, Real-time Object Det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Las Vegas, 2016.此外,贝努瓦·塞甘(Benoit Seguin)等学者在图像数据集中对视觉关联的图像进行编码,使用神经网络建立链接,对图像注释集群进行预训练,从图像中查询、检索、共享视觉链接,大大提高目标检索与分类的速度与精度。(18)Benoit Seguin, C. Striolo, F. Kaplan, “Visual Link Retrieval in a Database of Paintings,” in G. Hua and H. Jégou, eds., ECCV 2016 Workshops, Switzerland: Springer Cham, September, 2016, pp.753-767.在这些研究实践中,基于目标检索、搜索引擎和可视化技术等,神经网络能够感知和分析目标对象(数字信息)的视觉特性(如颜色、像素等信息),并根据视觉相似性特征等要素发现并标记目标对象之间的关联性,以表明物体的客观存在,简化分类任务,实现短时间内处理数千张图像而不依赖于图像的描述性标签,不仅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主观认知的影响,展示了神经网络感知内容的相关能力以及组织数据的高效性,使计算视觉分类研究取得新突破。
除了神经网络之外,深度学习也成为数字艺术史研究的重要策略。2014年,伊恩·古德费罗(Ian J. Goodfellow)等学者开发了“生成式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简称GANs)。(19)Ian J. Goodfellow, Jean Pouget-Abadie, Mehdi Mirza, et 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63, no.11 (2020), pp.139-144.GANs中包含了两个模型: 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和判别模型(Discriminative model)。其中,生成模型可以不断学习训练集中真实数据的概率分布,将输入的随机噪声转化为可以以假乱真的图片;判别模型能够判断图片是否为真实图片,目标是分辨生成模型产生的“假”图片与训练集中的“真”图片。例如,在生成模型中输入一系列小狗的图片,经过深度学习,系统可以自主生成一张新的小狗图片(该照片并不在输入的照片数据集中)。而判别模型的功能体现为利用系统自动判别图片中的动物是小狗还是小猫。
生成式对抗网络对数字艺术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通过不断“学习”(如在模型中输入相关作品),该系统可以掌握艺术家以及作品的艺术风格,并进行艺术品鉴定与修复。例如,有学术团队通过统计分析、边缘检测和聚类分割等方法自动提取梵高的笔触特征,(20)Jia Li, Lei Yao, Ella Hendriks, et al., “Rhythmic Brushstrokes Distinguish van Gogh from His Contemporaries: Findings via Automated Brushstroke Extrac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vol.34, no.6 (2012), pp.1159-1176.用于艺术鉴赏、身份认证、年代测定和作品鉴定等。目前,这种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对毕加索、亨利·马蒂斯和埃贡·席勒等艺术家的画作分析中,以辅助确定艺术品的归属或真假。
同时,该网络能够基于深度学习实现艺术风格转换,通过分离风格和内容的方式控制风格化过程等。例如,在具体研究实践过程中,深度学习等技术可以利用计算机程序和算法针对特定艺术风格(如构图、色彩、线条等)进行预学习,通过改变数字对象的样式属性、裁剪细节或在虚拟状态下重新创建缺失部分等方式,实现图像重构。这种图像生成方式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路径,使研究者可以基于图像重构过程直观研究类似“变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从而洞悉艺术发展规律。
不过,神经网络、计算方法以及深度学习等在数字艺术史领域的运用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数字数据的真实性。数字数据以图像或“值”的形式表示,可以进行修改和编辑,具有便捷性和共享性等特征。但是研究者似乎从未考虑过“数据”的真实性。换而言之,研究者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显然,在此类研究过程中,一个数值的微小差异有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对数据分析持谨慎的态度,摒弃唯数据论,意识到数字数据的可操纵性。二是方法的可行性。正如朗和奥默指出的那样: 神经网络是根据照片训练的,从未见中世纪服装或立体派变形物体的实例。(21)Sabine Lang, Björn Ommer, “Reflecting on How Artworks A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by Computer Vision,” in L. Leal-Taixé and S. Roth, eds., ECCV 2018 Workshops, Switzerland: Springer Cham, September, 2018, pp.647-652.显然,照片可以放大细节,但却无法反映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如材质、空间等。从这一角度看,这类艺术史研究的目标对象本身就是虚拟的而非真实的,其研究成果及学术观点缺少细节以及真实性支撑,是不全面的。
数字艺术史研究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差异化,利用新颖的数字技术代替传统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以新颖的方式揭示艺术品的特征,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身份、目的、用途和实质等,从而发现潜藏的或差异化的学术认知。事实上,“新文科的内核在于打破学科固有限制、强化学科交叉融合、适应时代发展需求”(22)李斌: 《新文科背景下比较文学学科的挑战与机遇》,《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第38—47页。。在新文科视角下,学术研究应该肯定新技术带来的新视角。在传统艺术史研究过程中,为了研究视觉联系,艺术史学者通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收集与分析图像,有时甚至不得不多地来回奔波。即使已经尽最大努力进行编目以及创建语料库,但是手动浏览的物理极限依然限制了研究的范围。而无论是基于神经网络的快速目标检索与分类,还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风格化与重构,都是艺术史研究的突破。这类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艺术发展规律,发掘特定色彩、线条、笔触等要素的艺术史意义,创造了艺术史新认知。
结 语
在数字人文影响下,计算机算法可以在数据集中自动建立链接,建构艺术作品之间的新关系,尤其是艺术史研究者所忽视的联系,使数据分析过程相对独立。此外,新方法克服了传统可视化研究的空间局限性,使艺术史研究者能够建立更全面、更广泛的联系,并通过链接访问等方式使艺术品永远置于与其他艺术品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中,有利于理解艺术史上的短期和长期现象。简言之,在数字数据和计算机算法支持下,艺术史研究不再是孤立的、先验的、静态的学术研究,而是形成一条或多条动态链条,建构动态的艺术发展过程。当然,数字艺术史研究也需要摒弃“唯数据论”“唯技术论”,不能盲目推崇计算分析,不能将关键性学理问题完全“量化”。
人文主义者倾向于重视模糊性、异质性和不规则性,而计算机学者则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强调模式、清晰性和规律性。那么,如何解决数字人文与数字艺术史研究过程中的这种冲突?就数字技术而言,往往需要更复杂的数据模型与统计,以及新的可视化和数字表达模式等。目前,艺术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正在考虑新方法与新功能对于艺术史研究的意义。未来,需要继续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共同开发适用于艺术史研究的计算方法和模型,建构更加完善的研究策略与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