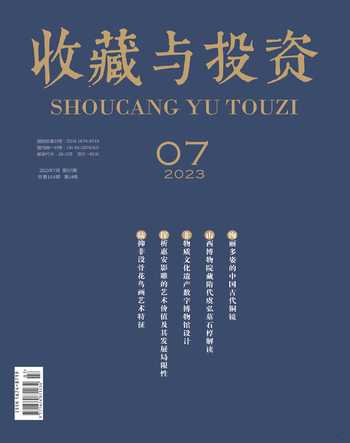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设计
沈罗兰 程晓曼 高菡
摘要:数字化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数字博物馆逐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担任重要角色,涉及记录、保存、展示、传播等数字化实践工作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文章通过对数字博物馆发展现状的调研,探索非遗主题数字博物馆的设计原则,为形成良性保护机制提供借鉴思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数据库
数字化技术作为新生力量,因在存储、传播、应用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已成为非遗保护和传播重要手段之一。数字化保护容易局限于非遗的表层数字化,大都停留在简单的图文描述或单一的影像记录阶段,对非遗的本真性、原生性及活态性的数字化保护还不够。本研究基于非遗文化的特点,探索此类数字博物馆的设计原则与实践方法。
一、数字博物馆发展现状
(一)数字博物馆概念
数字博物馆使用数字手段将实体博物馆的收藏品转化为数据资源,并辅以数字展示方法,通过互联网实现跨时间、跨地域传播。它在保存文物数据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博物馆研究、审美、科普等目的[1]。
作为一种新型博物馆,美国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起步较早。20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大型图书馆、博物馆机构陆续开展了馆内藏品的数字化建设。美国国会图书馆制订了“美国记忆计划”,提出在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融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以推进一系列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处理,并依据不同类别开展归档存储,构建数字化图书馆或博物馆。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建设现状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2]”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工作的目标方向和任务: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完善档案制度,加强档案数字化建设,妥善保存相关实物、资料。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专业记录水平,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记录。加强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共享[3]。
随着各项政策法规的出台,我国的数字博物馆已取得一定成果,展馆数量日趋增加,社会关注度逐步提升。
2011年数字敦煌博物馆拉开了我国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帷幕;2012年,百度百科博物馆大型公益科普项目正式上线,至2020年末,已上线的数字博物馆达到313家之多;2016年,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正式启用,至2020年共计上线49个数字展厅;2018年10月故宫博物院“智慧故宫”正式上线。
数字博物馆作为一类独特的博物馆在系统化建设中仍有亟待完善的细节,如参与者的主体范围广,知识背景差异较大,数字化手段是否能兼顾非遗的发展规律、满足大众不同需求及在技术实施上的可行性等问题还有待观察。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设计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设计旨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将传统博物馆所藏的文件、器物、标本等资料,依托高清晰度拍摄、扫描或三维建模等技术开展信息化处理,经互联网呈现传统展馆所具备的收藏、展示、科教等功能的非实体空间的“虚拟博物馆”,体现管理电脑化、传递网络化、存储数字化、资源共享化等特征。
面对我国丰富的非遗资源,相關数字博物馆设计原则主要有五条。一是生态性原则。非遗文化是以人为主线的活遗产,应基于非遗生态性的技艺链和生活场景的特点,对整体历史文化生态开展严谨分析,确保非遗与生态环境之间维系健康的稳定发展。二是统一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依赖于相应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呈现,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在设计中,应有意识关注与表现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关联。三是系统性原则。不同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叠加很难与全面系统的功能相比拟。应关注提供一站式浏览、检索与展示服务,实现博物馆的一体化管理。四是活态性原则。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博物馆需借助有效技术,既关注它的历史演变进程及现存状态,同时也要关注未来发展。五是持续性原则。数字技术无法长期维系非遗的生命力,但可通过对资源的数字开发来拓展非遗价值,尤其针对濒危非遗,要注重本体保护与元素创新相结合。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设计实践
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简称《意见》)对“十四五”期间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工作提供了指导,根据《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对新时代非遗主题数字化博物馆设计有以下建议。
(一)数字赋能,推进非遗数据库建设
以数据库的方式集中遗产数据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贯做法。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非遗数据库建设的规范化、网络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4]。数据库建设中要通过对存储的非遗资源的有序化整合,探索资源背后的知识讯息,以期获取各项非遗的文化本质与传承脉络,效益最大化地实现保护的目的[5]。
(二)深度开发,重视非遗文化内涵挖掘
简单的数字存储较易忽视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数字技术在赋能创新中,应不断开展对非遗资源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发掘其潜在价值。如从观众的认知出发,挖掘展品背后与观众相关的故事等,构建物与人的认知关联;或叙事中导入“亲历者”视角,引导观者开展主体性探索,在交互中体验“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意义和作用,塑造与文物主体同时空的共情触动与内省体验[6];或可依据人物、历史背景等创设情节化浏览线,通过设置相应的闯关情节、故事发展情境,让用户以角色扮演的方式直接参与情节发展。
(三)创新展示,提升非遗文化传播能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