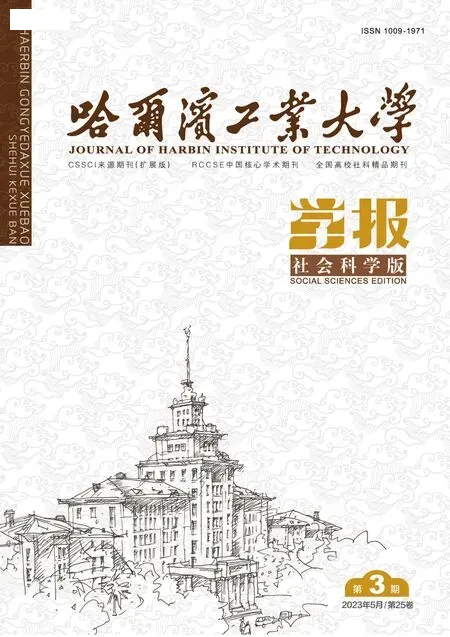《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
——兼谈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 的学术立场
赵 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史记》对邹衍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荀卿列传》。 明清评点家已然发现司马迁在《孟荀列传》中的行文方式十分独特。 本传虽以孟、荀二子为题,文中却主要论述了邹衍的生平与学术,“宾主参互”、叙议交织,清人牛运震即称其是“极错综变化之妙,《史记》最奇格文字”[1]。 近来学人亦从文体角度阐析了《孟荀列传》的写作特色[2],但却未能将本传与《史记》其他涉及邹衍篇目互见参照,因而尚未洞察本传所见太史公书法及其中深意。
所谓“太史公书法”,指的是《史记》表达个人意旨所用的较隐晦曲折的写作方法。 “书法”原指《春秋》的书写原则,其突出特点是“微而显,志而晦”[3],即在叙事中通过微妙的措辞差异,委婉曲折地表露作者的褒贬意图。 司马迁本着“继《春秋》”[4]3296之著作信念,亦多以隐晦书法来表达评判,成一家之言①古人讨论《史记》写作,多从史书编纂体例角度论其篇题、篇次、文体等结构特征,而对太史公具体书法留意较少。 以方苞为代表的明清评点家详细分析了《史记》“义法”,但以古文文章技法为主,未暇深考旨意。 章学诚始考察《史记》“笔削之义”,以史意论书法。受其影响,清末民初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对此展开了系统论述,《史记》书法研究渐兴。 本文所言“书法”承此而来。。 《史记》论载邹衍便使用了此类书法。 下文即尝试对此进行梳理,结合司马迁的身份,深入分析文辞所含幽微的天人深意,并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5]2735的学术立场略作探讨。
一、“怪迂阿谀”与“是时独有”:《史记》论载邹衍学说的多重层次
《史记》对邹衍学说的记载散布于全书诸多篇章之中。 其中明确提及邹衍本人学说内容的共有三篇,分别是《历书》《封禅书》与《孟子荀卿列传》,而尤以《孟荀列传》最为详尽。 本传亦是考察《史记》论载邹衍书法的切口。 其文云: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 1.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 祥度制,推而广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1)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2)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着,如一区之中者,乃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其术皆此类也。 2.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 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4]2344
《孟荀列传》对邹衍学说的论述隐含一逻辑线索,即将邹衍之学划为两个层次:“术”与“其归”。 文章先称邹衍学说的总体思路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进而将邹衍学说分为时间与空间两大类,时间上是五德终始说,空间上则是大九州说。 在描述了二说内容之后,司马迁总结道:“其术皆此类也。”点明以上所言都是邹衍十万余言中的“术”。 其中五德终始说“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则属于“学者所共术”。 结尾交代完邹术内容后笔锋一转,称“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指出邹衍之术尚有一共同旨归,即仁义节俭等人伦之道。
综合《孟荀列传》全文,司马迁认为邹衍之术的特点是“怪迂”“闳大不经”“迂大而闳辩”,而邹衍学说往往先以此类“术”为导引,可谓“始也滥耳”。 因此“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然而对于邹术旨归,却是“其后不能行之”。
司马迁对邹衍之术的类似述评也见于《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4]1368-1369以为邹衍之徒率先以“五德终始”“阴阳主运”之术显于诸侯,燕齐海上方士继其踵,然而却“传其术不能通”。结合《孟荀列传》可知,这是由于邹衍之术虽然起于逢迎君主意愿,最终还是能够指向仁义节俭等伦理价值,即所谓“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4]2345;然而燕齐方士却仅能传习邹术的表象,终不免停留于“怪迂阿谀苟合”的层面,未能深察其道。 可见如果没有具有道德价值的终极旨归,司马迁对邹衍之术的评价也便是如此了。
然而除了“怪迂闳大不经”外,《史记》对邹衍之术还有着另一种评价维度。 《史记·历书》追溯了历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言及战国时曰:“其后战国并争,在于治国理政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 是时独有驺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4]1257-1258意指战国时期因为兵乱频仍,君臣上下都无暇精研历法修订工作。 然而“是时独有驺衍”能够凭借其学说“以显诸侯”。 此句暗示邹衍掌握着高超的历法技术,《晋书·束皙传》即称汲冢书有“《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6]。 学者已发现“这种星象历法的专门学术……是邹衍的学术所以能够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卓然成立为阴阳家的一个重要特色”[7]。 而这一技术又与“明于五德之传”有密切关联。 《历书》下文便言,秦始皇“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4]1259。 说明秦人推五德借用了邹衍学说,但主要依据邹衍“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的内容,以符瑞判断自己获得水德,而未能通晓其中的历术原理。 以历术推五德恐怕正是邹衍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学者认为《易纬·乾凿度》卷上一段文字可能反映了五德相胜与历术之运算关系,可备一参。 其文云:“孔子曰:至德之数,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岁,五德备,凡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复初。 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纪七十六岁,因而四之,为三百四岁。”( 赵在翰辑《七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卷二,58 页)此节将五德终始与四分历历元推算结合在了一起,使用了四分历的基本数据,每隔1520年,历法会回到历元点,而这被视为一个五德终而复始的循环周期,每德当值304 年。 学者多认为《乾凿度》卷上形成于西汉,保存了汉初乃至先秦的早期易说(参见张学谦《关于今传〈周易乾凿度〉文本构成的再考察》,载《中国哲学史》2004 年第4 期,67-73 页)。 故此文虽未必是邹衍学说原貌,但仍可借之略窥西汉人以历法推算五德的思路。 详参刘彬《〈易纬〉“五德终故始术”考辨》,载于李锐、朱清华主编《学灯》2008 年第2 期;陈鹏《终始传和历谱谍》,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 年第1 期,134-142 页;郭津嵩《古四分历与汉代历学》,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24-29 页。。
总之,不同于《孟荀列传》总体对五德终始说持否定态度,司马迁在《历书》中十分认可邹衍将历法之学与五德终始说结合以推算王朝德运,并因此认为通晓历法之人最有资质负责这一工作。《历书》云:“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 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4]1260语中含有谴责之意,意指“习历”者既然明于历法,本不应支持刘邦定汉为水德。 《史记》也曾多次提到张苍因掌握律历之学而能判断德运,如云:“(公孙臣议改土德)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汉相张苍历谱五德”[4]1260,429,510等。 然而,司马迁始终反对张苍推定汉行水德。 《张丞相列传》太史公论赞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黜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4]2685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此句不可解”[8],其实是不明晓司马迁此处所言正是邹衍之术,即用历术判断五德。 而使用不同的历法很可能会推演出不同的德属,因此司马迁质疑张苍以颛顼历为基础推得汉行水德。 司马迁的立场与贾谊、公孙臣等人一样,支持汉行土德。
至此可见,《史记》对邹衍学说的论载呈现出了多重层次,其中不仅有“术”与“归”之别,“术”的内部又可分为《孟荀列传》所见“怪迂阿谀”的五德终始说,以及《历书》等篇所载“是时独有”的历术两类。《史记》多处暗示,邹衍的历术可以辅助论证其五德终始之说,以历术判断王朝德运归属。 然而司马迁却对二者分而评之,且态度褒贬不一,内含矛盾。 这些迂回、复杂的叙述方式便是《史记》论载邹衍之学的独特书法,而其背后隐含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宗旨。 欲理解《史记》论载邹衍学说微妙丰富的多重层次,需要我们深入司马迁的历史处境,进一步分析太史公的学术途径及立场。
二、“星历祝卜”:太史令之职与司马迁取舍邹术的立场
“天人之际”即天与人的交际关系。 天命如何影响人世,关乎着王朝易代之因、汉朝建立的合法性、施政之策等时人极为关注的政治命题。 学者已指出:“‘天人之际’在太史公时是政治上的常语。”①程金造《〈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释》,载于《人文杂志》1984 年第1 期,95 页。 武帝极为关注天人受命问题,其策问即言:“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汉书》卷五十六,2496 页)董中舒对策言:“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分际,甚可畏也。”(《汉书》卷五十六,2498 页)此外,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述诏书之美也说:“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卷八十八,3594 页)邹衍学说为这一讨论提供了思想资源,成为汉初一系列天人受命活动的重要依据之一。 太史令的工作内容亦与此密切相关。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言:“文史星历近乎祝卜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5]2732由于太史令与方士之职多有重合,司马父子往往被轻慢看待。 因此,司马迁如何理解自身本职与方士活动之间的同与异,将成为理解《史记》论载邹衍书法的重要线索。
受命改制是汉初与天人交际有关的重要活动之一。 《史记·历书》便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 改 正 朔, 易 服 色, 推 本 天 元, 顺 承 厥意。”[4]1256《汉书·律历志》载兒宽亦云:“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 创业变改,制不相复。”[5]975受命改制是为了宣告汉家已然奉天受命、改朝换代而举行的国家典礼,不仅象征政权一统,亦可彰明君主之盛德。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为全书写作了简短叙录,其于《今上本纪》云:“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 作今上本纪第十二。”[4]3303正是以受命改制活动作为武帝隆兴汉室的标志,视之为最值得刻记的功绩之一。
当时若施行受命改制必须利用邹衍五德终始之说。 西汉受命改制之议起于文帝时。 鲁人公孙臣上书云:“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 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文帝许之,“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4]1381。 前人已论,公孙臣所推“终始传”乃是当时流行的“记述五德终始的一种文类,如《终始五德传》《黄帝终始传》等,起源于邹衍所著‘终始大圣’等篇”[9]。 而公孙臣后亦有“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4]1260。 正历是受命改制的重要内容,需要大量历学知识,而这些知识也必然为司马迁所掌握②司马迁精通历术,今见《历书》结尾所附《历术甲子篇》虽被后人妄添了天汉元年、太始元年等年号年数,但学者依然倾向认为该篇出自司马迁之手,代表了其高超的历学造诣。 见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四“历术甲子篇”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96-97 页;郭书兰《司马迁的古代历制研究》,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 卷第6 期,106-108 页。。
学者对西汉太史令的职责多有讨论,总体而言,内容不出司马迁自言的“文史星历”之事。 翻检史书,司马谈、迁父子作为太史令的官方工作主要围绕着泰山封禅、受命改制等天人活动展开,而太初改历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汉书》载太初改历始于太史令司马迁等人的上书:“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武帝因命御史大夫与博 士共 议; “今 宜 何 以为 正 朔? 服 色 何上?”[5]975此举可视为受命改制的发起环节,不久武帝遂诏令司马迁等议造汉历。 元封七年太初新历正式颁布,诏书有言:“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 绩日分, 率应水德之胜。”[4]1260这表明修定新历最重要目的是为了“应水德之胜”,更改汉德。 此处使用的正是邹衍的五德相胜说①一般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遵从五行相胜的逻辑,王莽改制前后,刘向等人始倡以“相生”代替“相胜”,改称汉德属火。 如沈约言:“五德更生,有二家之说。 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沈约《宋书》卷十二,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259 页。)关于五德终始与汉代政治史的关系的讨论可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中华书局2006 年版。,土胜水,汉行土德,而历法计算“绩日分”是得出这一结果的重要依据。 太初历的颁布标志着武帝受命改制最终完成。
受命改制活动有赖于邹衍五德终始学说,因此即便司马迁对邹衍五德终始之术有“始也滥耳”的微词,也并不会全然否定其意义。 然而司马迁对邹衍之术总体持保留态度,这是由于在筹备诸受命活动的过程中,太史令往往需要与方士共事,见证了太多方士的怪诞欺伪。 《史记》多次提点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其一,就判断汉得天命及德属所归的途径而言,方士往往选择伪造、假称符瑞。 例如文帝时,公孙臣就称“土德之应黄龙见”,后因“黄龙见成纪”被文帝拜为博士推行受命改制。 其后新垣平也伪造汾阴周鼎出土作为受命之符。 武帝之时,方士齐人公孙卿也将“汾阴出鼎”视为符应,据此伪造了“黄帝得宝鼎宛朐”[4]1393的故事,认为应效法黄帝施行土德②公孙卿在武帝受命改制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太初改历正是对其所述黄帝“迎日推策”故事的追模和再现,武帝封禅规划也以其“汉兴复当黄帝之时”的理论为重要基础。 详参郭津嵩《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载于《历史研究》2021 年第2 期,89-108 页。。 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已然披露了这些行为的虚造本质[10],讽意隐然。
不同于方士之说,《史记》诸多篇目都强调了判断五德归属应依据历术。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当时人而言,历法不仅有生活日用之价值,更有着沟通天人的重要意义。 汉昭帝元凤四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即云:“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5]978正阐发了历法通天的神圣性质。 制定历法需要对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现象做长期观测,并经过细密的数学运算总结其规律,而最终还要经过天象的验证,以保证人间的历法与天之数度吻合,即所谓“历本之验在于天”[5]978。 对司马迁而言,这些可以被人们实际观察推算的“天道”无疑比方士符瑞所暗示的“天意”更为可信,其中怪迂荒诞的成分明显减弱。 《史记·天官书》亦有此意。 《天官书》中虽载有大量星占内容,但仍试图寻找出星体运行规律,而形成固定预言程式,与方士肆意鼓吹神异有本质差异。
其二,方士与司马迁对武帝封禅改制等天人受命活动的意义理解也并不相同。 方士往往更希望迎合武帝对于“不死”的期待。 如李少君劝武帝祠灶,目的是可以益寿见蓬莱仙者,“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4]1385公孙卿也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4]1393,并且利用了四分历术的周期结构制造了一套黄帝不死的学说[11],使得改历活动也具有了“不死”的象征意义。 武帝听信其言,太初改历诏中便出现了“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4]1260之语。 此后又有公玊带称:“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4]1403武帝亦从之祠于东泰山。 方士宣扬皇帝封禅、受命改制可得个人不死,其实消解了国家典礼的神圣庄严。
而与方士不同,司马迁对受命改制的重视出于更深的政治关怀。 此前秦始皇施用水德。 《史记索隐》以为“水主阴,阴刑杀”[4]238,因此秦政主法家。 司马迁称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于是急法,久者不赦。”[4]238秦行法家符合“五德之数”,因此一旦汉家改命,应新历之数,也就意味着会罢用水德之酷政。 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迁会始终不赞同张苍延用水德。 与其说司马迁认可邹衍五德轮转故事,不如说他是希望借助这一观念促使汉政从此转为宽松温和,罢酷法,行仁政。 究其根本,司马迁最关心的始终是邹衍学说“仁义节俭”的旨归,而非邹衍之“术”。 对于王朝易代背后的天人关系,司马迁认为关键在于人能行“仁义”而得天命,而非仅仅依靠客观条件。 《秦始皇本纪》论赞引贾谊言秦覆灭之由:“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282。 而《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记汉初诸侯损益则云:“形势虽彊,要之以仁义为本。”[4]803强调仁义的影响重于形势,自然也更重于“德运”。
综合来看,司马迁将邹衍学说分为多重层次,于不同篇目散开论述,且对邹学态度时褒时贬,反复迂回,这些书法背后皆有具体现实的原因。 司马迁深度参与了西汉受命改制活动,而后者的实施参照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司马迁对此说的怪迂多有微词。 但无论是为了不触怒武帝的现实考量,还是对自身职责的尊重,抑或是出于改秦德施宽政这一最终期许,他都不会全然否定此说。 尽管接纳了五德终始说流行的现状,但司马迁依然对其说学理内部有细致分辨,他赞许邹衍以历法推算德属的学术途径,而反感燕齐方士妄自敷衍邹说中的符瑞内容。 因为太史令作为世代司掌“星历”之事的天子职官,无疑比方士在“究天人之际”问题上更有权威,是真正传邹术而“能通”之人。 《史记》论载邹衍书法皆显示了司马迁批判同时借用邹学的复杂心路。
三、“务于治”:《史记》论载先秦诸子学术的书例
除上述天官星历之职外,西汉太史令亦执掌“文史”之事。 如《太史公自序》所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4]3319,司马父子曾负责图籍整理工作。 学者即以为《史记》诸子列传带有图书叙录的色彩[12][13],而《史记》对邹衍的评述也无疑带有辨章诸子学术的客观态度。司马迁将邹衍之学区分为“术”与“归”,正是《史记》评述先秦诸子学术时所用的一般书例义法,传达了司马迁对学术与治国关系的共通理解。
《史记》对诸子之学的直接评述见于《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指》。 其开篇云:“《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4]3288-3289。 表明诸子的言论内容虽然彼此殊途异路,但有一致之归,即“务为治”。 在这一“同归”之外,诸子学说具体内容则被《论六家要指》称为“术”:“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4]3289,3292。与治天下之“归”相比,“术”是则工具。 出于这样的实用考虑,《论六家要指》虽然偏袒道家之学,但依然得以超越学术的门户之争,较客观地评价诸子之学的优劣之处。
或曰司马迁的学术立场与其父司马谈有异,但从《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父命的尊崇来看,二人在学术取向上至少不应存在绝然对立的可能。 事实上,司马迁的书法也持有《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态度。例如对“儒术”一词的使用便显示出司马迁对“术”与“归”的清晰区分。 《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中从未出现过这一词汇,它集中出现在武帝前后叙事之中。 至于汉世,诸好学“儒术”者大部分都是司马迁隐秘讥刺之人,其中尤以公孙弘为代表。 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4]2950。 《儒林列传》曾借申公之语批评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4]3124《汲郑列传》更称其“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4]3108。 其他如陈余、窦婴、田蚡等“好儒术”之人,《史记》亦未曾给予青睐。 《史记》讽刺时人好“儒术”,与批评邹衍之徒用五德终始术十分相似,皆反感此类人阿谀诈饰、逢迎人主的本质,内里并无孔子师徒所传仁义之旨。 此外,《史记》也记载了不少修行“黄老术”之人,但司马迁似也并未认为修习“黄老术”是必要之事。 《曹相国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4]1975这里“不得不”与“尊其术”的语气中都有超然旁观的意味。 此外,《史记》也记载了“申韩之术”“帝王之术”“君臣之术”“危亡之术”等等,但均未对它们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偏好。
其实,《史记》并未将任何学派之“术”置于最高位置。 《史记》赞赏的许多人物甚至毫无学术师承可言。 例如《张丞相列传》便云:“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4]2685-2686申屠嘉“无术学”,异于前任宰相萧何、曹参、陈平曾修习黄老之术,但其德与治依然可以与这些开国名臣相并论。 又如《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将学士与游侠并称,曰:“学士多称于世云。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4]3181学士以“术”取宰相,多为世人所称羡,但他反而同情闾巷游侠,虽无学术仍持义怀德,却声名磨灭。
归根结底,司马迁并不过分看重“术”,他更关心这些“术”的实效和目的。 《货殖列传》便因此否定了老子小国寡民的主张:“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4]3253这便是司马迁对势变世异,而老子彼说于当下不再能够“为务”的清醒认知。 故《老子韩非列传》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4]2143表达了对非此即彼的门户之争不以为然。 正如《论六家要指》所论,六家皆有所短,然而其长处“虽百家弗能废也”。 故诸子之“术”所能“务于治”者,《史记》则取之,而并不求全责备。
《史记》对邹学的取舍态度正符合其一贯的论学宗旨。 从“归”的层面而言,邹衍学说有“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最终指向,因此司马迁未尽弃其学。 也正是由于邹说能够“后引之大道”,司马迁推测邹衍之术或也是一种曲折的劝谏方式。 《孟荀列传》称:“驺衍其言或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4]2345顾炎武曰:“谓伊尹负鼎、百里奚饭牛之意,借此说以干时君。”[14]这也符合《史记》对于“术”的工具性认识。 具体到“术”的层面,邹衍历术应属于《论六家要指》中的“阴阳之术”,有“序阴阳四时之大顺”的功能,因而也得到了司马迁的肯定;而对于“五德终始”之术,由于它仍可能有助于“为治”,司马迁也选择利用其说,辅助汉家受命改制。 也正是基于这一论学宗旨,司马迁并不会认可方士受命符瑞之术,因其目的是满足皇帝长生、好功的欲求而为己牟利,殊无益于仁治。
综合全文来看,《史记》对邹衍学说的态度与司马父子的太史令之职有关,且符合《史记》评述诸子之学一贯的书例宗旨。 这也导致了《孟荀列传》论载邹衍书法独特。 尽管本传在篇幅上极重邹衍,并在叙事中融入大量司马迁论述,然而司马迁的儒家立场,又使他绝不可能在篇目上以“邹衍”为题,最终造成了本传题目与内容的某种错位。 如此而言,《孟荀列传》确实是《史记》中司马迁刻意为文的代表,它不仅记载了司马迁对诸子及其学术的评价,更暗示了司马迁在“天人之际”问题上的立场。 正如清人吴见思所云:“此文纯以一气旋运,借诸公组织于中,非因事生文,反若因文生事,故并不见其多人也。”[15]此正乃恰切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