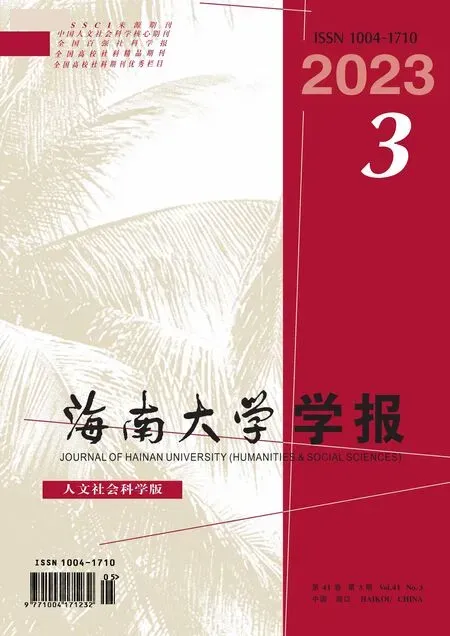智能时代的哲学
程志敏
尼采写过一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其中的“悲剧时代”仅仅是时间概念,并不说明哲学与悲剧之间有什么联系:哲学既不是悲剧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悲剧的外化。那时,哲学刚刚诞生,鲜活而灵动,蓬勃而明朗,尽管本质上是以特殊的方式来阐述悲剧所表达的核心主题(即对命运和自然的严肃思考),本身却还没有成为“悲剧”。但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似乎已耗竭了自己的生命力,从如歌的行板和狂飙突进的凯歌逐渐弱化成悲凉的挽歌。海德格尔断言“哲学的终结”,坐实了哲学的“完成”与“告别”,如今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哲学似乎更加可有可无了。
人类整体上撞上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观念,甚至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日新月异而不断强大的人工智能大有取代人类成为地球主宰之势。在经受了达尔文主义洗礼的现代人看来,存在物的无情演化乃是铁一般的规律,自然界曾经抛弃了恐龙而重新选择了灵长类,那么,它同样可能抛弃人类,再一次选择另一种存在物,这种存在物不必是纯粹的碳基生物,而是任何可能的存在者,比如硅基或者碳硅合成体。
全世界都沉浸在终末的气氛中,哲学界的焦虑不过是倾巢下的累卵,本来不值一提。但兹事体大,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皇冠上的明珠,必须对当前局势有所交代。不过,这可能超出了哲学的能力,因为哲学的本质在于反思(nachdenken),意即“后思”,哲学从来都不以预言未来为己任——那是宗教信仰的事情,毕竟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才起飞。哲学家往往以普罗米修斯自况,仿佛有能力“前思”(pro-metheus),这无非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其实,哲学家多是百无一用的书生,笃好空言,喜谈心性,醉心于逻辑,张狂于概念,乐此不疲,真正到了危难时刻,则张皇失措,束手无策。人类“沦落”到今天岌岌可危的境地,空疏、避世而滞后的哲学当然难辞其咎。
在当今的智能时代,哲学首先要做的,还是反思,以期通过“自刻”,即痛彻心扉的刮骨疗毒,完成初步的自我救赎。只不过这次的反思不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自我的检讨。哲学有自己的使命,不必因科学技术在近代的辉煌成就而亦步亦趋,也不能过于清高而无视现实的迅猛发展。但不幸的是,当前的哲学恰好就陷溺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极端的思潮中,一方面成为了科学的附庸,同时又高傲地沉浸在概念的思辨游戏里,另外因不甘心失败而逃避到理论的乌托邦中,总之未能跳出来作全面的观察和整体的把握。哲学必须作出重大改变:扬弃原有范式,更加亲近现实,转而关注存在的意义,与技术“若即若离”,与科学共同成长——科学技术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哲学不仅未能前进一小步,反而丢掉了先哲们艰苦思索所获得的深刻洞见。
其次,与宗教神学相比,哲学本来就是属人的学问,其首要的是关于人的思考,因而哲学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必须坚守自己的本分或职分。智能时代的技术如此强悍,似乎颠覆了人类对存在、世界和人性的认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但既然是“危机”,则在“危”之外必然还有“机”:智能时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困惑甚至恐惧,也带来了认识自己(gnothi auton)的良机。
古往今来的哲学都如是教导:世间万物唯人为尊,一切存在物如果还有意义或目的性,则都是以人的存在为判定标准。宇宙虽然不是人类创造的,但如果没有人,宇宙就是荒凉甚至荒谬的存在物。这种自以为是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终于养成了人类现今娇气、娇惯甚而骄横的习气,人类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宇宙万物中的一种。即便唯独人类才拥有理性,也远非宇宙之主,更何况现代日益狭隘的“理性”早已不再为人所垄断,人工智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类中心的神话。
人类只有放弃“地球主宰”之类的思维方式,才会彻底摆脱当今“科技奴隶”的地位。人类也许正是因为渴求主宰宇宙,才拿灵魂作了交换。主奴辩证法应该让我们清醒认识到:自然不是专供人类使用的资源,而是人类存在的母体,至少是休戚相关的“共在”(mit-sein)。人类不是天之骄子,不可为所欲为,否则“肆心”只会招来毁灭。传统哲学的“主宰”观念无疑是导致人类堕落的罪魁祸首,因为对自然的奴役也终将反噬自身,异化成自我的奴役。智能时代的哲学不是要人类放下身段,而是要人类回到实然和应然的存在轨道上。
最后,哲学要帮助人类充分把握“智能”的本质,并以此重新思考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人工智能”乃是理性理智化(即逻各斯的努斯化)的结果,理性的丰富内涵日益固化为功能性的理智和智能,最终成为技术化的“计算”或“算计”。机关算尽太聪明,人类焉得不沦为“算法”的奴隶?懂得这一点,也就找到了破解的入手处。
一方面,要正视并尊重人工智能的独立性和必然性,就像尊重世界上的每一种存在物一样。“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名称本身就有很强的误导性,依然表征着人类的狂妄自大。所谓artificial,来自art(技艺)和facere(制造),意指不是自然生成,而是人为之物。但这种智能归根结底在形式上是自然的,内容上也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要打破人类对“人工智能”不必要的恐惧,毕竟它并非真正的“智能”,而只是“仿智能”,即信息处理技术或者选择性计算而已。但人类也要把人工智能当作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惕厉自省。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好,更能让我们认识到自身的限度,从而走出单纯的技术化存在形式,重新回复到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之中。
总之,人工智能是否是人类自造的特洛伊木马或潘多拉魔瓶,目前还无法判断,但哲学必须对此有严肃的反思,不能像浮士德那样把魔鬼为他掘墓的声音当成天籁之音。与其悲观地断言人工智能为人类敲响了丧钟,不如更加现实、稳妥而富有建设性地说:人工智能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不能对此置若罔闻。人类究竟走向“超人”,还是堕落成“末人”,与外在的科学技术关系不大,而在于自身精神的历练和成熟,以及道德品性的提升。新的哲学依旧会探讨自然、政治、爱情与幸福,会继续陪伴着人类,关怀、指导、慰藉并温暖着我们柔软、敏感而本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