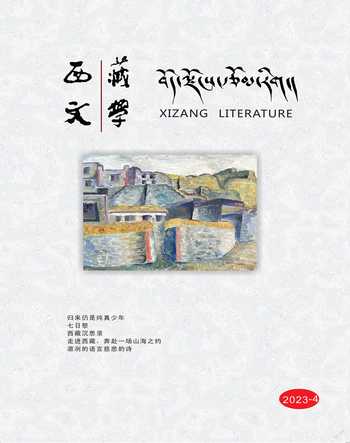高原的影子(组章)
杨乐
村里的小孩总喜欢追着云的影子奔跑,抑或是云的影子追逐着奔跑在阳光下的孩子们。大人们害怕孩子不懂得回头就这么一直跑下去,便捡起地上的干牛粪连喊带骂地追了 上去。
往回走的路上,大人厚实的影子将孩子紧紧地裹了起来,看不清那小脸上是失落还是依然欢快,只是飘向远处的那朵云突然停了下来,怅然若失地回望着这边。
羌塘十一月里的雪如期而至,又像是例行公事。它不顾小孩和云朵的美好情谊,它甚至不管太阳此时还明展大亮地挂在天边,便一顿纷纷扬扬、飘飘洒洒。
雪像是从太阳的光圈里突然喷洒了出来,在光的照射下,每片雪花都有了自己的影子。在蔚蓝和金黄的天空里,如《沉睡魔咒》里吵闹的小精灵乘着风去参加女王的婚礼。
雪落地即化,慢慢地将村里的青石路装饰得像一面镜子,牦牛傻傻地站在路中央,看着银辉落成金汤。
雪的影子终归会沉入大地,变成来年的草,掘地的鼠和肥壮的兔子。这些鲜活跳动的生命,却在雄鹰俯冲而下的影子中,缩成一团,露出自己最柔软的地方。好像它们长这么大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从大地的深处再回到天 空上。
鹰不同于一般的鸟,它见过世面,见过千里之外树的模样,它可以栖身在最高的山顶,让最烈的风替它梳理骄傲的羽翼,只要它愿意,只要它还没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雏,它随时都能到森林里换换口味,到大海的上空感受湿润的气流。
它的影子便是自由的形状。村里其他的鸟胆子再大,即使敢在狗嘴里抢食吃,也不敢跟鹰相比,它们的翅膀扇动频率太快,看起来一点都不稳重。最重要的是,它们终其一生也飞不出这个村子,看不到千里之外树的模样。
夜里的高原是白天延长的影子,因为它太过庞大,我们无法看清它的全部,只有在晚霞的余晖中,才发现它一步步潜入天的另一边。牛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可仍旧选择不声不响跟在人的后面,人回屋休息的时候,它也会煞有介事地躺在地上。
只有家里的女人们知道牛的秘密,知道它们趁着夜色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在男人们早上起来的必经之路上拉出一坨坨巨大的粪便。牛会在晚上十二点、清晨六点准时出现在女人们的视线里,女人用手一上一下按压着牛的乳房,牛也会一遍一遍倾听女人憋在肚里的“苦水”。漆黑的夜空下,女人戴在头上的电筒将牛身下那对乳房投影在屋后高耸的山梁上。
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也会对河水倾诉心声,只是河水急于远行,不愿意因为这些琐事而停下来。女人笑也好,忧愁也罢,河水都会驮着她此时的影子奔向远方。高山、雄鹰,万事万物都会把自己的影子交给河水,任由它讲述给下游的湖泊、鱼虾。
我也会蹲坐在村外的河边,看着那股细小的河水,你追我赶、奔腾跳跃。可我却不愿意将影子交付与它,这河中有太多相同的哀愁与 笑脸。
在我窥视高原的时候,高原也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我的影子。不再飘忽不定、模糊不清。它将自己投向巍峨的雪山,然后一步一步慢慢 往前。
河边的理发店
我曾经见过一只戴着黑色项圈的老黃狗,时常蹲在人民北路的十字街头等待红绿灯。它身旁并没有人跟着,却每天循着同样的路径像上下班一样穿梭于车水马龙之中。那时候的我刚来成都不久,总感觉周围的人说话都太快、食堂里的饭菜都太辣,便也经常独自穿过那条马路,跑到府南河边买包子吃。那家包子铺旁边有一家名叫“艺之剪”的理发店,忽而有一天,我发现那只独来独往的老黄狗正躺在旋转的彩灯下面晒太阳。
初春的府南河微波荡漾,墨绿色的河水之上偶尔还会掠过几只洁白的飞鸟。老黄狗趴在地上眯着一对三角眼,慵懒地看着漫步在河两岸形形色色的人们。当它看到我走过来时,竟起身一个劲儿地摇起了尾巴,像迎接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抚摸着它头上如松针般坚硬的毛发,跟着原地转了几圈,便莫名其妙地走进了那家理发店。
店里弥漫着柠檬洗发水的味道,明媚的阳光投射到圆形的镜子上,像是在天花板和墙面上又多开了几扇窗。吹风机将一位女士的长发吹散在空中,哗哗的流水声隐藏在人们熟络的谈笑间。其实这家热闹的店里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一对手艺夫妻,还有一位专门为客人洗头的胖姑娘。我那天理了一个板儿寸,就按照这个发型,一直保持到了七年后的今天。
夫妻俩就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女人负责纹眉、烫发和美甲,男人操着把剪刀从早忙到晚。给人洗头的胖姑娘来自西昌,据说她之前还在吉林长春干过几年足疗,因此手上的力道非常足。成千上百双脚丫子和成千上百颗脑袋,她说这就是自己青春的全部。而躺在门口的那条老黄狗,本来四处流浪,因为他们经常把剩下的饭菜拿给它吃,时间久了便留了下来。它只白天守在这儿,夜晚还是会消失在城市的街道里,不知在寻觅什么。
成都永远有开不完的花、闻不够的香。慢慢地,我开始习惯了这里的麻和辣,以及言语中的俏皮和优雅。我不用再独自前行,手中又多了一份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那河边的理发店在风吹雨打中、虫鸣鸟叫间过去一年又一年,还有那条依然孤单的老黄狗站在门口欢快地摇着尾巴。
时光像是府南河里流淌的水,缓缓向前,却日夜不停。
理发店的夫妻俩从当年的谈论房子问题到如今孩子该在哪里上学,经常吵得面红耳赤,还得让上门理发的老主顾们从中劝解。胖姑娘比以前更胖了,在给我洗头的时候还是特别喜欢提起曾经在北方的日子。第一次看见鹅毛般的大雪、遇见生命中的第一个男孩,长春和西昌的烤肉很像,可是她却没有福气能来尝一尝。
老黄狗虽然每天还是循着同样的轨迹准时出现在理发店门口,可它的耳朵和尾巴都已经耷拉了下来,那双三角形的眼睛又增添了几分忧郁和疲惫,见到路上的车子似乎都懒得去躲了。它的皮毛渐渐失去了光泽,变得行动 缓慢。
终于,我在人民北路的十字街头再也没有看见它。
胖姑娘说那段时间里它就不怎么进食了,趴在门口的毛巾架下面,只有店里面来客人的时候才会吃力地摇晃一下尾巴。再后来,它便彻底地消失了。人们都说狗在知道自己命数将至的时候,就会提前去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可是这三个人还是关了店门,找遍了周围所有的街道,那应该是一个秋天,成都的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每当走过那条熟悉的十字路口,我还是会想起那条蹲在地上等待红绿灯的老黄狗。它像是一个揣满了故事的人,只是不会把心中所想表达出来。它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懂得那么多的人情世故。是谁在它的脖子上套了一个黑色的项圈?它在无尽的黑夜里又在寻找什么?为何它会循着一条相同的路走了一辈子?
我仍然会每隔半个月来到这家河边的理发店,听那对夫妻因为生活琐事而拌嘴,听南方的胖姑娘描绘我千里之外北方的故乡。
回到普仓
那曲的草已经开始黄了。
重新回到这片熟悉的草原,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想牵着四郎的手,带她看看我曾经独自走过的那条路。
像是这世间散落的珍珠,四郎出生的草原距此竟相隔千里之远。对于她,这将会是一段多么奇妙的旅程啊,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风、湖泊和万物生灵。某一刻,我甚至会为她能够来到这里而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幸福。
我曾多次向她描绘过藏北的苍茫辽阔。如今,它正像汪洋大海一样向我们涌来。那远处的山峦、低垂的云朵,天地贴得那么近,像是一幅壮丽的油画,又像是宇宙交融在了一起。这里有我的孤寂、寒冷和而立之年才冒出来的 梦想。
我将再次拥抱这片草原,见到可爱的 他们。
当车驶过那道蜿蜒的山梁,被太阳晒成了金黄色的普仓村又一次跃入了我的眼帘。村里的小河还在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流,发出阵阵清脆的声响。除了风雪声,这曾是我在无数个夜晚相伴入眠的曲调。
那圆鼓鼓的山包上,一群可爱的牦牛正披着金辉慢吞吞地往家里走。它们可能都已不记得我了吧。我曾在这几座山上和它们一起喝过酒,一起晒过太阳。在那段又慢又长的时光里,我发现这群庞然大物不过是些流着鼻涕、倔强又贪玩的孩童。
推开村委会的大门,我带着四郎来到我住过的宿舍,生活、办公的阳光棚。我习惯在哪张桌子上吃饭、在哪里锻炼身体,又在哪里搓着手开始记录生活,我都一一指给她看。而我的目光不论停留在哪个角落,都能隐约看到一个披着军大衣的男人正侧着脸思考着什么。时光只过去两年,一些没有带走的东西都变成了 影子。
邻居端来了拉拉、酸奶和风干的牦牛肉。我们还和以前一样,简单地打个招呼便只剩下了笑脸。我像是一个带着媳妇回到老家的孩子。她们坐在对面,一会儿打量打量我,一会儿又仔细端详着四郎。
临到离开的时候,我才突然注意到蹲在院墙下面不声不响的二狗子。它就是我曾经在文章中牵肠挂肚的那条丢了女朋友的狗。听到我呼唤的声音,它竟拖着自己有些年迈的身体和那条笨重的铁链,原地转了一圈。这真叫人受宠若惊。要知道我曾经坚持跟它说了一年的心里话,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亲热过。我抚摸着它的额头,它吻了我的掌心。我应该给这位朋友带一只鸡腿或是其他的什么。不知道下次再回来,它还在不在这里,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脾性和它有些相似的男人。
在海拔4600米的羌塘高原,我和曾经一起并肩战斗的队友们热气腾腾地围成了一桌。聊着曾经驻村的往事,那些让人又爱又恨、艰苦和明媚的日子。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赤诚的红晕。在这天寒地冻的草原上,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为朋友遮挡来自四面八方的风。
我对四郎说,这就是我走过的那条路,和我路上认识的那些人。
深夜,我从睡梦中一次次惊醒。
干渴。疼痛。这似乎是藏北草原为我这位故人带来的风情特产,它让仅有的一个夜晚变得无限漫长。看着身旁已经睡熟的四郎,我盯着天花板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就像是几年前刚到这里时一样。
多少个难熬的夜晚啊,我一遍又一遍思考着自己困顿的旅途和平凡的人生。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辰,并将它挂在了山谷空旷的夜空。可如今,它却渐渐模糊在了城市繁华的灯火之中。我无法再平静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周遭是永不停歇的车水马龙。
我穿起衣服,来到了深夜草原的边缘。
风吹着千年的草皮,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伸向草原腹地。前方是无尽的黑暗。
我大步地走了进去,任由猛烈的风像海浪一样拍打在身上。我是一只归途的鸟,张开双臂拥抱和呼吸着眼前宽广辽阔的一切。细碎的雨点透过我的身体,横着飞向了另一片草原。我看着黑暗中白茫茫的一片,忽然想起了诗人海子的那首《日记》。
“姐姐,今夜我在藏北草原。”
老 家
内蒙的冬季里,只有芦苇挺着纤弱的身子迎着凛冽的西北风左摇右摆。一场雪飘落在泥土上,霜再打下来,松软的雪地上便又结起一层冰,万籁俱寂,偶尔听见一记爆竹声,响彻云霄。我会在清晨登上屋顶,看着一轮红日升过远处黑色的杨树林,散发出明媚耀眼的光芒。
十多年前,我曾日日夜夜生活在这个村庄,看四季轮回,浑浊的黄河水奔腾地灌溉着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壤。我曾折断过这路邊的一棵杨树苗,如果它还活着,应该也能昂扬地挺立在河套平原,直指深蓝的天空。可我却拿着它横扫了一片庄稼地,无数向日葵被拦腰折断,那些橙黄色的花朵,落到地上仍然笑得像一缕阳光。
我将纯白的口罩挂在带着刺的红柳上,然后蹲坐在雪地里看一条蜿蜒的兔踪伸向远方。这个位置夏天时是一片麦地,我曾被人追赶到这里,在漫天星辰下匍匐在地上,听着剧烈的心跳声撞击松软的土壤。我本打算把邻居家废旧的发动机偷出来卖个好价钱,攒着为父母修一栋大房子。而今,那栋破旧的泥坯房仍然在,时间并没能改变什么,只是把人活生生地拖向了岁月的另一边。
那年爆发了“非典”,所有出门在外的人一夜之间都回到了村里,我只记得周围突然出现了一帮光鲜靓丽的城里娃。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指着我露在外面的大脚趾头问:“你没有球鞋吗?”我说有,但要等到开学才能穿。第二天,她把一双打着“对号”的白色球鞋塞到我的手里说:“我爸没穿过的。”夜晚,那双球鞋跟天上的月亮一样皎洁,我和她坐在麦垛上,忘记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
后来那女孩突然消失了一个月,我翻了很多道墙,爬了很多扇窗户,甚至把耳朵贴在烟囱上仍未找到她。再见面时,我们一起在麦场上丢沙包,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又突然像只老虎一样咆哮起来,吼到声嘶力竭时泪流满面。
当初的麦场铺了青石板,上面修了些健身器材,有几个小孩儿将篮球扔在地上踢来 踢去。
硬化的路,新修的砖舍,以前的东西都被推到了偏僻的角落里慢慢老去。人的心似乎也变得更加坚硬,外面的世界让人遍体鳞伤,我们将冷漠的面孔乘着车带回了故乡。我也像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碰见谁也只是寒暄几句,我向母亲探听儿时玩伴的近况,内心却期待着生活的另一份悲惨。
老家在我眼里慢慢地只剩下冬日的景象,只是在三年前姥姥的葬礼上才又看到那漫无边际的绿色。一条大雾弥漫的村路上,有无数彩色的蝴蝶、蜻蜓,野草伸出水面,缠绕在树干上。我和表哥在灵前喝得烂醉如泥,当了五年兵的他被世事折磨得佝偻了身子,却像个相声演员一样,充满了欢声笑语。自始至终我们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只是长跪不起,让烈日灼心,让膝盖下的草钻到血里肉里。
出门在外的人们因为“新冠”又都回到了村里,当初的孩子早已变了模样,现在还随时随地戴上了一副口罩。可村口野滩里放羊的白姓老汉却能一眼辨认出来,他曾指着开裆裤里露出来的“雀儿”断定我们未来的人生走向,村里有一半的生瓜蛋子被他说成是能干县长的料。他满脸通红地站在地沿上,头上还冒着股热气,老爸说他这些年吃了上千颗羊宝,可惜就不知道娶个老婆。
排干渠里的冰被冻透了,冰层下面是已经干枯的土地,有一两只老鼠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我站在这里只要闭上眼,就会看到一副轻巧的身子奔跑在原野上,一直跑到那年夏天的某个黑夜里。我跳进了同样黑色的水里,那水流瞬间变得凶猛湍急,翻卷的泥沙里像伸出了一只只干瘪的手,缠绕在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拼命地爬上了岸,光着身子穿越了整个村庄,再看到家门口的破栅栏时,像是重获了新生。
就这样走走停停,模糊的影像和声音伴着刺骨的西北风拍打在我脸上。天空湛蓝,那轮红日已将村庄染成了金黄色。我看到路的尽头走来一个背着破旧书包的少年,我和他不约而同地俯下身体,捡起地上的一块儿土坷垃,用力掷向天边。
清凉的夜
我没有生出翅膀竟然飞了起来。
有两股强劲的力量从腋下将我托上了高空,原来云层之上的风如此清凉。月亮像一轮巨大的碾盘,白色,闪闪泛着寒光。薄薄的雾气笼罩着大地的一切。有一群不知名的鸟从我身旁飞过。我用力划动了一下手臂就将它们冲散在漆黑的树林里。整个城市都变成了点点星光。可以这样自由自在地驾驭自己,感觉真好。这一刻,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 地方。
我多么想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分享给朋友们啊!出现在他们的窗外道一声晚安。或是索性带着他们从这座繁华都市的夜空呼啸而过。可突然发觉,我并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即使我们共同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八年。
我尝试着旋转自己的身体,像筷子搅动鸡蛋一样钻进一层层的云雾里。青松、石涧、溪流,还有那些从未有人登上过的山顶。我又像是身处在汪洋大海,每摆动一下手臂,夹一下双腿,都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送我到更远的地方。
慢慢地,我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混杂着青草和泥土的清香。我看到了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像一条巨蟒朝着西北方的平原奔流而下。在月光的照射下,那河面上像洒下了一层白色的珍珠,随着水流的哗哗声,翻滚跳跃,灿烂夺目。我俯冲而下让身体贴近水面,又将双手轻轻伸进水里,带起两条绵长的波纹。河水从我指尖划过,清凉舒爽。黄河水的味道还像十多年前一样甘甜芬芳。它日夜奔流,从未停歇。
我果然飞回了老家的村庄。
我从村子后面的杨树林穿行而过,落在了自家的屋顶之上。门前的沙枣树,一口只能打得出咸水的井,一排木栅栏围成的羊圈、圈里有站着或是卧着的几十只羊。我本打算跳进院子从窗户看一眼熟睡的家人,却突然听到身后响起了母亲的声音:“乐儿是你吗?我最近老是做梦,梦到你要回来。你回来了咋不进家门呢?”我不知为何连头都没回便仓皇地跑开了。从自家的屋顶跳到邻居家的粮仓,翻过一座又一座用泥巴和麦秆糊砌的院墙。我拼命地奔跑着,还故意不断改变自己的身形,想极力地用后背告诉她,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趁着夜幕穿墙过户的贼人。一直到翻过村子边缘最后一堵墙,我再一次挥动自己的双臂,腾空而起。
我飞过麦田,掠过垂着头的向日葵。我再次飞越清凉的薄雾来到云层之上,只一瞬间,便回到了城市的上空。看着大地上璀璨的灯火,我将一切都抛之脑后,就连刚刚眼角流下的泪水也全被风带走了。
我又来到一座泛着红光的楼顶,看见一位熟悉的老人正扶着栏杆泪眼婆娑地对夜空诉说着什么。老人在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如今他已经老去并不得不离开这里。当我试图再靠近一点想要听清楚那些飘散在风里的话语。他突然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看着我。随后竟也像我一样腾空而起,挥动着手臂冲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飞向了府南河。我听到背后老人瘦削的身体像一面被风撕扯的旗子,在空气中发出猎猎声响。河面上潮湿的水汽像一只塑料袋糊在了我的脸上。我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出现了老人压下来的影子。而我却渐渐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双腿变得异常沉重,两只手臂也丧失了向上攀升的力量。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了,我的身体彻底地淹没进了冰凉的河水里。
我醒来在午夜的床上。脚下开了一晚上的风扇将我的两只脚吹得冰凉。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用笔将脑海中还未褪去的一些片段记了下来。梦境就像是用水写在岩石上的文字,稍纵即逝。我曾无数次做过这样奇奇怪怪的梦,不知它们因何而生,有何启示,却总在周围事物变得清晰时化为乌有。
我打开阳台的窗户,夜里清凉的风扑面而来。外面昏黄的路灯、安静的街道、笼罩在远山淡黑色的薄雾,还如同梦境一般。我大口呼吸着窗外的空气,感受着这秋夜里被风吹动的每一片薄薄的叶子。
院墙下的狗
向哥在电话那头说,那曲最近天气不错,中午坐在玻璃房子里比围着火炉都暖和。我望向窗外,今日立冬的成都也同样阳光明媚,虽然没有水洗般湛蓝的天空,但也一扫往日的阴霾,让人心情愉悦。他还跟我聊起了村里那些熟识的事,说村长家的外孙女英秋就要上小学了,次仁江村还会隔三差五抱着颗篮球问杨叔叔什么时候回来,那头喜欢喝拉萨啤酒的牦牛还是不服任何人的管教。一切都如往日一样,只是那只拴在院墙下的狗,如今变得越来越 瘦了。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提及這只狗,它就拴在村长家的院子外面,与村委会一墙之隔。每天清晨,我都会拎着保温杯蹲在墙边对它说些“半人半兽”的话,它一声不吭地盯着我,有时还会侧着眼睛露出一排锋利的牙齿。藏族人是不轻易训斥狗的,像斥责牛一样。牛记吃不记打,狗却都记下了,即使在没人的时候也会小心翼翼。也因为如此,它长到七岁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我将它命名为“二狗子”,很多穷苦出身的孩子都叫这个 名字。
二狗子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是附近山上的一条野狗。像它这种根本没有社交、一辈子宅在家里的狗,能碰到主动上门交往的,简直是老天恩赐。因此它倍加珍惜,每日都会剩些饭菜等待“佳人”回来,像是一个痴傻的汉子盯着山梁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呜咽声。远远地看见时,更会兴奋地直立起来,将那根拴在脖子上的铁链绷得笔直。
可是好景不长,那只放浪惯了的野狗没有满足于残羹剩饭,竟然在一天夜里,咬死了一头刚出生的小牦牛。牛跟村民一起将它围堵在了村委会的院里,旁边二狗子发出了像狼一样的哀嚎,把院墙上的泥土刨下一层又一层。村民不会轻易杀生,也没有把野狗的腿打断,只是捆在了摩托车上,扔到了两百公里外的班戈县。可二狗子毕竟只是条狗,它能理解的范围出不了这个村庄,连山的后面是什么都不知道,在那个嘈杂的午后,它那像春天一样的爱情,就此结束了。
我又一次望向窗外,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两边的脸颊竟慢慢地浮现出一片高原红。我曾在这样舒畅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去开导二狗子,甚至以身犯险拿根棍子想让它再恢复一点以往的活力。然而,它始终像一颗霜打的茄子,整日趴在一汪水坑上一动不动,牦牛吃光了它的饭还将盆子顶到了河边,墙上的麻雀开始肆无忌惮地往它身上拉屎,孩子们将它的狗窝当成了球门,即使踢落在了头上,它也只是不声不响地拖着那条铁链爬向另一边。
村长对我说,这条狗看来已经老了,它小的时候都不知道睡觉,听见山谷里面风吹的声音,就能挺着身子叫喊一晚上。再强壮的牦牛它都敢对着干,脖子上以前拴的麻绳也换成了现在胳膊粗的铁链。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变化,总会联想起他经历的事情,而对待一条狗,却只能看到它的牙口和身板儿。我每天一顿不落将剩饭倒进它的盆里,却在相处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它可能更想喝一口那不远处河里的水。
这村里每家每户都养着一条这样的狗,它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拴在一堵院墙下面,耳朵能听得很远,眼睛却跟着干着急看不见。它们那点可怜的见识甚至都比不上一头上山吃草的牛,于是就用爪子将脚下的那片泥土挖成一座座土坑,试图看看这地下能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它们看着村里的孩子长大、大人变老,看着山坡上的野草变黄变绿年复一年。它们记得眼前这条村路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并用短暂而又漫长的余生回忆昨天。
此时日头已经偏西。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又想起了那只拴在院墙下的狗,还有那段可以静下心来体会万物的时光。电话结束的时候我还特别提醒向哥,以后再给二狗子喂食,记得多加点水。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