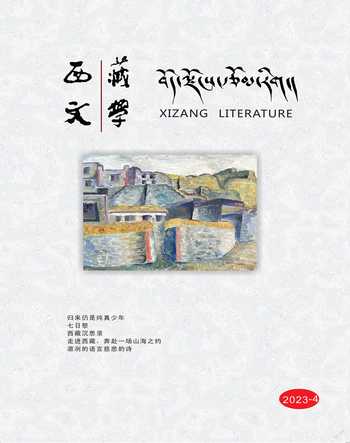走进西藏,奔赴一场山海之约(外三篇)

李慎秋,湖南洞口人。现居拉萨,为中央单位第十批援藏干部。长期从事立法工作,业余读书撰文,以个人微信公众号“市坪放牛娃”为平台,记琐事、发幽思、品生活、读人生。
西藏,在我的潜意识里,总是圣洁而神秘的。圣湖清碧湛蓝,神山巍峨苍莽,布达拉宫雄奇壮美,经幡斑斓多彩,冥冥中蕴着灵性、飘着仙韵。还有那匍匐在地磕长头的藏族老阿妈,将虔诚的祈福,深深地刻满大昭寺前,历经千年的石板路。
西藏,就像一位罩着红盖头的神秘新娘,披着朦胧摇曳的红烛光,迷离中飘逸着摄人心魄的体香。而我,就是那心痒难耐的毛脚女婿,猴急着想掀开那红盖头,去看看她,亲亲她,拥她入怀。
心心念念,必有回响。走进西藏的机会,倏忽间飘然而至——我被选派参加第十批援藏工作。消息来得有些突然,波澜不惊的皮囊里,塞进了一颗驿动的心。
如同丛林深处随风飘落的孤叶,原本也会如那些被我随意虚掷的日子,琐碎平常、淡而无味。然而,2022年7月27日这一天,因我将奔赴这场西藏之约,而变得迥异于寻常,仿佛一潭沉寂经年的死水,陡然间卷起巨澜。
北京的雨,不知疲倦地下了一夜,至清晨,依然淅淅沥沥不停,为众生洗净前行的路,也洗净我世俗的灵魂。“孔子沐浴而朝”,晨光中,我沐浴着天赐的雨水,辞别喧嚣的都市,向着雪域圣城,出发。
“多情自古伤离别。”可是这回,没有“执手相看泪眼”,也不需“无语凝噎”,只因为,我将如飞越峻岭的雄鹰,去奔赴,等待了千年的山海之约。
赴约的路,充盈憧憬、满怀希冀,哪怕再长,也是美好的。鲲鹏般的飞机,翱翔在白云之上,如同幸福的使者,载着我,去遇见,梦里的西藏。
脸紧贴着舷窗,挤压得近乎变形,只为把窗外看得更清楚。飘逸的云团,如缕如絮,变幻着、游弋着,疾速后退。云层间隙,层层青纱帐,道道黄土沟,漫漫戈壁滩,莽莽苍山巅,雄浑里写满沧桑,沉寂中透着寥廓,持续更替、不断闪现。一路风景似画,一路心绪如歌,终于,西藏,我走进了你的怀抱。
与援友一起走下舷梯,还来不及喘息,热情像热浪般瞬即围拢来,浓烈得可以点燃空气。早已等候在此的人群,呼啦啦迎上前,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整个候机坪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手足深情。
不绝于耳的“欢迎欢迎”声中,跨越千山万水的两双手,紧紧攥在一起,在雪域高原颤抖着、晃动着,不同民族的两颗心,深深地印在一起,滚烫滚 烫的。
此起彼伏的“扎西德勒”声里,淳朴的藏族阿佳,双手合十,躬身前倾,献上洁白的哈达,浓浓的民族情凝结成条条白练,戴在脖颈上,流进心坎里。
离开欢迎的人海,登车前往市区,圣城拉萨渐次展现眼前。
道路,在两山之间延伸。峻峭的山峦覆盖着淡淡的黛青色,莽莽苍苍中尽显粗犷豪放,让人顿生扯起脖子喊山的冲动。车行山移,“祖国万岁”四个大字,跃然山顶、艳红醒目,车厢里顿時欢声雷动:“祖国万岁!”这里,虽是边陲,却深深依恋着祖国!这里,天遥路远,却饱含着爱国情怀!
渐渐地,视野越来越开阔。宽阔的拉萨河从峰峦间逶迤而出,掩映在两岸的依依垂柳中,正午的阳光在水面上跳动,激起满河粼粼波光。河水如蓝宝石般晶莹清澈,轻快地跳跃着,奔向远方,唱着欢迎的歌。
穿行在山水拥围的拉萨城区,但见现代化与民族风交相辉映、完美融合。新区、开发区、民族文化园区,清一色裹着藏式风格外衣的建筑,色彩艳丽明快,装饰繁复精美,齐齐整整,美观又大气,处处交织着现代气息和民族 风情。
如织的人流中,穿着时尚、打扮前卫的小哥哥小姐姐穿梭其间。最耀眼、最新奇的,还是身着藏袍的藏族同胞,长袍大襟配上鲜艳腰巾或彩色围裙,或素雅,或艳丽,在金银珠玉佩饰的衬托下,或雄健豪放,或典雅优美。欣赏着眼前这片安宁祥和景象,不由得心生感慨,这不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好的例证吗?
车到住地,抬眼望,天瓦蓝瓦蓝的,澄澈透亮,偶尔飘过几丝薄薄的云絮,仿佛就在头顶,伸手可及。“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或许,李白当年也曾神游至此,才会有这神思和感慨吧。
安顿下来,斜倚窗前,静静地打量这将要工作生活三年的城市。朦胧中的我,似乎随着流动的白云,游走在雪域高原,去沐浴山口的朔风,去追逐盘旋的雄鹰,去穿越皑皑的雪峰,去抚摸悬崖上的野花。
慢慢地,我仿佛也幻化成一朵无名的小花,默默地,装点在山海之间……
煤油灯下那个身影
雪,纷纷扬扬地飘着,漫无边际。小山村的夜,在浓重的墨色中万籁俱寂,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稍显陈旧的小木屋里,透出一丝光亮,一盏煤油马灯,挂在板壁上的竹钉上,冒着黑烟。灯下的缝纫机旁,有个女人正在车衣剪线。
她体态端庄,面容慈祥,眼神专注,一会用尺子量量,一会用剪刀剪剪,一会又嗒嗒嗒地转动缝纫机缝缝,一件上衣初具雏形、呼之欲出。“素手抽针冷,哪堪把剪刀。”略显僵硬的手,粗糙中透着些许黝黑,手指上皲裂的口子有的干裂着,有的似乎快要化脓,但仍然双手熟练地忙活着。偶尔停下来搓搓手,或把手凑近嘴边哈口气,再继续转动冰冷的缝纫机,循环往复。
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多少年来,母亲雪夜里煤油灯下给人缝衣的身影,总会不时浮现在我脑海中,那样清晰、挥之不去,特别是在我想偷懒、想懈怠的时候。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母亲出生在“岩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窝窝里,是家中长女。十八岁那年,母亲嫁到我家。分家析产时,据说全部家当是一间木屋,一斗二升米,一个煮饭的鼎罐,连炒菜的锅都没有,用杉木皮隔个小棚作灶屋,近乎赤地立新、白手起家,母亲就这样拉扯大三个儿女,撑起这个家。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劳作是她生活的主旋律。母亲是个劳动好手,干活很麻利,搂茅背草的,速度快、做得开,村里人都称赞她是把好角色。
集体化时期,她和男劳力一样,挣十个工分,因为不惜力气、不占便宜,大家都愿意和她一个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背着我们挣工分,辛苦可想而知,我们姐弟仨都是在她背上长大的。稍大一点,母亲就用竹畚箕挑着我去上工,一头是我,另一头上工时是猪粪,回家时是柴草,泛黄油亮的竹扁担总是有节奏地颤悠着,吱吱呀呀的,似在诉说着辛劳和希望。坐畚箕是个技术活,不留神人容易“倒栽葱”,柴草猪粪也会撒落一地。“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我现在对猪屎味不太敏感,大概和小时候总坐畚箕有些关系。
实行责任制后,母亲更加忙得不亦乐乎。家里鸡鸭成群,猪牛满圈,水田旱地林地,稻谷玉米红薯,种树造林育林,四面出击、全面开花。凭着一双巧手,母亲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红红 火火。
搞市场经济后,母亲又开起杂货店、裁缝铺。母亲虽只读过两年书,却无师自通,能给人做衣服。农村讲究喜庆,过年都要穿新衣,年前就成了母亲最忙的时候。每晚喂过我们和猪,母亲就在煤油灯下开始忙活,直到后半夜。“家贫仰母慈”,靠着母亲的精明持家,我家成了当时村里数一数二的“万元户”,第一个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 机的。
母亲的劳动观念一直很强,我们姐弟仨都成家后,她仍然一如既往、勤耕不辍。随着时代大潮,她也出门打工。
山里修水电站,她去工地做饭,同时担土石挖洞隧,挑起一百多斤的土石,一趟走一里多路,比男劳力多挣十五块一天。她去砖厂做活,白天做饭,晚上搬砖。低矮阴暗的砖窑里,母亲推着几百斤重的板车来回穿梭,大汗淋漓、全身湿透。她还去快餐店打工,原来两个人的活她一个人干,洗菜切菜炒菜、淘米煮饭下面条、洗碗抹桌搞卫生,服务员加厨师,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脚不离地、忙得团团转。
我们反复劝说她停下来、歇一歇,母亲总是说,我有一双手,就是用来做功夫的;天天做做功夫,活动活动,还舒服些,坐在家里难受。
前些年,我們想给父母在小镇上买套房子,母亲给我两个存折,二十万。哪年在哪修电站多少钱,哪年在哪搬砖多少钱,哪年在哪个快餐店多少钱,砍树卖木材多少钱,母亲一笔一笔跟我算着这些钱的来路,我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难以言说。这两个存折上的钱,该是母亲怎样的奋力挣扎、怎样的拼尽老命、怎样的苦撑苦熬才换来的啊!我手里攥着的,哪是存折,分明是母亲的血汗啊!“慈母爱子,非为报也。”今天,母亲虽已慢慢变老,却还在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操劳,倾尽全力、毫无怨言。
小时候,母亲对我们姐弟三个异乎寻常地严。
她从不允许我们睡懒觉,总是教育我们,天上掉落个馅饼也要起得早才捡得到。我几乎每天都在母亲的喊声中艰难起床,“秋狗妹子,牛都哞哞叫了,还不起来放牛。”
母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这些古训,我们只要犯了错,挨打总是难免的,而且颇有点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的味道。我家的窗格子上总插着竹枝,为的就是打我们方便。我现在还记得因为偷扯人家马铃薯被打的情景。母亲很温和地喊我去洗澡,让我脱了衣服,然后一把扯住我,用竹枝一顿“竹笋炒肉”式的猛抽,我身上瞬间就出现一条条红痕,交叉斑驳,像一条条蚯蚓爬满全身。
我甚至被母亲饿过饭。因为没完成作业,被老师告知家长,母亲一把夺过我正在吃饭的碗,“啪”地一声砸在地上,虽是泥土地,碗也摔得粉碎。我只好含着泪去做作业,饿着。
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我放的牛跑了,怕挨打不敢回家。天黑了,我胆子小,不敢待在山里,只好偷偷地跑到晾在晒谷坪上的被单下藏起来,远远地看着家里烧得旺旺的灶火,闻着炒瓜子花生的香气,就是不敢进屋。好在老牛识途,吃饱后自己回家了,我才战战兢兢地跟着进了门,感觉年都没过好。
母亲的严还体现在要求我讲真话。她总是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一是一、二是二,讲话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放牛时如果牛偷吃了人家的庄稼,我从来都不敢撒谎,因为如果撒谎被母亲发现,会被打得更狠。母亲还要求我记人情、感人恩。她常说,哪怕人家给你吃了半个红薯、一截苞谷,回家也要告诉我,我好记人家的情。
直到现在,我依然比较怕母亲,以至于吵架时,某人总喜欢去母亲面前告状。我常想,正是有了母亲的严格要求,我这“孙悟空”才被降服走上了正路,多多少少有了那么点出息。
我特别感恩母亲的是,她极力支持我们姐弟仨读书,这在当时的农村还不多见。母亲常说的两句话是,养崽不读书,等于喂个猪。只要你们考得起,考到哪我送到哪,哪怕再没钱,脑顶不起背来挨也要送。
因为母亲的坚持,我们家送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研究生。
母亲送我们上学的学费主要靠卖猪卖牛卖树,还有卖山姜油(山胡椒油)。夏天最热的时候,太阳烤在地上像下了火,知了都懒得聒噪,我们从家里挑柴去近三里远的地方熬山姜油。我家在这边半山腰,熬油的地方在对面的半山腰,得走个大“V”字,那时感觉每走一步都像上刑场一样的难。火不停地烧,山姜籽在锅里熬,我们在灶火旁熬,最长的一次连熬四天四夜,那得烧多少柴、流多少汗啊!就这样默默地熬着,咬紧牙关,母亲把三个儿女都送到山外。
参加工作后,母亲常教育我要知足、要稳重。母亲常说的就是,你一个农村出身的,安安稳稳做事就要得了,不要麻雀跟到喜鹊跳,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做亏心事,睡得安稳觉。前些年我去市州挂职副市长,临行前母亲特意嘱咐我,崽啊,出门在外要稳重,不该呷的莫呷,不该拿的莫拿,小心驶得万年船,你要是出了事,我们这个家就垮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清清白白,除了岗位的因素外,母亲的经常敲打功不可没。
“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这些年我离家越来越远,陪伴母亲的时间越来越少。“悠悠慈母心,惟愿才如人。”我想告诉母亲,你的“秋狗”,正尽力如你所愿。期盼有一天,我能牵着母亲的手,就如儿时她牵着我的手一样,一起坐火车飞机,看天安门、大会堂,看大海浪花、春暖花开。
父亲是儿登天的梯
那年冬天,父亲降生在湘西南连绵苍翠的雪峰山中,没有人兽相交的传说,没有红光满堂的异象,甚至屋后光秃秃的柿子树上,麻雀也没有多叽喳两声。出生时的平平常常,似乎注定了父亲一生的普通平凡。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男人,如铺路的石,似登天的梯,引领我不惧风雨、一路向前。
一
人都说“严父慈母”,于我而言,恰好相反。我的挨打记忆中,“施暴者”好像总是母亲,父亲则是“和事佬”,往往一边对母亲说着“打两下就要得了”,一边把我往怀里拉,然后摸摸我的脑壳、拍拍后背,再教育一句“要长记性”,一场风暴就此化解。
现在想来,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了“爷娘疼满崽”外,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父亲性子相对和缓,母亲则比较急,我也遗传了母亲的性格;二是父母的策略,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避免混合双打往死里整,毕竟儿子是亲生的;三是父亲“二把手”的地位,注定他只能唱红脸。
正是这个红脸的角色,让我更愿意跟着父亲跑,哪怕太阳暴晒、汗出如雨。有次跟着父亲去挖红苕,他在前面挖,我在后面捡,因为挨太近,锄头把大幅前后摆动时,猛然冲在我的下颌上,留下了一道疤。
我那时很享受跟在父亲身后的感觉:不用紧张、有安全感,偶尔还可以好奇地问东问西、有说有笑,全然不觉苦和累。
二
父亲是兽医,小有名气。周围几个村子,谁家的鸡鸭鹅、猪牛羊有个小病小疫的,都来请“李师傅”。那时都是崎岖山路,交通基本靠走,翻山越岭地走,一个来回就是大半天。父亲是个“灵验菩萨”,有求必应,路再远、活再忙也从不推辞,一般都能药到病除,在十里八乡得了个好口碑。
山里乡亲淳朴热情,总会拿出好东西招待父亲。父亲出诊回来,都会变戏法似的,从衣兜里掏出落花生南瓜子、桃李板栗之类的零食给我们,因时而异。我们来者不拒,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窸窸窣窣如小耗子般喜滋滋地享用,慢慢地习以为常。父亲则拉张板凳坐下,身子微微后仰,翘起二郎腿,悠悠然点根纸烟,透过薄如轻纱的烟雾,看着我们吃,满足而慈爱。
父亲有时也会带回来猪牛羊的下水,那是劁猪、阉割牛羊的副产品。用饭碗盛了蒸熟,比一般的肉味道更美,细腻腻、粉沙沙、香喷喷的。父亲带回来的这种滋味,几十年来,一直是我记忆深处的甜蜜。
每逢晚上出诊,父亲总会带上我一起。一来壮胆,走夜路过坟场有个伴;二来授徒,传给我吃饭糊口的手艺。月朗星稀的夜晚,天空如洗,用不着马灯或枞枝来照亮。因了树的遮挡,斑斑驳驳、或明或暗的山路上,两个身影一高一矮、一前一后。父亲拿根竹棍走在前面,夏天惊蛇,秋天打露,我则像条小尾巴,紧跟在父亲身后,亦步亦趋。夜鸟啾啾、溪水淙淙,我和父亲,一起融入这如画的无垠夜色中。
潜移默化中,我慢慢成了“小李师傅”。有段时间父亲去长沙做木材生意,我便独自背起药箱,走村串户,出没在猪栏牛栏中,最远去过十多里外的鱼塘村。可惜我后来没继承家学,走了舞文的路,父亲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三
其实,父亲一直舍不得我再走他的老路,总希望我有点出息。用他的话说,你要不钻猪栏旮旯才好呢,一身猪屎气,婆娘都难讨得到呢。
在山里,要想不沾猪屎气,只有华山一条道:读书考学堂。父亲对我们读书向来重视,每当考了好成绩,他比我们还高兴,总是让母亲煮几个荷包蛋犒劳我们。要知道,在那时,吃荷包蛋可是只有过生日才会有的待遇。
我小学毕业时,父亲作为家长代表出席毕业晚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父亲铿锵有力、底气十足地发了言,几乎每讲一句都会看看我,似是感谢我给他带来的荣光。人逢喜事精神爽,父亲还即兴表演了一段现代京剧,杨子荣《打虎上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举手投足间,有板有眼、形神兼备,高亢嘹亮、声振屋瓦。其实,父亲在《智取威虎山》里,一直演的是少剑波,也许是确实兴致很高,也许是为了营造气势,他特意选了这段有名的高腔,看得我们拍红了小巴掌。
上初中后,父亲的愿望是让我考师范。老师,在当时的农村,是个很受尊敬的职业,更关键的是能吃国家粮,不用钻猪栏。去县城考试期间,父亲破天荒撂下农活,不惜花錢住旅社,破例去陪考,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足见他的重视。可惜事与愿违,我以两分之差落榜了。或许,父亲当时的天空,比我的还灰暗吧。
进高中后,父亲常搭乘拖拉机来学校,一身尘土。一是打听我的学习情况,请老师严格管教;二是送好菜、营养品,补脑汁、牛奶粉、“太阳神”,人说什么好,他就买了什么送来,当真下了血本。我高三在教师食堂搭伙,伙食不错,但父亲依然执着地经常送。我知道,父亲送的,不只是菜和营养品,更是他的鼓励、全家的希望。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送出了村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生,高兴得杀了两头大肥猪,喜气洋洋地摆了二十多桌,差点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四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为送我们读书,父亲从来不怕累、不惜力。他和母亲一起,牙缝里抠,穿用上省,苦撑苦熬,送三个儿女读书。
我家开杂货店,采购的任务自然落在父亲肩上。父亲常常吃碗剩饭,天麻麻亮就出门,中午舍不得花五毛钱买碗饺面,更别说买盘家常豆腐或者白菜梗炒油渣吃碗米饭。在路上掬一捧山泉水,既是解渴,又当充饥,太阳下山才到家,早已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 后背。
从我家到街上,有十五里不通公路,全靠肩挑。毒辣辣的太阳,炙烤得石板路直发烫,汗珠子摔下去立马就蒸发了。父亲黧黑清瘦的脸庞被晒得油亮通红,汗水如泉涌,一会儿就迷住了眼,他只得用早已湿透的衣角不停擦拭。肩上磨得包了浆的竹扁担,被货物压得颤巍巍的,咯吱咯吱地直呻吟。父亲佝偻着身躯,拼尽全力往前倾,挽起的裤腿下,露出只有皮包着的胫骨,干瘦的腿肚子绷得铁紧,汗水流进解放鞋里,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噗的响声。九十多斤的身躯,挑一百多斤的重担,每往前挪一步,都得攒多大的劲、费多大的力啊。
父亲有时也打屠杀猪卖,我曾和他一起,去隔壁的太平村杀猪。热天杀猪要趁早,一来可做早饭菜;二来白天气温高,肉容易臭。我和父亲凌晨三点多就出发,打起火把走八里山路,然后烧水杀猪,褪毛剖边,一通忙活完,天刚蒙蒙亮。父子俩一人挑担箩筐,沿路“称肉么”“称肉呢”地叫卖。若逢秋收时要下苦力,农家人都舍得买点肉打牙祭,一个猪半天就能卖完;倘若平时,常常得走两三个村才能卖完一头猪,一天下来,累得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吃不下喝不下,只想躺平了不再起来。
村里有红白喜事,父亲也应邀去做厨炒菜。头天下午,父亲就用篮子提了厨具出门,直忙到第二天中餐正席吃完,煎炒焖、炸卤炖,烟熏火燎一整天。都是邻里乡亲,钱是无论如何不要的,父亲每次提回的篮子里,总有金黄油亮的扣肉,外加一些小炒,给我们改善生活,省着点可吃好几天。
岁月不居,父亲已年逾古稀,身体大不如前了。如今的他,洗尽一身尘土,褪去半生沧桑,或是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或是约三五老友,打打牌、聊聊天,优哉游哉。
但愿此日,年年岁岁如是;惟愿此人,平平安安依然。
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亦似刀,不觉已人到中年,逆旅行程过半,似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往事如烟,风雨如昨。
一
立秋的早晨,雪峰山中葱茏苍翠,薄雾氤氲。孤零零的木板房,破旧泛黄,透着沧桑。
房中漏出的哭声,不甚响亮,不紧不慢、不情不愿,宣示着我的到来。迎接我的,不是寓意吉祥的喜鹊,而是满院子蹦跳的麻雀,叽叽喳喳。
颠着小脚的奶奶,颤巍巍跑进来,瞟见我来不及洗干净的血痂,和红彤彤皱巴巴的皮肤,伸出的双手又缩了回去。轻轻的叹息声中,有几分怜爱、几分无奈:“一个耗子,只怕是难带得大哦,唉——”摇摇头,灰白的发髻有些松动,几缕头发,覆在额前。
李家,又多了一个放牛娃。
二
穿着开裆裤,拖着鼻涕虫,伴着芦花鸡的啼鸣、黄斑狗的调皮,蹒跚前行。沧桑古旧的石板路,蜿蜒前伸,多情地盛满放牛娃的笑声。
牵着黄牛,背着竹筐,别着柴刀,奔走在春泥芬芳的田野,跋涉在夏花烂漫的山间,茫茫秋露,洇湿了卡其布的裤脚,皑皑冬雪,浸润了杉木皮的房顶。
和风徐徐,余晖映照着山涧。老黄牛伸长脖子,咕咚咕咚喝水。放牛娃摸摸牛屁股,趴在旁边,也伸长脖子,咕咚咕咚喝水。然后,跃上牛背,在一片蛙叫虫鸣中,晃悠悠回家,洒落一地长长的影子,和一串清脆的歌声。
和泥巴、过家家,爬草垛、捉迷藏,野孩子的笑声、哭声、喊声、骂声,一声声、一阵阵,在山谷回荡,驱散了,懵懂童年。
三
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土布书包,装着家人光耀门楣的朴素愿望,放牛娃走进学堂,在浩瀚书海的清新墨香里,放飞梦想,遨游徜徉。
东方欲晓的晨曦里,捧一本圣贤书,朗声诵读,任寒风呼啸,吹裂稚嫩脸颊。
昏黄如豆的油灯下,展一卷习题册,伏案疾书,凭汗水流淌,湿透泛白衣衫。
起五更鸡鸣,斗酷暑寒霜,翻烂资料无数,写秃钢笔几许。一次次练,一场场考,浴火涅槃苦修行,终究得窥法学门。
如迎风吹开的蒲公英,一路飘荡。放牛娃走出与世隔绝的偏僻山村,离开纷扰嘈杂的湘西小镇,经过热情似火的陪都重庆,落脚惬意淡然、韵味悠长的古城长沙。
四
“大智治制,中智治人,小智治事。”虽非大智,却事治制,犹如小马拉大车,拼命以外,别无他途。
一条一款一章节,反反复复斟酌,条条要熨帖;一字一句一标点,来来回回推敲,字字需锦绣。表己意口舌费尽,互辩驳唾沫横飞。无丝竹之悦耳,有案牍之劳形。
缘分天注定,有缘赴湘西。逮山里腊肉,喝苞谷烧酒,感民族深情,尽绵薄微力。编制年度立法计划,提出分为当年出台和调查研究两档,首开湘西先河;老司城遗址保护立法,从框架结构的酝酿到具体条文的打磨,几乎包了圆场;制定州府城管条例,调研座谈、组织协调、研究起草,一样都没落下。
岁月依稀,梦里常忆:
东塘十楼九年整,时有夜灯到天明。
不期两载湘西缘,今日犹是土家人。
飛花五月雨中行,辞却湘西赴帝京。
芙蓉国里争朝晖,燕京城内谱新篇。
五
人到中年,定有所获。
人到中年节到秋,恰是一年丰收时。人生打拼四十年,熟建安身立命之所,深谋展才用武之业,广拥亲朋密友之情,安享阖家天伦之乐,逐渐搭上发展快车,偶尔亦有高光时刻。
人到中年,或有所惑。
古人四十不惑,皆因世事单纯。当今世事,纷纭繁扰,纵然阅历深、经事多,也难免想不开、辨不明、理不清。官迷财癫、色魔花痴,所惑皆因有贪念。为官欲求升三级,经商惟愿进斗金,汉子盼逢潘金莲,妇人祈遇西门庆。如渊欲壑若难填,直呼苍天不遂愿。世事洞明皆学问,我辈尚需看得穿。
人到中年,杂事更多。
堂上有白发父母,倚门翘首盼儿归,平时常需勤问候,病时犹要侍汤药。膝下有垂髫小儿,吃喝拉撒都要管,各种培训兴趣班,花钱耗时也得干。兄弟朋友都得交,大事小情要帮忙,偶有事情没办好,情谊皆无把脸翻。自己还得求进步,学习充电要提高,参谋决策顶梁柱,熬死无数脑细胞。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需关心;老人小人旁边人,人人均要照顾。直熬得人到中年,体虚眼花头顶秃。
人到中年,宜淡泊,竹杖芒鞋、吟啸徐行,牢骚太盛防肠断。
人到中年,且豁达,一蓑烟雨、率性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编辑导语:在一个带着使命与激情的援藏干部眼里,高原古城有着别样的气象,这其中也折射出了个人的精神气象。作者是个有心人,情感细腻、懂得感恩,透过平实质朴的文字,他勤劳刚强、家教甚严的母亲,刻苦耐劳、宽厚担当的父亲跃然眼前。这组散文触动人心之处,不在于技巧,而在于真诚与真情,在乎有志男儿的昂扬精神。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