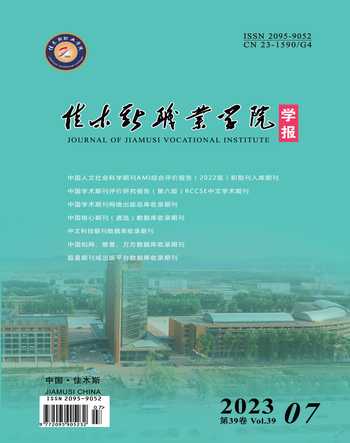梦得池塘生春草
肖肖
摘 要:吴福辉对海派文学概念的界定具有划时代的学术价值,他先划定了海派作家的范畴,区分了旧派文人与海派作家;进而梳理了海派文学的审美范畴,把都市文化中的文化因子凸显出来,赋予海派文学现代审美质素;他还纠正了海派文学的评价导向,将之视为重要的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既不夸大其成就,也不蔑视其审美。
关键词:吴福辉;海派文学;概念界定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3)07-00-03
吴福辉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初版)中就涉及了海派中的“新感觉派”以及徐訏和无名氏两位作家,冠名为“洋场小说”(第二十三章);1998年该书改动修订,直截了当打出“海派小说”的概念(第十四章),这是综合文学史中第一次出现明确的“海派文学”概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很多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也是许多高校指定的考研必备书,在高校的使用和学界的引用都是文学史中的佼佼者。所以吴老师的“海派文学”概念也随着此书的广泛传播更为学界广为了解和接受。
一、确定“海派文学”作家范畴
海派文学这一概念自“京海论战”,指向并不明确;基本成员划分标准不统一,沈从文在《论“海派”》《上海作家》等系列文章中论述海派,他所谓的海派作家系列既包括生活在上海的作家,也包括其他城市作家中写作风格具有匠风气的作家。因此,沈从文对海派的概念认定中接受了既定海派文人群体,其中包括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又进一步把海派作家范围扩展到左翼和民族主义作家中。当时在上海文人的心目中,海派即是“鸳鸯蝴蝶派”[1],施蛰存也认同当时的海派就是指“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周瘦鹃、张恨水、郑逸梅之流”。
吴老师的海派文学概念规定了海派作家身份标准。他对海派文学范畴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鸳鸯蝴蝶派等洋场气质文学处于“中国的现代都会尚未成型时期……不能称为海派”,海派作家的特征是从上海市民阶层的视角看待上海这座东方魔都。吴先生又试着:“给海派文学做一界定,把隶属于旧文学的鸳鸯蝴蝶派和三四十年代可归入新文学一翼的海派区别开来(二者自然也有割不断的联系),认定并勾勒了海派小说的大致轮廓。笔者认为海派虽无明显的结社行为,却是一种广泛的、有丰富内涵的流派现象,它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中国缓慢伸延的不平衡性,在由东南沿海局部的前工商社会,向大陆中西部的后农业社会,向西北残余的游牧社会逐步扩展的过程中,海派的畸形以及它遭遇到的误会,显示了中国人文历史的曲折与斑斓。”[2]
吴老师界定的海派作家范畴钩沉打捞了一些已经被遗忘的海派作家或者无处划分的作家如黑婴、东方蝃蝀等等,学界对这些作家进行了新的研究,左怀建《评东方蝃蝀的〈绅士仕女图〉》便明确提出是根据吴先生发掘的资料对作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根据著名现代文学史专家吴福辉先生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附录:海派小说家传略与主要书目——东方蝃蝀的内容[3]进行了对这一长期被主流文学遮蔽的海派作家文学的重新发现和认识。
二、梳理海派文学的美学范畴
吴老师审视海派文学时,主要以市民眼光和都市描写这两个维度进行判定。在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洋場小说中,这两个维度同时存在。关于海派文学的审美范式,吴老师将旧文学中的市民喜好、城市描写与海派文学中的市民眼光和新都市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辨析。
吴老师认为海派文学的第一品格应为是否具有现代性,“鸳蝴派”不应是属于海派的范畴,就是因为这一流派文学盛行时期,十里洋场的新都会文化并未呈现。而洋场文学“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章回小说的横移,只是更加媚俗,更加投合中国老市民的趣味而已。”把鸳鸯蝴蝶派的审美旨趣与海派区分开来,轻描淡写地解决了学界对海派附着鄙俗气息的批评。这个切割十分必要,也十分科学。
起初,海派文学被批判为低级趣味的消费文学。沈从文曾撰写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这里首次提出文学中的“海派”与“新海派”时候就带有此种倾向性,他指出礼拜六派(“鸳蝴派”)之所以说是海派,就是它具有十里洋场一切的趣味。所谓的“趣味”就是指向:市民趣和商业味。显然,市民又指的是老市民,他们的审美情趣是恶俗的封建文化的遗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等情节广受欢迎,以此套路做文,即便是十里洋场的生活,也只是穿着新衣的老故事。他又说“承继‘礼拜六,能制礼拜六派死命的……是如像《良友》一流的人物。这种人分类应当在新海派”。他对海派的概括是:“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这里他又提出了“商业”一词,再次以传统文人“经国大业”的高高在上姿态嘲讽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海派创作。沈从文的评价抓住了礼拜六派写作的特征,也说清楚了其对市场的依赖,客观地说,这是海派文学不可回避的特点,但是沈从文对文学的追求和个人的审美倾向不允许他对市场低头。1928年1月初,沈从文到达上海,抱有重造人心改造社会的文学态度,20年代末30年代初,《红黑》杂志、《人间》月刊创刊发行,编者为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坚持纯文学立场,不愿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商品竞卖之中[1],无奈上海的实际情形与沈从文他们的文化理想相距甚远。在上海那种纯粹的商业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刊物很快就夭折。《人间》和《红黑》月刊均出版了几期便宣告失败。这段经历可看出沈从文审美追求上他向往纯美的文学意境,理想读者追求上,他定位于纯朴人性的国民。因此,他与市民的鄙俗和市场的逐利格格不入。
可见,沈从文对上海大都市的消费文化十分抵触,由此对海派文学产生了负面情绪;但沈从文并不认为居于上海的作家都属于海派,甚至指出北方作家也具有海派习气。也就是说,沈从文是从文学审美趣味上去审视海派文学的,他用消费文学视角关照海派文学,认为海派文学偏重市场逐利,审美旨趣与纯文学大相径庭。因此,他又因审美趣味而将鲁迅、茅盾等居于上海的作家也排斥于海派之外,重点批判海派文学家卖文为生的商业气息。海派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韩侍桁撰写了《论海派文学家》一文,此文也将海派限定为某些上海作家,并且是带点儿下流甚至堕落的作家,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更明确界定海派为“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大家对海派的商业性关注颇多,认为商业行为偏离了文学本质,不具备审美性。
关于海派文学被批评的媚俗化、商业化的声浪日炽,海派作家们也不得不出面辩解,苏汶的文章《文人在上海》中,概述了上海大不易居的现状,他指出上海经济发达,居住其中的文人往往生活困难,难以悠然自得地进行文学创作,只能为追求金钱而卖文生活,既然生活所迫,文章略有粗疏也在所难免。对此,左翼文人森堡深以为然:“是的,上海(应该说是中国吧)的文人诚然要钱,而且,我也跟苏汶先生一样地,‘并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曹聚仁却有不同认知,撰文指出,“海派”是“摩登女郎”“是社会的,和社会相接触的”。以社会性为观照视角,曹认为海派更贴近社会,换言之海派文学并非闭门造车。沿用此观点的还有杨晦,上海《文汇报》的周刊《新文艺》在1947年3月份两期连载他的文章《京派与海派》,也认为“海派是进步的”尽管有限,但总是比京派的没落故步自封要进步。但是这些辩驳观点并未能扭转海派的声名狼藉,包括这些辩驳者自身的文章也一再承认了海派被批评的商业性和低俗化。
众说纷纭中,吴老师给海派文学下定义时,他摒弃了海派文学作为旧的批判对象的认知,他指出了海派的商业性被批判对象,但是其中有着重要的“现代质素”,海派的文化符号应该是现代都市。海派文学的核心是表现现代都市生活。其中的研究重点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中西文化之间的对立,现实与理想等纠缠矛盾统一关系。但笔者认为吴老没有完全摒弃传统对海派的认知,他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把都市作为人物活动背景来展示的,无论是在穆时英笔下的灯红酒绿还是张爱玲笔下的都市情爱,上海作为“东方魔都”它的租界背景与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他们天然的具有现代性。他把都市性当作海派文学审美的向度之一,都市与乡土的二元对立中,都市的现代性被凸显,海派致力于新的生活理念、哲学意蕴的挖掘,把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生活作为人活动的场景,用新的人生感受来描写人的离合聚散、主体性的分裂与重聚。
三、校正海派文学的评价导向
对海派文学的评价向例不佳,它从诞生起就受到来自文学界内外的双重攻击,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家对海派鄙夷溢于言表。沈从文明确批评了海派作家的“白相文学态度”。曹聚仁也说:“海派文人百无一是,固矣。”姚雪垠认为:“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苏汶是海派文人的代表他也认同:“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1]。批评之声并未随着时代变化而断绝,由于作家个体兴趣、知识领域和文化场域的差异,海派文学一直处于被批评的风口浪尖,鲁迅更一针见血指出“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海派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危机重重,鉴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海派文学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危机。吴福辉先生科学评价海派显得十分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这段时间国内学界要么对海派不再论及,要么以负面批评一语带过[4],海外夏志清、李欧梵等学者已经开始了对海派文学的研究和新认识。国内直到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也只是初步提及“新感觉派”这一海派文学的分支,1990年赵凌河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是最早的一部研究新感觉派文学的专著。杨义在文中对海派做了评价“上海现代派注重都市风的机械文明。”包括一些名家的文学史如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王泽龙、刘克宽的《中国现代文学》,刘勇、邹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只提到“新感觉派”这一海派的分支。学界对海派文学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与海派作家们的贡献不对等。
长期或被鄙夷,或被无视的海派文学在吴先生的梳理下得以有了清晰的概念,不仅把握了海派的特质,而且将海派文学的地域文化渊源进行了开拓,从海派文学扩大到对海派文化的探讨,对海派文学进行了正名,引导了学界对海派文学的新评价导向。吴先生从1970年开始涉足海派作家初期研读施蛰存,80年代初吴福辉老师发表在《十月》上的文章《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4],赞誉施蛰存先生的作品。在周遭都对海派缄默不语时,他以科學的实事求是态度,对海派作家进行了仔细梳理,给予其相应的文学价值。接着陆续撰写了《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崩坏都市中生长的“恶之华”》《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已经初步涉及海派文学,1989年8月5日《文艺报》与1989年《上海文学》第10期接连发表《为海派文学正名》和《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直至1994年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确立了海派文学的概念,厘清了地缘关系、时间跨度、代表作家和阶段性特征。海派文学终于从无视到深耕,从荒芜到繁荣,在吴老师理论架构和细读分析支撑下,海派文学的概念越来越丰满。于1997年出版了《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最早为“海派”正名,成为海派研究第一人[5]。一系列研究奠定了吴先生在海派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正如陈子善老师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吴的海派文学研究在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界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他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必要的准备、补充和深化。”[6]海派文学的概念成型后,围绕着一众作家的作品和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而出,海派文学终于不再是一个被忽略、轻视甚至被诋毁的地位,而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
在吴老师的引导下,对海派文学的评价,由三四十年代的批判商业和媚俗,转变为对其现代性和日常性的探讨。周小仪的《比尔兹利、海派颓废文学与30年代的商品文化》、黄建生的《重看海派文学的商业性》、曹超《文化市场下的海派作家及其写作》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海派文学的商业性行为,在客观抓住实质的同时,强调了海派文学商业性对都市文学发展的特殊贡献是“20世纪新文学与市场结合的先声”,张馥洁的《现代性视野下的海派文学》,林朝霞的《霓虹灯下的叛逆———论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寻求》以及许道明的《海派文学的现代性》等文章则重点探讨了海派文学的现代性,达成一致的认知是海派文学不仅学习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创作实践中。2000年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张鸿声撰写的《都市大众文化与海派文学》都重在研究现代都市文化与海派文学二者间的关系,将海派文学确认为“适应上海新兴市民阶层大众文化的新兴都市文学”。
四、结语
吴福辉海派文学的概念,具有明确的现代特色,不仅写作技法上同步于世界文学洪流,而且审美上凸显了都市文化,海派作家的界定不应以作家居住地为标准,而要以作品特色为依据。他给予了海派文学客观的评价,批评了其过渡面向市场的商业气息,也肯定了对现代都市品格的塑形意义。吴福辉先生第一个界定了海派文学的概念,是所有海派文学研究者绕不开的界碑。其对作家范畴的确认、对美学范畴的确立,并且直接影响了对海派文学的研究导向,引发了对海派文学现代性、日常性、文化性、地域性的研究[5],加深了学界对海派文学这一长期被主流文学史和研究排斥在外的流派的重新审视和理解,促使海派文学成为今日研究之显学。吴老师的这些影响和成就担得起学界一致认同的“文学史专家”“海派文学研究开拓者”“海派文学研究专家”的称号。
参考文献:
[1]黄德志.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J].鲁迅研究月刊,2005(6):4-12.
[2]吴福辉.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J].文学评论,1994(1):13.
[3]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
[4]杨迎平.海派文学研究综述[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7-42.
[5]钱理群.这一代人中的一位远行了——送别老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4):133-147.
[6]李楠.饱满的生命和学术:吴福辉先生及其海派文学研究[J].现代中文学刊,2021(2):23-29.
(责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