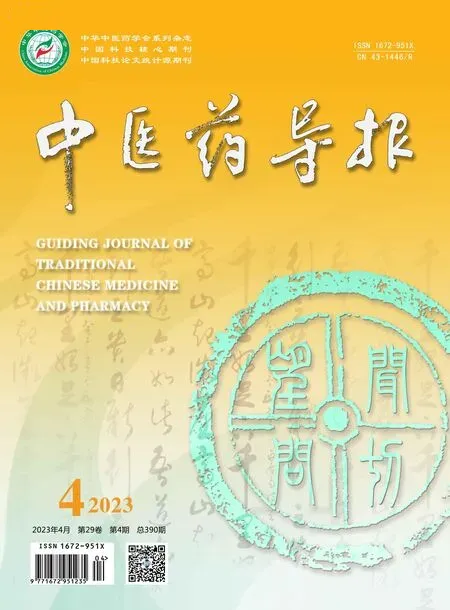中医脉诊起源考*
李亚飞,刘寨华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脉诊是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重要的诊断方式,常被认作是中医的标志性技术。近年来,脉学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然而,早期脉诊史的研究尚有薄弱之处。目前,学术界多关注与秦越人、仓公及汉初出土文献中有关的早期脉诊文献,尚未深入追溯秦越人之前脉诊产生、演变的历史。故考察脉诊起源时期的概况,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也能为脉诊的有效性提供原始的理论与史实依据。笔者以3个问题为主线,即在春秋战国善于诊脉的扁鹊之前,脉诊是如何起源、发展的?脉学如何摆脱巫术,成为王官之学,之后却又兴盛于民间?如果说早期脉诊并非全是经验的累积,那么在先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笔者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把上述问题具体于历史合乎规律的演变中做出具体解答,划分早期脉诊史为上古至殷商、西周、春秋战国3个时间段。考察早期脉诊史3个阶段,能够展现中医脉诊起源期的概况。
1 上古至殷商时期
1.1 脉诊源自上古巫医 脉诊的确切源点,尚难考辨,从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史看,医源于巫,脉诊当也源自集宗教、政治、医疗等职能于一身的巫师。巫师在当时被视为全能的存在,作为尘世与天国的媒介而获得上天的意志,实现尘世的祈愿。鬼神作崇导致疾病是上古先民的观念,他们相信巫师能够交通鬼神,以祭祀、忏悔、屈服等方式解除祸患而治病。从词源上讲,“‘医’字形原初与‘巫’一起构成从‘巫’的甲骨文‘毉’,恰恰反映了医生的职责在殷商时期是由巫医兼任的。[1]“理色脉”可能是上古巫师诊病的方法。《素问·移精变气论篇》云:“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2]122。这表明传说中的僦贷季可能具有观色察脉的经验,通过色脉的显像与神明沟通,获得疾病的信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上古巫师俞跗“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3]2788,巫师治病可能已探知筋脉,掌握一些脉学知识。另外,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有龟甲与针锥同葬的现象,提示墓主的巫医身份[4]。这些针锥刺向的可能是肌肤与筋脉,以祛除腐肉或排出脓血等。针刺前巫医当会触摸动脉,以避开危险之处。巫师对于筋脉、动脉、血脉的经验积累,为据脉察病的脉诊术的萌生创造了条件。
1.2 触摸脉动是上古巫医获取疾病信息的方式 脉诊是诊断的主要手段,针刺筋肉是治病的重要方法,上古巫师或开始发现筋肉、络脉、动脉、脉诊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十二经穴完备之前,有‘五体刺法’,包括刺肉、刺筋等”[5]168,早期的针刺术,可能是针刺病痛之处的筋肉、血络等。巫师触摸病痛周围的动脉,除了防止针刺误伤流血不止之外,可能也获取一些诊断信息,动脉作为流动中的血气出入的门户与聚藏之所,体现着血脉的运动状态。《灵枢·九针十二原》载:“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2]858其虽要求诊脉捕捉脉气的盛衰在先、用针治疗在后,但因该论述出现相对较晚,故不能作为脉诊术早于针刺术的证明,然而可作为二者关系密不可分的一个证明。
在“万物有灵”的泛神论盛行时代,包括脉动在内的身体行为,可能在殷商之前已被视为神圣的涌现,而这种涌动又蕴含着身体信息。《灵枢·九针十二原》云:“粗守形,上守神。”[2]850《灵枢·小针解》载:“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2]879张树剑[6]138认为“这里的‘守神’是通过脉诊实现的”,他将脉中之“神”称之为“脉神”。脉中有神,《黄帝内经》的作者及后世医家或依旧保留着远古巫医精神内守,意念专一地触摸“脉神”的习惯,只不过上古巫师认为其所触摸者为脉中微妙莫测的神灵、神明,他们的神显也预示神灵惩罚所致的疾病信息,后世“脉神”逐渐祛魅化,演化成为玄妙变动的“血气”与和谐的“胃气”等代名词。除了僦贷季、俞跗可能是能够触摸“脉神”,并与神明交通的巫师外,巫更、巫咸与巫抵等都从事针刺术[7]95-99,当对脉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1.3 诊察脉动与血脉或是殷商巫师的基本技能 在“尚鬼”文化浓厚的殷商时期,“天”主要是作为有意志的宗教之天出场,巫师通过巫术交通天意才能获得灵验,观色察脉或也是巫师的技能之一,其医疗技艺仍是巫术的重要部分,专门的医官尚未从巫师的众多职能中分化出来。据周策纵[7]76考证,“殷”字的甲骨文,左边所从的“”是“舞之容”,右边所从的“殳”为“舞之器”,器所指的对象可能为针,故他认为殷字可表义为“乐舞中象征针灸医病除疫的动作”,“殷字可能原指针刺医术”。周策纵[7]76基于此义,认为殷商的创国者帝汤或与巫医有关。另外,湖南石门县皂市的殷商遗址中也出土过砭针[8]。巫师乐舞通神,手持针具刺入肌肤与筋脉,因此与动脉、针刺、筋肉密切相关的脉诊,在殷商也有所发展。与血脉纵横交错,触之或观之能够获取病象类似,占卜直观甲骨裂纹的脉络象,也是王室获得神启的方式,当然也包含大量问询疾病的内容,血脉与甲骨脉的综合交错之象都作为疾病的征象,被巫师用来捕捉生命的信息。许进雄[9]经过对甲骨卜辞的考证得出殷商人把疾病归为四因,即鬼神作崇、气候突变、饮食不慎、梦魇。可见,殷商的医学也并非全是宗教巫祝之术。巫师集宗教崇信与医疗理性的灵验为王者服务,预知疾病的进展与转归,特别关涉生死吉凶。通过诊察脉动与血脉,获知疾病的轻重缓急,做出生死之域的粗略预判或许是殷商时期脉诊的主要功能。
2 西周时期
2.1 诊脉的天官从巫师中分化而出 巫师卜兆显象,筮法倚数,象数本用于预卜吉凶,但随着象数思维的日臻发展,“天”由神显之象数逐渐演化为气化之象数和神显之象数的交织并存,而脉理的支撑主要是气化的象数,脉诊逐渐成为可以数推、象显的技艺。《汉书·艺文志》以“方技”(医学)为王官之职守[10]1780。尽管周秦的医官从巫师中分化而出,成为王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周朝的文献中发现藉占卜知病之由的记载,则鬼神致病的观念依然存在,可见藉巫术之法疗疾的情形,仍普遍存在于周朝社会之中”[11]140。王官的医术仍脱离不开巫术。《周礼》载周朝的王官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周礼·天官冢宰》载有天官的职能[12]18-127。“天官”是效法天象所立之官,“冢宰”则指大官。六官主要法象自然的时空象数秩序,辅佐王者奉行天道而治人。人所处身的世界不再全由鬼神主宰,《诗经·大雅》曰:“天命靡常”[13]。《左传·僖公》引《周书》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4]347其指出天的意志不再固定不变,而是眷顾有德行的君王,天也由鬼神之天逐渐向自然之天过度,气化流行逐渐成为世界的运动方式,天由神化逐渐转向气化。
《周礼·天官冢宰》详载了周朝医事制度。该书称医官为“医师”,“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12]68。医师又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12]70。郑玄注云:“两参之者,以观其死生之验”,“藏之动,谓脉至与不至”[15]。可能最早于周朝已形成九藏的观念,并发现九藏的脉动,初步形成九藏脉诊的相关理论。“脉动之处多被认为是气之出入之门户或藏气之所。”[6]69肺、心、肝、脾、肾、胃、膀胱、大肠、小肠等九藏的信息显现在脉动的节律上。疾医已能以脉诊参知九藏的脉象,从而判断气血的状况,预知生死。“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12]71疾医通过反思并记载患者病亡的原因,进一步总结包括脉诊在内的医疗规律,充实王官之学中关于医学的知识,促进春秋战国时期脉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2.2 天官脉诊直观地脉、经水与月亮之象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2]33能够体现周秦之际的阴阳观念,该时期阴阳观念的理性思维已经能诠释自然与生命现象,故通天不再等同于通神,而是从上古时期巫师的通天即通神,逐渐转变为医官通天即通阴阳之气。《素问·移精变气论篇》载:“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色以应日,脉以应月”[2]122。上古的巫师僦贷季不可能通晓阴阳五行之学,摆脱巫术,纳五行说于脉学之中,并做时空象数规定当在周秦之际。《素问·举痛论篇》云:“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2]329。阴阳五行学说得以发展,阴阳五行的相互生克及其象数的顺逆吉凶,成为周秦之际天官把自然的气化现象加以演绎、推导的主要思维方式,促成象数之学映射于人身,使天的历数开显于身体之上。天官对脉象的体验、认识活动也遵照象数观念,以效法物象的秩序与运动方式,地脉、经水、月亮成为脉学直观的对象。
天官远察天地,近取诸身,以脉类天宿、地脉、经水,找到脉气与天地之气的共通之象。《国语·周语上》载:“古者,太史顺时脉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16]周人的观念中,地有地脉,地脉中所蕴藏的土气能量应适时疏导,农事顺时耕作就可疏泄地气。地有土脉,身也有体脉,体脉与地脉更多是在同属水脉的意义上加以类比,使脉有血脉、经脉、泉脉等多重含义。《说文解字》释脉的古字“衇”为:“血理分衺行体者。从血。”[17]570衇的右偏旁含义为:“水之衺留别也。”[17]570张家山墓出土的《脉书》也云:“脉者渎殹……脉痛如流”。《灵枢·邪客》载:“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2]1347《灵枢·痈疽》云:“经脉流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2]1461虽然十二经脉的说法可能晚出,但法天道以象人事的思维在西周已经出现。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与血脉的类比与实然上的联系在西周时期当已现萌芽。脉与天地相感应,经脉、血脉运动还要合于天之宿度,从而实现通过脉诊以探知身体节律是否与天地节律相协调。
天官仰观天文,近观人身,还以脉类月象。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巫师占卜日月蚀、救日月蚀、占星的记载,《周礼》《左传》还有周秦之际运用阴阳五行的原理救月蚀的内容[9]208-213。周朝巫师仍常使用占星术预测吉凶。《周礼·春官》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12]379-380其认为保章氏的占星术据天象能辨知天下九州的吉凶妖祥。《易经·系辞上》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18]天象的变动往往提示王土国运的盛衰。具体于日月蚀的异常天象则预示着自然与人事的吉凶,而日月之象同样与人身气色、脉象同气相求。
《黄帝内经》的文献可能反映周秦之时脉象与月象协调相感的观念。如《素问·移精变气论篇》云:“色以应日,脉以应月”[2]122。日光明而外显,与气色显露于外都是阳象,月阴柔而晦暗与脉藏于体内皆是阴象,且具有相对同步的运动周期,日光与年日及月光与年月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继而发现经脉的运动节律与月象的变化同样遥相感应。《素问·八正神明论篇》[2]238、《灵枢·岁露论》[2]1446都认为月满则气血盛,月亏则气血亏。可推测法天象地的医官能够仰观月象的盈亏,触摸脉动的虚实,获得气血与月象状态一致性的体验。所以,天官的视域广阔,并非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进行想象与建构脉象,而是以自然的世界为意识展开的基点,推天道以演人事,使脉学的客观性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使任何脉象的阐释与诊断都有天道的支撑,从而避免主观唯心论的空泛无根。
《汉志·方技略》载:“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10]1780西周之时,脉诊术主要掌握在王官之学中,但不能排除民间的巫师,或仙道方士也或多或少地拥有脉诊方技。除了王官中的天官从事脉诊活动外,民间巫医可能也施行脉诊之术。《逸周书·大聚》载:“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蓄百草以备五味。”[19]乡间巫医掌握药物方术需要对症用药,用药恰当要以色脉相参为前提,脉诊可能也在乡间施行察病的技术。
3 春秋战国时期
3.1 脉诊术在官学与民间并行 西周时期,王官是掌握脉诊方术的主体,但至春秋战国,周天子权力被削弱,诸侯兴起,政学逐渐分离,学术上有百家争鸣,民间方术也逐渐兴盛。“按古王官学统,官师合一,事有官守,政学未尝分。逮王官失守,政学分离,而有诸子之坟兴。由是周秦之时学在私门,汉兴遂有‘医家专门授受之学’。”[20]周秦之时,脉诊在私门传授、发展的同时,王官的脉诊技术也并未消失,周王室仍保留王官系统,诸侯国的公侯也拥有高水平的医官。如《左传·成公十年》[14]957、《左传·昭公元年》[14]1575分别载秦伯使秦医缓、医和诊治晋候之疾。当时脉诊与针、灸、药术都已施行。“则医缓的治病,以针、灸以及药物为之,此亦为后世专业医疗之术。”[11]140《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分析病因时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14]1575其认为气候的六气、饮食的五味、视觉的五色、听觉的五声都当节制,太过则引发疾患,医和又用蛊卦()形象地阐释病因与生死。五味、五色、五声都为数五,显然是五行归类所致。医和已经将阴阳、五行、六气、卦象等象数理论应用于诊断,而同时代的扁鹊“守数精明”,当把上述象数之学运用于脉诊之中。
《汉书·艺文志》云:“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10]1780。其把扁鹊和医和当作中世齐名的名医。《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诊晋侯之疾在昭公元年[14]1575,《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也载扁鹊诊治大夫赵简子之疾在晋昭公时[3]2786,考晋昭公于公元前531年至公元前526年在位,在位仅六年。这既可表明医和与扁鹊为同时代人,又能说明包括脉诊在内的医术,虽仍保存于有卜(巫)术的医官内,但随着贵族的没落、医官的流失,脉诊在私门逐步发展,水平也大有超越医官之势。《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3]2794便是医官技不如私门医的个别例证。
3.2 私门医扁鹊的脉诊术 东部沿海的齐地人秦越人,又名扁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称扁鹊为“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3]2785。但扁鹊为远古传说中的人首鸟身的神医,“扁鹊传说自新石器时代肇始,长期流传直至汉代”[21]72。显然,扁鹊并非专指秦越人,而是指远古神医,秦越人因医术高明,才被时人称为“扁鹊”。欧阳珊婷据汉画像石中“扁鹊针灸行医图”有扁鹊“人首鸟身”的形象,认为扁鹊神话是东夷古国与商民族鸟图腾崇拜的体现[21]11。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就刻有人首鹊身类似于扁鹊形象的鸟人一手切脉,一手针砭地画像[5]56。山东汉墓还出土有扁鹊艾灸的场景。直到汉代,齐地还流传着扁鹊行医的神话。扁鹊信仰自远古至汉代盛行不衰,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地也应有扁鹊信仰,而秦越人被认作扁鹊的化身,应也有针灸术及脉诊术的实践。
秦越人脉诊闻名,是脉诊初成体系的集大成者,直到汉时的司马迁仍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3]2794。《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长桑君秘授扁鹊禁书与上池之水,扁鹊遂能“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3]2785。扁鹊虽然望诊技术高超,但脉诊也没有流于形式,色脉相参才是他诊病神验的前提。扁鹊的脉诊思想难以复原,并没有著作流传于世。《难经》虽非扁鹊所作,但可能与扁鹊学派相关。李建民认为“大量扁鹊遗文出现于《脉经》也是可疑的。老官山医书无疑是汉初人的作品”[5]52,《难经》其实较早与黄帝相关联[5]16。《脉经》和成都西汉墓葬老官山出土的医简,收录了“扁鹊(敝昔)曰”等词条,可能多为假托之言,二者虽于起源期的脉诊术有所继承,但这些文字体现最多的是扁鹊之后,经过几百年发展演变后的脉诊学术,难以此为蓝本复原扁鹊的脉诊思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公乘阳庆授淳于意“禁书”扁鹊《脉书》,该书与《汉书·艺文志》所录《扁鹊内外经》一样,都已亡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简要记载有关扁鹊脉诊的医案,或可提示扁鹊脉诊的轮廓。
扁鹊脉诊术仍与巫术尚未脱离。当赵简子连续昏迷五日,不知人事,众人皆惧之时,扁鹊主要依据观色察脉,得出“血脉治也,而何怪”[3]2786,不出三日当苏醒的判断。扁鹊据脉观色还得出带有巫卜色彩的预言,准确预测赵简子与晋国国事走向有关的梦境。可见,扁鹊仍视脉为神圣启示的形式,有关生死的医理还没有独立于巫术的卜测。
扁鹊的脉诊法主要是遍诊血脉、部分经脉的动脉法及络脉法,并利用一些循经感传的现象发现病理。扁鹊诊虢国太子之病,色脉相参后认为“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3]2791。虢国太子之所以昏死,是因阳气被阴气束缚于内,胃气中枢运化不开,上下内外的气道不通,阳气当上行、外行反下行、内行,阴气当下行、内行反上行、外行。扁鹊的遍诊法,可能主要用到头部、胃部、腹部动脉的脉诊,另也有经脉的动脉脉诊,以及触诊经络关要发现循经感传的状态。头部是“清阳之会”,头部脉诊主要候取阳气及体表的状态。胃部脉诊主要诊断中焦阴阳气交是否顺畅。脐部脉动在《难经·十六难》中又称动气,该书载脐部的上、下、中、左、右的动气,分别与心脉、肾脉、脾脉、肝脉、肺脉对应,如出现病脉,则“按之牢若痛”[22]。寻按脐部动脉不仅能获知下焦及膀胱的气血流行状态,还能探知五脏的病因。通过触摸经络的循行状态,发现阴阳、上下、内外的经络传导是否逆乱。扁鹊通过色脉合参,探知虢国太子阴阳之气脉都已逆乱,阳脉陷入阴脉之中,阴脉上争于阳络,头部阳络交会枢纽与腹部阴脉交会枢纽都已逆乱,故使人昏死而无觉,表现为“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
“中经维络”可能隐含扁鹊具体使用诊经脉的脉动和触诊络脉的方法。“脉动的观察与经脉循行理论的形成具有密切关系”[4]13。扁鹊等古医家是基于脉诊发现了体表上下特定部位的联系,并用刺脉治疗加以确认,脉诊发现脉动的不同部位,使体表上下的经线得以贯穿[23]。针刺腧穴所干预的气血信息,能够传导至经络及脏腑,而后两者变化的几微又反映在脉动处,从而使脉诊与针刺术能够不断地相互确证经络的脏腑归属与循行路线。脉诊动脉促进了经脉循行观念的形成,而切按病理性的络脉则为早期医师针刺血络提供了基点,切按络脉的形态或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切之独坚”[2]852。“对脉动的诊察既是古人认识经脉的方法,也是古人发现腧穴的途径。”[6]69如四肢腕踝关节附近的动脉多为脏腑的原穴,作为早期脉诊的部位,多是由“经脉穴”演进而来的[24]。扁鹊主要综合脉诊经脉动脉、络脉、血脉动脉的病理信息,找到矛盾的主要点位“三阳五会”。“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3]2792三阳五会可能以百会穴为中心,如《针灸甲乙经》载:“百会,一名三阳五会”[25]。扁鹊针刺头部血脉枢纽的腧穴,使阻绝于上的邪气消散,阴阳之气上下通畅。
4 小 结
脉诊的起源期,巫术与医术并存,测算生死所用的巫卜与医理尚纠缠不清,但脉诊术正在尝试摆脱蒙昧,逐渐走出宗教的统治。关于腧穴动脉、五脏动脉、经脉动脉、络脉的脉诊术已经出现,但理论化与体系化水平还不够完善。气、阴阳、五行、卦象作为理论依据及推演方式,已经得到初步的运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推天道以演人事”。天之历数在吾身,主宰天地的“象数”或“数术”作为道的涌现,同样规定着脉象的运动,探知自然之理就能获取脉象的奥秘,已然成为脉诊起源期医家逐步达成的共识。以身体作为宇宙之身,人与天地交融一体,天人的气化运动协调一致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已成为脉诊宇宙论的核心。虽然关于经脉的脉诊术已经出现,但关于十一脉、十二脉的经脉动脉系统可能仍在酝酿之中。起源期的脉诊术为中医执简御繁,提升诊断的效率和客观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脉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有效的实践经验。由于脉诊起源时期文献与出土文物的缺乏,以及史料重精简叙事而不重细节原理阐释等原因,目前关于脉诊起源期的研究存在详细考证的困难,需要更多出土文献的出现,和学者综合医史文献与临床体验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