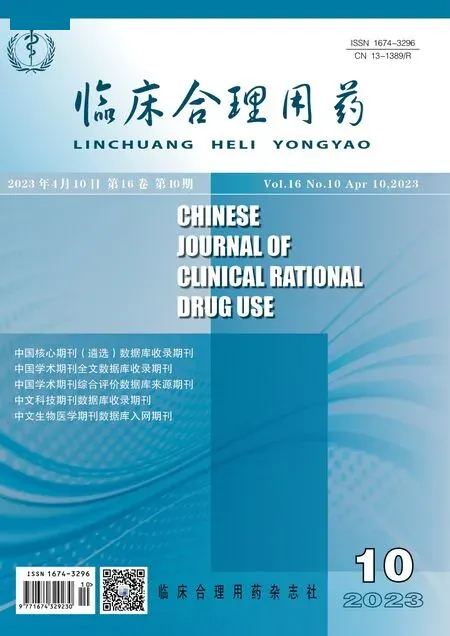抗凝治疗出血并发症的管理现状
唐凤如,林芸竹
抗凝药物已被证实可有效预防和治疗血栓栓塞性疾病,但在显著降低血栓事件发生的同时,可能导致出血并发症,严重时可致命。由于颅内出血(ICH)、大量消化道出血等主要出血并发症,许多患者和医师尽可能避免临床使用抗凝药物治疗。有研究显示,对过去1年发生2次跌倒的患者、有消化性溃疡出血史目前正在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患者或每2个月发生1次流鼻血的患者,即使发生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增加,家庭医师更倾向于选择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或不治疗,而非抗凝药物治疗[1]。临床相关性非主要出血事件可能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降低患者对抗凝治疗的依从性。据报道,口服Ⅹa因子抑制剂可导致高达30%的年轻女性月经量过多,明显高于华法林,从而导致药物或手术干预增加[2]。因此,为提高抗凝治疗的安全性、增加患者对抗凝治疗的依从性和抗凝持久性,寻找血风险较低的新型抗凝药物至关重要。
1 一般支持治疗
抗凝相关出血的基本治疗原则与其他病因的出血治疗原则相同。首先必须暂停使用任何抗凝药物、抗血小板药物或非甾体抗炎药物,然后查找出血原因,进行一般支持治疗。可立即采取的治疗措施包括局部止血、吸氧、静脉输液、其他血流动力学支持及输血。创伤相关出血建议使用氨甲环酸,因其可降低非抗凝创伤患者的出血病死率,但禁用于血尿,因其在输尿管中有形成血栓的风险。药用活性炭可加速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s)的清除,若在近2~3 h内过量服用或意外摄入DOACs导致出血,可用活性炭吸附。
评估抗凝作用有利于优化出血处理。在某些情况下,停用抗凝药物数天后,其抗凝作用可能才会消失,此时的出血治疗应集中于出血源上。对维生素K拮抗剂(VKAs),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可快速准确评估其凝血功能。而对DOACs,凝血酶时间(TT)、凝血酶原时间(PT)或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等检测凝血功能的试验最多只能对凝血功能进行粗略的定性评估。在临床治疗血药浓度范围内,达比加群呈浓度依赖性地延长APTT、利伐沙班呈浓度依赖性地延长PT,但不同试剂间敏感度差异较大,仅可用于紧急情况下快速测定抗凝活性。虽TT在较低血药浓度时即对达比加群反应敏感,但由于其结果高度依赖于仪器和试剂的使用,仅适用于检测达比加群的存在。目前,已有研究证实校准稀释的凝血酶时间(dTT)和蛇静脉酶凝血时间(ECT)可用于达比加群抗凝效果的监测,较可靠地反映抗凝效果[3]。而紧急情况下APTT若大于正常上限的2倍以上亦可初步判断抗凝过量及有较高的出血风险,但dTT、ECT多用于科研实验,目前临床应用较少。目前专门针对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的抗因子Ⅹa生色试验,对阿哌沙班、利伐沙班或依度沙班抗凝状态的快速精确定量分析也仅可在少数医疗机构中实现。
1.1 ICH ICH是抗凝治疗最严重的并发症,致死致残率高。最近一项多中心汇总分析显示,DOACs和VKAs相关性ICH的90 d病死率分别为33%和31%[4],这是所有出血并发症中病死率最高的事件,也高于非抗凝患者ICH的病死率。由于血肿会随着出血时间的延长而扩大,推测早期干预可能会获得更好的预后效果。一项队列研究评估了逆转VKAs的预后效果,结果显示,校正INR并未改善病死率或功能结局,但该研究从症状出现到治疗这一过程耗时太长,可能无法预期效果[5]。因此,与缺血性脑卒中的超早期治疗时间窗类似,ICH的止血治疗可能同样存在积极干预的时间窗。
硬膜下或脑内血肿的清除只能在抗凝作用消失或逆转后才能进行,此类侵入性操作应遵循现行指南建议[6]。可使用间歇性气压疗法预防静脉血栓,病情稳定的患者,可在出血后2~4 d内开始预防使用肝素或低分子肝素。若要重启抗凝,必须全面评估患者血栓栓塞风险和ICH复发的风险,结合患者临床特征综合考虑,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ICH恢复的最佳时间一般为8周左右,外伤性ICH恢复时间较短,硬膜下血肿、再出血或淀粉样血管病恢复时间较长[7]。
1.2 消化道出血 消化道是最常见的抗凝相关出血部位。内窥镜检查既可用于出血部位及病因的诊断,同时又可进行止血治疗,后者可通过局部注射肾上腺素、烧灼、消融术、止血夹、氩离子凝固术、硬化疗法和套扎术实现[8-9]。美国胃肠病学会分别针对静脉曲张出血、胃溃疡出血、小肠出血和下消化道出血发布了相应的治疗指南。胃溃疡出血应静脉注射质子泵抑制剂。消化道出血后应避免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如果必须治疗,可选择最低剂量的COX-2抑制剂。重启抗凝的理想时间点难以确定,但有研究显示,上消化道出血后3~6周重启效果较好[10],如果血栓栓塞的风险较高,可考虑提前重启。
2 抗凝剂的逆转
抗凝效果的逆转必须根据患者的综合情况进行个体化。逆转抗凝作用需平衡血栓栓塞的风险、考虑抗凝治疗的适应证和出血的严重程度、逆转的紧迫性及对完全逆转的需求。
2.1 VKAs的逆转 VKAs通过影响维生素K循环使维生素K依赖的凝血因子Ⅱ、Ⅶ、Ⅸ和Ⅹ及抗凝蛋白C、S和Z无法羧基化,从而使凝血因子的合成受到抑制。大出血时可使用血浆、维生素K或凝血酶原复合物浓缩制剂(PCCs)替代凝血因子逆转VKAs的抗凝作用。
2.1.1 维生素K:维生素K可通过静脉注射、口服或皮下注射的形式给药,前两种给药途径的生物利用度高于皮下注射[11]。虽口服和静脉注射维生素K 24 h后的INR校正效果相似,但静脉注射的优势在于6~8 h内可实现INR的校正。因此,美国胸科医师协会指南建议采用缓慢输注(超过30 min)的方法静脉输注5~10 mg的维生素K逆转VKA相关大出血,同时使用凝血酶原复合物(PCC)等快速逆转剂[12]。联合用药的原因在于维生素K依赖性凝血因子,特别是凝血因子Ⅶ的半衰期较短,PCC给药仅可短暂校正INR,若要更持久地纠正INR,则需服用维生素K,因其可恢复这些凝血因子的肝脏合成。
2.1.2 PCC与血浆:血浆中含有所有类型的维生素K依赖性凝血因子,其理论浓度为1 U/ml。然而,若要补充等量凝血因子,大约需输注2 L血浆,这是难以快速输血的体积,尤其是对有容量超负荷风险的老年患者。此外,血浆必须解冻并且与血型匹配,同时血浆输注可能会引起感染、急性输血反应或急性肺损伤等并发症。相较于血浆,PCC无需解冻或与血型匹配,并且所需剂量是血浆的1/25。非活化的PCC有3F-PCC和4F-PCC两种形式,但3F-PCC的凝血因子Ⅶ的浓度非常低。因此,若使用3F-PCC逆转华法林的抗凝作用,需添加血浆以提供凝血因子Ⅶ。Chai-Adisaksopha等[13]的荟萃分析比较了血浆与PCC在因大出血或急诊手术前需紧急逆转华法林的患者中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PCC可更迅速地校正INR值、更有效地降低全因病死率且可避免输血引起的容量过载。与接受血浆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PCC的患者有效止血率更高,但结果无统计学意义。此外,2组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无差异。鉴于此结果,美国胸科医师学会指南建议使用PCC而非血浆快速纠正华法林相关出血[12]。
2.2 肝素的逆转 普通肝素(UFH)本身不能直接灭活凝血因子,通过与抗凝血酶Ⅲ(AT Ⅲ)结合改变构象,从而增强AT Ⅲ对凝血因子Ⅹa和Ⅱa的抑制作用。
2.2.1 硫酸鱼精蛋白:硫酸鱼精蛋白是一种从鱼类成熟精巢组织中提取的强碱性阳离子多肽,可通过与强酸性阴离子肝素形成复合物完全逆转UFH的抗凝作用。硫酸鱼精蛋白的半衰期很短,若要完全逆转UFH可能需重复给药,但一次用量不超过50 mg。APTT可用于监测鱼精蛋白的逆转作用。鱼精蛋白仅部分逆转低分子肝素的抗Ⅹa活性。因此,即使服用鱼精蛋白后APTT可能恢复正常,也需同时监测抗Ⅹa活性。
2.2.2 重组活性凝血因子Ⅶ(rFⅦa):有研究显示,rFⅦa可逆转UFH和依诺肝素的抗凝血作用[14];动物研究[15]和病例报告显示[16],可控制UFH和低分子肝素(LMWH)引起的出血。然而,鉴于超说明书使用rFⅦa的有效性缺乏依据,其应用应限于UFH或LMWH相关的严重出血[17]。
2.3 戊糖抗凝剂的逆转 磺达肝癸钠是新型Ⅹa凝血因子选择性抑制剂,是目前唯一用于VTE治疗和预防的戊糖类抗凝剂。磺达肝癸钠无特效解毒剂,鱼精蛋白不能逆转磺达肝癸钠的抗凝血作用。
2.3.1 活化凝血酶原复合物(aPCC):一项动物模型研究显示,aPCC修正了内源性凝血酶电位(ETP),缩短了磺达肝癸钠相关出血的持续时间[18]。在一项由无出血健康志愿者参与的体外研究中,比较了PCC、aPCC和rFⅦa在纠正凝血酶生成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低剂量aPCC完全纠正凝血酶生成,而rFⅦa部分纠正凝血酶生成[19]。这一逆转效应仅限于体外,可能无法在体内实现。
2.3.2 rFⅦa:研究表明,在使用治疗剂量(10 mg)磺达肝癸钠的健康志愿者中,高剂量(90 μg/kg)rFⅦa除可逆转磺达肝癸钠的体外抗凝作用外,还可使EPT、APTT和PT恢复正常[20]。此外,Luporsi等[21]的报道显示,在8例与磺达肝癸钠相关危及生命的出血患者中,使用90 μg/kg rFⅦa进行治疗,4例患者的出血得以控制。因此,rFⅦa可用于逆转磺达肝癸钠相关的严重出血,同时应注意其超说明书使用时增加血栓栓塞发生的风险[17]。
2.4 直接凝血酶抑制剂(DTIs)的逆转 DTIs可直接抑制凝血酶活性而不依赖于辅助因子。按照与凝血酶作用位点的作用方式,DTIs可分为二价抑制剂(水蛭素和比伐卢定)和非二价抑制剂(阿加曲班和达比加群)。除口服的DTIs达比加群外,所有肠外DTIs均无直接逆转剂,考虑其半衰期较短,可通过停药控制出血症状。
2.4.1 血液透析:达比加群与血浆蛋白的结合力较低,血液透析法可将其从体内清除。一项涉及22项研究的系统评价显示,在35例接受肾脏替代疗法逆转达比加群相关出血的患者中,24例成功止血[22]。肾脏替代疗法治疗显著降低达比加群的血药浓度,而停止血液透析后,12例患者的血药浓度出现反弹性增加,提示延长肾脏替代疗法过程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2.4.2 PCC:在一项由12例健康受试者参与的Ⅰ期临床试验中[23],评估了PCC逆转达比加群和利伐沙班抗凝作用的能力,结果显示,4F-PCC不能修正达比加群造成的aPTT、ECT及TT这3个凝血指标的升高;相反,4F-PCC可完全逆转利伐沙班对TT和内源性TT的作用。因此,该研究未深入探讨4F-PCC对达比加群抗凝作用的逆转效果。
2.4.3 aPCC:一项涉及14例达比加群相关大出血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评估了50 U/kg剂量下aPC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中9例患者获得了良好的止血效果,其余3例止血效果中等,均无血栓栓塞并发症[24]。因此,在无法获得idarucizumab的情况下,aPCC可作为达比加群相关大出血治疗的替代方案。
2.4.4 idarucizumab:idarucizumab是一种特异性拮抗达比加群的人源性单克隆fab抗体片段,与达比加群有极高的亲和力,可迅速完全地逆转达比加群的抗凝血作用。一项涉及503例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开放性研究评价了idarucizumab在301例达比加群相关大出血患者和202例需接受紧急手术患者中的抗凝作用,结果显示idarucizumab止血效果较好,有67.7%的大出血患者在24 h内完全止血;在接受紧急手术的患者中,93%的患者止血效果被评定为“正常”,5%的患者被评定为“轻度异常”,2%的患者被评定为“中度异常”;503例患者中有24例在30 d内发生血栓栓塞并发症,34例在90 d内发生血栓栓塞并发症[25]。在紧急情况下,idarucizumab可快速、持久且安全地逆转达比加群的抗凝作用。
2.5 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的逆转 阿哌沙班、依度沙班和利伐沙班等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与间接抑制剂不同,直接抑制凝血因子Ⅹa不依赖抗凝血酶发挥作用。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相关出血的治疗与达比加群相似,但由于其与血浆蛋白的结合力极强,血液透析法难以将其清除。
2.5.1 PCC: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26-27]评估了4F-PCC治疗阿哌沙班或利伐沙班相关大出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中,瑞典的一项研究[27]显示,在84例接受4F-PCC治疗的患者中,有效58例,无效26例,26例无效患者中有61.5%的患者发生ICH,2例患者在30 d随访期间出现缺血性脑卒中。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6例接受4F-PCC治疗的大出血患者中,有效45例,无效21例,在30 d随访期间,5例患者出现严重血栓栓塞,9例死亡患者中有7例是由于ICH所致[27]。
2.5.2 andexanet alfa:andexanet alfa是人源性重组凝血因子Ⅹa(FⅩa)诱导蛋白,用于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的逆转,是Ⅹa因子的一种非活性形式,通过与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特异性结合从而阻断抗凝药物对内源性Ⅹa因子的作用,实现抗凝逆转。一项前瞻性、开放性研究评估了228例急性大出血患者应用andexanet alfa逆转Ⅹa因子抑制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该试验的中期结果显示,andexanet alfa治疗的有效率为58%,有109例患者在12 h内获得良好或极好的止血效果,在30 d随访期间,有24例患者发生血栓事件,27例患者死亡[28]。该药适用于逆转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所致的大出血,但不适用于紧急手术。有些医疗机构无法获得该药,也可使用4F-PCC逆转直接Ⅹa因子抑制剂引起的大出血。
3 总 结
抗凝药物的研发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虽发展迅速,但目前仍未找到最理想的抗凝药物。靶向于凝血因子Ⅺ和Ⅻ的新型抗凝药物正在研发[29],虽与目前的抗凝药物相比,这一研发的主要目的是预防血栓并进一步降低出血风险,但当遭遇创伤、血管破裂或需急诊大手术时,出血永远不能避免。因此,具有特异性逆转剂未来可能会成为新型抗凝剂获批的一项要求。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