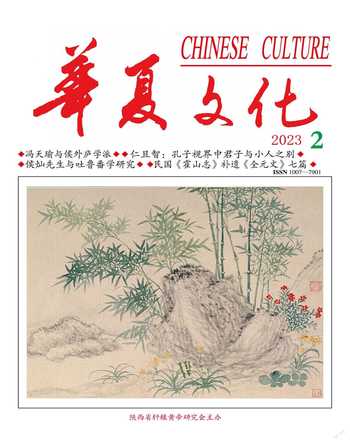天理之节文
屈泽平
在宋朝时期,儒家面临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朱熹重新诠释了《论语》中的“礼”,将其推至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他深入研究了从先秦到汉、唐、宋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礼学思想,对传统的“礼”进行了深度梳理和创新性改革。在继承和发展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基础之上,朱熹将理学与礼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礼”与“天理”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其晚年,朱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将“礼”与“理”相融合的解释,将“礼”释为“天理之节文”(参见申淑华:《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中华书局2019年,第186页)。朱熹对“礼”的这种诠释为后世的中外儒家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日本的儒学研究中,日本学者们明确地提出了“理即是礼”。他们认为,朱熹理学思想的本质就是将传统的礼学推向了宇宙论的高度([日]小島 毅:《東アジアの儒教の礼》,东京:山川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虽然学界对朱熹的“礼”与“天理”的理解已有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礼”与“天理”的辩证关系、“礼”的内涵和功能以及其在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朱熹如何将“礼”与“天理”有机地结合,以及这个问题上的困境和不足。有的研究过于强调“礼”与“理”的二元对立,忽视了朱熹通过“礼”阐释“天理”的深刻内涵。有些研究过于关注“礼”的形式化和外在表现,而忽视了朱熹在“天理”与“礼”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将以朱熹晚年释“礼”为“天理之节文”为中心,通过梳理朱熹“礼”与“天理”关系的发展过程,揭示朱熹在礼学与理学构建过程中的相互促进与影响。望能为深入、全面理解朱熹的思想以及宋明理学的研究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朱熹“礼为天理之节文”思想的来源
朱熹在提出的“礼者天理之节文”这一思想的过程中,深受早前的理学家张载与二程思想之影响。关于“理”与“礼”关系最早的交融可追述到《礼记》,其中写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其意思为“礼”所表达的是不可变易的的道理。(胡平生张萌译著:《礼记》,中华书局2017年,第655页)此处的“理”所表达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逻辑,并未上升到道德法则与宇宙秩序的高度。
张载开创了以重“理”为特色的儒家思想派别——关学,提出了“本体论”即“理气”的观念,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由“理”和“气”所共同构成。“理”是事物存在的最本质原则,“气”则是物质实体的具体表现。将“理”从事物发展的规律逻辑上升至宇宙秩序的高度。同时,在张载的《张子语录》中写道:“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26-327页)。张载在这了阐述了“礼”与“理”之关系,认为“理”为“礼”之源、标准,“礼”则是“理”在现实世界的具体表现。人们只有在明“理”之后才可明“礼”。虽然张载对“理”与“礼”之关系的探讨尚未达到很深入的程度,但其为后来朱熹关于“理”与“礼”的关系论述奠定了理学发展之方向与基础框架。
二程在张载所建立的“理学”框架上提出了“理”为“天理”的概念并与人的道德品性做出了结合。强调人类在追求道德价值时,应遵循自然和宇宙的普遍规律。二程指出:“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程顥、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此处的“天理”以不仅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原则,而是上升到了覆盖道德伦理的高度,指导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一概念强调了人类在追求道德价值时,应遵循自然和宇宙的普遍规律,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在“理”与“礼”的关系方面二程指出:“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 (《二程集》,第143页)二程将“理”与“礼”进行了融合统一,“天理”为源,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性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礼”为表,在此过程中则作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做具体指导,这对朱熹后来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基于张载与二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理”与“礼”的关系,使之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他继承了张载对于“理”与“礼”关系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理”与“礼”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朱熹接受并发展了二程“理”为“天理”的观念并提出了“天理论”,更进一步地强调了“理”的普遍性,朱熹认为:“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和宇宙原则,它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贯穿在整个宇宙之间,而且是统一不变的。所有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围绕这这个“理”来进行的。“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栽了”。(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5页)然后,在“礼”这一方面朱熹则认为以“天理”来释“礼”很难体现“礼”的精湛细腻,因此提出了“礼”即“节文”,“无礼则无节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21年,第141页)朱熹对“节文”的解释为“节文,谓品节文章,节谓等差,文谓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第963页)即“节文”为文章之品节,让文章的各个部分组织有序,各司其职。朱熹认为:若心中无这“天理”,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等“节文”动作皆为空有,不能算作真正的礼乐。“天理”为根本,周旋百拜等礼之仪节是“天理”的表现形式。(郭春兰:《朱熹对〈论语〉“礼”的三维解释》载《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三期)“若天理不亡,则见得礼乐本意,皆是天理中发出来,自然有序而和。若是胸中不有正理,虽周旋于礼乐之间,但见得私意扰扰,所谓升降揖逊,铿锵节奏,为何等物!不是礼乐无序与不和,是他自见得无序与不和,而礼乐之理自在也。”(《朱子语类》,第607页)
二、朱熹“礼为天理之节文”的表现
朱熹释“理”为形而上之“天理”,释“礼”为形而下之“节文”,就体用而言则“天理”为体,“节文”为用。朱熹曾深入讨论过关于“何为体?何为用?”这一问题,当被问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如何看‘体字?”朱熹回答:“体,是体质之‘体,犹言骨子也。易者,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谓,如寒暑昼夜,阖辟往来。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盖与道为体也。寒暑昼夜,阖辟往来,而实理于是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所顿放。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实理寓焉。故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此理之体质也。”(《朱子语类》,第2422页)朱熹在此处认为“体”为事物的内在本质,犹如骨架,是支撑事物存在的内在基础,且不随着事物外在改变而改变。而“用”则为阴阳交错,寒暑昼夜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表现,为万事万物在具体环境中受自然规律影响后的具像化表现。
在这段话中,朱熹同时也阐述了“实理流行,盖与道为体”。他认为“实理”穿流于自然循环中的阴阳交错、寒暑昼夜、阖辟往来之中,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中穿行,这与“道”一样,构成了世界的“体”。在这里,“实理”与朱熹理论中的“天理”有着相似的含义,都是指普遍存在的道德和宇宙原则,它贯穿在整个宇宙之间,是一种至高的真理,构成了支撑宇宙和人际关系背后的本质原则。朱熹在此处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这些自然现象和人际关系作为载体,“天理”则将无处安放,也无法得以真正的实现。
关于体用之别,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的解释如下:“问:‘先生昔曰: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朱子语类》,第101页)在朱熹的理念中,“体”代表了事物的本质、是最根本原则,不受外在因素影响的存在,“礼”是“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表现和功能,是“体”在受到外在影响因素的引导下的应用状态。朱熹在此明确的强调“礼”并非“体”。朱熹通过对“体”与“用”的划分,深化了对它们之间互动和区别的理解。
在朱熹的理念中可以看到,“天理”贯穿于宇宙的一切事物,如果没有特定的载体,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而“礼”则是“天理”的载体,作为其在这个宇宙中的具体投射。“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是朱熹对“礼”的阐释,这之中针对的对象有两个,两者对“礼”的阐释,共同揭示了“礼”的本质和功能,即“天理”的具体表现和应用。“天理之节文”主要描述了“礼”在“天理”中的表现,强调了“礼”的抽象性和普遍性。这一观念侧重于“礼”的宇宙性,即“礼”是宇宙中的普遍法则,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体现。相对地,"人事之仪则"则着重强调了"天理"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现,它提供了对"礼"的具体化和具象化的解释。这一观念突出了"礼"的实用性,即"礼"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指南。
这两个解释的层面,一方面揭示了朱熹对“礼”的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他的“体用”理念——“礼”不仅具有其固定的形式和规则,同时也在特定情境中有其独特的表现和功能。在朱熹的体用论中,“节文”被视为“天理”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与功能,即当“天理”被置于特定载体后的应用状态。
朱熹对于“天理”为体,“节文”为用的思考,不仅赋予了“礼”宇宙性和实用性,同时也深化了其对“体用”理论的阐述。在朱熹的理念中,理解和实践“天理”为体,“节文”为用是理学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实现个人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它能引导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正确地应用道德原则,从而达到内心的平和与社会的和谐。进一步地,这种理念也强调了对于个体的道德自律与对于社会的责任认知,为个人的道德提升与社会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评价
朱熹对“礼”的阐释其本意为应对佛道对儒家思想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使得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佛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宇宙观极其完善,吸引了大量的人民。而朱熹释“礼”为“天理之节文”,强调了“天理”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实现。在朱熹的理念中,“礼”不仅是规范和约束的外在行为,更是“天理”的具体表现。朱熹的这一观点把“礼”与宇宙的本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礼”不再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的规范,更是一种深层次且普遍存在的道德和宇宙原则在人类生活空间的投射。这大大的升华了“礼”的思想高度,使之具有了更深刻的道德和哲学含义。
朱熹的“天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这个理论将儒学思想直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天理”终究是一个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虽然完善了儒家思想中贯穿于整个宇宙统一不变的终极本质真理,让儒家思想更具有深远的哲学内涵和积极的道德价值,但由于其形而上的特性,“天理”并不能直接解答所有具体的社会与自然世界的问题,也不能直接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所以朱熹晚年的释“礼”为“天理之节文”可以视其为朱熹对其“天理”思想的一个补充。赋予了“天理”更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应用方式,即通过遵循和实践“礼”,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实现天理,使形而上的“天理”具有了形而下的“礼”这个具体的实践路径。这样就使得朱熹的“天理论”不仅仅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具有了现实的指导意义,也使得他的儒学思想更具有了生活性和实践性。
然而,正因为朱熹晚年在阐释“礼”的思想过程中大量借鉴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并且将“天理”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将“礼”从原本孔子时代的崇高地位降低到“天理之节文”,这引发了清代儒家学者们的激烈争论。清儒凌廷堪尖锐地指出:“后儒置子思之言不问,乃别求所谓仁义道德者,于礼则视为末务,而临时以一理衡量之,则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鲜矣。”凌氏认为,凭空来谈天地之先的天理是无意义的,礼是直接针对心性的节文,而与这个先天之理无关。(吴飞:《礼者天理之节文”平议——从文质论的角度看》载《孔学堂》2022年第4期)凌廷堪认为朱熹的天理之学乃是出自佛学,认为“理”根本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概念,推崇将“礼”恢复到孔子时期的高度。这种批评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争议,包括“礼”与“理”的关系,如何理解“礼”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等。
尽管朱熹晚年关于“礼”的论述使儒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使得朱熹的理學体系更加完善,但他的这些论述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细节问题,从而引发了后世儒家学者对其理学的争论。朱熹将“礼”解释为“天理之节文”,赋予了“礼”更深远的哲学内涵,使得“礼”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而且是通往理解宇宙终极本质的重要途径。这种思想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争议,包括“礼”和“理”的关系,如何理解“礼”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等问题。这类问题在后世所引发的激烈讨论虽然主要集中在对朱熹理学的理解及其应用的层面,但却深刻地揭示了朱熹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度。这种争论在推动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它激发了对朱熹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力和广度。朱熹将“礼”视为“天理之节文”,巧妙地把理论与实践,形而上与形而下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大价值,对后世儒家思想的研究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日本国士馆大学硕士研究生,邮编:154-8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