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诸之麋”与两周时期麋鹿的文化意蕴
罗笛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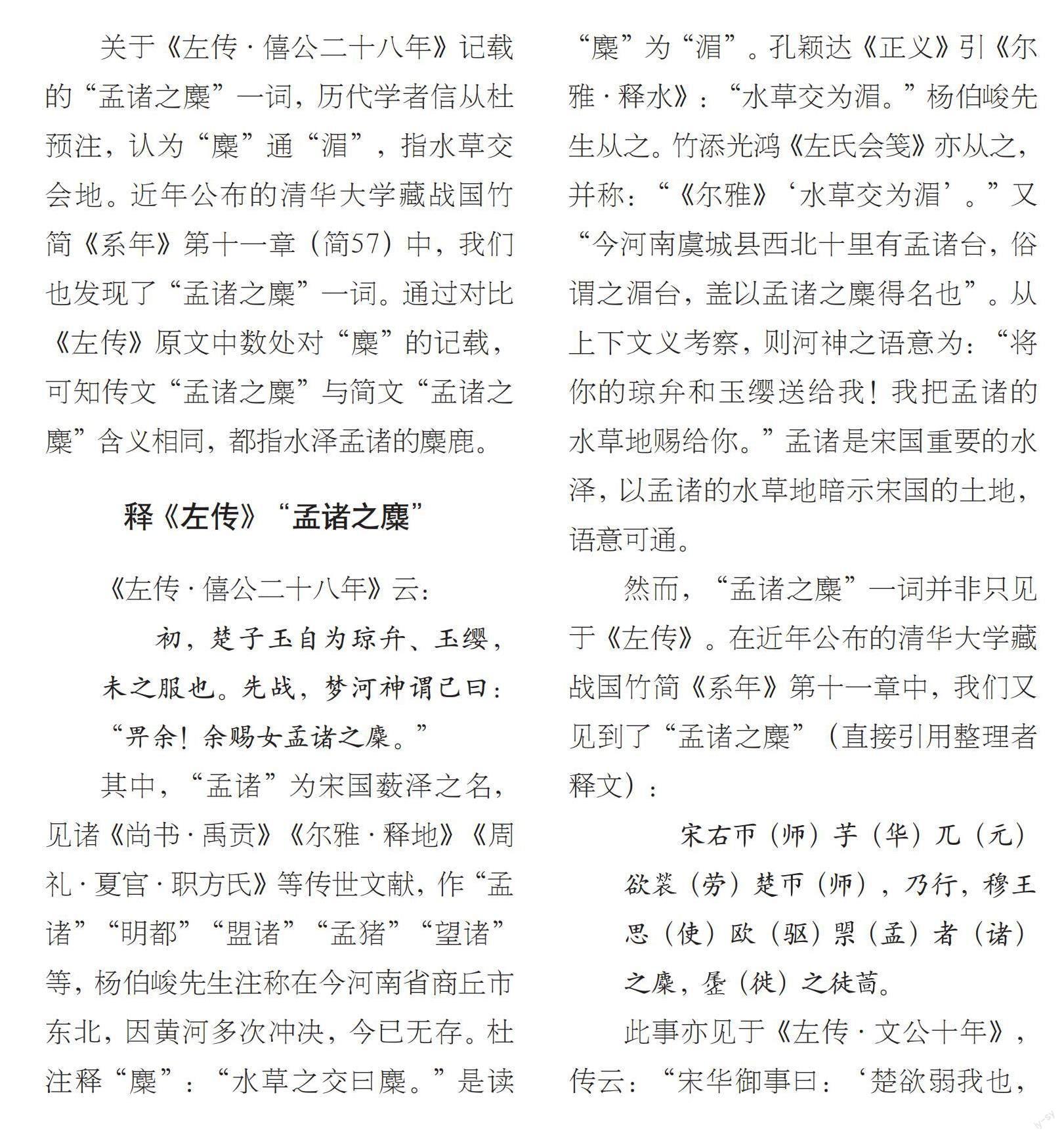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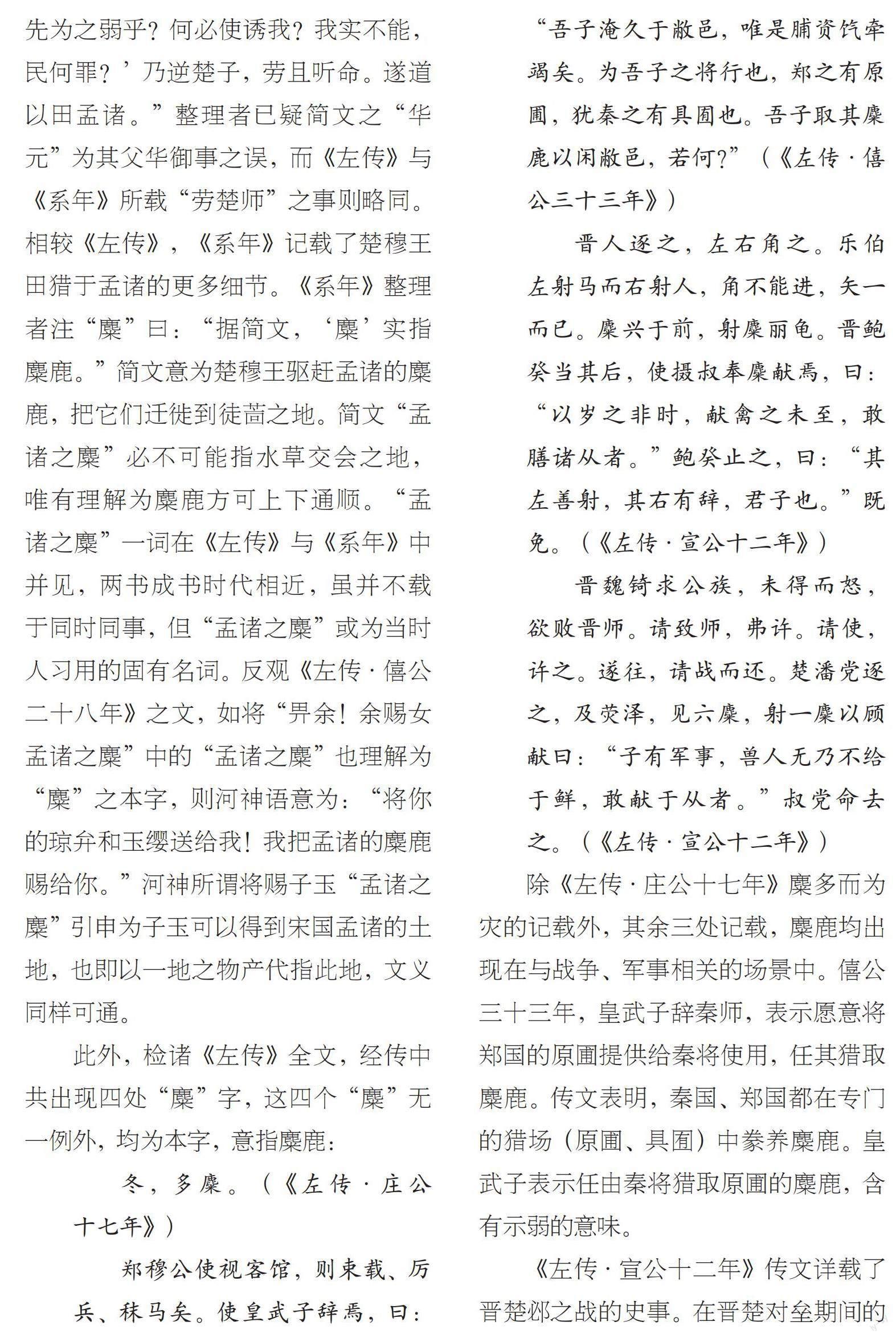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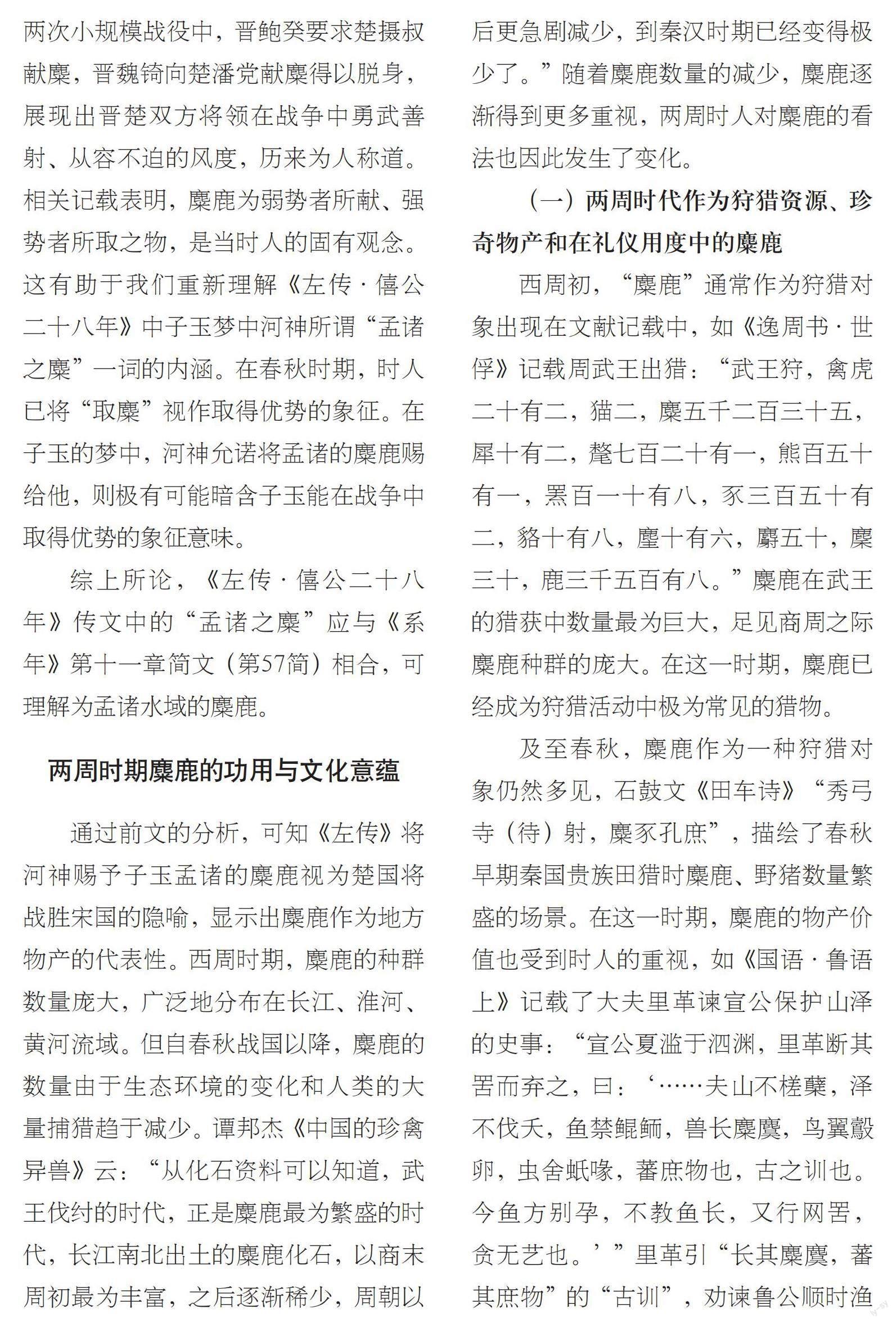
关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的“孟诸之麋”一词,历代学者信从杜预注,认为“麋”通“湄”,指水草交会地。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十一章(简57)中,我们也发现了“孟诸之麋”一词。通过对比《左传》原文中数处对“麋”的记载,可知传文“孟诸之麋”与简文“孟诸之麋”含义相同,都指水泽孟诸的麋鹿。
释《左传》“孟诸之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
其中,“孟诸”为宋国薮泽之名,见诸《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夏官·职方氏》等传世文献,作“孟诸”“明都”“盟诸”“孟猪”“望诸”等,杨伯峻先生注称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因黄河多次冲决,今已无存。杜注释“麋”:“水草之交曰麋。”是读“麋”为“湄”。孔颖达《正义》引《尔雅·释水》:“水草交为湄。”杨伯峻先生从之。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亦从之,并称:“《尔雅》‘水草交为湄。”又“今河南虞城县西北十里有孟诸台,俗谓之湄台,盖以孟诸之麋得名也”。从上下文义考察,则河神之语意为:“将你的琼弁和玉缨送给我!我把孟诸的水草地赐给你。”孟诸是宋国重要的水泽,以孟诸的水草地暗示宋国的土地,语意可通。
然而,“孟诸之麋”一词并非只见于《左传》。在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十一章中,我们又见到了“孟诸之麋”(直接引用整理者释文):
宋右(师)芋(华)兀(元)欲(劳)楚(师),乃行,穆王思(使)欧(驱)(孟)者(诸)之麋,(徙)之徒。
此事亦见于《左传·文公十年》,传云:“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整理者已疑简文之“华元”为其父华御事之误,而《左传》与《系年》所载“劳楚师”之事则略同。相较《左传》,《系年》记载了楚穆王田猎于孟诸的更多细节。《系年》整理者注“麋”曰:“据简文,‘麋实指麋鹿。”简文意为楚穆王驱赶孟诸的麋鹿,把它们迁徙到徒之地。简文“孟诸之麋”必不可能指水草交会之地,唯有理解为麋鹿方可上下通顺。“孟诸之麋”一词在《左传》与《系年》中并见,两书成书时代相近,雖并不载于同时同事,但“孟诸之麋”或为当时人习用的固有名词。反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之文,如将“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中的“孟诸之麋”也理解为“麋”之本字,则河神语意为:“将你的琼弁和玉缨送给我!我把孟诸的麋鹿赐给你。”河神所谓将赐子玉“孟诸之麋”引申为子玉可以得到宋国孟诸的土地,也即以一地之物产代指此地,文义同样可通。
此外,检诸《左传》全文,经传中共出现四处“麋”字,这四个“麋”无一例外,均为本字,意指麋鹿:
冬,多麋。(《左传·庄公十七年》)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左传·宣公十二年》)
晋魏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荧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除《左传·庄公十七年》麋多而为灾的记载外,其余三处记载,麋鹿均出现在与战争、军事相关的场景中。僖公三十三年,皇武子辞秦师,表示愿意将郑国的原圃提供给秦将使用,任其猎取麋鹿。传文表明,秦国、郑国都在专门的猎场(原圃、具囿)中豢养麋鹿。皇武子表示任由秦将猎取原圃的麋鹿,含有示弱的意味。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文详载了晋楚之战的史事。在晋楚对垒期间的两次小规模战役中,晋鲍癸要求楚摄叔献麋,晋魏向楚潘党献麋得以脱身,展现出晋楚双方将领在战争中勇武善射、从容不迫的风度,历来为人称道。相关记载表明,麋鹿为弱势者所献、强势者所取之物,是当时人的固有观念。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子玉梦中河神所谓“孟诸之麋”一词的内涵。在春秋时期,时人已将“取麋”视作取得优势的象征。在子玉的梦中,河神允诺将孟诸的麋鹿赐给他,则极有可能暗含子玉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的象征意味。
综上所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文中的“孟诸之麋”应与《系年》第十一章简文(第57简)相合,可理解为孟诸水域的麋鹿。
两周时期麋鹿的功用与文化意蕴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左传》将河神赐予子玉孟诸的麋鹿视为楚国将战胜宋国的隐喻,显示出麋鹿作为地方物产的代表性。西周时期,麋鹿的种群数量庞大,广泛地分布在长江、淮河、黄河流域。但自春秋战国以降,麋鹿的数量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大量捕猎趋于减少。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云:“从化石资料可以知道,武王伐纣的时代,正是麋鹿最为繁盛的时代,长江南北出土的麋鹿化石,以商末周初最为丰富,之后逐渐稀少,周朝以后更急剧减少,到秦汉时期已经变得极少了。”随着麋鹿数量的减少,麋鹿逐渐得到更多重视,两周时人对麋鹿的看法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一)两周时代作为狩猎资源、珍奇物产和在礼仪用度中的麋鹿
西周初,“麋鹿”通常作为狩猎对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如《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出猎:“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麋鹿在武王的猎获中数量最为巨大,足见商周之际麋鹿种群的庞大。在这一时期,麋鹿已经成为狩猎活动中极为常见的猎物。
及至春秋,麋鹿作为一种狩猎对象仍然多见,石鼓文《田车诗》“秀弓寺(待)射,麋豕孔庶”,描绘了春秋早期秦国贵族田猎时麋鹿、野猪数量繁盛的场景。在这一时期,麋鹿的物产价值也受到时人的重视,如《国语·鲁语上》记载了大夫里革谏宣公保护山泽的史事:“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麋,鸟翼卵,虫舍喙,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里革引“长其麋,蕃其庶物”的“古训”,劝谏鲁公顺时渔猎,保护山泽。以是言观之,麋鹿已经被视作一种需要保护的物产资源,在山泽兽类当中具有代表性。此外,为保护麋鹿这一狩猎资源,春秋各国建立起名称各异的园囿猎场来收容麋鹿,“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可见在春秋中期,麋鹿已经得到贵族阶层的重视。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的兽人一职“掌罟田兽,辨其名物。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正与摄叔所谓“岁之非时”相合。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规定如何运用麋鹿制品的礼仪制度已经形成。麋鹿皮革还被用于射礼中矢侯的制作,《仪礼·乡射礼》载:“凡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周礼·天官冢宰》载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显然麋鹿裘皮的使用又与射礼矢侯的等级设置相关。《仪礼·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又升鱼、腊,鱼十有五而鼎,腊一纯而鼎,腊用麋。”这些载于礼书的材料表明,麋鹿及其制品已广泛地融入了周人的贡献、飨宴、射礼等诸多礼仪活动中,麋鹿的贡献有时间规定,麋皮箭靶(麋侯)又对应射礼中相应的贵族等级。麋鹿在贵族的礼仪用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将麋鹿视为狩猎资源加以保护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如《管子·国准》谓:“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其反映出的保護山泽、“用而勿尽”、任麋鹿牛马保有其地的思想与《国语》所载里革之语一脉相承。由于战国时代麋鹿数量的减少,各国贵族延续了在园囿、庭院中豢养麋鹿的习惯,麋鹿开始被视为“珍奇”受到保护。在齐国,齐宣王设囿方四十里,严令禁止捕杀麋鹿:“(孟子)曰:‘……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国贵族亦在庭院中饲养麋鹿,如《楚辞·九歌·湘夫人》云:“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而在战国末期的魏国:“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说明魏国也在国都大梁附近设置苑囿来豢养麋鹿,《史记》载其麋鹿尽失,足见魏人亦将麋鹿视作珍奇。
(二)春秋战国时期麋鹿的文化意蕴
前文引及的《左传》和清华简《系年》第十一章对麋鹿的相关记载,鲜明地展现了麋鹿在春秋时人心目中的形象。《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皇武子辞秦师,表示愿意将郑国的原圃提供给秦将使用,任其猎取麋鹿。不难发现,在僖公时代,秦国、郑国都已经在专门的猎场(原圃、具囿)中豢养麋鹿,这说明麋鹿作为一种贵族狩猎的猎物开始得到重视。而郑国任由秦将猎取原圃的麋鹿,已然显示出“降服、示弱”的内在含义,十分值得注意。
清华简《系年》第十一章记载:“宋右师华元欲劳楚师,乃行,穆王使驱孟诸之麋,徙之徒。”这对《左传·文公十年》所载宋华御事“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的史事提供了补充,楚穆王在孟诸田猎,将孟诸的麋鹿驱赶至徒。前辈学者已经指出,楚穆王驱麋至徒,“大概是君主们敛聚珍奇之物一类的行为”。由是观之,在楚穆王时期,楚人将麋鹿视为“珍奇之物”,而宋人任由楚穆王将孟诸之麋驱往楚国的园囿,一方面展示了宋人“先为之弱”的姿态,另一方面又说明楚人也将“取其麋鹿”视为“使之屈服”的象征。显然与皇武子辞秦师中所谓“吾子取其麋鹿以闲鄙邑”异曲而同工。由这两则材料来看,在春秋时期,献麋与取麋已经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从《左传·宣公十二年》传文对晋鲍癸要求楚摄叔献麋,晋魏向楚潘党献麋的记载,可见晋楚双方都将“献麋”视作降服的标志。这又将《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文与《系年》简文当中“麋鹿”作为顺服一方贡献之物的做法加以延续。麋鹿为败者所献、胜者所取之物的传统已然树立起来,在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同样适用。这些记载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子玉梦中河神所谓“孟诸之麋”一词的内涵。在僖公、文公、宣公时代,时人已将“取麋”视作战役胜利、取得优势的象征。
考古资料显示,战国以后,中国北方的麋鹿数量开始锐减。各诸侯国都将麋鹿豢养于苑囿、庭院中加以保护,而麋鹿这一形象也开始大量地出现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其文化意蕴又经历了新的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周威王与晋太史屠黍论及中山国风俗:“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吕氏春秋·恃君》谈到四方之族无君时则称:“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我们不难发现,“麋鹿”往往与原始、野蛮的状态相关,而禽兽麋鹿并称的用法则说明“麋鹿”成为一种对野生动物的泛称。《庄子·杂篇·盗跖》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此语可以与《庄子·天地篇》“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一句并观,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看来,麋鹿(或野鹿)具有“返璞归真、放而自得”的文化内涵。
战国时期北方麋鹿种群数量锐减,但在南方的楚国,麋鹿的生存状态又是另一番景象。楚国的云梦泽宽广无垠,是泽兽的理想栖息地。故而战国时期,楚国仍然拥有大量的麋鹿,《山海经·中山经》载:“东北百里曰荆山……其兽多闾麋。”《墨子·公输》也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这些记载反映出楚国麋鹿种群的繁盛。楚国贵族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兴建庭院,豢养麋鹿,又将麋鹿制品和刻画着麋鹿形象的艺术品带到了逝者的世界。包括麋鹿角在内的各种未经加工的鹿角和饰以鹿角的镇墓兽、漆木鹿、虎座飞鸟在战国时代的楚人墓葬中多有发现。大量的文物为我们了解麋鹿在楚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材料。
楚人随葬麋鹿,将麋鹿角安插在造型怪诞奇诡的镇墓兽、虎座飞鸟形器身上的习惯鲜见于文献,但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十分常见。楚墓中大量出土的镇墓兽仿佛表明,饰以鹿角的镇墓兽的设置,是贵族死者入土为安、安居阴宅的重要条件。《说文解字》谓:“麋,鹿属,从鹿,米声。麋冬至解其角。”在巫风盛行的楚国,麋鹿在万物寂灭的冬季解角而又在万物复苏的春季迅速恢复,无疑成为生命力和再生的神秘象征。这或许是楚人墓葬重视麋鹿,直接使用麋鹿角陪葬的重要原因。
周初至春秋初期,麋鹿数量丰富,成为周代贵族狩猎活动的重要猎物。春秋以后,保护山泽禽兽的思想得到发展,麋鹿成为时人眼中重要的物產。战国时代,随着麋鹿数量的逐渐减少,各诸侯国纷纷兴建苑囿豢养麋鹿以为珍奇。此外,各类礼书中也记载了麋鹿及其制品在周人礼仪中的应用情况,说明麋鹿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贡献、飨宴、射礼等贵族礼仪中不可或缺的物质素材。
两周时代,麋鹿作为狩猎资源、珍奇物产受到周人的重视,在礼仪用度中广泛使用,其在时人眼中的文化内涵也经历了丰富和发展。西周初至春秋初期,由于种群数量的丰沛,麋鹿只是作为常见的野兽或导致灾害的野兽得到记录。及至春秋中叶,麋鹿成为各国重视的物产资源,交战双方中的“取麋”“献麋”开始具备胜利或屈服的政治意义。战国以后麋鹿数量锐减,在战国诸子的作品中,麋鹿一方面被视作原始野蛮的野兽,往往出现在对上古时代的追述中;另一方面又成为恬静自然的象征物。此外,崇巫信鬼的楚人还将麋鹿的形象带入了逝者的世界,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贵族墓葬中,麋鹿的骸骨和装饰着麋鹿角的镇墓兽、虎座飞鸟被广泛发现,说明在战国楚人的观念中,麋鹿和鹿角又获得了驱恶辟邪、护佑死者的特殊内涵。
——————————————————————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