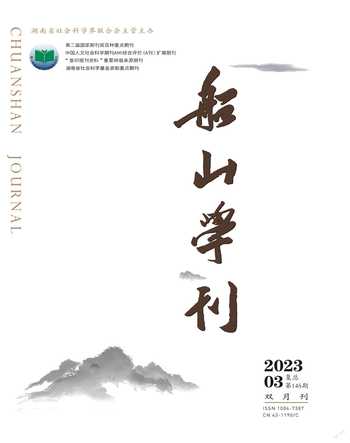在人心与道心之间
摘要:王夫之对“四情”的解释有其与理学对话的背景,在此对话关系中,四情即喜怒哀乐。在王夫之的诗学中,“四情”与“兴观群怨”分别是情的“体”与“用”,“兴观群怨”将情从“私情”的偏狭中引导到包蕴伦理潜能的“道心”之中。因此,文学或诗歌不再是局限于审美内部的“雕虫”小技,其本身就是社会中的重要环节,王夫之通过阐述《诗经》的“周文”传统揭示了这一点。王夫之“兴观群怨”的整体观有其政教含义,即揭示一种无偏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属于“道心”的普遍的善的情感,能够塑造社会的伦理。
关键词:王夫之四情兴观群怨人心道心
作者战智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既往阐释者多将王夫之在《诗译》中的“四情”解释为“兴观群怨”。如毛宣国认为,王夫之将兴观群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兴观群怨即四情,突出的是情感作为诗之本体存在的意义。[1]75-77萧驰认为“在船山看来,‘兴观群怨是诗中‘四情”,且四情在创作与接受之间共同构造了“空灵、朦胧、缭绕、无端无委为样态的审美境界”。[2]148袁愈宗也以此为预设反观《诗广传》中王夫之对“兴观群怨”的论述,并认为“四情”并不单是描述读者阅读感受的概念,而且也是描述写作的概念。[3]113戴鸿森则避开了“四情”,着力解释“随所以而皆可”,认为“可以兴观者即可以群怨,哀乐之外无是非……古之为诗者,原立于博通四达之徒,以一性一情周人情物理之变,而得其妙”[4]7。崔海峰指出古人的“情”往往是指喜怒哀乐等[5]9,但他仍然跟从学界的既定之论。王夫之同时论述“四情”与“兴观群怨”的原文为《姜斋诗话·诗译》中的一段: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 而即为冰鉴。“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是故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谢叠山、虞道园之说诗,井画而根掘之,恶足知此![4]4-5
“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这段论述实际上并没有说明“兴观群怨即四情”。由于主语不明,即何物出于四情之外是被省略了的,这句话的阐释仍然是有疑问的。“兴观群怨即四情”的观点应当是将主语当作了“诗”,由此整句的意思就是:诗发挥了兴观群怨的作用,并且在兴观群怨之中得以自由表达情感。但观察此句之上均是以“兴观群怨”为论述对象。“雅俗得失以此”“必此也”的“此”都指的是“兴观群怨”。因此,“兴观群怨”也完全有可能是该句的主语,“兴观群怨出于四情之外,而生起四情”,显而易见,若从此说,四情必定另有所指。
首先应当寻找是否有其他疑似“兴观群怨即四情”的论述,用于佐证“兴观群怨即四情”的可靠性。但实际上在王夫之的诗学论述中,“兴观群怨”和“四情”并举的情况只出现了一次,即上述引文。既然王夫之十分强调《诗经》的经典作用和兴观群怨的情感价值,那么为什么偏偏在其诗论中只有一处将兴观群怨冠以“四情”之名呢?
为了甄别对该句的阐释并理解兴观群怨在王夫之诗学乃至其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必须梳理王夫之其他著作对于“四情”“情”的描述,深入王夫之探讨“情”时所处的思想语境、时代语境。这就不能局限于王夫之的诗学,而是要在他的整体思想中定位诗学。因此,本文意在揭示王夫之“诗学”中诗歌的“政教”功用维度。此处所说的“政教”,意为“政治与教化”,但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诗教”,同样也指对人心之中的“公共性”潜能的激发,是对人心及其内在的德性的培养。
一、王夫之的“四情”
通過检索《船山遗书》电子书,能够发现“四情”共出现了13次。除去上述《诗译》引段中出现的3次(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再除去《礼记章句》卷四十二中的两处衍文,其余共有8处。笔者据此引用了更为全面的《船山全书》,版本之间的差异和收录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结果,也存在着不同词语指涉相同概念的可能。现将结果陈列如下:
(1)何以明其然也?有中者奇,无中者偶,奇生偶成。聚而奇以生,散皆一也;分而偶以成,一皆散也。故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未发者,四情合一,将盈天下皆一,无非中矣;已发者,各形为理,将盈天下皆道,不见中矣。[6]1064-1065
(2)于恻隐而有其喜,于恻隐而有其怒,于恻隐而有其哀,于恻隐而有其乐,羞恶、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于喜而有其恻隐,于喜而有其羞恶,于喜而有其恭敬,于喜而有其是非,怒、哀、乐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以恻隐而行其喜,以喜而行其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怒、哀、乐之交待以行也。故曰交发其用。[7]262
(3)后两言曰“谓之”者,则以四情之未发与其已发,近取之己而即合乎道之大原,则绎此所谓而随以证之于彼。浑然未发而中在,粲然中节而和在,故不容不急其词,而无所疑待。实则于中而立大本,于和而行达道,致之之功,亦有渐焉,而弗能急也。[8]470
(4)在中则谓之中,见于外则谓之和。在中则谓之善(延平所云),见于外则谓之节。乃此中者,于其未发而早已具彻乎中节之候,而喜、怒、哀、乐无不得之以为庸。非此,则已发者亦无从得节而中之。故中该天下之道以为之本,而要即夫人喜、怒、哀、乐四境未接,四情未见于言动声容者而即在焉。所以《或问》言“不外于吾心”者,以此也。[8]473-474
(5)朱子为贴出“各有攸当”四字,是吃紧语。喜、怒、哀、乐,只是人心,不是人欲。“各有攸当”者,仁、义、礼、知以为之体也。仁、义、礼、知,亦必于喜、怒、哀、乐显之。性中有此仁、义、礼、知以为之本,故遇其攸当,而四情以生。乃其所生者,必各如其量,而终始一致。[8]474-475
(6)惟性生情,情以显性,故人心原以资道心之用。道心之中有人心,非人心之中有道心也。则喜、怒、哀、乐固人心,而其未发者,则虽有四情之根,而实为道心也。[8]475
(7)《中庸》言“未发”,但就四情而言,不该一切。则以圣贤之学,静含动机,而动含静德,终日乾乾而不堕于虚,极深研几而不逐于迹。其不立一藤枯树倒、拆肉析骨之时地,以用其虚空筋斗之功者,正不许异端阑入处。儒者于此,壁立万仞,乃为圣人之徒。故上蔡云“此之谓‘思诚”。思而言诚,是即天之道而性之德已,复何有一未发者以为之本哉![8]859
(8)以在天之气思之:春气温和,只是仁;夏气昌明,只是礼;秋气严肃,只是义;冬气清冽,只是智。木德生生,只是仁;火德光辉,只是礼;金德劲利,只是义;水德渊渟,只是智。及其有变合也,冬变而春,则乍呴然而喜。(凡此四情,皆可以其时风日云物思之。)[8]1070
第一段来自《周易外传》,第二段来自《尚书引义》,随后六段均来自《读四书大全说》,其中四段解释《中庸》,一段解释《论语》,一段解释《孟子》。所有引文中“四情”都指的是“人心”(与道心相对)的“喜怒哀乐”。王夫之在上述八段引文中,从三个角度描述了“四情”:
第一,“四情之未发”是指尚未有“情”时浑然无偏的状态,即“中”。“中”是“四情”的源头且“未发之中”有着内在的“节”(乃此中者,于其未发而早已具彻乎中节之候)。也正因此,才有了“发而中节”的可能。见引文(1)(3)(4)(7)。第二,人心“四情”与道心“四端”之间存在着相互激发的关系,即“互藏其宅”。仁义礼智发源于“四端”之道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必须依赖于人心四情才能体现,即“仁、义、礼、知,亦必于喜、怒、哀、乐显之。性中有此仁、义、礼、知以为之本,故遇其攸当,而四情以生”。见引文(2)(5)(6)(7)。第三,四季之德及相关的自然现象也被纳入“人心—道心”的体系中,因此人能够通过“四情”来理解自然季节的变化。人与季节的对应实际上规划了集体的生活空间、习俗、礼仪,以及“人生”与“节候凋荣”的对应关系,为“人心—道心”构建了丰富的外在对应关系。这一对应体系正是对文化的构造。见引文(8)。
王夫之的思想有其与理学对话的语境。在上述的引文中,无论是对“中”“和”还是对“人心”“道心”的理解,王夫之都并未将“情”限制在阅读感受的范围内。就上述总结的三点来看,第二点可谓第一点的基础,第一点则是第二点的具体呈现,而第三点则属于“情”进一步外化的结果。“情”由此得以具有内在于自身的伦理可能,并逐渐外化、扩充到万事万物之中。
二、“四情”与人心道心论
理学语境下对“人心”“道心”的讨论,首先来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情附属于人心,朱熹从张载之說,认为“心统性情”,且发扬伊川“性即理也”的观点。由此产生了关于性的“二元说”:作为现实的性的气质之性以及作为理本身的义理之性[9]125。前者可被人心所统,后者则是高于心的不变的“理”。因此,“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10]3589。“四端”实际上属于已发之情,只不过更有“性”层面的善的根据。陈来认为,理学通过发挥《中庸》中已发未发的学说,扩充了原先泛指“七情”之“情”,加入了新的与“思虑”相关的内容。[11]245
鉴于《姜斋诗话》和王夫之其他诗学、评点文章大多属于他后期的思想,所以暂且搁置王夫之思想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以他后期的思想立场为准。他认为“道心即性”“人心即情”,二者互藏其宅,互相激发。性必然要依靠情来显现,性不可离情而存。情有善有不善,其“中道”就是“四端”,“四端”为“性”中离情最近的萌发所在。谢晓东认为朱熹和王夫之在“人心”“道心”的关系中,都遵循了“人心通孔”说。[12]55人心居于“道心”和“人欲”之间,具有向善与沉溺两种发展方向。而王夫之将“四端”划为“性”则使得“四端”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进一步强化了“情性”之间的融通可能。这意味着,需要注重情本身的价值,它决定了人的有限性和具体存在,须臾不可离。同时,“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13]137,也强调了即使最偏颇沉溺的“人欲”中也存在着用以修养德性的“理”。而“公”字也说明了,基于一己私欲的“推己及人”以及对集体所欲的实现则分别是这一修养的起点和目标。
在互藏其宅的“人心—道心”结构中,诗歌在对人心“四情”施加影响的同时,也具备了道心所具有的伦理和政教内涵。以此反观《诗译》中的叙述,“情”当然等同于审美之中的一己私情,但它同样具有“中”(未发)和“和”(已发)的潜能。这使得文学的写作与阅读有了一种公共性的“政教”意义。
但是,既往的阐释都未能充分阐发情感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例如宇文所安认为王夫之的诗学观点与伽达默尔相似,后者认同读者的“偏见”(私情),而反对施莱尔马赫对文本及其“原始意图”的理论预设。[14]506而孙筑瑾将王夫之的诗学归结为以“宇宙阴阳二气活动”为背景的“连续而动态的过程”,并且认为王夫之的诗学虽然没有超出现代的“读者—反应”理论,但他领先后者三个世纪,并且从另一种认识论的传统中生发而来。[15]153-154二人都强调了王夫之对阅读感受的重视,虽然他们也指出了王夫之思想背后的经学、宇宙论背景,但最多是将诗学视作一种世界观的延伸,并仍然将之限制在了纯粹的文学领域,而忽略了“情”在“人心—道心”框架之中的丰富内涵。
“故圣人尽心,而君子尽情,心统性情,而性为情节。自非圣人,不求尽于性,且或忧其荡,而况其尽情乎?虽然,君子之以节情者,文焉而已。文不足而后有法。”[16]308此处体现了“文”先于“法”陶冶人心的教化作用。“文”首先是在“周文”的意义上使用的,包括文章之学,也包括典章制度和礼乐。从“政教”的角度来看,“情”是出发点而不是目的。以私情为基础而体验到无偏之“中”,从而把握情感的“节”,达到已发中节之“和”,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圣人尽于性,能够通过道心抵达伦理层面的普遍性,典章制度皆出于此。君子尽情,君子以文节情,通过文呈现情感,激发情感,并且将情感延伸到读者各自的人生情境与社会空间中。通过外在的礼乐、诗歌陶冶自己与他人的性情,君子意识到了“道心”的普遍意义并付诸实践。这能够让君子以外的普通人不只以一己之情为情,同样以他人之情为情,这就抵达了伦理层面的体谅和社会层面的和谐。
若将这些话题延伸到“诗学”之“情”中,能看出王夫之的思想并无意于建构个人情感的“自洽自足”,因此基于个人情感的阅读感受虽然被肯定但并非最终的价值依归。王夫之实际上强调了诗歌的“政教”“以文治情”作用,诗歌将一己私情上升至公共性的情感和道德之中。此所谓“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穷,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16]392。
三、兴观群怨与情
若搁置对“四情”的不同理解,王夫之“兴观群怨”说所具有的整体性可以说是学界所公认的。所谓“随所以而皆可”,就在于《诗经》能够从“兴观群怨”中的任意一项通达四项之整体。但是,“兴观群怨”作为诗的功用,在《诗经》的时代语境中无法与政治、文化、社会的环节分开。同时,王夫之诗论中的“兴观群怨”与“情”的关系也需要作出界定,上述提到的“以文治情”“人心”“道心”与情的关系,都有利于使兴观群怨在其对情感的引导过程中获得更为具体的政教意义。
况“兴观群怨”,非涵泳玩索,岂有可焉者乎!得其扬扢鼓舞之意则“可以兴”,得其推见至隐之深则“可以观”,得其温柔正直之致则“可以群”,得其悱恻缠绵之情则“可以怨”,得其和柔肫笃之极致则“可以事父”,得其恺弟诚挚之至意则“可以事君”。“可以”者,可以此而又可以彼也,不当分贴《诗》篇。[17]261-262
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可以”云者,随所 “以”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又下或一可焉,或无一可者。故许浑允为恶诗,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尔。[4]42
第一段引文就是王夫之对《论语·阳货》中“小子何莫学夫《诗》”句的解释。在此处,王夫之将“可以”阐释为“可以此而又可以彼也”,这与“随所以而皆可”是一致的。“兴观群怨”不仅仅是一个相互贯通的整体,同时也和“事君”“事父”是一个整体。个人的情感在达到“和柔肫笃”“恺弟诚挚”的中和境界时就摆脱了人心中的偏狭,同时又保留了个体内在的诚恳。值得提出的是,这不仅仅是对《诗经》的事实判断,同样是对普遍的诗的价值判断,即真诚地表达人情的诗作应该能够在这四个方面相互贯通。因此,王夫之批判元稹、白居易“言悲则悴以激,言愉则华以慆”[16]392的诗风。王夫之在以“兴观群怨”论诗时,也将割裂四项而将某一项附会到具体诗篇的做法视作“小人一往之喜怒”。这正是第二段引文中王夫之“崇古抑今”的原因。
王孝鱼在《船山学谱》中将王夫之思想中“情”的特质归结为三点:一是情无自质,依赖于外物引起;二是情无恒体,此由无自质推论而得;三是性以节情,而情本身无节情之性质,“合正则正变,合邪则邪”。[18]305情依赖于外物,表现为各种偏颇的“爱恶欲”,并塑造着个体的世界,而且由于情本身无自质、无恒体、无法自我节制,所以这些偏颇的情感无法得以纠正。相对而言,诗歌的优势就在于“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4]5,这也就是说,诗歌能够激发起这些情感(各以其情),并将其导向“群”“观”层面的艺术境界或公共认同。
基于以上的前提,“兴观群怨”属于对情感的激发与文学呈现,是情在诗中之“用”,而非“体”。萧驰认为“兴观群怨”所引发的“扬扢鼓舞之意”“推见至隐之深”等都属于生命体验[2]152,这其实符合王夫之所强调的诗歌功用。但是,萧驰认为生命体验能够摆脱既往的政教观念,将“兴—观”“群—怨”的关系视作“作者—读者”的情感连接,这显然是对人心“四情”与道心“四端”的割裂,而与王夫之本意不符。
在诗歌与情的关系中,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体”(人心“喜怒哀乐”)与“用”(“兴观群怨”)都达成一种整体的状态,而且后者的圆融在诗中承载并体现了前者的圆融。否则,个人的喜怒哀乐陷于偏狭,就会导致“喜而更喜”“哀而更哀”,由此在美学旨趣上失去“温柔敦厚”的境界。如果诗人割裂地沉溺于“用”的一项,同样会反过来导致情感的枯竭,此种舍情逐文的做法同样是王夫之所厌弃的。如果考虑到情感对个人认同、行为、实践等现实层面的影响,“有偏”的情感一旦盛行便会增加现实之中的不稳定因素。王夫之之所以认为君子应当“以文治情”而非“以法治情”[16]307-308,就在于要将时时刻刻塑造人们喜好和行为的情感,导向伦理性和社会性的“公”,而用于约束情感的法实则无助于人心的教化。因此,“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13]137,在这一意义上人情之“美”与世间公共之“善”是并未分离的,所有人欲人情之中最为公共可通约的部分,就是理本身。
“圣人能即其情,肇天下之禮而不荡,天下因圣人之情,成天下之章而不紊。情与文,无畛者也,非君子之故啮合之也。”[16]308此处的“情”有别于上文所提及的所“治”之情。此处是站在“发而中节”的角度对情的反观,圣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情为天下设立伦理礼法,但又不过度。周朝的“文治”显然在更高的性或曰道心的层面消融了私人之情与典章制度之间、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差异,其理想之情正是“圣人之情”。王夫之在追溯并塑造“周文”传统的过程中,实际在其中寄寓了融通诗歌“情感”与“政教”的愿望。杨宁宁对于“贞情”和“淫情”的考察说明了“情”在王夫之诗学中“上升”与“下降”的两条道路[19]65。前者属于“性之情”,不断接近“圣人之情”和共通的人伦,而后者属于“物之情”,沉溺于一己私情。
但人的情感真的能够承担生发伦理的责任吗?王夫之的“气学”本体论能给出一定的回应。由于个体本身是阴阳二气化合而成的产物,“气”在流行化合过程中的可塑性也就为个体的可塑性提供了可能。唯其如此,“导天下之广心”的教化立场才不显独断。换言之,王夫之思想中的本体论是他理解“情”的基础。
张载认为,“天包载万物于内”[20]63,气的流行根本上是“乾坤、阴阳二端”之气的相互作用。王夫之继承张载这一观点,认为阴阳“相感以动而生生不息”,有气之“体”(阴阳)而未成形(具体的感受模式,如人体)。而“人物各成其蕞然之形,性藏不著而感以其畛”,于是有内外之别,有耳目之引取。[21]363人的感受区分了外物与自身,并且感官被外物吸引,人依靠感官的感受确认、把握有限的物,而对感官之外的事物漠然无觉。虽然人有“尽性知天”的潜能,但能做到的人很少。在“尽性知天”的路径上,王夫之有其独特的阐释:
既已为人,则感必因乎其类,目合于色,口合于食,苟非如二氏之愚,欲闭内而灭外,使不得合,则虽圣人不能舍此而生其知觉,但即此而得其理尔。[21]363-364
王夫之显然肯定了人“因乎其类”的“蕞然”之感的必要性,这只有依靠在具体的生命中对“性”的恢复才有可能(“但即此而得其理尔”)。也就是说,对具体事物的感受和情感并不截然与“性”矛盾。虽然沉溺于“蕞然”的感受中与“性”的要求相悖,但却可以通过对“感”的磨炼功夫抵达“性”的普遍要求。换言之,从圣人之情到常人之情之间存在着不断的修养阶次,这一阶次,与王夫之“气学”中“尽性知天”到“因乎其类”之间的连续性是同构的。
由于王夫之的“互藏交发”说将“人心”和“道心”结合为一个互动的整体,所以诗学视野中的“情感”就可以通过诗的启发,在公共性的层面达到对情的节制与安置。由此就既坚持了个体情感的本真,又避免了私情泛滥的可能。诗歌的“兴观群怨”恰恰是二者的中介,是君子在诗中治情的手段,也是诗歌走向圆融之美时所要达到的境界。总体来说,“诗以道情”对王夫之来说是适用的,但绝不是情感的自洽,而是在情感的公共性层面发现善的可能,是内在的真挚(情)与诗歌伦理价值(性)的结合。
四、“出于四情之外”再解读
王夫之说:“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4]4-5当把“四情”与“兴观群怨”区分开后,就可以看出,作为主语的“兴观群怨—诗”对于人心“喜怒哀乐”的调节、引发、塑造作用。“兴观群怨”在人心四情之外,但是却能够激发人心的“喜怒哀乐”,并使之显明;“兴观群怨”能够在四情中自由运作,并且人心之情并不为此感到窒碍。
诗在“出于四情之外”的同时,也将情从现实的“物”中转向了自身。在王夫之诉诸的“周文”传统中,诗本身就是对情感及其秩序的规划。祭祀共同的祖先,在酒宴之际相友相敬,以诗歌表露或喜或怨的真情,都或表露出对他人的体谅,或将个人情感普遍化为对共同体的认同。在王夫之所秉持的“气学”本体论中,人心可以通过修养而尽“性”,基于人类所共有的“蕞然”之感而知“天”。“情无所窒”就体现了人情在诗歌中的普遍化。圣人、君子并不脱离 “情”,而恰恰是在体察情的过程中把握“性”和“理”。
王夫之在“情”方面的理论是从具体的“情”“感”出发的,因此是及物的。王夫之认为 “心”(四情自然在人心之中)和“物”彼此不能独立,此所谓“色声味为性之显物,无非心也;色声味为道之撰心,无非物也”,“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18]349。由此,物就得以在“人心—道心”“情—性”之间获得解释。在王夫之整体的思想中,性和物都可以从“情”之中生发出来,在情更高层次的表达中呈现出来。因此,对情本身的重视和对情的擢升都是必要的。在诗学的意义上,无视“情”的重要性(“舍情逐文”)和沉溺于“情”(滥情)就成了诗歌的两个弊病。“谢叠山、虞道园之说诗,井画而根掘之,恶足知此!”[4]5王夫之批评二人过分追求诗歌技法,忽略情感。元稹、白居易沉溺于私情,“一率天下于褊促”[16]392-393,同样有违王夫之所强调的“中”“和”。萧驰虽然并未发现“四情”与“人心”的联系,但同样肯定了诗歌情感中的伦理价值。这一伦理价值既是内在修养的环节,又能够外化到艺术境界和宇宙观之中。他认为,船山之诗学理想其实是将内圣学的生命情调化为艺术情调,以内圣为尺度反观诗歌艺术审美境界的一种体现。[2]211在“情景关系”中,萧驰认为,王夫之诗学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有机”宇宙观念,即宇宙秩序呈现出人类艺术的形式,承载着人类的价值、善和美。[2]242在诗的“政教”阐释框架之下,这一美学论断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诗在“私情—公情”“人心—道心”之间的连接作用。实际上萧驰所强调的宇宙观和艺术情调,唯有建立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亲近的伦理关系中,才能够被真诚地生发出来。
王夫之对“情景”关系的论述也可在这一框架中获得新义。“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天物其何定哉!当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当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浅人以其褊衷而捷于相取也。”[16]392景本身所具的复杂性与圆融境界,若能以一种“发而中节”的情感观照,便可韵味无穷,王夫之称之为“不穷于情”。从对人心的修养培育层次上讲,这也是将一己私情提升为“圣人之情”的道路。
以景为契机,人得以向外发现某种一己之情无法融贯的例外之物。文学传统所塑造的“情感对应物”体系,往往使诗人因循守旧,反而落入俗套,情感枯竭。换言之,诗人若闭塞于自己的“已发之情”,就会无力突破传统并转化传统,一旦沉溺于文法或某种风格,就会忽视文体对于情启发、引导的根本作用与价值(在这个层面上的任何复古都失去了“情”的根基,都属于囿于文法)。这种作用当然可以服务于教化。所谓可悲可愉之情都是四情之已发,理想的诗情要努力回到“未发之中”,若回不到“未发之中”则先悬置一己之偏,使阅读的主体走出他的“蕞然”舒适区。为了悬置,需要将情与景、当下与传统、私情与公情、兴怨与观群互为参照,从而将诗歌的领域拓展到他人、生活现实、伦理规范之中。对情的解放,在“人情”与“公情”之间,在“人心”与“道心”之间,这本身就是对文的解放。“情与文,无畛者也,非君子之故啮合之也。”同样,君子治情也并不是用文来体现真切的私情,而是通过私情抵达公情,从而节制私情。因此,真切的私情是文的开始,而不是文的目的。
在社会的维度上,情也有不稳定的一面。“下叛而無心,上刑而无纪,流散不止,夫妇道苦,父母无恒,交谤以成乎衰周,情荡而无所辑有如是。故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16]342此处的“情荡”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伦理、道德随之崩解。王夫之认为,“情之不可恃久”也就意味着只有不断地“治情”才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与伦理的延续。而民众认同的情感必须不断地被“文”(道德、礼乐制度和诗歌等)激发出来。通过将情感导向各自的私情之外,由人心转向道心,君子就实现了治情。道心既是对他人的体察与关怀(以他人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同时又接受了共同的文化前提与政治前提。
主观情感在王夫之“人心道心论”中有着公共性的伦理潜能,而在“兴观群怨”的引导机制中,潜能便可转化为现实中对他人的体谅和对文化前提、政治前提的认同。人情本身各有其偏,君子以文治情,并不能指望将所有人提升为君子乃至圣人,而是要让他们能由“偏”望“通”,实践而不必充分实现,从而提升原先的一己之四情,以为政教、民族之用。如果常人如此,那国家在文化、政治上就有根基。周文达到了这一境界,并可为后人所效法。明末清初之际,在政治、文化、文学各个层面的人情之“塞”使王夫之产生了极大的焦虑。这种“塞”若投射到诗学领域,便是“舍情逐文”和“滥情”两种弊病。
结语
综而言之,通过考察王夫之对“四情”一词的应用,可以对王夫之诗学中的“四情”进行全新解释:“四情”即“人心”之中的“喜怒哀樂”。若将理学视作王夫之对话的对象与背景,则可以理解王夫之为何不作交待地在诗论中使用“四情”,因为他将“四情”即“喜怒哀乐”看作普遍接受的思想前提。但以往的阐释都将“四情”等同于“兴观群怨”,这实际混淆了情的“体”与“用”。
王夫之将诗歌建立于“情”之上,但在其讨论理学的语境中,则强调了人情“未发之中”和“发而中节”的两个维度。这使得诗歌的“兴观群怨”成为沟通“人心”与“道心”的桥梁。诗歌在情感诚挚的层面展现美,但并不与“善”相违背。若沉溺文法或放纵私情,则都是对诗歌艺术的破坏。《尚书引义·康诰》有言:“性隐而无从以贞,必绥其情。情之已荡,未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枢,情安之而性乃不迁。故天下之学道者,蔑不以安心为要也。”[7]366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同样对“文”(包括文章但不限于文章)提出了“文以治情”“导天下以广心”的要求。以此为背景来锚定“文学”的位置,文学便先在地超出了审美的领域。文以治情也是文以安情,是由情而达性的“内圣”的修养过程,是对更广阔情感的体谅与伦理承担。
【 参 考 文 献 】
[1]毛宣国.王夫之《诗经》阐释的三个重要诗学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
[2]萧驰.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袁愈宗.王夫之《诗广传》“四情”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4).
[4]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5]崔海峰.兴观群怨说:从孔子到王夫之.船山学刊,2009(4).
[6]周易外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7]尚书引义∥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8]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9]谢晓东,全林强.论东亚儒学中人心道心问题的哲学意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1).
[10]朱熹.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2]谢晓东.互藏交发说的困境及出路:王船山的人心道心思想新探.哲学动态,2019(4).
[13]四书训义∥王夫之.船山全书:第7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14]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5] SUN Cecile Chu-chin. Pearl from the Dragons Mouth: Evocation of Feeling and Scene in Chinese Poetry. 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5.
[16]诗广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17]四书笺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18]王孝鱼.船山学谱.北京:中华书局,2014.
[19]杨宁宁.王夫之诗情论辨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20]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21]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编校:祝美玉)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