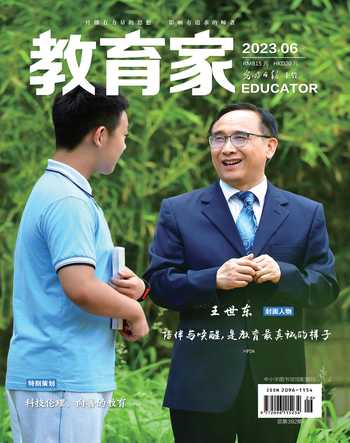融汇文理,应对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合作难题
孔青青 徐飞
为促进我国新兴科技向善发展,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开放合作,建立多方协同合作机制,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运行事关治理能否真正落地实施,虽然建立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多元主体参与科技伦理治理时,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常常难以达成共识,本文将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跨学科合作难题为例,分析科技伦理治理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就跨学科合作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及对策。
跨学科合作是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必要前提
伦理治理需要以跨学科为根基。自20世纪以来,科学研究从“学院科学”转向“后学院科学”和“产业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生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分支学科发展模式,当今的新兴科技大都属于跨学科合作的产物,如合成生物技术、脑机接口等,其知识背景涉及多个学科。面对风云突变的复杂技术风险,仅凭单一学科显然是无法解决的,由于科技伦理教育的相对不足,传统的伦理理论更无法适应新兴技术对伦理的需求,经常出现“科学家不通伦理,伦理学家不知科学”的尴尬局面。因此,科技伦理治理必须以自然科学面临的问题为切口,用人文学科的视野审视科技发展可能存在的问题,文理协同为科技发展提供规避现实风险的治理方案。
科技发展需要以伦理为边界。自17世纪开始,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组织化的社会活动,科学家也不再是自由探索者或科学的“神圣卫道士”,许多科学家希望通过不断产生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来获得地位、声望和权益,以满足功利主义的价值需求。然而,这种需求也可能使科学家们丧失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成为各种权力的附庸或利益代言。过度的利益取向可能会麻痹科学家对技术的风险意识,科技发展也将陷入以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模式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纠缠使得科技伦理治理愈加困难。因此,科技探索只有将伦理规范作为边界条件才可能持久健康向前发展。
科技与伦理具有触发扩散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也如同上述这个具有差序格局的水波圈,自然科学家构成了科技工作者的圈层,人文社科学者构成伦理圈层,圈层之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差序格局体系。差序格局敏感易扰动,具有触发和扩散的效应,触发效应由科技伦理的典型事件引发,比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消息一出便引来全世界的热议,如同石头投入水中泛起涟漪;扩散效应则是触发效应的发酵,此类事件引起不同知识背景圈层的讨论,更引发伦理学与法学圈层的波动。不同圈层的水波只有从自身开始不断延伸,逐渐向外层扩张,消融边界感才能平息波澜。
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跨学科合作困难的成因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地位的严重失衡。首先,自然科学的资源投入远高于人文社科。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科学成果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不断获得政府与实业界的青睐,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5年度发布的《大学和学院研发支出概览》,用于自然科学研发的开支是人文社科研发开支的46倍。其次,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然科学家们同样也拥有更高的地位,具有更多的话语优势。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通常由自然科学的权威代表牵头参与,其拥有的丰富资源不由自主地吸引着其他自然科学团体,使得自然科学学者的话语权愈发增加,这就导致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壁垒越来越高,进一步强化了跨学科组织内可能的“学科沙文主义”,影响了人文学科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积极性。最后,自然科学的学科专业性所形成的强大文化壁垒,使自然科学家似乎具有天然的学科优越感,专业性越高就显得越神圣,而人文社科就泯然众人,伦理、文学、教育学等专业门槛似乎相对较低,常给人一种“无专业深度”的错觉,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之间常常难以平等交流,甚至走向自然科学时常贬低乃至否定人文科学的极端情况,这种学科歧视在跨学科交流中将进一步固化不同学科专家的思维方式,不利于平等理性地推进跨学科交流合作。
自然科学家关于科技伦理的认识误区。自然科学家“科学探索无禁区”的理念深入人心,他们对一切未知抱有巨大的好奇心与探索欲。由于前期教育的不足,部分自然科学家可能存在伦理意识薄弱的情况,“北京地区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意识”调查显示,约33%的科技人员对科研伦理有所了解,仅17.5%的科技人员知道本单位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有人认为科技伦理就是一套“假大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囊括了科技发展的所有方面,像一个套子,将科技发展的活动套在其中,不仅影响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进度,也让伦理治理成了“纸老虎”。例如硅谷的科技专家大多信奉“先发展再治理”的原则,有的甚至直接把科技伦理视为科技创新的绊脚石。
学科范式不規范,联动机制不健全。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缺乏有效的组织模式。尽管有些机构鼓励跨学科研究,少数机构建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但大部分机构还未设计和实施促进跨学科研究的有效组织模式,包括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激励政策,伦理治理共同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现有的伦理委员会大多挂靠在学校内部,导致伦理委员会长期受学校行政权力支配。由于缺乏统一管理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平台,除若干专业机构外,多数单位实际上依然难以有效规范实施常态化的伦理治理工作,因此也阻碍了共同体从承担后果责任向承担预见责任的转变。
提升教育理念促进科技伦理治理跨学科合作的建议
树立学科平等意识,融汇文理协同发展。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艺术、宗教、伦理都是一棵树上的分支,具有共同的价值内涵,在追求真善美上是相通的。自然科学学者应像爱因斯坦一般,以包容开放的姿态迎接人文学科的加入,人文社科学者也应虚心听取自然科学家的意见建议,只有文理交融的跨学科合作才能以多维视角观察问题;在教育方面, 建议科技伦理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伦理学相关知识外,也必须选择若干自然科学作为必修课,加深自己的多学科背景;从更广泛的教育角度看,可以考虑在自然科学的专业课程中增加科技伦理的选修课,从教育的层面实现跨学科的交叉融通。
注重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事实表明,只有专业知识的教育是不够的,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获得对美和道德的辨别力,促使自身的和谐发展。建议在大学教育中注重道德教育,促进专业知识与科技伦理的共同发展,科学工作者只有在符合伦理的前提下创造造福于人类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自身价值。每个人都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不仅要考虑相关技术对自身造成的风险,也要考虑对他人和社会及未来产生的风险,不能为追求自身利益伤害他人利益,应将诚实、信誉、社会责任、合法、相互尊重、尊重主体等科技伦理准则作为行动指南。
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完善跨学科体制机制。从国家层面来说,应重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特别是伦理学跨学科平台的建设,设立垂直管理的规范性行政机构,例如科技伦理治理研究机构、管理委员会等,使其成为专业职能部门,协助原有的科技伦理机构脱离所在单位的权力束缚,从而独立自主地开展伦理评估与治理管理工作,明确相关伦理机构的日常职责和共同体的专属责任等。其次,应加大对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跨学科合作的投资力度,资助文理科开展跨学科交流活动,举办圆桌会议、学科研讨会、专业论坛、共建项目等日常交流合作,搭建文理交流互动的学习平台,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L212403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YD2110002004);中国科大新文科基金项目(FSSF-S-220201)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