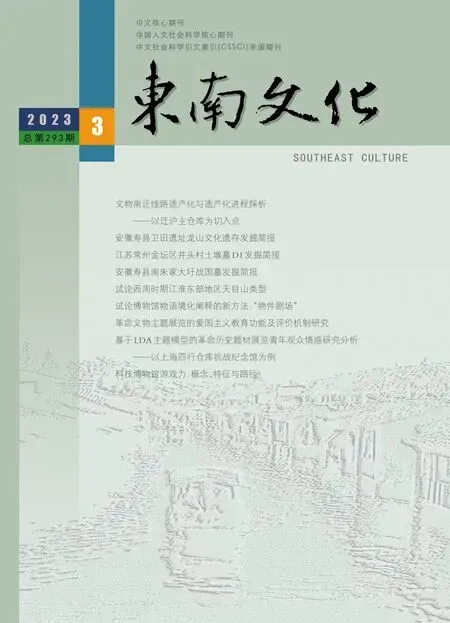文物南迁线路遗产化与遗产化进程探析
——以迁沪主仓库为切入点
夏才艺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1900)
内容提要:“遗产化”是近年来遗产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建筑学、地理学、旅游学等多个学科均对这一现象有所关注,遗产产品模型和遗产化进程模型是该领域中两个典型的研究思路。对于文物南迁线路遗产化的研究显示,遗产定级是遗产化的过程性结果而非开端。文物迁沪主仓库即仁济医院旧址仓库具体位置的考证,在揭示出遗址保存状态和遗址拥有的多层历史文化意义的同时,从实践层面论证了遗产化进程模型中“成为遗产”与“赋为遗产”相统一的理论构架,并对“再遗产化”的表现形式作了补充,对具有多重意义建筑的保护与展示问题作了探讨。
一、“遗产化”与“遗产化进程”模型
“遗产化”关注的是“物”如何转变成为“遗产”的研究,这一概念形成于20 世纪后期,凯文·沃尔什(Kevin Walsh)于1992 年首次提出“空间遗产化”(heritagization of space)概念,用于描述不同历史时期影像的选择性构建下,真实场所转变为旅游空间的过程[1]。之后在格雷戈里·阿什沃斯(Gregory J.Ashworth)“遗产产品生产模型”(Heritage Product Commodification Model)[2]、彼得·霍华德(Peter Howard)“遗产化进程模型”(Heritage Process Model)的补充完善下[3],“遗产化”发展成为关涉遗产认定、遗产保护与利用、遗产商品化与遗产旅游、遗产与身份认同等多角度发展的研究领域。在此领域中,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的遗产权威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讨论[4],以及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突破物与人、自然与社会二元论后对遗产的批判性研究[5],是近年来“遗产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内学界对“遗产化”研究也有相关回应:李春霞在“遗产制造”的观点下讨论了滇越铁路的遗产化问题[6];燕海鸣在界定“本质遗产”与“认知遗产”的基础上,认为“遗产化”是从“本质遗产”到“认知遗产”的过程,其本质是知识话语在遗产领域的介入[7];对“遗产化”持相同认识的吴晨辉、何银春、赵栀等学者,分别以南海《更路簿》[8]和湖南老司城遗址[9]为例研究了遗产化的路径;何文还关注到遗产化过程中的遗产认同问题,用遗产进程模型分析了在老司城遗址遗产化过程中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与内涵;同样从认同角度理解“遗产化”的还有董一平和季国良,董文从遗产价值角度阐发了对工业遗存的遗产化价值的思考[10],季文以“遗产化本质上是一个认同过程”为论点,研究了近代外国人在华建筑的遗产化问题[11];司道光等对国外“遗产化”研究作了研究引介,并希望借助遗产过程理论突破“本质遗产”与“认知遗产”的禁锢,以对国内遗产知识与实践产生启示[12]。此外,也有一些重要译文陆续发表,如沈燕翻译了木村至圣关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工业遗产的遗产化研究,提供了有别于线性的遗产进程模型和遗产产品模型外,基于自治体、社会制度和人群的,横向的、模块化的遗产化研究模型[13];吴秀杰翻译了克里斯托弗·布鲁曼(Christoph Brumann)关于“遗产化”批判性关照的研究,指出个人层面上对文化遗产的依托是尚未得到重视的重要话题[14]。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关于遗产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商品化、遗产与认同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基本涵盖在阿什沃斯的遗产产品生产模型和劳拉简·史密斯的遗产权威话语讨论之中。然而,商品化并不一定是遗产化的组成部分,遗产权威话语也不一定带来遗产认同方面的偏差与矛盾。霍华德的遗产化进程模型从一个更动态、更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角度对遗产化作了解读;司道光认为这一模型的提出意味着遗产化已不再是从“本质遗产”到“认知遗产”的多重利益相关者的抉择过程,而是转变成一个持续进行的文化实践过程[15]。因此,遗产化进程模型不仅增加了遗产化研究的过程化视角,更是对遗产化概念本身的反思与突破,而学界目前对此研究尚少。本文拟以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的遗产化进程为例,结合遗产化进程模型,对这一模型进行细化与补充,并对遗产化的概念进行再反思。
“遗产化进程”(heritage as process)是霍华德在《遗产:管理、阐释、身份》(Heritage:Management,Interpretation,Identity)一书第七章的章节标题,该章中作者按“遗产形成、编制清单、分类定级、保护修复、阐释/商品化、遗产消亡”等过程对遗产化进行了分析解释。之后这一分析方式在司道光及何银春文中被进一步深化为一种遗产化阐释模型[16],何文也据此对老司城遗址的遗产认同作了过程性分析。在该模型中,可作为遗产的“物”被分为三种,霍华德借用“有些人生而伟大、有些人成就伟大、有些人被赋予伟大”的名句,将其对应为“生为遗产、成为遗产、赋为遗产”(born heritage,achieve heritage status,have heritage status thrust upon them)。其中“生为遗产”指的是从设计之初就被保护的物,即艺术品;“成为遗产”指的是因为年代价值以及稀有性而成为遗产的物;“赋为遗产”指的是因与著名人物或事件相关而被定为遗产的物[17]。有意思的是,这一分类中的“成为遗产”和“赋为遗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本质遗产”的概念相对应,而“认知遗产”则大致对应遗产化进程模型中“分类定级”阶段的遗产。在燕文中,“本质遗产”关涉遗产本身的历史和艺术内在价值,“认知遗产”指当代遗产标准话语下“认定”的遗产[18]。目前国内学界普遍使用的“遗产化是从本质遗产到认知遗产的过程”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基于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关于年代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讨论,历史价值之于年代价值,已经经历过一次人为情感选择的价值赋予,历史价值本就不是“物”自身携带的性质;另一方面,当代遗产标准话语下对于遗产的选择判定,也是基于“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评估完成的,也即“认知遗产”和“本质遗产”的界定标准是相同的,那么“从本质遗产到认知遗产的过程”便成为一个悖论。事实上,造成“本质遗产与认知遗产”话语自相矛盾的关键点在于,这一话语未能说明遗产化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也即遗产化进程模型中的第一步“遗产形成”中,遗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二、文物南迁线路遗产的形成与迁沪主仓库遗产化的开端
关于遗产是怎样形成的,曾有学者认为“遗产化”过程始于“申遗”,认为对于遗产的各种“制造”活动是在被列入人类遗产“正册”(指《世界遗产名录》,WorldHeritageList)之后才开始的[19];霍华德在书中也未对遗产的形成过程进行理论性论述,而只是通过举例说明[20]。在其案例中,“物”会因为历时久远、数量稀少而显得珍贵,或因为与重要人物、事情有关,从而被视为遗产。事实上,“历时久远、数量稀少”带来的珍贵感以及与重要人、事相关所暗含的独特性,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遗产的形成并非始于“申遗”活动,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遗产的形成始于价值的判断与认定。以下试以文物南迁线路遗产的形成,特别是其中迁沪主仓库遗产化进程的开端,作详细说明。
抗战时期,为躲避战火,在政府安排下,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子监等处所藏珍贵文物、典籍被打包南迁至上海、南京等地,后随战事扩散又分三路西迁至西南大后方;抗战胜利后,部分文物留置南京,部分文物北返北京,部分文物随国民党迁至台湾。整个文物迁徙的过程,在学界通常称为“文物南迁”。文物南迁过程跨越大半个中国,持续十几年时间,涉及文物近两万箱,是世界范围内开始时间最早、涉及文物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文物迁徙活动,改变了中国珍贵文物的分布格局,并一直影响至今[21]。长期以来,文物南迁一直是两岸故宫院史叙事的一部分,而最先将注意力由文字叙述转移到南迁史迹的,是南迁亲历者。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谭旦冏于20 世纪90 年代初多次回访南京、台中等地文物迁徙、存放相关场所并拍照留念[22];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后人庄灵,同时也是南迁亲历者,也曾于1999 年和2004 年两次探访南迁文物存放地贵州安顺华严洞[23]。如果说南迁亲历者对于南迁史迹的关注与回访是基于个人怀旧情感的价值认定,那么2010 年“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活动则将之上升到了半官方的、群体的价值认定。这次活动的参与者除南迁亲历者及其后人、两岸故宫相关科研人员外,还包括南迁东归后接收古物陈列所文物的今南京博物院相关科研人员、南迁城市当地的史地工作者以及部分记者等,形成了一个小范围内群体性、规模性的文化宣传。在这次重走活动中,依据历史记载去寻找、考证南迁史迹的思路首次出现,南京、贵州安顺、陕西汉中、重庆、成都、四川乐山等地的南迁史迹由此得以明晰,文物南迁史迹作为一个整体概念逐渐明显。如果说南迁亲历者和相关机构对于南迁史迹的关注仍是基于一种“我者”的价值认可,那么2014 年日本广播电视台(NHK)对于台中北沟文物典藏史迹的踏寻和2018 年“国之重宝在上海”文化走读活动的举办,则暗示了“他者”和普通民众对南迁史迹的价值判断。2014 年NHK 的踏寻直接促成北沟文物典藏山洞于当年列为台中市“市定古迹”[24],而2018 年的走读活动也强化了迁沪史迹在普通民众心中的价值判定。
由亲历者到普通民众,由官方机构到国外媒体,几十年来不同人群对于南迁史迹的关注,在重新挖掘南迁历史的同时,也使得南迁史迹不断“增值”。因为作为“赋为遗产”的南迁史迹,其价值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后被不断赋予的,而不同群体长时段的关注及回访、保护行动,无疑促进了南迁史迹成为“赋为遗产”的过程。而本文今日能以标准化的准确定义去讨论文物南迁和南迁史迹,正是故宫文物南迁事件及其史迹自1990 年以来积累的先验价值的证明。量变的积累产生质变,从徐霞客式的“访古”行为到以保护为目的的现代“遗产”话语的转变,是在一次次考察的量变积累中产生的。2010 年“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活动的考察对象仍以“古迹旧址”而非“遗产”的话语出现[25],但此次考察及之后的系列考察、研讨活动,却直接促进了各地对于南迁相关史迹的关注,开启了各地对于南迁相关史迹的价值思考,逐渐促成了安顺华严洞故宫文物南迁存放旧址于2018 年被评定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欧阳道达故居等四处南迁相关旧址于2021 年被评定为“乐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被列入人类遗产“正册”或“副册”“又副册”并非“遗产化”的开始,反而是其进程中某一阶段的结果。
2018 年安顺华严洞故宫文物南迁存放旧址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认定,是南迁史迹中第一个因为文物南迁的历史价值赋予而进入遗产体系的史迹。两年后,《作为“遗产线路”的文物南迁与“遗产线路”概念再认识》一文从理论上将南迁史迹带入了“遗产话语”,进一步确定了自“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以来将文物南迁史迹作为整体看待的观点,并基于现存史迹虽分散于各城市区域、但总体沿南迁线路分布的特点,选择线路类型的遗产作为其发展方式[26]。线路类型的遗产自2005年起以“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之名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Guideline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WorldHeritageConvention)之中,成为遗产领域关注的重点遗产类型,亦是各国“申遗”的热门选择。该类型遗产的特点是不刻意寻找实体的路,而是将传统意义的遗产——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等有形的物质遗存纳入抽象的线路体系之中[27]。对于文物南迁而言,南迁线路的道路本体虽是连接南迁事件的重要载体,但作为文物、人员庇护及中转场所的仓库、办事处、故居、车站码头等具体地点,在从亲历者到外媒的历次回访中,显然占据了更大比重。这样的价值赋予以及南迁线路的线性特征,使得南迁史迹与线路类型的遗产认定要求相契合,决定了南迁史迹作为线路类型遗产的可能性。而进入“遗产话语”的主动选择,在整合南迁史迹、为其保护发展提供支撑的同时,也反向对南迁历史及南迁史迹进行了价值的再编码,使得南迁所涉城市相关史迹的确认在南迁线路整体保护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然而,文物迁沪史迹的相关信息在其中尚是一片洼地。
故宫文物迁沪属于文物南迁的第一阶段,上海即是文物南迁首站,1933 年3 月以来,共有19 557箱文物分五批迁至上海存放,分存于天主堂街26号上海仁济医院旧址仓库和四川路32 号业广公司仓库,其中天主堂街仓库存放了除故宫文献馆箱件外的全部南迁箱件,是迁沪文物的主仓库。迁沪期间,文物经历编目造册、沪上展览、赴英参展等事项,至1936 年12 月底迁至南京,作“沪上寓公”三年有余。
2010 年以来,应当至少有两次实地考察与科研活动注意到迁沪史迹。首先是2010 年“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活动。上海作为文物南迁的首站,且文物在此存放三年间经历清点造册、赴英参展等重大事件,但重走活动没有在上海停留,而将南京作为考察首站。其次是2018 年“国之重宝在上海”走读活动。这次活动以上海为主题,以详实的文献梳理为支撑,将文物迁沪路线进行了复原,但仍没有考证出迁沪相关史迹旧址的具体位置,走读活动也只能在史迹记载中的相关街道上进行想象与怀念。因此,找到迁沪文物仓库和办事处等南迁旧址,对于上海南迁史迹的遗产化、对于南迁遗址整体的遗产化而言,都至关重要,而曾作为上海南迁主仓库使用的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仓库则首先成为被找寻的对象。
南迁相关文献对仁济医院旧址仓库的地理位置和相关特性有明确记载,“其地点位于法租界天主堂街,是一个七层楼的仓库,(为)钢骨水泥建筑,是仁济医院的旧址,与其他房屋不相连接,对于警备消防都很便利”[28]。而《申报》则直接报道了这栋仓库的具体位置是“天主堂街二十六号”[29]。但长期以来仁济医院旧址仓库的位置及留存状况仍未能确定,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天主堂街”是一个俗名,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内,凡是有天主教堂处,均可被称作“天主堂街”,迄今为止,上海仍有三四处街道名为“天主堂街”;其次,所谓“仁济医院旧址仓库”是一个令人迷惑的表达,今山东中路145 号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西院)前身可追溯至1862 年建院于山东路的仁济医院,而山东路附近并没有名为“天主堂街”的街道。因此,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不知文物迁沪主仓库位于何处,也有学者猜测其已毁于战火。事实上,仁济医院曾于1929—1932 年翻新山东路院址,而将医院搬至“爱多亚路天主堂街平治门房屋”[30]。有意思的是,这处房屋实际是仁济医院通过法租界公董局向业广公司租用的[31],与故宫博物院租用的四川路仓库指向了相同的东家。而更重要的是,爱多亚路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信息,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爱多亚路为今日延安东路,而与爱多亚路十字相交的确有一条“天主堂街”,又名“孟斗班路”(Rue Montauban),今为四川南路[32]。在1933年出版的上海地图中(图一)[33]仍可见,仁济医院在天主堂街与爱多亚路相交西侧转角处,由此直接定位到迁沪主仓库的具体位置,应当在今日延安东路与四川南路交界西侧转角处。

图一//《实测上海明细大地图》可见爱多亚路与天主堂街交界处标有“仁济医院”字样(图片来源:同[33])
在实地考察中,现延安东路与四川南路交界西侧转角处确有一栋七层楼建筑,门牌号为四川南路26 号,名为“友谊大厦”,因处于外滩风貌区,已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登录,并在2017 年由黄浦区文化局(今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为“黄浦区文物保护点”。在文物保护点的标牌介绍中可知,此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800 平方米,1928 年由英商建造,1949 年前曾作纺织品仓库使用,1956 年由上海市商业一局接管,为上海纺织品第一批发部,1992 年后由友谊集团使用。该建筑在21 世纪初经历过一次改建,大厦外墙东、北两侧采用了混合幕墙,西、南两侧采用了面砖和水泥粉刷。这段文字介绍中并没有显示出该建筑与仁济医院、与文物南迁有过丝毫联系,然而地点、门牌号和建筑特点上的呼应关系,都将友谊大厦与文物迁沪主仓库相联系,甚至始建于1928 年、1949 年前曾作为纺织品仓库的信息点,也能从历史的尘埃里找到蛛丝马迹:首先,1928 年10 月仁济医院搬迁前,天主堂街26 号建筑曾拆除新建[34];其次,1939 年10 月洋行拍卖印度棉花时,让“各客可先到天主堂街念六号瑞丰堆栈内看明大样”[35],而瑞丰堆栈最迟至1949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出版时仍是四川南路26号的实际使用者,由此可以印证该处作为纺织品仓库使用的历史也是由来已久;最后,2018 年“国之重宝在上海”走读活动时,曾有学者找到迁沪主仓库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旧照(图二)[36],与今日友谊大厦(图三)对比,亦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总之,从时间、地点到建筑特征、曾经用途,多条线索均已有明确指向,现四川南路26 号友谊大厦就是1929—1932 年仁济医院所在地,也是1933—1936年存放故宫迁沪文物的主库房。

图二//1934年《北晨画刊》刊登的库房照片(图片来源:同[36])

图三//友谊大厦现状(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2019年12月)
迁沪文物主仓库已然确认,意料之外的是此处已被列为“黄浦区文物保护点”,不过相关文物工作人员及文保部门显然并不知道这栋建筑曾经的全部历史。从保护点标牌介绍来看,始建于1928 年带来的年代价值和身处外滩风貌区以及由英商建造带来的地理优势与独特性,是该建筑能够成为“文物保护点”的主要原因。按霍华德的遗产分类方式来说,这是一种“成为遗产”。然而,因与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相关,由文献记载让人们了解到其历史价值与情感、社会价值,再去寻找“物”本身,则应当属于“赋为遗产”。“成为遗产”和“赋为遗产”的重合,在霍华德的案例中并未提及,但在此处却真实发生了,并且,作为“成为遗产”的友谊大厦已经完成了“遗产形成、编制清单、分类定级、保护修复”的过程,进入“阐释/商品化”阶段,而作为“赋为遗产”的故宫迁沪文物主仓库,其遗产化进程才刚刚开始。
三、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遗产化进程反思与建议
在阿什沃斯的遗产产品生产模型中,遗产的出现是以遗产消费为导向的,甚至他认为,遗产消费的需求是遗产产生的原因,而非结果。由此,遗产成为一种产品[37]。然而,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的遗产化却并非如此,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其遗产化虽是价值判定与认可的结果,却不是以遗产消费为导向的,也即上文所述,商品化不是遗产化的必然条件,也并非每处遗产都会经历商品化和遗产消费。遗产化的目的应当是遗产保护和知识传播,而并非商品化和遗产消费。在霍华德的遗产化进程模型中,“遗产阐释”和“商品化”是两个并行且可以相互转换的阶段,“商品化”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作为“成为遗产”的友谊大厦也验证了这一点,已经列入“黄浦区文物保护点”的遗产至今仍作为公司办公场所使用,为维护公司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该遗产地甚至不对外开放。如此,此处建筑便和以消费为导向的遗产商品化没有任何关系,但仍然真切地以遗产的身份存在着,并可能一直以这种不对公众开放的状态存在。事实上,众多近现代历史建筑类型的遗产都在以不对公众开放的状态存在着:它们或转变了原来的使用方式,由仓库转变为办公大楼;或延续着原本的使用方式,作为普通百姓的公寓住宅、作为仓库堆栈等,现上海徐汇区亚尔培坊的居民住宅、外滩区域的众多堆栈建筑就是其中案例。这些不对公众开放、但已进入区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系统的“遗产”,在建筑醒目处都标有相关历史信息的介绍,也会有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建筑风貌维护,它们努力传承着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文化风貌,传递着历史、艺术、科学信息,也在人类纵向的代际更迭与横向的人口流动中,与每一群人产生不一样的情感联系,提供归属感或成为持续向前的动力,这或许是更多非世界级、国家级“遗产”的普遍状态,也昭示着遗产化除了遗产消费与商品化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对于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而言,它的遗产化在获得从特殊个体到普通群众的价值判定与认可后,需要通过刻意找寻遗产本体来实现,这一过程看起来像是一种建构,似乎落入了“遗产制造、遗产工业”的窠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过程主义考古学将“物”的存在看作一个过程,即它会经历生产、流通、使用和改造、遗弃、埋藏、后埋藏、发掘、修复、阐释与展示等系列过程[38]。如果将这一概念借用到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上,那么该仓库显然经历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埋藏与发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物库房的天主堂街26号随着1936 年文物迁存南京而被“遗弃”了,与之相关的历史与文化信息也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埋藏”;而作为纺织品仓库、作为办公大楼的四川南路26 号,都是对作为文物库房的天主堂街26 号的“后埋藏”。在此过程中,“物”曾经的使用方式和意义被掩盖,以至于即使该建筑已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进入“修复与阐释”过程,但因为缺少“发掘”环节,这样的修复与阐释对于作为文物库房的天主堂街26 号而言是无意义的,对于作为遗产的四川南路26 号而言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刻意找寻遗产本体的行为并非“遗产制造”,而是“发掘”,以还原完整的遗产过程与意义。事实上,“成为遗产”与“赋为遗产”的割裂,也是因为意义被“埋藏”而导致的。从这一角度而言,重新“发掘”的“赋为遗产”构成了对原本“成为遗产”的“再遗产化”。在珍妮·肖霍姆(Jennie Sjöholm)关于“再遗产化”的相关论述中,“再遗产化”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在城市发展或新的城市规划被制定时,原有“认定遗产”(designed heritage)的价值需要再次重申而自动纳入新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依然具有遗产属性;其二是“认定遗产”的空间、结构发生增减,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或整体被异地重建之后,原有遗产价值发生改变的过程[39]。而此处“赋为遗产”对“成为遗产”的“再遗产化”则显示了“再遗产化”的第三种表现形式:“认定遗产”本体意义的再“发掘”。
“再遗产化”的本质是对“物”价值多元性和多重性的再认知,而这样的情况似乎在古今中外文物遗产化进程中普遍存在。苏智良曾关注到“一栋叠加多重革命史迹之建筑”,提议具有多元价值的史迹遗产的保护需要认真探讨与规划[40]。而马塞洛·奥利维拉(Marcelo G.Oliveira)和伊莎贝尔·露西亚(Isabel Luzia)则讨论了葡萄牙阿尔加维洛莱(Algarve,Loulé)一座17 世纪基督教堂发现的中世纪伊斯兰文化遗存及其处理的问题。文中通过实践及访谈调查,认为考古学可以揭示出文化的重叠和潜在冲突产生的新层次的意义,在宗教场所的遗产化过程中,拥抱而非压制不同的意义层,在更好地认识建筑的同时,可以促进多方对话,有助于维持并丰富社区记忆[41]。该教堂遗产化过程中,文物价值多元性问题的出现是基于实践层面的考古,而文物南迁史迹是基于知识层面的“发掘”,两者具有相似之处,而从基于文物保护与知识传递的遗产化进程方面来说,该教堂拥抱、展示多层次文化的做法也有可供参考之处。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正处于遗产化初始阶段的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未来进一步遗产化进程,提出两点建议和展望。其一,鉴于四川南路26号建筑原本被“埋藏”的、曾作为仁济医院院址与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的历史信息已经被“发掘”,故宫文物迁沪主仓库的遗址位置已然被确认,出于“物”的遗产化是为了知识传播和遗产保护这一目的,那么,在原本四川南路26 号黄浦区文物保护点的文物档案中应当补充完善这一信息,并应当将这一信息补充在文物点标牌的历史介绍中。对于相关科研与文保部门而言,这是一种知识的补充,同时也便于以后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对于公众而言,这是一种知识的传递,同时也促进知识的传播,这不仅是“遗产权威话语”体系下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是公众自下而上对于历史与知识的探寻。因为近十年来文物南迁的遗产化进程是在获得不同群体价值判定与认可的基础上发展的,加之近年来以文物南迁为背景的相关话剧、综艺节目、电视剧等也使更多公众对文物南迁产生兴趣,社交媒体上也有因讨论剧情而探究文物南迁历史本身的帖文,那么该地点文物南迁相关历史信息的添加,无疑是符合公众求知需求的。对于文物本身而言,这是使“成为遗产”与“赋为遗产”重新合体的标识,保证了遗产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其二,文物迁沪主仓库遗产化进程的发展方向应当放在文物南迁遗产整体框架下进行规划。前文已述,自2010 年“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以来,人们已逐渐认识到遍布全国的文物南迁旧址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2020 年《作为“遗产线路”的文物南迁与“遗产线路”概念再认识》一文则是从学理上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巩固。从全国文物南迁遗址整体的遗产化进程上来看,一方面,各地文物南迁旧址的遗产化进程并不均匀,目前除安顺华严洞故宫文物南迁存放旧址、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遗址公园、台中北沟故宫文物典藏山洞等处使用了“南迁”相关术语外,其余旧址或多或少存在“成为遗产”与“赋为遗产”相分离的情况。另一方面,对比遗产化进程较快的这几处文物南迁存放旧址,目前唯有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遗产消费与商品化。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遗址公园尚在建设中;安顺华严洞故宫南迁文物存放旧址因为和宗教场所空间重合,目前其主要用途还是满足宗教生活日常所需;而北沟故宫文物典藏山洞出于各种原因目前多已处于“遗产消亡”阶段,但仍有再保护修复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回到文物迁沪主仓库的遗产化发展方向上,在2022 年7 月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文物保护方针由1982 年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改为“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对文物价值发掘和有效利用的强调成为新时期文物保护关注的内容。对于四川南路26 号来说,其建筑已经因为“成为遗产”的价值判定进入遗产保护体系,那么如何进一步“挖掘价值、有效利用”,关键在于如何挖掘其作为“赋为遗产”的遗产价值,并将两者相结合以发挥更大的效用。四川南路26号作为南迁仓库的历史,既是该建筑成为“赋为遗产”的历史价值所在,也可以将该建筑作为仁济医院与作为普通纺织品仓库的前后历史相沟通,这在丰富建筑多元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四川南路26 号在南迁史迹中的独特性。由此,参考葡萄牙教堂既作为基督教教堂用于礼拜,又开放参观、组织讲解展示伊斯兰文化历史的态度与方法,并结合南迁史迹整体的遗产化现状,避免与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和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遗址公园的商品化遗产发展方向出现同质化发展,四川南路26 号在现办公大楼的基础上,开放部分区域作为建筑历史及文物迁沪历史相关的展示空间,或是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