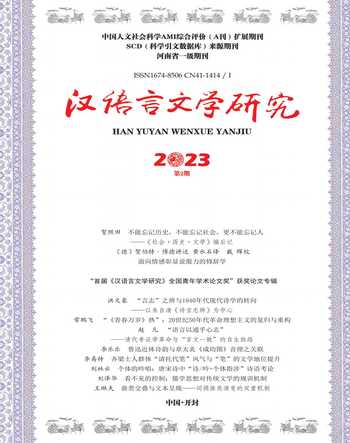看不见的控制:儒学思想对传统文学的规训机制
摘 要:福柯通过“权力—知识”的概念将规训看作一种持久的运行机制,以“知识”控制人的行为,通过规范化裁决、监视和检查的手段,将人规训成某一类人。在传统文学的发展中,儒学形成了独特的“权力—知识”规训机制:儒学通过对“诗言志”命题的掌控,以之为传统文学话语场的信条,将“志”由起初泛指心中所思而趋向狭义,成为儒学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言;“礼以别异”的观念促成的文体等级谱系,充当了规范化裁决的规训手段,将其他文体的发展导向诗学传统;“文如其人”的观念让“文”成为审查作者道德是否合乎儒学思想的“全景敞视”监视机制,而儒学促成的传统道德成为这个规训机制的惩戒方式。在儒学“权力—知识”机制的规训下,文人的创作活动常常笼罩在偏离的焦虑中,这种心态在文学史上扮演着驱动器的角色,推动着文学的发展,或将偏离的文学拉拢回归,或采取尊体的方式使新兴的偏离文体向诗学称臣。
关键词:儒学;规训;诗言志;文如其人;焦虑
“规训”往往让我们联想到惩罚,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压力;人们为了获得某种身份主动去学习相关的知识,获取相应的资格,则是“规训”所蕴含的另一意义。福柯通过“权力—知识”的概念将两方面的意义联系起来,认为不应当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而是应看作一种持久的运行机制,以“知识”控制人的行为,通过规范化裁决、监视和检查的手段,将人规训成某一类人。福柯对于规训的深刻讨论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无处不在的权力,当带着他赋予的眼光去审视我国悠久的文学史时,我们发现作为维护统治秩序的主流思想,儒学逐渐形成“权力—知识”机制,并以之规训着传统社会话语的发展。于是,在传统语境中,对一种文体的批评常常会牵扯功用、审美与道德三个层面的问题,当娱情遣兴的功用与绮丽繁缛的审美占据上风时,儒学价值观便会站出来争夺失落的权力,重整脱离儒家经典笼罩的文学秩序,将与儒学伦理道德渐行渐远的文学重新拉拢回来,以此建立起一种以儒学思想为主导的文学价值观。学界在对于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诸如理学与文学、政治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但对于儒学思想如何规训文学创作却缺乏更为宏观的考察。本文意在揭示传统文学中的“权力—知识”机制,破译隐藏在文学史中处于紧张和运动中的控制网络。
一、 作为信条的“诗言志”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将“诗言志”称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山纲领”,并辨明“言志”总是关乎政教,和主张抒发性灵的“缘情”相对。此观点流布甚广,一度成为不刊之论,但近来多受质疑,如杨明指出“志”与“情”在批评史上其实并非截然二分,“志”本身就多指情的自然抒发,与“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诗言志的命题起初与儒家礼义并无关系,“志”是泛指心中所想,但随着儒家思想对文学的规训,“志”呈现出逐渐向儒学价值观靠拢的趋势,而“诗言志”则成为儒学价值在文学中的代言,作为传统文学话语场的信条,导引其发展。
(一)情志离合
“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要求已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旨。显然这句话不会真的出自上古,一般认为反映了周代乐官思想,至于记载可能是战国或西汉史官。诗言志的观念在《尧典》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诗”的字形为我们考察这一观念提供了更早的依据。《说文解字》:“诗,志也。从言,寺声。”“志,意也。从心,之声。”③段玉裁认为“志”是亦声字,训为“从心之所之”。无论哪种看法,从文字的角度看诗即是内心所想的表达,对所想内容并无具体限制。闻一多释“志”为记忆、记录和怀抱,怀抱泛指人心中各类情绪,可谓不谬。但闻先生将上古歌诗分作两途,认为歌用来抒发感情,诗用来记录,后世逐渐合流。陈伯海在《释“诗言志”》一文中对闻一多此说进行驳斥,因为诗乐舞相伴并生,非但不是由分而合,实则由合而分。可陈先生自此出发,认为正是因为诗乐舞一体,和宗教活动相联系,“演化为礼乐文明制度确立后与政教、人伦规范相关联的志向和怀抱”。笔者认为陈先生的观点卷入到文学起源的问题中去,其说实则是以巫术起源说立论。但文学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或劳动说,或过剩精力说,巫术并非唯一,所以将宗教活动作为诗早期的唯一形态恐怕未为妥当。此外,无论是宗教活动的祝咒还是劳动号子,都只是诗歌的原初形态,诗歌观念还未形成,要讨论“诗言志”的命题还需将“诗”的造字作为最早的可靠依据。据此,笔者认为“诗言志”是把各类情感和事物当作诗歌记录的对象,至于具体的记录内容并无特定的区分。如《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 栩栩然胡蝶也, 自喻适志与!”⑥“自喻适志”指自快得意,“志”表示心中所想。宋玉《神女赋》:“罔兮不乐, 怅尔失志。”“失志”指楚王与神女梦中相会,醒来后若有所失,“志”也是泛指心中所想。再如《周易》:“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礼记·曲礼》:“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其中“志”都是表示心中所想,并无特定要求。
所以,“诗言志”命题本是讲诗用来表达心中所想,并没有朱自清《诗言志辨》中所说的言志与缘情的对立,“志”和“情”也常常混用,如屈原《九章·怀沙》:“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严遵《老子指归》:“奋情舒志,各肆所安。”庄跽《哀时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蔡邕《难夏育请伐鲜卑议》:“情存远略,志辟四方。”曹植《感婚赋》:“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以上材料皆上下句相对,情和志作为近义词互文见义,显然二字的意思是大体接近的。屈原在《九章·惜颂》中也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情”与“志”一样泛指全部思想感情。
在儒家思想的要求下,诗歌肆无忌惮地抒发个人情绪是不被允许的,由文学逐渐被经学收编的《诗经》就体现了这一点。《诗经》中存在着大量描写男女爱情、抒发个人怨怼的诗歌,经过采诗和改编,使得这类诗歌或被删削,或被赋予新的意义。在批评史中被历代文学奉为圭臬的《诗大序》显示着对情和志的区别:“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段所述分别为诗、乐、舞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三者皆本于情,是“情动于中”的产物,且自诗而舞的表达能力呈递进的状态。不难看出,这一段所本即《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尧典》将诗乐舞的表达对象指定为“志”,自此看《诗大序》貌似将“情”和“志”视作同义。但是《诗大序》在开头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③,将“志”与下文的“情”做出了区分。细审文义就可以发现《诗大序》对人之情作出了规定,文中所谓变风、变雅虽然是“吟咏情性”,但是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并进一步解释“发乎情,民之性;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可见《诗大序》所说的“诗言志”中的“志”与“情”不同,并不是人心中所想所感就可称为“志”,只有“止乎礼义”的情才合乎《詩》的要求,才能纳入“言志”的范围内,才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礼记·孔子闲居》中子夏问《诗》,孔子对以“五至”“三无”,所谓“五至”即:“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⑥这里的“志”指“君之恩意”,君王恩意所至,诗歌也就随之而至,礼也随之而来,君王与人民也哀乐相生。孔子在这段话中阐述的“诗言志”,是指诗歌颂君之恩德,同时体现着礼,诗作为连通君民的中介,“志”也不再是泛指心中所思。孟子在阐述“志”的时候,也体现出“志”的规范:“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认为通过志来帅气,使气成为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可见他谈到的“志”也是带有儒学礼教色彩。
《诗经》作为沟通经学与文学的媒介,儒家思想常常通过它来渗透进诗文创作中去。与“情”相近的“志”逐渐向表示政教礼义的“志”靠拢,这在经生们对《诗经》的阐释中就可管窥一二。如今人一般认为《葛覃》是写女子归宁之情,《毛诗》认为:“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一首本是抒写归宁之情的诗,被阐述为赞颂后妃本性,其“志”“贞专节俭”“在于女功之事”,并推及“化天下以妇道”,已经是关乎儒家之礼了。又将描写妻子怀念丈夫的《卷耳》阐述为“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詖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为本身抒发男女思念的“志”强加上政教礼义的外衣。
(二)情志相侵
如上所述,“志”在最初确实与“情”无二,但随着儒学经典地位的确立,逐渐将“志”揽入麾下,实现“志”与“情”的分离,“诗言志”中的“志”逐渐缩小意涵,更多强调诗歌表达带有儒家礼义色彩,这一点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已多有阐发,兹不赘言。以《诗经》为典范的风雅精神也成为贯穿文学史的精神家园,为历代文人不断回溯,“兴、观、群、怨”的诗学功用也扎根在传统诗学精神之中。
但是文学批评史中的“志”也会呈现出与“情”意义相混的情况,“情”有“志”义者如《七略》:“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游酢:“诗者,言此情而已。”王夫之《诗广传》:“夫诗以言情也,胥天下之情于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奚其情哉。”③董思诚《香草溪乐府后序》:“《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有正变之不同,而皆本于和平之旨。诗以言情,情之所不能达者,词足以达之。”“志”泛指心中所想者,如潘岳《悼亡》“赋诗欲言志, 此志难具纪。”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序:“盍各言志,以记芳游。”⑥
朱自清认为情志的混用是“词语一般用例影响的强大”,笔者认为这背后有更深层的意味。儒学对“志”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了划分出与“情”相对的意含,而是以儒学之礼去约束人本身之情,使人之情归于儒学的笼罩下。面向政教、礼义的“志”向“情”的侵占,正表现出儒学思想在文学中的强大力量,要求人所发之意念本身就带有“礼”的色彩,才符合儒学规训下的文学价值要求,即达到礼与情的统一。这样“志”在使用时,即使说者主观上是要说明“心中所思”,并没有自觉去表达有关政教礼义的意识,但是无意地将只拥有描述义的“情”作为具有价值判断义的“志”。
对人之性情作合乎政教礼义的要求,才能符合“诗言志”的文学纲领,如韩愈提出“气盛则言宜”,认为作者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达到“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再如《诗人玉屑》录韩驹《室中语》云:“仆尝论为诗之要。公曰:诗言志,当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淳厚之义自具。”这种以涵养性情来要求文学创作的意识在理学家那里尤为自觉。如游酢在解释《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时,认为“入孝而出弟,行谨而言信,处众而泛爱,交友而亲仁”是君子之本,在此基础上才可以“从事于文”。他将“诗、书、礼、乐”并列,认为是“仁”的显现,诗是“言此情而已”。这里“情”与“志”出现了混用,他要求通过涵养人之情,使之符合儒家仁义的规范,这样人本身自然所思所想,就不自觉地成为符合儒学思想之“志”。张九成《题孙叔谐序王文炳》提出要正心诚意,琢磨修省,才能使“睟然者粲于人伦事物之际,被于文辞动止之间”,即通过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修养,使人未发之心规范于儒学价值,这样所发之性情也就不自觉地符合儒家思想,文就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也就没有不在“志”包蕴范围内的“情”了。
“志”与“情”的混用,是儒学思想对自我意识的规训,这种规训是儒学知识对主体的要求由自为指向自在。所谓“自在”,就是还没有实现、没有生成的未发之潜能;“自为”则是已经生成的、发出之实现。“志”本身泛指人所有意念,包含着未发之本性,既是自在又是自为的,是已发和未发的统一。儒学思想对“志”进一步的规定,在“诗言志”的命题下让广义的“志”走向狭义,由自在走向自为的规定下的一种,而“情”则递补了“志”留下的缺失。儒家话语体系借助权力认同和经典教育的形式,逐渐完成了传统道德价值的构建,这让“诗言志”的“志”重新挤占“情”的领地,儒家思想对于性情的规定不再满足于自为的已发,而是对于意识的整体规训,这样“志”既是面向礼教政治的,又是包含性情的自在自为的整体意识,是宋儒所谓涵养于未发。正因为如此,杜诗被传统诗学奉为历代诗法的典范,杜甫的诗在个人动静止息之间深刻体现着忧世的情怀。这种情怀包蕴着典范的儒家精神,如北宋胡宗愈谈杜诗:“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甫的诗达到了个人的情绪动静与社会时代的统一,“一饭未尝忘君”就表现在杜甫的性情已经完全置于儒家道德价值之中。他的每一次自我情绪的抒发都是“诗言志”的完美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的“诗史”成为诗人们所标举的典范。
在“志”对“情”的要求和侵蚀下,文如其人的观念也应运而生,同时也造就了进一步的规训机制的生成。但是性灵的强调作为对礼教的摆脱一直存在于文學史中,这造成了“志”“情”概念的混乱,也造成了“志”“情”在文学史上的争夺。
二、作为处罚机制的文体等级
规训系统的核心都存在着一个小型的处罚机制,其未必是法律的裁决,而多是以制定规则纪律的形式,作用于道德、活动、空间、时间等等。传统文学活动正是通过以儒学价值观为标准制定出一套文体等级制度,通过文如其人的训导将道德裁决揽入文体等级谱系中。
作为儒学价值观核心的“礼”,在以“节情”训导文学发展的同时,还以“别异”的基本功能完成了文学中等级观念的塑造。对于礼与等级的关系,《荀子·王制》中云: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荀子》认为没有差别会导致社会混乱,为了建立秩序,先王制定礼义来明确高低贵贱,礼通过对名分的确定让人处于等级谱系中,从而使社会获得秩序,按照这样的逻辑,等级的明确成为保障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使等级得到不言自明的正当性,《荀子》将“礼”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有上下亲疏之分也。分莫大于礼,分生于有礼也。礼莫大于圣王。”③孔子对于违背等级的僭越便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论语》中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可见孔子同样以等级观念无可辨别的正当性作为礼的要求。
为了维护等级结构的正当性,儒家不断申述“名分”的重要,孔子以“正名”作为理政之先,认为“名不正”会进一步导致“礼乐不兴”和社会的混乱,荀子也强调“制礼义以分”“辨莫大于分”,对于结构形式的标举就顺理成章注入儒学文化之中,如《论语·八佾》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郑玄注云:“牲生曰饩。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故欲去其羊。”每月告朔的古礼自鲁文公开始便已经不再施行,但是子贡要废除行告朔用的羊却遭到了孔子的反对,由此可以看出“礼”对于“名”的重视。关于儒学对“名”即形式的正当性的重视,我们可以《二十四孝》故事为例证。《二十四孝》故事可以称作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代言,其中的后母形象就表现出对于结构形式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强调。舜、闵子骞、王祥的故事中的后母都承担着一个恶毒的角色:舜的父亲与后母合谋要杀掉舜,闵子骞的后母用芦花替代棉花作为闵子骞的御寒衣物,王祥的继母朱氏对王祥“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可以说在这三个故事中母亲这个角色完全丧失了正常的母子关系,不但没有血缘关系,甚至是扮演了一个施虐者。但三个故事无一例外儿子不仅要顺受虐待,而且还依然要以孝事“母”,直到其态度发生改变。后母的形象意味着即使其完全无法承担“母亲”这个角色,但是只要有了“母亲”的名义,作为孩子则必须承认其正当性。这三则故事是儒家对等级制度所赋予结构正义的宣传手段和绝妙隐喻,其情节今天看来恐怕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其所传达的,正是儒学思想中对于等级制度所赋予的不言自明的正义性和道德感。只要拥有了自上而下的等级差异,处于这个结构中的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才符合儒学所宣扬的价值观。
早期文体谱系的形成与礼制有着密切的关系③。学在王官的时代,不同的职官司职不同的事物,同时也要掌握相应的书写规范,如大宰、小宰对法典类的书写,内史、外史负责王的政令的传达。早期的文也往往承担着在特定场合下的功能,如祭祀神明用祝、诸侯结盟用盟,礼义要求也自然渗透其中,像“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和“生无爵,死无谥”的等级观念也由此成为早期文体谱系所建构的依据。此外,“文”作為“礼之文”,也自然接受着“礼以别异”影响下形成的等级观念。对“名”的重视也植入其中,因此,在礼的影响下,文体谱系形成了以崇正抑变为主导的等级秩序。
《诗经》作为圣人删述的经典,最能体现儒学礼义思想,被确立为谱系中的正宗,但对于《诗经》本身,不仅有着“正风”“正雅”,也存在着怨刺为主的“变风”“变雅”。虽然“正”有着被尊崇的地位,但是“变”也被放置进儒学的秩序中,获得被认可的地位。在谱系秩序中,越接近《诗经》的文体就有着更高的文体地位,如同样是诗,但因《诗经》以四言为主,所以四言诗就获得了雅正的地位,挚虞《文章流别论》云:“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⑥《文心雕龙》亦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早出的文体获得了儒学价值的经典化认证,则后出的文体便只能屈居于“变”的位置,伴随着儒家以古为贵的观念,文体谱系便呈现出代降的趋势。如郎瑛《七修类稿》谓:“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王世贞在《曲藻》中描述这种退化的文体价值谱系云:“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这个等级森严的文体谱系并非完全僵化不动的,代表风雅传统的《诗经》牢牢占据雅正的地位,因为与《诗经》的关系最为密切,诗体也因此获得了韵文中无法撼动的位置,而其他后起的文体也通过对《诗经》的攀附来获取谱系中的合法性,这体现在对“变”的认可上。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云:“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则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志亦可也。”奇,就是变,虽然是变,但是自正而来。因此,“变”虽然不如“正”,但其合法性也可以得到承认。这样的逻辑普遍为文学史的发展所接受,因为任何一个发展的事物不可能拒绝新变的产生,新产生的文体在等级谱系中的合法地位,便依靠向“正”即以《诗经》为代表的诗学传统而来。如刘勰对《离骚》地位的确认,便将之等同于自《风》《雅》以后的变体。班固在推尊赋时,也将之认定为“古诗之流”③;苏轼在推尊词体时,认为词是“诗之裔”;黄庭坚效仿东坡,称词为“诗之流”,都是这一理论逻辑的体现。
在儒学思想对等级形式的强调下,文体的等级秩序有着无可争议的正义性。传统士人在“文如其人”观念的影响下,从事低级的文体创作就意味着道德有所亏损,如黄庭坚因为作词而被法秀和尚斥责当下犁舌狱。面对着这样巍峨的谱系,文人很难去从事后起的不符合等级规定的文体创作。于是,当文人士大夫参与到一个新出现的文体创作中后,他们内心的不安情绪,让其所书写的新生文体不得不被迅速地放置在文体谱系中,参与到雅化的过程中去,以此获得“变体”的定位,并在雅化的过程中不断向风雅传统挺进,使得书写者免受等级的谴责。这样,在森严且不容置疑的等级秩序中,伴随着文人作为书写者的焦虑,文学获得了儒学思想的规训。
三、作为监视机制的“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在规训机制中不仅仅是将道德与文章联系起来而使文体等级的规范化裁决成为可能,更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监视手段存在于规训机制当中。
“文如其人”作为批评史上的重要命题,其形成可追溯至孔子所谓的“有德者必有言”⑥,将道德与言语相关联。《周易》所载:“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也同样将言辞与人品对应,使得“文如其人”的内涵更为丰富。扬雄《法言》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王充《论衡》云:“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而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文”作为人真实情感的流露,作者的道德品性可以直接反映出来,通过“文”可以探明作者是君子还是小人,文与道德的一致性成为“文如其人”命题的主要内涵。
魏晋时期,随着品评人物风气的流行,“文如其人”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曹丕谓“文以气为主”,而“气”体现在作者的性情、气质不同。宋代姜夔云:“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宋濂对“文如其人”的阐说亦着眼于此:“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躁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这样“文如其人”的命题其实有着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强调道德与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将作者的性情、气质视为文之风格的关键因素。
批评史上对“文如其人”持怀疑态度的亦不乏其人,如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指出了文与人之间的错位。元好问就感慨潘岳为人与为文的差异:“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③若将“文如其人”的命题限定为道德,在逻辑上确实难以成立,蒋寅曾撰文从多方面给予驳斥,并认为“如其人”应该理解为文章风格与人的气质和性格相似,这才是更符合逻辑的命题。蒋先生的观点在逻辑上当然更为严谨,但他也注意到在文学批评史中将“文如其人”作道德解恐怕是大多数,只是从逻辑上对这一现象给予否定,恐怕忽视了这一命题背后的文化问题。
在对“文如其人”的讨论中,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不仅仅是实然的描述,还包含着应然要求。如《文心雕龙·情采》云: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⑥
刘勰将人与文的关系分为“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种,“为情造文”强调文是因情而生,人与文有着一致性;而“为文造情”则是重视文辞的雕琢,忽视了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刘勰肯定了“为情造文”的价值,其实就是认为“文如其人”是作者创作时应当因循的原则,这才合乎诗言志的传统。朱熹对“文如其人”有着类似的表述:“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朱熹将文如其人的道德判断落实在“诗言志”的命题上,以“志”之高下作为“德”之高下的衡量标准,可以说揭示了“文如其人”命题的本质,即是“诗言志”的要求。
对“文如其人”命题的解释,包含了“志”与“情”之间的对抗。《修竹庐问答》中徐熊飞解释“文不如其人”的原因时说:
盖诗者,性情所寄托,非心术所见端也。性情同而心术异,故贤者不必皆工,工者不必皆贤。
徐熊飞所谓诗寄托的“性情”无关乎道德,是泛指作者心中所思所感,而关乎道德的“心术”与之并不具有一致性。可见当文学不再拘束于“文如其人”时,也就丧失了诗学传统中对“性情”的规范。在儒学思想的规训下,“文如其人”是一个应然命题,所以即使不断遭受质疑,但在“诗言志”的召唤下,道德判断依然成为主流。“文如其人”也是对“文—人”之间阻隔的打通,而对“情”的要求是对“人—道”关系的打通,二者共同搭建起“文—人—道”的文学结构,是否合乎儒学的“道”,就成为文学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
在“文如其人”观念的影响下,作品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的依据。如白居易谓:“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方东树谓:“有德者必有言,诗虽吟咏短章,足当著书,可以觇人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陆游甚至认为作者的道德品行在作品中显露无遗,甚至难以遮掩:“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这导致在评价作品时,文辞是否妥当退居为次要标准,而作者的道德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如朱熹在《向薌林文集后序》中鄙薄王维等人的道德节操,进而否定其作品的价值:“王维、储光秀之诗非不修然清远也,然一失身于新莽禄山之朝,则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姿耳!”“因人废言”的批评也成为常态,如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安可将‘不以人废言为借口。”③
在“文如其人”观念的影响下,作品与作者的道德被紧紧绑定在一起,伴随着版刻印刷的发展,作品被传播的范围早已脱离了作者的掌控,这时作品便成了他人对作者道德窥探的媒介,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全景敞视”的监控机制。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是福柯《规训与惩罚》在描述规训机制时所选择的著名意象:它是一种环形结构的监狱,囚室被制作成单间,围绕着中心的监视塔环形展开,同时监视塔利用逆光的效果,可以随时看到每一个囚室的情形,但是处在囚室内的囚犯却无法看到监视塔里是否有人在施行监视。这种全景敞视的监视是持续的、自动的,被监视人完全不能得知什么时候正在被审视,于是只能无时无刻不处在被监视的状态。这种机制还是去个性化的,它不依赖于某个人,而是仅仅依赖监视结构本身。“文如其人”恰恰构成了儒学规训机制中的监视机制,作者一旦开始参与书写活动,就陷入到被监视的状态中,阅读者可以通过作品去审查他的道德,而他却不能得知自己的作品被哪些人看到,在这种“全景敞视”的监视中,作者的创作活动始终带着焦虑,不断接受儒学“权力—知识”的规训。
四、偏离的焦虑
在儒学的规训下,一方面赋予了符合儒学要求的文学以崇高的地位,“立言”以不朽的观念让文人把文学创作视作理想追求,如杨万里在《龙湖遗稿序》中所言:“读其集见其人,了了在目中也。而其人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岂真亡也夫?”另一方面,文学有着自身偏离儒学思想的潜在势能,不符合儒学要求的文学被视为“小道”“末技”。范泰恒《濑园全集序》:“文章小技也,以为德充之符,又大业也。惟卓然自立者为能不朽,而不朽又或兼在文章。”⑥文章本身是小技,只有其在儒学价值范围内体现道德时,它才具备了“不朽”的职能。于是,当作品偏离儒学价值时,创作者便常常陷入偏离的焦虑中。
如前文所述,在文学史上,偏离儒学思想规训的文学不需太久就会被变革的力量重新拉入“正轨”,但即使在“正轨”文学占主流的时代,也常常有文学走上偏离,这时作者就常会被焦虑的心态所支配。从事“偏离”的文学创作的作者,常常选择抹除自己的作品,阻隔传播途径,来抵御偏离的焦虑。如五代北宋时,词往往被视作不入流的“小道”,虽然作者甚众,但多“随亦自扫其迹”。《北梦琐言》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焚稿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新兴文体的创作活动中,即使是偏离正轨的诗歌,作者也会选择以焚稿的方式来掩盖他们认为的道德上的瑕疵,如赵维寰《雪庐客问》云:
亟舆归雪庐以待尽。久之不死,起视案头平日墨卿之所染,颖生之所记,堆堵樊乱,丛于汗牛。谛视之,大半皆感时激衷,牢骚怨憨之语,业敕童子持付祖龙。
赵维寰在晚年审视自己生平创作时,认为自己所作诗文“大半皆感时激衷,牢骚怨憨之语”,不符合儒学的道德规范,于是命童子付之一炬。一些作者为了阻斷传播,也采用隐去真实姓名的方式,这在小说中较为多见。
有的作者在偏离正轨后,选择改弦易辙,与曾经的自己划清界限,以显示对儒家思想的回归。如扬雄“少而好赋”,然而晚年他对少年时这段经历却嗤之以鼻,认为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小技。《汉书》记载扬雄这一态度的转变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③扬雄认为的“贤人君子诗赋之正”,是符合诗学传统中“赋比兴”之赋,正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在偏离的焦虑影响下,作者对于所钟情的文体或采取尊体的策略,使其置身于文体谱系中,获得亲近风雅传统的身份。如扬雄鄙薄的骚赋,在尊体运动中被追溯为诗的变体。被视为有碍道德的小词,也在苏轼等人的推尊下被认为是“诗之裔”,在清代更是承担了“存经存史”的重要功能。对于偏离的焦虑还体现在对文人身份的自嘲和蔑视中,过于重视文辞雕琢就成为孔子口中“巧言令色”之人,辞人、曲子相公等称呼都包含着对作者身份的蔑视。
五、结语
综上所论,福柯通过“权力—知识”的概念将规训看作一种持久的运行机制,以“知识”控制人的行为,通过规范化裁决、监视和检查的手段,将人规训成某一类人。在传统社会,通过对经典的确立和科举制度的施行,儒学思想成为文人必须学习的知识体系,而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渗透进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文学的发展中,儒学形成了独特的“权力—知识”规训机制:在儒学的影响下,“诗言志”命题中的“志”由起初泛指心中所思而趋向狭义,成为儒学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言;在儒学规训下形成文体等级谱系,利用人的心理欲望,将文体发展导向诗学传统;“文如其人”的观念让“文”成为审查作者道德是否合乎儒学思想的“全景敞视”监视机制,而儒学促成的传统道德成为这个规训机制的惩戒方式。在儒学“权力—知识”机制的规训下,文人的创作活动常常笼罩在偏离的焦虑中。这种心态在文学史上扮演着驱动器的角色,推动着文学的发展,或将偏离的文学拉回“正轨”,或采取尊体的方式使新兴的偏离文体向诗学称臣,总之,只有不断向儒家价值观靠拢,才能驱散焦虑的阴霾。
作者简介:刘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