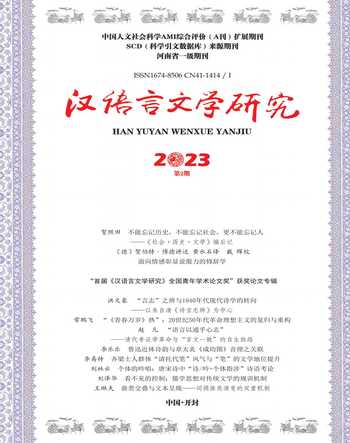“受戒者的文学”说的希腊渊源补证
摘 要:周作人《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时出现了一处错版问题,且因有所谓作者“自注”,所以被误信不疑,这一问题又容易引起关于其中《会饮》篇内容出处的误解。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可以避免错讹的流播,亦有助于说明“受戒者的文学”说源流考释的相关论证。此外,关于“周作人熟悉本杰明·乔伊特的《会饮》英译本”的情况可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全集》;错版;《妇人美的宗教》;“受戒者的文学”;《会饮》
一
《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乃学界所熟知的周作人文章,第一、二节与第三节先后发表在1921年4月5日第7卷第4号、10月1日第7卷第10号《妇女杂志》上,亦被收入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此文中,周作人为了解释“柏拉图的爱”谈到《会饮》篇,即其所称“宴飨(Symposion)”,并引用了苏格拉底口中第俄提玛(Diotima)谈“爱情秘教”(the mysteries of love)的五阶段之论(亦被概括为“审美教育”,依据不同划分标准,有不同的阶段说)——
进行的次序,或被引而历经所爱事物的次序,是以世上诸美为梯阶,循之上行,以求他美:自一至二,自二以至一切的美形,自美形至美行,自美行至美念,自美念以上,乃能至绝对美的概念,知何为美的精华。……这是人所应为的最高的生活。从事于绝对美的冥想。③
而这段引文下面还有另一段引文——
爱是最上的力,是宇宙的,道德的,宗教的。爱有两种,天上的与世间的:世间的爱希求感觉的美,天上的爱希求感觉以上的美。因为感觉的美正是超感觉或精神的美的影子。所以我们如追随影子,最后可以达到影后的实体,在忘我境界中得到神美的本身。
只是这两段引文在初刊本中和全集本中的排版有点差异。在横排印刷的全集本中,这两段引文紧相接连,整体退后两格作为引文标识,并以区别于正文的仿宋字体显示,在第二段引文末尾右顶格还加括号特别标注了出处“《妇人美的宗教》七”。由此,不少读者很自然地就会将这两段引文一并认作《妇人美的宗教》一书中的内容。而在竖排印刷的《妇女杂志》初刊本中,第一段引文以退下两格的形式标示引文,无引号,字体与正文一致;第二段引文则以顶格的形式作为正文内容出现,加了竖排繁体所使用的双引号,在双引号之后插入两竖行小字“妇人美的宗教七”作为出处说明,后仍接续正文。这样,读者也很自然地会将两段引文分开理解,不会将两段引文内容都归于《妇人美的宗教》。
因第一段引文前面有提示,“……柏拉图在宴飨(Symposion)篇中记梭格拉第述女祭司神荣(Diotima)之言云”,其实在形式上也可以说是表明全集本中的两段引文都出自《宴飨》篇,与后面《妇人美的宗教》之出处说明无疑就有了矛盾,全集本的问题正由此呈现,所以两段引文都需要核实出处。核对初刊本,则排版的错误显然发生在全集本。笔者亦曾核对弗勒丘(Jefferson Butler Fletcher,1865-1946)《妇人美的宗教》一书的英文版(The Religion of Beauty in Woma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1),第二段引文正出于此书第“七”页,乃对《会饮》篇的阐说,该页出现了英文名Symposium,但并无周氏文章第一段引文,全书亦无。该书实际上多次谈到柏拉图的“the ladder of love”,只是并未引用《会饮》篇相关原文。
由此,第一段引文(亦可能是关于《会饮》篇的首次中译)并非转引自弗勒丘的《妇人美之宗教》,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这段引文很容易被误认为转引自弗勒丘此书,且因有所谓周作人的“自注”而较难引起警惕或怀疑。但这一判断实际上是由《周作人散文全集》的错版引起的误读。2018年9月笔者曾在“周氏兄弟与文学革命”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举办)的发言中谈过此错版问题。而2021年出版的修订版《周作人散文全集》并未修正2009年版中的这一错版问题,这一问题虽然看起来很小,但关涉较大,所以,有必要指出问题的存在,以免错讹的流播和误读的继续发生,笔者亦顺带补充说明与此错版问题相关的周作人“受戒者的文学”说的考释问题。
二
拙文《源流与意义:“受戒者的文学”说考释》③曾引用周作人《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中的《会饮》篇译文,并进一步分析周作人“受戒者的文学”说与柏拉图《会饮》篇中“爱情秘教”阶段升进说的关联。王媛、余斌《“希腊之馀光”——论周作人“受戒者的文学”概念之产生与发展》一文在拙文对“受戒者的文学”说进行希腊宗教与哲学思想溯源的基础上,更多地将此说与普罗提诺神秘主义、德墨忒尔秘仪相联结,并指出周作人由“受戒者”升华为“爱智者”的过程,由此提出了新见。然而王文断定拙文将“受戒者的文学”说与柏拉图《会饮》篇中“爱情秘教”具体关联的证据与分析不足,并在注释②(第118页)中指称拙文有“五个主要例证”存在问题,则比较随意。笔者在此逐一做出回应,其中第五例证涉及上文所谈《周作人散文全集》的错版引起的误读问题,王文对所谓周作人“自注”即深信不疑,以至于对拙文的分析进行了错误的评判。
整体来说,王文从拙文中摘出的所谓五个例证并非拙文的“主要例证”,而是后面文章进行具体分析的一点背景性说明,远非拙文最后结论的足证。王文称这五例将周作人“与柏拉图完全联系在一起则存在问题”,然而这是误解,拙文并非以此说明周作人与柏拉图的完全联系,这些材料反而正如王文对拙文的肯定部分所言——“(虽然能)指向周作人与古希腊神秘主义的关系”,这一“指向”正是这几个“例证”的实际意义,即可以证明周作人对古希腊神秘主义的了解,且周作人认为柏拉图也具有秘教思想。
第一例,王文称“只能证明周作人对古希腊神秘主义确有了解”,这恰恰是拙文原本所说明的——“这即显示出周作人对古希腊秘教传统的了解”。第二例,王文称“该例中英文引用出现错误”,然而拙文此处并未出现英文句子,“the initiate”是唯一出现的英文词语,此乃斯柏勤原作中所用,这一用法的确与周作人所用的“the Initiated”不同,但应依尊原作(王文在引述斯柏勤这一用语的时候写成了“the Initiated”,反而不妥)。王文又称“作者有意忽略了斯柏勤的观点,即柏拉图只是欧洲神秘主义的一个可能的源头,真正的奠定者是普罗提诺(斯柏勤在导言中仅用半页提到柏拉图,而用四页半写普罗提诺)”,然拙文并非“有意忽略”,关于斯柏勤《英文学上的神秘主义》一书,拙文已说明斯柏勤导论部分分析了“神秘主义”的希腊语源,介绍了早期的“神秘主义”作家柏拉图和普罗提诺,并对英国历史上的神秘主义思想作了概述。普罗提诺对欧洲神秘主义思想的作用当然很重要,但如拙文所言,在对柏拉图神秘主义思想的介绍中,斯柏勤指出《会饮》篇与《斐德若》篇的“神秘主义”最为突出,并引述了《会饮》篇中第俄提玛关于“爱情秘教”五阶段的内容,这足以说明她对柏拉图秘教思想的认同,与王文所称的普罗提诺对欧洲神秘主义思想的奠基作用并无矛盾,而笔者也无必要再另去介绍这一作用,拙文此处的结论仅是“周作人熟悉且认同此书,那么其中所谈‘神秘主义对他应该有一定影响,而周作人对柏拉图的‘秘教思想的確是有所认识的”,这一点与周作人在其文中对《会饮》篇“爱情秘教”五阶段内容的引用应存在一定的关联。但王文指出笔者将斯柏勤书中提到的《斐德若》篇误写成了《斐多》篇,这的确是本人笔误,拙文另一处所写即是正确的。
第三例,王文称“该例恰恰证明未必直接来自柏拉图”,然而拙文原指出的只是,因周作人的注释中提到品达洛斯与柏拉图对于俄耳甫斯教的教旨都很感兴趣,所以,“可见周作人对古希腊秘教传统以及柏拉图秘教思想的了解”,并非王文所称周作人理解的“神秘主义”思想“直接来自柏拉图”。第四例,王文指出笔者将“亚铺刘斯”误标作奥维德,此处的确是拙文不该出现的错误,是笔者的疏失,然而这一点并未影响笔者的主要判断,即“周作人说罗马‘亚铺刘斯的《变形记》‘一面是柏拉图神秘思想的末流,一面已有基督教思想的空气,亦可见出他对柏拉图‘秘教思想(‘神秘思想)的熟悉”,却仍然成立。因笔者此处论述重点是周作人又一次谈到“柏拉图神秘思想”,王文的指摘无疑是避重就轻,并未概说笔者论述的重点。
第五例,王文称“作者推测成分较重,其判断周作人熟悉本杰明·乔伊特的《会饮》篇英译本并不可信:周作人对《会饮》篇的首次中译,其自注是转引自弗勒丘的《妇人美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Beauty in Women)。而李文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例关涉拙文后面的具体分析论证最大,也正是本文第一节所讨论的由《周作人散文全集》的错版引起的误读问题。核查周氏文章的初刊本,并核实弗勒丘原英文著作,即知王文所谓周作人“自注”其实是由全集中的错版引起的误读,而拙文引用的乃初刊本,并无这一问题,所以文章当时并未对全集本存在的问题另作说明。此外,王媛所著《“希腊之余光”: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绪论》第7页注释②的内容与其2018年的论文《“希腊之余光”》中的注释②内容一致,其论文和著作正文中亦都称此段《会饮》篇译文来自弗勒丘《妇人美之宗教》一书,可见错版引起的“误读”之深,而她对拙文的“误解”“误判”也仍然存在,在《绪论》中仍以她列举的这“五个主要例证”判断拙文“存在较明显的问题及例证错误”。且王文及王著不同时间先后两个注释中《妇人美之宗教》的英文题目都寫成了The Religion of Beauty in Women,不知这一标注的英文标题是否出自她的自译,但在弗勒丘原英文著作中无论是书名还是第一章同名标题中出现的都并非“Women”,而是“Woman”,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王文注释③(第122页)指称拙文关于“钱周二人所言‘受戒的内容不同”所用的判断标准并不令人信服,且称“作为彼此的知交,他们肯定就所使用的关键概念进行过深入讨论,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大;且内容引用出现在周作人自己的文章中,用为佐证也更合理”。然而拙文并无提出任何标准来下判断,仅是对二人陈述的观点进行具体比较,之后得出结论。拙文原表述为:“对比来看,周作人所谓‘受戒者的文学乃就读者而言的,是适合‘受戒者阅读的文学,强调受众的特点;钱玄同所言‘受戒的文学‘受戒的书物,乃就作品来说的,是令人‘受戒的文学,侧重这类文学的内容,而且钱氏以之指斥两千年来主要的中国文学。‘受戒者的文学是称赞,因为此类作品可以给予‘受戒者稀有的力,而钱氏之‘受戒的文学则是否定和批判,因其具有‘妖怪化、超人化的内容。以此可知,钱周二人所言‘受戒的内容甚是不同。”反而是王文就“知交”关系来断定“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显得有些主观了。例如,周作人与钱玄同在重要的“名教”问题上,一个曾言“得罪名教”,一个则言“未尝敢得罪名教”,正反映出他们在同一问题上的相反态度与思想分歧,所以,知交私谊显然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上的思想共识。而且拙文还指出,虽然钱周二人所言“受戒”的内容不同,“而有意思的则是,周作人认为‘少年‘儿童‘蒙昧者不是‘受戒者,不适合阅读《沉沦》这一类‘受戒者的文学,钱玄同则认为‘青年不适合‘受戒的文学,道理却与周作人相似”。这一分析比王文注释中笼统所称“以‘净化论观,二人所言实属一事”,显然更进一步,但王文并未注意到或理解到拙文所分析的这种复杂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受戒者(the Initiated)”在词语基本意义上好像与周作人所推崇的哈里孙(Jane Ellen Harrison)著作中的古希腊宗教秘仪及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有某种关联,但理解周作人这一观念不能脱离周氏表达的核心内涵,即“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而理解“受戒者的文学”说则不能剥离周氏当时十分关注的文学“道德”问题,更不能除去他以此说为郁达夫正受到社会激烈批判的反映青年爱欲问题的小说《沉沦》进行辩护这一背景。且“‘受戒者的文学一说因为对《沉沦》进行了受众范围的划定,及‘艺术性质的评定,从而根本上否定了对之施以道德评判和干预的正当性”③,实际上周作人的文章也的确有效地帮助郁达夫抵挡了一些舆论攻势。正是以此为基础,笔者进而发现了周作人的“受戒者”观念与《会饮》篇中“爱情秘教”的关联,及周氏对柏拉图思想的“创造性误读”。而王文、王著显然对这些内容并未加以重视,且对拙文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出语亦稍嫌随意。但感谢她指出拙文的一处笔误与一处错识,使笔者以后可以继续完善此文。
三
关于周作人对柏拉图的熟悉情况,拙文《源流与意义:“受戒者的文学”说考释》发表时限于篇幅,删去了部分内容,这里笔者稍作补充,并对“周作人熟悉本杰明·乔伊特的《会饮》英译本”的情况也再作说明。
拙文判断周作人关于《会饮》篇的节译所依据的是Jowett所译英文版《柏拉图对话》的第3版,并做了对照,而笔者后来有一新的发现。周作人的翻译跟Jowett英译本《柏拉图对话》第3版中的《会饮》篇已经很贴近了,笔者在原来的论文中说,除了有一处语序的调整,其他没有任何跳脱,笔者作了分析,也举例说明了其他译本和Jowett的译本差别很大。但笔者之后发现,周作人的翻译应该根据的是Jowett英译本《柏拉图对话》的第2版,这两版之间有一些差别,差别主要在这句话——
…is to use the beauties of earth as steps along which he mounts upwards for the sake of that other beauty…(Jowett译本第2版)
…is to begin from the beauties of earth and mount upwards for the sake of that other beauty, using these as steps only…(Jowett译本第3版)
……是以世上诸美为梯阶,循之上行,以求他美……(周作人译文)③
对照第2版,则周作人的翻译完全吻合,连语序调整都没有。另外,斯柏勤《英文学上的神秘主义》(Caroline F. E. Spurgeon,Mysticism in English Literature)一书中有一段《会饮》篇的引文,所依据的也是乔伊特英译本柏拉图对话的第2版,周作人当时对斯柏勤此书十分熟悉,所以,亦有可能他是以斯柏勤的引文作为依据来翻译这段内容的。然而,周作人不大可能不熟悉《会饮》篇就单引其中一个语段,而且数次提及。他最初学习希腊语就读了柏拉图的对话,就柏拉图《会饮》篇来说,周作人应该阅读了希臘语原文、英译本,也读过日文译本,这里可能有一个复杂的接受来源。比如,拙文《源流与意义:“受戒者的文学”说考释》在注释中提到周作人可能读过一个日译本,即生田春月译《饗宴》(东京越山堂1919年出版,主要依据乔伊特的英译本《柏拉图对话集》)。周作人1921年才使用“宴飨(饗)”作为《会饮》篇的中文名,之前使用的是“宴集”,而且他曾翻译过生田春月的诗《小悲剧》(1920年10月16日《晨报》)。一般看法认为Jowett 译本流畅好读,只是有所省略,某些哲学名词也译得不够准确,然而影响力非常大。汉译柏拉图对话,较早依据的也多是这一译本。所以,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周作人熟悉并读过这一译本。
笔者2018年曾在国家图书馆查到周作人外文藏书中有一本1903年初版、1924年重印的柏拉图对话集(The Four Socratic Dialogues of Plato,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此书即Jowett的英译本,收有Euthyphro(《游叙弗伦》)、Apology(《申辩》)、Crito(《克里托》)、 Phaedo(《斐多》)等四篇与苏格拉底有关的对话,该书扉页钤有朱文方印“周作人印”。此书周作人购于1927年2月,尽管书中并没有《会饮》篇,而且购买时间晚于写作《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的1921年,然而这作为周作人熟悉Jowett柏拉图译本的一个间接说明,应该还是可以成立的。另,1930年鲁迅日记中记载他所购金鸡公司之柏拉图的《斐多》也是Jowett的译本。而从周作人的文字来看,他对柏拉图的熟悉则是确定无疑的。
作为“爱希腊者”的周作人对柏拉图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1908年学习古希腊语之初周作人就阅读了柏拉图对话,“一九〇八年起首学习古希腊语,读的还是那些克什诺芬(Xenophn)的《行军记》和柏拉图(Platōn) 的答问”⑥。其《欧洲文学史》(1918年)一书则给予柏拉图很高评价,认为“其宴集Symposion一篇,尤杰出”,这篇对话主张“以美与爱,乃能导人止于至善,此实Platon美之宗教观,足为希腊思想代表者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则多次说起柏拉图,如《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1921年)、《圣书与中国文学》(1921年)、《〈理想中的教师〉按语》(1925年)、《戏译柏拉图诗》(1926年)、《希腊人的好学》(1936年)等文。而在1948年所写的《闲话并耕》一文中,他对柏拉图下了“体大思精”的评语,“《孟子》里许行这一章,是全书中的一篇大文章,虽然比不上柏拉图的问答那么体大思精,有戏曲的风味,却也写得很有趣……”。在《欧里庇得斯传略》(1952年)中,周作人说,“……虽然在柏拉图的对话上不见有欧里庇得斯的名字”,尽管事实上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和《国家》篇(另有《理想国》、《王制》等译法)里都出现过欧里庇得斯的名字,《国家》篇第八卷中还说到欧里庇得斯是一位伟大的悲剧家,但我们至少看出晚年的周作人仍然显示出他对柏拉图了解上的一种自信。于此亦可见出周作人对柏拉图的关注与肯定并非忽然而来亦非忽然而去,而是相当持久的。
周作人曾多次引述柏拉图年轻时的小诗,尤其是《咏星》的情诗③,虽然是在说诗,但也包含了周作人对柏拉图一种特别的理解,即哲人柏拉图亦有其现世、感性的一面。的确,对于柏拉图,周作人看重的并不是其最为著名的“理念”说,而是他在《会饮》篇中所提出的“爱情秘教”(亦被概括为“审美教育”)五阶段说,因为其中指出了认识“绝对的美”“美的理念”所必经的肉体与感性之爱的阶段(周作人将之概括为“体美为精神美之发现”,“不爱美形就无由爱美之自体”),正符合周作人“灵肉一致”的人性理解与推崇。但柏拉图对“肉体(欲望)”的摒弃与敌视在其对话中更为突出,如《斐德若》篇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比喻成“蚌束缚在它的壳里”,《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则坚信死亡会使其灵魂从玷污、束缚它的肉体中解脱。柏拉图大多数的对话中,“理念”是绝对超越于具体可见的现象世界的,是与具体事物相分离的(关于柏拉图的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分离”“分有”关系有争论)。柏拉图所看重的是绝对而真实的理念世界,可感可见的现象世界不仅与其理念世界相分离,而且是不重要的。因此,周作人所理解和阐释的柏拉图思想,是不大符合整体的柏拉图哲学的。不过,中国现代文人根据当时的中国文化情境对希腊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并“为我所用”,是较为普遍的。同是推崇柏拉图的《会饮》篇,朱光潜和周作人从中所看取的思想就有所不同,朱氏即接受柏拉图的“理念论”(即其所谓“理式说”),着重静观思想。
“受戒者(The Initiated)”虽有明确的英文标注说明其外来文化的属性,从而使其在崇仰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对中国“旧文化”相联的一切分外具有“威力”,但具体的来源背景又不甚显明,由此带来了理解上的偏差。现在来看,乔伊特英译本的特色和不足都很明显,而且,随着之后新的英译本不断出现,一些译本在表达贴切和翻译准确方面好过乔伊特的翻译亦属自然。但乔伊特的版本在普及柏拉图对话方面功不可没,在1920年代及之前备受欢迎也是事实(郭斌龢翻译《筵话》、生田春月翻译《饗宴》,亦主要依据这一译本),而懂古希腊语的周作人喜欢这一译本,有时代风尚的影响,亦应有其偏好所在,就像他对柏拉图整体的阐释即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
作者简介:李雪莲,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