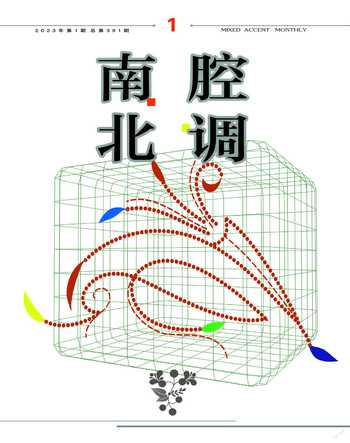传奇叙事的沿袭与突破
闫敏
摘要:葛亮的《朱雀》《北鸢》《问米》《谜鸦》《瓦猫》等小说从不同层面流露出复归传统叙事的倾向。葛亮以宿命感和历史感介入叙事,通过家族传承的形式凸显人物的传奇色彩,呈现出宏大叙事的历史脉络同人物成长之间的关联。葛亮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受到古代小说的影响,不仅继承了“传奇”中的志怪因素,还因循传奇叙事的世俗化、生活化倾向。同时,葛亮也并非孤立地继承传统叙事模式,而是在沿袭古代传奇叙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关键词:葛亮;传奇叙事;古代小说
引 言
“传奇”一词,缘起于唐代传奇,中唐时期元稹的《莺莺传》原名即为“传奇”,而后又有裴铏的小说集《传奇》问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唐传奇时提道:“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1]鲁迅肯定唐代传奇叙事中寓言化倾向,同时也关注到了其内在的审美意趣。随着文学史进程的演变,小说家对于“传奇”的理解,已经不局限于一种传统的文体样式,而是将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传统和叙事方式,也就是所谓的“传奇叙事”。张文东先生在《“传奇”传统和20世纪中国小说》中也指出:“‘传奇已经超越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本身,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各种体类、各个阶段都难以摆脱的一种叙事模式。”[2]
葛亮被认为是具有“老灵魂”和“葛亮味”的青年作家,一方面是基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家族传承,另一方面体现在葛亮小说向传统文化的复归。传奇叙事作为具有中国经验的叙事传统,在葛亮小说中体现为以传奇色彩裹挟人物宿命,同时将民间精神融入传奇叙事之中,通过复归传统的文化意蕴呈现具有感伤意味的“老灵魂”状态。著名评论家王德威先生评价道:“当代作家竟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他遥想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未来的成就必可期盼。”[3]葛亮对于传统文化底蕴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他小说中的传奇叙事,葛亮在以传奇叙事笔法讲述历史和现实人生时,通常以表现普通人的“人之常情”着手,赋予人物奇特、神秘的超常态的生命际遇。在创作时,葛亮还通过设置巧合和偶遇突出情节的离奇色彩,在故事发展中增添陡转式的情节设定,这无疑都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传奇色彩。本文主要着眼于葛亮小说传奇叙事的表现,探讨葛亮在创作中对于传奇叙事这一文学传统的沿袭与突破。
一、葛亮小说中传奇叙事的表现
葛亮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兼顾传奇性与现实性双重因素,将传奇与日常并置,在历史的大开大阖中书写世俗人生和日常生活。小说情节波澜曲折,大量的悬念与巧合贯穿其中。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有着理想化的性格以及超凡的人生经历,葛亮正是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超常态的人物际遇,营造出富有传奇意蕴的艺术效果。
葛亮在塑造人物时发扬了“无奇不传”的传奇叙事脉络,小说以“宿命”指引人物境遇的起承转合,人物命运受历史和时代的裹挟,带有不可控的传奇色彩。长篇小说《朱雀》以流落民间的“朱雀”挂饰揭开家族中祖孙三代女性的传奇人生,小说中人物的宿命带有不可抗拒的悲剧性,富有戏剧化色彩。在一次有关《朱雀》文本的访谈中,葛亮提道:“其中有传承,有碰撞和异变,也有宿命。在我的历史观念中有宿命的成分。而家族感似乎与之相关。”[4]《朱雀》以古城南京为背景,讲述了祖孙三代女性的传奇人生。从民国时期的叶毓芝到“文革”年代的程忆楚,再到新时代女性程囡,小说以宿命意识贯穿不同时代下人物的成长历程,通过民国物件“朱雀”挂饰引出人物身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情感纠葛和生命际遇。生逢乱世的叶毓芝,在国土覆灭的前夕,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日本人芥川发生关系并怀上孩子,经历过千夫所指后死于南京大屠杀。以“这城市女人骨子里的烈”来形容叶毓芝是恰如其分的,父爱的缺失使她比常人更为渴望得到爱与理解,同芥川的“苟合”成全了她“骨子里的烈”和对父权的反抗。第二代女性程憶楚正是叶毓芝“反抗”的结晶,成长于“文革”时期的她也依然有着执着和一往无前的一面,和右派分子陆一纬的情感纠葛使她在无意识中步入母亲的后尘。程忆楚后来即使未能追随陆一纬到北大荒,但多年后和已经有家室的陆一纬生下私生女程囡,这种超常态、奇特的人生经历也给小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新时代女性程囡,前后同“美国间谍”泰勒、“瘾君子”雅可、“外国友人”许廷迈的来往,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但这三段感情纠葛本身也带有曲折离奇的奇幻色彩。在程囡怀上瘾君子雅可的孩子之后,程忆楚也发出了“这是血里带来的”这般宿命意识的感慨。葛亮以“性”贯穿三代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独特的生命体验,无论是叶毓芝和日本人芥川的虐恋故事,还是程忆楚同归国华侨陆一纬的纠葛,抑或程囡三段奇特的爱情经历,其本质上都是葛亮精心设置的“异国恋”爱情模式,以此关照异质文化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而三位女性的奇特爱情经历和宿命感的轮回体验,实际上也表现出具有传奇色彩的生命际遇。
“故事是我写小说的基石。没有故事,我就基本上不想写小说了”[5],葛亮将故事作为他小说创作的基石,其作品中的传奇因素不仅表现在人物的传奇性上,情节的“奇”和“异”也是葛亮传奇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小说集《浣熊》《谜鸦》是葛亮香港写作的尝试,他在《浣熊》自序中写道:“小说香港,为这些年的遇见。”[6]葛亮以“遇见”作为讲述香港故事的缘起,实则是通过设置奇特诡异的情节,突出文章的传奇色彩,通过透视香港边缘人物的挣扎和反抗,凸显都市的诡异氛围。小说《浣熊》讲述的是一场狩猎与被猎的博弈,葛亮将都市中一场名为“浣熊”的热带风暴与人物的欲望结合,随着“浣熊”的逼近,欲望也逐渐浮出表面。文章以夸张的笔触将“浣熊”风暴人格化,并由此牵动人物命运,情节的离奇给都市蒙上一层神秘且诡异的色彩。小说《谜鸦》讲述的是新时代一对男女(毛果和简简)偶然间饲养一只乌鸦并将其命名为“谜”,此后遭遇了一系列离奇事件。葛亮在小说中以日常化的叙述描绘都市生活中的“乌鸦”怪谈,谜一般的宿命因素指引着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小说最终以简简因谜的死亡而丧失求生意志跳楼自杀结尾。葛亮将都市中的奇闻异谈诉诸笔墨,以诡谲的情节凸显都市的神秘感,从而揭示人性幽微处的阴暗面。小说《猴子》中猿猴杜林的出逃情节本身就带有传奇色彩,猴子偶然间破门而出后引发都市中一连串的异闻怪谈,各色人物在这场诡异的出逃中粉墨登场。猴子游刃有余地逃遁使都市充满了神秘诡异的气息,而它与偷渡漂泊的童童、精神失常的台湾女星的对视,也揭示了都市中的众生百态。小说《龙舟》中的于野因孤独和苦闷产生对于生的无力和对自由的渴望,离岛上的白衣女子实际上给于野带来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抚慰。小说结尾处情节发生“陡转”,在和于野春风一度后,白衣女子竟被证实是在半年前失踪的女孩,骨骼已然腐坏,在她的身上还发现了“男子新鲜的体液”。由“人”到“鬼”的情节设定,也使小说充满了神秘恐怖的传奇色彩。
二、葛亮小说传奇叙事的沿袭
传奇作为一种叙事传统,既有着对于史传传统的承袭,坚持叙述本真的创作前提,同时又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和虚构力,使小说极具“文采与想象”的文本特征,从而试图以世俗化的生活场景,表现浪漫奇情的理想主义色彩。葛亮在沿袭传奇叙事这一文学传统时,一方面着眼于传奇叙事中的“志怪”传统,以“幽灵”现象凸显俗世中的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则是沿袭传奇叙事中世俗化、生活化的创作倾向,将历史场景置于日常语境之中,彰显浓重的民间意识。
葛亮小说中的“幽灵”现象,实质上是对中国古代传奇叙事中志怪观念的继承,他多次提及曾阅读过《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等古代笔记小说,这些阅读经验成为葛亮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资源。在谈到鬼神之说时,葛亮直言:“我不会回避鬼神这个概念,西方有自己的一套志怪传统,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换个角度去看待社会平静的表象或者说是社会内在的乱象,这也是生死观的折射。”[7]葛亮小说中的志怪因素,并非单纯以志怪营造神秘诡谲的艺术氛围,更多的是借鉴了传奇叙事传统中以志怪为题材,表现俗世中人之常情的一面。《罐子》这部小说中的“幽灵”书写,即体现出葛亮对于志怪传统的继承,小说主要讲述女知青丁雪燕为获得返城指标怀上村长的孩子后被凌辱致死,多年后“回魂”到少女“小易”身上回村完成复仇的故事。“回魂”是指古代人迷信人死之后灵魂能够短暂回归,对生前未完之事作一个了结。《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云:“然回煞行迹,余实屡目睹之。鬼神茫然,究不知其如何也。”[8]可见,在古代小说中“回魂”一说,一般是作为生活琐事和奇闻异谈出现。小说沿用“回魂”这一离奇的故事设定,并将故事线索指向“欲说还休”的“文革”时期,揭示特殊时代人性的罪恶和救赎。小说通过人物自身的“回魂”揭开时代的伤痕,因此这里的“回魂”,又可称为历史记忆的“回魂”。
葛亮在小说创作中不仅关照到传奇叙事中的“志怪”传统,更是沿袭了传奇叙事中的世俗化、生活化倾向。中国小说叙事自唐代以后,开辟出了一条走向世情传奇的道路,宋代的话本传奇、明清戏曲中的传奇,乃至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红楼梦》,无一不是通过描摹世俗生活书写传奇故事。“世情”,简单来说就是以世俗形态揭示普遍的社会现象,摒弃时代语境中的政治形态因素,将俗人俗事以平实逼真的语调呈现出来,正是传奇叙事走向世俗化的一大特征。葛亮小说中的传奇叙事立足于民间,将人之常情作为塑造人物的基本准则,书写世俗场景和人生百态,以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再现时代的跌宕流转。在关涉历史的小说中,葛亮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着重以世俗化倾向的日常叙事描摹民间文化意识,将日常化叙事中的饮食、风俗文化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在提到饮食文化时,葛亮认为:“民间一如小说之源,犹似田稗,不涉大雅,却生命力旺盛。以食物喻时代,也是由平民立场看历史兴颓,林林总总,万法归宗于民间。”[9]其中,以“食物”喻时代体现出葛亮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长篇小说《燕食记》即以世俗生活中的饮食文化,淡化百年间的历史流转,将江湖儿女的爱恨、帮会传奇的恩怨都融入岭南饮食风俗之中。此外,葛亮的“匠传”系列小说同样体现出对于民间文化和世俗化倾向的靠拢,《书匠》中“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古籍修复师、《飞发》中坚守传统的翟师傅、《瓦猫》中精益求精的荣师傅,无一不是葛亮借小说回归生活的本质,通过洞察市井人情冷暖,以世俗化的民间立场探究匠人精神底蕴的叙事尝试。
三、葛亮小说传奇叙事的突破
传奇作为一种贴近大众阅读审美的叙事方式和文学传统,随着时代的变化,其自身也不断进行创造性地改造。葛亮小说的传奇叙事受到古代小说的影响,不仅继承了传奇小说中的志怪因素,还因循传奇叙事的世俗化、生活化倾向。然而,葛亮并非孤立地继承传统叙事模式,而是在创造性地沿袭古代传奇叙事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首先,葛亮在传奇叙事中将心理描写作为表现人物之奇的重要维度,通过多感官交织的手法透视人物心理,以人物内在的奇特感受突出小说整体上的传奇性。在都市传奇中,葛亮刻意追求奇崛的人生体验,以个人生命体验为基础,揭示都市人异化的心理状态。葛亮在《杀鱼》《不见》《龙舟》《朱鹮》等文本中,大量运用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感觉使人物处于特定状态中,并且将这种状态延续到心理空间,营造出一种紧张焦灼的心理状态。《龙舟》中“海浪的声音”、风沙的走向、“海鸟”的“惨烈”叫声,在文章中同人物心理空间相联结,于野同白衣女子具有传奇性的相遇和交合,也运用到了多重感官书写,在和白衣女子纠缠时回忆中的“热”同现实中“身体冰冷”形成巨大的感觉反差,也暗示着于野的死亡。“红色的细流”“艳红的水滴”也见证了人性中的卑劣、紧张的心理状态。《朱鹮》通过“无声”状态营造悬疑氛围,小说着重描述了失语儿童的反抗和挣扎。在无声的状态下,童童以“呼吸急促,身体震颤”作为对外界刺激的回应,在靠近“我”时,童童“嗅一嗅”,伸出手“拉住我的衣角”,这些动作对于失语的童童来说具有极强的暗示意义,也为后文案件告破埋下了伏笔。“笼在光影里”的画作、幻灯片上“鸟的形状”汇成的“轮廓”完成了对“我”的指认,这里将光影和画作同心境结合,在表现人物紧张心理的同时,使文章带有神秘悬疑的色彩。
其次,以辩证思维书写“常”与“奇”是葛亮小说常用的行文方式。葛亮在历史书写中通过日常叙事消解时代人物的传奇性,以世俗生活中的“常”淡化历史事件“奇”的一面。他提出:“因为时代的缘故,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太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10]葛亮在传奇叙事中着重将日常生活放置在历史语境中,以世俗性“常”的一面,表现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即使是书写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大人物,也往往更关注其“常”的一面。《北鸢》中的“常”与“奇”表现在从平凡人中挖掘其闪光点,呈现庸常百姓的传奇人生。面对战争的冲击,租界的“寓公”、要员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避开是非之地,可见在光环之下的风云人物,也是贪生怕死的普通人。反之,书中的文笙、逸美、思阅等普通人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他们身上大无畏的品格正体现了管窥之下的民间真精神。《北鸢》在塑造军阀混战中的传奇人物如石玉璞、柳珍年等人时,多是采取日常生活场景叠加历史语境的叙事方式,淡化战争和革命场景的时代背景,将视角放在日常生活叙述之中,呈现出传奇人物“常”的一面;石玉璞在面对柳珍年挑衅后神采全无,露出“虚弱与惊惧”的神情,这是属于他“孩子的”一面;小湘琴的“丑事”被揭露后,冲动的石玉璞将她一枪击毙,反映了他鲁莽蛮横的一面。这些日常化的叙述也从侧面预示了石玉璞英雄末路的结局,柳珍年假意给石玉璞拜寿后,昭德曾说:“你造出了时势,就莫怪时势造出他这个英雄。”[11]这一番言论也体现了小说中“常”与“奇”的辩证统一。
四、结 语
纵观葛亮的小说创作,从整体上来说呈现为向传统叙事方式的复归,而传奇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传统,在葛亮文学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葛亮在小说中以诗意的笔触呈现传统文化底蕴,融传统思想与文化艺术于传奇性文本之中,也凸显出葛亮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创作意图。现代以来,作家们实际上视“传奇”为一种叙事传统,在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中传奇因素的同时,也自觉转变叙事思路,将新的元素融入传奇文本中,从而使小说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因素,在表现出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同时,使传奇叙事散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4.
[2]张文东,王东.“传奇”传统与20世纪中国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6.
[3]王德威.抒情民国——葛亮的《北鸢》[J].南方文坛,2017(01):92.
[4]葛亮,刘涛.小说应当关乎当下、关照历史——与香港青年作家葛亮对谈[J]. 朔方,2014(04):96-99.
[5]卢欢.葛亮:尊重一个时代,让它自己说话[J].长江文艺,2016(23):112-121.
[6]葛亮.浣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4.
[7]澎湃新闻.专访|葛亮《问米》:在文学创造的世界里做一个观察者[EB/OL]. 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2303769.2018-07-30.
[8]紀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0.
[9]葛亮.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1):31-40.
[10]葛亮.他们的声音[M]//七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11]葛亮.北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7.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