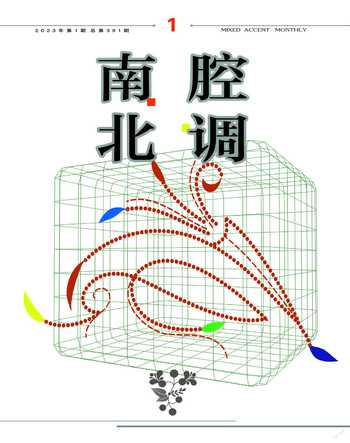刘震云《一日三秋》空间诗学研究
梁增凯
摘要:刘震云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中的人物,为生活奔波却都活成了笑话,小说在展开过程中呈现了大量的空间样貌。本文运用空间理论对小说进行阐发,从人物存在角度归纳出凡人的地理空间和鬼神的异质空间这两种空间形态,建构出并置的空间地图;另一方面,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构成权力空间建构的基础,人物主体成为空间关系抽象的能指符号,在人物的行动中,小说展现出花二娘异质空间的支配地位和其他空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本文从刘震云的小说中总结出一条地理空间—权力空间分析的经验路径,以期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空间书写提供一点儿思路。
关键词:空间;权力;《一日三秋》;并置
劉震云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是以“寻找”为主题而展开的,小说人物在找寻过程中的出走和回归轨迹呈现了多种样态的空间样貌。当前学界对于刘震云小说的分析侧重于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叙事方法,尚未重视对其小说空间维度的分析,所以本文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对小说进行阐发,来解读小说的空间建构以及依托于空间而呈现的权力关系等深层内涵,并从中管窥中国当代小说的空间书写经验。
一、空间建构:从真实空间到异质空间
海德格尔以“栖居”来形容人生存在于大地上,其中蕴含着人和作为物理空间的大地的关系。从人物生存之地的角度来看,《一日三秋》至少呈现了三个维度的空间样貌,这体现了小说文本对叙事的空间特征的强调,这种强调本身所体现的是小说叙事性的消解,从而展现一种“反叙事”特征。何为反叙事?龙迪勇认为:“如果说叙事凝固了时间、建构了历史的话,那么反叙事则可以拆解历史、重塑过去。”[1]龙迪勇是从叙事目的的角度阐发“反叙事”,这是对线性时间的因果叙事的一种反思和反叛。小说中,神仙花二娘和尘世凡人处于两种形态的空间之中,在故事展开中,两种空间分别体现为线性时间和永恒时间的存在,因此小说所呈现的空间样貌是反叙事的,或者说,小说空间呈现的形式并非叙事性的线性结构,而是一种并置的空间关系,并置空间中的样貌各自呈现着不同的时间形态。空间的并置所体现的是空间之间的对立关系,空间的对立往往基于两种依据:界限和异质。鲁斯认为小说中的空间有三种结构形式:一是连续空间;二是特殊情况下可以跨越的异质空间;三是不能直接沟通的异质空间[2]。这种分类方法在《一日三秋》中也是有效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日三秋》中空间的异质往往依靠空间中所存在的人物的特殊性来区别,空间的对立是人与非人的身份的体现,也就是说,在连续性的人存在的地理空间之外,与其相对立的异质空间是具有神话色彩的,需要依靠基于真实地理空间的想象而建构,所以,空间的对立是人与非人的对立,也是真实与联想的对立。如果说,小说文本所呈现的真实地理空间已经体现为虚构的产物,那么,基于此而产生的空间联想的建构则是虚构的虚构,所以,这种对立也可以说是虚构与虚构之虚构的对立。在《一日三秋》中,这种对立的人物存在的空间被分为两种,这里命名为地理空间和异质空间。
(一)寻找中建构的地理空间
小说中,基于真实地理空间的空间建构并非真实地理空间本身,而是对真实地理空间的一种还原性地模仿。刘震云在《一日三秋》中沿用了“寻找”的叙事主题传统,在小说中,尘世里的人物(区别于花二娘等非人人物)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旧地而踏上寻找之路,地理空间的全景就是在人物的寻找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从具体来看,尘世中人物的找寻分为“出走”和“回归”两种形式,他们为着寻求精神上或者生活上的新生而出走,但这种目的却往往落空,因为他们发现地理空间的转换并不能改变自身命运,在新空间里的探索似乎是原来生活的一种循环,而其苦苦寻求的答案却可能存留于出发的起点。于是,人物又开始了地理空间上的回归,这种寻找成了“兜圈子”式地寻找循环,人的寻找一无所获,带着目的地出走和回归,使他们的目的性成为无意义。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他们的脚步却使得整个小说的地理空间地图清晰了。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一日三秋》主要分为《樱桃》《明亮》两个主线故事以及《花二娘》一个副线故事,其中,尘世凡人的行动所建构的三个主要的地理空间分别为:河南延津、湖北武汉和陕西西安。第一,河南延津。河南延津是刘震云的故乡,所以刘震云常以延津为其小说的发生地。在《一日三秋》中,延津也是整个故事开始的地方。陈长杰、李延生和樱桃是风雷豫剧团的演员,以唱《白蛇传》闻名。后来剧团解散,陈长杰的老婆樱桃上吊死了,陈长杰带着儿子明亮去了武汉。后来明亮坐火车回到延津,在这里长大成人。小说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延津,就连花二娘也在延津扎根几千年,延津是小说地理空间上的根。第二,湖北武汉。樱桃死后,陈长杰带着明亮来到武汉,后来结识带着女儿秦薇薇的离婚女人秦家英,重新组建家庭,在这里生活到晚年。武汉是陈长杰逃离延津的归宿,是樱桃追赶的地点,也是明亮逃离的第一个地方。第三,陕西西安。在延津长大成人的明亮与有过性工作经历的马小萌成家之后,为了躲避当地人的流言,离开延津去了西安,最后彻底与延津断了联系。
这三个具体的地理空间,都是通过人物的寻找和出走而应运出现的。在真实的地理地图上,河南延津、湖北武汉和陕西西安构成一个地理上的三角关系,这是在人物出走之路上建立起来的地理地图上的闭环。刘震云并没有浪费太多笔墨在具体的地理空间细节上做文章,而是把重点放在对整个地理空间的把控上,极大限度地抛开了地理空间中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保留了地理空间中的地标建筑作为地理地点的参照,例如武汉的黄鹤楼、西安的大雁塔等。此外,刘震云也关注地理空间在时间流变中的历史真实,小说人物的“去和回”成为观察时间变化的空间见证者,通过人物来展现建筑空间这一凝固的时间。
在这三个地理空间点中,延津是故事的原点,也是小说中人物逃离的起点,而其他两地与延津联系的起点都建立在老董的算命上,算命代表的是人与鬼神以及命运的联系,反映了对从前的逃离和未来所要奔赴、寻找的目标都建立在与命运的联系中,这不仅体现出作者所要传达的命运的必然性,而且展现了个体对于命运的反抗,这些都反映在地理空间中的人物的找寻之路中。
刘震云在《一日三秋》里把对地理空间的建构和人物的命运、故事发展交织起来,黄清秀认为:“刘震云小说有着深刻的漂泊感,透露出现代人的孤寂,这种孤寂感的书写与呈现,既有对人自身存在的虚无性的探讨,也有对整个社会民族的存在规律的探寻。”[3]人物在找寻之路上的循环和兜圈子,展现了普罗大众对生活意义之追求的困惑,以及作者对于普通人面对命运无知又无力的同情。一方面,人物自身的奔波在行动中体现为盲目和无意义;另一方面,众多人物无意义的奔波,体现了刘震云对社会生活存在主义的反思。
此外,在对地理空间的建构中,刘震云把延津作为西安和武汉的对立面,以突出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对比。延津作为人物逃离的起点,其相对于他乡之独特性也凸显了出来。对陈长杰来说,故乡是充满记忆的地方,在故乡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充满了熟悉的味道,而这些片段的记忆正是他要拉开距离的、逃离的东西。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里称家宅为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物:“在这个遥远的区域,记忆与想象互不分离。双方都致力于互相深入。二者在价值序列上组成了一个回忆与形象的共同体。因而家宅不只是在历史的流逝过程中,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日复一日地被体验着。通过幻想,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居所共同渗透开来,保存着逝去岁月的宝藏。”[4]家宅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可能体现为一个区域的紧密联系,延津这个小城镇之于陈长杰就有这种家宅色彩,每一次对延津的直观,都会勾起陈长杰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和体验,正是陈长杰所要逃离的,他要把一个个通过直观达到的记忆拉长,成为可以回避的远方的回忆,而这个逃离或找寻,就是通过地理空间的转换来实现的。作为陈长杰的儿子,明亮三岁的时候回到了延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陈长杰自己的回归。陈长杰说自己一生走错了两步,都是因为唱戏,因为唱戏结识了樱桃和秦家英,可见,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地理空间的转变而改变,无论是地理空间上的奔走还是命运的轮转,都似乎是在兜圈子。相对于陈长杰的逃离,明亮离开延津除了对小环境流言的躲避,還有对新生活的追寻。明亮的结局看起来似乎在地理空间上与延津断了关系,但其实并非如此,甚至明亮的回归是小说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回归。中年的明亮去寻找奶奶院子里的枣树树心,在延津没有找到,小蔡把一个假的刻有“一日三秋”的门匾送到了西安,可明知是假,明亮还是将其挂在了他经营的店铺总店的墙上。明亮的回归是对故乡的回忆和眷恋,通过一块门匾的形式,种种情感被放在了身边,兜兜转转一生,明亮最离不开的或者一直找寻的正是逃离的起点。门匾是假门匾,这更体现了小说人物对生命意义追求的虚无,一切的努力都具有盲目性,最终并非修成正果而是一场虚无。
(二)重构后的异质空间及其两种形式
如果说,地理空间是对真实地理区域的还原性虚构,那么异质空间就是对虚构后的地理空间的重构,它是与地理空间并存并置的空间整体,在《一日三秋》中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花二娘所在的空间,一种是樱桃所在的空间。两者的区别在于,花二娘的异质空间是一个在空间上等同于地理空间而时间上区别于地理空间的空间整体,其时间是非线性的,而樱桃所在的异质空间体现为樱桃所存在的空间地点,她时而隐没于照片之中,时而出没于其他空间,因此樱桃所在的空间可以被视为花二娘空间的变形,它范围狭窄且无法逃离时间流变。由此可见,花二娘和樱桃存在于同一异质空间的不同空间层级中。总而言之,地理空间和异质空间的并置关系,基于两者质料的区别和界限的隔离,虚构和重构之间的空间想象又区分出两者不同的空间结构层次。
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空间建构呈现出层级结构的特点,从真实地理空间过渡到异质空间,存在一个越来越虚化的建构过程。刘震云对异质空间的建构基于对时间和历史的解构,在小说中呈现为反叙事的特征以及对时间和历史的消隐,这种对于线性的叙事时间的反叛并非对时间的否定,在小说中,刘震云往往通过空间结构来表达时间。龙迪勇分析了现代小说的三种空间叙事形式,认为空间可以作为时间的标识物,凝聚着时间的空间形式,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5]这种凝聚着时间的空间形式,在《一日三秋》中不断推动着故事前进,也是花二娘异质空间的特征。
在小说人物寻找的历程中,读者对事件流变的把握往往是通过人物地理空间的转变而获得的,而地理空间的变化则通过建筑物等空间形式的变化来体现。以明亮的行动路线为线索,明亮又二十年后再回延津,“街道两旁的楼房和商铺,都感到陌生”[6],他看到的是建筑物的变化,可内心涌起的却是对时间流逝、物非人非的失落感。段义孚认为:“建筑空间似乎会折射出人类情感的韵律,所以它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空间化的时间。”[7]所以,空间的叙事也是情感的叙事。
花二娘异质空间的一个特征体现为时间的消隐。在花二娘的异质空间中,时间是变动不居的,久居其中的花二娘“青春永驻”。由此可见,在花二娘的异质空间里,时间只是代表数字的抽象符号。花二娘异质空间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空间之质料区别于地理空间,按照鲁思·罗侬的说法,其异质的特征在于地理空间的人是无法主动进入的,这也就使异质空间具有神话色彩,并且为读者提供空间联想的可能。花二娘的异质空间对于小说人物和读者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这个空间更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是泛神的和绝对的所在。那么,这个花二娘的异质空间和地理空间的连结在哪里?连结在于夜晚的梦境。花二娘具备进入延津人梦境的能力,她让梦里的人讲笑话,把她逗笑就万事大吉,否则就会一命呜呼,在小说里体现为被花二娘变成的大山压死。
此外,上面提到异质空间的另一种形式是樱桃的小范围空间,如果说花二娘连接空间之间的能力是其选择的结果,那么,樱桃的异质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则充满了被动性。樱桃的存在需要依附于相片或者他物(比如海报),物本身不是异质空间,而是为樱桃提供了一个寄身之处,而物则是空间之间的连接。也正是因为樱桃异质空间的被动性,才使地理空间中的人物可能与之主动联系。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主要来自能够通鬼神的天师老董和马道婆。在文本中,刘震云不仅安排了“人死之后是有灵魂的”的预设,而且在小说中用了中国传统中“人间—地狱”的神话体系,人死了是要见阎王的,这就给老董或者马道婆能够通灵提供了可能性。老董能够算出樱桃在李延生的身体里,马道婆能够镇压樱桃使她受尽折磨。
总之,刘震云基于真实的地理空间在小说中构建出两个等级的空间层次:基于对真实虚构的地理空间和对地理空间重构而成的异质空间,而异质空间又分为花二娘主动的异质空间和樱桃被动的异质空间,这三个空间形态在小说文本中处于并置结构。通过天师老董等人,小说展现了命运的必然性,因为命可以被算出来。刘震云笔下的普罗大众在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于是老董家常常门庭若市,而算命的意义在于希望能够改命,这代表的是对命运的一种反抗精神,但是矛盾之处在于:既然命运是必然的,那么,算命给人带来的就是更大的绝望感,可是人们乐此不疲地信命和算命,正是人们对命运的无知和充满盲目感的人生追求的体现。另一方面,樱桃和花二娘对于不同空间之间的把控能力,也体现了她们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空间的把控体现为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花二娘的把控力、樱桃的被动性以及人物的盲目性形成了鲜明的权力对比,而这种权力对比是通过空间建构来表现的。
二、权力空间:基于多层空间中主体关系的建构
刘震云所建构的多层次空间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同一空间整体的内部并非均质的,空间之间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被理解。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先验的感性形式,但是在刘震云所构建的神话世界里,空间的感性形式似乎对主体失效了。我们对具体的空间关系进行阐发,是要回答几个问题:首先,并置的空间形态发生关系何以可能?其次,并置的空间形态之间是什么关系?以怎样的方式相互关联?再次,这种空间形态之间的关系于文本有怎样的作用?
(一)权力空间的构建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到,刘震云所建构的神话世界呈现出复杂的空间样貌,空间形态的建构是具有层级结构的。从单一的空间整体看,同一空间内部也并非均质化的呈现,否则小说人物也不会踏上找寻之路,这在地理空间中尤其明显,延津—武汉—西安的三角结构的呈现,就是人物探索未知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花二娘的异质空间中,时间的相对永恒使得此异质空间更加具有神话色彩。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先验的感性形式,然而,刘震云的神话世界对于时间的消解使得康德的理论难以适用于此。那么,这种并置的、非均质的、难以用一种理解方式把握的空间之间的关系是可能的吗?从文本的叙事情节来看,它是可能的,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花二娘能够进入延津人的梦,明亮和李延生能体会到樱桃,不同空间中的人物发生着关系。
空间并非不言自明,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生产的结果,但是生产的空间并非作为一个容器而存在,而是体现为一种关系:“空间作为一种产品,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一种事物或物体——而是指一组关系。”[8]按照列斐伏尔的路子,可以说《一日三秋》中的三种空间是关系着的,具体的关系如何呈现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福柯也考察过人与空间的关系:“建筑的工具复制了社会的等级。”[9]在福柯这里,建筑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空间本身呈现着权力关系,其中的身份主体都在权力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存在于空间中的主体首先都是关系着的人,他们自身具有在关系中形成的属性(比如职业),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之间就会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如果按照福柯所说,监狱长控制着囚犯,他对他们是一种绝对的把控权力,那么囚犯在监狱长面前则显得无能为力。学者童强也认为:“就权力与空间的关系而言,任一空间中的主体,将自身的意志体现在这一空间中的过程就表现为权力。”[10]由此可见,不论是从福柯出发,还是在童强这里,空间之间的权力关系都体现于空间中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可见,权力空间是一种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抽象空间形式。读者理解刘震云所建构的三种空间形式之间的关系,就要从具体的小说人物入手,先来分析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小说中的人物处于一个整体的空间之中,人物所代表的具体空间也要面对总体空间的审视。换句话说,人物的权力大小并非绝对的,人物是其他人物观照的对象,也是自我观照的对象,空间也要以自己为对照,这样的建构才能体现空间权力关系的全部可能性。
(二)面对空间整体的自我观照
前文分析了小说人物与命运的关系,发现在刘震云的神话世界里命运是可知的,也正是在这种可知的命运中,人物才会在寻找中探索一条出路。《一日三秋》中,所有的人物都在命运的洪流中沉浮,但是“命运”本身是一个虚无的概念,相对于具体的人物更具有形而上的色彩。在文本中,每个人物都在感慨命运,陈长杰漂泊一生没有离开戏词“奈何奈何,咋办咋办”,李延生等人都感叹自己活成了笑话,这体现的正是人物对命运的感受和总结,而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感正是人物和命运关系的体现。所以,人物何以审视命运以及何以从命运中审视自身,正是权力空间建构的关键。
福柯在《另类空间》里认为:“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类似的总的关系的地方……在所有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實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简历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 [11]福柯认为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空间的直接表现或颠覆反映,异托邦可以是真实生活的真实对照。福柯以镜子为例,说明人可以借由异托邦来审视自己:“在镜子确实存在的范围内,在我占据的地方,镜子有一种反作用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异托邦;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可以说由镜子另一端的虚拟的空间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我自己;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12]由此,人物或者人物所代表的空间自我审视成为可能,福柯的异托邦观点为自我审视也提供了方法。在《一日三秋》中,每一个人物都在寻找,也可以被视为每一个人都在和命运抗争,每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主体都是正在抗争的自己的变形,这正是主体本身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花二娘在延津等待花二郎等了三千年,把人等成了“望夫山”也没能等到花二郎的出现,花二娘的寻找和期盼在等待中化为荒诞;樱桃生前因为陈长杰“没劲”而生活不顺利,又是因为自己“没劲”而一命呜呼,更是为了摆脱“没劲”而苦苦寻找笑话希望投胎重生,于是樱桃永远在“没劲”的循环里打转;陈长杰、李延生兜兜转转找寻一生,最后都在生命的尽头里慨叹自己“活成了笑话”,也就是对自己的一生的彻底地否定。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对抵抗命运的无能为力。那么命运真的是不可改变的吗?明亮在天师老董的指引下一路西行,在西安落了家,摆脱了过去缠身的坏名声,并且通过努力赚到了钱,过上了富有的生活。但是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明亮和“翰林”冥冥之中的关系,老董也惋惜明亮没能继续读书,这是否意味着明亮最后能够幸福收场也是命中注定的呢?如此看来,在绝对的命运面前,小说中的人物尽管都表现出了顽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只得草草收场。
从人物之于命运的无可奈何中,可以看到在面对绝对时人的无能为力,而从人所代表的空间权力来看,在总体的空间面前,并置的三种空间形态同样被审视被关照。同时,三种空间形态之间也在发生着关系,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会通过空间中的主体的具体关系形式来展现,这要放到下一部分来进行具体阐发。
(三)多层空间的权力关系解读
刘震云建构的多层次空间形态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空间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空间中的主体是其所处空间的抽象符号,人物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空间关系的具体体现,不同空间形态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人物关系的所指和意义。
《一日三秋》主要呈现了两种空间形态,即地理空间和异质空间,而异质空间又呈现出两种空间样貌,即花二娘的异质空间和樱桃的异质空间。地理空间的主要人物为明亮、李延生、陈长杰等凡人,花二娘的异质空间主要以神仙花二娘为代表,樱桃的异质空间的人物为樱桃和通灵后的凡人。小说的故事从这三个维度同时展开,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小说人物对各自的命运无可奈何,彼此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权力关系。
对于明亮等凡人和樱桃来说,花二娘是具有不可抗力的神仙,与花二娘接触时要完全按其原则做事,也就是说,花二娘空间的禁忌不可被触犯,否则就会一命呜呼。这种关系并非刘震云独创,它能对应于某个人类思维发展的阶段。按照恩斯特·卡西尔的说法:“即使在神话思想的原始阶段,也存在着一种信念,这种观念相信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与自然以及自然的神圣或者邪恶的力量协作。”[13]在异质的鬼神空间里,人和鬼神的对立也体现着这样一种协作关系,或者服从关系,人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和支配的地位,成为完全的被控制者,不能触犯禁忌。卡西尔认为:“禁忌,从原初和字面的意义上仅仅意味着一个被划分出来的东西,它不再与其他平常的、世俗的以及无害的东西等同。它被恐惧和危险的氛围笼罩。人们常常把这种危险描述为一种超自然的危险,而不是道德的危险。”[14]照应于小说,花二娘要听笑话,违背她的意思就是触犯禁忌,结果就是死亡。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花二娘对于其他空间人物的完全把控的能力,这种权力关系是命令与服从,或者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那么,地理空间中的人物和鬼魂樱桃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这里选择三类地理空间人物代表来讨论其与樱桃的关系,包括李延生、明亮、马道婆。李延生最早是樱桃唱戏的搭档,后来樱桃死后借由海报寄身并附身李延生的肚子里,使得李延生心头常常烦闷,开心不起来。为了使樱桃离开自己的身体,李延生只好听樱桃的话,去武汉找陈长杰。可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樱桃对于普通凡人是有制约和操控能力的。明亮是樱桃的儿子,樱桃死后来到武汉,看到明亮后舍不得离开就留了下来,其间借由相片寄身,后被秦薇薇发现这个秘密。从中可以看到,作为鬼魂的樱桃并非像花二娘那样对凡人具有不可抗力,代表着禁忌与不可侵犯,在樱桃这里,她首先是依附于物而与人平等相处的,她的弱点也会暴露并为凡人所制约。下面再说马道婆,樱桃寄身的弱点被秦家英的女儿秦薇薇发现,秦家英就把照片交给了马道婆,马道婆做法使得樱桃受尽折磨。马道婆和老董都是能够通鬼神的凡人,作为鬼魂的樱桃在他们面前也显示出无能为力的状态。
借由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三种形态的空间关系也从中展现出来了,这关系并非小说里空间关系的还原,更具备相应的现实意义。古希腊美学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而刘震云的神话世界也必定是有真实依托的,这就使得小说空间呈现为一个个隐喻实体,与现实有着种种关联:首先看空间关系。通过小说人物权力关系分析可以看到,在整体空间内三种样貌的空间呈现并置关系,其中花二娘的异质空间是全部空间的权力中心,制约、支配着其他空间形态;而樱桃的异质空间和地理空间则呈现为一种互相制约、权力和能力此消彼长的局面。何雪松认为:“福柯开辟了经由地理学概念重新解读空间、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滥觞。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或者说是权力的容器。权力的空间化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权力作为一个生产实践背后隐匿的一整套的策略和逻辑地理学面向。”[15]也就是说,从空间权力关系分析,可以看到一套社会权力空间的建构和权力分配的关系。这体现出刘震云《一日三秋》中权力空间的现实性,这里并不过多展开。
总之,通过对本文的分析结合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理论论证,空间中的人物成了空间的抽象符号,人物关系呈现了总体权力空间中各空间形态的关系形式。在各空间的自我观照中,其各自表现了面对命运和总体权力空间的无力感,但在其相互的关系中,花二娘的异质空间具有支配地位,樱桃的异质空间和凡人的地理空间则表现为互相制约、权力此消彼长的状态。无论是空间的自我观照还是互相关联,都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社会现实的面貌。
三、结 论
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体现出对线性叙事消解的特征,小说是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呈现大量的空间样貌。从人物生存的空间来看,不同小说人物处于不同的时空中,由此便出现了处于并置结构的三种同时进行着的空间形态,分别为凡人的地理空间、花二娘和樱桃两种形式的异质空间。处于并置的空间关系中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种权力关系,此时,人物就成了各空间之间关系的抽象的能指符号,在整体空间中体现着人与空间、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和意义。神仙花二娘对其他人物的绝对控制能力,体现了花二娘异质空间的支配权力,而鬼魂樱桃和凡人的互相纠缠,则体现了地理空间和樱桃异质空间的互相制约、势力此消彼长的权力地位,此时,人的权力是空间赋予的,人也是空间的权力的具体体现。但是在命运面前,所有人物的無能为力体现为各种空间之于总体空间的权力的丧失。
《一日三秋》的叙事框架是空间化的,并置的故事空间消解了单一的线性叙事,使得小说的人物和空间关系得到突出而故事的因果逻辑性退居其次;另外,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加强了文本的空间化特征。叙事学的空间转向是一些文学作品的时代性特征,本文从小说《一日三秋》中探索到一条从地理空间建构到权力关系阐发的空间诗学研究路径,以期为当代小说空间经验书写提供一点儿思路。
参考文献:
[1]龙迪勇.反叙事:重塑过去与消解历史[J].江西社会科学:2001(2).
[2]Ruth Ronen. Space in Fiction[J].Poetics Today,1986(7).
[3]黄清秀.刘震云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8.
[4][法]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4.
[5]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3(10).
[6] 刘震云.一日三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7][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97.
[8][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2.
[9][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累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C]. 陈志梧,译.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9.
[10]童强.空间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3.
[11][12][法]福柯.另类空间[J]. 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
[13][1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李琛,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89,93.
[15]何雪松.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J].学海,2005(6).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天马形象与丝路审美共同体”(项目号:20BZW033)、兰州大学2020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先秦审美文化的时空意识研究”(项目号:2020jbkyzy026)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