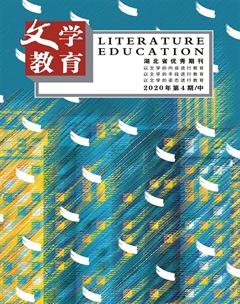空间视域下的葛亮南京题材小说研究
内容摘要:70后作家葛亮因其生活背景、求学经历等因素,使其格外重视小说中的空间建构。葛亮在建构其“家城”南京的时候,不仅关注了南京的历史积淀和世俗日常,同时还关注了南京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关于南京的书写,葛亮采取的是想象与真实相结合的手法。在空间书写的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人的思考以及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关键词:葛亮 南京小说 空间化书写
葛亮作为当下较有话题度的作家,著有小说《谜鸦》《浣熊》《戏年》《七声》《朱雀》《北鸢》《问米》,文化随笔《绘色》等。其小说《北鸢》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提名,并且他还曾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他的长篇小说《朱雀》获得了2009年“《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凭借《北鸢》再获此殊荣。
在葛亮的创作中,城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从“家城”南京到“我城”香港,再到虚构的城市襄城,都在葛亮的小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作家而言,其文化身份与空间背景密不可分。作家们通常通过地域意识标识自我,他们对某一地域空间的体认与感知往往超越了单纯的地理坐标,并糅杂着历史、情感、记忆等综合文化体验”[1]。南京被葛亮称为“家城”,不同人物在这个城市里演绎着各自的人生。透过人物的命运,南京这座城市也彰显出其独特的韵味。
葛亮生长于南京,求学生活于香港,并在两地间进行多次往返。在书写南京的过程中,葛亮借用在香港的生活经验对其南京的记忆进行加工和整理,这使得他的南京书写多了一种客观化和理性化。“流动的生活促使葛亮在香港来书写南京这个地方,这不仅源于个体对熟悉的地方的再回忆,还表现为人类本身对一种陌生空间,或者说是‘陌生化的应答。”[2]葛亮也在他的小说《朱雀》后记中承认:“是因为惯常于此,出于一个本地人的笃定。我突然醒悟,所谓的熟悉,让我们失去了追问的借口,变得矜持与迟钝……于是,有了后来的寻找与走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在原本以为熟识的地方,收获出其不意,因为偏离了预期的轨道。”[3]在葛亮的笔下,南京是一座融合了历史积淀与世俗日常、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城市。
一.历史积淀与世俗日常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葛亮的童年与少年时光都是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度过的。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氛围,以及葛亮自身的家世背景都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南京,又名建业、建康、秦淮、金陵,曾经是六朝古都。诸葛亮曾经叹咏过:“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從古至今,文人墨客的青睐,使得南京的古典气息浓厚。古有苏轼的《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忧,晋代衣冠成古丘。”;近有毛泽东的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南京,总会让人兴起叹咏一首的感慨。无数文人骚客的创作,在南京悠长的历史中沉淀下了古典文艺气息。
建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处处彰显着一座城市的风格。哈斯克尔曾提到:“有一种建筑却一直被认为能激起鲜活的历史感,那就是废墟。”[4]南京遗留下很多能够体现其特点的古建筑。
南京的文人风气渗透在其建筑里,如夫子庙,是中国古代文化枢纽之地、金陵历史人文荟萃之地。葛亮在《朱雀》中写到:“他看到前面有了红墙金瓦的建筑,虽然颜色是旧了,但是在这嘈杂中却有股肃然之气”[5]尽管传统的夫子庙已经沾染上现代色彩,但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文人气息仍让外国人许廷迈感到敬畏。同样文人气息浓厚的建筑是魁光阁。魁光阁旁边的红色墙头里是江南贡院,中国古代最大的考场。各地应试的秀才中了榜,就到魁光阁里来庆祝,原先还有在墙上题诗作对的,风雅得很。与夫子庙的情况相一致,魁光阁也免不了现代化的侵蚀。不过,“里面有一道曲折的回廊,新也是新,结构却是透着古意的。回廊又连着一座石舫,却一眼看得出是旧物,很见沧桑。”“他四处打量着,的确是看不出。这茶馆似乎太安静了,陈设也厚重,并不是与民同乐的类型”[6]历史遗留下的痕迹使得现代化的茶馆魁光阁仍有掩盖不住的文人气息。南京悠久的历史及其形成的古典文人气息让身为外国人的许廷迈敬畏不已。
南京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让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南京的大“是忍受得住寂寞的”。当程囡带着许廷迈来到南京的郊区浏览时,他们看到了古时候遗留下来的一块未完成的石碑。“这石上面坑坑洼洼,粗糙如从地底生出,是很见沧桑的。然而十几米高,几十米长,峭拔而立,却有着垂直的立面,几乎是纯然的矩形,边缘有着锐利整齐的角。而前面一块稍小的,竟还凿着几米见方阴飒飒的孔穴。他站过去,抚摸这石壁,兴奋地击打。”[7]面对这么一块庞然大物,震惊的不止外来人许廷迈,连从小生长于此的本地人程囡都不作声了。他们被南京的大所震撼了。“在这阔大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压逼,禁不住互执了双手,觉得自己站在了宇宙苍穹的核心。林寒涧肃,岚气袭衣。他们渺小如一粒尘,几乎感觉不到自己。他说,我明白了,这就是南京的大。”[8]尽管如此旷古罕见的大材没有物尽其用,埋没于荒野之中,却有一种怡然的感觉。面对着南京深厚的历史底蕴,无论怎样大的事物在其面前都会自惭形秽。
与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相得益彰的,是南京轻松活泼的世俗日常。葛亮不仅关注那些能够体现文人气息的建筑,同时,他还关注南京的另一面,即世俗化的历史的场所。龙迪勇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场所:“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者地点变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9]。不管时间的流逝,事件的完结,只要发生事件的地点还存在,只要储存记忆的空间还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唤醒过往的记忆。正如学者冯炜所指出的:“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10]不同种类的体验丰富了叙事空间。南京作为葛亮笔下重要的叙事空间,其世俗日常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建筑与地点,还包括体现南京文化的场所。
在《七声》中,葛亮借用儿童毛果的口吻说道:“我成长的城市,是中国的旧都。老旧的东西是不会缺乏的。既有十竹斋这样的雅处,也有朝天宫如此平易近人的地方……后者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乐园……那时候的朝天宫,远没有现在的博物馆建筑群这样规整,有些凌乱。也是凌乱,所以带有了生气。”“如今记忆犹新,尹师傅在当时,是朝天宫的一道风景。”[11]尽管朝天宫在岁月的侵蚀下早已没了往常的热闹与活力,泥人尹师傅也成为了过去,但是当毛果看到自己尘封多年的泥人的时候,关于朝天宫的记忆立刻就被唤醒了,连带着关于童年的记忆、关于尹师傅的记忆都又重生了。在朝天宫里,毛果见识到了三教九流的人,有卖古董的,有耍猴卖艺的,有做小本买卖的,还有真本领并脚踏实地的艺人。这些人都是生活在南京城的普通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从事的职业也千差万别,他们共同丰富了南京的世俗生活。葛亮正是借用这些人、这些地点来构建南京世俗日常的叙事空间。
在生活习俗方面,葛亮用南京人爱泡澡这个习惯来刻画南京的特点。为此,葛亮选取了一座解放前就已经开张的澡堂子——白下池。澡堂子作为既私密又公共的场所,它是平民的聚集地,它让所有人都放松警惕,卸下了伪装,展示出“本我”。看到四处都是白花花的裸体,外族人许廷迈刚开始还会觉得尴尬。不久,因为澡堂子私密性的空间特征,使得许廷迈放下了在外所要带上的人格面具,融入到南京人中,逐渐放松直至显露“本我”。当他像众多南京人那样边泡澡边吃萝卜,再学人家呷上一口热茶,他的行为完全符合了南京的民谚,叫做“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最后,他好像如释重负似的打了个畅快的嗝,整个人都很松快。“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世俗空间中有时也能体验到能够唤起空间的宗教体验所特有的非均质的神圣价值。”[12]当他向程囡讲述自己泡澡的经历后,连程囡都认可了他像个南京人。
正如孔庆东在评价北京文学所指出的:“北京文学既有鲜明的平民气,又有鲜明的贵族气,二者彼此融合相映生辉,而这正是北京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13]南京同样拥有着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种文化。在葛亮关于南京的书写中,富有文人气息的建筑和世俗日常的场所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了葛亮关于南京的空间化建构。
二.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杂糅
南京的历史悠久,遗存的古迹、文人作品等都熏陶着葛亮的古典涵养;同时,葛亮的家世背景也令人惊叹。他的祖父是葛康俞教授,其评论中国古代书畫名迹的著作《据几曾看》,是葛亮放在案头常常翻阅的读物;太舅公是陈独秀,叔公是邓稼先。从太舅公到外公,从祖父到父亲,这也让葛亮继承了家族独特的文学审美与鉴赏风格,并融入其之后的文学创作中。从葛亮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古典艺术的喜爱。上文已经详细分析过葛亮在书写南京时所选取的富有传统文人气息的建筑,在此就不加以赘述。
爱德华·布洛认为,文学艺术中美的欣赏、美的创造与保持现实生活的适当距离是分不开的。尽管葛亮非常熟悉南京,并对南京有着别样深刻的见解,但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正是对南京这座城市太过于熟悉,可能会对南京的独特之处视而不见,以至于葛亮对自己的认识产生了不自信,从而没有在南京这座家城开始其写作生涯。之后他求学于香港,在香港那样一个高度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在香港,葛亮作为一个异乡人,在思乡的同时,自然会把南京和香港作比较,把南京投射于香港之上,从而进行一番权衡。在对比的时候,葛亮在香港这座城市中看到了对传统的保护,同时也看到了现代化的大行其道,因而他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南京,他看到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其特有的传统气质;但同时,在全球化的进程下,南京也顺势被卷入到现代化中。因而葛亮笔下的南京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杂糅。
夫子庙是南京历史与传统的象征,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也被刻上了现代化的标记。《朱雀》中借用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的观察,道出了夫子庙的现况:“他没料到夫子庙是个极热闹的所在。他总以为纪念圣人的地方应该是肃穆的,就像莎士比亚的墓地和司各特的故居。而这里却满是香火气。”[14]在外国人许廷迈的想象中,南京应该是具有古都气息的一座城市,理想中的南京应该具有一种古典美,就像朱自清和俞平伯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样,秦淮河具有六朝脂粉腐朽和黏腻的余韵,在这条河里能够看出历史的积蕴。然而现实却是“待站到秦淮河边,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把他吓了一跳。这河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让他失望,不仅是浑,而且黑得发亮。他于是很坦白地说,这河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污染最严重的河流。”[15]由此看来,现代化对古典南京所造成的破坏性极大。现代化给南京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而南京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它的历史与古典氛围,这之间的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然而,现代化为南京带来的不全是弊端,葛亮也没有一味地批判现代化对南京的改变。葛亮选取了尹师傅新的工作室作为着眼点,刻画了尹师傅新工作室的样貌:“说是工作室,其实是靠着莫愁湖的一间民房。改建过了,四周都是大块的玻璃,采光很好。透过窗户,可以看得见大大小小的泥人,摆在通顶的木架上。”[16]对比之前尹师傅那个十多平方米、极为简朴的斗室来说,作者隐含的态度是庆幸的。虽然尹师傅拥有一双巧手,掌握着一项传统技艺,但他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得不到国人的重视,使他几乎连自己和养子的生活都担负不起。幸而南京走向了现代化,尹师傅捏泥人的手艺才得以被英国人赏识,并远渡重洋,受到西方人的喜爱。传统手艺的现代化保证了尹师傅的个人生活,也让国人重视了这门艺术,没有让这项传统技艺失传。由此可见,葛亮与一般以古都为描写对象的作家有所区别,他并没有对现代化深恶痛绝,而是采取宽容开放的态度,展现了一位年轻作家多元包容的心态。
葛亮的南京书写,是建立在其拥有多元的文化观念之上的书写,是融合他的古典素养与现代性认识而形成的。
三.宏观的想象与细节的真实
作为70后作家,葛亮既没有经历过巅峰时期的南京,也没有经历过南京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他如何进行南京的叙述,王德威教授说得很准确:“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间,在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之间,葛亮寻寻觅觅,写下属于他这一世代的南京叙事。”[17]想象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过:“事实上,我们处于形象和回憶的统一之中,想象力和记忆力的功能性混合当中”[18]。记忆不仅和时间有关,它同时也与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空间特性必然会给虚构叙事带来深刻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说,相较于其他空间,故乡对于作者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它很容易成为人们记忆的承载物。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提出了“存在空间”的概念:“所谓‘存在空间,就是比较稳定的直觉图示体系,亦即环境的‘形象。”[19]故乡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空间”,“它往往承载着我们最初的重要记忆,以后不管到了哪里,我们总是以这一‘存在空间作为参照系去体验世间的万事万物。”[20]葛亮发挥想象,在其关于南京记忆的基础上构建了历史叙事。
在《朱雀》中,葛亮并没有采用一般作家写古都时所常用的宏大叙述,而是着眼于小处,以想象南京城三代女性的爱情悲剧,用“朱雀”这个物件来指代南京,进行关于南京的想象。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就消解在人物的命运和日常生活中。程云和每天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做饭,而在这看似安宁的背后,中国却处于“文革”那个疯狂的时期;叶楚生满怀志气来到南京做生意,而他看似兴旺的生意背后,中国却处于战争动乱时期。葛亮放弃了历史宏大叙述,更多地关注人物自身的性格和命运,使得他的南京书写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色。
“葛亮更有兴趣的应该是召唤一种叫做‘南京的状态或心态;南京于他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近于耽美的向往。”[21]。当叶楚生站在去往南京的船头吹箫遥望的时候,不禁让人联想到“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豪迈模样;年轻的程囡和许廷迈在开阔的明朝墓碑上尽情释放激情,不由得令读者会心一笑:青春使这座古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葛亮赋予这座城市的想象,使得这座旧城散发出青春的气息。
想象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遐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在熟悉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有根据地进行构思。为此我们看到《朱雀》中,就连一副弹琵琶的假指甲,葛亮都毫不吝啬自己的文字去细细描写。尽管他的南京历史叙事是靠想象创造的,然而这种类似考证的精细,使得读者对葛亮的叙述信以为真。
同样,为了适应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人物,还需要有相应的语言文字进行加持,这样更能体现叙事的真实性。南京既有古典的诗意,又有市井的平俗。葛亮为了写好南京的人与事,下足了功夫去研究南京的历史与人文,这才让我们看到《朱雀》中典雅的语言文字,诸如“他独自伫立在大片的阴影中,看着眼前的风光,以为自己误打误撞走进了守旧人家的大宅门。总觉得这里,该有个光艳的戏子唱起了幽怨的戏。然后年华也在这咿咿呀呀的腔调里,身不由己地老过去。”[22]同样,南京也有市井风光。在《七声》里,葛亮所使用的语言更多的是平实易懂、简单朴素、带有南京俚语的语言。
正是因为葛亮对南京这“存在空间”有很深的记忆,才能使他运用想象来构建历史中的南京。葛亮笔下的南京,一房一巷都具有真实感,这也出于葛亮对故乡的熟悉。
参考文献
[1][法]加斯东·巴拉什:《空间的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2]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3]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J].《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11期.
[4]史倩文:《历史本真性探寻下的城与人书写——试论葛亮〈朱雀〉中的南京叙事和宿命意识》[J].《名作欣赏》,2018年07期.
[5]刘红娟:《葛亮论:城与人,诗与史》[N].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
[6]朴婕:《论葛亮的“南京”书写》[J].《小说评论》,2018年01期.
[7]周蕾:《历史、日常、他者与“南京”想象——评葛亮的长篇〈朱雀〉》[J].《名作欣赏》,2015年04期.
[8]王存弟:《金陵王气黯然收——论〈朱雀〉的城市空间叙事》[J].《名作欣赏》,2015年09期.
[9]刘莹:《想象与记忆的重奏:葛亮的南京书写——以〈朱雀〉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10]葛亮:《葛亮:我喜欢历史中的意外》[N].文艺报,2014年8月20日第003版.
注 释
[1]房广莹:《叶广芩家族小说的空间化书写——以<采桑子>为例》[J].文艺评论2016年8月.
[2]王丁叮:《葛亮小说的流动性研究》[D].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44页.
[3]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9页.
[4][英]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M].《艺术史与艺术理论I》,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5]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6]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7]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8]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
[9]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84页.
[10][英]冯炜:《透视前后的空间体验与建构》,李开然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11]葛亮:《七声》[M].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55页.
[12]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5页.
[13]孔庆东:《北京文学的贵族气》[J].《当代文坛》,2004年第6期.
[14]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5]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6]葛亮:《七声》[M].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8页.
[17]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J].《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11期.
[18][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19][挪]诺伯格·舒尔兹:《存在·空间·建筑》[M].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20]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5页.
[21]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IX页.
[22]葛亮:《朱雀》[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作者介绍:路璐,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