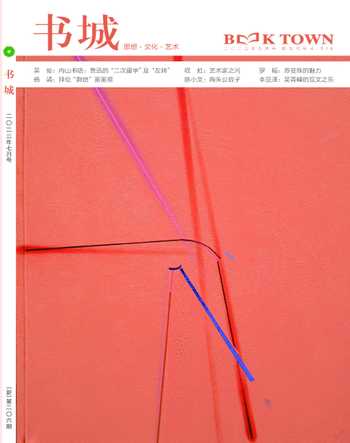吴青峰的互文之乐
李亚泽
翻开二○二二年各大平台的华语流行音乐榜单,一张名为《马拉美的星期二》的专辑赫然在列。马拉美是谁?他的星期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找来专辑曲目再看,更是奇葩:《(……小小牧羊人)》《(……海妖沙龙)》《(……老顽固博士)》《(……醉鬼阿Q)》……歌名有些俏皮,也不免让人心生疑问:为什么非得用括号括起来?省略号又是什么意思?臂弯般的括号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暗示,珍珠般的省略号又似一种意犹未尽的召唤。谁在召唤?是作为创作者—词曲作者、歌颂者的吴青峰?还是歌词里各种鲜活的文艺经典,例如,塞壬的歌声?都可以。因为这张唱片刻录的声音足够诱惑,专辑概念与歌词创作也极具创意,航行在这片诗意之海,或许连奥德修斯都愿意抠掉耳朵上的蜜蜡“洗耳恭听”。
作为一位中文系毕业的歌手,吴青峰在歌词创作上可谓妙笔生花,从他笔下流淌出的词句经常受到业界的肯定。单是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他就五次被提名、一次获奖。在吴青峰的歌词中,总是能听到、读到一些“出其不意”。他善于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并且恰到好处地运用到歌词中去。传唱度最高的那首《小情歌》就曾化用战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借以表达恋人内心的痛苦和纠结:“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捱的离骚。”其实,早在苏打绿“维瓦尔第计划”时期,身为主唱及主要词曲作者的吴青峰就已经有意识地借助希腊罗马神话、中国古典诗词、西方文学经典等元素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思考:《春·日光》的牧神潘、庄周梦蝶;《夏/狂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浮士德;《秋:故事》的丰收之神德墨忒尔、陶渊明、苏轼;《冬 未了》的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极富哲思的严肃文学为青峰的作品提供了稳定的内核,灵动优美的旋律又为意蕴十足的歌词添上了一双轻盈的薄翼,文学的音乐或是音乐的文学就这样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可谓艺术歌词的典范。
在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看来,“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由此提出的“互文性”理念开拓了文本的边界。从词源上说,文本(texte)即是编织的产物,七彩的丝线捻在作家手中,织出一匹匹亮眼的绸缎。二○二二年九月,吴青峰再一次开启了他的纺织艺术,试图在个人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中探讨丝与手—创作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这张专辑的创作同样离不开对文艺经典的吸收和借鉴,甚至在以往的基础上迈向了一个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互文世界,让我们既能以耳享乐,又能以思享乐。
先来说说这张专辑的“缪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马拉美每个星期二都会在巴黎的罗马街或是乡下的房子里举办一次文艺沙龙。当时参与的嘉宾不乏先锋艺术家,例如,诗人兰波、魏尔伦、瓦莱里,作家纪德、普鲁斯特,音乐家德彪西,画家塞尚、马奈等。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交流彼此的艺术理念,最后也酝酿出许多优秀的艺术成果。就拿德彪西来说,他的那首印象主义代表之作《牧神午后前奏曲》正是从马拉美的著名诗篇《牧神午后》当中汲取的灵感。一个多世纪以后,马拉美的文艺沙龙仍有余温,影响了一位来自东方的歌者。在《马拉美的星期二》这张专辑中,十二首歌曲,每一首都邀请了不同的音乐人参与制作,如华语歌手孙燕姿,日本歌手小野丽莎、大桥三重唱,以及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等。对吴青峰而言,这些合作伙伴都是他的沙龙嘉宾,每一位都或多或少地在他的音乐世界里留过一段故事,“从一个创作源起,激发了另一个人的创作”,就像德彪西运用管弦乐的色彩建构起一个牧神午后那样,吴青峰的这场音乐沙龙也充满了梦境般的美好气息。
除了音乐人之间的灵感碰撞,我们还会看到一些“纸上的共鸣”。这样的文艺沙龙,自然不会缺少吴青峰在书中结识的伙伴。在接受《南都娱乐周刊》的采访时,吴青峰说:“我很喜欢读各种故事与神话,所以我幻想我自己有个沙龙,有一些人物来到我身旁,有些定期拜访,有些偶然闯入,他们分别或交集,丢下各自的故事,像阿拉伯花纹般交织在我身上。”抛开吴青峰之前发表的、从歌名就能看出主题为何的歌曲(如《巴别塔庆典》《水仙花之死》《男孩庄周》)不谈,光是《马拉美的星期二》就化用了希腊罗马神话的诸多意象,维纳斯的镜、卡戎船、特洛伊、象牙门、多头蛇、阿波罗、墨丘利、斯芬克斯等。这些典故的运用并非混乱的堆砌,而是针对特定主题的巧妙贴合,因此,歌词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一团晃眼的马赛克,而是一枚精致的阿拉伯花纹。这种花纹同样是马拉美在《音乐与文学》中宣布的法则,“将它们(词语)连接起来的阿拉伯花纹有着令人眼花的跳跃,形成了一种熟悉的恐惧”。对此,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在《马拉美:塞壬的政治》中解读道:“阿拉伯花纹的说法消除了一种错觉,即认为诗歌旨在描写一个人或一个故事,一样东西或一种情感,好让它们被认出来。”马拉美的诗歌总是被人冠以“晦涩”之名,而吴青峰在《马拉美的星期二》中进行的互文实验显然也不是为“流行”而作。新专辑发行后,许多听众都在歌词面前迷失了思维:太多典故,太多意料之外的词语并置,太难懂,太晦涩。能指或许熟悉,所指又该如何把握?这种“熟悉的恐惧”,或许正如朗西埃所说,是“筑起的一道特殊的城墙,但构成这城墙的,并非晦涩的词语,而是不断逃脱的句子的灵活线条”。通过交织的阿拉伯花纹,“吴拉美”同样选择了一种隐晦的方式来诉说自己对创作的思考。
仔细“阅读”过《马拉美的星期二》的听众不难发现,整张专辑应用最广泛的互文手法就是“引用”与“暗示”。“引用”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呈现作者的文学记忆,不加掩饰地让读者发现其他文本的痕迹;“暗示”则被作者别出心裁地隐藏在文本之中,旨在唤起与读者之间的默契。在这两种互文手法的重叠中,我们毫不费力地就能捕捉到小王子的身影。作为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所塑造的最为经典的文学人物,小王子一直是各个艺术领域的宠儿,绘画、电影、时装,到处都有这位小黄毛的身影。流行音乐领域同样如此。早在二○○七年,吴青峰就已经将《小王子》里的金句引用到《白日出没的月球》一曲:“是你浪费在我身上的时间/使我变得/如此珍贵。”《马拉美的星期二》同样邀请了这位文学大咖,在《(……恋人絮语)》中,吴青峰直接引用了《小王子》的法文片段,颠倒了小王子与玫瑰相遇、相识与离别的情节,从小王子的离开,慢慢倒回故事伊始玫瑰的苏醒。随着音符的跳动,画面由暗转明,歌中的主角从一开始的绝望与冷漠,不再相信世界的善意,到最后“像个傻子问花瓣/你爱我不爱我”,如小王子般天真,对这个世界仍然抱有美好的想象。对于曾经因为深陷版权之争而对音乐产生怀疑的吴青峰来说,创作正是這样一种遇见,一种被理解,一种恋爱,“你就这样发现了我/认出了我的伤口”。此外,这首歌曲的名称同样来自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同名著作《恋人絮语》,根据吴青峰在歌词里留下的踪迹,我们不难找到对应的那一章“夜照亮了夜”:“夜是黑暗的,但它照亮了夜”,如同这首歌曲的单曲封面,一个黑色的影子伸出双手,温柔地抱住吴青峰,“恋人正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挣扎或是平静下来”。或许词人也没有忘记这本著作的解构意图,机灵地在歌词里写道,“而你将累化作了甜蜜”,他把“累”字拆解成“田”和“糸”,合在一起唱出了“甜蜜”,进行了一场能指的游戏。而在为小王子量身定制的歌曲《(……小王子)》中,青峰没有选择直接引用原文,而是通过暗示的方式,让读者在那些熟悉的语词中发现惊喜。“那个不安的、逃避的、虚空的我/忍受每个日落”,是那个难过时爱上四十三次,甚至是四十四次日落的小王子;“那个想念的、贪恋的、沉迷的我/一片花丛里头”,是那个发现自己爱的玫瑰不过万花丛中的一朵之后,躺在草地上痛哭的小王子;“生命中真正重要的/眼睛看不透”“在你驯服了、解剖了、治愈了我/沧海桑田之后”,是那个遇见狐狸、驯服狐狸并在狐狸那里学会用心看清重要的东西的小王子……就这样,伴着温暖的旋律与真挚的歌声,听众用耳朵重温了一遍《小王子》的精髓。有趣的是,小王子的影子还游荡在专辑的其他角落—与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一同拍摄《(……催眠大师)》MV的地点恰好就在里昂,小王子的故乡!
在互文性的研究中,法国学者热奈特还提出了“超文性”的概念,即通过戏拟和仿作的互文手法来实现对原文的转换或模仿。热奈特认为,“戏拟不是对前文本的直接引用,而是对前文本进行转换,或者以漫画的形式反映前文本,或者对前文本进行挪用”。在《马拉美的星期二》这张专辑中,歌曲《(……醉鬼阿Q)》就灵活地使用了“戏拟”的手法。在读者解码文本之前,词人就已经对歌名中的“阿Q”作出了自己的阐述。吴青峰表示,“阿Q”既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里的人物,又是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更是词人自己—吴青峰的“青”字拼音首字母正是Q。在词人看来,擅长“精神胜利法”的阿Q和不懈追求目标的低智商阿甘都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惧他人眼光的可爱角色。吴青峰希望借“醉鬼”之名,探讨创作者在创作时的沉醉状态,歌颂坚定本心的艺术精神。然而,在鲁迅的笔下,阿Q并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这位受尽欺压凌辱反而自輕自贱的“精神胜利者”,在国人的记忆中似乎一直是以负面形象登场的,被作者拿来批判旧社会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麻木。吴青峰则通过“戏拟”的手法,抓住阿Q在假想中克敌制胜的那份偏执特性,使其服务于歌曲所要表达的“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大主题。歌词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希腊神话“食莲忘忧”的食莲族和“驴耳朵国王”弥达斯被塑造成沉醉自溺、坚守自我的形象;唐代诗人白居易追念往昔的《花非花》和歌颂友谊的《问刘十九》被裁剪拼贴在一起—“花非花/雾非雾/能饮一杯无?”用以描写饮酒场面与醉酒状态;元代戏曲家关汉卿抗衡黑暗社会现实的《一枝花·不服老》经过“戏拟”之后,随着动感的节奏释放出了那份“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念。《(……醉鬼阿Q)》像是马戏团的杂耍表演,各种奇珍异宝抛在空中,令人眼花缭乱。如热奈特所言,“内行的戏拟作家对正在模仿的主体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一位成功的戏拟作家在作品中展示的不仅是他对原作家、作品的理解,而且还有他自己的风格与技巧”,吴青峰在歌词里的巧思并没有把他从别处借来的巧丝织成笨拙粗劣的图案,反倒让那些看似不搭边的元素互相融合得恰到好处。它繁杂,但爽目,豪迈饮下之后,嗝出一片酣醉的快乐。
跳出歌词的绚烂,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何要把歌名搞得如此复杂?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踏上通往词人意图的道路了,或者说,已经伸出双手接过词人的邀请了。吴青峰在采访中表示,歌曲标题的设计是受到了德彪西的启发。德彪西钢琴作品同样带有这样的小标题,特意附在乐谱最后,为的是在表达创作心境的同时,不去限制听众的想象力,让听众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感受作品的魅力,形成自己的“印象”。是的,无论聆听还是阅读《马拉美的星期二》,我们都不是以一种被动的姿态来接受意义,而是通过主动的阐释来参与创作、完善作品。早在一九六八年,罗兰·巴特就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观点,他认为,作者在完成写作之后,不再是作品的主导,文本的众多可能性是由话语来言说,由自身来运作。凑巧的是,也是在马拉美的诗歌中,巴特找到了充分的证据,“马拉美最先试图动摇作者的统治地位,他企图用言语活动自身来取代进行言语活动实践的人,是言语在说,而非人在说,写作不是一种人格行为,其中,只有言语活动在进行,而没有作者‘自我的存在”。读者听见了言语的声音,感受到了召唤,也总想拨动嘴唇说些什么。他要与它形成对话。对话的音律也许合调,也许变调,但只要是和谐的,就不会让言语沉默,就会让言语的传播得到可能。
吴青峰的歌词也不乏被听众玩味的例子。二○一六年,青峰为杨丞琳量身打造了一首词作《年轮说》,作为专辑的首波主打,一经推出便广受喜爱。词人将回忆隐喻为刀,切开树木般的身体,露出一圈圈年轮,诉说着成长之悟。副歌唱道:“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十是寂寞夜里/百是怀了疑/千是挣扎梦醒/万是铁心离开你。”从事件到情绪,数字的递进传达着人生各个阶段的感触。这段书写令许多听众动容,简单几行便启封了窖藏心底的往事。而文字越是简单,就越有解读的空隙,越有供人玩味的朦胧。有人这样理解词作中的数字,“伊始婴儿哭啼/儿时学游戏/散是青春物语/似是碰巧遇见你”“失是寂寞夜里/败是怀了疑/堑是挣扎梦醒/忘是铁心离开你”。这种谐音式的解读为听众提供了另一种美学体验:“伊始—婴儿”“儿时—游戏”“散—青春”“似—碰巧”“失—寂寞”“败—怀疑”“堑—挣扎”“忘—铁心”,时间、情感与事件的连接消解了原作模糊的隐喻,使读者掠过理解的障壁,直接获取记忆的共鸣。这样的解读虽不及原作那般隽永,却为《年轮说》延续了一个崭新的生命,它的身影出现在各大音乐软件的评论区,也收获了不少愿意这样欣赏词作的思绪。
遗憾的是,就算利用再多的篇幅探索《马拉美的星期二》,也只能局限在文字的层面上:我们的眼球听不见奇妙的旋律。流行音乐终究是词与曲结合的艺术,吴青峰的互文之乐既是字里行间的互文乐趣,又是已然形成风格的互文乐曲,它们等待手指按下播放键,等待感性去发掘。或许就像《(……小小牧羊人)》唱的那样:“暧昧如这宙和宇/在我嘴里/在我嘴里。”创作暧昧着文本,解读暧昧着可能,如果遇到一张互文织就的大网,干脆就义无反顾地坠落吧,坠入一个个可能的世界,再用收获的可能去塑造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