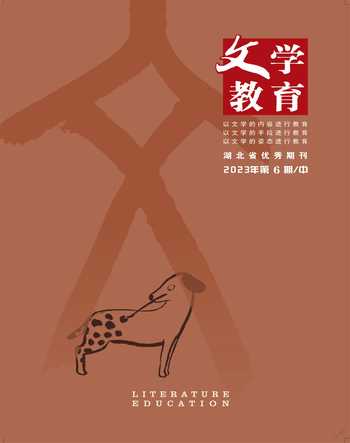独树一帜的夏志清与《中国现代小说史》
张彩霞
内容摘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来一直备受争议,但是作为第一部以语体文写作的史书,在其独特的文学史观、文学叙述和批评之下,通过对文学小说家的重新评价和批评,使一些被传统文学史书写遗漏的作家被重新挖掘出来,从而掀起了一股新的文学浪潮。
关键词:《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文学观 独创性
1961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的夏志清先生用英文写了使其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专著,也是一部开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先河的文学史专著,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此书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关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评论和研究成果卓著,其中并不缺少对于其内在理路和思维拓展的探求,但从1960年代初版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对于夏志清的这本小说史的评论仍是文学史书写领域的一座难以绕过的大山。本文试图从夏志清独特的写作风格入手,分析其另辟蹊径的中西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背后产生的原因,
一.别具一格的书写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分为三编19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姓名为标题,如鲁迅、矛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全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到1957年共40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16个作家及作家的作品,并辑有“附录”和“参考书目”等内容。
1.独特的体例
小说史写作一开始并不在夏志清的考虑范围之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序中夏志清提到“我打算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开头文学各部门都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九册(第十册是《史料索引》)都一字不放过地读了。《大系·诗集》那一册读来实在不对胃口,散文家个别讨论也感到不方便,到后来决定专写小说史,实在觉得新文学小说部成就最高,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虽然我一直算是专攻英诗的,研究院期间也没有专修一门小说课程。”[1]7于是夏志清开始着手准备写一部中国现代的小说史。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以语体文写作的文学史。
面对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一直为学界所争论,并难以有一个规范统一的时间规定,直至今日,仍有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现代小说”时间的跨度有独特的解读。夏志清先生把中国现代小说的时间上限定为1917年,下限则推到了1957年,整个时间跨度为40年。大部分文学史(小说史)的体例特征,是以时间先后顺序为纵向的述史线条,又以作家的流派分为横向的板块,文学史的脉络井然有序,如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解构并不复杂,夏志清把中国现代小说分为三个时期:初期(1917-1927)、成长的10年(1928-1937)和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全书共有19章。《小说史》对一个时代小说整体情况的评述只有5章,却用了14章来讨论作家作品,其中10章直接以作家的名字为标题,进行专章论述,这样的框架体例在小说史中也是富有独创性的。
2.“畸偏畸重”的选择
《中国现代小说史》收录的小说作家共16位,夏志清对这些其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在作者对作家的专章论述中,除了对小说家生活背景的介绍之外,还列举出作家的诸多代表作,并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往往是出自于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渗透着作者自己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但是夏志清对于鲁迅的论述一直遭到人们的质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中对鲁迅的论述篇幅共有19页,而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论述篇幅达到了22页,在中译本中还看不出有很大的差别,照英文本统计,鲁迅只占了28页篇幅,张爱玲却占了43页,在夏志清看来,“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254所以在夏志清完全颠覆了人们一贯的认知,其认为张爱玲的文学地位超过了传统视野中人们认定的“鲁郭茅巴老曹”等名家。写张爱玲的时候,比如写到《金锁记》,他会把最美的四五段文字全部引录下来,而鲁迅的《故事新编》连介绍加评判,只用了五行半。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中说到“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那些我认为重要或优越的作家,大抵上和他们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在技巧上,所持的态度与幻想方面,有共同的地方。然而凭借着他们的才华与艺术良心,因此自成一个文学传统,与仅在左派作家和共产党作家所组成的那个传统,文学面貌时不一样的。”[1]319所以夏志清用较大的篇幅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并把张爱玲放在鲁迅地位之上,说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兼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態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1]257张爱玲文字介乎于旧文体和新文体之间,卫道之士以通俗作家的鄙视眼光评价她。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肯定了张爱玲的旧体新用,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功能。他认为张爱玲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的作品中对白的圆熟和被她摸透的中国人的脾气。
二.中西结合的文学观
1.文学观念的形成
夏志清亲近西方文化,始于中小学时期对电影的痴迷。后来大学时进入英文系研读英诗,醉心于欧西古典,课余精读但丁、歌德、海涅、席勒的诗;毕业在台北任公职时,仅有的休息时间也要阅读西方小说戏剧以及文艺诗评;在北大任助教的时候,更重点阅读英美批评著作与莎翁时代的戏剧,还专门研究布雷克的诗歌,并凭借此成果赢得了留美的名额。后来尽管转而研究中国文学,几十年来却也没有改变对西方文学的“初心”:“英美文学是我的‘first love……我对英美文学,或者广义地说,西洋文学,一直也没有变过心。”而对中国文学,却缺少了发自内心、源于爱好的欢喜之情:“中年读中国文学,与自己的事业有关,动机就不太纯真,不免摆出‘判官的面孔来……笔尖上不带一点情感”[2]。
身为资深汉学家,夏志清对中国文学的传统有充分的了解,但知识上的了解并不代表“真正”的理解,对西方文学由衷的亲近与认同,使他对中国文学及其传统的评价不免有“感情用事”之嫌。他曾写道:“最近常看到学者前辈赞扬我国固有的文化和道德……每读这些文章,我总想起清末民初直至四十年代作家写给我们那些悲惨故事:一个真正代表开明文化、富有仁爱精神的社会,是不容这类故事发生的。”[3]134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序中就有提到:“1952年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凭我十多年来的兴趣和训练,我只能算是个西洋文学研究者。二十世纪西洋小说大师——普鲁斯特、托玛斯曼、乔伊斯、福克纳等——我都已每人读过一些,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于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1]11文学的纯是指它没有实用的目的(宣传、有目的的煽动和直接的行动等),也没有科学目的(提供情报、事实,积累知识等)。对文学功利的追求妨碍了作家对纯艺术的追求,文学应该更关注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心理深度的开掘以及人生哲理的探寻。同时,文学应该关注人性和道德,而不是被功利所左右。他反感左翼作家利用文字来推行意识形态的写作方式,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为了迫切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而放弃自己对艺术的严肃态度的人,是根本不认真为艺术而努力的作家。因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分关注,必然会导致小说对人性和道德的忽视。当大陆的文学史专著以“阶级论”或“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写史的标准之时,夏志清从文学性、人性和道德感情的角度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2.文学批评实践
夏志清批评实践中的中西比较不乏精彩之处,以人道精神、批判眼光出发重审中国文学也的确可圈可点。但是也不能全部采纳他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评价,因为评判的标准毕竟是多样的,不能因不符合某一种特定标准,而连带着中国文化传统一起遭受过度批判。对于本土文学批评而言,用中西比较的方法、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文学文化已然势在必行,但在批评实践中不可一味推崇西方,应在吸纳、借鉴了西方文化思想之后,再回到中国本土文学文化语境之中,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接上血脉。夏志清对于西方文学观念的认识和把握早已内化为自身所形成的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体系,借此建立起中西方文学对话的理论机制。
夏志清四十年代专攻英美文学之时,正是“新批评”文学理论的鼎盛之际。夏志清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对“新批评”的传承,其中尤以“文本细读法”与耶鲁学术精神的影响最大。“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使夏志清受益匪浅,他的文学批评无不以“文本细读法”展开:以精读文本为建立批评的基础,不放过文本最微末的细节,深究作品内部的结构,对意象、情境、暗示、象征、讽刺等等做最细致的分析,进而解读、感受小说情节、语言的张力,对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优劣判断。他为了论述《围城》主题的深刻性,竟将原著结尾一节完整地录入,并指出文中时钟、手表所象征的深意,让读者在细读的体验中进入他的批评思路与作者的创作意图。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也时而可见利维斯式的“传统”建构。他从历史、文化史、文学史中追溯中国文学的源头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将中国文学建构为士大夫文学传统与“新文学传统”,后者包含古今一切具有写实精神、关注世道人心的文学作品,并不以年代为依据。另外,目前很多研究者认为夏志清的“道德批评”也主要受利维斯“大传统”理论的影响。然而早在读利维斯之前,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仁爱精神,基督教精神的美、善道德观念,西方近代浪漫主义对人道主义的宣扬,还有艾略特的人性道德批评标准,莫不构成夏志清文学批评中的道德观念。因此“道德批评”在夏志清的批评观念中早已形成,共同构成其文学文化传统观。
夏志清真率扬厉、毫无学究气的批评风格,与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颇有共通之处。而在价值好恶、叙事结构、道德关怀、入世精神等方面,夏志清对威尔逊亦有所见略同、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情。威尔逊好用比较法,如评论叶芝,便“借”来马拉美和但丁这一今一古两位诗人,让读者明白叶芝的诗中如何拥有“神话象征之中让人理解的世界。”[4]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也是积极入世的“道德批评”,他虽然对几位象征主义大师评价很高,却还是在《城堡》最后一章中流露出对象征主义作品沉浸玄想、脱离人生的失望;另外,威尔逊对文学“真实”的要求与夏志清也是一致的。上述批評特色及观念在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均有迹可循,甚至《小说史》的结构体系都与《城堡》相似,因此将威尔逊作为夏志清的未曾谋面的“知音”,是恰如其分的。
三.独特的意义
夏志清先生通过分析评论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模式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作家论”式小说史的编撰体例,为以后的“作家式”小说史的编撰开创了新的局面,如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继承和丰富了这种编撰体例。
尽管中外各国的语言、文学风格和发生的时间都不同,但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精妙之处是相通的。夏志清对作家的比较是在对作家作品分析评论的过程中,选取恰当的比较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评述。没有比较就无法凸显文学的内在精神,也难以发现上乘的文学作品。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虽然也能看到中外文学的对比,却难以像夏志清一样信手拈来,给予读者开阔的文化视野。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不乏作者对中国现代小说家之间的比较。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小说中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首屈一指,他写道:“钱锺书善用巧妙的譬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相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比较狭小。”[1]259夏志清还比较了20世纪30年代的两个主要长篇小说家——老舍和茅盾,他认为茅盾的文章用字华丽铺陈,老舍笔下则是地道的北平方言;老舍代表北方和个人主义,而茅盾择优阴柔的南方气;茅盾善于写女人,老舍小说中的主角往往是男人;茅盾很早就转向共产主义,而老舍在1937年写《骆驼祥子》之前,一直忠实地相信一个比较单纯的爱国信条。作家之间的对比在经纬分明的文学史著作中往往难以看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没有遵守传统文学史写作的体例,而把现代小说家们放在一起做比较,让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的小说的发掘、论证和高度评价,让国内文学界开始关注张、沈、钱三位小说家的作品,因此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或许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热。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夏志清.《鸡窗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4]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广西职业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