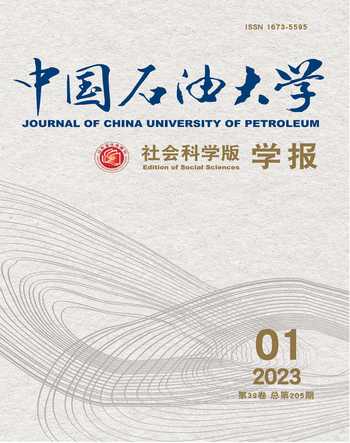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与计算
李佩哲



摘要:《民法典》实施后,惩罚性赔偿扩展适用至生态环境侵权领域。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颁布,为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一定依据,但具体适用规则仍不完善,司法实践状况不理想,存在类案不同判的现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生态环境公益,惩罚性赔偿代表着对侵权者的严厉惩罚,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能否恰当地适用惩罚性赔偿,影响着生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关系。因此,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各个环节都应保持谨慎。在计算环节,应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原则。计算出数额后,应当探索多样的惩罚性赔偿承担方式、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通过完善立法、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等手段有序引导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展开适用。
关键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环境侵权;绿色原则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3)01-0076-08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实施后,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领域得到扩展适用,产品侵权继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商标侵权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扩展到所有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生态环境侵权创新性地适用惩罚性赔偿更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2022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颁布,其中第12条指出,法定的机关和组织也可以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请求惩罚性赔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的決心。但无论是《民法典》还是《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对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都仅具有框架性的指导作用,只是解决了惩罚性赔偿可否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如何适用的问题。然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不同于私益诉讼的公益特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一般更高,在缺乏具体规则指导的情况下,随意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将产生类案不同判的现象,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且可能给被告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当在金额计算、责任承担方式、赔偿金管理等环节加以谨慎考虑,合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作用。
一、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与现状分析
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既包括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包括法律视角下的合法性。但在法律规则的设计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缺乏具体规则指引;在实践运用中,司法经验不足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难以平衡,因此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具体适用问题亟待研究。
(一)正当性具备: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合理且合法
在诉讼信托理论视角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请求惩罚性赔偿具有合理性。诉讼信托理论是指当公众交给国家信托管理的财产遭受侵害时,公众将一部分诉权也托付给国家,国家派出合适的机关或组织代表公众进行诉讼。[1]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院和社会组织为法律授权的机关和组织,其起诉资格由社会公众信托而来。
对检察院而言,检察院的权利来自于人民授权,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维护的是人民群众共同的生态环境利益。
对社会组织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58条,社会组织要想具备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资格,首先应当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其次应当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这足以表明满足起诉条件的社会组织已得到了国家与法律的承认和群众的认可。
因此,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代表了若干被侵权私主体的利益,检察院和社会组织与《民法典》第1232条中的“被侵权人”存在间接联系[2],与私益诉讼原告同为民事侵权之诉的原告,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具有依据《民法典》第1232条之规定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权利。
从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分析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也具有合法性。在《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颁布前,可以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进行论证。惩罚性赔偿基于其对不法行为的遏制而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色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维护由私益集合而成的公共利益,并由社会组织和检察院起诉,也具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色彩,与惩罚性赔偿结合适用能够更充分地弥补民法作为私法在打击生态环境侵权问题上的不足。此外,生态环境侵害的后果包括公共环境利益和具体人身或财产损害两种,呈现出损害结果的二元性,将惩罚性赔偿扩展适用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能保证环境侵害二元后果的同步救济[3],更好地体现《民法典》的绿色原则,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颁布后,明确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基数、举证责任等具体问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解决生态环境侵权纠纷的重要途径,因此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该解释第2条指出,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都属于被侵权人,且第12条明确赋予了国家规定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中请求惩罚性赔偿的资格、明确了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由此,检察院和社会组织作为符合条件的机关和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二)制度状况:具体适用规则尚不完善
虽然从《民法典》以及《环境保护法》中可推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备起诉资格的社会组织和检察院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但是,《环境保护法》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以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7章作为生态环境侵权纠纷请求权基础的来源,都未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在其他生态环境单行法中,也没有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一方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内的大多数生态环境单行法颁布时间早于《民法典》,在这些法律颁布时,惩罚性赔偿尚未扩展运用至生态环境侵权纠纷中;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单行法往往以政府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管控为主,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对民事生态环境侵权纠纷的解决关注较少。
《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颁布,为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的适用指明了方向。由于公益诉讼案件仅为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的一部分,而该解释主要在整体上对所有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的共性问题作出了解答,因此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具体适用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相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等单行法,在产品侵权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关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具体规定①,《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仍是片面的。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未来还应着力解决金额计算、责任承担方式与赔偿金管理等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生态环境的特点,对现有的框架性规则进行填充,有序推进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三)实践状况:司法适用少且具体做法不统一
在法律依据欠缺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侵权中的司法适用不尽如人意,司法机关难以探索出统一的适用规则。与生态环境侵权相比,产品侵权领域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已较为成熟。在威科先行数据库中进行检索②,将生态环境侵权和产品侵权的有关案例进行统计与对比(见表1),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的司法实践现状。由表1可知,在民事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无论是私益诉讼还是公益诉讼都很少适用惩罚性赔偿,与产品侵权案件存在很大差距。在该数据库中对2021年裁判的相关公益诉讼进行检索后发现,独立起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真正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案件有3个,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中真正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有3个,对这些案件中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适用情况进行统计(见表2)。由表2可知,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不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具体计算标准、赔偿金管理方式存在不同,有些法院甚至对判决理由和计算原则、管理方式避而不谈。
此外,惩罚性赔偿实际上是对“同质补偿”的突破,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盲目适用可能产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难以平衡的问题。2014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判处6家污染企业承担1.6亿元具有惩罚色彩的天价赔偿③,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看,环境公益诉讼的直接救济对象为环境本身的损害,而非具体的人身或财产损害[4],涉及人類整体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问题,使侵权人承担高额赔偿具有合理性。但由于只有当被告故意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结果时,原告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此时修复生态环境的成本已比较高昂,盲目适用惩罚性赔偿将给被告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
因此,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充分考虑现实情况,明确具体适用过程的计算原则、赔偿金承担与管理问题,选择合适的规制路径,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中寻找恰当的平衡点。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计算的原则
《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对环境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计算作了具体规定,而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计算,该解释只在基数上作了具体规定,其他方面仅有第12条以“参照前述规定”的形式作出准用性规定。“参照”一词表明,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可以借鉴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某些适用规则,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照搬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式。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计算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惩罚性赔偿本身的功能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由此明确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若干计算原则,从而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提供指导。
(一)理解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妥善把握与基数的关系
惩罚性赔偿兼具补偿功能与惩罚教育的功能,补偿功能是实现惩罚教育功能的桥梁。对于惩罚性赔偿基数来说,根据《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9条,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是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数额,往往仅具有补偿功能;根据第12条,在由法定机关或组织提起的生态环境诉讼中,应以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可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利益本身为赔偿对象,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与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不同,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与损害修复等专业性问题,较为复杂、数额难以计算,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惩罚性赔偿与其基数本身的关系。
首先,在判处惩罚性赔偿时,应同时判处被告承担补偿性赔偿。若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仅具有补偿功能,则应首先请求其承担该基数,再请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说,根据《民法典》第1235条,在生态环境责任纠纷中公益诉讼原告人可以请求五项费用,一般来说其中的补偿性赔偿包括三项:(1)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2)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3)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的费用。这三项中(1)(2)两项也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这三项补偿性赔偿一般仅具有补偿功能,而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为惩罚和教育,因此惩罚性赔偿可以与这三项补偿性赔偿同时适用。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认为,补偿性赔偿具有前提性作用,请求惩罚性赔偿应当以补偿性赔偿的成立为前提。[5]因此在被告承担此种补偿性赔偿后,再要求其同时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并非不妥。在产品侵权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判令被告返还消费者支付的金额,对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后,再要求其缴纳惩罚性赔偿金,对其侵权行为予以惩罚和教育,已是产品侵权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时的通行做法。
其次,若基数已有惩罚性功能,不宜再同时判处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能够对不法行为予以惩罚与威慑,此种功能也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但需要注意威慑的适度性,赔偿金额不可过高或过低[6]。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之一,虽具有补偿性质,但由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复杂性而常采用具有惩罚性色彩的计算方法,例如,在环境污染纠纷中采用虚拟成本计算法,在计算出的虚拟治理成本上乘以相应敏感系数;若是捕猎国家保护动物,则按照《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2017年10月25日国家林业局第46号令),判处该动物基准价值相应倍数的赔偿作为生态修复费用。采用这些方式计算出的赔偿基数已经高出补偿损失所需费用,本身已具有惩罚、遏制的属性,此时应当不再同时判处惩罚性赔偿。若同时判处惩罚性赔偿,则会将惩罚性功能过于放大,威慑过度,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是对被告经济负担的加重。
(二)考虑不同生态环境特点,选择适当的区间倍数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司法实务来看,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常运用区间倍数计算法,此种计算法既能够促进个案正义的实现,使法官根据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对赔偿数额进行调整;也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未给法官留下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10条规定,环境侵权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采用区间倍数计算法,惩罚性赔偿数额应为人身损失赔偿金或财产损失数额的2倍以内。但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说,人身或财产损害不是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因此该解释第10条不能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区间倍数的选择依据。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区间倍数亟待明确。武汉大学陈海嵩教授等认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复杂性要求对区间倍数计算法进行进一步细化,根据不同案件的主观恶性程度、违法次数、故意程度适用不同的区间计算倍率。[7]笔者认为,相较于生态环境侵权,产品侵权领域更早适用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其对生态环境侵权中惩罚性赔偿区间倍数的确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产品侵权中,不同类型的产品可能存在不同的区间倍数,例如,若产品为商品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惩罚性赔偿的区间倍数为1倍以下;若产品为食品,则原告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请求被告支付价款10倍或损失3倍的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对于公共生态环境利益的保护,因此需要结合被保护的具体客体,即不同的生态環境利益来确定区间倍数。在生态环境这一上位概念之下,水环境、大气环境等下位概念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确定区间倍数时,也应当考虑所涉及不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在环境单行法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应当适用的不同区间倍数。
(三)兼顾侵权者合法权益,多责任竞合时整体考量
在民法领域,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7章的规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可以通过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种方式进行诉讼。在民法领域之外,行为人还可能面临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等财产性处罚。可见,同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行为可能存在多个责任的竞合问题。在责任的承担顺位上,《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11条将民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置于其他民事责任之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前。在责任数额调整问题上,笔者认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为了兼顾对侵权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避免给侵权者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不可对多个责任下的赔偿责任数额进行机械叠加。
在民法领域,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的目的并不相同,惩罚性赔偿在私益诉讼中适用时以保护私益为目的;在公益诉讼中适用时以保护公共生态环境利益为目的。因此,同一生态环境侵权问题,同时存在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时,不能用私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直接抵扣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而应在考虑行为人的承担能力后,整体考量赔偿数额。此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不宜兼用,理论上二者的起诉主体存在重合④,可以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部分[8],当同一事实造成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后果进而请求赔偿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重合性,应当只采用一种诉讼请求此种赔偿[9],不应有并存性的叠加或抵扣。
在民法领域之外,有学者指出应当先以行政罚款全额抵扣刑事罚金,再以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中超出损害填补范围的金额按比例抵扣剩余的刑事罚金。[10]实际上,惩罚性赔偿、罚款、罚金的资金归属不同,不能直接采用抵扣的方法。采用整体考量的方法更为合适。[11]在某一领域追究行为人财产责任时,只需将该行为人在其他领域因同一行为被追究的财产责任承担情况作为考量因素即可。例如,美国在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时,若在民事诉讼中已经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认为其认错态度良好,从而减轻其刑事责任,在行政处罚时也可据此酌情减轻。若已经被处以罚金或罚款的,则可以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选择较低的倍数计算或不适用惩罚性赔偿。[12]这也是我国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做法⑤,不仅避免了僵硬抵扣在理论上的不合理之处,又能在实现惩治目的时减轻违法者的经济负担。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承担、赔偿金管理与规制路径选择
数额的确定并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终点,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对生态环境的修护作用,还应重视惩罚性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的灵活性,严格管理赔偿金以保护生态环境,同时通过立法、司法等途径在个案启发下完善规则架构,全过程地合理规制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一)灵活责任承担方式:运用劳务代偿的恢复性司法措施
在生态环境侵权领域,可以探索恢复性司法理念在惩罚性赔偿中的运用。恢复性司法本为刑事司法领域的概念,在环境司法中指的是对破坏的环境采取恢复性的方式进行修复,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13]对惩罚性赔偿来说,司法实务中普遍采用金钱赔偿的方式,但有学者提出,当金钱赔偿难以执行时,可以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寻求“补种復绿”等替代执行方式。[14]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也明确指出,原告请求被告修复生态环境,被告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民法典》实行后,在2021年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青岛市崂山区某艺术鉴赏中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市检察院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⑥,并根据诉讼双方的协商情况,判处被告以参与生态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部分惩罚性赔偿,指出若在规定期间内没有完成相应劳动,则仍应以金钱方式承担该惩罚性赔偿。可见,我国不仅在理论上对劳务代偿惩罚性赔偿这种恢复性司法方式有所探索,也在实践中进行了尝试。
劳务代偿惩罚性赔偿有两大益处。首先,从“成本—效益”分析法的角度,此种方式可以在减轻违法者经济负担的同时,让违法者亲身感受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达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达到“帕累托最优”。其次,
2020年3月,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若适用此办法,以金钱缴纳赔偿金后,赔偿权利人需向财政部门申请,并经过财政部门审核批准,才可将赔偿金用于环保工作以实现环保目的,过程如图1所示;若采用劳务代偿的方法,则可以减少缴纳赔偿金后再申请、审核、使用的繁琐步骤,直接通过行为人自身的行动,更加简洁、直接地实现环保目的,其过程如图2所示。
此外,笔者认为,使用劳务代偿惩罚性赔偿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劳务不应作为金钱赔偿无法实现时的第二选择,而是应该将金钱赔偿和劳务代偿作为并列的两种选择。即使有能力履行金钱赔偿,若经过协商,行为人有意向并承诺以完成劳动的方式进行赔偿,就应当尊重意思自治、鼓励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提高行为人参与环保工作的积极性。第二,只能以劳务代偿部分惩罚性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往往数额巨大,通过劳务代偿全部惩罚性赔偿是不现实的。以前文提及的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青岛市崂山区某艺术鉴赏中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按照青岛市2020年职工平均工资,两人劳动60日仅抵惩罚性赔偿2.4万余元,而该案件中判处惩罚性赔偿的总金额已达到10万元左右。根据《民法典》第1232条,生态环境侵权只有造成严重后果才会适用惩罚性赔偿,此时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往往比较大,全部转换为劳务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对于企业来说可能影响其正常经营,得不偿失。因此,只需对部分惩罚性赔偿采取劳务代偿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能够减轻企业负担,又达到了惩治和教育目的。
(二)统一赔偿金管理方式:作为非税收入上缴国库
《管理办法》⑦明确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损害赔偿金应当作为非税收入上缴国库,由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向财政部门申请使用。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仍存在法律上的空白。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金管理问题上,是否可以直接适用《管理办法》尚不清楚。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管理办法》的印发主体之一,检察系统内的各检察机关在提起生态环境诉讼时,所请求的惩罚性赔偿金也要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应当作为非税收入上缴国库,由财政部门审核、批准赔偿权利人指定的相关部门或机构使用。在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践中的做法通常是被告将赔偿金缴纳至法院账户,再转交给本级政府用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工作⑧或转入该地区的专项环保基金⑨,并非直接由被告交给环保组织,其中专项环保基金并非私人设立,而是由政府或有关环保机关设立。例如,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办法》第2条⑩明确将该办法中的基金定义为政府投资基金。可见,缴纳给政府或缴纳给专项基金是形式不同但实质相同的两种选择,最终都由有关国家机关进行管理。因此,若按照《管理办法》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缴纳的赔偿金,将其作为非税收入上缴国库,由政府部门审核并分配,并非不合理,而是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相统一,便于权威机关更有效地管理使用该赔偿金,提高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工作的效率。
(三)完善规制体系:在《民法典》外选择规制路径
《民法典》属于民事法律领域总领性、概括性的法律,且条文数量已有1 260条之多。若过分细致,会导致《民法典》更加冗长。例如,在侵权责任编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无论是在产品责任侵权、知识产权侵权还是生态环境侵权方面,法条对惩罚性赔偿的表述都仅为“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并未说明惩罚性赔偿适用中应遵守的具体规则。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适用问题,若在《民法典》中作以详细规定则会打破《民法典》概括性、总领性的特点,无法和《民法典》中产品责任侵权、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保持体系上的一致,因此需在《民法典》以外对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具体适用问题进行规制。
在《民法典》之外,主要可以通过其他立法途径、司法途径对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具体适用进行规制,笔者认为此两种途径应当配合使用。首先,对于不同生态环境侵权纠纷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具体认定,应当在相应的环境单行法中通过立法途径进行细化。例如,在《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针对水污染和噪声污染的不同特点,可以适用倍数区间不同的惩罚性赔偿。其次,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定,可以采用司法途径,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典型案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指导。即使法官裁判只对个案具有拘束力,但在诸多个案裁判的作用下,现实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故具体个案实际上在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执行中发挥着确认与补充作用。[15]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指导B11,随后《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于2022年初正式施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供框架性的指导。此外,实践中已有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做法,可以在此趋势下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通过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裁判参考功能,淡化个案审判中裁判者价值偏好对裁判结果的影响,以兼顾司法审判过程中个案的灵活性与类案的统一性。[16]
四、结语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有其正当性。但不同于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倾向于对生态环境公益的保护,赔偿数额较高、确定难度大。目前,对于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导致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式不统一、管理方式不确定,生态环境保護与经济发展难以平衡。因此,需要完善具体适用规则,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的各个过程提供有效指引。一方面,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过程中,应当确定计算原则,通过把握与惩罚性赔偿基数的关系、根据个案选择适当的区间倍数、综合考量可能竞合的多个财产责任的方式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另一方面,计算出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后,应积极探索劳务代偿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展现司法温度的同时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应进一步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非税收入上缴国库,保证惩罚性赔偿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在适用规则的完善路径上,应通过完善环境保护单行法或颁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提供依据,更理性地发挥惩罚性赔偿的惩罚与教育功能。
注释:
① 参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2款、《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商标法》第63条。
② 检索数据库为威科先行数据库,检索时间为2022年4月5日,检索案件的裁判时间范围为2021年全年。
③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环公民终字第00001号判决书。
④ 《民法典》第1234条中生态环境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国家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与《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存在冲突。
⑤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等关于印发〈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应当根据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⑥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法院(2021)鲁02民初69号判决书。
⑦ 参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第4条、第6条、第9条。
⑧ 参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5民初148号判决书。
⑨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初3509号判决书。
⑩ 参见《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办法》第2条,该管理办法所称的基金,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财政通过预算安排资金,单独出资或者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土壤污染防治,支持土壤修复治理产业发展的政府投资基金。
B11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等关于印发〈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参考文献:
[1] 齐树洁,郑贤宇.我国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司法,2005(3):11-14.
[2] 吴卫星,何钰琳.论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审慎适用[J].南京社会科学,2021(9):91-100.
[3] 孙佑海,张净雪.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证成与适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1):26-37.
[4] 王小钢.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3):50-57.
[5] 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122.
[6] 孙佑海.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障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374.
[7] 陈海嵩,丰月.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解释论分析[J].环境保护,2021,49(13):27-31.
[8] 程多威,王灿发.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衔接[J].环境保护,2016,44(2):39-42.
[9] 潘牧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冲突与有效衔接[J].法学论坛,2020,35(6):131-139.
[10] 王冲.《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审视与规制[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5.(2021-10-21)[2022-01-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11020.1812.002.html.
[11] 陈学敏.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制——基于《民法典》第1232条的省思[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6):57-69.
[12] 金福海.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9.
[13] 李挚萍.生态环境修复司法的实践创新及其反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52-156.
[14] 王树义,刘琳.论惩罚性赔偿及其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适用[J].学习与实践,2017(8):64-72.
[15] 吕忠梅.环境法学概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40.
[16] 唐克,王灿发.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妥当责任边界——以美国埃克森案展开[J].求是学刊,2021,48(5):120-130.
责任编辑:姜洪明、康雷闪
Application and Calcul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LI Peizhe
(Tianjin University Law School,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Punitive damages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eco-environmental tort since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e into for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Trial of Cases of Disputes o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rt issued in 2022 provides specific regula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to environment-related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but leaves some to be improved with specific regulations short of applications, judicial practice unsatisfactory, like cases treated differently. Punitive damages, a strict punishment for eco-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means a balance between eco-environmental interest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where applied appropriately. Therefore, punitive damages shall be applied with caution in every respect for th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erms of calculation, make sure of the calculating principles. Once well-calculated, punitive damages shall be assumed differently, managed by standardization and guided regularly by improving legislation, issuing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r guidance notes on case settle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unitive damages;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green" princi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