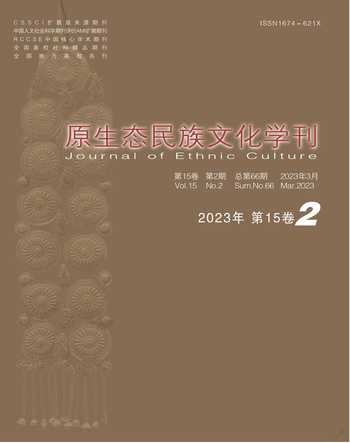变法强秦的政治空间诉求及其空间共同体建构
蒋亚星
摘 要:因政治空间需求而开展的变法强秦运动,对处于低迷发展期的秦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治空间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作为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声誉的重要尺度,政治空间诉求是为国家发展考量的战略基点。秦国面对高强度的兼并态势,以资源 - 空间整合的内政转型和领土 - 空间扩张的邦交博弈,应对于零和博弈的战国丛林。又以编民耕战体制下空间治理的临民理政和族群认同的空间坚凝,构建起大国共同体模式。可以看出,政治空间思维能够促进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适时转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理性面对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变法强秦;政治空间;转型与博弈;空间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2 - 0001 - 12
战国时代,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风行于各国的政治实践中。政治空间成为各邦国寻求生存之本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利益追求。这是因为“政治空间是国家政治与地理空间相结合的产物,是政治生活发展和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1。换言之,政治空间就是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时空范围。在缺乏周王室权威的有效制约下,邦国间以政治权力较量的方式来规避争霸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以追求邦际政治权力的最大化,来实现政治空间的拓展与国家利益的增进。权力谋求渐成各邦国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而寻求更大的政治空间就成了各邦国角逐于政治舞台的最终目的。
内政变法与外交制衡虽作为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存在,但秦国的崛起却显得独树一帜。这源自于秦政治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其转型与博弈的巨大张力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说服力和话语权。以打破血统和地域来重构政治文化共同体,以强烈的领土 - 空间诉求抵抗他国威胁。为此,通过重新审视秦国国家治理的转型与博弈,对变法强秦的政治空间诉求做以探讨,进一步认识秦能并天下的空间共同体模式的建构渊源。
一、政治空间诉求:转型与博弈的联结
变法强秦作为秦国对政治空间诉求的一种道路选择。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精神力量的极大凝聚,来提升综合国力。通过建构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商鞅以法家思想结合秦人的生存环境、民族气质、人口状况、军备状况、外交能力和社会结构等要素进行的制度化改革,实质是秦国国家发展转型和邦际政治博弈的联结。
(一)诉求产生的现实困境
地理空間的争夺与政治权力的谋求,始终是秦人维护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纵观秦国发展史,世居西陲,效力商周。脱胎于戎狄之列,竞争于丛林法则,受周王室照拂而始立国。周天子封秦非子为附庸,都秦邑。庄公伐戎有功,封西陲大夫。襄公护送平王东迁,获封诸侯并“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1。秦国由此享有与中原邦国交往的政治权力和地位。这是秦国凭借周之威望与秦人的勇毅坚韧获得的政治权力。但“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2的现象长期存在。即使经过秦人“以夏变夷”的数代努力,位列春秋霸主,仍不能改变此种状况。面对地多人少,山林材物不能尽其用的惨淡现实。秦国虽在农耕与战事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国内奴隶制的腐朽衰败,愈加深了秦人的民族危机感。“秦僻在雍州”“诸侯卑秦”成为秦孝公布惠振孤寡,广招天下贤士,尊官分土的心理根源和现实依据。
(二)诉求形成的思想根源
变法强秦的政治空间诉求有着秦人“受命”意识的驱使。一方面在于秦人承王室之命保西陲之地,伐戎获胜后拥有宗周故地。于西方立国的秦与周有相似之兴国经历。冥冥中似天意所为的境遇,极大地刺激了秦人东征的野心。另一方面在现实主义的渗透下,秦结合周之天命观念构建起上帝神与人格祖先神二元一体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宗教祭祀的神权体系宣告了秦国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和权威性。秦国成为周王室抵御西方戎狄的依靠,同时又为秦国之东扩披上了谨承天命的合法外衣。故而秦襄公西畤白帝并未遭到周王室的阻止。面对春秋离乱,这有王室寄希望于秦的力挽狂澜恢复旧制,也有秦人并未直接祭祀昊天上帝的因素。周太史公儋曾言:“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3在天命靡常观念与王室衰微的影响下,“太史儋之谶正是周亲授天命于秦之明证”4。这无疑给秦人创造了成就霸业的正当性。
因此,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四帝的祭祀,更多的承载着秦人征伐四方的天命意志。这是对地理空间与政治权力扩张,代周而王霸天下之雄心的神意化。总观遍布秦域的祭祀活动和祭祀对象,有着区域祭祀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特征。正是这样的特征在民间不断渗透着秦受天命之意涵。从而建立起秦人承接周命和构建秦命的意识形态体系。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性信仰、记忆和认同的文化,恰恰是构建秦国国家政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诉求解决的道路选择
变法强秦是秦国意图雄霸天下的道路选择。贾谊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1代周而王何止是秦孝公的雄心,寻求更大的政治空间是秦国历代君主不断描绘的宏图伟业。商鞅以王道、帝道、霸道游说孝公,而孝公独对霸道感兴趣,这实质是历史的选择。秦从附庸国到诸侯国的发展历程,一直竞争于零和博弈的邦国丛林中。霸道之选,有秦人贪狼强力的一面,也有东周之时各国道德仁义尽失的现实压迫。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邦国间的权力之争与综合国力的较量已经成为战国的时代主题。
所以,变法强秦是一种资源 - 空间整合的转型与领土 - 空间扩张博弈的联结。“民族文化特质与独特战略范式的结合,构成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商鞅之霸道是遵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4的宜时权变理念。针对秦国内外交困之现状而制定“循名责实”5“信赏必罚”6的强国方案。为顺应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大整合的趋势,以举国之力提升综合国力促进国家转型。从国家结构、意识形态、行政控御、经济形态等方面布局秦国的霸业之路。在治国理政重心下移的历史趋势下,建构起秦能一统天下的权力 - 制度 - 社会发展的共同体模式。
二、资源与空间整合的内政转型
面对秦国发展的江河日下,商鞅综合分析秦国内外环境,认为国力是邦国间较量的根本。“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7。“力”是一个国家“制度时”“治法明”“国务壹”“事本抟”8的有序发展态势。故此,商鞅变法内政转型的资源—空间整合,以政治整合为核心,经济、社会整合为基础。
(一)法、信、权的政治形态调适
法、信、权是商鞅针对秦国民心不壹、内乱频发、政府无信的国内政治形态,所施行的强秦之计的总纲。“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9。这是将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大权总揽于中央,增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与制约,最终达到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制度建构。法、信、权三者之间互相依赖、相互牵制,以君臣共守共立、君主独制的政治形态模式为运行机制。一方面是商鞅对秦国原有政治生态朝向封建君主专制的改造,另一方面从权力掌控者入手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杜绝对变法可能造成的阻碍。法律作为一种权衡与尺寸,能公平而有效的平抑社会矛盾。信作为官府执政的社会公信力,是法令文武之约的服从。权力从贵族领主收归君主,是君主法令严明的号令如一。缘法而治是秦国内政转型的准绳和依据。因法而抟民气于一,因法而民安其次,因法而集权于君。法、信、权建起秦国政治形态稳固的三角架构。法、信位于底部两端,服务且服从于顶端的君主集权。打破旧贵族中间阶层的世卿世禄特权,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式中央集权控制体系。商鞅变法即是以此为核心对秦国内部政治空间进行的整合。
破“室”集权与行政建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1的法令,虽然表面上看似是“遗礼义,弃仁恩”2的风俗改造,实则是对社会关系结构与权力结构进行的重组。社会旧传统的彻底改造是对国家转型的必然迎合。从风俗习惯入手,瓦解原有经济单位,增加国家对户数的控制。剥夺领主的世袭权力,使社会结构出现跃进式转变。在政治统治层面,设置官僚机构,以地缘代替血缘建立领土国家的郡县制,施行国家对社会基层的垂直化管理。在经济发展层面,强制析产分居,统一实行授田制,统一赋税制度,统一度量衡。从而增强国家对民众的人身控制权和赋役征收权,以达为农战造势的目的。
戒“斗”集军事之权。“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3的法令,将社会治安管理之权以军功赏罚的方式,巧妙的上升到軍事集权。不仅转移社会矛盾,使民众怯于私斗勇于公战,聚民气于一,还保障了君主对民众参战的统一指挥权。在孝公改革之前,秦国陷于长期私斗的内耗中。前有劳动人民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抗斗争,后有新兴地主阶级与顽固保守势力之间的夺位之争。虽然秦献公陆续采取了废除奴隶制、发展封建制的政治经济措施。但这些“新政”并未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商鞅以强制性的法律条令严禁私斗,看似整肃民风,实则转移民斗的视线于邦国之争。把秦人尚武好斗之风改造成一致对外的保国民气。以国家法律的不可抗力压制旧势力,避免其对改革的从中作梗。通过增强秦国内部各族、各阶层的凝聚力,以达到使秦人务本于内,应敌于外的最佳状态。
(二)“利出一孔”的资源整合
“利出一孔”是法、信、权能够发挥现实作用的关键。这是针对君主专制权力结构中的民众,进行的社会化资源整合。战国时期,社会资源的整合以围绕“重地(义)到尽地力”4的转变而展开。商鞅认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5于是提出“民资藏于地”6的解决方案,巧妙地建立起富国强兵与外争国权紧密联系的农战体制。如何实现“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蓄长足”7的农战目标?
商鞅变法的“利出一孔”“因性刑赏”具有现实主义的工具理性。商鞅认为人性有趋利的自然属性和自为的社会属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1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岂有不得民心的道理。作为学术杂家的商鞅正是顺应秦人尤重利、轻伦理的社会性特点,利用趋利性和“自为心”2将秦国民众引入重农战以求名利的发展轨道。“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3。民以尽力垦草不荒而获利,出战取胜为名而致死。于是压制不从事农战者,“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4。使万民所欲之利出于一,农功耕地,军功拓疆守土。因性刑赏、因性利导,使民众由内心及外行的认可和参与到农战中。农耕保障着战事,人力充足着兵源,财税富足着国库。从“自为”到“为国”,进而达到抟民力于一,使民乐战的目的。这是法家利用人性蓄力谋治的精明之处,也是秦国内政转型成功的关键。
三、领土与空间扩张的邦交博弈
春秋时期,领土国家已初具规模,有了较明确的边界划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发,守土拒敌成为各国政治空间变迁的头等大事。商鞅变法强秦的内部政治空间整合与外部领土 - 空间博弈,是在综合分析战国社会发展态势中对秦国霸业的长远谋划与协调执行。“在崛起过程中,国家需要动态执行战略以适应战略主体和客体的各种变化”5。这就需要谋划者根据战略目标适时把握战略节奏,全方位分析战略环境,正确预判战略能力。以适宜的政治制度设计与雄厚的国家实力,保证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战争目标的有效性达成。
(一)东出扩张的布局与动态平衡
秦东出扩张的战略布局把握住了战略取胜的两个关键点:战略的时效性和战略据点的地利优势。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结束,变法强秦取得初步成效。但并非国内转型结束后才开始对外反攻。自公元前359年秦用商鞅变法至公元前350年徙都咸阳,期间经历了秦败韩师于西山、与魏王会社平、与魏战元里、围魏安邑、围魏固阳。6如此频繁的战事,确保了商鞅强秦之计的战略实效性,也为变法暂时争取到稳定的环境。利出一孔、因性刑赏皆需要与战事保持高度一致的内外联动。这有对领土 - 空间扩张战略的动态执行,也有与国内改革步调的动态平衡。进而使得法、信、权的政治机制得到实践的检验,并以立竿见影的效果,将立信于民、刑赏有信落到实处。
第二次变法始于迁都咸阳的同一年,这是孝公与商鞅结合改革后变化了的形势,对战略博弈的再次预判和布局。这次的战略节奏为大举应敌之前的韬光养晦和国内改革的政策过渡。“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1。”迁都咸阳是孝公与商鞅对东出席卷天下的战略布局。秦于西陲立国,深知地理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利弊。数次向东的迁都,皆是以都城为战略据点的空间扩张。关中之地“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2。在战略地位上退可守、进可攻,有东向以制诸侯而高屋建瓴的地利优势。在农耕发展方面,八百里秦川,黄壤优质,水利资源充沛。咸阳所处为国中之腹地,东西南北尽至其辐射扩张的范围,大有坐拥天下,傲视群雄的盛势。农战之利加之变法成效,秦国东出犹如虎添翼。
战略的时效性和战略布局的地利特点,贯穿秦国东征的整个过程。如在东方六国合纵攻秦期间,秦虽应敌于前线,但仍旧考量着统一四海的谋篇布局。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不贪恋眼前利益。以北灭义渠、南并巴蜀、借道攻楚的深谋远虑,为南伐和东进奠定坚实的后方。同时,作为区域民族治理的典范,以羁縻制与郡县制相结合成功地使西南民族融入秦的统治。从而解决了“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3的新领地得而复失的问题。4秦这种差异化的区域治理,何尝不是审时度势与尽地利。因此,战国时代的五次联盟攻秦,两次胜利、两次战败、一次未正面交手。这种战略博弈的动态平衡,未能击垮秦国,反而使其后来居上。从而获得“秦军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5的高度评价。不仅是秦人坚韧、强力的尚武民气所为,更是决策者以全局、长远、纵深的战略眼光,考虑到战略目标与战事环境、国家实力的相匹配所致。
(二)政治空间的膨胀与隐患潜伏
秦国政治空间的扩张,经历了邦国间合纵连横与远交近攻的战略博弈时代。“秦为了拆散六国合纵联盟,对山东六国采取了联合、分化、声东击西、以敌弱敌、间谍、心理慑服、欲取先予、因势乘便等策略”6。凭连横之策,利用山东六国间陷于战争之机,攻占三晋阏与、河间六城、邺、安阳等大片领土,并设置太原郡、东郡。秦国在邦国博弈中,将相时而动与无往不利的邦交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既掌握了邦交的主动权,又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敌国的实力。以至于在政治空间争夺中,获得了“东周君来朝”7,与齐并称东、西帝,以及诸侯“西面事秦”8的邦际政治地位。
秦国政治空间的膨胀始于长平之战后,势如破竹的攻战态势加速了秦统一全国的进程。公元前268年,范雎以“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为秦的统一道路更加指明了方向。他主张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式,避免秦国多方作战,保存国家实力。同时,改“攻地”为“攻人”1的策略,以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公元前256年,灭西周,西周君献其邑三十六城。至公元前221年,俘齐王建,六国皆亡,全国统一。
秦国的邦交博弈和政治空间扩张,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资源。孝公之后历代秦王继续沿着变法强国的路线前行,即使强国之策有所损益,但不出其总纲。秦国与其他六国作战约155次,其中与魏57次、与齐10次、与楚19次、与韩35次、与燕6次、与赵28次。从商鞅变法至统一全国,近140年的时间,作战如此频繁几近无歇,秦国人力不足以致徕民。即使有尚武民气、赏罚激励,但农战体制高压太久反成疲民弱国之弊。这为后来秦王朝的短祚,埋下了刑罚严苛、赋役沉重、人力损耗、心理消极、社会矛盾尖锐的亡国隐患。
四、秦并天下的空间共同体模式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2。孝公变法强秦的政治空间诉求是秦并天下之帝业的开端。帝业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政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态。它是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集中整合,而构成的政治空间层面的命运共同体。秦国在由王国向帝国迈进的过程中,农战体制和民族治理的羁縻创制,有超越时代的政治意义。农战体制构建起了君主专制的政治权力结构。民族地区的羁縻统治创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空间坚凝的社会基础。秦国在内政改革与民族关系的处理方面,为历代王朝提供了大统一空间治理的政治范式。
(一)君民联结的农战体制——空间治理的临民理政
将“民资藏于地”转变为藏富于国的农战体制,是商鞅变法为秦争夺更大政治空间所采用的切适宜、合国情的强国之策。商鞅对秦国内部政治形态的调适,是对有周一代大一统模式的深刻改造。在理论层面,以君权的集中为核心,建立起一套贯穿政治、文教、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伦理、价值体系。以人治的形式、法治的方式建构起中央与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避免因世襲血缘的淡化,出现中央对地方统御权威的衰弱。在实践层面,战国国家治理的关键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提升国土空间的开发与利用效率。面对秦国地多人少的现状,症结就在国家对农民的支配方式、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民资与地利结合,既保障着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又支撑着国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李治安认为编民耕战“摈弃贵族私人领属,与郡县官僚制配套,构建藉授田、户籍、赋役直接控制役使全体百姓的国家农奴制秩序,进而为君主专制集权提供最大化的社会平台及经济资源”3。由此,秦国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君民联结的编民耕战。这成为“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4。
秦国君民联结的临民理政主要涉及了国家治理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这符合传统大一统的天下观、人伦观和权御观,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社会的一体和政治的一体。1因此,围绕政治空间共同体建设的多维联动与共治,就是“在政治制度与公共生活之间构筑紧密关联而又互动调适的联结机制”2。此处的空间是指“空间要素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空间关系,包括自然关系和利益关系”3。空间治理虽在当代是隶属于空间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一个概念,但这又何尝不是秦国以超越的政治眼光,在抟力于一中对价值与空间的整合。总的来说,在权力本位思想指导下,秦国的政治空间诉求与集权化的制度设计,皆朝向多元一体政治格局迈进。
秦国权力本位的政治空间治理,体现在权力主体由国家本位向君主本位转变,政治形态由西周的封国制向君主专制转变。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直接支配社会经济、社会资源、社会治理。这是封建地主阶级自身发展强大的根本需求,也是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孙闻博认为:“‘农战是君主为使民众提供最大限度赋役而做出的政策设计……强调‘君—民关系的‘农战政策,在更广阔层面建立起新的国家秩序。”4操纵这一切的地权、治权、刑赏之柄皆掌握于君主之手。此种君民关系模式是以土地为中介的联结。凭借“利出一孔”的措施,控制民众生存的资源,将民众固着在土地上。利用军功刑赏为君主构建全国由下而上臣服的政治权力基础。
地理空间是国家政治空间形成和存在的根本性要素。“国家本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国家治理必须确立地理空间思维”5。在君民联结的农战体制中,负责地理空间管理的郡县制是临民理政的现实依托。其通过地域划分与组织民众,构建起层层联系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秦国变法推行的“内史—县—乡—里的行政建制模式”6,加之“令民为什伍”7的基层组织设置,进一步打破了宗法血缘为主的地方管理系统。“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8。中央对地方严密而集权的垂直管理,避免了周代封国制地方坐大的分裂威胁。同时,农战刑赏的捆绑式发展模式,使土地制度由领主所有转变为国家和地主所有。由此,在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地理空间单位三维一体的有机建构下,君主可直接管辖国土上耕战的民众,形成由中央王畿向边疆领土辐射的地理空间新整合。
社会空间表现为在相应地理空间中,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具体涉及了地理环境、疆域大小、人口规模与来源、经济生活、阶级结构、国家制度、法律等方面。1国家治理转型决定和影响着社会转型,这是因为“文化、社会结构根本上是由政治权力结构所设定并强化的”2。秦国变法的社会习俗改造,以缘法而治的强制性,切断封建宗室的血缘政治纽带。用析产分居的形式剥夺世卿世禄的政治经济特权。“弱民,是从家天下角度,即国家立场,对整个民间社会的组织系统及其观念意识进行压制打击”3。从而造成国家行政系统与社会宗法组织系统的二元分离。“家国异构”4保障了战时农战体制以军功刑赏和法治的公权力形式,将社会与国家紧密融合。进而促进了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建构。
文化空间涉及秦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秦国变法后在公共生活领域对意识形态所做的改造,成了秦国空间治理联动的枢纽。其中法治文化与宗教祭祀文化是战国时秦文化圈构建的核心要素。由农战体制而生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5,将秦国社会上下以法治思想进行全方位武装。该政策涉及了思想文化的统一与基层社会秩序的整合,是秦在促进大一统空间坚凝的过程中建构国家认同的产物。6秦国的宗教祭祀文化伴随着空间扩张和华夏认同而形成。其畤祭文化兼具少数民族祭祀特征和中原祭祀文化因素。上帝祭祀系统的完善,代表着“虔敬朕祀”7的政治宗教体制在秦国的确立。畤祭炎黄,一方面在于秦文化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驱使,另一方面在于秦对于政治空间追求的不断膨胀。因此,“畤祭文化的演变过程是西秦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的具体反映,也是秦灭诸侯、代周王而作‘天下共主意念形成的具体反映”8。此外,陈宝、怒特神灵的信奉与祭祀,在民间塑造了秦人族群认同的共同记忆。从民间至国家秦祭祀文化对文化空间的坚凝起到不容置疑的作用。
(二)民族治理的羁縻创制——族群认同的空间坚凝
秦国民族治理的羁縻创制,是农战体制之下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的主要策略。随着秦国征战空间的不断扩张,对新征地的空间坚凝成为秦巩固共同体发展的现实问题。秦人自立国至东出,其疆域的西部、北部、西南部边境,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各色少数民族。为统一之大局考量,避免在东进中腹背受敌并使其服务于秦国,对边疆征服地实行羁縻统治。所谓“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勿急武穷兵,过深残掠”9。秦国用怀柔的方式使各民族从沾沐王化、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到政治认同,拉近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从羁縻属邦管理到郡县一元治理,将各民族置于共同的政治体系中,进而衍生出边疆向中央靠拢的民族内聚力和中央控御地方的国家稳定秩序。
秦国民族治理的羁縻创制脱胎于周代的五服朝贡模式1,形成于秦大一统政治格局中文化、社会多元一体的包容性。其克服地域、族类疏离矛盾的关键之处,在于东周时民族观从夷夏之分到天下一家的转变。战国时代,秦因变法跃居七雄之一,于现实中冲击着“夷夏之防”的觀念。虽然秦人常因贪狼强力的戎狄气质被东方六国诟病,但强烈的族群认同观始终驱使着秦向华夏文化不断靠拢。渡边英幸认为秦国在春秋中晚期已将自己置于君临“蛮夏”的地位。2《法律问答》中“臣邦人”脱离“秦属”称为“去夏”,显然秦以“夏”自居,并视治下的臣邦为“夏”的范畴。3
秦国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治理,具体以纳入秦法系统和爵制系统的行政管辖为核心。云梦睡虎地秦简《属邦律》和《法律问答》的部分内容是秦国对民族地区缘法而治的产物。以法律的形式“对‘臣邦君长的地位、民族身份确认、继承人保护、政治经济利益的保护做了规定”。同时“涉及了属邦内部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秦中央政府对属邦居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属邦内部官吏的职责等”4。正如邹水杰所言:“秦国正是通过立法,赋予属邦管控这些‘秦化蛮夷君长和君公的权力,再通过他们治理少数民族,使非秦人向郡县编户民过渡。”5工藤元男认为“秦依据真、夏子6做出身份区别,其目的不在区别本身,而在于为占领下的六国旧民和少数民族作为‘新秦人编入秦国提供法律手续”7。这种从“真”到“夏子”血统身份的转变,是“世尚秦女”的深层影响。作为臣邦君长、君公在潜移默化中失去政治优待权的隐性“秦化”手段,目的为实现郡县一元化的过渡。秦国对被征服地的民族立法,是其编民耕战体制向边疆地区的延伸。因此,作为构建大一统立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秦政统辖边地民族的法理性依据。
蛮夷君长、君公政治地位的被爵制化是秦国法理性威权树立的又一举措。这是秦参照“‘五服体系的圈层规划由外至内分别是:蛮夷—诸侯—天子”1的关系,来构建臣邦归服、天下共主的不可抗之威权治理模式。在秦领土不断外扩的过程中,对原有周室分封诸侯国的蚕食兼并,从地理空间上更加拉近了中央与蛮夷之间的关系。以“民爵比不更”2、“爵当上造以上”3和保留夷民部族管理权的优待方式,来巩固秦夷间行政上隶属管辖、军事上互不相犯的央地关系。“爵禄之权是君权的象征”4。赐爵是对臣邦蛮夷君长、君公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目的是建立一套以秦国君主专制权力为核心的身份等级秩序。秦官爵合一的赐爵是任官的身份前提,也是由世袭爵制转变为官僚制的序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给少数民族赐爵的制度又脱胎于宗法血缘关系,这又成为蛮夏之间建立族群认同关系的重要手段。
当然,族群认同的关键在于族群本身所具备的社会化共性特征。马克思·韦伯对族群的定义影响巨大,他认为“某种人类群体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因为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是因为对殖民或移民的历史有共同的记忆,而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5。“共同的世系”“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共同的记忆”这些构成族群的基本特点,符合司马迁《史记》历史书写中五帝世系的华夏民族标准。“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6,进入中原、“华夏”者,必定进入该历史系统。由此反观秦国在笼络少数民族不生异心的羁縻治理中,渗透着“以夏变夷”的大一统民族观。采用间接而缓和的“因俗治俗”的方式,保留和认同各民族文化生活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政治统治上寻求统一和一元化。目的是为在族群认同的族际融合中,达到政治共同体建构的空间坚凝。
五、结语
在一个兼并战争频发、激烈博弈的时代,能否充分利用国家治理的效能实现成功转型,并为国家的外部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这不仅关乎国家眼前利益,更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考量。变法强秦的政治空间诉求并非追求一时的安稳,更重要的是为长远计摆脱兼并的威胁和民族的歧视。发展和维护超越领土空间范围的国家利益,保持国家发展在内政外交中的动态平衡,最终成就大一统的天下格局。“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也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区域,更是衡量一国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声誉的重要尺度”7。这正是孝公与商鞅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所要实现的谋天下的战略发展目标。除了在政治形态调适中具備空间整合的思维外,在以土地为媒介的国土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利用方面,做了政治经济空间发展的综合布局。以立体多维的角度将国家发展的地理、人文、社会等空间,进行多方位的联动共治。同时,在秦国国家内部空间格局的坚凝中,统治者认识到以统合代替威权统治的民族关系对大一统格局形成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对“大一统的地理观、大一统的政治观、大一统的思想观以及大一统的民族观的华夷一统”1,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重要过程。
当然,秦国统治并天下的可能性在于对权力和资源的绝对垄断和掌控。商鞅变法以举国之力为改革之速成,表现出贪狼强力的一面。战时体制下的制度设计以权力为本位,以法律为手段,以刑赏为威信。以“破”和“立”为改革的主旋律,围绕权力结构的建设与运作,支配国家政治和公共生活。有效地解决了领土空间广阔的大国建构与发展的现实问题。空间治理的临民理政,使得君主的权力直接延伸至基层民众的生产生活。家国异构促进了古代民族共同体国家的建构。族群认同的空间坚凝,巩固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避免了被征服地得而复失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但政治统御的权力至上、经济发展的简单粗暴、文化发展的片面偏激、社会治理的法治严苛,又造成了过度依赖制度的行政扭曲与违背人情。“离散宗族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2,成为秦汉国家在社会空间治理中短期内无法消解的难题。文化专制无法完全将东方六国的士族群体整合于秦的法家秩序框架内。权力膨胀和滥征徭役,造成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与官民对立。编民耕战体制为秦提供了空间共同体建构的平台与资源,但也因其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与权力专制,为秦国超越时代意义的大一统制度创见打上了暴政的烙印。
[责任编辑:孟凡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