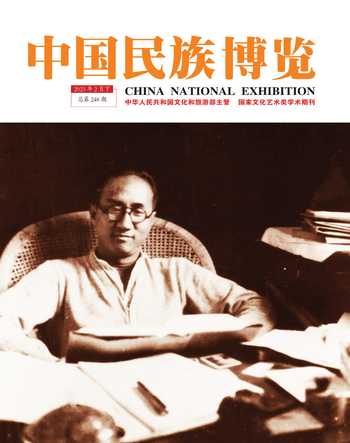语境顺应论下的中国文化英译译者主体性探究
王 君
(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维索尔伦将语境划分为交际语篇和语言语篇,指出语篇的动态顺应是语篇运用的关键。语境适应,也就是语境适应,它要求在语言环境和交际环境下进行选择。语言有两大类,分别是上下文和信息通道,也就是信道。“上下文是指逻辑、对比等在篇章中的衔接、话语间的制约(受叙事内容、文体类型、情境等因素的制约)。还有一系列的线性(语言的选取要注重语篇的整体逻辑与联系,按照语序来进行叙述)。”
一、理论基础
(一)语境顺应论
“语言顺应论”是1987年由比利时语用学学者维索尔论撰写的《作为顺应的语用学》一书提出的[1]。《语用学新解》在1999年问世,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维索尔论在《语用学新解》中对顺应论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三个关键概念,四个研究角度。语言顺应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指“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语言选择的三个关键概念是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四个研究角度是指语境、结构、动态性、意识凸显。了解顺应论的相关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语言交际的本质、机制与策略,从而帮助我们达到交际的口的。从维索尔论《语用学新解》中可以看出:
(1)语言的产生与发展,是为适应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所必需的。从共时角度来看,语言的运用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而要实现一定的交际目的,就要适应交际的环境。
(2)语言运用是一种在不同层次上进行选择的过程。它涉及到语音,词汇,语法,篇章,代码,文体等。语言的选择既要考虑到语言的形式,也要考虑到如何进行交际,这就需要对语言的选择进行选择。此外,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说话人不但要选择怎样说,而且要让对方自己去理解。
(3)从根本上说,语言的选择是顺应的。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常常会根据不同的语境来选择自己的语言。顺应理论认为,语言顺应论主要研究语境、结构、动态过程和突出程度。这四个层面构成了四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语言顺应现象的四个维度。
(二)译者主体性与翻译
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作品的译者的工作只是语言间的转移,而译者则只能一昧的按照原文的意思去模仿和进行翻译。译者在整个作品翻译过程中几乎是透明的,与原文相比,翻译成了一种“寄生的艺术”。人们把以原文为基础进行的翻译活动,看作是“复写”,其价值远远超过了译者的语言转化。“文化转向”后,译界对译者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从以源语为中心的翻译理论转变为以译入语为导向的文化学派。翻译学界对翻译主体的理解、操纵、解构主义、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研究视野。
二、语境顺应论下中国文化英译译者主体性的应用分析
(一)顺应心理语境
在心理世界中,交际双方的心理状况是相互适应的,其中包括了交际者的心理世界。精神状态,包括人格、情感、观念、动机、愿望、意图等。说话者的语言选择就是对自己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的一种适应,要实现一种成功的交流,让对方准确地了解它的话语含义,就需要相信对方能够从对方的言语中找到或者推断出对方的语用和顺应性。心理环境与交际对象的精神状态有关。语言是人们日常交流的一种手段,它能从人们的言语中推断出人们的情感、愿望、交际意向,以及人们的性格、态度等[2]。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它是以译者和译者为对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根据所涉及到的各种环境要素,这就是译者所处的心理环境。以《三国演义》的英译为例,译者在翻译《三国演义》的开头部分时,要认真地揣摩杨慎的感情,使之与其心灵相通,并能顺应其心理,最终成为一部好作品。
心理世界的交际意图也是影响说话人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说话人会根据自己的意图选择合适的语言策略,如果说话人可以准确理解受话人的交际意图,并在语言选择时顺应交际意图,也可以取得交际的成功。例如:《红楼梦》中有两个重点描写“空”,把词的意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与不成”是对“长江东去,浪花洗去英雄”的概括。回溯历史,他觉得,无论多少英雄豪杰,都会像潮水一样,随着历史的流逝,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烟消云散,最终成为“空”。罗译文《英雄与英雄》的选词很好地表达了“空”的意思,表达了作者对英雄人物的遗憾。“一坛好酒,一杯好酒。古今有多少,尽在一笑之间。”又一次凸显了“空”的形象。当一个英雄死后,他的成功和失败,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料,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一切都是“空”的。“空”形象传达了作者的空灵、超然的生命观念,而对“空”意象的领悟,则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作家对生命的感悟。罗译文:“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但很难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张译文:Life’s happiness lies: a wine jar, and good company—Doesn’t many a precedent event。小说中的“hang on the lips”生动地再现了主人公对与错的口耳相传的情景。在翻译中,反问句的作用并不在于向读者提问,而是由发问者自己对问题的答案表示肯定,而采用问句只是为了突出句子的内容。作品所使用的反面问句,具有修辞功能,传达出作者的强烈情绪,使其更符合作家洞察世事的心态,无论成功与否,都只是一个笑话。
(二)顺应社交语境
社交世界是指社会环境、交际活动的规范,交际对象并非抽象、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而是社会中的特定个体,其言语行为必须遵守社会和文化规范[3]。语言选择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特定社交场合的制约。社交场合有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之分。在正式场合中语言的选择往往会比较正式、严肃,交际时会选择书面语的语体。在非正式场合中,语言的选择相对比较宽松,可以选择舒适、口语化的语体。例如: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必须要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没有交流的情报,没有意义。”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只关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语言信息和文化意义的转换,则译文必然会失去其精神。“满地皆怨,一枕黄粱重生”出自《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前半句。这首诗表达了“军阀混战,为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枕中记》中有“一枕黄粱”一词,“黄粱”是指黄粱,意思是一夜醒来,发现大米还没有煮熟,原来是“人生虚幻”,后面是“不可能的梦”。许先生把“They dream of reigning but in vain”翻译成了“一枕黄粱重生”。“in vain”这个字确实是“徒劳的、徒劳的”,准确地表达了一种失望和无助。尽管翻译和原文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仍然保持着“一枕黄粱”的含义,并适当地传达了作者的交际意向,使其更好地发挥了翻译的作用。巴恩斯通翻译成“Rancor rains down on men who dream of a Pillow of Yellow Barley”的“撒在地上都是怨气,一枕黄粱重生”。这篇译本表面上是“一枕黄粱”的忠实译本,实际上却忽视了交际维上的适应性处理,从而影响了译本的交流效果。
以毛主席的诗歌来说吧。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把感情寄托在事物上,也就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感。译者必须注意源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创作背景,从而正确地理解意象的含义,从而达到沟通的目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开头的“杨”是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柳”是李淑一的夫婿刘直荀。这首诗把“杨”和“柳”两个字结合起来,不仅体现了诗歌的魅力和美感,还体现了一种惺惺相惜、惺惺相惜的精神,而不是单纯的“杨树”“柳树”。许渊冲和巴恩斯通则把这两个词翻译成“poplar”和“willow”。区别在于,许先生的翻译把“波普拉”和“威尔洛”的缩写成“波普拉”和“威尔洛”,这样既能保持“原作”的形象,也能间接地表达出“巴恩斯通”的意思。但如果没有注解的支持,这种翻译只能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转换,导致读者对其的理解出现偏差,从而使其丧失交际意义。归根到底,“翻译是一种沟通的过程,它是一种沟通的手段,也是两种语言的交流。”为确保信息的等值最大化,两个译者在交际维中进行适应性的选择变换,以适应信息传递,从而达到沟通目的。
(三)顺应语言维度,再现原作美感
维索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选择的原因可能出自语言内部也可能出自语言外部。结构的顺应是指语言各层次的结构顺应。总的来说,结构顺应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选择:一是语言、语码、语体的选择;二是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它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各个方面;三是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它主要包括的是句子的组织、语篇连贯和关联问题[4]。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翻译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审美的再现。翻译是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工作者在接受到原始文本的信息后,首先将其传递给大脑。在翻译过程中,通常的情感形象在翻译过程中被升华为美学形象,并不断地被丰富。译者在成为解释者之前,首先要做一个读者,而在阅读过程中,审美情感会依附在美学形象上,从而使译文得以保存原作的情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翻译过程中的基本信息与审美形象结合起来,对其进行再编码,使之成为翻译作品。一方面,翻译人员要对著者尽忠,对原文进行延伸和延伸。另一方面,译者也要从读者的语言、语用、文化等方面来考虑。作为原文的第一读者,译者常常是与其审美思想最贴近的人,而在这个时候,译者和读者通过审美和想象完成了文本的意义建构。审美意蕴的重建需要译者自身的审美认知,从而使译者成为创作主体。在生态翻译中,译者要正确处理原作、原作者和读者三者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充分利用主体性来理解、解释和再创造。例,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迭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回环曲折,极其险峻。Sometimes it comes up against a narrow section flanked by high mountains and steep cliffs ,winding through a course with many a perilous twist and turn.译者们把李大钊的作品选译出来,并把它放到第一册的首部,除了要传递原文的语言美、汉语的特点外,还要从宏观的翻译生态环境(社会、政治、语言、文化)等角度来调整和选择“译境”,从而达到警示和鼓励的作用。汉语中,词与词、句与句的结合常常没有明确的外在表现,而是以语义的联系为纽带;英语重形合,在形式标记不足的情况下,译文采用了重构法,把短句改成了长句,具有严密的结构和简洁的特点。译本中,译者把“极其险峻”翻译成“回环曲折”,翻译成“perilous twist and turn”,既增加了曲折,又增加了情感,使人能体会到河流蜿蜒曲折、狭窄、凶险、险恶的特点;另一方面,它的运用也很好地弥补了四个字在转换过程中丢失的“音美”,同时也保留了原语的“形美”。
三、结语
在语境顺应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必须对原文的语言环境和交际环境进行深刻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原文的语境,使译文能够更好地表达原文的内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原文、源语、目标语以及其他译者的影响,因而,在语境适应的语境下,译者并非“中心”,因为译者的参与范围过大,而译者与译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健康,当某一方处于优势地位时,另一方被“压制”“颠覆”,必然会影响到这种和谐的环境,从而使翻译工作的开展变得困难。因此译者就是实现平衡源语生态与目的语生态的最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