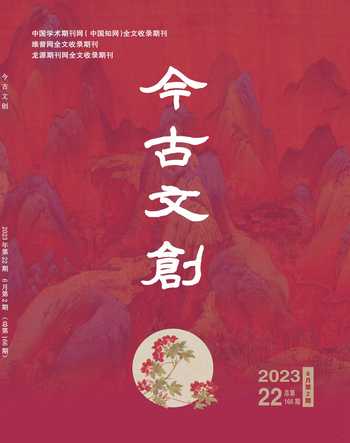《片刻荣耀》中的女性意识解读
李雪松
【摘要】《片刻荣耀》是恩古吉·瓦·提安哥所著的重要短篇小说。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一个在城市酒吧做女招待的乡下女孩遭受压迫和自我觉醒的故事,以此展现女性生存困境和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景。女性意识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该作品中有着生动的展现。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作品从社会现象切入,将父权社会下女性承受的压迫与自我拯救的努力过程展现出来,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艺术价值。
【关键词】恩古吉·瓦·提安哥;《片刻荣耀》;女性意识;压迫与觉醒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22-001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05
一、引言
恩古吉·瓦·提安哥是享譽世界的肯尼亚作家,其短篇小说《片刻荣耀》被收入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的世界文学选集。小说中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从事酒吧女招待的工作,作为黑人女性面临来自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在困境与阴霾中比阿特丽斯反思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最终反叛传统父权社会规则,获得关于自我认知的觉醒。故事以生活中边缘人物的经历为线索,反映出恩古吉·瓦·提安哥对于社会特定群体中普遍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本文从《片刻荣耀》中的女性意识出发,关注女性真实生存境遇,探索女性的生活走向与心灵救赎之路。
二、种族压迫之苦
种族压迫是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其实质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其他种族进行掠夺和奴役。种族压迫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奴隶社会。古罗马帝国将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视作“野蛮人”和“劣等种族”,强迫其服从大罗马帝国。进入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后,白人殖民主义者更竭力散布“人种优劣论”,宣扬为殖民侵略、扩张政策而服务的殖民主义,对非洲的黑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及其他有色人种进行残酷镇压和野蛮掠夺。
种族压迫并不会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而随之消亡,往往转化为一种内在隐秘的形式嵌入民众内心。在《片刻荣耀》中,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一度刻意追随迎合白人审美标准,对于黑人女性的天然美感嗤之以鼻,迷失在黑白之间进退两难。比阿特丽斯在酒吧工作却不得客人眷顾,她将此简单归因于自己黑色的皮肤。于是她涂抹一种名为“阿姆比”的亮肤霜,天真地希望“擦去黑皮肤带来的耻辱”[6]96。“阿姆比”亮肤霜对于比阿特丽斯来说,是十足的奢侈品,她只能少量地涂抹在脸和手臂上,但一些较隐蔽的部位仍然是黑色,这让她觉得“羞耻且恼怒”[6]96。同时比阿特丽斯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众多黑人女性存在自我憎恶这一现象。比阿特丽斯的行为及思想体现出在长久以来的强势殖民之下,黑人女性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渐行渐远,倾向于以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为标尺衡量自己。
比阿特丽斯对于假发的渴求反映出另一重形式的种族压迫。在非洲,黑人女性审美标准和白人女性审美标准共存,但后者处于强势地位,影响众多黑人女性的美与丑审视范畴。非洲女性对头发造型的改变,或是拉直或是染发,都在很大程度迎合白人女性审美标准,她们的最大愿望就是以头发为媒介从身体特征上来接近白人女性。她们之所以如此在头发上下足功夫,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黑人男性。
非洲国家经历过白人殖民统治时期,白人审美使得黑人男性价值标准发生变化,不自觉地向白人审美文化靠拢接近。学者雪莉·安妮·塔特指出审美的种族属性,美与丑的种族话语隐藏在各式各样的美的模式中,“美”是在文化中被演绎的,文化意义上的美就是话语的结果[1]9。比阿特丽斯希望拥有“各种颜色的假发,金色的,深褐色的,红色的”[6]100,“羡慕头上戴着欧洲或印度式假发的女孩”[6]95。她作为酒吧服务生,对于假发种类的需求量本不该如此之多。比阿特丽斯每多拥有一顶假发,便是她靠近黑人男性的一步跨越。比阿特丽斯的假发喜好暗示出自己的种族身份和男性审美偏好,此时头发已经超越生物意义上的身体体征,成为比阿特丽斯获取男性目光与焦点的有效工具。可悲的是,在此过程中比阿特丽斯不自觉地落入白人审美拥有者——黑人男性的价值取向之中,沦为盲目追逐外在实则深陷种族压迫泥淖的羔羊。
三、性别压迫之痛
性别压迫是种族压迫的变种与支撑,二者相互独立又犬牙交错,形成复杂多变的压迫系统。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写就这样一段带给众多女性主义者以启示的话语:“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4]72
恩格斯对女性地位和生存境遇予以深切的关怀和思考,但现实中仍有众多女性长久地囿于性别压迫之下难以逃脱。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同时兼具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双重身份,而以女主人公比阿特丽斯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则永远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承受痛苦和磨难。比阿特丽斯的动荡人生是男性对女性压迫的真实写照。比阿特丽斯家境贫困,中途辍学,不擅长打字和速写,缺乏基本工作技能。向往大城市生活的比阿特丽斯被一个年轻男子骗至酒吧,她透过酒吧看见被霓虹灯点亮的城市,误以为此处便是梦想开花之所。实际上,涉世未深的比阿特丽斯误打误撞跌入性别压迫的深渊,由此开启噩梦般的人生轨迹。
“那个黎明的许诺让她感到快活而飘飘然”[6]103,一觉醒来,带领她来到酒吧的男人已经不知去处,比阿特丽斯不情愿地拥有新的身份——酒吧女招待。来到酒吧时至一年半,比阿特丽斯从未得到机会回去探望父母。比阿特丽斯“对自己饱受的凌辱和辗转的经历记忆犹新”[6]103,不甘心屈居于此却难以另谋出路。比阿特丽斯的悲惨遭遇正是由男性骗子肇始的性别压迫所导致。
比阿特丽斯作为酒吧女招待,酒吧老板对她轻蔑克扣是性别压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酒吧老板被尼娅古蒂拒之门外后找到比阿特丽斯,对她又是侮辱又是奉承,“方式有些勉强甚至轻蔑”[6]97。在比阿特丽斯疲于招待过多的顾客而略显力不从心时,老板在既不预先通知,也不发放工资的前提下就单方面通知她被解雇。这实际上是在强化黑人女性的“骡子式”存在状态,骡子般的命运规定黑人女性永久忍耐、不停劳作,是性别歧视对女性自我带来的压抑与扭曲。在比阿特丽斯的前期认知中,出卖身体、依赖男性客人以期从其身上获取资源价值是无可厚非的。“她幻想着情人们开着油光锃亮的奔驰双人跑车来接走她,看到自己和他手牵着手走在内罗毕和蒙巴萨的街道上”[6]99。比阿特丽斯甚至在看到“比她更丑的女孩,在临近打烊的时候,被一帮顾客争抢着”[6]94,怅然若失,她渴望自己可以在某一个酒吧中“至少也位居统治者之列”[6]94。这些无一不在言说着比阿特丽斯曾经妄图成为男性群体中炙手可热的一员,把自己生活的前景与希望寄托于毫不相关的男性客人之上,也从侧面勾画出她潜移默化中接受“女性依赖男性,处于从属地位”这一观念。现实给予她沉重而清醒的认识,比阿特丽斯不过是在接受一镑钱后,“充当一位倾听者,一个盛放他满腹牢骚的器皿,充当接受男人一夜负担的容器”[6]102。至此不难发现,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女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带有性别压迫的烙印。在父权制性别规范的不断内化和强制操演下,比阿特丽斯丧失了自我主體意识,质疑自我存在的意义与归属。
四、反叛与觉醒之路
福柯指出,“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 而是指它来自各处”[5]67。压迫与反叛相伴相生,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剥削与掠夺是造成女性反叛与崛起的重要原因。
比阿特丽斯一方面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屡遭欺凌,成为男性寻欢作乐的工具,另一方面在潜意识中追求男性的认可和夸赞,以此作为审美标准与存在价值。正如波伏娃所说,“她们始终依附于男人,男女两性从未平等地分享世界”[7]16。可见,比阿特丽斯长期处于男性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下,落入根深蒂固的传统俗套。
那么比阿特丽斯的反叛意识从何时萌生呢?回顾全文,她的反叛具有阶段性,并不是一蹴而就。首次拒绝老板的无理请求让比阿特丽斯初尝打破既定规矩的可能性。面对老板的侮辱行为,她异乎寻常地对老板身上的一切产生反感。即便老板以送礼物为由,她依旧严词拒绝,违抗“规矩”从窗户跳出,另寻住处。“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奇” [6]97,由此可见比阿特丽斯不甘愿乖乖顺从父权社会,开始萌生探寻自我价值的想法。
在居无定所、漂泊流浪之时,比阿特丽斯想起母亲居住的小镇——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也是记忆中遥远的风景,梦想着“与土地、庄稼、清风、明月同乐;在漆黑的树篱下窃窃私语;在明亮的月光下跳舞相爱”[6]98。在对反叛的认知过程中,个体往往需要通过他者或外部刺激来唤起自我记忆,进而达成对现存状态的批判性否定。
更深层次的反叛发生在偷窃客人钱财之时。这位客人与其他众人概不相同,他身世可怜,生活贫苦。在他自言自语式讲述自己辛酸过往之时,比阿特丽斯竟看到他内心深处存在的“一团火,一粒种子,一朵正被慢慢窒息的花”[6]102。比阿特丽斯以同病相怜的受害者视之,准备同样地将自己的曲折过往与之一吐为快。在动情讲述之后,她被一股莫名的空虚感袭击,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因为“那个男人早就盖着被子睡着了,鼾声如雷” [6]103。在她看来,自己“内心深处的骚动成为他的催眠曲” [6]104,于是比阿特丽斯带着冷酷而坚定的眼神带走他身上五张粉色的新纸钞。此时的纸钞对于比阿特丽斯已经失去平日里金钱交易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对积压的愤怒与受辱的委屈变相疏解。
偷窃举动娴熟自然,仿佛经历过历练一般。这说明比阿特丽斯往常不屑于做此种事情,这一次偷窃是以往数不胜数的内心断裂感集中爆发,是对父权社会加之女性“召唤功能”的否定与抑制。经与尼娅古蒂交谈之后,比阿特丽斯的反叛意识彻底得到释放与肯定。尼娅古蒂勇敢追寻个体解放,为比阿特丽斯摆脱阴霾性的现存状态提供参考与指引。
尼娅古蒂家境殷实,父母笃信基督教,生活在宗教礼仪的繁文缛节之中。最终尼娅古蒂不堪重重规则制约,选择逃离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走向纷繁复杂却享有自由的社会,并将此视为暂时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尼娅古蒂的出逃行为揭示出众多女性悲剧命运之后隐藏的传统父系社会体制。值得庆幸的是,尼娅古蒂拥有强大的精神与内心作为支撑,跳脱父系社会规则架构,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二人的交谈使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借助语言的形式得以传递给比阿特丽斯,赋予后者新生的希望与憧憬。
比阿特丽斯与尼娅古蒂的促膝交谈在房间之中进行,自然而然会使读者联想到伍尔夫的经典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她认为“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2]4。女性想要从“共有生活”中跳脱出来,必须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可以上锁的房间。上锁的房间给人以空间,使人获取思考和表达的自由,是女性得以庇护的安全避难所。在房间中,尼娅古蒂讲述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表明对比阿特丽斯的赏识与吸引。长久以来困扰比阿特丽斯的命题“尼娅古蒂恨我,看不起我”不攻自破。比阿特丽斯从尼娅古蒂的经历认识到身为女性实现自救而非他救的必要性。
黑人女性主义运动初步萌芽于19世纪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洗礼后,黑人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壮大,其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黑人女性觉醒者不断加入黑人女性解放的事业,从多方面入手明确地对黑人女性主体意识进行探讨。比阿特丽斯是黑人女性觉醒者的典型代表,历经对父权社会反叛,达到自我价值与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比阿特丽斯一改往常刻意取悦男性的心理状态,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我的情绪感受。比阿特丽斯在商店给自己购买长袜、新衣服和高跟鞋,走到镜子前,打量全新的自己。服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人内心状态的外化体现,换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比阿特丽斯获得经济独立的开端,也是她理性选择下与过去软弱自我的决裂。面对陌生男性的悦色与欲望,比阿特丽斯勇敢地走出酒店,“抛下没吃完的饭和没碰过的酒”[6]106。在酒吧里接二连三的邀请向比阿特丽斯递来,她不为所动,“却毫不客气地接过他们为她送来的酒”[6]107。酒在特定场合是建立联系、沟通情谊的有效工具,此刻比阿特丽斯拥有拒绝或是接受的权力,将选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自动唱机旁边手舞足蹈的比阿特丽斯,“她的身体是自由的,她也是自由的”[6]107。
关于身体的研究,福柯指出现代权力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对身体的控制”[3]251。当父权统治阶级的欲望对女性实现征服,女性便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与控制权。而比阿特丽斯的身体和自我反抗被动接受书写的地位,勇敢地直面残酷冷淡的命运纠葛,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思考与诘问,颠覆旧有父权制成规,积极进行个人心灵探索与调整,理性思考女性价值和主体地位所在,最终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
五、结语
比阿特丽斯是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代表,打破父权制对女性思想和身体的禁锢。通过对自我价值与主体意识的找寻与坚守,比阿特丽斯勇敢地反抗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坚定信念。恩古吉·瓦·提安哥关于女性命运的书写不仅仅局限于肯尼亚,他反抗压抑人性的传统制度和观念,追求普遍意义上的两性平等和个性解放。恩古吉·瓦·提安哥为女性走出压迫迈向觉醒提供乐观的尝试,为新时代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展示美好的期盼与愿景。
参考文献:
[1]Tate S A.Black Beauty:Aesthetics,Stylization, Politics[M].Routledge,2016.
[2]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3]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钦努阿·阿契贝,C·L·英尼斯编.非洲短篇小说选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