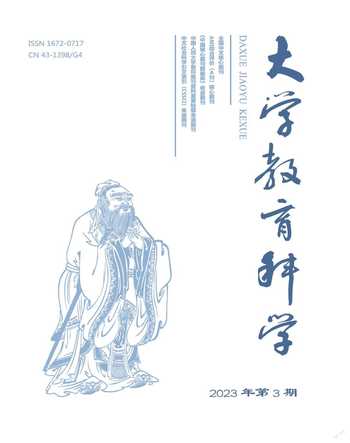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审视与集群化建设
摘要: 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但实践中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国元素”仍有不足。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创造提供了依循。基于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模式,需要在微观上为之提供合理的实践机制,而大学集群治理在价值导向、组织机制、治理主体、文化建构等各维度上集中反映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逻辑,因此是落实新型举国体制的有效机制。这也意味着,探索实施大学集群治理是构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向度。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型举国体制;高等教育治理;大学集群治理;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3-0013-09
“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提供了思想指引,具体到教育领域,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肩负着促进科技创新、自主培养人才和服务国家战略的重任。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而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思想为之提供了根本依循。质言之,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将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但从现实来看,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着诸种局限,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以问题解决为起点,在真诚而深刻的审视与反思中建构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为指导,从新型举国体制的视角出发,探讨大学集群治理新范式,以此作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建设路径,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具体的向度。
一、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审视
(一)高质量发展要求探索建立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模式”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轫自中世纪的欧洲,由此衍生至世界各地,并分化出不同的大学模式,如英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以及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不同的大学模式是普遍的大学组织规律与特殊的本土需求相互作用的产物,探索建立相宜的大学模式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我国而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在移植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阿特巴赫认为,发展中国家依据美、英等工业化国家的大学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具有依附性特征[2]。我国学者则强调,中国高等教育走的是“借鉴—超越”式的发展道路[3]。但不可否认,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都曾在特定时段为我国所学习甚至搬用。经过较长时期的曲折探索,尤其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之基本国策,我国各行业各领域逐渐走上探索自主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高等教育亦启动了以教育规律和大学组织特征为依据、以优化权力与责任配置为核心的本土化探索。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同时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凸显,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逐渐成为改革的中心任务。十八大之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现代化随之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要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高等教育重要论述中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方向[4],而推进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即作为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而备受关注。客观而言,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在长期探索中不断完善,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如吴岩就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5]。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驱动下,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导向,而高等教育亦需要持续推进和实现内涵式发展,为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这无疑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进一步探索和凸显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及其优势。
我们之所以强调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模式”,其一是因为建立本土的大学模式是一国高等教育实现自主发展、创新发展的基础,后发型国家的高等教育必须摆脱依附式发展的束缚;其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必然要求,即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尊重国家体制,并发掘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及中国力量,驱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其三是源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及其模式变革的需要,即从移植到依附再到借鉴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需要对传统模式进行“中国式”的改造和创新;其四是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即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治理需适应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双循环”战略和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6]。概言之,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保障作用。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缺乏充分的“中国元素”
在很大程度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及改革趋势反映了后发外生型高等教育体系的普遍特征,即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或大学的成功几乎都绕不开从“移植”到“改造”再到“创新”这三个发展阶段[7]。虽然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治理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受体制、传统、文化等主客观因素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在本土化创造方面依然存在较多局限。“在我国大学发展百年史中,简单移植、照搬国外经验比较多,根据我国的实践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十分有限,缺乏原创性探索。”[8]质言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國元素”较为匮乏,“跟跑”欧美大学模式甚至试图借用所谓的“国际化”模式来改良本土制度,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思维,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这既体现了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被动性,也隐藏着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扩张中的战略构陷。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以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为基础,走向独立发展、自主发展和创新发展之路。
具体来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国元素”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主体性自觉缺失下对欧美模式的迷思。在一定范畴内,我国大学发展及其治理过于迷信美英等国家大学模式的先进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批判性。例如,教师聘任中的“非升即走”机制,从21世纪初被北大在人事制度改革中较早引入,到如今相当比例的重点大学甚至地方院校纷纷仿效施行,正日益凸显出其伤害青年教师职业信念和专业持续发展动力,加剧学术GDP主义而束缚学术自由、阻遏科学创新的制度之恶。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健全、社会宽容相对缺乏、职业流动存在重重障碍的条件下,我国需对“非升即走”机制进行合法性的再审视或者本土化的再造。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主体需要进一步强化主体性自觉,进而建立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自主探索适宜中国国情、凸显中国智慧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其二,市场竞争的单一化与过度倚赖。在通过市场促进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竞争机制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管理传统,但另一方面,在资源依赖和单一的竞争驱动模式下,大学竞争突破了合理界限,校际零和博弈强化了大学的功利性、自利性和排他性,甚至产生恶意竞争行为,狭隘的利益观致使大学失去应有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同时,过度竞争还增加了高校间的壁垒,在以融合发展为重要特征的当今时代,高校封闭办学致使高等教育的生态性、整体性、协同性效能被严重束缚[9]。如何克服自由主义、市场主义的负面影响,科学设计国家介入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制度与路径,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治理优势,仍亟需深入探讨。其三,量化主义绩效管理的过度泛化。即基于绩效导向和量化技术的院校评估与资源配置制度,使得大学陷入资源依赖和“指标化”办学的陷阱,大学普遍缺乏结构优化、制度创新意识,内涵式发展能力不足。在醉心于“排行榜一流”、沉迷于“漂亮数字”的过程中,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却变得越来越没文化。“五唯”是大学遭绩效主义、评估主义、量化主义肢解的必然结果,是大学“去生态化”和“被工具化”的集中反映,严重阻碍了大学的原始创新和优秀人才培养。绩效、量化、问责和资源的分配捆绑在一起,更加强化了大学的功利性与零和竞争的冲动,使其进一步忘却了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引导大学从世俗乃至庸俗中解放出来,重回追求真理、追问价值的智识世界,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其四,改革主义导向下本土资源的遗弃。所谓改革主义就是以改革为名赋予任何有意义、意义甚微或无意义的改变以合法性,以频繁的“运动”“项目”等来彰显改革的积极性。在“改革主义”影响下,大学陷入“不破不立”的怪圈,本土资源的价值遭到简单化否定。在此,仍以“非升即走”制度为例,该制度的另一端就是近些年甚嚣尘上的“编制废除论”,其基本假设是“编制”导致教师职业投入不足和大学缺乏创新。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编制或许正是反映中国制度特色与文化传统、符合中国大众思维与心理范式并彰显民族智慧的本土资源,其在为教师提供职业安全、强化组织及职业认同、保护大学自由文化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反之,大学教职的高竞争性、高风险性反而会对崇尚自由、依赖自由甚或说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创新机制的学术志业造成压迫。从现实来看,大学的教师管理机制及其背后的基于行为主义的激励约束机制已经对教师学术职业环境形成冲击,影响了教师职业投入。
以上诸点的共同特征是对“中国元素”缺乏充分观照而表现出显见的“欧美痕迹”,这种“跟跑”思维不仅弱化了本土化的自觉与自信,而且消解了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建设。所谓的“国际惯例”或“先进模式”同我国国情产生了种种不适,尤其是“无根”的高等教育治理导致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失去价值依据,这是束缚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效能的根源性因素。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找回”丢失的中国元素,走中国式的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道路。
二、基于新型举国体制的中国式高等 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路
(一)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核心内容和实践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走出一条“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也是一种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路径[10]。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国家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11]。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势表明,现代化将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处于持续的建构之中;同时,现代化不仅反映社会变迁的普遍规律,还表现出基于不同道路、体制与文化的多样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以社会主义规定性为导向,以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为动力,以本土资源(如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以绿色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与格局)、传统精神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出场为基础,并以主体的制度自觉与文化自觉来推动本土资源持续优化,最终转化为现代化建设效能。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否决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和“历史终结”论调,有效消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话语霸权[12]。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宣告我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基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和遵循。因此,要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就必须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构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引导各治理主体在发掘中国智慧中增强现代化治理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恢弘的理论与战略体系,而新型举国体制不仅集中反映了其核心,还为之提供了向实际效能转化的实践机制。所谓新型举国体制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立足于全国改革发展大局,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通过体制机制、政策与法规、战略规划等管理或服务方式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尤其是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动员、组织和统筹协调全国性资源及相关积极因素,集中攻关战略性重大工程项目[1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型举国体制为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根本性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具体来说,其一,在方向上,新型举国体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因而具备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这构成了新型举国体制保持正确方向、发挥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的根本。其二,在立场上,新型举国体制服务于国家和民族事业,旨在提高人民福祉,人民性既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质,同时也确保这一体制能够在获得最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的基础上发挥全局作用。其三,在文化上,新型举国体制强调目标行动的一致性,凸显集体主义义利观,并深刻反映“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宇宙观、发展观和实践观,即强调整体系统、自然协调和相互成就的中国传统文化[14],因为制度只有在文化上契合于人们的价值与思维,才能获得认同从而转化为实践。其四,在实践形式上,新型举国体制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全国资源进行统筹配置和科学管理,优化資源布局,实现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尤其是能够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效调度各种优质甚或稀缺资源,组织社会和市场力量协同攻关,以实现重大突破,可谓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资源配置模式[15]。新型举国体制不仅集中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立场及其逻辑,还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路径,并且对于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觉与自信具有重大价值。因此,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必须遵循新型举国体制的逻辑与指向,发掘和应用这一体制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与中国优势。
(二)基于新型举国体制的中国式高等教育 治理现代化进路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缺乏本土资源的深度发掘和积极转化,难以凸显出应有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优势。因此,要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体系,就必须在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充分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主动进行中国式的本土建构。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和实践载体,因而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遵循新型举国体制的要求,借助新型举国体制来实现高等教育治理创新,最终达成现代化建设目标。
可以说,新型举国体制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价值、思想和行动的框架。具体而言,其一,重塑大学的国家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立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高等教育更是凭借独特的知识生产能力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智力支持作用,高等教育与大学堪为“国之重器”。对于国家来说,需要加强对大学的统一领导,以保障其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主义价值观。对于大学而言,则应明确自身关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加人民福祉的公共使命与人民性立场,进而以此为价值取向,深化制度改革和生产模式创新,不断增强自身的生产力和服务力,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从性质上讲,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大学及其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的重建将引导大学克服功利化、自利化甚至庸俗化之弊病,主动构建以“质量”和“贡献”为取向的办学机制。其二,增强主体自信,深度发掘本土资源价值,促进传统向现代化转化。我国通过学习和移植建立起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但中国大学的持续、创新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从跟跑欧美大学模式的路径依赖或制度锁定中解脱出来,强化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国文化的自信,并从中汲取改革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进步显示,中国当代发展的动力根源主要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而非转向西方世界[16]。比较教育学者露丝·海霍即认为,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必须建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唯此才能跟西方大学进行平等对话[17]。当然,在发掘中国本土资源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客观理性和批判创新原则,促使本土资源转化为科学的、现代化的力量,这是当前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模式的重要方法论。其三,以内涵式发展为导向,强化大学的组织结构优化、制度与文化创新。高等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由资源驱动的外延式战略转向以要素创新为基础的内涵式发展战略。而引导大学由“强竞争”走向新型竞合关系,尤其是强化建立合作共生型关系,以达到协同发展的成效,同时以促进协同为导向,引导大学内外部资源合理流动,在大局、全局范畴内建构有序的资源格局,以实现高等教育场域的生态化,这正是结构优化的核心。在制度建设上,打破单一的、基于绩效与竞争的管理模式,围绕大学强化校际合作与协同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新的院校评价和资源配置机制,则是制度改革的关键。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以合作为取向,通过大学协同关系的建立来克服无序竞争,重塑高等教育生态,符合社会主义体制下集体主义的义利观及以“和合”为特质的传统思维与文化,这为大学通过协同机制实施学科融合、建设交叉学科以及探索跨界融合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文化范式。
显然,上述三个主要向度的探索反映了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逻辑要求。进而言之,新型举国体制以党的领导为根本特征,以国家性和人民性为价值立场,以国家力量为组织动员机制,以资源的全局性优化为作用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内在规范,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重塑以国家主义为标志的大学观和发展观,深度发掘本土资源价值并实现其现代化出场,以协同发展观和传统文化观为指引重塑大学校际关系、建构大学协同发展新范式,提供了意义与行动上的纲领和路线。尤为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权力、责任与利益格局的系统性重构,在此过程中必然要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和阻力,而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力量为组织动员机制,将为改革的深入持续推进提供充分保障。从本质上说,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改革,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引下探索形成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充分释放中国体制效能,进而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
三、集群治理是探索高等教育治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向度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核心,新型举国体制将是充分利用中国智慧解决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难题,进而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依据。但新型举国体制是党带领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程中建立起来的基本体制、基本经验,要将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需要进一步为之提供具体实践机制。本研究认为,集群化大学治理将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有效实践路径,是建设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向度。
(一)大学集群与大学集群治理的涵义阐释
集群问题研究较早出现于产业管理领域。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认为,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地方,能够产生分散状态下企业难以企及的效率,这种基于高效率的外部规模经济促使形成了产业集群[18]。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形成的有机整体。集群从多个方面促进了创新,如集群中的企业由于对客户和其他实体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和沟通,获得了认识创新机会的“窗口”;集群企业能更便利地吸收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参与创新过程,从而获得快速创新所需资源;企业便于同其他组织协调,进行低成本的创新试验等[19]。可见,集群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合作提高效率和增加收益。
產业集群对于区域内教育结构调整具有启示性。从国际上看,英国在20世纪中后期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集群,通过实施资源共享来改进办学质量[20];德国在近些年以协作、集群理念为导向,启动“卓越大学计划”“未来集群计划”,引导大学调动整合资源、统筹把握重点、开展共同协作,以增强其跨界能力、科技转化和知识服务能力[21];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日本东京湾区的“湾区型”高等教育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大学集群化思维[22]。在我国,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正通过组建大学战略联盟等形式加快一体化发展[23],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也正成为我国创新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重要机制。区域内高等教育要素优化组合,显著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和参与地区发展的服务能力。纵观国内外集群思维在教育系统中的应用可以发现,引导学校打破边界限制,相互开放资源,通过资源共享来实现共同利益,这是大学集群发展的第一要义。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之下,资源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大学办学资源不仅仅指传统意义的基础设施、学科与课程、教师等,还包括思维、价值观、文化以及管理机制等。在创新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的背景下,“创新”本身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因而在深度合作框架内,大学合作的资源是全过程、全要素的,这是大学集群发展的第二要义。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并不是大学办学资源的物理相加或等量交换,而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效能的过程。因此,大学集群追求的是增量型收益,甚至期待通过立体化、深度化合作能够创造新的生产要素,例如共建交叉学科、复合型专业以及联合开展重大攻关以实现原始创新及核心技术突破等。因而,创新是大学集群发展的第三要义。大学要走向集群发展,需要进行思想观念及制度体系的重构,即建立大学集群治理体系。
根据集群概念及大学集群发展的三维要义,本文提出,所谓大学集群治理就是以政府和大学为中心的各利益相关主体通过法规、制度、经费、评估等不同手段引导大学以共同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发现和创造共同需求为基础,在办学资源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创造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扩大自身办学收益的过程;通过集群治理,大学走向集群发展新范式,这一范式将促使大学主动开放办学,并在合作中形成有机耦合关系,从而优化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为大学科学办学、提高办学能力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可见,以生态观为指导,以大学校际合作为基础,以协同创新和整体发展为导向的大学集群治理,对于解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过度竞争、校际隔阂、绩效泛化、结构欠优、文化功利等诸种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集群治理之“集群发展”效应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其在保障大学个体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还有利于打造复数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体系,促进解决长期以来重点建设战略导致的院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即推进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而2021年由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就明确体现了通过协同发展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战略思维,提出“鼓励跨校跨机构跨学科开展高质量合作,充分发挥建设高校整体优势”,“充分发挥建设高校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学科合建、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科研互助等实质性合作,强化辐射引领,加快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此外,大学集群治理也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曾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而大学集群治理将有效促进高等教育共建共治,进而实现共同发展、增加共同收益。总之,大学集群治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指导下,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积极作用的有效治理机制。
(二)大学集群治理的实施及其新型举国体制特征
组织间进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存在共同的利益需求、共同的组织目标,大学要走向集群发展,首先要建立共同的需求和目标。而从治理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为大学确立共同目标,创造共同需求,并确保共同目标转化为各大学的发展愿景和制度设计,落实到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另一方面则需要破除阻碍大学合作的壁垒,如本位主义的大学观、重点建设政策与资源驱动发展战略导致的大学资源依赖等。总体而言,探索大学集群治理是一个从理论认识到制度实践进行重塑的过程。
1.价值导向:基于国家主义的使命。从逻辑上讲,大学形成共同需求,建立共同目标,是一个摆脱狭隘的利益观的过程。也可以说,引领大学超越自利主义藩篱的共同目标,应该深刻反映基于大局观的利益观。进言之,大学应充分认识到,大学作为国之重器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公共责任,尤其是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大学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智力支撑是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月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强调的,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而引导大学坚守国家主义的价值立场是大学走向集群发展的根本前提,唯有基于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大义,大学才能脱离自我中心的价值立场和狭隘的利益观,清晰认识到自身追求真理和为国育才的天赋职责,从而意识到实施校际合作乃至建立集群是实现公共价值的有效措施和必要形式。教育在本质上属于文化事业,大学应主要遵循文化的逻辑,体现“善”的价值[24]。而大学的这种“善”首先应是“公共之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所呼吁的,教育是“共同的利益”[25],是“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默示协议”[26]。这意味着,大学摆脱“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束缚而回归至承担公共使命的社会机构,是大学治理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2.组织机制:国家战略需求的牵引。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要求大学围绕现代化强国建设对先进技术和创新人才的需求,深化办学模式和治理机制改革,增强生产和服务能力。同时,这也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导向。比如,从《长三角地区教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协作框架协议》,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都体现着国家通过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思想。而大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秉持生态化思维,积极推进大学校际合作,以大学集群为生产单位,实现协同创新效应。对于直涉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基础性工程,需要突破区域性局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大学集群,为优势资源强强合作、特色资源互补提供载体。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有组织科研”日益成为科学研究模式的新形态,而大学集群无疑为有组织科研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原始创新和“卡脖子”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尤其需要以大学集群为机制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范围内调配优质资源,有组织地进行科研攻关。同样,国家急需学科专业、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交叉学科建设以及大批卓越创新人才的培养等,都有必要突破大學边界,发挥集群的资源集聚和提质增效作用,彰显协同建设和协同育人效能。以国家及地方战略需求为牵引,调动大学实施合作,这是构建大学集群的重要组织机制。
3.治理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主体协同。大学集群的构建与运行需要各级政府、大学及相关机构共同参与。其中,大学是建立集群的直接主体,其自主性、战略性选择是建立集群的基础;高等教育学会等行业性社会组织亦将发挥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产业机构积极参与产教融合,亦将在客观上为大学提供合作的契机。相对而言,政府的宏观统筹作用则更为根本,即通过其元治理为大学集群发展和治理建立起必要的支持系统。具体来说,一是改变量化主义的绩效评价及以此为基础、以学校个体为单位的资源分配机制,逐渐打破大学的“数字化迷信”和“人造壁垒”。二是构建以实质性的“质量”和“贡献”为标准、以实际参与生产创新的主体为对象的新评价体系,引导大学主动加强合作,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同时,以评价机制改革为突破点,优化大学发展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这是大学走向集群发展的现实必要条件。三是对于跨区域大学集群的评价和资源配置,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建立共商机制,合理配置融合发展、协同发展中的权责利,为大学集群的有序运行提供适宜的大环境。四是充分发挥市场的教育集聚功能,即以现代产业的科技与人力资源需求为吸纳机制,汇聚具有相应智力生产和服务能力的大学共同参与产业升级,在客观上形成协同关系,而这需要政府赋予市场主体和大学以足够的自主空间,调动其治理主体作用。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挥政府与市场的联合主体作用正是其基本内容。
4.文化建构:中国文化要素的发掘与利用。文化建设是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文化具有治理性,它能够促使主体积极有效地实施自我监督、自我发展[27],现代化所吁求的主体自觉性从本质上说首先是文化自觉。与作为硬约束的制度体系相比,组织文化更能够促使形成广泛而深度的认同、促进主体行为自觉,因此文化建构在大学集群建设中具有重要治理意义。我国传统文化以融通、辩证和整体为特质,例如“天人协调”“和与中”等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28],在整个社会建构中发挥着根本性规范作用。直至新时代的今天,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保障社会稳定方面都表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在大学治理中,要通过传统文化的“和合”机制促使大學由竞争性分裂走向共建共治共享。具体来说,一方面,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办学及其治理过程,促使管理者逐渐破除大学之间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的种种隔阂;另一方面,通过传统文化的动员、弥合、认同功能,促使重构校际关系、构建大学集群的理想和制度设计成为广泛的价值与行动取向,促使集群发展顺利转化为具体的办学实践。如前所述,大学是文化机构,保存和创新文化是大学基本职能,大学在走向集群发展、探索集群治理的过程中,发掘并运用以“和”为标志的传统文化来促成相互间的融合共生,体现着其固有的性格。
综上,大学集群的建立与治理意味着重塑国家主义的共同目标和价值立场,重新发掘具有整体性、强调和谐观的传统文化力量,由各主体共同推动大学集群建设,同时强调国家保障作用,进而以此为实践机制来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显见的是,这个动员、组织、协调的过程正集中反映了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逻辑,彰显了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集群治理具有高等教育新型举国体制的特征,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实践机制,堪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高等教育治理领域的探索路径。
(三)实施大学集群治理过程中的关系协调
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主要构成,其制度和效能优势源自其科学性,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建立起了相对均衡关系,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充分空间[29]。这意味着,在实施大学集群治理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从而才能更好地反映新型举国体制的科学性和制度优势,发挥其在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其一,统一领导与高校自主创新间的关系。大学集群分为不同属性和类型,如大学自发建立的集群、政府发起组织的大学集群,仅依据大学内在发展需求而构建的集群、以社会目标为导向构建的集群,以卓越为导向的高水平大学集群、以均衡发展为导向的“结对”式大学集群等。当大学集群由政府基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价值而发起构建,政府显然要发挥重要的治理功能,但政府应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协调好统一领导和高校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也意味着,政府作为大学集群治理的元治理者,必须不断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实现其善治的价值。其二,竞争与合作两种发展机制间的关系。实施大学集群治理的首要目的在于强化大学合作,深入发掘大学协同的独特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集群治理绝对否定竞争,其实竞争依旧是其中重要的发展驱动机制,集群治理的要义是在大学之间建构起新型竞合关系,竞争与合作以相互关联的“立交桥”形式共同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30]。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人文的价值引导、法治的理性规制等,促使大学竞争摆脱过度化、无序化,成为哲学家休谟所说的“高尚”的竞争[31]。其三,集群组织与大学独立法人间的关系。大学集群治理是由多所大学构建起来的共同体,其独特价值和功能优势源自这种松散的共同体形式,因而集群成员之间应遵守共同的目标导向,以合作协议为基础采取一致性行动。但大学集群治理要充分尊重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因为大学办学的多样化是形成耦合关系、实现集群合作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大学集群治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提升大学自主办学能力。
四、小结
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与实践要求,从而构成了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价值论和方法论遵循。在逻辑上,我国要构建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必然要充分践行新型举国体制,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从现实来看,要解决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价值引领、政策引导、制度保障、资源调配及文化发掘等维度的独特功能。从事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治理的变革与创新,正是探索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并发挥其制度优势的过程。在当前,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对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建立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的要求,找寻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路径尤显紧迫。而大学集群治理积极建构合作取向的新型校际关系,以协同创新形式适应新时代科技与产业革命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既遵循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也反映了强化国家主义价值立场、彰显统一领导制度优势、顺应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趋势、促进现代性的本土化创造等客观要求,因而构成了实践高等教育治理新型举国体制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 石中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内涵和实践路径[J].人民教育,2022(23):24-28.
[2] [美]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3.
[3] 陈兴德,潘懋元.“依附发展”与“借鉴-超越”——高等教育两种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9(07):10-16.
[4] 胡金波.再创佳绩、争做表率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N].光明日报,2022-05-23(07).
[5] 吴岩.中国式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22(11):21-29.
[6] 马陆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高等教育新使命[J].探索与争鸣,2019(09):26-28.
[7] 邬大光.走出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J].中国高教研究,2021(10):14-20.
[8] 刘献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思想及面临的主要矛盾[J].高等教育研究,2017(01):1-7.
[9] 张继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语境下合作型高校校际关系的建构[J].高校教育管理,2022(04):20-30,40.
[10]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高培通,黄群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经济前景与战略任务[J].经济研究,2022(08):26-39.
[11] [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王铭铭,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75.
[12] 韩保江,李志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挑战与路径[J].管理世界,2022(11):29-43.
[13] 唐皇鳳,徐植.新型举国体制的科学内涵、独特优势与运行机制优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83-93.
[14] 沈湘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J].中国社会科学,2022(08):109-123,206.
[15] 杨承训,徐子健.新型举国体制:资源配置机制和理论创新[J].经济纵横,2022(08):1-7.
[16]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12-114.
[17] 王洪才.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模式:对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文化逻辑解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01):144-152.
[18]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朱志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3-144.
[19]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序言Ⅱ-XXⅡ.
[20] 赵丹,范先佐.以集群发展促进教育质量提升:英国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路径与启示[J].比较教育学报,2022(05):96-107.
[21] 陈志伟,廖智鑫,余烁.德国未来集群计划“研-产-服”特征导向及运行模式[J].比较教育研究,2022(10):58-65.
[22] 陈先哲.从竞争到竞合: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109.
[23] 卢威.治理视野中的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进展、困境与突围[J].大学教育科学,2022(06):34-42.
[24] 王建华.加速社会视野中的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21(07):35-44.
[2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摘要3.
[26] 林可,王默,杨亚雯.教育何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报告述评[J].开放教育研究,2022(01):4-16.
[27] [英]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3.
[28]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
[29] 包炜杰.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历史与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1(05):104-110.
[30] 卢晓中.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竞争或合作?[J].江苏高教,2022(10):1-8.
[31] 杨俊一,等.制度哲学导论: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170.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quires exploring the modernization system of Chinese-styl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However, the Chinese element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l are still insufficient.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practice mechanis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localization creation of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o build a Chinese-styl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practical mechanism at the micro level, and university cluster governance reflects the new model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governance subject,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national system i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implementing the new system nationwide. Thus,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y cluster governance is an essential dimension for building a modern model of Chinese-styl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w national system;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university cluster governanc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