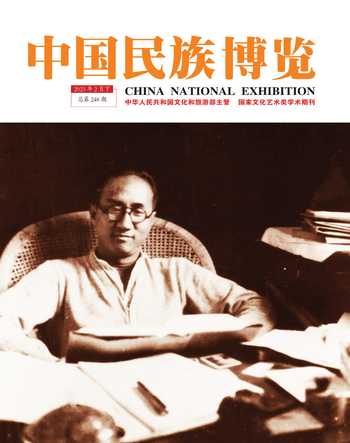湘北澧水的地方艺术生态重构
王晓月 刘鹤翔
【摘 要】河流是人类生命的滥觞,对河流的考察,本身就带着生态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和诉求。当前,河流正在经历从单纯的地理概念向文化空间的转变。从艺术生态学与流域人类学视角,以流域为单位,视河流为人类生活中固有复杂性的媒介,可见出河流与地方艺术的地域性、亲水性及都市文明发展的关系。湘北澧水提供了探讨地方艺术生态从失衡回归平衡的流域文本。
【关键词】河流;澧水流域;地方艺术;艺术生态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4
一、随河流动的文化
从历史到现在,河流的流动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河流是水资源的载体,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自然资源,一座城市有了水的流动,才有了人脉、商脉和文脉。人与水的关系是历史的,古代人类逐水而栖是生存本能,河流为人类提供维持生命必需的淡水,水中生物及农产品的发展带来了食物;人类对于天然河道、河谷的利用是人水关系的进一步延伸,有了便利的水上交通,流动的河流将上下游和左右岸的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整体,群落、城镇因此产生。河流为地方带来了生命,也带来了繁荣,因此,河流流动的不仅仅是水,还有流动的权利,英国学者米森提出“权力也是通过水来获得的”,因为河流“可以促进贸易,而贸易一直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力”。[1]在人类与自然水系漫长的磨合中,地方民众对水的历史认同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形态、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文化习俗。
现代社会中,人与水的关系又是现实的,河流的速度已不再适应现代性交通信息流的快速流转,在水流及其承载的物产上的流动性下降,更重要的是河流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共享的载体。以河流为空间单位的地方文化的形成,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因素的结合,形成于河流两岸的城市,都隐藏了人类文明在河流流动中的历史与经验。现在我们看到的河流,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开放式的“流动博物馆”,虽然往日货船带来的繁荣已不复存在,但城市滨河景观设计以及河段周邊简单却意义丰富的雕塑、石碑,都在讲述着河流的故事,展示着河流的文化。这些具体化的社会文化共享空间,折射出来的是一段流动的历史,一段由流动的人群、固定的土地、流播的风俗等多重要素编织的历史。[2]
二、地方艺术的亲水性
流域是以河流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综合体,自古以来,临水而居、择水而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亲水性的体现。同时,便捷的水上之路为人在空间上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也成为形成独特地方艺术的空间媒介。
澧水是湖南“四水”中最靠北的一条河流,澧水船工号子是其以河流为载体产生的地方艺术最直观的体现。澧县古称“澧州”,这里是湘北通往鄂、渝、川、黔的重镇,在澧水河道两岸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也依附于这条河流。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一座座商行码头、大大小小的商业船只,让湘北地域从荒蛮之地成了商业网络中的重要连接点,伴随着船运商业的萌发,澧水船工号子在明朝中叶产生,与其他号子的功能一致,为集中力量,振奋精神,统一步调而唱。因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澧水不同河段的水情差异与澧水号子的风格特点紧密相连,在桑植以下石门以上的号子,以高亢铿锵短促有力来适应上游高山水急、河面狭窄的水情;澧县至津市安乡一带,由于处于湘北平原,地势平坦、河面宽广,故号子的声腔趋于舒畅和优雅,节奏也放慢许多。并按照劳动需求,形成了装载号子、下水号子、双水号子等不同种类,每一种号子都与劳动类型和自然条件紧密相关。可以说河流既是艺术的媒介,也是艺术表达的载体。
截取澧水船工号子这一水系艺术文化中的每一个片段,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澧水流域古往今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方经历和体验。虽然澧水船工号子在2006年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由于木船运输的社会形态消失、水电站的建立导致河流不再通航,旧时的船工被人们所遗忘,澧水船工号子产生时期的自然环境已成为我们的记忆,号子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其劳动功能难以展示,因此现在对其保护中能做的大多是收藏并保存于博物馆、档案馆中,失去了“活态”发展的可能,但这种有着强烈地方性的艺术形态与文化精神是我们不能抛弃的。
以河流为中心的传统商路上,除了商人与商货的流通,世俗娱乐文化依附于商业经济产生。以地方戏曲为首,在繁华重要的商业集镇中,简易可移动的草台、堂会不断流行,在市集开张和流动中,出现了“赶场”的现象。带着各自乡土文化的外地商人形成商帮、建立客籍会馆,此时地方戏曲除了有娱乐休闲的作用之外,还是调解客商矛盾、团结一心的手段,更为同乡会的商人一解思乡之苦。常德丝弦的形成正与其所处澧水流域和沅江流域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和商业汇集有关,江浙乐师、歌女等往返沅澧之间,武陵山脉一带的武陵戏、澧水流域的荆河戏以及宫调、元杂剧、昆曲等多种曲牌音乐,糅以常德本土的音乐特色,逐渐形成了曲调优美、歌词典雅的常德丝弦。河流的功能区别于山脉,它往往扮演着文化通道的角色,便利的水路通道正是流域内文化沟通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常德丝弦所呈现出的艺术风格不仅是依托在长江流域、沅澧流域中跨区域、跨文化的艺术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四方文人商客繁盛的物质文化交融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多样的空间和丰厚的土壤。这样的一种商业的勾连,其实更是一种文化的错综与流变。
在现代城市中,人们在繁华都市中依旧想从喧嚣的生活回归自然,去追逐静谧的河岸美景,大量公共艺术、特色文旅小镇等仍会选择依附在河边建设,时代在变化,但人与艺术文化的亲水性始终没有变。
三、地方艺术与都市文明
城市和乡村有着当今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其分别塑造的文化类型也各不相同。都市文明更多代表了现代化、科技化的文明,而在地方,百姓视“土”为命根,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常态,使乡土社会的文化富有了强烈的地方性。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土社会的人向城市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不仅是地域空间的迁移和社会角色的变化,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的转化,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的体验。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环境下,都市文明也不断影响、改造着乡村景观。在田野调查中,当汽车驶入常德市鼎城区中河口村村口的时候,远远望去便可看到乡村现代洋楼的墙壁上,粉刷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红色墙面,写着“弘扬扛鼎精神,打造现代江南,建设幸福鼎城”三行大字,仔细观察墙面,依可判断墙面背后藏着被新标语覆盖的旧图绘的存在,墙面标语是乡土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每条不同墙面展示的标语以及被覆盖的标语背后,浓缩的是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乡村社会的发展。
在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的交融互换中,逐步使地方艺术挣脱“土”的束缚和“乡”的限制,它们留下的“种子”以及文化“基因”,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展现出独有的魅力,成为都市文明中新文化产生的动力和源泉。以位于澧水和沅江下游的常德市为例,地方艺术以“非遗”的方式和身份,进入到了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和城市空间规划中。
在常德市文化馆一楼的“常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厅中,占满整个墙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图,展板与资源信息库的建立系统收集了地方艺术,在展厅中可以看到嘉山孟家女传说、桃花源传说等民间文学;听到铿锵有力、节奏统一的澧水船工号子等传统音乐;在多媒体设备中可以欣赏到古今不同的常德丝弦、荆河戏等曲艺,是现代科技赋予展厅生命力,参与式、多样化的参观体验同样也拉近了我们与非遗的距离。
依附于澧水河边存在的河街亦是根植于本地的水文化、船文化、码头文化之上,将历史文脉和城市空间融合设计的。傍晚行走在河街的光影之中,地方特色的建筑以及船夫、曲艺人、工匠人物等雕塑,船夫雕塑、钵子菜与擂茶餐馆等地方文化元素的呈现,“常德网红基地”电商的直播卖场设立以及回荡在耳边的街头艺术表演音乐,不仅让我触摸到远去的沧桑,也让我感受到了非遗带给这座城市的文化力量,是唤醒这片复古建筑物的精髓。
地方艺术在都市文明建设中的融入,不仅体现在上述所讲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和河流景观的规划中,还包含在国际化的展示平台之中。如鄂湘赣皖四省非遗联展、全国非遗曲艺周等,独具魅力的常德丝弦冲破了地域方言的限制走出了国门,在法国巴黎及中澳青少年非遗国际文化交流中表演。
从乡村到城市,从作坊到网络平台,从小众到大众,虽然这些景区、展演及新的销售活动被承载着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使命,但它们却是让地方艺术快速融入到都市文明中可行方式的一种。
四、地方艺术生态的失衡与回归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人们思想观念、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轉变,造成了地方社会环境、艺术功能、创作机制和创作主体等要素的丧失和离散,地方艺术生态系统正处于失衡状态。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学者沈勇提出艺术生态失衡主要表现是“自维持、自调控性降低,开放性、多样性消失”[3]等方面。以澧水流域为例,花鼓戏、常德丝弦、澧州大鼓等艺术形式在地方的保护与创新下,把日常生活变成了表演或比赛,把民俗活动变成了更盛大的晚会,虽然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已经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地方文化的再现,仍然面临着文化自觉意识缺失和艺术多样性下降的困境,地方艺术自行维持生命寸步难移,需要外界力量的推动。当中国处在“非西方式文艺复兴”[4]的阶段,如何完成地方艺术的现代性转化,实现地方艺术生态从平衡到失衡再回归平衡,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在常德市鼎城区中河口村杨府操办的“慈母龙老太君远行”吊唁会中,可发现地方艺术生态失衡最首要的原因。依照习俗,搭台唱戏是必不可少的,而观众无一例外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大片红色袄子与黑色、军绿色的衣服相穿插,统一揣手势的姿态,他们坐着各自搬来的椅子排列在马路对面,在戏曲幕间,几个人相互交谈,有一位老人把手指远远地伸向戏台处,像是说身边就有戏里唱的故事一样。地方丧事中的唱戏环节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的一部分,是生者寄托哀思的方式,而这场花鼓戏的呈现,其观众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感,要远大于花鼓戏保留了其自身艺术功能价值的可喜之处。通过对比常德市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即2020与2010年人口数量,除了武陵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外,其他地区均为负数,全市共减少43.8万人。与大都市相比,人口流动带来的地方空心化与老龄化,是导致地方艺术实践与传承的弱化、观众培养困难、创作人才流失等一系列地方艺术生态失衡表现的首要原因之一。
面对祖辈留下来的“遗产”,虽是已经过去了的、看似静态的东西,但学者方李莉“遗产资源化”路径的提出正是对静态的打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是地方艺术复活的机遇。这一措辞的改变“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新定义”[5]。
探讨现代社会时始终离不开对传统的思考,像湘北澧水流域地区这样以河流为起源的地方艺术文化遗产,一定不仅仅是一个被保存和收集记忆的对象,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当我们再次启动它时,其流动性、亲水性的特点依旧会体现出来。
在文化复兴时代背景下,只有将地方艺术放在现代文化的坐标上来审视,更好地理解传统、重构传统,完成地方艺术的现代性转化,地方艺术生态才可能回归平衡。
五、结语
以河流为单位,地方艺术在空间上是流动的,在文化中是延续的,在社会认同秩序的建立中,又富有浓厚的地域性。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地方艺术生态呈现出失衡的状态,我们需要在传统中寻找正在失去的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性智慧,建立起地方艺术的新形象。“尽管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已经突破了流域的限制,但流域仍然为文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维持着流域生境及生物体的物质和能量平衡,为人类文化的生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源泉。”[6]
参考文献:
[1](英)史蒂文·米森,休·米森,著.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M].岳玉庆,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王健,张应强.河流与人群:清水江流域“散葬”现象的历史人类学探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4).
[3]沈勇.艺术生态批评[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
[4]方李莉.“后非遗”时代与生态中国之路的思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
[5]方李莉.“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6]孟万忠,王尚义.试论流域功能与文化[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7]田阡.流域人类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赵书峰.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J].民族艺术,2021(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澧水流域艺术生态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053320211577)。
作者简介:王晓月,中南大学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艺术文化、艺术史论;刘鹤翔,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特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艺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