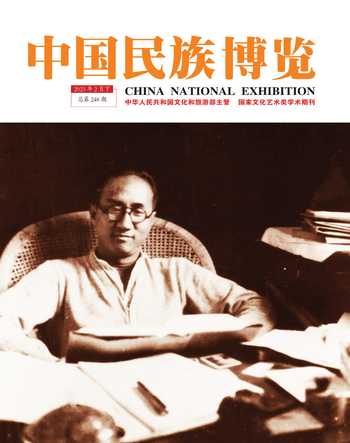《活着》三十年接受研究
朱梦露
【摘 要】本文将从“谁在活着——人物形象内涵与寓托的接受史”“因何而活——小说主旨的接受史”“如何书写‘活着——小说写作风格、手法之接受”三个部分展开对《活着》三十年接受研究的论述,并兼谈人的“塑造”问题。
【关键词】《活着》;接受研究;塑造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4
引言
《活着》作为余华的一部经典代表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92年《活着》首次在《收获》上发表,距今正好整三十年。研究《活着》三十年接受史,既可以让我们对此书有一个纵深的理解与剖析,也可从中窥见人之“塑造”、社会发展的一些现象与规律。
一、谁在活着——人物形象内涵与寓托的接受
首先无可否认,《活着》中从头到尾唯一在生物意义上存活下来的只有福贵一个人。在1992—2022三十年里基本上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是认为福贵是千千万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陈孟、陈煜、王鸿雁《生命之轻与生命之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活着〉比较》(1996年)中这样写道:“福贵寻求的是农民式的朴素真理:和平地生活,自由地劳作。”[1];袁丁的文章《以哭的方式笑——读余华作品〈活着〉》(2017年)中谈到:“反映了作者对几千年来农民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农民生活的同情和悲悯。”[2];贺仲明的《在融合和创新中迈向经典——重读〈活着〉并论余华的文学史意义》(2020年)则指出:“对农民和乡村的认同是《活着》最显著的思想特点。”[3]
但是不同阶段的研究者对于福贵这个小说人物背后所指代的“某一类人”,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活着》中活着的可以是福贵本人、知识分子、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
李湘玲《个人的历史——评余华的小说〈活着〉》(2006年)一文中这样阐述:“《活着》完全是从知识分子的叙事使命和价值出发,对历史进行解构和重构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文本。”[4]认为《活着》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
周良娥的《〈活着〉的文学人类学解读》(2010年)采用文学人类学的批评方法来看《活着》,文章作者认为余华在《活着》小说文本中用芸芸众生中具体的一个的生活经历来形象地再现现代文明的痼疾、并对其进行艺术的批判。[5]
贾小瑞《内心的需要与真理的寻找——余华小说〈活着〉的民族性分析》(2011年)中谈及:“余华90年代创作的内心需要是和自己的民族根性相系的,都可以解释《活着》民族性特征的主观源泉。”[6]认为《活着》具有民族性的特征,将福贵的人物内涵展示出了整个民族的某些精神特质。
李艳丰《从〈活着〉到〈第七天〉——叙事转型与余华主体精神的成长》(2015年)讲到:“余华的小说《活着》无疑具有强烈的个体化叙事症候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持重,是小说《活着》的文化母题。”[7]相对于将福贵的意涵所指泛化的倾向,李艳丰则将福贵的形象突出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强调个体价值。
从这些不同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福贵形象所能够代指的范围时大时小,他可以是知识分子、中国人乃至人类的一个微小缩影,也可以仅仅只是代表他自己。我们以一种更加宏观的角度看《活着》,于是找到了福贵这一形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种普适性,从中看到了全球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当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不断提升,我们开始更多地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活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故事,具有中国烙印,福贵身上的某些特质正是所有活着的中国人身上所具备的。同样是受到世界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将目光从集体转向个体,关注某个人本身的活着。
二、因何而活——小说主旨的接受
对于因什么而活,《活着》的作者余华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他的看法与结论:“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不为别的,为活而活着。”[8]
或许原作者的说法是最为权威的,但是对于文本的解读或许不该仅仅局限于原作者的特殊写作动机之中。因此三十年来《活着》的研究者们对于活着的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正如夏中义、富华的文章《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2001年)中认为福贵是凭借中国古老的生存智慧而活着。[9]笔者也认为研究者们对“因何而活”这个问题,都可以在“中华传统价值精神”中找到相对应的回答。
(一)道家文化中的乐天精神
张梦阳《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2000年)中曾明确点出:“福贵继承并凹显了阿Q的乐天精神。”[10]王达敏《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2003年)一文中也指出福贵是靠着精神胜利法活下来的,但表面乐观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消极无奈的人生态度。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点明:“我以为《活着》是写给那些如今年龄在45岁以上,并且家庭或个人曾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如同福贵一样苦难的人看的,这些大体验过人生的大悲大劫、大苦大难,能于《活着》的简单平实之中读出别样的况味。”[11]
(二)儒家文化中的顽强精神以及对亲情人伦的珍视
唐渊《从余华小说〈活着〉看体育竞技人生》(2012年)中指出人生百态,重在历练,顽强精神很是重要。[12]
郭百灵《残酷叙事中的人性礼赞——余华的〈活着〉赏析》(2015年)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支持福贵活下去的是人性中的真情,是出现在福贵生命中的亲情、爱情以及友情。”[13]
事实上以上所有的观点都有合理之处,因为倘若福贵没有参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没有乐观顽强和命运死磕到底的坚持、没有他生命中曾出现的真挚感情,那么福贵能否依然选择活下来或许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三、如何書写“活着”——小说写作手法、风格之接受
(一)写作手法
1.独具开创性
刘建彬《回归当下——余华〈活着〉重读》(2003年)对《活着》的开创性表示赞同之情:“这部小说在文体上的意义是具有开创性的:作家不再刻意于虚构、设置,采用装饰性、技术性的形式因素,终于结束了一个模仿的时代,开始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学的返朴归真。”[14]刘艳《心理描写的嬗变:由“心理性”人物观到“功能性”人物观的叙事演变——以余华〈活着〉为例》(2021年)点明:“《活着》中几乎完全废止了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描写,将中国新文学自现代以来所重视的小况人物心理描写予以扬弃或者是几乎弃置不用。”[15]研究者认为在文体和人物描写上,余华的《活着》都独具开创性。
李育红《后悲剧时代的来临——从余华的〈活着〉谈起》(2006年)认为:“《活着》标志着当代悲剧叙事的后悲剧时代来临。一方面达到了先锋悲剧叙事的最高点,同时也显露了悲剧精神疲软的端倪和中庸的庸人气息。”[16]贺仲明的《在融合和创新中迈向经典——重读〈活着〉并论余华的文学史意义》(2020年)指出:“中国传统文学写农民,多习惯于居高临下的批判和怜悯,以旁观者的姿态表达同情,很少有平等的姿态,更很少有人以理解、认同的态度去对待乡村。《活着》在平等中蕴含认同的叙述立场。”[17]相对于传统文学写作,余华的《活着》显然具有了明显的敢于大胆书写人生悲剧的先锋意识和突破身份等级意识的现代观念。
2.走向写实、回到日常
对于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事件、细节的捕捉,体现了作家的写实功夫。
徐正龙《看不见的障碍——论余华和张艺谋〈活着〉的差异》(2006年)讲到:“余华对偶然事件比较重视。巧合与宿命之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在《活着》中偶然性得到延续。”[18]同样裘文意在《〈活着〉:精英亦或大众》(2009年)中也谈到:“《活着》中人物的生死无关的时代变迁、只关乎命运的无常。描述个体的偶然性、以个体福贵角度阐述。”[19]
葛丽娅《先锋到现实叙事的演变——余华〈活着〉之我见》(2008年)点出:“《活着》中,余华热切地表现出他对民间话语关注。我们明显感到作记笔下的人物开始挣脱幻想的囚笼。”
叶淑媛《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2009年)表明:“余华由‘先锋转向‘写实,写作转向从形式到内容的复杂嬗变是一种必然,这其中有余华对文学的重新理解。”
杨荣《重返现实:再论〈活着〉与先锋文学的转型》(2014年)认为:“《活着》重返现实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叙事由抽象转向具象,一切都落实到日常生活和基的人生经验之中。”
(二)写作风格
1.重复与否
余弦《重复的诗学》(1996年)中指出:“余华对重复的喜爱体现在不断地叙述重复和主题重复,其叙事技巧的繁复令人佩服,但感知方式的单调却令人惋惜。”
袁珍琴《重新解读〈活着〉——兼谈小说批评的价值砝码》中(2000年)则针对余弦《重复的诗学》(1996年)表达了自己完全相反的见解:“从文本的表现来看,《活着》非但不是重复的诗学,它所用来展现平民命运与历史苦难的生活场景,几乎无一不是选用寻常生活中偶然的、独特的、近乎荒诞的和出人意外的情节。”
2.“雅”或“俗”
金红的《〈活着〉:雅文学嬗变寻踪》中(2005年)认为《活着》是当代文坛雅文学的精品。然而刘兰芳在《〈活着〉——雅小说,俗小说?》中(2005年)却认为《活着》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十分具有娱乐消遣性。
对“如何书写‘活着”的回答同样有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觉,站在不同的位置用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研究者对《活着》这个“书中之庐山”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四、结语
从“谁在活着?”这一问题的答案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年代的研究者会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从不同的角度来解答福贵的象征含义。这里笔者想将社会思潮的变化带给研究者的影响称作是客观条件过滤,历史自有其演进的自然规律,实际上并不受个人的主观意志影响,所以研究《活着》的学者们其实并不能选择出生的年代以及此年代的社会思潮,于是乎他们的研究角度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的社会存在为他们做了选择。
从“因何而活、如何书写‘活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中,笔者提出主观过滤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不同的观点很多都是在同一时代提出的,但是不同的研究者会对《活着》的文本以及搜集到的各种信息加以私人化地处理,他们会主观地加以筛选,最后凝练出一个符合自己价值构造的结论,这便是主观过滤带来的影响。
我们接受的信息被两次过滤,一次是客观条件过滤,命运让我们生于不同的时代,给我们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样貌性别,给予我们不同的客观信息。一次是主观意识过滤,我们选择我们喜爱的,远离讨厌的,过同一百度的推荐新闻都因个性化推荐而人人各异,于是我们每人选择接受的信息有所不同。我们被给予信息,自主筛选信息,最终信息塑造了思维,思维反作用于行为,行为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个体,也影响了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活着》三十年的接受史,既是对这部小说阐释解说的历史,也折射出社会条件和社会意识变迁的历史。
参考文献:
[1]陈孟,陈煜,王鸿雁.生命之轻与生命之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活着》比较[J].学术交流,1996(6).
[2]袁丁.以哭的方式笑——读余华作品《活着》[J].语文建设,2017(3).
[3]贺仲明.在融合和创新中迈向经典——重读《活着》并论余华的文学史意义[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1).
[4]李湘玲.个人的历史——评余华的小说《活着》[A].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汇编[C].2010.
[5]周良娥.《活着》的文学人类学解读[A].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汇编(现代文学部分)[C].2010.
[6]贾小瑞.内心的需要与真理的寻找——余华小说《活着》的民族性分析[J].小说评论,2011(2).
[7]李艳丰.从《活着》到《第七天》——叙事转型与余华主体精神的成长[J].文艺争鸣,2015(2).
[8]余华.活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9]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J].南方文坛,2001(4).
[10]张梦阳.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J].文学评论,2000(3).
[11]王达敏.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J].人文杂志,2003(3).
[12]唐渊.从余华小说《活着》看体育竞技人生[J].语文建设,2012(6).
[13]郭百灵.残酷叙事中的人性礼赞——余华的《活着》赏析[J].理论视野,2015(4).
[14]刘建彬.回归当下——余华《活着》重读[J].齐鲁学刊,2003(3).
[15]刘艳.心理描写的嬗变:由“心理性”人物观到“功能性”人物观的叙事演变——以余华《活着》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5).
[16]李育红.后悲剧时代的来临——从余华的《活着》谈起[J].小说评论,2006(1).
[17]贺仲明.在融合和创新中迈向经典——重读《活着》并论余华的文学史意义[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1).
[18]徐正龙.看不见的障碍——论余华和张艺謀《活着》的差异[J].艺术百家,2006(7).
[19]裘文意.《活着》:精英亦或大众[J].名作欣赏,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