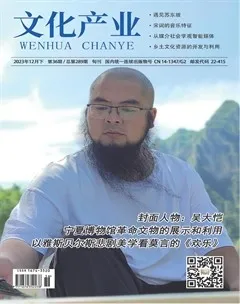解读清代判词
刘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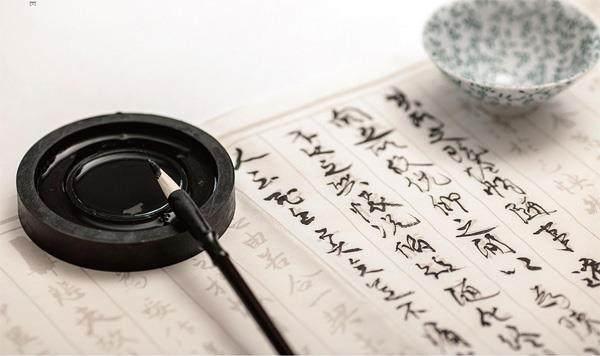
清代是古代判词的发展成熟期,清中期以前传统法治环境下的判词与历代判词相比并无根本变化,且数量、类型和水平均有提高。清代判词继承了古代判词的传统,即使是晚清判词仍具备朴实典雅、引礼入法、追求情理法合一等特点,且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晚清西方入侵对于中国社会与法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一时期的判词试图摆脱衙门式写作,以适应新的法治环境,体现法治精神。
判又称判文、判词、判牍,是古代记录案件审理的文件。比较有名的判词主要有唐代张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百道判》(也称《甲乙判》),五代后晋和凝《疑狱集》,宋代郑克《折狱龟鉴》、桂万荣《棠阴比事》、南宋实判文集《名公书判清明集》等。除此之外,很多文献诸如《全唐文》《文苑英华》也收录了大量判词,《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也收录了一些判词。
唐宋之后,实判创作占据主要地位,文体逐渐由骈入散。明清时期,古代判词逐渐步入成熟阶段,同时空前完备的法律制度促使“专门研习法律、专司公牍文书制作的刑名幕吏阶层出现,产生了专门研究判词的著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制判理论,有力地指导了判词的制作”。
清代判词多为散体实判,且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将这些判词收集起来,便形成了判集。明清时期的判词总数有188种,其中清代判词占很大比重。
在中国古代判词发展史上,清代判词达到了巅峰,这一时期也是古代判词的发展成熟期,主要体现在文学色彩上,即判词老辣简练,精当深刻。从法律精神来讲,清代判词大多依法据礼,将情理法相融合。而清代法治现代化视角下的判词由经世致用演变为中西交会,是共性之下的现代转型。
清代判词的经世致用——朴学的影响
清代经学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朴学影响下的文学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清乾隆、嘉庆时期,朴学文士提倡经世致用,重视考证的求实精神。他们除了经学造诣突出之外,在史学上也有可观的成果。例如,“惟以考史为务”的王鸣盛,他的《十七史商榷》备受学者推崇;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被乾嘉学者称为“巨擘”;还有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崔述的《考信录》等,都为清代经史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清代判词的作者大多为文人士大夫,即使有部分判词由幕僚代笔,但这些幕僚本身也深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因此,清代的判词,尤其是中前期的判词大都被朴学所影响。这一时期的判词仍然极力讲求经世致用。从文学形式看,清代判词大多文风质朴,文体骈散杂糅,不讲究华丽辞藻。
相比唐宋时期的判词,清代判词作者追求判词的司法文书属性,判词充满了实用色彩。当然,清代判词中也不乏文人雅士的戏谑之作,或者受骈文文风影响,刻意追求词采之华美。但总体而言,清代判词注重实际功用,具有司法属性。
语言行文特点
雅俗相谐、文质相生
清代判词的作者大多为科举出身的文士,他们创作的判词语言雅致,行文流畅。但是他们深知作为“父母官”,写出的判词需要雅俗共赏,要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百姓也能看懂,如此才有信服力和执行力。
这里的“俗”,主要指既要行文质朴、语言通俗,也要将一些村言俚语乃至方言、顺口溜等写入判词中;“雅”,主要指遣词用句精练。其中,一代廉吏于成龙创作的判词最为典型,他在广西罗城任职时,留下了著名的《婚姻不遂之妙判》:
“关雎咏好逑之什,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钱万青誉擅雕龙,才雄倚马;冯婉姑吟工柳絮,夙号针神。初则情传素简,频来问字之书;继则梦稳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作东床之快婿。方谓情天不老,琴瑟欢谐。谁知孽海无边,风波突起。彼吕豹变者,本刁顽无耻,好色登徒。恃财势之通神,乃因缘而作合。婢女无知,中其狡计;冯父昏聩,竟听谗言。遂令彩凤而随鸦,乃使张冠而李戴。婉姑守贞不二,致死靡他。挥颈血以溅凶徒,志岂可夺?排众难而诉令长,智有难能。仍宜复尔前盟,偿尔素愿。月明三五,堪谐夙世之欢;花烛一只,永缔百年之好。冯汝棠贪富嫌贫,弃良即丑,利欲薰其良知,女儿竟为奇货。须知令长无私,本宜惩究。姑念缇萦泣请,暂免杖笞。吕豹变刁猾纨绔,市井淫徒,破人骨肉,败人伉俪。其情可诛,其罪难赦,应予杖责,儆彼冥顽。此判。”
于成龙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自然明白判词需要文质相生、雅俗共赏。这篇判词以事实为依据,以说理为主导,同时又兼顾法理。
从文学角度来看,此判词通篇骈散杂糅,大量用典,语言文雅又不乏质朴。只有这样的判词,才能做到语言老辣,文学与说理并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同时还能起到教化百姓,减轻司法执行阻力的作用。
文辞典雅、骈散杂糅
唐代骈体判文文藻华美,而清代判词认为文辞质朴是文学美的一种,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前文提到的于成龙的判词便是骈散杂糅,文质相生。《于成龙判牍》表明清代判词文学迈入新发展阶段,是清代判词文学化发展的范本。于成龙判词文体骈散并用,不拘一格。下面对《代饰新郎之妙判》进行分析。该判词原文如下:
“高贤相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颜俊卿借人饰己,实出奇文。东床已选佳婿,何知以羊易牛;西邻纵有责言,终难指鹿为马。两次渡湖,传书柳毅;三宵隔被,何惭秉烛云长?风伯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于佳女,两得其宜。求妻到底无妻,自作孽也。高氏应断归钱青选,不须另作花烛。颜俊卿既不合设骗局于前,又不合奋拳于后,事已不谐,姑免罪责。所费聘仪,助钱青选作成婚之资,以赎一击之罪。媒妁尤原、言福焘,往来诓诱,实启衅端。各重笞一千,以示惩儆。此判。”
这篇判词叙事说理在先,依法断决于后。前面叙述部分文采飞扬,质朴无华,“东床快婿”“柳毅传书”“指鹿为马”等典故运用得恰到好处;后面说理、判决部分则为散体文,用语简练。这体现了于成龙高超的文学水平,也说明清初判词大体上是骈散并用,不拘一格,文质相生,工于炼字,同时又不乏叙事说理。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判词为了使语言更加灵活生动,更易为人接受,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一些文学手法融入判词写作中,比如唐代的判词文辞雅致、善用典故且对仗工整,既风采雅致又文理兼容。
下面以晚清名臣能吏胡林翼判词为例,略作说明:
“贾祥状告偷盗,樊洪自供强奸。名节虽失,廉耻尚存。不忍掌上明珠,再蒙羞辱;难消心头之恨,告上公堂。虽然所说不实,其心应是可哀。白璧受玷,不是出于本心;贞洁虽失,事情出于无奈。避重就轻,樊洪真是刁徒;倚轻倚重,还想蒙混过去。这般恶棍,心似豺狼,不加严惩,何能示儆。根根木棒,与我重重打来;条条律例,不能把你轻饶。此判。”
在古代,但凡事涉风化,很多当事人都会选择隐忍。胡林翼一眼就看出当事人的顾虑,将狡诈的樊洪痛打个半死,以示严惩。从言语文风视角来看,胡林翼的判词老辣简练,文风质朴,骈散兼有。清代判词即使是在晚清时期仍然时有骈体文风存在,这是身为文人的法官将平时创作风格融入判词的结果。
清代判词情理法融合
不论是唐宋还是明清,判词写作都非常重视“情理法”合一。这与中国古代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理念相一致。清代是中国古代判词发展成熟时期,清代判词的情理法融合也较为明显。例如,于成龙便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熏陶下文人士大夫为政优缺点并存的特点。在审理案件方面,于成龙作为地方长官兼理司法,深知作为一方“父母官”的职责所在:上要向朝廷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掌管民众教化;下要对得住治下百姓,“为政以德”,宽仁慎刑,面对普通诉讼案件还是重在调解,以教化为先。在写判词时,于成龙常常综合各种情理因素,重视伦理道德教化,比较灵活。下面以《祝寿起衅之妙判》判词试作说明。该判词原文如下:
“禀悉。据称该民于五月十六日前赴陈家祝岳母之寿,未婚妻舅陈毛金因与其堂兄禄生饮酒争论,遂至互殴。该民上前相劝,被毛金用铁铲柄打伤胸胁各部。该民未婚妻秀全,亦帮同毛金从旁凶殴……夫该民与毛金,即舅也,秀全,该民未婚妻也,纵谓友于笃爱,宁能伉俪忘情?……事既异乎寻常,情尤深夫疑窦。姑候验伤,集讯察夺。此批。”
在这件案件的审理与批复中,于成龙十分慎重,因为他认为这件案子的案情本身不合情理,可能事存“暧昧”情由,至于事情真相,却已不可得知。这篇批词既显示出于成龙出色的文采,又表明其重视叙事说理,同时还不忘法律,兼顾人情、法理。
樊增祥的判词在这方面也堪称典范,下面以《批郝克栋呈词》为例,试作分析。现将判词摘录如下:
“查党见邦之兄党逢辰,先年在家教书,郝氏子弟相率受业。尔兄郝睿现为大荔校官,即其弟子。党逢辰以先生借东家之银两百六十两,除陆续清还外,下欠七十金未还,迄今三十余年……尔所恃者,不过乃兄现为教官,即著尔兄自行投案,待本县面加训斥,以为薄待师门者戒。尔乃无知之物,本县不屑与言也。仰将此批抄给尔兄阅看,伊是读书人,见此批后定打尔三十戒尺。尔其凛之。”
负责审理本案件的樊增祥认为,老师借门生的钱,即使偿还时间持续过久,作为学生也不可“逼讨”“恶闹”。这篇判词从整体上看都是法官在叙事说理。樊增祥站在儒家礼教的角度极力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秩序。清代的书面语已趋口语化,在文学作品中用俚俗用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樊增祥在判词中融入俗语村言,化用经典名句,使得判词生动形象,雅俗共赏。
事实上,古代法官之所以努力使判词做到情理法融合,一方面是古代社会历史背景使然,另一方面是情理法合一的判词,易被人接受。因此,能否巧妙地将情理法融合在判词中可以体现出官员的从政水平。古代法官身兼行政、司法职权,理应在保障公正司法的同时尽力调解纠纷,以减少治下的诉讼案件。基于此,中国古代判词并不是单纯的法律文书,优秀的判词中蕴藏着古人的大智慧。
晚清西方列强入侵,朝廷腐败暗弱,司法独立不保,很多清廷重臣很难做到视百姓为子民,也无法公正处理事关洋人的案子。从晚清开始,中国传统的判案方式逐渐由情理型判决转变为西方现代的规范型判决。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晚清判词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道德与人文素养并重,重证据事实,态度谨严,推进了判词书写的现代化转型。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于成龙
——浅谈《红楼梦》中的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