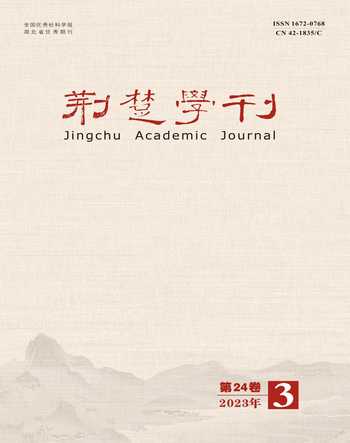历史法学视域下西方法治理念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启蒙价值与反思
杜鑫
摘要:文章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事实角度,分析西方法治理念在近代思想启蒙时期所展现的价值与意义,并就其中的逻辑关联性构架起一个将二者结合的理论体系。西方法治理念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从国家整体位阶的角色维度讲,以“国家主权”替代了“天下秩序”;从文明国家内部整合的模式来看,以“民族精神为纽带的共同体”替代了“王朝国家”;从处理民族国家疆域内各民族群体间关系的方式来看,以“国族构建”代替了“族际政治”。从这三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出发,分析价值逻辑,并对西方法治理念最终未能对近代中国民主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形成深度影响的原因加以分析、反思。
关键词:西方法治理念;民族国家;启蒙价值;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3-0068-08
20世纪前后,民族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现代社会科学以“西学”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近代学人的眼前时,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和论战历经了数次“异化”的蜕变与洗礼,清王朝以封建皇权、天下观、礼法等政治哲学观念构建并维系的“王朝国家”受到了来自西方现代文明方方面面的冲击,原本处于较为平稳的天下秩序、边疆秩序、国家法治体系、社会规范体系均开始藉此历史契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具体表现为中央权威削弱、民族群体性分离、法律体系的崩坏等等。一方面,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西学先行倡导者试图将“民族”与“国家”联结起来,以文化的纵向脉络和横向群体搭构起超越封建王朝的更为宏大的政治单元,促使民众形成国民团结共进的意识;另一方面,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清廷“法统改良”派也意识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近现代法制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也努力地以重构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为核心,建立具有广泛社会领域调整作用的法制体系。马歇尔·萨林斯曾经就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 1 ]
但无论是思想领域的发声,还是政治领域的变革实践,我们从中其实都可以领会一个历史事实——即构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必然趋势(尽管清政府上层人士主张法制改革的初衷还是为了延续封建政府的统治地位,理论家们也有着以“改良”为基础的保守立场,但从历史的最终走向看,这些主张和行动都是促使中国国内各族统一,完成近代民主国家构建的先导要素)。西方法治理念与中国传统法治模式的区别就在于其各自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差异性,主要包括:社会矛盾冲突的复杂程度、纵向的社会阶级与横向的民族群体的互动、文明国家历史文化体系的不同等等。但国家构建形式的历史走向却在这一时期有了道路的重叠性,清末立宪也试图以“共治”“宪制”“现代成文法典”等方式来完成这一过渡的平稳着陆,虽然在近代中国,民族发展程度程度参差不齐、中国传统人治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民族习惯法层面的社会规范体系与外来法治文化的互不兼容等原因是使得西方法治理念无法深度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土壤问题”,西方法治理念本身也存在不够完善和未能触及的领域,然而对于二者在相互铆合、变化、适应的探索过程中所揭示或是依仗的理论逻辑我们不可忽视,亦当对其进行当代历史视角下的分析与重构,并加以反思。
一、西方法治理念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关联的历史事实
(一)从“天下秩序”的瓦解到国家主权的明確
“天下秩序”是建立在中国多民族共生疆域内部牟求构建“大一统”格局基础之上的,它的初衷是以确立王朝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促使空间疆域内部的多元单位形成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向心力”,以此来维系统治秩序的稳固。自秦之后,无论历朝统治主体的族属、血缘、风俗文化为何种样态,均以建立“天下秩序”为政治统治的终极目标,并以“藩属”的基本形式来确认外延化的边疆地区。清王朝建立之后,以“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并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发端,这种以“内在力量和传统秩序所主导的自我赋权”[ 2 ] 28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格局受到了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巨大冲击,可以说是被动地参与进了以“民族国家”身份确认身处国际社会中参与各领域交互应当具备的一种法律拟制,即“主权”。
让·博丹在1576年所著的《共和六书》里将“主权”喻为一种“超越国民与法律的无上统治权力”,同时也指出此项权力“仅仅能够被行使于公共领域而不可滥用于私权”,这一权利的存续“将随着共和国的存在而无限延长,并不以掌权者的变动而变化”这三大要素特点就奠定了主权概念的基本形式。之后卢梭也以“人民主权论”的观点角度对主权概念进行了论述,但除却对主体描述的差异性(卢梭主张人民这一社会群体才是拥有行使主权的主体,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公权力机构仅仅是代议制的工具),其它方面基本都秉持了相同的思路。
随着鸦片战争对国门的叩响,自其之前的西藏治理问题(1727年设驻藏大臣)、西北地区的分裂问题(1755年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叛乱)等边疆地区的持续动荡和民族分裂端倪的进一步激化,到之后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间反抗力量斗争方式的极端化(太平天国运动),以封建皇权统治为基础而构建的“天下秩序”可以说在内外的不断冲击下已经无法再起到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的作用了。因此,以一种新范式来重构国家制度构成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统治地位并起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用成为了近代思想家们所迫切牟求的进路。其主张的逻辑顺序大致可分为三步:一是借助西方民权理论抬升民众在民族国家中政治参与的地位;二是以国家主权观念建立对国内外事务治理的正当化秩序;三是在此基础上完成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防止分裂。以王韬为例,其主张“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其上同其害;与民共乐者,民必与其上共其忧”。郑观应也主张“宜速开国会,以固民心”[ 3 ]。这种本质上将世俗之法和“天理”进行二维连接(外在表现为提出主权观念,建立公民参与机制)并将历史进程的主体资格赋予“民族国家”而非君主或政府的主张已经成为了“时局所趋之进路”。
(二)从“王朝国家”到“民族精神的共同体”
若以鸦片战争为时代划分节点,王朝国家“一家一姓”的构建特点无疑是无法应对国际社会中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对抗的,由此现实出发,就必须将王朝政权覆盖下的特定民族(如汉、蒙、满等)或是文化圈(汉民族的儒学文化圈、藏地的藏传佛教信仰文化圈)等抽象空间积极地拓展,重新构建起一个能够统合诸民族、信仰、风俗等诸多要素的联合体。而之所以要构建这样一个联合体,根本目的还是要通过以统一且被多民族国家内部诸成员普遍认可并遵行的规范秩序体系来完成“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蜕变。西方法治理念所带来的启发便是催生这一蜕变的重要线索。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4 ]。
进入晚清后,清王朝已经在国际领域的政治交互和国内管控中处于非常“飘乎”的境地了。对内,“中国”及“中华”等名词开始向现代意义的国家名称转化,其原本字面意义上的华夷观念内涵逐渐有了消解的中性化趋势。民间尤其是边疆地区的诸族对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已经出现了不认可甚至反逆的状况,以至于在帝国主义煽动下进行以“王朝国家内部角色的自我剥离”为内涵的分裂活动。对外,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后,清王朝已经彻底失去了朝贡体制意义上的藩属国,帝国主义试图通过改变外交活动和条约具名的途径来切断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联系。1871年,中日在商定《马关条约》的立约标题时,日方提出应以“大清国”作为与“大日本国”对等的缔约国署名,其提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约内两国相称,明书国号为正”[ 5 ]。在与欧美各国的外交条约和公文往来的文本中,更是被迫地使用了具有歧视性意味的“China”一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王朝上层也意识到了“中国”、“中华”等具有民族精神统合效果的词语称谓的重大意义,也逐渐开始默许并践行使用“中国”及“中华”作为国格代表的称谓。纵览1870年至1871年间中日鉴定的诸多外交文书,上至恭亲王奕,下至李鸿章,皆以“中国”自称( 1 )。汪宝荣所著供清中学堂、师范学堂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在清学部的审定下由“本朝史讲义”更用此名。这其中的意义绝不止于通过“以中国代指清国”而维护清王朝统治,其更应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国格转化”。即由封建皇权主导的权利分配模式开始向以国家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构建过渡,借此方式稳固民族国家内的诸民族成员,使其不作为“王朝国家”的藩属,而是以“民族国家”成员的角色存在于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互和对内的统合管控。
(三)“从族际政治”到“国族主义”
所谓“族际政治”,即是指以民族为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具体表现为政治博弈、冲突战争、族际联姻、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这些族际交互的形式显然不利于统合诸民族而形成一个以各民族共同利益为原则的联合体。以清王朝为例,出于“皇权一统”对各民族的管控目的,清政府族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族类隔离”的意味。一是划定疆界,严格限制族际人口流动。通过实行山禁、河禁、围场、牧群、哨道等制度极力减少汉文化与满洲边地、蒙古各旗、新疆六城、西南藏苗的接触。二是建立区分内外的藩属体制。在关外盛京设留都,任命满洲尚书和五部(无吏部),对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仅置将军总领军政,其余事务任其自理(也有派遣驻藏大臣与达赖共治的例外)。内地则以严格的中央集权政体严密把控各级机构的动态。其目的并非贯彻民族平等的理念,而是在维系皇权统治的基础上防止各族内部团结统一,形成具有“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政治集团——而这是不利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至19世纪末,这种“族类隔离”的政策已经造成了一系列国家危亡的严重后果,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条件推动下,清政府开始试图以西方法治的诸多形式来维系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过程中的稳定。以“新政”为例,其主要实施了“改革地方行政体制、抑制宗教势力、兴办实业并移民放垦、发展现代教育文化事业、鼓励族际通婚、改革中央集权体制”等诸多举措。这种影响力无疑来自于西方对建立包含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两种内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成功范例。“民族主义”与“国民”身份的提出正是民族国家主权建设的对内举措。梁启超曾言:“民族之政治能力常有优劣焉?能由專制政体而进化与民族国家者,则能优胜;不能由专制政体而进于民族国家者,则常劣败。”[ 6 ]这种主张造就拥有主权即主人翁意识的国族,建立以民族共同体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理念正是中国近代反“族际政治”博弈而崇尚“国族构建”的重要标志。
二、西方法治理念影响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价值逻辑
(一)法治“公意化”的聚合效应
要实现“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最先实现的应当是使民族国家作为主权范围内法治的核心主体而非个人或某一社会阶级。即所谓“人民主权”。梁启超关于立法权的论述便能形象地反映这一点:“国家者,人格也。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无意志而有行为者,必疯疾之人也,否则其梦呓时也。国家之行为何?行政而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 7 ]这里梁启超显然发现了“王朝国家”的君权具有行政权力恒具扩张冲动的特点,要想把控这一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的界限,就必须建立一种最能够体现国家公意的权力分配模式。国家作为一种超然性的位格角色,其象征着一切具有“善意”“良法”的潜在精神内涵,理想的国家应当以国内各成员的公共利益诉求为先,以平衡、仲裁、调剂等方式对利益博弈的相关活动进行调节,除却民族理想、国民利益等它不应当具有“非中立”意义上的立场。作为受托于民族国家内部诸成员来行使“代言人”义务的政府,如果坚持以组成自身的个体的本位利益为首位而忘记了赋予自己这项权力的民族国家国民的公共利益,无疑它就是一个不会为民族国家诸成员所容忍的“寡头政府”。
因此,民族国家的法权立场一方面要坚持作为中立者以自身内部诸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先;另一方面把政府作为实然的“代言人”以强调其受托义务。结合这两项原则来推动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其路径可以通过程序法的法制安排,尤其是增强政治决策中的民众参与,把国家融入民众之中,实现多民族构建的文化共同体向现代的法律共同体的转化。1907年,胡炳熊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论中国种族》一文,强调实现包括满汉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融合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古来历史发展规律的最终结果[ 8 ]。 1906年,被派遣出国考察宪政的满族官员端方递交了名为《请平满汉畛域密折》的奏折,强调欧美各国因国内种族、民族关系不同而强弱有别,其言“苟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非先靖内讧,其国万不足以图强;而欲绝内讧之根株,唯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 9 ]。随后清廷于次年八月特谕令内外各地衙门议奏消除民族界限、实行民族共治的可行性方案。大部分主张立宪修法的官员均认为应当从形式和精神两方面逐步消除长期族际政治所形成的民族界限。熊希龄就主张“夫法者,所以齐不一而使之一也,必令一国人民,无论何族,均受治于同等法制之下,权利义务悉合其宜,自无内讧之患”[ 10 ]。这其中的意义绝不止于通过“以中国代指清国”而维护清王朝统治,其更应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国格转化”。即由封建皇权主导的权利分配模式开始向以国家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构建过渡,借此方式稳固民族国家内的诸民族成员,使其不作为“王朝国家”的藩属,而是以“民族国家”成员的角色存在于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互和对内的统合管控。这样就基本形成了“民族”与“国家”以“国族”形式形成政治意涵上的构联。
(二)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治体系对民族国家的“规训”意义
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对外的独立主权和对内的管控地位无疑会产生统治集团对“自益”的无限趋向可能,公共利益、国民普惠、民族共进等民族国家本身应当承担的义务出现缺位的情形。这种“寡头”式的政体无疑是对民族国家位格意义的践踏。如此,宪制政体针对法权的安排和设计方案便能帮助民族国家在形成之后积极地完成内部各相关主体的受托义务,完成“文明共同体”向“法律共同体”的转化。
宁骚在其《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一书中指出:“民族是由族类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形成,在经历了民族统一、民族自决运动后产生了旧式的民族国家,其对内具有促使诸族体间互动、权利分配的作用,对外则在国际法的秩序体系下与诸国际组织之间进行双边或多边的活动。”[ 11 ]康德认为“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它不是教权或者王朝的产业,相反,它是由所有生活在一个法律联合体中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人们所组成的公民联合体”[ 12 ]。此论在承认民族国家是实在法的源泉的同时,还隐含了以实在法驯化立法主体甚至于民族国家本身的含义。也就是说要实现民族国家的成功转型,就必须运用现代性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对其进行规训,使这一本质上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主体服从普遍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要遵循“依宪治国”的基本内涵和路径,否则民族国家同样有可能走向新的压迫主义,参与缔约的人民反而又陷入了遭受奴役的境地。因此,现代法制和宪制政体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制度表现形式,更是驯化“利维坦”的体制利器,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航标。
中国虽古有“宪法”一词,但这是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制度的,鸦片战争前后,关于西方宪法的理念、制度、原则和概念等知识范畴通过以郭守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其还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宣传西方法治文化的刊物。随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在各自的作品中也广泛传播了西方的宪政制度和宪法理念。熊元翰依据在日留学期间的学习成果,首次将“国法”的概念系统提出,认为一国之“国法”当囊括国家、人民、统治机关等要素,“国法”则是调整三方关系的秩序原则。随着清末立宪活动的开展,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对采纳西方宪制政体事实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倡导(尽管各自所期许的政治目标有差异),如康有为就在其论著中提出要仿照西方各国,实行君主立宪、公民制度、地方自治等宪制政体。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也竭力宣传西方的宪制理论:“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订立。自治之法悉照美国自治法律。”[ 13 ]
(三)法典制颁:法制统一对各民族社会规范体系的熔铸价值
民族国家的建立,其必然要求能够以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将整个空间疆域范围所覆盖,实践、知识、制度经验等都应以明确的规则形态表现出来。就大陆法系传统而言,法典的制颁“负有统一杂乱的法律制度并以此帮助形成一个坚如磐石的民族国家的任务”[ 14 ]以统一的立法来安排分配反映公共群体利益诉求的权利,并辅之以具有社会公义性质的来自于多元文化群体(具体表现为各民族群体因民族风俗传统的差异性而拥有不同的道德观)的价值立场来调整和保障结果正义。这样较为完备的、涵盖多元化价值本位的法律体系既是实现民族国家对于各族规范的秩序化安排和表明公民政治联合的基本立场,又是充分体现构成文明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将自己疆域内部的万民笼罩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之下,把一切社会规范、哲学体系、道德价值理念、文化风俗等意义系统悉数归置于法治,把他们转化为规则和程序形态,就意味着该民族国家的建设任务尚未完成。东方古代的《唐律》;西方近代历史上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无一不是承载着民族国家当下的历史现实、政治与道德承诺、民族认同和国家构建等一系列内容,充分体现了一个具有民族国家意味的法律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理想。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它与旧有的传统法典不同,打破了中华法系的传统结构,使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独立于刑法、民法等普通法律之外,规定了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而后清末宪政编查馆与法律修订馆以《各省调查局办事章程》为先导,收取了《直隶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调查书(一)》《山东省调查地方绅士办事报告清册》《山东调查局编辑民情风俗报告书》《吉林调查局文报初编》等多个省份的调查报告书,采用直接问答与陈述、整理记录的方式形成了丰富的关于民事习惯规范的资料库——《调查民事习惯问题》[ 15 ] 34-45。而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大量各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内容,《大清民律草案》一共1 569条,《调查民事习惯问题》一共348条,其中内容重合的部分就有213条之多。
清王朝沿用数百年的《大清律例》虽具有成文法典的基本体例和形式,但其内容不仅局限于封建社会长久的“刑狱”法治思想,而且并无将“宪政、国家制度”等公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置于其中,在具体的细则上也无法以高度的适应性来囊括疆域内各民族的法律关系。而中国又是一个以“礼”为基准点在民间、边疆等皇权无法触及的空间内散发出无数社会规范并形成完备体系的“法律渊源多元化”的社会(这种“礼”的概念不仅是中原汉地的儒家礼治思维,许多少数民族以其风俗、宗教思想来作为本民族习惯法原则和精神的指导的形式也可以理解为“礼治”),如能够以法典形式承载着这些纷繁复杂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把特定空间的历史——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法律形式、民族文化及其政治生活表之于具体的法制结构,就能达到使整个文明共同体紧密凝聚、一体整合的效果,从而以近代化范式的法律文明秩序来构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三、西方法治理念无法深度影响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各民族发展程度差异大,缺乏民权政治的土壤
按照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而言,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想要通过践行法治来构建民族国家的基础,便是能够将法律规定的权利公平无失地赋予每一位成员个体。而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政治态势——尤其是各民族发展差异的极度不平衡,便决定了平权式的法律体系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意义极为有限。清中期以后,国内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已经初步定型,除汉民族以外,蒙、满、回、藏等主要分布于边疆地区,部分散居于中原内地。东北地区以满、蒙、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清王朝建国之后,东北地区设有留都,用以安置留驻的满族人口,其余的蒙、达斡尔、鄂伦春大部分是游离于封建社会边缘的原始部落的社会形态,仅仅在战争动员、征发劳役等国家公共工程的号召下才会与中央政府形成明确的归属联系。他们拥有社会规范、宗教信仰、组织构建模式等原始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的结构还相当完备。北方分布着以各蒙古部落为主的民族人口,他们一方面处于各部分治、互不勾联的分散状态,另一方面又以盟旗、爵制、游牧、萨满信仰等对本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进行着与中原地區文化内涵完全不同的规范体系构建,尽管康熙、乾隆都曾有过“满蒙一家”的言论,但是纵观清王朝民族政策的“隔离”意味,实质上北方蒙古各部的社会运转模式与中原地区几乎就是两条进路。西南地区的藏地,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均实行着达赖与班禅的政教二元治理模式,尽管清王朝取得了册封和任命的权力地位,也派遣了驻藏大臣从旁参与藏区的行政事务管理,但中央直辖的集权体制并未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权力构架模式在中央王朝权威衰落的情况下便会立刻失序,造成分裂和动乱的后果。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想要实现西方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权政治体制,无疑是难以实现的。而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并不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和民族平等思想,反而全盘推翻了古代中国处理族际政治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急躁冒进,一味强化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不顾蒙藏等边疆地区的特殊区情,也没有与各地的宗教、地方势力达成合意,又无法动员各民族地区的群众来推行法治近代化的进程。其自身有不具备足够的财政和政治承受力,在英军入侵西藏时,清政府无力进行军事援助,反而采取了“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 16 ]的旁观态度,使得包括外蒙古、藏区保守势力的分离主义势头愈加激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二)人治主义传统与法治主义观念的矛盾冲突
西方法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经的争论、阻力极多。在日本的引进过程中尽管也曾出现过是否应当让法国专家保阿索纳特起草的旧民法生效的争论(最终因其家族法的部分规定有违日本的传统家族伦理观念而被否决)[ 17 ],但总体而言西方法治理念在日本的立法、司法、法律教育等领域迅速地扎根并确立起较为完善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但在中国,自1901年变法修律开始,在私法领域,以沈家本、伍廷芳为代表的法治改良派与张之洞、劳乃宣等为首的礼教派之间就以“干犯名义”“故杀子孙”“子孙违反教令”等罪名是否应当保留在以西方法治理念为干城的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中。在公法领域,又产生了中国是否实行联邦制度,湖南、浙江、江苏等地要求制定“省宪”的主张是否应予以认可,在中国应当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还是“总统制度”,“监察制度”的存废,“三权分立”与“五权体制”,司法独立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关于具体制度、罪名的争论事实上是对于中国是否要接受西方传入的法治理念,主导近代中国法治变革的究竟以西方法治理念为主,还是以中国传统的礼教思想为纲?
而中国礼治的历史传统又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儒家对“人治”和“法治”之间逻辑位阶标准的论断。以孔子“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为例,其想要表达的内涵有两点:一是坚持君王对于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及官吏自身的政治素养远比制度本身重要,想要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良人政治”的意义大过“严刑密法”;二是立法者的表率才是敦促社会成员遵行法令的前提,完备的制度建设并不是根本因素。荀子在后期更是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明确论断。在司法领域,中国古代法律的社会效果往往取决于各级官吏的自律与明察,民众对于法律的评价也不止是以法律规范自身的完善与否,更要以执法者个人的道德品行作为标准。尽管这样的习惯与传统在司法过程中有益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并起到教化万民、宣传法令的社会效果。但是,比之西方法治理念中的法律本位、司法独立及其法律文本本身的科学性,以礼教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特点就决定了其实施依靠的便是“良人政治”的基础,如沈家本所言“有其法尤贵有其人矣”[ 18 ]。
(三)本土传统习惯法规范与外来法治文化的冲突
在近代中国,对域外法治文化的排斥性不仅仅体现在“礼治”与“法治”逻辑的矛盾冲突中,以其“传统法被动式的异化发展”这一根本原因来推导,民族习惯法规范与西方法治理念所包含的法治文化的碰撞亦是西方法治理念无法深度影响近代中国民族构建中法律体系统一问题的表现。法律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都是从立法本质的法律作用角度来考虑的,即“立法是对现有社会规范体系的记录还是对新秩序的创设?法律是归制国民生活还是重构国民生活?”清政府为了改变传统行政体制,推行近代化的国家构建模式,在东北地区,废除封禁制度,改设奉天、黑龙江、吉林三省;在新疆地区,削弱伯克制度,增设府县;在内蒙地区筹划改革传统的盟旗制度、设立行省;在西藏地区,试图重构政府组织和权力框架。宗教方面,以藏区和蒙古为例,清政府长期采取扶持“黄教”势力强化对藏地的管控,但在“庚子之变”期间,八世哲布尊丹巴听信谣言,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图谋分裂蒙古,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藏战争”期间擅自挑起战端又临阵脱逃,还将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任转嫁给中央政府。清政府也在西方“政教分离”的历史趋势下试图改变藏蒙地区的积弱、愚昧状态,剥离宗教势力在世俗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一方面限制诸宗教领袖的权力;另一方面缩小各地寺院等宗教团体的规模。但在这过程中又借助英法宗教势力来挤压本土宗教的生存空间,加之其皇权对地方宗教势力的原生依赖,这种中央皇权与地方教权的联盟彻底崩塌了,也把诸地方宗教势力彻底地推向了中央政府的对立面,遗祸不浅。在婚俗、文化、经济生活方面,清政府试图建立现代的户籍制度,鼓励通婚,缓和民族关系,消除族际隔阂。但由于在民族地方的税制局限,清政府推行政策方针的经济来源都要通过藏地寺院贵族、蒙古王公来统一征收、上缴、划拨,但最终来源依然是对各民族群众的摊派,而在解除封禁后,内地商人开始大量向民族地区涌入,无论是王公贵族還是人民群众,几乎都沦为了内地商人的债务人,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矛盾。在政府主导的交通、垦荒、开矿等大型实业工程的开发过程中,军事冲突、贪污腐化、人地矛盾等情况错综复杂,边疆地区的军队又缺乏严格的管控,导致战乱不断,民族关系出现了全面恶化的局面[ 19 ]。
(四)西方法治理念的实践土壤缺乏“大国模式”
民族国家这一概念诞生于西欧之时,与之应运而生的法治理念其所适应的国情便是单一民族所组建的政治共同体。这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是不一样的,故而西方法治理念在某些制度设计、权力分配等领域的效果并不能直接体现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法律移植中。民族主义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借以团结民众,推翻君主制政体的有力武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自由、人权、公民权利为革命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基础,在此过程中凭借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们对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共同体”道德的期待与塑造,“民族”这一具有悠久文化渊源,以血缘、语言、地域等社会初级纽带联结的社会共同体,被赋予了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政治新含义:掌握国家主权的公民共同体。他们从中看到了基于文化、语言、血缘和地域意义上的原始“民族”概念在反抗君主专制、建立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试图利用“民族”力量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扩散和成功,主张以“民族”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并坚持“民族自治”是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 20 ]。坚持族裔界限不能成为政治隔离的借口。
然而从“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基准与社会历史事实出发,西方国家主张的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和出发点与中国有着先天的差异性。首先,从国家疆域和人口规模上来讲,西方各国的民族成分、分布、民族群体的特殊性均没有中国那样复杂,即使民族群体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互动关系甚至是历史冲突和矛盾,但并不存在民族政权频繁更替且民族群体均拥有各自的极为完备的社会规范体系和民族文化体系,其本身就拥有较强的被同化、异化的可能性,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和精神也不失可以视为一种新文化的涵化驱动。而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们都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敌对势力,清王朝一方面要延续自身的存续,一方面要对抗帝国主义的不断蚕食,还要面对因管控失序而试图分裂的藏、蒙等民族地方——这些民族区域还拥有相当大的地理空间和极为集中的族群规模。国民政府对内要推翻代表封建政權的旧势力,竭力维持民族团结不至国家分裂的混乱局面;对外还要在与帝国主义势力周旋的基础上将让步与对抗同步进行。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仅凭西方法治理念对民族国家内部权力的分配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如何能够形成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四、大道行思,取则行远:“铸牢中华民共同体意识”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法治历史再回顾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1 ]。可以说法治对于自中国近代以来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有着极其深重的意义,这种积极意义既反应在宪法视域中针对国家、人民的政治属性定位和相关权利义务(民族法律法规的精神从来不是单向赋权,而是将义务性条文隐含于法律文本的阐述之中。故而从法治理念的研究场域中把握“民族”与“国家”的理论意涵关联性要注意两点:
一是重新认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横向关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专门设置“民族条款”,强调蒙古、西藏、青海等民族地区是中国领土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宪法原则,规定了边疆民族地区代表参加国家代议机构的权利。如《蒙古西藏青海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令》《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法》《西藏第一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修正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日期令》等。二是承认地区、民族社会历史性的客观差异,尽力牟求实质平等。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蒙古、西藏、青海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令》《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法》《修正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日期令》《西藏第一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等国家立法文件将地方参政权与民族因素相结合,以单行性立法的形式“别置殊权”,确保蒙古、西藏等民族地区能够跟上内地政治改革的民主步伐。可见,在中国“民族国家”理论研究的历史叙事场域中,“法治”曾经是占据了一定的话语空间的。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从以封建王朝的“天下观”到对“多民族共生疆域”的客观认识,再到近代中西交互的时代背景下由“立宪”“开国会”“五族共和”等革命话语所伴随的西方法治观念的推行,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鄂汉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特色因子,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中也是以先锋志士的角色而活跃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便诞生在此。作为青年后学,对于学理性研究的讨论不应当囿于时代风尚所限,对于其“昔在”的社会历史事实的关注也是裨益当下的积极方式。2021年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与“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宏观指导下向前迈进的起点,未来民族法学的理论研究又该如何延展,正待吾辈求索。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教授在《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中集中对自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如中国属地方可行”的说法,到清末《黄埔条约》《望厦条约》中外国人将“大清”与“中国”对等看待的事实进行阐述,驳斥了美国“新清史”学派将清王朝称为“满洲帝国”的观点。
参考文献:
[1]SAHLINS M.“What Is Anthropological Enlightenment?”[R],in International Lecture Serie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Peking:Beijing University,June-July 1998.
[2]许章润.历史法学:第一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郑观应.与潘兰史征君论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300.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3.
[5]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友好条规》的再认识[J].近代史研究,2016(9):69-83.
[6]梁启超.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梁启超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03:297.
[7]梁启超.论立法权.梁启超法学文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75.
[8]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2.
[9]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9.
[10]故宫博物院.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945.
[11]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
[1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林远荣,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37.
[13]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M].上海:三联书店,1978:649.
[14]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高鸿钧,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3.
[15]陈斌.不可承受之重:民国法典编纂时刻的习惯调查[J].西部法学评论2020(2):34-45.
[16]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231.
[17]何勤华.中国法学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9.
[18]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51.
[19]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1:39.
[20]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21]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EB/OL].(2021-08-08)[2022-03-12]. https://www.ccps.gov.cn/tpxw/202108/t20210828_150303.shtml.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