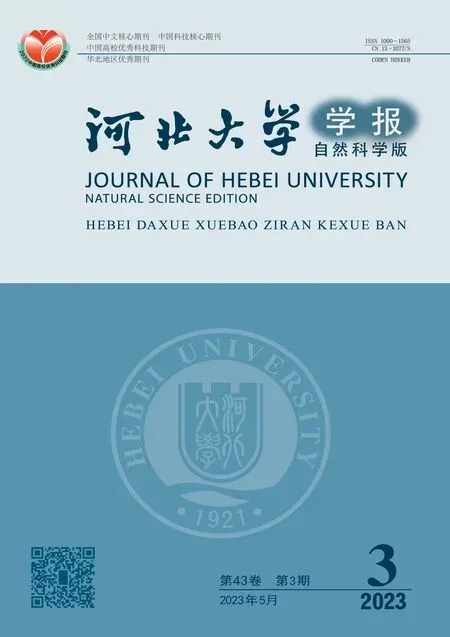猴痘病毒动物宿主的研究进展
耿彦生,夏子涵,石腾飞,曹志然
(1.河北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2.河北大学 基础医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monkeypox virus,MPXV)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病,曾主要流行于非洲.自2022年5月,非洲以外的许多国家报告了猴痘病例,并且报告病例数快速增加.由于猴痘在全球广泛区域的迅速传播,2022年7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猴痘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2022年11月16日,WHO所有6个区域的110个国家/地区报告了实验室确诊猴痘病例.
长期以来,非洲西部和中部是猴痘的自然疫源地,猴痘病例通常出现在一些野生动物与人接触频繁的热带雨林附近的村庄,以散发和小规模暴发为主.2022—2023年的全球猴痘疫情,被认为是非洲或旅游归来的感染者携带病毒输入欧洲,进而引发了“人—人”的传播,而非洲感染者最初的病毒来源仍然可能是动物[1].自然界的动物储存宿主可能是人猴痘长期流行的驱动因素,控制病毒“动物—人”的传播是最终控制猴痘流行的关键环节.本文综述了MPXV在动物中的流行情况及动物对MPXV易感性的研究进展,对MPXV可能的动物宿主及“动物—人”相互传播的危险性进行了评价.
1 MPXV的病原学特征
MPXV属于痘病毒科(Poxviridae)、脊索病毒亚科(Chordopoxvirinae)、正痘病毒属(Orthopoxvirus)[2].同属中除MPXV外,对人类具有致病性的病毒还包括天花病毒、牛痘病毒和痘苗病毒.20世纪70年代天花病毒被根除后,猴痘病毒成为致病性最强的痘病毒.
痘病毒有包膜,形体相对较大,电子显微镜下病毒体呈砖形或椭圆形,长200~250 nm.病毒内含线性双链DNA,基因组全长约200 kb,紧密排列着约200个基因[3].正痘病毒属中各种病毒的外膜表面蛋白序列同源性高达89%~100%,表面蛋白含有许多中和抗原表位,因此,异种病毒间有交叉免疫保护作用,例如,天花疫苗对猴痘的保护率约为85%[4-5].MPXV有2个基因不同的进化分支,即中非(刚果盆地)分支和西非分支,2个分支的基因组核苷酸序列差异约为0.5%[3].中非分支的致病力较强,致死率高达10%,西非分支的致病力较弱,致死率为1%~3%[6-7].最近的猴痘疫情所检测到的病毒属于西非分支.有学者提出对MPXV新的分类方法,将MPXV分为3个进化支(Ⅰ、Ⅱa和Ⅱb),导致2022年全球暴发的MPXV属于Ⅱb[8].目前为止,没有发现MPXV的新变种,但对最近来自多个国家的MPXV分离株进行基因组学分析,发现系统发育分支分离趋势明显,表明病毒在人类传播的过程中在持续加速进化[9].
2 MPXV在动物中的流行情况
猴痘被认为是一种人兽共患病,非洲中部和西部的热带雨林地区是MPXV的自然疫源地,人猴痘的发生与动物传播有关.为了探明MPXV的来源、宿主范围及在自然界中的循环或传播机制,研究者一直致力于调查野生动物的感染和流行情况.
2.1 MPXV在灵长类动物中的流行情况
MPXV于1958年在丹麦一个研究机构的食蟹猴和恒河猴中首次发现,并因此命名,该机构用于科研的猴子主要从新加坡进口.此后,欧洲和美国圈养的灵长类动物种群中,也曾出现类似猴痘感染的病例或暴发.规模较大的一次暴发发生在荷兰鹿特丹动物园,从非洲引进的一批食蚁兽在到达动物园后不久出现猴痘疾病,紧接着居舍邻近的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狨猴等多种灵长类动物被感染,有不同程度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0].这些灵长类动物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于是,有学者对分别从亚洲和非洲猴群采集的2 000多份血清进行正痘病毒(OPXV)抗体检测,但结果均为阴性[10].
人猴痘病例于1970年首次在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11],此后,中非和西非不断有猴痘病例的报告,这些病例大多出现在热带雨林地区附近的村庄,常与捕猎、屠宰和食用森林动物有关,推测可能在与动物接触时感染.于是,研究者对动物宿主的寻找和调查转向非洲猴痘流行区,开展了大规模生态学调查和长期监测项目.早期在西非森林调查的灵长类动物OPXV抗体阳性率为8%~28%,其中一些动物为MPXV特异性抗体阳性[12].例如,在扎伊尔北部发现22只冠猴(刺尾猴)中的2只(9.1%)MPXV抗体阳性,3只红尾猴中的1只(33.3%)MPXV抗体阳性[12].
在长期监测项目中,2012年在非洲科特迪瓦的国家自然公园发现1只死亡的白眉猴幼崽呈现猴痘的典型皮肤病灶,MPXV DNA检测为阳性,首次在野生灵长类动物中确认了MPXV的自然感染[13].2017年在该森林公园的不同观测点3次观察到黑猩猩群落的猴痘暴发,病毒序列分析发现3次暴发中的MPXV病毒株均属于西非分支,但病毒株之间有一定差异,也不同于2012年在白眉猴中分离到的病毒株,因此认为这几次疫情是分别的独立传播事件[14].这些研究表明,灵长类动物黑猩猩、猴子能够自然感染MXPV,但无法确定引起暴发的病毒来源,因为对动物的监测没有发现其捕食和任何其他行为的显著变化.
2014年和2016年喀麦隆的2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圈养的黑猩猩也被发现有猴痘疾病表现[15],但同样未能确定病毒来源.
在非洲中部和西部连续多年开展生态学调查,目前已明确野生灵长类动物中有猴痘暴发和流行,这些动物感染后会出现类似人类猴痘的疾病表现,例如皮肤黏膜出现痘疹等.但是灵长类动物在自然界中病毒传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不确定,推测有2种可能:一是某些灵长类动物是MPXV的自然宿主,能够直接或间接传播病毒、感染人类;二是它们并不是主要宿主,而是像人类一样偶然被感染引起暴发,另有其他自然宿主为传染源.由于非人灵长类动物MPXV抗体阳性率较低,并且迄今为止只在少数几只野生动物中分离到MPXV,所以,第2种可能性更大,即猴痘暴发可能只是偶然发生.
2.2 MPXV在啮齿动物中的流行情况
在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的大规模生态学调查,涵盖了多种野生动物.调查发现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为OPXV抗体阳性,尤其松鼠等陆生啮齿动物阳性率较高.1986年美国学者在捕获的18只绳松鼠(Funisciurussp.)中发现2只(11.1%)MPXV抗体阳性,并从其中1只分离出MPXV,提示绳松鼠中可能有MPXV流行,这是第1次在野生的啮齿类动物中分离出MPXV;随即对所保存的采集于1979年的51份松鼠血清样本进行回顾性检测,其中5份(9.1%)MPXV抗体阳性,进一步证实了MPXV在该地区野生绳松鼠中的流行[12].在扎伊尔的另一个猴痘流行地区Bumba开展的调查,野生松鼠中也检测到了MPXV抗体,阳性率为24.7%,而同时捕获的其他属种啮齿动物均为阴性[16].一些学者认为陆生啮齿动物种群密度高、与人类接触多,应是维持MPXV在自然界传播的优先考虑的种群.松鼠是该地区人类活动领域中唯一检测到MPXV感染的哺乳动物,并且有持续较高的抗体流行率,很可能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动物宿主.
2003年美国猴痘暴发,这是非洲以外国家首次报告人猴痘疫情.流行病学调查认为,宠物批发商在将本地草原犬鼠(Cynomysspp.)与非洲进口的啮齿动物一同运输时使前者感染,而作为宠物的草原犬鼠引起了人类猴痘暴发[17].疫情发生后,对从加纳进口的这批动物(或尸体)进行检测,其中绳松鼠、非洲巨鼠(Cricetomyssp.)和非洲睡鼠(Graphiurussp.)3种动物MPXV DNA阳性或病毒培养阳性,显示有MPXV感染;对动物首次到达口岸采集的血清样本进行回顾性检测,发现12只(66.7%,12/18)非洲巨鼠为OPXV抗体阳性[18].这批动物来自加纳南部森林地区,但此前加纳没有关于猴痘的报道,为明确动物感染的来源,美国学者在加纳开展生态学调查,发现当地捕获的非洲巨鼠、睡鼠和绳松鼠有MPXV感染,并且太阳松鼠和非洲地松鼠(Xerus)也有OPXV DNA和/或OPXV抗体阳性[18].而美国当地动物,除与进口动物接触的草原犬鼠,野生和圈养动物均没有检测到OPXV抗体.因此推测,加纳进口动物的MPXV感染发生在非洲.
最近20年在加纳、刚果开展的生态学调查显示出基本一致的结果,即在绳松鼠、非洲巨鼠、非洲睡鼠、太阳松鼠等啮齿动物中能检测到抗OPXV抗体,特别是绳松鼠和非洲巨鼠多次检测到抗OPXV抗体并检测到了猴痘病毒DNA,充分证明MPXV在这些动物中流行[6, 19-20].此外,从褐鼻鼠、条纹鼠、沙鼠及象鼩目岩象鼩中也曾检测到OPXV抗体[19-20],说明这些动物也曾有正痘病毒感染.
目前的数据表明,在非洲猴痘流行区,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尤其是一些啮齿目动物有MPXV的流行.而这些小型哺乳动物具有典型的储存宿主的特征,即它们能使病毒复制、增殖,但不会出现严重的疾病[21-22],因而很可能在丛林中参与病毒循环、维护病毒的持续存在,是最可能的自然储存宿主.值得注意的是,MPXV在非洲的维持和传播可能涉及多个动物物种,但其自然宿主范围及传播机制仍不完全清楚[23].
3 不同种类动物对MPXV易感性的实验研究
MPXV发现后不久,有学者就开展了病毒感染实验研究,以了解各种动物对MPXV的易感性.例如,Marennikova等[24]利用家兔、小鼠、大鼠、豚鼠及仓鼠5种实验动物进行实验,结果显示:小鼠、幼兔及新生大鼠对MPXV易感,能够通过滴鼻、皮下注射等不同途径感染,并有不同疾病表现及死亡;成年大鼠、家兔和仓鼠经皮内攻毒后,健康状况没有异常,但经过一定时间后,肺、肝和脾中能检测到病毒,表明病毒在体内进行了复制;豚鼠对MPXV不易感.
美国草原犬鼠因被非洲进口的啮齿动物感染而作为传播媒介引起了1983年的美国人猴痘暴发,已表明其对MPXV易感[18].在实验室,低剂量的中非和西非分支病毒株悬液通过滴鼻、皮内注射方式均能使草原犬鼠感染,感染后,在眼睑、舌、肺、肝、脾等组织样本及咽拭子中均能检测到活病毒,样本的病毒载量最高达到107pfu/mL,表明MPXV能够在草原犬鼠体内大量增殖且全身分布[25-26],证实了其传播病毒的巨大危险性.
对捕获的野生啮齿目动物如非洲绳松鼠、非洲巨鼠、非洲睡鼠等进行滴鼻、气溶胶吸入、皮肤及静脉注射等多种途径的感染实验,均能引起全身感染,显示这些啮齿类动物对MPXV均易感[21-22,27].Falendysz等[27]利用剂量为106PFU的MPXV悬液接种绳松鼠,通过3种途径攻毒:4只滴鼻、4只皮内注射、1只仅注射生理盐水但与已攻毒动物同笼饲养,结果所有这9只动物均被感染,说明除了呼吸道、皮内注射外,接触污染物也有可能使动物感染.实验研究也发现,感染后的这些小型哺乳动物有中等强度的疾病表现,并通过口腔、鼻腔、直肠和眼部分泌物排出大量病毒[25-27],说明这些啮齿动物能够作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播给与之接触的其他动物和人类.
目前为止,没有对非洲野生灵长类动物进行MXPV感染实验的研究.但是,曾多次利用食蟹猴和恒河猴进行MPXV感染的研究,均显示这2种原产于亚洲的猴子对MPXV易感,通过静脉、肌肉及皮内注射或滴鼻、气溶胶吸入等途径攻毒,都能引发感染并导致疾病[28-30].食蟹猴和恒河猴的疾病表现与人类感染类似,除全身症状外,可在面部、手臂、腿和尾巴的真皮层上出现特征性的猴痘痘疹,而痘疹的渗出液及结痂有传染性[28-30].
动物病毒感染结果显示,许多动物对MPXV易感,而这些动物存在的地理区域非常广泛,几乎世界各地都有.显然,MPXV具有感染分布在全球不同地区的许多野生和圈养动物的潜力.其中一些啮齿动物,由于种群数量大,分布广泛,被感染后能使病毒在其体内大量复制增殖,并通过多种途径排出体外,具有传播病毒的能力,并有可能成为MPXV的储存宿主.
4 MPXV的人兽共患传播
2020年之前发生在非洲中部和西部的人猴痘暴发大部分由动物引起,非洲以外的病例也能够确认或疑似是由动物向人传播的结果[6].
4.1 “动物—人”的传播
在非洲,大多数猴痘病例出现在位于热带雨林或雨林边缘附近的农村,与野生动物接触是猴痘病毒感染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31-33].自1970年人猴痘病例发现以来,中非和西非发病人数逐渐增加,尤其近年增加明显,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当地人口与野生动物接触界面增大,从而增加了人的感染机会[1].2020年之前非洲以外地区发生的几起人猴痘疫情也基本能够确认与动物传播有关[6].
对自然感染和实验感染动物的研究发现,MPXV在动物体内全身分布,皮肤、脏器组织及血液中有病毒存在,在感染动物的痘疹的渗出液、口腔及鼻腔分泌液及粪便、尿液等排泄物中均能检测到病毒[25-27].因此,MPXV从动物到人的传播可能有多种途径.例如:动物通过咬伤或抓伤可能直接将病毒注入人体内导致感染;在狩猎、屠宰、烹饪动物肉类或与宠物动物玩耍互动时,接触感染动物的组织、体液,可通过吸入或破损皮肤黏膜感染.对草原犬鼠研究发现,从痘疹病灶、鼻腔和口腔分泌液检出的最大病毒量分别为1.05×108、9.63×104、3.8×107pfu/mL,显示痘疹病灶分泌物病毒浓度最高[25],因而,黏膜皮肤直接接触和呼吸道传播可能是重要的传播途径.
研究人员在非洲热带雨林的观测点对黑猩猩群体中的个体进行跟踪调查,在该群体猴痘暴发时采集了粪便和尿液,并在啃咬后的水果采集了唾液样本,这些样本中MPXV DNA的检出率分别为12.6%、20%和19.2%,同时,在周围的苍蝇及苍蝇反胃/排泄物(植物叶子上的黑点)中也检测到了MPXV DNA,表明苍蝇具有介导MPXV污染环境的可能性,有可能偶尔导致黑猩猩和其他易感物种的间接感染[13].
研究发现猴痘疾病的表现和严重程度与感染途径有一定关系,经皮暴露感染更易导致皮肤痘疹和更严重疾病[13].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经常接触多种动物,感染之后通常很难确定到底与哪种动物有关及具体的传播途径.2017年,尼日利亚发生由西非分支引起的大规模猴痘暴发,直到目前仍不清楚疫情的人兽共患病源,也不清楚环境或生态变化是否促成了疫情的突然再次出现[34].
4.2 “人—动物”传播的潜在危险性
目前非洲以外地区没有发现MPXV的自然动物宿主.但已知草原犬鼠、松鼠、家兔等多种啮齿类动物对MPXV敏感,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感染.由于小型啮齿动物分布广泛,与人类共栖生活环境,接触密切,在最近人猴痘全球流行的情况下,许多学者担忧感染者能否将病毒反向传播给动物,导致非洲流行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建立新的动物储存宿主[35-36].
最近法国的报告首次证实猴痘患者传染了1只宠物犬[37].在一对男男同性恋配偶猴痘症状出现12 d后,他们的宠物狗的腹部皮肤及肛周黏膜出现了痘疹样病变,肛门和口腔拭子检测MPXV DNA为阳性.对其中1名患者和病犬检测到的病毒DNA进行测序和比对,2株病毒基因序列(19.5 kb)的同源性为100%,因此推定患者将病毒传播给了宠物狗[37].由于该宠物狗感染MPXV后能够再排出病毒,表明病毒在宠物狗体内进行了复制,提示狗被感染后有成为新的传染源的潜在危险.
因此,猴痘流行期间,患者应避免与动物接触.假如病毒由人传播到动物,在非流行区建立新的动物宿主,不仅将导致猴痘流行区扩大、感染率上升,并有可能为MPXV基因变异、进化提供机会,形成猴痘的循环暴发,使得预防和控制猴痘流行更加困难[35-37].
5 结语
已知非洲热带雨林中灵长类动物黑猩猩和猴群中曾有猴痘暴发;小型哺乳动物,尤其是啮齿目一些种属的动物有MPXV感染并且流行率较高,推测可能是MPXV的自然宿主.实验室感染实验也证实多种动物对MPXV易感.然而,猴痘病毒的确切宿主范围、主要储存宿主及从“动物—人”的传播链尚未完全明确,有待深入研究.对于猴痘的预防与控制,在采取措施阻断“人—人”传播的同时,各国人类和兽医公共卫生部门应共同制定措施,加强动物检疫、检测,打破“动物—人”的传播链并防止“人—动物”的反向传播.天花疫苗对猴痘病毒有交叉保护作用,疫苗接种对MPXV的人兽传播具有防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