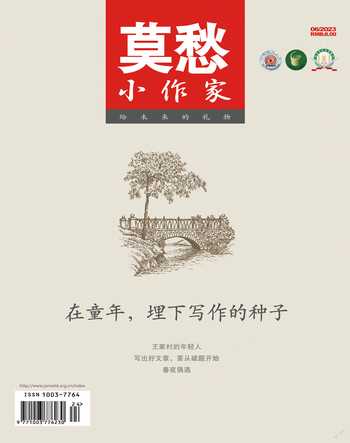棕叶簌簌响
棕树是铁炉冲的热情观众,铁炉冲有喜事了,比如开花的春天来了,抽穗的夏天来了,结果的秋天来了……先是风儿送爽,后是棕叶送响,沙沙沙,哗啦啦,乡村都响亮了。棕叶长了一副观众手,伸举、展掌、鼓舞,一气呵成,仿佛随时为铁炉冲贺喜点赞。
棕叶这么热烈吗?也不尽然。棕叶多是温婉的,唱得多是乡间小夜曲。棕叶做扇,若懒,但把枝节剪剪,便是扇;精致点,费心些,剪个半月形,缝上布条,扇子成。夏之夜,大人搬竹椅,伢子妹子搬矮凳,置瓜棚下,棕扇轻轻摇,晚风轻轻吹,乡村之夜,唯美。
我曾经对棕树有些轻慢。棕树能干什么呢?娘的囤谷桶,是杉木制造;姐的嫁妝箱,是樟树打造;爹的顶梁柱,用的是从山深处砍来的枞树。棕树何用?棕树都长不高,两三人高,已是高高的了。我见的棕树往往是田间有条坑,溪上缺条路,剁了棕树,放倒,做条桥。家里用不上,发配到野外。
棕树用于野外,却貌似不是野生,母亲把棕树当家树养着。我家对面的菜园子里,母亲植了一溜棕树,排列成行,弄得挺阵势。棕树也是结果的,春来,棕树肘腋间,长出苞谷般的穗子,可以吃,未开最好,要开也只是露点点芽。我少年读书是差生,爬树却是一把好手,蹭蹭蹭,爬上棕树,扳下棕把子来,但见嫩白嫩黄,颗粒簇拥如鲤鱼蛋,微微甜,也曾是乡下孩童的上佳水果。棕树有妇子公子之分,腋间结果的是妇子。妇子长得不高,不难爬。当年爬棕树如上楼,如今呢,上楼如爬棕树。
母亲家养棕树,立意不是种水果。棕树的苞谷不是太好吃,也吃不上几天,顶多三四天便吃不得了,果子开裂,黄了、黑了,又苦又涩,如吃沙子。母亲植棕树,谋算的是割棕皮。棕树多皮,一圈圈,一层层,须得年年割。唐诗描述棕树与棕皮,是这样的:“叶似新蒲绿,身如乱锦缠,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棕皮要千度剥,剥皮长千年。不割皮的棕树,长不高,长不大,长着也是邋邋遢遢的样子。棕皮是棕树所生,棕树却把棕皮当身外之物,由人割去,割不惜,反生喜。身外物,死死捆住自家身,会把自己困死的。这道理,不是圣人所教,是棕树告我母亲,母亲传教于我。
雨日,上不了菜园与水田,母亲哼着歌,把饭桌板翻盖起,将破衣剪条条,一层一层,比画着,用糯米和水做糨糊,再镶叠,铺一层棕皮,纳成千层底,暖暖的布鞋就在母亲的手中诞生了。棕皮纳的鞋牢靠多了。
母亲的布鞋,棕皮参建;父亲的蓑衣,棕皮包圆。“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蓑衣是写入诗歌中的,有了蓑衣,便是诗和故乡。不过,我对张志和这首诗有些不太理解,箬笠或是青的,蓑衣也不是绿的,棕制蓑衣,是棕色,用得久了,还是黑褐色。绿蓑衣是直接把棕叶剁下来,连起来?刘禹锡《插田歌》:“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得,蓑衣也是绿色,难道古时候的蓑衣不是由棕皮制作?
我所见的蓑衣是棕色的,如半边披风,披在背脊,再戴个棕斗笠,豪情侠气冲天。老天再怎么给乡村与乡亲横降风雨,穿蓑衣戴斗笠的乡民都可以顶住,“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没有一个老农没有一件蓑衣一顶斗笠,蓑衣与斗笠是乡亲的标配,有了这两样,风不怕,雨不怕,霜与雪都不怕,一件蓑衣穿天地。春寒料峭时,乡亲多是披蓑戴笠,“两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常常半夜,听得雨哗啦啦,看见父亲披蓑衣,在漠漠水田,吆喝着水牛:“哦,起哗。”
一声吆喝,风起了,但见草绿了,山青了,稻谷噌噌噌。棕树当起热心啦啦队,合掌打拍子。
刘诚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品发表于多家报刊,出版《腊月风景》《心心点灯》等。
编辑 闫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