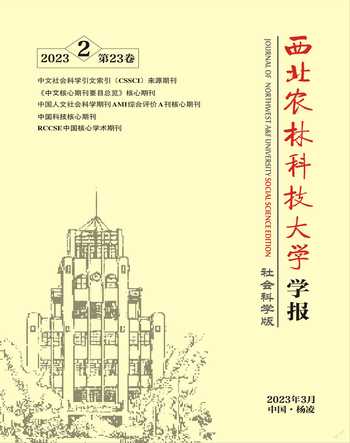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摘 要: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关键词:嵌入理论;资源型乡贤;产业振兴;产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323;F3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3)02-0094-09
收稿日期:2022-07-10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SH013)
作者简介:韩庆龄,女,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与基层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乡贤返乡投资兴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现方式。回顾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乡贤是乡村社会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乡村自治、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化等层面承担了诸多社会职能[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乡村精英和农村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失,降低了乡土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对农村经济发展、村庄规范维护、基层组织建设带来诸多不利影响[2]。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和全面乡村建设行动的推进,需要多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更需要乡贤群体的贡献反馈和资源链接。学界普遍认为乡贤回归有利于引入外部资源来推动乡村建设。吸引外流乡贤回归、实现乡村精英再造[3],是修復城乡循环、开拓乡村发展新动力源和实践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乡村振兴是一场国家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实现产业兴旺和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进入共同富裕阶段的新使命。区别于学界对政治类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研究,本研究重点关注乡村振兴进程中资源型乡贤返乡助推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探讨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结合机制。本研究中资源型乡贤主要是指在外经营的企业家、乡土老板等资本主体。他们既有新乡贤的贡献情怀,又有资本经营的市场期待,选择带着外部资源回归自己的故里投资兴业,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和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的一股新力量。近年来,国家围绕乡村振兴不断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通过财政资金的支持倾斜,使农村交通、电力、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创业的新政策,包括融资扶持、财税优惠等,对民间资本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大,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形成新产业业态和经济增长点,并且地方政府也为吸引乡贤精英回流创业纷纷匹配各种具体性优惠举措。高速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消费转型,乡土社会呈现出特色产业、农产品电商、乡村旅游、健康康养等新经济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利润空间,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的时代需求与国家政策吸引、农村产业机会拓展和传统家乡情怀牵引等多元因素相互交织,为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综合拉力和落地土壤。
目前学界关于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主要关注吸引乡贤返乡回流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以及该群体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与实践功能,主要从吸引人才回流的角度展开对返乡创业乡贤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及畅通返乡渠道、搭建参事议事平台、支持项目资源建设等多元方面[4]进行研究。基于对乡土社会的地缘认同和反哺情怀,返乡乡贤利用自身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主要通过集体土地和政府项目从事特色产业种养、开发农村闲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三产融合产业[5-6]。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主要聚焦本地精英返乡创业的“归雁经济”效应,认为乡贤回归能在短期内为乡村社会集中注入新发展动能,激发乡村内生力量成长[7]。具体而言,乡贤返乡参与产业振兴可以优化农村经济产业结构,推动资源整合与产业集聚,带动农村特色经济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8];能够助力乡村引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农民的议价和抗风险能力[9];能够帮助家乡解决就业和税收问题[10],同时有利于保障农户收入的稳定性和带动农民增收等[11]。此外,还有学者从富人治村,经济能人返乡参与乡村开发的角度,关注到该群体返乡带来的自利性与政治社会风险,认为存在经营失败风险转嫁和私人关系消解公共规则的隐患[5],以及经济导向的村集体经营导致农户与集体对立等问题[12]。学界关注到了资源型乡贤返乡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将资源型乡贤转变成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力量,这一核心问题仍需系统研究。
综上,已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资源型乡贤返乡偏重道德期待和经济带动功能的阐释,缺乏对该群体本身经济社会效益获得的目的关注,忽视了资源型乡贤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属性;二是对资源型乡贤与村庄社会的互动融合以及该群体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机制缺乏具体阐释。乡贤与村庄社会的互动融合过程,直接决定了其在乡土社会扎根的深度和可持续性。鉴于此,本研究对资源型乡贤本文论述过程中的乡贤均是指“资源型乡贤”。这一特殊类型作重点分析,立足该群体市场获利的目的理性和带动家乡致富、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性分析,探讨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开拓发展为抓手的嵌入实践路径,防范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的风险。通过提炼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机制,助力外部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有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和疫情后乡土经济的有效恢复,进而助推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二、理论基础与案例选择依据
(一)理论基础:嵌入理论
嵌入理论是经济社会学解释经济行为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分析范式,该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之间博弈关系。他通过梳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大转变,认为19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即经济并非自足,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13]。”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从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互动的关系论视角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指出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是“社会人”而非完全的“经济人”。他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认为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并受到社会关联的影响[14]24-27。相较于经济学视角下的“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市场”等基本假设。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都强调了现实社会关系和生活情境对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的重要影响,两人的理论呈现较强现实解释力的同时,却忽视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利、组织、文化等要素的重要功能。弗雷格斯坦引入“政治-文化”方法,提出了嵌入理论的综合分析方法,他认为市场的形成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建构的一部分,也是本土性文化的反映[15]。弗雷格斯坦着重分析政治权利、组织文化等要素对经济行为的规约作用,呈现出对社会结构多维属性的综合关注。
综合嵌入理论,采用多维嵌入的观念,从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和关系嵌入的角度考察乡贤返乡对村庄内外各类资源的利用和整合,剖析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机制。通过多维嵌入,资源型乡贤与地方社会实现融合发展,与地方政府、村庄村民之间形成互惠合作,激活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活力,以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并且在多元主体的深度合作中形成一定的风险共担机制。区别于以往城市外部资源对乡土社会的策略性和临时性嵌入,资源型乡贤对乡土社会的嵌入呈现出融合性和合作性特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二)案例选择依据
根据地域社会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笔者选择皖南一农业型乡镇的乡村作为典型分析案例。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和中西部农业型乡村,该地属于中间类型,具有丰富的田野切面。本研究主要基于笔者与研究团队2021年4月2日-5月8日在安徽省郎溪县P镇的田野调研。P镇是城关镇,有19个行政村,7个社区。目前,乡村振兴主要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展开,计划在5年内完成14个省市级中心村打造和240个重点自然村整治。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吸引社会力量尤其是本地在外的企业家返乡投资,是P镇弥补自身资源不足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P镇的盆村为田野表述对象,盆村共1 047户,5 345人,辖31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约5 600亩,以水田为主,村庄无集体经济收入。盆村里的W自然村是P镇重点自然村打造的对象,W自然村分为东、西两个村民小组,约60户,水田270亩,旱地200多亩。该自然村多面环山,南面临河,入村口有一古寺,香火很旺,村庄资源禀赋较好。2014年該自然村在北京从事建筑行业的资源型乡贤返乡投资,先后投入约300万元进行自然村内道路硬化、环境绿化、清修河道、安装路灯等。同时结合自然村内不同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展开村庄产业发展规划,在土地流转整合的基础上,带动村民开展农家乐、茶园、芍药园、水上乐园等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W自然村形成一定建设规模后,逐步向周边几个自然村形成辐射发展。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盆村以W自然村为核心,于2018年申报了省级美丽乡村。
盆村的振兴过程是地方政府指导、乡贤牵头、村民参与等多主体有效合作的呈现。在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为主的社会关联结构中,加之基层政府的正式制度约束和监管,资源型乡贤遵循的不是市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而是在与村庄社会深度融合基础上多元主体之间合作利益最优的共享原则,其实践机制具有借鉴价值。
三、乡村振兴与资源型乡贤的“经济与社会”属性
乡村振兴开启的乡村全面建设发展进程中,型塑了吉登斯视野中“出于偶然的社会”,改变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背景。在这一结构关系的新场域中,资源型乡贤返乡投资兴业,既要实现个体层面经济利益获取的工具目标,又要实现带动村民致富的传统价值目标,同时还要践行政策层面建构本地就业体系,助力本地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的社会稳定功能。资源型乡贤“经济与社会”属性和乡村振兴发展要求的有效统一,是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可持续性结合发展的前提基础。
(一)资源型乡贤主体的经济属性
乡村振兴进程中,推动乡贤返乡需要兼顾资源型乡贤的市场获利需求和带动村民致富发展的社会效益。从资源型乡贤主体的角度来讲,获取经济效益是其返乡的根本激励目标。返乡创业乡贤与乡村振兴的持续性有效结合,不能只让乡贤讲奉献与带动,还要尊重和给予他们合理的利润空间。当前城市工商资本过剩,城市投资的机会竞争和风险压力与日俱增。新一轮的城市资源转移中,乡村成为既有市场经济机会,又有伦理温情的投资新场域。
伴随互联互通社会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加之国家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乡村地区的经济机遇分布相对均匀,近年来各地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亦持续跟进,“与其东奔西跑,不如回乡发展”逐渐成为资本主体的共识。此外,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提出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著名论断,认为包括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内的社会因素,与市场有着深度契合的一面[16],传统的血地缘关系往往是新的生产网络和市场网络建构的基础[17]。由此,相较于城市激烈的市场竞争、高昂的土地租金和人力成本,乡村的新市场机遇与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资源支持相互结合,可以极大降低乡贤参与乡村产业的交易成本及生产要素成本,有效回应了资源型乡贤的“经济属性”。
(二)资源型乡贤主体的社会属性
1.带动村民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振兴还承担着服务农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带动农民发展致富的社会效益功能。乡贤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有回馈家乡和建设家乡的朴素情怀。在村庄建设和产业发展中,资源型乡贤通过挖掘地方特色产业来带领村庄产业振兴,让分化的农民群体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在村庄产业链上实现不同程度的就业创业,并从中获得经济效益,由此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不能只认钱,不认人”,是乡土社会带动村民致富的重要驱动和支撑力量。在村庄和家族的关系网络中实现贡献与反馈,获得家乡社会的赞誉与认同,是乡贤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
2.建构本地就业体系,助力社会稳定的新社会属性。新冠疫情带来人员流动性的降低,服务业恢复缓慢,传统建筑行业和制造业亦受到明显冲击;加之国外疫情的不稳定,外需收缩和内需不足的双重压力更加阻碍了国内企业的全面复产[18],由此导致了就业机会萎缩,劳动力供需失衡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局,相应稳就业成为一项基本的民生指标。该背景下,发展本地经济、建构本地就业体系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而资源型乡贤返乡作为内生性的村庄精英,其与村民处在同一张社会关系网上,有倫理、情感和信任的联结,可以有效调动和聚合村庄内外系统中的社会发展资源,对于激活乡村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培育地方社会稳定有序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无疑起到重要的助推功能。
简言之,当前乡村振兴的社会背景,对资源型乡贤返乡发展既提供了新空间,也提出了新要求。明确资源型乡贤的“经济与社会”属性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契合性,亦是剖析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实践路径的基础。
四、多维嵌入: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资源型乡贤返乡的多重目标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之间的利益期待高度一致,促成了资源型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嵌入路径。在多维嵌入中,资源型乡贤与乡村多元主体之间建构出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实现与村庄社会的深度融合和有序发展。
(一)政策嵌入:资源型乡贤与地方政府形成借力合作
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引导对于资源型乡贤返乡有着重要影响。乡村振兴背景下,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成为县乡基层政府乡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具体到案例地区,P镇现有5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中心村)在打造创建省级和市级美丽乡村,同时计划每年新增6个非中心村进行重点自然村整治。省级中心村的打造创建需要匹配污水管网处理、道路交通硬化、公园绿化环保等相关配套建设,重点自然村整治则由县级财政每村投入20万元进行人居环境整治,这些基础建设均需要庞大的建设资金。在基层政府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加之近年来的新冠疫情亦对地方政府的人力和财力造成一定挤压困境,并对地域社会的经济建设发展带来多重冲击,由此引入外部力量进行亮点和重点村庄打造,就成为县乡基层政府进行乡村发展规划的重要任务。
盆村中W自然村在北京从事建筑行业的企业家乡贤与P镇基层政府一直存在招商关系介绍、项目招投方面的政商互动。为吸引其回流发展,地方政府在乡贤返乡开发中面临的土地、资金等难题上制定了疏解规划和政策支持。在乡村振兴的开发建设和政策吸引下,资源型乡贤通过政策嵌入,将乡贤开发建设的规划与政府层面的发展规划形成契合统一,并在稳定性的政府框架内投资建设。该过程中,乡贤立足市场经营,返乡投资乡村建设是其新经济效益和产业转移的来源点。同时开发建设的结果又迎合了地方政府增强集体经济、打造特色产业等发展目标,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发展资源的不足,还可以起到稳定地方经济、助力疫情防控的社会功能。两者互惠借力,构成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政策支撑。
(二)组织嵌入:激活村庄组织体系实现社会动员
资源型乡贤返乡后,要嵌入村庄社会展开依托土地整合为基础的具体建设行动,不仅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对分散农民进行有效宣传动员。乡贤长期在村外从事生产经营,对村庄社会内部的利益关联难以有效梳理,直接对接分散农户的交易成本高,而组织内部的关系和信任可以有效降低交易和沟通成本[14]56。于是,乡贤依托正式的村社基层组织和非正式的理事会组织的综合力量,通过组织嵌入来实现对分散农户的具体对接和社会动员。
村社“两委”组织是乡土社会中最具公信力的正式平台,资源型乡贤首先借助村社基层组织,将县乡政府对村庄发展建设的政策话语在村庄整体层面进行正式传达,并与村干部之间达成建设发展的共识,获得村干部的认同和配合,从而在村庄政治层面建立起建设行动的合法性认同。其次,因案例地区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民小组是土地产权的实有组织,因此乡贤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成立理事会,将自然村中的家族代表、小组长、小包工头等有社会和经济声望的人组织起来,先对内生精英群体进行村庄发展规划的介绍与开会动员,再通过他们建立与群众之间的意见沟通和诉求反馈。村民小组、理事会组织等民间力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宣传吹风,逐渐将基层政府和乡贤传达的村庄发展方向、土地规划管理、种茶种花的特色产业开发、群众务工吸纳等建设内容向村民介绍宣传。资源型乡贤通过调动处于关键结点位置的内生精英力量,获得村民的认知了解后,再亲自入场召开全体村民大会,逐步获得群众“同意”的支持。
资源型乡贤通过组织嵌入,以开会的方式逐步对村庄精英、普通群众进行层级性的民主动员,实现了一家一户的群众工作对接,有效激活了村庄社会,实现了低成本的土地流转与整合,以及社会关系和发展利益的系统性整合,为村庄特色产业开发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保障。
(三)关系嵌入:分类建构利益关联实现产业合作
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建立在亲属、朋友或其他信任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行动[14]7-11。乡土社会关系对乡贤返乡的作用既体现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有效获得上,还体现在资源型乡贤的经营建设过程中。本地村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资源型乡贤扎根乡土社会的关键是与分化村民建立利益关联,获得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资源型乡贤开发建设最大的阻力是村庄中生活的老年人群体,他们不可能离开村庄,对村庄和土地怀有天然的感情,且部分老人还需通过种菜的方式来自我养老、维持家庭生计。让村庄中的老年人退出旱地种植、同意土地流转是W自然村整片旅游开发建设的前提。于是,乡贤依托捐款唱戏等公共文化活动,期间宣传村庄开发建设的规划,转变老年人的保守思维,以获得老年人群体的支持配合。同时,针对尚有劳动力老年人群体的生计问题,在土地流转给乡贤后,用工优先考虑本村老人,“只要能动,身体健康的,哪怕是80岁的老太太不管活干的怎么样,一天也给108元”。乡贤通过带有情谊照顾的就业机会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恩惠,解决老年人群体的后顾之忧。
资源型乡贤开发建设的阻力群体疏通后,关键是对村庄的中坚力量即中青年群体进行吸纳动员。村庄中的中青年群体原先主要在县域范围内务工,多从事建筑、装修、耐磨材料生产等工作。他们一直参与延续村庄中的人情往来,对美丽乡村建设充满期待,并对回归村庄存有美好向往。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这些传统行业的发展渐趋缓慢,市场经济机会不断萎缩,面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该群体也有返乡就业的强烈意愿。该背景下,资源型乡贤首先对该群体中自己的同辈玩友、同学等进行关系整合,优先向他们提供村庄开发建设中的管理岗位,村庄未来旅游发展中的新经济机遇等,再由其对村庄的其他同辈形成延展效应。由此,部分中青年群体直接参与到村庄建设的产业链上,并获得优于外出打工的经济效益,成为乡贤市场经营活动的重要合作伙伴。在村庄开发建设遇到村民负面评价和质疑乡贤渔利时,这部分中青年群体会主动为乡贤进行正义伸张,为村庄持续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通过资源型乡贤的多维嵌入,村外的政策、项目资源与村内的组织、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被有效动员整合,分散的旱地、闲置的荒山、传统的民房都被集中改造为适合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等新兴产业链发展的要素。资源型乡贤通过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建设、老年人灵活务工就业、中青年群体新经济机会获得等方式与分化村民之间形成了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在乡土社会关系的黏合中,道义伦理与经济效益相互融通,转变了乡村振兴建设中农民旁观者的角色,形成政府指导、乡贤牵头、农民参与等多元主体之间合作共赢的集体行动新机制,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发挥积极推进功能。
五、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风险防范
资源型乡贤返乡通过多维嵌入与乡村产业振兴实现深度结合,在提高农民发展能力和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同时,还要关注与之伴生的经济社会风险。其中经济风险的防范和社会风险的规避,是资源型乡贤返乡助力乡村建设且与乡村产业振兴长效结合的重要保障。
(一)经济风险防范:多元主体共同规约
1.政府建立对资源型乡贤和村庄的双向筛选机制。为避免返乡乡贤投资兴业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P镇基层政府对返乡乡贤设有严格的准入门槛,重点考察资源型乡贤的市场经营能力、对村民的带动意愿、投资创业的持续性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倾向选择与自己有长期合作关系、信息对称的本地乡贤主体进行合作。稳健、诚信、有经营能力且对农村有贡献情怀成为P镇返乡兴业乡贤的重要特征。政府对乡贤主体进行稳健筛选的同时,亦对乡贤参与投资的村庄进行合理选择。案例地区,基层政府的规划布局稳中求进,以点带面,首选地理要素、市场区位、环境资源较好的村庄进行重点和亮点的打造。然后带动周边条件适宜的自然村一起发展,避免大面积铺开的“一刀切”形式,从而确保乡贤投资经营的社会经济效益。可见,政府层面对资源型乡贤和村庄的双向筛选,极大降低了乡贤主体引入和投资落地的经济风险。
2.村民自主选择差异化的参与路径。从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民角度看,外来经营主体与农民利益的冲突主要聚焦在劳动排斥和地租拖欠两大方面[19]。案例地区,农民有选择土地是否流转的自主决策权,且村民流转给乡贤的主要是旱地。该过程中,少数老年人不愿意参与流转,则在村小组的协调下按照田亩数置换土地位置,土地连片基础上确保他们的耕作权利。同时,同村的地缘关系增加了农民对乡贤的信任和稳定预期,“他家就在这里,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这个村,怎么可能不给钱跑路”。
从直接参与乡贤合作的中青年角度看,资源型乡贤是自己的同辈群体,有共同成长的生活经历。中青年群体根据自己职业发展需要、能力所长、家庭资源等自主选择与乡贤的合作点,该群体既有市场经济的利益期待,也有对村庄美好生活的期待。他们表示,即使在市场经营中碰壁,自己建设的是家乡,也可打造回村后的高品质生活,即“进可攻,退可守”,并非对单向市场经济效益激进追逐。分化的村民分别根据自己家庭的生产生活目标来与乡贤互动调适,通过差异化的参与路径抵御经济风险,实现家庭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总之,各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目标稳健合作的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村庄身份,促使其与村民之间在共享地方性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形成稳定、信任的预期。依托传统社会关联生发出来的伦理约束亦可制衡社会关系网络和经济活动过度理性化的趋势,形成对不良社会经济后果的有效規避。
(二)社会风险规避:双重规范约束
1.制度规范的硬约束。伴随国家资源和服务下乡,与确保资源利用效率相匹配的监督管控日趋细化和标准化,数字化、技术性的过程管理取代传统科层体制的结果考核,基层治理规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该背景下,县乡基层政府利用各类政策工具吸引村外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建设的同时,亦在法律框架内对乡贤主体行动制定了系列性的制度举措。比如P镇超过5万元的项目必须走乡镇统一的招标程序,项目资金的审批利用和后期项目工程的监管验收均严格规范。并且,根据当地省市级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乡村具体的建设开发项目必须前置民主议事程序,乡贤的规划决策必须建立在村民主体的意见基础上,需要经过村级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的层级确认。资源下乡、服务下乡、监督下乡同步开启,这对乡贤主体形成了制度性硬约束。资源型乡贤返乡投资兴业主要是面向市场经营获利,而非套取项目资源和争夺村庄内部资源,且主要依靠自身的社会权威而非政治手段嵌入村庄社会。制度规范的硬约束为乡贤的行动提供了基本遵循,避免其与民争利。
2.村庄公共性的软约束。在乡村振兴的建设进程中,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促使村民之间形成新的关系网络,传统村落社会关系与新的产业合作关系相互结合,滋养出公共性的成长基础。这种公共性表现为集体性的共识规则、约束性的舆论评价等多种样态,是村落生活中不成文的软约束。正如W村乡贤所言:“我是这个村子的人,自己建的村里的工程、搞的产业开发,不是建完了就走人的逻辑。工程做得怎么样的舆论评价一直会跟着自己,肯定不敢乱来,人都要脸面。”村庄公共性的评价赋予了资源型乡贤行动的社会规范,对“乡贤”荣名的珍视也进一步规范其行为的公益取向。同时,W村返乡乡贤表示,他们以后很可能就回村养老。晚上在村子里散步时,村里老人会说享自己的福,每当听到这种评价时,自己心里感觉很踏实、很有成就感。可见资源型乡贤不仅与村庄社会有经济关联,还有无法剪断的先赋性纽带,存有深层次的情感互动。村庄层面的共识评价和正向反馈,不仅对乡贤的经济行动形成一定规约,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资源型乡贤对村庄整体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不过,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因社会资本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影响,社会资本会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的制约,但在利益与道德的权衡中,道德的约束力非常薄弱[20]。由此,国家政策层面的正式行政约束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公共性软约束共同发力,才能使资源型乡贤对基层秩序保持敬畏,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结合过程中的政治社会风险。
六、结 语
城乡发展资源失衡背景下,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引进多元社会力量来助力推动。在城市资源过剩和新冠疫情冲击下,乡土社会既为资源型乡贤提供了乡村新业态的发展机遇,又为其提供了基于传统社会关联的伦理温情,即乡村振兴带来的政策机遇、市场机会与乡贤的市场获利需求和家乡反馈情怀相互结合,助推资源型乡贤返乡扎根。并且,资源型乡贤返乡创业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其发展的多重目标与地方政府、村庄社会、分化村民之间的发展利益形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贤市场营利与乡村建设发展之间的根本张力,奠定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长效结合的根基。
相较于以往外部资源下乡带来的“外嵌型悬浮”,资源型返乡乡贤具有扎根和融入乡土社会的便利性。通过多维嵌入,该群体与地方政府、村社组织、分化村民之间形成了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具体而言,资源型乡贤通过政策嵌入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借力合作,他们的市场经营目标与政府发展目标达成有效契合。在政府规划主导和政策支持下,通过获得处于关键结点位置的村庄精英的支持信任,乡贤实现了精英整合基础上的组织嵌入。通过激活村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体系,乡贤精准对接分散农户进行土地等发展要素的整合。立足对村庄资源的初步整合,返乡乡贤通过关系嵌入,与分化村民之间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产业合作。分化村民在新兴产业链上实現就业创业,形塑出以产业利益为联结纽带的共同体,村庄内部的各类发展资源被有效盘活。
可见,资源型乡贤通过对村庄社会的多维嵌入,将自身在外积累的经济社会资源移转到乡土社会落地扎根。一则可以降低自身交易成本、获得经营利益;二则可以提高农民群体的发展能力和市场能力,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并由此激活村庄整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资源型乡贤返乡助力本地经济发展,通过建构本地劳动力在地化的就业体系,还可稳定民生与就业,助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弹性与活力。并且,通过产业利益共同体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功能,由此带动村民致富、乡村发展和社会稳定。此外,诸多新闻报道显示,乡贤群体还通过嵌入基层组织体系、志愿服务组织等平台载体来捐钱捐物、协调物资[21],将自身人力、物力和关系资本优势转换成了地域社会发展新力量,为地方作出积极贡献。
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经济利益的获得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相辅相成,回归故里贡献家乡,获得熟人社会中的荣名反馈和尊重认可是乡贤群体至高的价值追求。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向逐利资本的异变转型和无序扩张,助力形成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则激活了村庄公共性的成长,形成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规约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经济和社会风险的有效治理,为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乡村振兴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不能脱离本地群众的需求。返乡乡贤与分化村民之间合作共赢的产业体系要想长久维系,还要避免资源型乡贤向单向营利资本的异变。村庄建设开发的不同阶段中应始终留有农民主体的参与机会与利益空间,而基层政府的强治理能力以及村庄社会健全有效的村组治理与群众监督,无疑是应对和牵制乡贤异变、确保农民主体利益的关键。返乡乡贤要实现稳健发展,还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用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教化乡贤群体,使资源型乡贤担当起来自于乡村、服务于乡村的历史责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乡贤发展之路,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和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 张陈一轩,任宗哲.精英回乡、体系重构与乡村振兴[J].人文杂志,2021(07):113-121.
[2] 阙春萍,周毕芬.农业人口转移背景下乡村精英流失的影响及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18(03):157-160.
[3] 应小丽.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以浙江省绍兴地区为例[J].探索,2019(02):118-125.
[4] 蒋伟峰,方杰,何斐.从乡贤回归走向乡村善治[J].农村工作通讯,2017(22):53-55.
[5] 陈锋,孙锦帆.返乡能人“经营村庄”的路径、机制与风险探析——基于两个村庄的案例研究[J].社会建设,2022,9(03):7-17.
[6] 王海娟.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农民组织化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20(06):163-168.
[7] 姜方炳.“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J].浙江社会科学,2018(10):71-78.
[8] 李建民,李丹.乡贤返乡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J].中国集体经济,2021(12):15-16.
[9] 吴晓燕,赵普兵.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J].理论探讨,2019(04):158-164.
[10] 李传喜,张红阳.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J].党政研究,2018(01):101-110.
[11] 周耀杭,刘义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乡贤:价值与限度[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6):32-39.
[12] 杜鹏.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集体经营机制:类型与比较——基于村庄治理能力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1):52-63.
[13]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71-80.
[14]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5] 尼尔·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甄志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序言.
[16] 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J].开放时代,2012(06):69-81.
[17] 韩庆龄.电商经济与村落社区的现代性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90-191.
[18] 余泳泽,赵成林,张少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目标战略性调整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11):3-18.
[19] 曹俊杰.资本下乡的双重效应及对负面影响的矫正路径[J].中州学刊,2018(04):38-43.
[20] 陈晓燕,董江爱.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9,40(05):65-72.
[21] 方晨阳.汇聚乡贤之力共筑疫情防控堡垒[EB/OL].(2022-03-18)[2022-10-13].http://www.zj.chinanews.com.cn/jzkzj/2022-03-18/detail-ihawqrpf1214476.shtml.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Resource-based Rural Sage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Theory
HAN Qingl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00,China)
Abstract:It is the key to transform external resources into new kinetic energ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clarify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resource-based township sages returning home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embedded theory.It is found that the practical action of resource-based township sages returning home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economic attribute of their own market profit,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ttribute of feeding back to their hometown and driving the villag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become rich,as well as the new social attribute of stabilizing loc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rder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This group is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village society through policy embedding,organization embedding,relationship embedding and other paths,and forms an industrial community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differentiated villagers and other diverse subjects.At the same time,the geographical identity of resource-based township sages “hometown people” and the connection of common industrial interests help to form economic risk prevention measures with common regulations of multiple subjects,as well as social risk management mechanism with double constraints of national system norms and village publicity.Therefore,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township sages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realized.In addition,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ability of grassroots society,and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township sages to cop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source-based township sages to profit-making capital.
Key words:embedding theory;resource-based rural sages;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industrial community
(責任编辑:马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