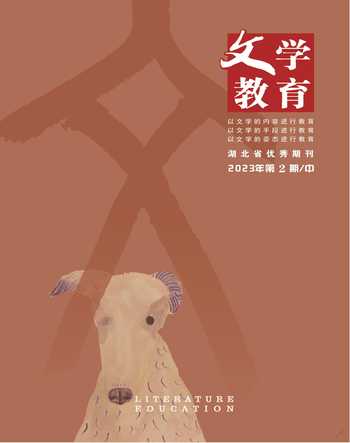《晚秋》中情节虚实的诗意美
高云天
内容摘要:《晚秋》是2010年由金泰勇导演的影视作品。影片秉持了文艺片的一贯风格,忧伤而朦胧。除却荧幕中展现的“实境”,即影片中的现实世界,《晚秋》还为我们呈现了富于情感的“虚境”世界。不管是从影片内容的台词和画面看,还是从影片结构的意象重复和开放性结局看,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整部影片就从这种虚实结合之中,为我们呈现了带有文学性的诗意美。
关键词:《晚秋》 情节分析 虚实结合 诗意美
《晚秋》最早是导演李晚熙于1966年拍摄的文艺电影,但由于胶片遗失,使其无缘再现荧幕。导演金泰勇于2010年重新改编、翻拍了这部电影,赋予了其新的生机。[1]翻拍的版本中并没有使用大量对白来叙述剧情或是塑造人物,而是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或者是大片的留白镜头来带领我们走进影片的世界中。
内容与结构是电影二分后的重要成分。结构是电影的骨架,内容是电影的血肉,二者有着相同的分量与解读价值。电影《晚秋》的这两方面都具有文学性的特点[2],让这部电影如同诗歌一般——除去荧幕上为我们呈现的“实境”,它的叙事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游离于荧幕之外的“虚境”,这使电影具有了很高的解读价值,赋有了一种诗意的美感。
一.內容中的虚与实
《晚秋》的台词大量运用隐喻等文学表现手法[2];没有台词,依靠动作、神态,或是留白来叙事的画面也都颇具深意,在荧幕展示的“实境”电影世界之外又营造了一个等待我们去解读的“虚境”世界。
1.台词与虚境
台词是属于角色的言语,是角色内心。在塑造人物、叙述故事的时候,台词都是重要的工具之一,台词功底的深浅也是衡量一部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对《晚秋》这部影片来说,总体上虽然台词不多,但都有着“话外之音”,充满隐喻,引导观众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为观众营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虚境。
影片中,安娜(汤唯 饰)和勋(玄彬 饰)在碰碰车结束后看到一对欧洲男女。起初,勋为了逗安娜开心,自编台词为这对男女配音。或许出于对其男性视角的不满,安娜也加入了这场配音游戏。
孤立来看,二人对配音游戏中台词不同的编排反映了他们各自对于爱人的心态——勋的男性视角把伴侣当作持续纠缠的烦人鬼和将自我感动当成付出的麻烦精;安娜的女性视角则将伴侣视为自私又冷漠、让自己成为无耻求爱之人的元凶。而若联系全片剧情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二人在各自的处境下对于爱人的真实态度。勋被有夫之妇玉子纠缠,无法脱身,后者甚至不惜从韩国飞来美国向前者求爱。勋为了保住性命,不被玉子的丈夫因情谋杀而离开,并想在美国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安娜被最爱的人抛弃,却心甘情愿地回来为他顶罪入狱,而爱人全无感激之情,反倒觉得她是一个麻烦。出于两人当下的处境,勋让男子明确地告诉女子自我感动的纠缠并不是爱,并成功在美国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安娜则让女子毫不留情地揭穿了男子的眼神和语言中对女子归来的期盼,以及其明哲保身的伪善面孔。
这段台词本身是影片中为观众直接呈现出来的文本,是二人说出的实实在在的言语,也是由语言表象展示出来的触手可得的“实境”;而需要观众深入解读、品味,乃至联系全文才能得知的“话外之音”既不是由台词中体现出来的二人大相径庭的爱情观,亦不是二人在当前处境下对于爱人的真实想法。而是二人未能向爱人说出心中埋藏的话语的纠葛的心态。尽管二人都对自己的处境认识清晰、对自己同爱人的情感也十分清醒,却因为心中仍有残存的爱意,而未能将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想法完全地表达给对方。这样复杂且矛盾的真实心态才是此处所展现出的“虚境”,从这种诗意的真实中蕴生出美来。
配音过后,安娜跑到了幽灵集市,在那里向勋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勋则以“好”和“坏”的评价来回应。安娜对于她过去最爱的人是这样描述的:“我甚至想为他去死。”此时勋的回应是“坏”。之后安娜说到这个爱人离她而去时,勋却评价为了“好”。在一般的爱情中,爱人的离开通常会为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勋作为颇受欢迎的“牛郎”,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他仍然选择评价为“好”,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若联系影片稍前一点的内容则不难看出,这段情节中“好”与“坏”是错位的。
刚到集市时勋已经向安娜讲明,除去“好”和“坏”两个词外,他是一句中文也不懂的。所以,他对事件作出的“好”与“坏”的评价并不是基于他对于安娜描述的事实的判断,而是勋通过安娜细微的表情、神态乃至于动作和语气得出的结论。[3]于是勋口里的“好”“坏”评判就不出自于勋自身,而是出于已经被陷害入狱的安娜潜意识中对于过去的事件和过去的自己的评判。当时的爱人离开了她,这在安娜的潜意识看来是“好”的——已然入狱的安娜回头来看,那个满口花言巧语而并未付出真心的男人怎会对自己有益呢?作为高情商的“牛郎”,勋自然善于察言观色,于是他读出了安娜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替她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而“愿意为他去死”的“坏”,不仅仅是安娜对这一病态心理的评价,而且是她认为当时的自己是“坏”的。痴迷于爱人,为今日替罪坐牢埋下伏笔的天真的自己是“坏”的,是应当抛弃的。
在这样“好”与“坏”的错位中,金泰勇为我们呈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荧幕中被我们所看到的,电影里正在发生故事的这个物质的、实在的现实世界,也就是“实境”;另一个则是通过台词制造的,需要观众在了解前因后果之后,从一个通古博今的上帝般的视角去感受、分析的,我们看不见的、虚幻且属于角色自己的精神世界,便是“虚境”。这样的虚实之间,造就出的是一部达到了诗意之美境界的电音。
2.画面与虚境
画面是观众能最直观地感知电影的部分,也是除台词外,电影的重要组成。电影艺术可以说是视觉艺术,对电影来说画面是不可或缺的。《晚秋》这部影片善于利用人物动作或是大片留白的画面来叙事,这种方式为观众提供了充足的解读空间,也在引导观众想象和联想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可直观感受的画面之外的“虚境”世界来。
在安娜刚回西雅图不久,她去服装店里买了新衣服,购入了新耳钉。但此时的她已经入狱七年,简朴的监狱生活自然没有让她戴耳钉的条件,安娜的耳洞自然已重新长死,需要很痛苦地将它冲破。对安娜来说,她的内心就像长死了的耳洞一样。七年的替罪生活,她追求美的本性和她向往自由的精神已然被痛苦的服刑压抑得麻木了,不再有情感的渴望,亦没有了对美的追求。就如同新购入的这幅耳钉重新扎开了耳洞一样。这次短暂的赴丧之旅,以及和勋的邂逅,也在她封闭的心上重新扎出了孔洞,让生活、甚至说是生命的光重新照了进来。
在享受过短暂的自由之后,监狱打来的电话又将安娜拉回了残酷的现实:在奔丧的期限结束以后,她要及时地回到监狱里去,继续她剩余的监狱生活。于是她像把新买的衣服扔在了洗手间一样,把刚刚得以解放的精神也抛之于身后了。[2]自由的精神对于此时的安娜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就如同冲破的耳洞将要重新长死,解放了的精神要在监狱中重新被压抑,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渴望也要被重新扼杀。与其重新经历这样的痛苦,不如早早地将它抛弃,只要封闭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变得麻木,就能在被重新压抑的过程中少受些伤害。但也正像耳洞被冲破后不可能马上愈合一般,重新品尝了解放和自由的安娜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回到这样麻木的状态。安娜不断抓挠着耳朵周围,不仅仅是她对于马上回到监狱的这种焦虑的躯体化的症状,更是外面这个自由而美丽的世界骚弄着她心灵的体现。
外面世界中自由的生活与不得不回去继续服刑的监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安娜在这种矛盾中焦虑、徘徊,于是她在机场售票处的柜台前一言不发,来了又走。最终她没有选择买票,而是直接走出了机场,她在这一对矛盾中做出了选择。再次面对勋的搭讪时,安娜只回应了一句“Do you want me?”至此,安娜的选择已经非常清晰——她要在短暂的自由中恣情,彻底地解放情欲。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这一层“虚境”还没有体现出那么强的审美性来,这是角色情感的宣泄,是一种非自由的表达。然而在宾馆里,主动提出纵欲的安娜却在中途把勋推开了,在最后关头拒绝了这种原始的情欲放纵。而后在勋的建议下,安娜选择和他去游乐园放松一天。在这个过程中,安娜拒绝了这样原始的、肉体的情欲宣泄;而是在马上要回到监狱服刑这种极端的外部环境下,与勋建立了更加理性的、精神上的爱恋关系。这实质上是由“宣泄”转而成为“抒情”的升华,使得二人感情的这一层“虚境”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是一首理性的“诗”。
二.结构中的虚与实
《晚秋》的叙事结构也使用了大量的文学表现手法,使得原本通过“情节”来推进故事的影片产生了情节的虚化[4],营造了虚实共存的诗意境界。
1.重复与虚境
依约瑟夫·弗兰克的观点,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里,重复的意象能使文本取得连续的参照和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5]在同样注重叙事的电影中,这种观点依然适用。影片《晚秋》里,出现了诸多意象的重复,使前后情节照应,实现了一些特定情感的共通,也使得影片更具连贯性。[2]
在影片的开始,安娜伴着警车的鸣笛在街上走着,此时的她刚刚经历一场家暴,目睹了抛弃过自己的爱人杀害了家暴自己的丈夫。无助且痛苦的安娜并没有就此远走高飞,而是选择回去替罪,她为了爱而失去了自由。而在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安娜举着两杯咖啡,同样伴着警车的鸣笛在街上走着,此时的她刚刚经历一场爱情,在心中已然冰冷的爱意重新燃起后又发现爱人消失不见。这时的安娜即将获得自由之身,然而却失去了爱。
“警笛”“警车”的意象在这兩处镜头重复,形成了一种照应关系,把整个故事首尾相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安娜看似是偶然的命运。[4]过去的她把全部都寄托于爱人,现在的她又从三天短暂的爱恋中得到救赎,看似是偶然的悲剧命运实则暗含了某种必然,如同影片中游乐园里欧美男女的舞剧,一出戏剧一样的爱恋必然要迎来谢幕的一刻。但在这样极端的道德环境下,安娜与勋萌生出的爱情才显得尤为珍贵。
除却警笛外,还有诸如巴士站的意象,也贯穿着安娜的三日爱情。[2]安娜与勋在巴士站初次相遇,勋的搭讪就像那副新买的耳钉一样,轻微刺激着已经长死的耳洞。尽管巴士上的这段初识对话以安娜的一句“你不需要还我钱”无情地回绝了勋的搭讪为告终。之后二人在西雅图的巴士站重逢,此时的安娜已经决定通过恣情的方式来反抗这荒谬的命运,虽然在这段情节的最后原始的欲求未能如愿,但却让安娜已经麻木压抑到封闭了的心重见了光明。第三次在巴士站相遇是在二人的分别之际,安娜坐上回监狱的车。而本该留在西雅图的勋却出人意料地跳入车中,以“重新相识”这种玩笑的方式融化了安娜因为压抑的监狱生活而冰封的心。巴士站最后一次出现在影片中时,勋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只留下安娜一人举着咖啡怀念这段短短三日的感情、重复那一句对未来的约定。
这些意象的重复不仅仅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更是一种“叙事的地标”,它们标志着事件的连续或是情感的重复与深化。这些重复意象为我们划出了另一条时间线,一条并没有实体的情感之线。影片把情感寄托于物像中,造出了情真意切的诗意境界。
2.结局与虚境
一个故事的高潮如果留下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情感没有满足,则称其为开放式结局。[6]这样的留白给了观众“最圆满的结局”。补足故事的权利交到了观众的手中,根据不同人的理解,这个结局将有无数种答案。对于影片本身而言,这样开放性的结局则是构建了一个充满可塑性的空白“虚境”,这种“虚境”是需要通过想象与联想才能到达的故事结局之外的情感结局,这样到达“结局外的结局”的方式制造了一种朦胧的诗意。
影片最后,服刑期满重新获得自由之身的安娜坐在约定的咖啡馆里,等待着勋来兑现当时他在巴士站作出的承诺。这是一段无对话的镜头,安娜的顾盼、张望都昭示着她的感情、她的心境——她对当年的承诺既怀疑又期待、既欣喜又不安。她担心勋像她生命中其他几位男人一样,做出承诺后就消失不见,却又不由得对勋抱有希望,期待他是与其他男人不同的。在最终,安娜终于开口,说道:“好久不见。”虽然这像是一句对他人说出的话语,但镜头中只有安娜,我们无从得知勋是否出现。这样的问候像是对前来赴约的勋说的,也像是对着重获新生的自己的自言自语。而究竟是哪一种情况,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沈从文的《边城》是这样结尾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晚秋》的结尾与其有着非常高的相似性,都是提出了一个不确定的、没有问题的答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尽情想象的“虚”的世界。不同的是,《边城》的等待更多昭示了翠翠的悲剧结局——无论结果如何,她都要承受着这样的离别之苦;而《晚秋》的等待则更强调这段短暂爱情对主人公的救赎,即便最终勋没有出现,这三天的爱恋也是闪光的、值得回忆的,这份约定也支持安娜度过了服刑的年岁,也从中得到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力量,这与《边城》结局的悲剧基调是大相径庭的。
无论如何,这样的开放式结局都制造出了朦胧的诗意效果,于有问无答中将画外之意、话外之音的“美”激发了出来。
“意境”是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7]影片《晚秋》不管从叙事结构还是叙事手法来看,都可以说成功地塑造出了一定的意境来。由于全片的多处隐喻与留白,为观众提供了可开拓的想象与联想的空间,藉此造出了诸多可以解读的“虚境”,增加了观众的审美体验。就其题目而言,影片中的这段爱情已是“晚秋”。在这样略带悲凉的诗意季节,以诗意的手法讲述了诗意的故事,让观赏故事的观众们在无尽的想象与联想中体验到了一种虚实相生的诗意美。
参考文献
[1]乔淼.論电影《晚秋》开放式结局与人物塑造的关系——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视角[J].电影评介,2012(12):67+74.
[2]廖白玲.电影《晚秋》的文学表现手法[J].电影文学,2013(02):35-36.
[3]王子玉.电影《晚秋》的语言艺术[J].大舞台,2012(06):156.
[4]唐浩然,黄大军.建构与消解:电影《晚秋》的叙事艺术[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34(01):49-52.
[5][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
[6]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7]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39.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