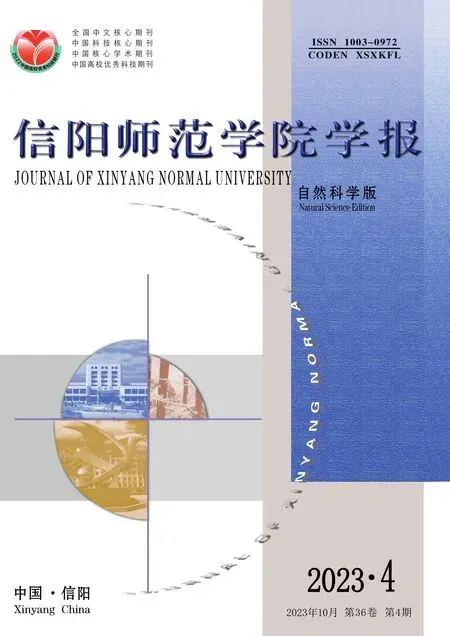植食性昆虫对植物的反防御机制研究进展
刘清松,李一萌,荆胜利
(信阳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0 引言
在长期的协同进化过程中,植物和植食性昆虫形成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植物由于其长期固着陆地上,无法主动逃避植食性昆虫的取食,从而发展出一套复杂的防御体系以抵御植食性昆虫的为害[1]。这套防御体系按照其表达模式可以分为组成型和诱导型两种类型[2]。组成型防御是植物通过自身固有特征或结构来阻碍或者阻止植食性昆虫的取食,譬如表皮的绒毛、蜡质和刺等结构[3];诱导型防御则是指植物受植食性昆虫为害后,通过调控自身基因表达及防御物质的合成等方式[2],增强对植食性昆虫的防御。诱导型防御按照作用方式又可以分为直接防御和间接防御:直接防御是指植物受到植食性昆虫为害后,产生调节昆虫行为的物质和影响其取食及消化的防御蛋白或者有毒次生代谢物等来应对害虫为害;间接防御是植物受到植食性昆虫为害后释放挥发性化学物质(herbivore-induced plant volatiles, HIPVs)或者分泌蜜露吸引天敌对害虫进行寄生或者捕食[4]。
尽管植物为了保护自身而进化出多种防御体系,但植物和植食性昆虫的协同进化类似一场“军备竞赛”(arm race),植食性昆虫也发展出了多种反防御策略来逃避、克服,甚至操纵植物的防御系统,实现对寄主植物的反防御[5]。植物对植食性昆虫的防御因环境、位置和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应地,植食性昆虫的反防御策略也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6-8]。相对于植物对植食性昆虫防御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与进展,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的反防御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研究发现植食性昆虫不仅可以依靠自身的免疫防御体系,还能通过借助共生微生物和其他植食性昆虫等方式实现对寄主植物的反防御。本文在简要概括植物对植食性昆虫防御的基础上,分析和归纳了植食性昆虫对植物的反防御机制,以期为深入理解昆虫与植物间互作关系及害虫综合治理提供参考。
1 唾液效应子介导的反防御
根据取食方式的不同,植食性昆虫主要分为咀嚼式和刺吸式害虫。咀嚼式昆虫啃食植物组织形成明显的缺口、孔洞和伤残等,给植物带来了大面积的损伤[9]。而刺吸式口器昆虫通过纤细的口针刺吸植物韧皮部汁液,形成伤口较小[10-11]。尽管两种取食方式在昆虫为害植物时均给植物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但二者所造成的损伤同机械损伤有本质区别,这种差异主要源自它们分泌的唾液[10,12]。植食性昆虫在取食过程中会分泌唾液,唾液组分直接与植物接触并被植物防御系统识别,进而激活或抑制植物的防御反应。
唾液中可以被植物识别并激活防御反应的组分为激发子(elicitors),而干扰或者抑制植物防御反应的组分则是效应子(effectors)。植食性昆虫唾液激发子主要包括酶类、消化植物蛋白释放的多肽、脂肪酸-氨基酸共轭物和含硫脂肪酸等。目前,研究最早发现的激发子是从欧洲菜粉蝶(Pierisbrassicae)幼虫口腔分泌物中分离的β-葡萄糖苷酶,其可以激活寄主植物甘蓝(Brassicaoleracea)的防御反应,并产生类似于昆虫取食诱导的挥发物,吸引天敌昆虫粉蝶盘绒茧蜂(Cotesiaglomerata)[13]。随后,研究者们又陆续在不同昆虫唾液中鉴定到不同类型的激发子,这些激发子均能触发植物体内的早期防御信号事件,进而调控防御相关基因的转录水平,促进防御化合物的积累,从而增加植物对植食性昆虫的抗性[14]。
虽然植物可以识别昆虫唾液中特异性激发子,从而启动抗虫防御反应,但在与寄主植物的博弈中,植食性昆虫也可以利用唾液中的效应子干扰或者抑制寄主植物的防御来满足自身的生存。按照作用机制,唾液中的效应子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促进昆虫取食、影响植物早期防御信号通路、调控植物激素信号途径和调节植物免疫等[10,12]。例如,黑尾叶蝉(NephotettixCincticeps)唾液蛋白NcSP75是帮助取食水稻(Oryzasativa)韧皮部的关键效应物,通过RNA干扰(RNA interference,RNAi)技术降低NcSP75基因表达后,其取食韧皮部的时间显著降低[15]。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迸发是植物早期防御信号通路之一,植食性昆虫通过各种效应子降解植物细胞活性氧物质而抑制ROS,从而抑制植物防御反应。例如,绿盲蝽(Apolyguslucorum)唾液腺中的效应子AI6具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其能抑制本氏烟(Nicotianabenthamiana)早期信号ROS的积累,减弱植物对病虫害抗性[7]。SU等[16]发现烟粉虱(Bemisiatabaci)唾液蛋白BtFer1可以抑制番茄(Solanumlycopersicum)中H2O2产生的氧化信号。沉默BtFer1基因增强了茉莉酸(jasmonate, JA)介导的防御信号通路,并导致胼胝质沉积增加和蛋白酶抑制剂的产生,从而阻止烟粉虱连续取食韧皮部汁液。在植物激素信号途径介导的抗虫防御中,JA、水杨酸(salicylic acid, SA)途径以及二者间的交叉对话(cross talk)发挥重要的功能。棉铃虫(Helicoverpaarmigera)唾液中的效应子HARP1可以与棉花(Gossypiumhirsutum)和拟南芥(Arabidopsisthaliana)等植物JA信号途径中的JAZ蛋白互作,通过与COI1蛋白竞争性结合JAZ而稳定JAZ蛋白水平,抑制JA防御信号途径,促进自身取食[17]。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昆虫唾液蛋白通过调控SA途径抑制植物的防御反应。例如,在烟草(Nicotianatabacum)中烟粉虱唾液蛋白Bt56通过与烟草转录因子NTH202互作,激活SA途径,抑制JA途径,抑制植物对其抗性[18]。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植食性昆虫效应子通过靶向寄主植物的免疫相关因子抑制植物抗性。例如,在桃蚜(Myzuspersicae)中,其唾液蛋白MP64通过靶向烟草免疫调节剂SUMO E3连接酶SIZ1,干扰寄主植物的免疫反应[19]。烟粉虱唾液蛋白Armet通过与烟草胱蛋白酶抑制剂NtCYS6结合抑制烟草防御反应,从而促进烟粉虱的生长发育[20]。在褐飞虱(Nilaparvatalugens)中,唾液蛋白Nl12可以诱导细胞死亡、Nl40诱导萎黄病,但这些唾液蛋白的具体作用机制仍不清楚[21]。近年来,研究者通过大规模的转录组学和蛋白学组学等技术,在绿盲蝽、马铃薯长管蚜(Macrosiphumeuphorbiae)、褐飞虱和烟粉虱等昆虫中筛选出了大量的候选效应子[7,20,22-23]。值得注意的是,候选效应子是一类潜在的效应子,其是否真正发挥功能仍需通过体内外试验进一步验证。
2 解毒酶介导的反防御
通过长期的进化,植食性昆虫已经进化出复杂的解毒酶系来应对基于寄主植物的毒性化合物的防御。一般来说,植食性昆虫解毒酶系对毒性化合物的解毒过程主要分为3个阶段,即Ⅰ相反应(phase Ⅰ)、Ⅱ相反应(phase Ⅱ)和Ⅲ相反应(phase Ⅲ)[24-25]。Ⅰ相反应解毒酶包括细胞色素P450单加氧酶(cytochrome P450 monooxygenases, P450s)和羧酸酯酶(carboxylesterases, CarEs)等,直接作用于毒素分子;Ⅱ相反应是轭合反应,增加毒性化合物的极性和水溶性,涉及的解毒酶有谷胱甘肽S-移酶(glutathione-S-transferases, GSTs)、磺基转移酶(sulfotransferase)、甘氨酸-N-酰基转移酶(glycine-N-acyltransferases, GLYATs)和尿苷二磷酸(uridine diphosphate, UDP)-葡萄糖基转移酶(uridine-diphosphate glycosyltransferases, UGTs)等;Ⅲ相反应的解毒酶主要是ABC转运蛋白(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genes, ABCs)和其他跨膜转运体等,它们大多具有转运活性,利用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水解产生的能量逆浓度梯度进行跨膜运输,将极性化合物或外源有毒物质运出到胞外。
近年来研究发现,上述3个阶段的解毒酶均在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的反防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Ⅰ相反应解毒酶中,细胞色素P450是昆虫中广泛存在的超基因家族酶系,作为重要的解毒酶,其参与植食性昆虫对植物次生代谢物质的代谢,促进昆虫对寄主植物的适应。例如,研究者发现桃蚜体内的P450基因表达量升高促使其代谢尼古丁和新烟碱等次生代谢物质,从而降低这些化合物的毒性[26]。研究也发现褐飞虱CYP4C61基因在对抗虫水稻YHY15具有较好适应性的生物型Y褐飞虱中表达量较敏感品系显著升高;通过RNAi技术沉默生物型Y褐飞虱CYP4C61基因后,其取食抗性水稻后的蜜露和体重增量均显著降低,研究者推测该基因参与褐飞虱对抗性水稻次生代谢物质的代谢[27]。GST是Ⅱ相代谢解毒酶,也参与昆虫对植物次生代谢物质的代谢。研究者在比较了3个GST基因在两种寄主专化型棉蚜相同龄期表达后发现,在大部分龄期,这些基因在黄瓜型棉蚜中的表达量都显著高于棉花型棉蚜,研究者推测这些基因的差异表达可能与棉蚜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适应相关[28]。YANG等[29]利用寄主诱导的基因沉默技术,在水稻中表达靶向褐飞虱NlGST1-1基因的双链RNA(double stranded RNA,dsRNA),生物测定结果显示这些水稻可有效抑制褐飞虱的生长发育和种群繁殖。在Ⅲ相反应解毒酶中,ABC转运蛋白可以促进毒素主动跨膜运输,并将结合毒素输出到细胞外。最近,BRETSCHNEIDER等对取食植物次生物质阿托品、尼古丁和番茄碱后的棉铃虫进行转录组测序,并分析ABC转运蛋白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表明这些基因的表达模式呈现多样化并且表现出组织特异性,在取食不同的次生物质后,中肠、马氏管和残体组织中均检测到ABC基因上调表达,特别是在中肠组织中发现53个ABC基因上调,反应最为强烈[30]。也有研究表明,烟草天蛾(Manducasexta)可以利用马氏管中的多药转运蛋白(multidrug resistance, MDR)将源自烟草的神经毒素尼古丁排出体外,从而促进其对烟草的取食[31]。这些研究表明,解毒酶基因及其表达量升高,促进昆虫对有毒环境的适应。
3 共生微生物介导的反防御
在自然界中,植物-植食性昆虫-微生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昆虫共生微生物在调控宿主寄主选择行为、营养物质代谢、生殖代谢以及为宿主提供直接的防御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32]。近年来研究发现,一些植食性昆虫共生微生物(如植物病毒和细菌等)亦能通过调控植物防御反应而间接提升宿主的生存适合度。
如前所述,JA和SA信号途径在植物对植食性昆虫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昆虫共生微生物也能通过干扰这些信号途径及其调控的防御反应,抑制植物的抗虫防御反应,促进其宿主昆虫的生长发育[33]。例如,中国番茄黄化曲叶病毒(TomatoyellowleafcurlChinavirus,TYLCCNV)的致病因子DNAβ上βC1蛋白[34]和黄瓜花叶病毒(Cucumbermosaicvirus,CMV)上的2b反防御蛋白[35]通过抑制寄主植物JA信号途径,促进烟粉虱和蚜虫的存活和繁殖,提高这些昆虫对病毒感染植株的致害性[34]。萜类物质作为植物代谢产物中种类最多的一类化合物,可通过JA途径参与对病虫害防御反应[36]。中国番茄黄化曲叶病毒可通过抑制JA途径而抑制烟草中萜类合成基因表达,从而降低萜类化合物的释放,促进烟粉虱在寄主植物的生存和繁殖[37]。另外,研究表明与未携带番茄斑驳病毒(tomatomottlevirus, ToMoV)的烟粉虱相比,携带该病毒的烟粉虱取食番茄后强烈诱导番茄病程相关蛋白(pathogenesis-related, PR)表达,促进烟粉虱的生长发育和繁殖[8]。一些研究者发现植食性昆虫内共生菌通过调控JA和SA信号途径间的交叉对话,抑制植物的防御反应,间接提高其寄主的适合度[33]。例如,烟粉虱共生菌(Hamiltonelladefensa)通过激活番茄SA信号途径基因、抑制JA信号途径,抑制番茄抗虫防御反应,从而促进烟粉虱的生长发育[38]。类似地,斜纹夜蛾(Spodopteralitura)幼虫的口腔分泌物(oral secretions, OS)中的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epidermidis)可激活植物SA途径、抑制JA途径[39]。而番茄木虱(Bactericercacockerelli)内共生菌(CandidatusLiberibacter psyllaurous)通过抑制JA和SA途径调控的抗虫防御反应,促进其寄主在番茄的生长发育[40]。此外,昆虫也能够利用共生细菌来降解次生代谢物质,从而抑制宿主植物的防御反应。例如,中欧山松大小蠹(Dendroctonusponderosae)的细菌共生体富含参与萜类化合物降解的基因,促进其克服含有高浓度的萜类化合物针叶树(Pinuscontorta)的抗性[41]。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为害寄主植物蚕豆(Viciafaba)时,豌豆长管蚜(Acyrthosiphonpisum)体内的共生菌可以协助抑制寄主植物HIPVs的释放,降低豌豆蚜被阿尔蚜茧蜂(Aphidiuservi)寄生的风险,从而增强其适应性[42]。上述这些研究表明,共生微生物在植食性昆虫的寄主适应性中发挥重要作用。
4 水平基因转移介导的反防御
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是在生殖隔离的不同生物体间、单个细胞的细胞器(如叶绿体和线粒体之间)及细胞和细胞器之间进行的DNA片段流动现象,其有别于常见的由亲代到子代的垂直传递(vertical gene transfer, VGT)[43]。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和基因组分析技术的发展,大量昆虫基因组测序陆续完成,在昆虫中也发现普遍存在水平基因转移现象[44-46]。植食性昆虫中,水平基因转移的供体基因主要源自细菌,也有部分来自植物、真菌、病毒和原生动物等。近年来研究表明,部分水平基因转移有助于植食性昆虫降解植物细胞壁、促进吸收营养以及实现对植物的反防御[43-44]。在家蚕(Bombyxmori)中,源自细菌的β-呋喃果糖苷酶(β-fructofuranosidase)GH32具有降低桑树生物碱等毒素功能[47]。一些研究者在烟粉虱和温室白粉虱(Trialeurodesvaporariorum)中发现源自植物的核糖体失活蛋白(ribosome inactivating proteins, RIP)基因,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这些基因可能有助于提升这些昆虫在寄主植物上的生存适合度[48]。最近的研究发现,烟粉虱通过水平基因转移从植物中获得酚糖丙二酰转移酶基因PMaT1,该基因可以促进烟粉虱降解植物有毒次生代谢物质酚糖,促进烟粉虱实现对植物的反防御[49]。在螨类如二斑叶螨(Tetranychusurticae)中源自细菌的β-腈基-丙氨酸合成酶(β-cyanoalanine synthase, CAS)可以分解植物氰化物等防御物质[50]。上述这些研究表明,植食性昆虫通过水平基因转移,从细菌和植物等供体中获得相关基因,从而实现对寄主植物的反防御。
5 HIPVs介导的反防御
尽管HIPVs在植物对植食性昆虫间接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一些植食性昆虫亦能利用HIPVs实现对寄主植物的反防御[51-53]。例如,一些鳞翅目幼虫利用HIPVs直接提高其对寄主植物适应或者间接降低天敌昆虫的控害能力。禾灰翅夜蛾(Spodopteramauritia)幼虫暴露于其为害诱导玉米释放的化合物吲哚后,改变自身气味,降低红腹侧沟茧蜂(Microplitisrufiventris)的定位与寄生能力,从而提升自身适合度[54]。斜纹夜蛾幼虫暴露于番茄HIPVs后,在先前感染相同幼虫的番茄叶片上和含有蛋白酶抑制剂的人工饲料上的存活率和体重显著增加;进一步结果显示,HIPVs后诱导幼虫8个表皮蛋白基因和7个P450基因上调表达。这表明番茄HIPVs的诱导提高斜纹夜蛾幼虫对植物化学防御的适应[55]。也有研究显示,一些植食性昆虫通过操纵植物挥发物的释放而调控邻近植物的防御反应,促进同种或者异种其他昆虫的生长发育。譬如,烟粉虱为害诱导番茄释放β-月桂烯或β-石竹烯等物质,抑制临近植株中SA途径介导的防御反应,使临近植株更适于烟粉虱的生长发育[56]。类似地,暴露于豌豆蚜(Acyrthosiphonpisum)为害蚕豆(ViciaFab)诱导的挥发物后,改变小麦(Triticumaestivum)植株的代谢物组分,促进麦长管蚜(Sitobionavenae)的存活[57]。最近的研究发现,HIPVs介导的反防御也存在于为害植物地上和地下部分的植食性昆虫。红胸律点跳甲(Bikashacollaris)地下幼虫取食乌桕(Triadicasebifera)激发寄主植物系统性的防御反应,诱导叶部释放2-乙基己醇和壬醛等挥发物吸引同种成虫取食,趋避异种害虫乌桕卷象(Heterapoderopsisbicallosicollis);而红胸律点跳甲成虫取食乌桕叶片则诱导植物产生系统性反应,导致根部营养物质增加、酚类等次生防御物质含量降低,从而促进跳甲幼虫的生长发育[51]。类似地,研究发现南美斑潜蝇(Liriomyzatrifolii)取食番茄叶片后改变根部HIPVs的释放,促进其地下虫态蛹的发育[53]。在水稻与害虫互作研究中,发现褐飞虱偏好在二化螟(Chilosuppressalis)为害的水稻植株上取食和产卵,其原因在于二化螟为害可诱导水稻释放高浓度挥发物如2-庚醇、α-蒎烯、D-柠檬烯和β-石竹烯等信息化合物,这些物质对褐飞虱若虫及成虫均具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二化螟为害水稻植株中利于褐飞虱生长的氨基酸含量的增加,对褐飞虱发育不利的甾醇等物质含量降低,使得褐飞虱在二化螟为害水稻上适合度增加[58]。进一步研究表明,褐飞虱还可以借助二化螟诱导水稻挥发物降低其卵被稻虱缨小蜂(Anagrusnilaparvatae)寄生的风险,为其后代提供规避天敌昆虫的庇护所[59];而二化螟雌成虫亦能利用飞虱诱导的水稻挥发物,选择合适的水稻产卵,降低其卵被稻螟赤眼蜂(Trichogrammajaponicum)寄生风险,并提高其后代的生存适合度[52]。上述这些研究表明,植食性昆虫可通过利用或者操控寄主植物挥发物促进自身种群的维持和发展,从而实现对植物的反防御。
6 其他方式介导的反防御
除了上述方式介导的植食性昆虫的反防御,一些昆虫还能够通过逃避、选贮、产卵等方式来适应植物的防御。在选择寄主植物过程中,部分昆虫对营养物质较少或者次生代谢物含量较高的植物会采取逃避反应,从而有效应对植物次生代谢物质的毒害。例如,粉纹夜蛾(Trichoplusiani)幼虫选择取食欧洲防风草(Pastinacasativa)维管束之间的叶肉部分,从而减少次生代谢物质呋喃香豆素的摄入[60]。选贮是昆虫应对植物的防御反应和天敌捕食的另一种有效反防御策略。当受到天敌攻击时,植食性昆虫释放储存在体内的寄主植物的次生代谢物质,从而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研究表明,差翅堇蛱蝶(Euphydryasanicia)通过储存光叶吊钟柳(Penstemonglaber)的防御化合物环烯醚苷可以有效避免蚂蚁的捕食[61]。此外,一些昆虫还能够通过产卵来应对植物防御。欧洲粉蝶(Pierisbrassicae)通过其产卵行为能够诱导拟南芥植株中的SA积累,抑制JA反应,从而干扰植物的防御反应,促进昆虫取食[62]。最近的研究表明,烟草天蛾(Manducasexta)利用渐狭叶烟草(Nicotianaattenuata)中源自不同代谢通路的二萜类化合物和绿原酸在肠道内进行生化反应而解除这两种物质的毒性,从而维持其在烟草中的生存[63]。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研究者势必会发现并解析更多其他类型的植食性昆虫反防御方式及其作用机制。
7 展望
植物和植食性昆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复杂的互作关系。一方面,植物发展出一系列防御体系以应对植食性昆虫的危害;另一方面,为应对寄主植物的防御,植食性昆虫亦进化出相关的反防御机制。植物防御性状的多样性导致植食性昆虫反防御机制也呈现出多样性。这些反防御机制涉及行为、生理和生物化学等方面,主要包括唾液效应子、解毒酶、共生微生物、水平基因转移和虫害诱导的植物挥发物等多种方式。植食性昆虫-植物的协同进化过程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随着植物防御反应的发展,植食性昆虫也将不断发展出新的反防御策略来适应寄主植物。
近年来,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植食性昆虫反防御机制的研究带来极大便利。研究者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生物信息学分析等手段,发现植食性昆虫普遍存在水平基因转移现象,并解析部分水平基因转移在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反防御中的功能。未来,继续鉴定并解析水平基因转移在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反防御中的功能,有望为发展农业害虫绿色防控策略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分子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