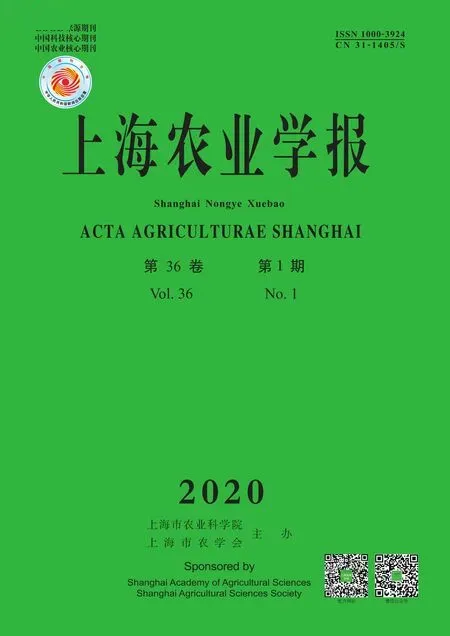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食性昆虫和主栽作物的影响及其生态学机制
万年峰,蒋杰贤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上海 201403)
植物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扮演重要作用[1-2],如减轻病虫危害[3]、提高初级生产力[4]、增加作物产量[5]、减少化学农用品投入[6]。植物物种多样性的诸多功能,已驱使生态学家研发多种多样化种植模式。目前,从空间上而言,多样化种植模式主要包括种植诱集植物[7-8]、间作(套种)[9-10]和地面生草[11-12]。这些多样化措施作用于生态系统后,对植食性昆虫[13]、植食性昆虫的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14-15]、作物产量品质[16-17]、土壤微生物等均有一定影响[18-19]。本研究仅概述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植食性昆虫的丰度(Abundance)以及对植食性昆虫危害主栽作物的影响,并用天敌假说、资源集中假说、推-拉假说、屏障假说和保险假说等理论,剖析植物多样性调控植食性昆虫的机制,以期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提供参考。
1 诱集植物对植食性昆虫和主栽作物的影响
植食性昆虫对某些植物具有明显的嗜好性,合理种植这些植物可以诱杀植食性昆虫,进而保护主栽作物免受虫害,这类植物被称为诱集植物[7-8]。诱集植物被引入农田后,一般会降低农田靶标植食性昆虫(靶标植食性昆虫指诱集植物的防治对象)的数量、减轻靶标植食性昆虫对主栽作物的危害,也会影响非靶标植食性昆虫以及整个昆虫群落的组成与结构。
1.1 植食性昆虫的丰度
1.1.1 靶标植食性昆虫
人为添加诱集植物后,主栽作物上靶标植食性昆虫丰度下降。例如,母菊(Matricariarecutita)被种植到草莓(Fragaria×ananassa)田后,草莓上的欧洲长毛草盲蝽(Lygusrugulipennis)种群数量下降38.2%[20];花椰菜田周边栽种芥菜(Barbareaspp.)后,花椰菜上的小菜蛾(Plutellaxylostella)种群数量下降18.5%[21];香瓜(Cantaloupe)被种植在棉花(Gossypiumspp.)田后,棉田烟粉虱(Bemisiatabaci)数量下降46.2%[22]。正是源于诱集植物具有较好控制靶标植食性昆虫的优势,该模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譬如,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北方,种植者采用茄子(Solanummelongena)诱杀菜豆(Phaseolusvulgaris)上的银叶粉虱(Bemisiaargentifolii),使其种群数量下降26.7%[23]。类似的报道见于澳大利亚维也纳南部,该报道也得到了科学验证:将豌豆(Pisumsativum)种植在马铃薯(Solanumtuberosum)田后,后者植株上的叩甲(Agriotesspp.)数量降低49.6%[24]。诱集植物之所以能有效控制靶标植食性昆虫,主要是这类植物能从物理性状和化学特性两个层面调控植食性昆虫的感觉器官,进而形成比主栽作物更强的引诱力[25-26]。
1.1.2 非靶标植食性昆虫
诱集植物能抑制靶标植食性昆虫数量,已得到广泛认同。此外,诱集植物对非靶标植食性昆虫的影响,也引起了一些科学家的关注。例如,将诱集植物大白菜(Brassicapekinensis)种植于甘蓝(Brassicaoleracea)田后,甘蓝植株上的跳甲(Phyllotretaspp.)数量竟然增加 120.6%[27];印度芥菜(Brassicajuncea)虽然降低甘蓝上(B.oleracea)菜心螟(Hellulaundalis)、粉纹夜蛾(Trichoplusiani)和南方锞纹夜蛾(Chrysodeixiseriosoma)数量,但会引起小菜蛾(Plutellaxylostella)和菜青虫(Pierisrapae)种群数量上升[28]。由此可见,诱集植物对非靶标植食性昆虫的影响是正负两面性的。非靶标植食性昆虫的数量降低,与诱集植物增加主栽作物上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的数量有关[7]。然而,诱集植物增加主栽作物上非靶标植食性昆虫的丰度,可能与诱集植物干扰天敌捕食或寄生非靶标植食性昆虫有关。
1.2 主栽作物的生长
诱集植物的“引入”,能降低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的数量,减轻植食性昆虫对主栽作物的危害,进而促进主栽作物的生长发育与繁殖。例如,在绿肥田种植诱集植物马铃薯后,会促进绿肥的鲜重[29]。诱集银叶粉虱(Bemisiaargentifolii)的南瓜(Cucurbitapepo)被种植在菜豆(Phaseolusvulgaris)田后,增加菜豆产量高达86.7%[30]。然而,主栽作物的生长除受靶标和非靶标植食性昆虫影响外,还与植食性昆虫的天敌[31]、土壤微生物及其根系分泌物[32]等因素有关。据此推理,诱集植物会通过调控植食性昆虫数量直接引起主栽作物生长特征的变化,也会通过其他途径间接诱导主栽作物发生变化。
2 间作对植食性昆虫和主栽作物的影响
间作是指在同一农业系统内相同生长周期内、分行或分列间隔种植2种或2种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33]。将间作植物种植于主栽作物田后,会引起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丰度发生变化,也会影响植食性昆虫对主栽作物的危害。
2.1 植食性昆虫的丰度
间作植物往往为植食性昆虫的天敌提供营养资源,有助于增加主栽作物上天敌的丰度,而天敌丰度的增加,会更好降低植食性昆虫的丰度[6,34]。棉花与茴香(Foeniculumvulgare)按1∶2比例条带间种后,后者植株上捕食性天敌瓢虫(Cyclonedasanguinea、Scymnusspp.)和草蛉(Chrysoperlacarnea)数量增加,这使得茴香上蚜虫数量下降40.5%[35]。Ribeiro等[36]也报道了类似结论,香雪球(Lobulariamaritima)与甘蓝条带间种后,前者能够吸引天敌至后者的植株上,进而导致甘蓝上烟粉虱和小菜蛾数量分别降低48.8%、64.8%[36]。然而,也有案例表明,间作植物被引至主栽作物田后,并不会降低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的丰度,甚至会出现相反趋势。如将臂形草(Brachiariaspp.)与相思树(Acaciamangium)间种,后者旋枝天牛(Oncideresocularis)数量增加28.4%[37]。据推测,间作植物释放的挥发性气味,会对某种(或某类)植食性昆虫具有引诱能力,能将在其他地方活动的雌性个体“招引”至主栽作物上产卵,进而增加植食性昆虫在主栽作物上的种群数量[38]。
2.2 主栽作物的受害率
间种其他植物后,主栽作物系统的天敌库源一般会增强,这使得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数量下降,进而降低植食性昆虫对主栽作物的危害。玉米(Zeamays)、芋艿(Xanthosomasagittifolium)和葫芦(Lagenariasiceraria)间种在芭蕉(Musabasjoo)田后,香蕉球茎象鼻虫(Cosmopolitessordidus)对芭蕉的危害率降低5.00%—6.88%[39]。类似地,苹果(Malusdomestica)和桃(Amygdaluspersica)间种后,车前圆尾蚜(Dysaphisplantaginea)对前者的危害率降低0.43%[40]。然而,Pascual-Villalobos等[41]观察到相反结果:将芫荽(Coriandrumsativum)或菊花(Chrysanthemumcoronarium)与莴苣(Lactucasativa)分别间作后,莴苣蚜(Nasonoviaribisnigri)侵害莴苣的百分率分别增加 188.1%、98.5%,这种侵害率增大的现象,可能与芫荽和菊花引诱莴苣蚜至莴苣上产卵有关。此外,在间作作物干扰下,植食性昆虫对主栽作物的危害,会因主栽作物生育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譬如,与单作苹果园相比,在桃-苹果复种系统里,绣线菊蚜(Aphisspiraecola)侵害萌芽期至开花期的苹果叶片的概率较低,但对果实生长期的危害加剧(侵害率增加30.9%)[42]。
3 地面生草对植食性昆虫和主栽作物的影响
地面生草,也被称为“地面覆盖生草”,一般是指在主栽作物行间或周边保留自然杂草、种植人工驯化的草或绿肥作物,并加以管理,使主栽作物与草协调共生的一种栽培模式[11-12,43-44]。农田生草后,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与其天敌的互作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导致植食性昆虫的丰度以及对主栽作物的危害也会发生变化。
3.1 植食性昆虫的丰度
生草既可为主栽作物上的天敌提供避难所,又可为天敌群落的繁衍提供栖息场所。这有利于天敌对植食性昆虫的控制,进而表现为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的丰度下降。譬如,Wan等[44]研究发现:桃园(上海)林下被种植白三叶草(Trifoliumrepens)后,三叶草上培育的天敌能迁移至桃树上捕食或寄生植食性昆虫;较单作桃园,生草桃园桃树上捕食性天敌数量增加 116.7%,蚜虫群落和梨小食心虫(Grapholithamolesta)种群数量分别降低31.4%、33.3%。同样,三叶草被种在甘蓝田后,甘蓝上跳甲(PhyllotretaCruciferae)数量降低21.4%—55.0%[45]。 然而,生草后,草、主栽作物、植食性昆虫及其天敌之间的营养级关系(Trophic interactions)变动复杂,此时,主栽作物上天敌数量会增加,但植食性昆虫数量有时甚至呈相反趋势。例如,将大巢菜(Viciasativa)覆盖在葡萄园地面后,葡萄上蜘蛛数量增加1.6倍,但斑叶蝉(Erythroneuravariabilis)的数量增加3.33%[46]。这可能与生草措施弱化天敌的迁移能力有关:若天敌能在草上找到充足食物资源,就“懒得”再迁移至主栽作物上猎捕或寄生植食性昆虫。
3.2 主栽作物的被害程度
生草后,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的数量下降,进而降低了植食性昆虫对主栽作物的危害。目前,三叶草是被视为降低植食性昆虫危害主栽作物效果较佳的草种[44,47-48]。譬如,将三叶草覆盖于棉花田后,美洲牧草盲蝽(Lyguslineolaris)危害棉花的概率降低39.4%—48.5%[47]。同样,神香草(Hyssopusofficinalis)、樟脑草(Nepetacataria)等草种,也有类似的功效,如在甘蓝田行间撒播这些草种后,甘蓝被跳甲(Phyllotretacruciferae)危害的百分率降低11.5%—41.1%[48]。然而,有案例表明,生草也会“刺激”植食性螨虫对主栽作物的危害,主要缘于螨虫是广食性有害生物——既危害该类草,也危害主栽作物。譬如,在桃园林间地面生草后,二斑叶螨(Tetranychusurticae)侵染桃树叶片的概率增加5.0%—7.0%[49]。由此可见,植食性昆虫(害螨)危害寄主植物,不仅与其被天敌控制的效果有关,也与其食性有联系。此外,在生长、繁殖与代谢过程中,草释放的挥发性气味化合物或次生代谢产物,对植食性昆虫也会有驱避或引诱作用,这也会影响植食性昆虫取食主栽作物的选择。
4 植物物种多样性调控植食性昆虫的生态学机制
额外的植物物种被添加到生态系统中,可能会干扰主栽作物、植食性昆虫及其天敌之间的食物网关系,进而影响植物多样性调控植食性昆虫的效果,其生态学机制有:天敌假说(Natural enemy hypothesis)、资源集中假说(Resource concentration hypothesis)、推-拉假说(Pull-push hypothesis)、屏障假说(Barrier hypothesis)、保险假说(Insurance hypothesis)等。
4.1 天敌假说
该假说推定,较单作系统,植物多样化种植的系统,拥有更多的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敌,更多的天敌会增强对植食性昆虫的控制作用[6,34,50-51]。与单一种植模式相比,多样化种植能为天敌提供更多更好的栖息地和活动空间[6,12],能在多个时段为天敌提供花粉和蜜源,能吸引更多天敌并增加其繁殖能力[52-54];当主栽作物上植食性昆虫数量不能满足天敌食物需求时,这些额外的植物能够作为替代食物源而使天敌继续保留在生态系统内[55-56]。迄今,该假说已被成功应用于解释间作[57-59]和地面生草[60-62]控害机制的研究中。例如,玉米和大豆间作后,蜘蛛、瓢虫、草蛉等捕食性天敌以及寄生蜂的数量较玉米或大豆单作系统的高[57]。同样,将牧草(Loliumperenne、Phalarissp.等)种植于葡萄园后,葡萄上的捕食螨、蜘蛛、瓢虫、寄生蜂等天敌的数量明显高于单作葡萄园[60]。
4.2 资源集中假说
该假说由Root[63]、Risch[64]等提出,阐明的是昆虫与植物的反馈机制,但该机制通常只在植物群落中起作用[65]。该假说的提倡者普遍认为:植食性昆虫更可能找到和停留于大面积、高植物密度、低物种数量的寄主植物斑块(Patch)[66-68];当单作寄主植物系统被种植非寄主植物后,非寄主植物会通过物理和化学的因素扰乱植食性昆虫的视觉、听觉和嗅觉,从而抑制其在寄主植物上栖息定居的速度、交配产卵与繁殖的概率[69-71]。与多种(≥2种)植物混种系统的寄主植物斑块的密度相比,单作系统的相对高,这有利于植食性昆虫更容易找到寄主植物,也为植食性昆虫在寄主植物上的滞留、觅食和繁殖提供了较佳条件[72]。迄今,该假说已在美洲牧草盲蝽危害草莓[73]、潜叶虫危害夏栎(Quercusrobur)[74]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然而,一些科学家对此理论持怀疑态度,他们通过试验验证,却得出了相反结果,并定义为资源稀释(Resource dilution)假说[75-78]。
4.3 推-拉假说
推-拉假说是基于化学生态学原理的植食性昆虫生态调控的理论,最先由Pyke等[79]在防控澳大利亚棉田棉铃虫(Helicoverpaspp.)实践中摸索而来。随后,Miller等[80]对该控害措施进行了规范和定义。目前,学术界对该理论已形成共识,一致认为,推-拉假说是将利用驱避物驱避植食性昆虫与运用诱集物诱杀植食性昆虫相结合形成的策略,是一种高效、可持续、无环境污染的控害技术理论[81-83]。“推”的诱因分成2类:1)视觉线索的抑制,即寄主植物的形状、大小、颜色等抑制植食性昆虫的定向与觅食[84-86];2)挥发物的掩盖,即非寄主植物释放的挥发物,能掩盖寄主植物的气味或引起植食性昆虫对寄主植物的排斥行为[87],如天堂椒(Aframomummelegueta)、生姜(Zingiberofficinale)等非寄主植物释放的挥发物对象鼻虫(Sitophiluszeamais)具有较强的驱避效果[88]。此外,合成驱虫剂[89-90]、抗聚集信息素[91]、拒食剂[92-93]等也是引起“推”的因素。同样,产生“拉”的因素分类与上述“推”的类似,只不过,植食性昆虫对前者的响应效应与后者的完全相反[94-96]。
4.4 屏障假说
该理论也被称为“物理障碍假说”(Physical obstruction hypothesis),最初被应用在植物病害领域[97]——主要防控蚜虫传播病毒病[98-99]。2012年,Parolin等[100]提议,此理论也适合于植食性昆虫管理。该假说推断,高秆的非寄主植物(玉米、向日葵、高粱、芝麻等)能够阻隔植食性昆虫在作物系统内多个生境之间的移动与扩散,进而降低了植食性昆虫在较矮的主栽作物上的定殖概率[101-103]。例如,芫荽(Coriandrumsativum)与甘蓝间作后,前者能较好地阻隔小菜蛾在后者田间的危害[104];玉米阻隔甘薯象虫(Cylasformicarius)危害马铃薯[105],同样,红豆(Vignaangularis)和金盏花(Calendulaofficinalis)对该虫也有相同的阻隔效果[106]。此外,这些高秆植物也能阻挡空气流动,这不仅会阻止一些随风扩散的植食性昆虫对主栽作物的侵害[107-108],也会降低较强的风对天敌的伤害风险[100]。然而,Parolin等[100]认为,屏障植物并不一定都是高秆的植株,也可能是一些不容易感染特定病虫害的植物,即非感受性植物(Non-susceptible plant),它们作为主栽作物的掩饰物,抑制植食性昆虫在主栽作物上的迁移与扩散。
4.5 保险假说
Yachi等[109]提出保险假说,并将该假说首先应用于探讨波动环境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生产力关系。随后,该理论被运用到植食性昆虫防控研究中。该假说的倡导者们推测,在某个(些)斑块里,有的物种并没有发挥生物控制功能,但在其他斑块里,却扮演重要角色,提供空间上的“保险”[110-111]。Ives等[112]坚信,在植物物种较多的系统里,当该系统被干扰后,一些表面上似乎多余的植物物种,很有可能肩负起生物控制的功能。最常见的实例,当属天敌在作物与非作物生境之间的移动[6]。例如,作物被播种移栽后,非作物生境的捕食性天敌会迁移至作物生境取食植食性昆虫;随着农田作物的生长发育,这些迁入的天敌在农田逐渐建立种群;当作物被收获后,这些天敌会因缺乏食物或栖息场所而主动迁移至原先的非作物生境[113-115]。此外,该假说还认为,当主栽作物上的优势性天敌数量不足以控制植食性昆虫时,临近非作物生境的天敌会作为“辅助救援部队”,以弥补优势性天敌的控害作用[116-117]。
5 结论与展望
种植诱集植物、间作和地面生草,是从空间上增加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增强了天敌对植食性昆虫的调控作用,表现为植食性昆虫的丰度及其对主栽作物的危害降低。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植物物种多样性会引起“天敌-植食性昆虫-主栽作物”之间的营养级联动(Trophic cascade),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然而,正如任何干扰都有生态两面性[118-126],这些多样化措施作用于主栽作物系统后,也会扰乱植食性昆虫与其天敌群落之间组成结构及其互作关系,有时甚至削弱天敌对植食性昆虫的调控效果[127-128]、加大植食性昆虫危害作物的强度[129-130]。为此,如何利用植物之间相生相克原理,优化天敌对植食性昆虫的调控能力,亟待科学家深度挖掘。
虽然,种植诱集植物、间作和地面生草,对植食性昆虫具有较好的防控作用,但实践中,大面积推广应用这些措施也受一些因素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不同作物的生育期和长势形态的差异,增添了规模化机械播种与收割的难度;2)在主栽作物田,额外种植其他作物,会增加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也会增加农事管理投入;3)多样化种植对病虫防控与农药污染控制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种植者的积极性不高。研发与机械化相配套的多样化种植技术和多功能的智能农业机械,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本研究强调,种植者经营管理的农田系统是人类共有的食物资源载体,不仅要兼顾种植者的经济利益,也要关注农田系统被化肥农药的污染。因此,科研单位、政府管理和技术推广部门应加强合作,对植物多样化种植技术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优势,进行宣传、普及与政策推行,以便发挥土地和植物对人类提供更多更佳的食物以及更美更优的环境。
除植物物种多样性外,植物与动物(如稻鱼共生[131-133]、竹林下养鸡[134]、草原养牛[135])以及植物与微生物(例如,黄瓜套种侧耳[136]、杨树林下套种香菇[137])耦合成的物种多样化模式(该模式可称为“动植物混合物种多样性”),也是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内容。这些不同的物种多样性模式,是否都能提升天敌对植食性昆虫的调控效果、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需要被生态学家逐一证实。除物种多样性外,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另外两个重要的研究层次;后面两个层次对植食性昆虫的影响及其机理,可能与物种多样性的不完全相同。揭示植食性昆虫对这些多样性的响应机制,应该聚焦于分子、个体、种群、群路、生态系统及全球尺度,借助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化学、同质园试验、数据库和整合分析等手段,从上行和下行控制角度出发,剖析不同营养级之间的食物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