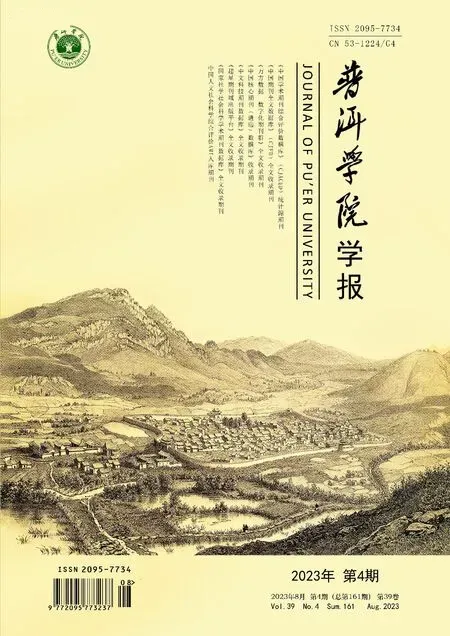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分析
周 怡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六安 237000
纵览莎士比亚戏剧史,莎剧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以《亨利四世》《威尼斯商人》为代表的早期历史剧和喜剧,延至以《哈姆雷特》为典范的中期悲剧作品,最后以《暴风雨》为代表的晚期传奇剧,无不沁入文艺复兴时期独有的人文情感及艺术理念。莎剧蕴含着其对人生、人性及社会的思考,彰显出新时代的精神,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之光熠熠生辉。
一、莎士比亚人文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戏剧作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起至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文艺复兴运动是指14—16 世纪繁荣兴盛于罗马、希腊时代的古典文化在欧洲封建教会统治下的“黑暗时代”日渐萧条衰落,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混沌阴晦时期以后,由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的一场以复兴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为名,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倡导人文主义精神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文化运动。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思想,秉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以“科学和理性”为主要形式,以坚持“人本位”,反对“神本位”为主要内容,竭力颂扬人文主义精神,笃志不倦地为人的精神世界开疆拓土,对近代欧洲文艺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无论是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还是在当今世界对于个人的人格塑造、精神成长还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人文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坚持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的一种文化思潮,其主旨思想聚焦于“人”,强调“以人为中心”,是以人与自然的世俗文化为研究对象,反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神学;关注人的尘世需求,排斥封建宗教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宣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亦可被视为人道主义的雏形。后者将其精神思想视作欧洲社会中一种先进的文化内容,强调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人权、哲学、文学、教育、艺术等人文学科发起的以提倡尊重人性、倡导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冷傲的教义文化,重视在建筑、医学、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学科方面追求科学真理,反对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
二、莎士比亚前期剧作的人文主义精神
作为“时代的灵魂”,深受文艺复兴思潮影响的英国戏剧之父——莎士比亚,通过各类体裁的剧作将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他对人文主义精神中“幸福生活”与“道德宿命”的多元理解。
莎剧创作前期主要指莎士比亚于1590—1600年创作的戏剧(9 部历史剧,10 部喜剧和2 部悲剧)。莎剧故事通常改编自罗马、希腊的戏剧脚本。莎士比亚对源流素材进行了莎氏风格的重新编创,尤其是大量枯燥乏味的对白部分,莎士比亚不仅使用白体诗(无韵的五步抑扬格)或韵文来诗化语言增加了对白的韵律感,还使用了平白直接的口语化散文体台词,使对白更加通俗易懂。因此,经过改编后的莎剧可谓是雅俗共赏,受到了社会各界欢迎,在欧洲社会得以广泛地流传。
莎士比亚早期剧作的对白总是洋溢着对真善美的诚挚追求和热情讴歌,散发出浓郁的诗意及人文意蕴。作为该时期唯一的一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亦不例外,其思想主旨依然是对真挚友谊、坚贞爱情和婚姻自由等人文主义理想中的良好品德的“颂歌”和真善美的“礼赞”。戏剧讲述了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两大家族的子女超越家族世仇诚挚相爱,为爱抗争、双双殉情,双方家族透过儿女的爱情悲歌对自己封建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冰释前嫌、握手言和的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通过子女的爱情理想与家长的陈旧思想的尖锐矛盾制造了系列戏剧冲突,将本剧推向高潮——戏剧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生命为代价,为爱情演绎了一首千古绝唱。艺术手法上,莎士比亚采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一方面,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将男女主人公为追求爱情自由和幸福生活而勇敢斗争的故事描绘得如歌如泣,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力量悬殊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相比,人文主义势微力弱。所以,莎士比亚通过现实主义手法勾画的双双殉情的悲剧情节,是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的行动表达。简言之,罗朱爱情如泣血玫瑰绽放的人文之光征服了人性的幽暗,生命消逝的震撼使封建家长的人性得以洗礼升华,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乐观主义精神。而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以“签约割肉”“恋爱私奔”和“鲍西亚选亲”为三个平行线索,围绕爱情、友谊、平等及博爱等人文主义主题,讲述了资产阶级新人以人道主义准则和法律为武器,与高利贷者之间斗智斗勇,以理性和人性战胜了邪恶和非人性的故事。该剧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道德要求,与旧式社会高利贷者利己主义行为准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充分表达了莎士比亚惩恶扬善的人文主义理想,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法律、金钱等问题的人文主义思考。作品结构清晰、高潮迭起、人物性格鲜明,虽有悲剧元素,但喜剧氛围及色彩更为浓厚。因此,该剧应该属于悲喜剧,它是莎剧由喜剧向悲剧过渡的关键作品,充分体现了莎士比亚歌颂人类美好品格和强调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文主义理想。
三、莎士比亚中期剧作的人文主义精神
政治与文学相互交错、互为影响,而非并行不悖的。政治既需要文学支持,又不能任其自流,文学是政治状况的反映,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的。1603 年伊丽莎白时代结束,詹姆士一世的政治统治残暴昏庸,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经济衰退。在残酷现实面前,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日益幻灭,创作风格也由诙谐乐观变为抑郁愤懑。莎士比亚在该时期创作了很多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经典悲剧,其中《哈姆雷特》最为杰出,是其戏剧文学造诣的最高峰。《哈姆雷特》讲述了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虽然哈姆雷特贵为王子,但他却具有普通人的特质,内心迷茫彷徨却又矛盾重重,他渴望报仇但又拒绝报仇,他理性而感伤,忧郁而睿智。在看到父亲的亡魂后,他第一时间不是燃起复仇的怒火,而是怀疑亡魂的身份。当确定父亲被害后,他又通过“戏中戏”的方式,试探眼前的“国王”是不是残害父亲的真凶。直到真相大白,他才开始他的复仇之旅。哈姆雷特是在封建王室成长起来的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有复仇的热血,却又作茧自缚于自我怀疑和愚钝固执,牢牢地困囿于人心丑陋、社会黑暗和人文主义理想的矛盾深渊。随着剧情的演变,剧中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将哈姆雷特复杂的内心矛盾外化为人文主义理想与封建黑暗势力的哲学矛盾和社会冲突。植根于其内心深处和社会阶层的矛盾与冲突使哈姆雷特注定无法摆脱复仇牺牲品的悲剧命运。
哈姆雷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意蕴,他注重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他是理性的、科学的个体,但因为从他出生那刻起就深深烙在身上的封建思想印痕,使他缺乏反对封建思想的坚定决心,这也恰恰是他悲剧的根源。在复仇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特征的理性与善良,但在追求亲情、友情及爱情时,哈姆雷特彷徨又迷茫,迟疑又固执,无法摆脱优柔寡断的“桎梏”,以致错失报仇良机,最终引发悲剧。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出发,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这一人物塑造暴露了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是封建迂腐思想的根深蒂固的深刻揭示,它左右了人的行为、决定了人的命运,进而制约了幸福社会的实现。作为莎士比亚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哈姆雷特》以王子之死颂扬了人性的尊严,奏响了反封建的前奏。但也指出了人文主义者在构建幸福社会中的“问题”,即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别人,不能寄托于英明的君主。该剧一边呼吁人们在詹姆士执政的背景下,不要迟疑、不要对封建思想残留丝毫幻想,要敢于站出来与假丑恶进行彻底斗争,影射了莎士比亚对詹姆士执政的反对态度;一边借助哈姆雷特的悲剧命运,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与难以冲破黑暗现实的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奥赛罗》中,莎士比亚通过描写奥赛罗因小人的谣言沉溺于嫉妒与猜忌的情绪中,最终杀死妻子的情节,讲述了一个高尚的灵魂被恶意与怀疑所腐蚀的故事,展现了人文主义的悲观前景,强调怀疑和嫉恨是“人”获得高尚品德的最大天敌。
四、莎士比亚晚期剧作的人文主义精神
莎士比亚晚期的戏剧主要以悲喜剧或传奇剧为主,与其年轻时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其中很多作品都带有魔幻主义色彩,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乌托邦社会及道德感化的绝望。如果说《哈姆雷特》《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审视,是对实现美好社会的手段的思考,那么他晚期的作品则充满了绝望和无奈。以《暴风雨》为例,莎士比亚描写了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在孤岛上被道德“折服”,从而浪子回头的过程。即米兰伯爵被弟弟篡权夺位后,独自带着女儿逃到荒岛,他多次使用魔法统治小岛、制造暴风雨,嫁女给王子,最后以米兰伯爵恢复爵位、宽恕敌人、返回家园的大团圆为结局的喜剧。该作品的主题是“和解”与“接纳”,莎士比亚借用贡柴罗之口描绘了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富有、没有职业、没有官职的乌托邦社会,又运用夸张的对白和情节来讽刺所谓的乌托邦社会,暗示了莎士比亚对乌托邦社会的绝望。此外,剧中真正实现“理想”的手段不是道德感化,而是魔法。虚无缥缈的魔法则体现出莎士比亚对道德感化手段的质疑,表达了实现乌托邦社会的手段的绝望。毋庸置疑,莎士比亚依旧是个人文主义者,依旧赞颂真善美,依旧对美好生活抱有希望,但这种希望只能是寄托于魔法。在晚期的其他作品中,莎士比亚依旧采用魔幻的手法来表达自己“无望”中的“希望”,表达自己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执着”。例如《冬天的故事》,讲述了专制的国王怀疑自己的女儿是私生子,将其抛弃。妻子郁郁而终,国王因此充满了悔恨,结局却是被牧羊人收养的女儿长大后历经波折又回到了国王身边,假死王后复活,最后骨肉团聚的故事。从情节铺陈出发,《冬天的故事》虽然融入了莎士比亚的追求女性解放、倡导两性和谐的人文主义情怀,但离奇的情节却暗示了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想如海市蜃楼般不切实际,难以实现。
五、结语
莎剧及其蕴涵的人文主义精神随着政权更迭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相异。从早期代表人文主义理想的历史剧和喜剧,历经中期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冲突的重挫下对人文主义深刻探讨的悲(喜)剧,直至晚期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人文主义理想寄托于魔法的传奇剧,表现了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理想从憧憬、到怀疑、再到无望,也从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的发展历程:即从积极的社会思潮逐渐发展为日渐奢靡的社会风气,致使人文主义精神成为“虚谈”。莎士比亚虽具有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但毫不影响莎剧对世界文学人文传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