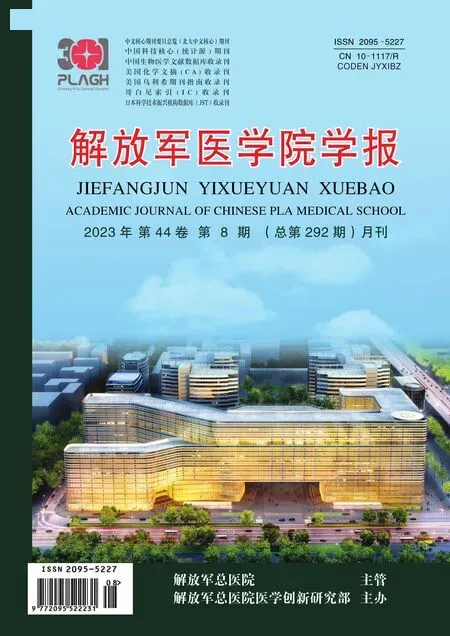高原低氧环境对肠道菌群影响的研究进展
杜文琪,闫 馨,马 燕,张 伟
1 青海大学高原医学研究中心,青海西宁 810001;2 青海大学医学部,青海西宁 810001;3 高原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青海西宁 810001;4 青海-犹他高原医学联合重点实验室,青海西宁 810001
肠道是人体共生细菌的最大储存库。肠道菌群是肠道微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促进形成稳定的营养平衡微环境,与人体相互作用,影响免疫、代谢和疾病的形成。越来越多的证据强调肠道微生物群在人类健康和疾病中的重要性。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是宿主选择和共同进化的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低压缺氧是高原环境的一个主要特征,导致生活在高原上的个体发生许多变化。暴露于低氧环境会增加胃肠道炎症、氧化应激和胃肠道通透性,同时伴有血浆代谢组学和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及活性的变化[2-3]。本文对高原低氧环境如何影响肠道菌群变化及其可能原因进行综述。
1 肠道菌群及其影响因素
肠道菌群已鉴定出的细菌包括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梭杆菌门、疣微球菌门和蓝藻菌门等。其中,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占总数量98% 以上[4]。肠道菌群的功能类似于内分泌器官,产生生物活性代谢物,如三甲胺-N-氧化物、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可以干扰宿主的生理功能[5]。肠道菌群失衡和肠道功能障碍与多种疾病有关,包括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力衰竭、肥胖症和糖尿病等。胃肠道中丰富多样的微生物群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肠道屏障的维护、营养代谢、抗肿瘤作用和免疫调节等。肠道微生物群在一生中会不断影响肠道屏障功能和完整性[6],对于肠上皮屏障功能的维护和生理稳态的维持至关重要[5]。肠道菌群与免疫系统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在肠道菌群缺乏的情况下,肠道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7]。
肠道菌群在出生期间或出生后不久定居在人类肠道中,并持续生长和发展,直到在成人肠道中建立稳定的环境,随年龄持续增长又会进入老年退化期[8-10]。目前研究发现的影响肠道菌群的因素有很多,肠道菌群的变化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肠道菌群的可变性和复杂性受到生活方式的影响,包括饮食、运动、心理和吸烟等;此外,环境、衰老、药物和疾病也会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11-12]。环境因素对微生物群的稳态控制也具有重大作用,包括温度变化、氧气浓度和大气污染等[13-14]。
2 高原低氧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与免疫、激素和代谢稳态、各种疾病和特定的环境密切相关。肠道微生物群是人类适应环境的重要指标。生活在不同海拔地区的人,肠道微生物群组成是不同的。环境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在动物和人身上都得到了证实。
研究人员在低氧条件下饲养的小鼠中发现了不同于氧供给充足条件下小鼠的粪便微生物群落,但在α 多样性方面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15]。功能分析表明,受高原低氧影响的微生物群落与多种代谢途径相关,这进一步表明高原低氧可改变微生物群落,从而导致生理和代谢功能障碍[15]。采用低压氧舱模拟海拔5 000 m 高度,构建8 周龄雄性小鼠低氧模型,随机分为1 d、3 d、5 d、7 d、14 d 和 30 d 低氧组和常氧对照组,通过16S rDNA测序分析发现不同低氧时间组与其常氧对照组的肠道菌群构成有统计学差异,在菌属水平上,低氧组中普雷沃菌属、阿克曼菌属、颤螺菌属、拟杆菌属、脱硫弧菌属和臭气杆菌属,相对丰度较高且有统计学差异(P<0.05)[16]。Sun 等[17]也发现高原低氧环境导致大鼠粪便中拟杆菌属数量显著增加(P<0.05),而棒状杆菌、普雷沃菌属和粪球菌数量下降(P<0.05)。此外,高原低氧环境导致大鼠肠道菌群代谢活动减弱,改变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大鼠迅速上升到平台期后,对阿司匹林的吸收增加[18]。Zhang 等[19]同样发现高原低氧环境可引起肠道微生物数量和组成的变化,改变了肠道菌群的代谢活性,这些变化会增加硝苯地平的生物利用度。Wan 等[20]将小鼠分为平原组、高原低氧组和高原低氧给予益生菌组,平原组小鼠肠道菌群以乳杆菌科为主,高原低氧组小鼠肠道菌群以葡萄球菌科为主,高原低氧环境下给予了益生菌后的小鼠肠道菌群组成与平原组小鼠相似。葡萄球菌与肠道感染密切相关,是肠道潜在的致病菌。这一结果表明高海拔缺氧环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致病菌成为优势种。但这一假设有待后续研究分析来确定。Pan 等[21]将大鼠放入低压低氧环境中,发现低压低氧可导致大鼠肠道菌群组成发生长期变化,其特征是副杆菌属、另枝菌属和乳球菌属的丰度增加,拟杆菌属与普雷沃菌属的比例增加。
通过比较海南、南宁、贵州、西昌、剑川和西藏地区的中国恒河猴种群肠道菌群特征,同时也发现不同地理环境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恒河猴肠道菌群在门水平上主要由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组成,这种情况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相似,西藏恒河猴厚壁菌门丰度高于其他5 个地区恒河猴,拟杆菌门丰度低于其他5 个地区恒河猴,西藏类群厚壁菌门丰度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瘤胃球菌科和克里斯滕森菌科的显著增加[22]。Ma 等[23]发现高原低氧地区食草动物往往具有相似的肠道菌群组成,这也表明其肠道菌群可能参与了机体适应高原低氧环境。
一项关于在高原地区居住时间不同的汉族和藏族人群肠道菌群变化的研究,共采集了393 例中国青年男性的粪便和血液样品,包括了居住在平原的汉族96 例,在青藏高原居住4~ 6 d 的汉族61 例,在青藏高原居住3 个月以上的汉族50 例,离开青藏高原并在平原地区生活了3 个月的汉族84 例,以及家族世代生活在高原的藏族102 例[24]。该研究提供的数据表明,在高原居住4~ 6 d,汉族个体的肠道菌群发生了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在高原上至少维持3 个月,与平原汉族人群相比,高原汉族人群的肠道菌群与藏族人群的菌群更相似,高原低氧环境对肠道微生物区系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是快速、一致、定向和持久的,并且微生物区系的变化可能与汉族人群的高原适应过程有关[24]。高中山等[25]收集了8 例高海拔藏族(海拔3 600~ 4 500 m)冠心病患者、14 例中海拔(海拔2 260 m) 冠心病患者和14 例低海拔(海拔13 m)冠心病患者的粪便组织样本,并对肠道菌群做了16sRNA 测序分析,发现高海拔冠心病患者肠道菌群与中低海拔患者相比,在α 多样性和β 多样性方面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肠道菌群组成方面,高海拔组也显示出不同于中低海拔组的特征,其致病菌如链球菌、埃希菌_志贺菌和克雷伯菌的相对丰度下降,有益菌如粪杆菌、产黑素普雷沃菌、链型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升高。
通过既往的研究结果发现,环境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是明确的,高原低氧环境下动物和人肠道菌群的改变都是显著的,但具体到菌属的变化会有不同的研究发现,其可能是氧浓度不同、海拔高度差异、在高原低氧环境下生活的时长及饮食方面的差异等原因造成。
3 低氧环境造成肠道菌群改变的可能原因
高原低氧环境会对人体功能和发育造成影响,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人适应高原环境的机制是不同的。藏族人为了适应低氧环境,在进化过程中部分基因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自然选择的结果。全基因组相关研究揭示了EPAS1 和EGLN1 基因含有的序列变异,在高原世代居住人群中高度富集,在平原地区不存在或很少[26-27]。EPAS1 基因编码转录因子低氧诱导因子-2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2α,HIF-2α),刺激红细胞的产生,从而增加血液中血红蛋白的浓度和血液黏稠度,但在世代居住于高原低氧地区的人群中EPAS1 会发生变异,这一变异体在高原低氧地区只会轻微提高血红蛋白和红细胞水平,血红蛋白浓度随着海拔的增加而增加很少或没有变化[28-30]。藏族人群的EGLN1 基因携带两个特有的错义突变,这导致缺氧条件下HIF 降解增加,从而减轻HIF 介导的红细胞生成增加,保护人在高海拔地区免受红细胞增多症的影响[30]。有研究发现基因的差异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发生变化[31]。Wu 等[32]研究发现HIF-2α 可以通过控制肠道Ldha 基因的表达正向调节肠道乳酸水平,从而影响肠道菌群的改变,使乳酸水平降低,拟杆菌减少,扭链瘤胃球菌增加。
根据以往研究,高原低氧环境下,参与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和能量代谢的基因及肠道菌群相对丰度会增加。有关研究发现高低海拔人群之间在梭状芽孢杆菌属、脱硫弧菌属、拟杆菌属、乳酸杆菌和普雷沃菌属方面有统计学差异。这些微生物群均与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的产生有关[33-34]。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有很高的能量需求和肺动脉压力[35]。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通过参与宿主代谢而在宿主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肠道菌群可以利用结肠中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并产生SCFAs,主要是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36]。SCFAs 可作为肠上皮细胞的能量来源,还广泛影响细胞功能,可能具有抗癌和抗炎的潜力,并在饱腹感和氧化应激中发挥作用[37]。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的SCFAs 也具有降压作用,这种降压作用可能是依赖于丁酸盐的直接血管舒张作用[38]。丁酸盐被认为是上皮能量稳态的有利代谢底物。在氧气不足情况下,高浓度的丁酸盐可以调节代谢避免糖酵解,并进一步利用丁酸盐[34]。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通过调节获取的能量和血压应对高原缺氧环境的反应,从而影响健康状况[39]。此外,短链脂肪酸可以降低宿主血压,缓解肺动脉高压,保护心肌功能,帮助机体高效利用能量以适应高原环境[40]。Du 等[41]的研究也发现可以通过重塑肠道菌群来适应新环境,肠道菌群通过增加宿主能量和多糖生物合成,促进宿主对高原低氧环境的适应。
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使高原人群与平原人群在生活饮食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已经有研究确定拟杆菌属和普雷沃菌属的比例是人类肠道菌群个体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拟杆菌属和普雷沃菌属的比例也与长期习惯性饮食模式相关,但在短时间内似乎相对稳定,即使有重大饮食变化也是如此。这些发现也表明,拟杆菌属和普雷沃菌属的比例可以作为一个用于识别可能对高原低氧作用更敏感的个体的标记[42]。
高原低氧对于肠道菌群结构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尚未见报道。综上所述,肠道菌群的改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世代居住在高原低氧环境下的人群会发生特定的基因改变来适应环境,基因的改变从而也会影响到肠道菌群的变化。
4 结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肠道菌群受环境的影响较大,高原低氧环境可以塑造肠道微生物群落,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结构,但人们对于高原等极端环境对肠道菌群影响的认知还远远不够。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低压缺氧暴露后肠道微生物群发生了变化。然而,这种微生物组的变化究竟是宿主生理变化的衍生反映,还是协同加剧了高原疾病,仍难以确定。高原恶劣环境在人群中形成了自然选择的结果,低压低氧、低温和高辐射等外环境条件影响了生物体的繁衍与生存,也加速了人群的进化和生理改变,同时对不耐受人群也造成了高原反应或高原疾病,引发机体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不仅会受到高原环境的影响,本身也可以作为重要的调控因子,反过来调节机体的适应过程。肠道菌群合成的各种酶、代谢产物和分解宿主肠道物质所生成的各种小分子,均有可能通过各种信号通路影响机体对高原环境的反应程度。
不同海拔高度人群和高海拔不同民族肠道菌群具体是如何变化的,高原环境对人肠道菌群的影响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哪些机制,是否与高原病存在相互关联,都还有待继续研究,可通过哪些更有效的手段来避免高原肠道菌群失衡也需要不断探索。这对于高原土著居民、初入高原人群和驻守部队官兵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贡献杜文琪:总体构思,起草和修改论文主要内容;闫馨:总体构思,起草和修改部分内容;马燕:总体构思,对文章知识性内容进行审阅;张伟:总体构思,监督指导。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