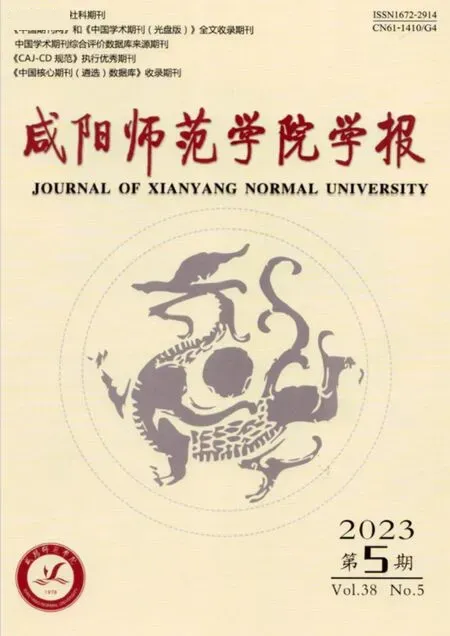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关系论要
陈文畑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文法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
诗乃唐“一代之文学”,唐诗繁荣的具体表现,大致可概括为“名家荟萃,菁华宏富”“题材宽广,内容丰富”“体制完备,形式多样”“百花齐放,风格繁多”“继往开来,影响深远”等五方面特征。[1]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多年以来,学界已有颇具价值的探讨,或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交融等外部因素加以分析,或从诗人和诗歌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加以解释。吴相洲曾在《唐诗繁荣原因重述》中对这些解释加以归纳,得出以下数端:一是经济的繁荣为诗人们提供了四处漫游的物质基础;二是皇帝的提倡开启了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诗赋取士吸引了众多士子致力于诗艺探索,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诗人们敢于直抒胸怀;三是相关艺术的繁荣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滋养;四是佛教道教的兴盛促使诗人对人生和艺术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五是前代诗人的各种创作试验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2]以上诸端,均是推动诗歌在唐代实现繁荣的重要因素。从艺术发展规律而言,文学创作的繁荣离不开“继承”和“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两个方面。从这一角度对以上所举五种影响因素加以考察,第五点所言为继承,继承前代诗歌艺术的沉淀,第一至第四点所言为实现创新的动力、条件和素材来源。
家族作为社会的基础细胞并对社会文化生活形成多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自古有“知人论世”之说,从文学阐释的角度强调了环境对于作家及其作品的塑造,家族无疑是影响唐代诗人创作极为重要的环境因素。是以,本文尝试从家族意识在上文所言五种影响因素中的存在、在诗歌艺术继承和创新两个环节之中所发挥作用入手,讨论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之间的内在联系,概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影响家族文学观念和创作法度的继承,助推唐诗的繁荣发展
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唐诗的繁荣离不开对前代诗人创作经验的吸收借鉴。前代艺术经验之所以能够在后世实现继承并产生影响,其所依赖之方式大致有二:一是社会传播,二是家学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家族已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学教育,一些家戒类文章和家训著作,对家族文学教育多有涉及,如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张融的《门律自序》、梁简文帝的《诫当阳公大心书》等均如此。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也有《文章》篇讨论文章撰写之事,文中还有言曰“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3]243。此外,《世说新语》和一些史籍文献也对文化家族开展文学教育的情况有过细致描述,谢玄与族子讨论《毛诗》和咏雪之事即其例。家族之中文学人才辈出,族子能够在文学创作上祖袭先辈、承荷家声者,在当时往往能够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许,成为足以矜夸的荣耀。[4]文化家族的文学传承在唐代依然普遍存在。随着唐代科举对诗赋的强调,文化家族对文学传统的延续更为重视,这种重视无疑是家族溯源意识、延续意识与责任意识的交融流露。而唐代众多诗人在若干文化家族中的集中出现,便是文化家族实现文学传统延续的最好证明。“集中出现”既有共时性的,即一个文化家族在同一时期出现多名“善诗之士”;也有历时性的,即文化家族往往存在“代有诗才出”的情况。有的家族甚至终唐一代能够出现多名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杰出诗人。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了文化家族文学传统的延续对唐诗“质”和“量”上的繁荣所作出的实质性贡献。下文试举诸例以见文化家族诗学传承的情况。
隋末大儒王通的家族人才辈出,其兄王度、王凝专注儒学、史学,颇被世人所称道,弟王绩为初唐著名诗人,子王福畤以才学称名于世。王福畤子王勔、王勮“磊落辞韵,铿鍧风骨,皆九变之雄律也”[5]76,子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王福畤友人杜易简常称勔、勮、勃三兄弟为“王氏三珠树”[6]5005。王勃声名尤盛,崔融曾言“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其时海内将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为“四杰”[6]5003。王勃的三个弟弟王助、王劼、王劝,同样有突出的文学才能,胡应麟《诗薮》中有“六王”之称,其言曰:“勃兄弟六人,并以文学显,殆古未有。今但传勮、勔、勃三珠树,助、劼、劝稍晚出,遂鲜知者,实六王也。”[7]170
陕郡姚崇家族亦颇出善诗之士。姚崇出身官宦家族,其高祖、曾祖、祖父均为前朝五品以上的高官,父亲姚懿于唐初曾任嶲州都督、硖州刺史等职,属于清望官,列流内官的最高品秩[8]。姚崇以门荫入仕,为孝敬挽郎,又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参军,五迁夏官郎中,后官至宰相,史称贤相。姚崇长于诗文,今存诗虽仅有六首,然已足见诗才。如其所作的《夜渡江》,谭元春在《唐诗归》中赞为“静思妙手”[9]84;所作《秋夜望月》,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评曰“琢不留痕,率不露迹,高亦不亢,清亦不洗,洵五言宗匠”,并以“波入夜池寒”句为“咏月神语”[10]103。姚崇曾侄孙姚合,在当时也享有盛名,据他在《寄贾岛》中自称,有“新诗有几首,旋被世人传”[11]13的情状,其诗风在后世颇有影响。姚崇裔孙姚岩杰,也有一定的诗文名气。
京兆韦氏家族先后出现了韦应物、韦庄两位著名诗人,《全唐诗》中尚存诗作的还有韦承庆、韦承贻、韦元旦、韦嗣立、韦安石、韦抗、韦述、韦丹、韦济、韦建、韦迢、韦元甫、韦夏卿、韦执中、韦渠牟、韦皋、韦杼、韦式、韦处厚、韦瓘、韦蟾、韦镒、韦绶、韦澳、韦希损、韦坚、韦洪、韦斌、韦振等30余人。此外,见于史传记载但作品已佚者,如韦执谊,据《旧唐书》载:“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年才二十余。德宗尤宠异,相与唱和歌诗,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备顾问。”[6]3732又如韦湑、韦温兄弟,据《新唐书》载:“颇以文词进,帝(中宗)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乐。”[12]5844
唐代弘农杨氏亦颇有诗文之士。尤为知名者如初唐杨师道,据《新唐书》,杨思道“清警有才思”,“与文士燕集”,“捉笔赋诗,如宿构者”[12]3928;有“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另如杨巨源,张籍曾在《送杨少尹赴凤翔》诗中称其“诗名往日动长安,首首人家卷里看”[13]4346,王夫之曾评价他的“七言平远深细,是中唐第一高手”[10]215;又有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的杨凭、杨凝、杨凌兄弟,俱善文辞。
另如河东柳氏家族、京兆杜氏家族、薛道衡家族、刘知幾家族、乔知之家族、独孤及家族、韩愈家族等也均诗才辈出。王维、王缙兄弟也俱有俊才,以文翰著名。诸如此类文学家族的存在,足可称为唐诗创作的中坚力量。
家族文学传统的延续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在尤其强调家风、家学、家法传承的社会背景下,常常可以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文体风格中窥见切实的家族印迹。其中的典型例证,如自称“诗是吾家事”的杜甫承继并发展了祖父杜审言的诗风诗法,将律诗的创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白居易弟行简,据《旧唐书》载,“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6]4358。自称“我祖文章有盛名”“世业相承及我身”的皎然,对以谢灵运为核心的陈郡谢氏诗学推崇备至,并在继承谢氏文学观念、诗歌创作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了诗学新变。来自于桂州而自称曹操后人的曹邺,虽其家族溯源似乎经不起推敲,却并不影响他模仿建安诗风,积极创作古风乐府。优秀的诗人们,其文学观念和诗歌创作的核心特征,往往会受到来自于家族不同程度和层面的影响,因而展现出一定的家族色彩。这是家族意识影响唐诗繁荣之“质”的又一呈现。
二 影响诗人对思想观念的汲取与接受,深化唐诗思想内涵
唐代是一个思想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时代。唐初,儒学的复兴已成为政治学术的主流,终唐一代,儒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佛教之入中国,蝉嫣五六百年”,至于隋、唐之时,进入了“极盛时代”,“唐代之于佛教,不独译经求法、分宗立寺为最盛也,即整理佛教经籍,亦以唐为大。藏经之确定,即缘于开元释教之目录”[14]484-492。道教至隋唐,也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开启了“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南北朝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道教教主老子“被尊为唐宗室的‘圣祖’,成为唐皇朝的护国神”,“唐代在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唐皇朝的扶植和崇奉。当时道教宫观遍布全国,道教信徒众多”,除道教理论之外,“道教科仪、道教艺术以及炼养术等各个方面均得到全面的发展”[15]249-266。
唐代思想的开放对于文人及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推动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若从唐代文人个体对思想的接受而言,社会思潮连同地域风气的浸染固然是主要途径,其中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师承授受。此外,家学传承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文人对不同思想的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家族既足以为思想的接受提供铺垫,也可以为思想的传播设置藩篱。
以下以杜甫家族的儒史传承,以及王维、柳宗元、陈子昂、李白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差异二例对此加以阐释。
杜甫源出京兆杜氏的一支襄阳杜氏。京兆杜氏的儒学传统可上溯至西汉时期的“小冠子夏”杜钦。下至魏晋,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曾作《春秋左传经传集解》,据《旧唐书·礼仪志》和《贞观政要》所载可知,从太宗贞观年间,“杜预开始进入了配享孔子庙堂的儒家先贤之列,享有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年官方春秋祭奠的崇高地位。自此以后历世不绝”,“在唐朝廷和地方州县推尊杜预等儒家先贤的同时,杜氏家族自身也开始通过在杜预墓次营建祖茔这一举动着意建立与之联系的有形纽带,强化家族内部尊崇这位远祖的氛围。”[16]杜甫曾作《祭远祖当阳君文》,当阳君即杜预,祭文追溯了杜氏家族的起源,“初陶唐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旧德”,以及杜预的“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建侯于荆,邦于南土”“春秋主解,稿隶躬亲”的德业,并感叹“苍苍孤坟,独出高顶,静思骨肉,悲愤心胸”、“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17]1620。所谓“不敢忘本,不敢违仁者”,指的就是继承杜氏家族深厚的儒学传统。杜甫一生以儒士自居,儒家精神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特征在其诗歌中表现明显,浓郁的家国情怀即是典型呈现。杜氏家族的史家精神在杜甫的身上也得到传承,如杜甫诗即被称为“诗史”,据《本事诗》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8]18胡震亨《唐音癸签》有“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19]275。张高评认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揭示了《左传》以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历史叙事,诠释孔子《春秋》经。杜甫新乐府之‘诗史’叙事,绍述其祖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历史叙事,薪传《左传》揭示之‘《春秋》五例’,发扬孔子《春秋》藉其事、凭其文,以寓寄微辞隐义之书法义法”[20]。此说对于杜甫“诗史”与杜氏家族史学底蕴之内在联系,剖析甚精。晚唐杜牧同为杜预一支后裔。杜甫曾作诗多首赠予从侄杜位,杜位的兄长,是官至宰相、曾撰史学著作《通典》的杜佑,杜佑是杜牧祖父。杜牧亦推崇杜氏家学,他曾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留诲曹师等诗》等诗文中追溯杜氏家世,也曾在诗文中表达对杜甫的崇敬,如《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中所说的:“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21]160薛雪曾言:“杜牧之晚唐翘楚,名作颇多,而恃才纵笔处亦不少。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而已哉。”[22]152从诗歌的思想内容而言,杜牧集中既有《感怀诗》《李甘诗》《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等积蕴着儒士家国情怀的史诗篇章,又有《过骊山作》《过华清宫绝句》《华清宫三十韵》《过勤政楼》《题武关》《兰溪》《题魏文贞宅》《赤壁》《泊秦淮》饱含忧患意识的咏史绝唱,此类诗作及其思想精髓是杜氏儒史家学对杜牧深刻影响的体现。
唐代诗人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如上文所举诸位诗人王维、柳宗元、陈子昂、李白,均对佛教义理有所接受,然接受程度之深浅不一,差异存在的原因与各自家族有着密切联系。
王维一生服膺佛教,对佛学义理的研习体悟达到极高的境界,这与王维母亲崔氏笃诚的佛教信仰关系密切。王维母亲亡故,王维表乞将母亲奉佛山居草堂精舍施作佛寺,在《请施庄为寺表》中,他描述了母亲长年累月精进修行之情状:
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园,并是亡亲宴坐之余,经行之所。臣往丁凶衅,当即发心,愿为伽蓝,永劫追福,比虽未敢陈请,终日常积恳诚。[23]320
受母亲佛教信仰及修行的影响,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兄弟二人同样笃信佛教,有着类似的供奉佛教的修行行为: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6]5052-5053
王维自幼接受来自于母亲的耳濡目染,他的佛教信仰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贯穿一生。在人生顺遂之时,他借佛教以修养情性,当遭遇困窘之时,他又能借佛教实现自我解脱。王维的部分诗歌营造出了诗佛交融的境界,他以诗的方式描述佛教修行的体验,而佛教修行也为他的诗歌带来了独特的韵味,其中禅意与山水共融之篇章成为王维独具一格的山水诗。
柳宗元家族源出河东柳氏。河东柳氏对佛教有着长期的信崇。“北朝时期,蒲坂等地是河东地区重要的佛教信仰与传播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地区大族信仰佛教也是比较常见的”,是以,早在北朝时期河东柳氏的佛教信仰就比较普遍,“中晚唐以后,河东柳氏信奉佛教的现象更常见”[24]213-219。柳宗元为其从兄柳元方所撰的《万年县丞柳君墓志》有“少孤,季父建,抚字训道,通《左氏春秋》,贯历代史,指画罗列,接在视听,嗜为文章,辞富理精”,“常好竺乾之道,自搌尘昏之外,泊如也”[25]1389-1390。其中,“竺乾之道”即指佛学,可见其兄属于儒佛兼修。柳宗元的母亲也笃信佛教,柳宗元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写道,母亲卢氏“世家涿郡,寿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岁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25]325。由于家族绵延的佛教信仰传统,柳宗元与佛教之间也无甚隔阂,他服膺佛教,并曾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写道,“或问宗元曰:悉矣!子之得于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对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25]671佛教义理对于柳宗元的思想确有实质性的渗透,且在诗歌中颇有呈现。
陈子昂对佛教也有所接触。陈子昂所效忠的武周,曾有意推广佛教,他在时风影响下接触佛理教义,也是极为自然的事。陈子昂今存诗中,有与“晖上人”之间的6首酬唱诗,闻一多先生认为,晖上人即是玄奘的弟子圆晖。酬唱诗或多或少地表达了陈子昂对佛禅境界的向往。陈子昂天资异于常人,从他的赠僧诗中,可见他对佛义的领悟和一定程度上的接受,诗歌如《酬晖上人夏日林泉》《夏日游晖上人房》颇具禅趣。然而,佛禅在他某一阶段的心境中,或许曾起涟漪,但最终并没有真正融入他的人生和思想,也没有成为他的归宿。受“儒学传嗣”[26]149和“家世好服食”[26]15等家族传统的影响,他对儒道二者的尊崇,更占主流。
李白诗歌中也有佛教元素的文学表达,从特定的诗歌载体上看,主要集中于“社交应酬性作品”之中;从表现形式上而言,主要体现在对佛典语汇的运用。李白对佛教思想的接受是有限的,“故作品的意义世界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佛教思想未能进入诗歌的意境创造”,所以他也“未能形成诗禅融合无间的诗歌意境”[27]。李白自始至终都对道教怀抱着极大热情,视之为归宿,且数十年不渝地追求神仙梦想。此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素蓄道义”使“名为朕知”的想法,也有借“遐登蓬莱”以“挥斥幽愤”的情感需求,同时也与其强烈的“谪仙意识”相关。李白“谪仙意识”的最初萌发,与其自幼的家族暗示有着莫大关联。李白的族叔李阳冰曾在《草堂集序》中解释了李白名字的缘起:“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由此可见,“李白父母是把他当做转世仙人来看待的,李白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并从少年时代开始即以一生不悔的好仙道实践证实了这一点”[28]。
由上文可见,王维、柳宗元对佛教有着较为彻底的接受,思想上的深度融合影响了他们二人诗文创作的核心特征,陈子昂、李白对于佛教则只是了解性的接受。以上四位诗人对佛教的接受之异,稍能管窥家族因素对诗人思想接受及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
三 影响诗人的生命轨迹,拓宽唐诗社会历史画卷
远离乡闾的游历开拓了文人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阅历,深化了他们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上文所引杨世明《关于唐诗的繁荣与分期诸问题刍议》一文对唐诗所描述“人世间”“世象、景象、兴象”的罗列,其中的山河、边塞、都会、蛮荒、宴享、叙事、民俗、风情、酒肆、青楼、寺观等类别,大多与文人游历有直接关系。[1]
文人远游以事求学、干谒、赴举、佐幕等,其目的离不开追求功名与仕进,而“耀族”“荣亲”“养亲”等观念的存在,是促使和支撑他们建构和追逐人生理想过程中虽非唯一但却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在家族责任意识和延续意识的助推下,文人从乡里奔赴遥远而广阔的山川、城隅、都市,从家族走向陌生却精彩纷呈的交游际会。陆机在《文赋》中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所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29]20-60诸语,均指明了丰富的物象和素材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物色”篇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30]566,其理亦然。故闾与家族圈毕竟是熟悉而狭窄的,文人们在行万里路中频频感物兴怀,唐诗的物色情境也因此更显纷繁摇曳。据《新唐书》,张说“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12]4410。文人们因游历得到了自然环境的陶冶、社会环境的浸染、创作热情的激扬。是以,随幕出塞的陈子昂有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6]276的风骨咏叹,边塞风情与其豪家子性情相碰撞,造就了《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赠赵六贞固二首》等“以气格为诗”的吟唱。孟浩然则有了《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31]282的奇妙之句;王维有了《少年行四首》其一中“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23]258的豪迈诗句;岑参留下了《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火山云歌送别》等“雄奇”之作;贾岛有了《忆江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32]254的“灏气”充盈的名句;杜牧有《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21]266和《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21]695的跌宕流畅之句。山川风物、民俗风情、人世百态映入了诗人们的视野,投射在他们的心灵,从而也走进了他们的诗歌世界,这些同样可以称为“江山之助”。
如果说,远游拓宽唐诗的社会历史画卷,从而助推了唐诗的繁荣,那么这也就说明了家族意识与唐诗内容广度之间的关联。
四 激发诗人的创作动力,丰富唐诗情感积淀
“诗缘情而绮糜”[28]99,情感是诗之所以为诗、诗之所以感人肺腑的实质性存在。唐诗正因倾注了诗人们真挚且丰富的情感而异彩纷呈。上文言及唐诗繁荣的表现之一还有“百花齐放,风格繁多”。在某种程度上,风格亦为情感之展现,情感基调之异是造就风格之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情感之丰富也就直接影响了风格的多样化。在诸种以家族为缘起的诗性情感书写中,最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往往是被家族亲缘归属意识、地缘归属意识和家国责任意识所激发起的情感书写。
普遍性的背井离乡,心甘情愿或情非得已的游历、仕宦和贬谪,给唐代文人创造了更多的别离,更深的对亲族和乡关的眷恋和思忆。许多传唱千古的佳作,例如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月夜》、孟郊的《游子吟》、王维的《杂诗》、岑参的《逢入京使》,正属此类。
家国责任意识点燃了诗人们追逐功名的热情,家国情怀激发了他们的雄心壮志。理想的实现让诗人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则催生了他们顾影自怜的悲鸣与怀才不遇的咏叹。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33]126即是一首包蕴着强烈家族情愫的经典之作,带着光耀门楣的狂喜。元稹、刘沧、徐夤、韦庄、卢肇、张孝标、袁皓等也均有类似的及第诗存世。另如张九龄《和裴侍中承恩拜扫旋辔途中有怀寄州县官寮乡园故亲》中的“自家来佐国,移孝入为忠”[34]284、郑愔《塞外三首》其一中的“丈夫期报主,万里独辞家”[13]1106、刘长卿的《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中的“唯有家兼国,终身共所忧”[35]350等诗句中深厚的家国情怀,也均被历史所铭记。
唐诗中的某些作品也书写了家族责任与个人志趣之间的摩擦,如前文所举萧颖士《游马耳山》的“宿心尚葛许,弥愿栖蓬瀛。太息宦名路,迟回忠孝情”、《蒙山作》的“白鹿凡几游,黄精复奚似。顾予尚牵缠,家业重书史”[36]133-135,顾非熊《陈情上郑主司》的“求达非荣己,修辞欲继先”[13]5831等,即其例。诸如此类,诗人真诚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唐代文人更为立体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丰富了唐诗的情感积淀。
综上,推动唐诗实现繁荣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家族意识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当然,家族之于唐诗的影响不是孤立的,通常是与其他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发挥作用,在唐诗的题材内容、思想情感、风格形式等方面均有所展现。家族意识不失为唐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