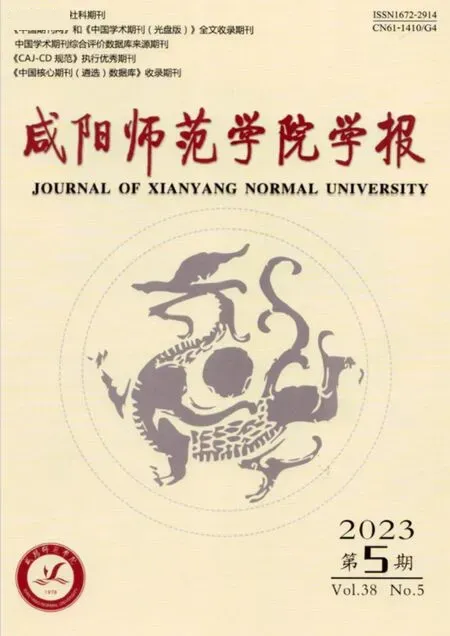汉魏六朝诗歌对《史记》实录精神的取法
苏悟森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扬雄曾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738,这是对司马迁史德史才的充分肯定。“实录”不仅是一种史学笔法,更是一种史学精神,它包含着批判现实政治的巨大勇气,反映社会民生的理性自觉和刚正深广的忧患意识。《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影响了古代的史书写作,还影响着历代的诗歌创作,这在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汉末至六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世积乱离,风衰俗怨”[2]674的现实催生了众多记述时事、反映民生的诗史之作。这些诗作所表现出来的评论时事之热忱、反映民生之广泛、揭露问题之自觉,正是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
一 世积乱离:反映时事民生的直笔之诗
汉魏六朝诸多诗作都以直书其事的方式实现对时政的评价,通过这些时评,乱世的政治风貌和社会生活都得以清晰呈现。
东汉初盛之期虽不是乱世,但已经蕴藏着众多潜在危机。梁鸿《五噫诗》就揭露了盛世背后潜藏的社会矛盾。梁鸿生活在光武至和帝的盛世,然而他登高远眺帝京,看到的却是统治阶层“宫室崔嵬”和底层民众“人之劬劳”的两级情形,二者的强烈反差,深刻地暴露了盛世光华下的腐朽统治,从而传达出诗人深重的忧患意识。这种见盛观衰的思维模式,与司马迁极为相似,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是通过平准政策、酷吏制度、外交态度的展现,揭示了汉武盛世背后的巨大隐忧。二者一以诗一以史,记录了同样真实的时代现状。
到了汉末,时局更加动荡,三曹七子的诗歌对此多有反映。例如曹操《薤露行》和《蒿里行》两首乐府诗就以直笔记录了汉末的动荡历史: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3]83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3]85
关于此二诗,明人钟惺就曾评价它们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4]1。而我们通过诗歌的描述,也确实可以约略还原汉末那一段动乱史事。《薤露行》揭示了汉朝倾覆的原因,即所任非人。诗人指责了何进等人的刚愎无知给宗庙社稷带来的损失,也鞭挞了董卓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通过诗歌,汉末统治集团内部的无能与腐朽,董卓对政权及社会的破坏与摧残,都得以清晰地展露。《蒿里行》则记述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情景。在诛讨董卓匡复天下的过程中,各路军阀并非同心协力,而是各怀鬼胎,进行着“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的内部倾轧,由此导致了“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的悲惨结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表现了诗人对苦难现实的沉痛哀悼。这两首诗歌以宏观而富有表现力的视角,展现了汉末乱离下的社会民生。其后,曹植《送应氏》一诗也记录了董卓西迁屠烧洛阳的时事,诗人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焚烧后洛阳颓圮、萧条的景象,从而揭露出董卓之乱对社会民生的巨大损伤。王粲《七哀诗》也反映了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诗歌一开篇即概括描写了中原丧乱的可怖事实,接着又具体展现了子母不能相顾的途中所见,二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汉末民生凋敝的触动与体认。
除了三曹七子之外,蔡琰五言《悲愤诗》更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诗史佳作。诗人叙述了自己流离失所、委身匈奴、别离二子、归来重嫁的血泪史,表露了其悲痛难言的心路历程。但是,诗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自己身世的感伤中,而是以如椽大笔记录了汉末史实。诗歌一开始就勾勒出时局变迁的线索:“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在描述完时局背景之后,诗人着重描绘了董卓之众的倒行逆施:“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诗人更是通过对被虏人群具体而微的描写,展现了董卓之乱中的民生形态:“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5]199-200面对这样的人世惨剧,诗人发出“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的悲愤呼号。蔡琰自觉记录史实、反映民生的博大胸怀,很难说没有受到史学担当精神的陶冶。蔡琰父亲蔡邕是汉末著名史学家,深受《史记》影响,以至于临刑前还“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6]2006,由此可见其对史迁精神的认同,只是最终王允还是以“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6]2006的理由,拒绝了蔡邕的请求。蔡琰从小接受家教熏陶,必然深受父亲的影响,《后汉书·列女传》即记载了她记诵父亲书籍的事迹。因此,深受蔡邕追捧的《史记》,很有可能也影响了文姬;文姬《悲愤诗》透露出的诗史意识,正折射了《史记》实录精神的影子。
到了西晋和南朝,虽然玄言诗和宫体诗蔚为主流,但是记录时事、反映民生的诗作仍在夹缝中求生,继承与取法《史记》的实录精神。如张骏《薤露行》即记录了西晋灭亡的过程:
在晋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艰乱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权纲丧典刑。愚猾窥神器,牝鸡又晨鸣。哲妇逞幽虐,宗祀一朝倾。储君缢新昌,帝执金墉城。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坰。三方风尘起,玁狁窃上京。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誓心荡众狄,积诚彻昊灵。[5]876-877
诗歌开篇就展现了西晋主暗臣乱的政治局面:惠帝无能、杨骏专权、贾后密谋、八王作乱。通过诗人的揭露,西晋朝廷黑暗的内斗史清晰地剖露在读者面前。也正是由于朝廷昏暗,才使得外族趁机入侵,从而导致了西晋政权的覆灭。西晋灭亡之秋,仍有义士怀愤,他们奋力抗击外族以求收复故土。如此种种,张骏一一纳入诗歌,以洗练的语言描绘了西晋灭亡前后的历史画卷。梁、陈之际,贺力牧《乱后别苏州人诗》也记录了侯景之乱的历史一幕。贺诗以“子常终覆郢,宰嚭遂亡吴”的历史,影射苏州沦陷的现实原因;并通过对乱后苏州“宫毁无巢燕,城空馀堞乌”的环境描写,展现侯景之乱对社会民生的毁灭,从而传达出劫后馀生的丧乱之感。
此外,汉魏六朝由于政权动荡、征战频繁,通过从军行役反映社会民生的诗歌也不绝如缕。曹操《苦寒行》一诗就通过对行军途中恶劣环境的渲染,揭示了军士生活的艰辛。王粲《七哀诗》在描绘了风雪凛凛的边地环境之外,还揭露了“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的社会现实,从而展现了乱世流离的民生状态。陆机《饮马长城窟行》一诗更是多方面展现了军旅生活的实情:从军之人既要克服“仰凭积雪岩,俯涉坚冰川”的自然磨难,又要忍受“冬来秋未反,去家邈以绵”的思乡之情,还要面对“师克薄赏行,军没微躯捐”的生存状况。刘琨在《扶风歌》中表述了类似观点的同时,还通过对《史记》典故的化用,表露了对无端获罪、前途未卜的隐忧:“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由上述诗歌可知,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夹击下,军士的处境尤为艰辛。而鲍照《拟行路难》一诗,更是从时间维度上揭示了征人的悲剧人生:少小从军,白头未返;妻子远隔,生离死别。何逊《见征人分别诗》也记录了真实的从军情景,诗人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凄凄日暮时,亲宾俱竚立。征人拔剑起,儿女牵衣泣”这一极具感染力的生活画面,从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后来杜甫“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描绘正是基于此的超越。魏晋南北朝从军行役之诗,不仅揭示了军旅生活,也反映了社会民生,是蕴含了实录精神的诗史。
二 感时伤乱:慨叹历史现实的曲笔之作
汉魏六朝除了直笔评论时政、反映民生的作品之外,还存在很多曲笔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这些诗歌往往通过对历史生活的追述,或是对历史典故的化用,以借古讽今的方式评论时局政治,记录社会生活。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诗即通过对秦朝修筑长城史事的追述,还原了汉末徭役繁重的民间生活: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5]367
筑城役卒与其妻往来书信内容的转述,带给我们极大的心灵震撼。虽然诗歌通篇讲述的都是前朝往事,但是,一方面诗人感慨史事的深层来源是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诗人述古也是为了表达对现实政治的讽刺。因此,陈诗描述的社会图景,也可以看作对汉末民生的曲折记述。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借对蒙恬修筑长城的批判,讽刺武帝时期民生凋敝的手法如出一辙,是曲笔评论时事的表现。
晋张载《七哀诗》也继承了这一手法,以曲笔述古慨今:
北芒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园寝化为墟,周墉无遗堵。蒙茏荆棘生,蹊径登童竖。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颓陇并垦发,萌隶营农圃。昔为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感彼雍门言,凄怆哀今古。[5]741
其中,“季世”四句正是通过对《史记》记载的盗墓典故的化用,揭露了董卓之众发掘汉陵的恶行,从而重现了汉末史事。诗人对汉陵“蒙茏荆棘生,蹊径登童竖”的触目惊心,对“昔为万乘君,今为丘中土”的深切感慨,正折射出对西晋政权行将覆灭的深刻隐忧。
此外,陶渊明《述酒》一诗也通过晦涩的历史典故曲折地表达了对时政的评述: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生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7]67-68
与陈、张二诗通过展现历史生活来讽刺现实政治的方式不同,陶诗是通过对一系列历史典故的运用,隐晦地传达出刘裕篡权、杀害恭帝的时局政治,从而表达了诗人对刘宋政权的不满与愤怒。此诗由于用典过于晦涩,一直是陶诗中最为难解的作品之一。苏轼追和陶诗大半,却不和此首;黄庭坚甚至直言此诗“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直至南宋汤汉才发掘出微言大义,指出此诗乃渊明悲叹恭帝被弑、晋祚消亡的忠愤之辞。这从诗中“流泪”二句即可窥见端倪,而全诗众多历史典故的汇聚,更强有力地隐射了晋宋时局,流露出诗人的悲愤之情。
汉魏六朝这些慨叹历史现实的曲笔之作,与那些书写时事民生的直笔之诗,共同记录了乱世政治和社会生活。其反映现实的自觉与广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史记》实录精神的延续。
三 风衰俗怨: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史之笔
汉魏六朝诗人评论时政、反映民生之馀,也对社会风俗和社会问题多所关注,并往往以实录之笔揭露不公的社会现实和浇薄的社会风气。
首先来看阮瑀《驾出北郭门行》一诗对孤儿深受后母虐待的家庭问题的反映。诗歌通过诗人与故事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展现了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的生活现状。同类题材在汉乐府中已经出现,汉乐府《孤儿行》即以孤儿的口吻,抒发了父母早亡备受兄嫂虐待的悲痛之情。很显然,阮诗是对汉乐府的继承,但二者还是存在诸多差异。对此,葛晓音在《八代诗史》中指出,阮瑀“仅以旁观者的同情客观描述此事,所以无论就感情的惨痛还是思想的深度而言,都不如琐碎质实的《孤儿行》”[8]71,可谓一语中的。但是,二者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差别,还在于作者的作诗目的本不尽同:汉乐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自发之作,而阮瑀却有“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的自觉追求。反映社会、批判现实的理性精神,使得阮瑀在对孤儿故事叙述中,时常以抽离的态度思考问题,因而也就拉开了与故事主人公的情感距离,从而造成了客观冷静的抒情效果。阮瑀批判现实的文化担当意识,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向《史记》实录精神靠拢的趋势。
西晋傅玄也表现出关注社会问题的极大热情。傅玄博览群书,曾著《傅子》一书评断“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9]1323,他在书中就曾指出《汉书》相较于《史记》的不足:“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10]390由此可见,傅玄更为推崇史迁直录现实的担当人格,也可见实录精神对其心灵的润泽。在史学担当精神的陶冶下,傅玄对诸多社会问题都充满了理性思考,并由此写出了很多具有道德意味的诗作,这在“士无特操”的西晋社会尤为难得。傅玄模拟自汉乐府《日出东南隅》的《艳歌行》,以及改编自《列女传》秋胡戏妻故事的《秋胡行》,就因道德训诫意味太浓而常受后人诟病,但这恰好说明了他期望改良社会风气的殷切心情。除了拟古之作,傅玄也创作了很多实录之诗,例如《豫章行·苦相篇》一诗即是对重男轻女社会现象的揭露。诗人首先将“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的得意处境,与“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的卑陋情形进行对比,揭示出女性卑微低下的社会地位。接着,诗人又叙述了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弱势定位,妻子对丈夫既要“低头和颜色”,又要“跪拜无复数”,但即便如此,仍然可能招致“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尤其是“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最后惨遭抛弃。《苦相篇》以概括的语言客观描述了女性悲惨的生活境遇,反映了普遍而深刻的女性问题。此外,傅玄《墙上难为趋》一诗,也是针砭时弊的作品。诗歌前半篇通过描写贵族来客对贫士主人颐指气使、讥笑鄙夷的言行举止,揭露了嫌贫爱富的社会风气;后半篇通过列举众多起于微贱的历史名人,表达了诗人对嫌贫之人目光短浅的批评与讽刺。
到了南朝,沈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诗》也同样反映了趋炎附势的社会恶习:
廉公失权势,门馆有虚盈。贵贱犹如此,况乃曲池平。高车尘未灭,珠履故馀声。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11]239
诗歌开篇即引用廉颇失势的典故,写出了世态炎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12]2448司马迁此番对世态炎凉的感触,于沈约心有戚戚。沈诗中廉颇典故的运用,正是为了援古例今,说明古今同一的炎凉世风。接着,诗人翻进一层,“贵贱犹如此,况乃曲池平”,揭示出丞相新薨、宾客散尽的事实。“高车”“珠履”所折射出的往昔繁华,与“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的今日凄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与《史记·汲郑列传》“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的叙述异曲同工。沈诗正是通过古今映照、死生之别,揭露出浇薄的社会风气,表达了对趋炎附势之徒的憎恶之情,而这也正是对《史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2]3114之感触的体认。
以上诸诗都是对具体社会问题或社会风气的揭露,而王褒《墙上难为趋》一诗则是以概括之笔揭露了社会的种种不公:“末代多侥倖,卿相尽经由。台郎百金价,台司千万求。当朝少直笔,趋代皆曲钩。廷尉十年不得调,将军百战未封侯。”[13]197诗人通过对一系列不平现象的描述,展现了混乱无望的末世之风。可见,深受《史记》实录精神影响的汉魏六朝之诗,正是通过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风气的自觉揭露,记录了“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
四 余论
实录精神不仅是良史之德,也是难能可贵的诗学传统。《诗经》中已存在诗史之作,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诗、史同源,诗歌也往往渗透了史学的实录笔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经》面向现实的品质,必然带来诸多反映生活的诗篇。汉乐府在继承《诗经》的同时,进一步发扬了实录传统,相比于《诗经》以言志的方式反映生活,汉乐府往往是通过对生活片段的直接叙述,来呈现更为清晰的社会图景。《史记》在整合诗、史实录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呈现出有别于《诗经》和汉乐府的实录特点:
第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更侧重于政治生活。由于《史记》所载人物多为王侯将相,政治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实录精神展现的主场。因此,史迁对历史人、事“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里,正包含着批判现实政治的勇气。同时,诸多时局大事,也依赖“其文直,其事核”的史笔得以呈现。
第二,《史记》反映生活的视角更为宏观。虽然《诗经》和汉乐府也反映了广阔的生活画卷,但它们反映生活的广度,是多篇一鳞半爪的记录集腋而成。由于作者各异,篇章之间相互独立,一篇往往是采用具体而微的方式,记述某一历史事件,或是揭露某一社会问题,因而也就缺少了宏观概括性。《史记》则不然,司马迁经常在一篇之内,或是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或是描摹形态万有的社会图景。如《货殖列传》即通过历史各时期及各地富商大贾的发家史,以及社会各类人群的求富心态和经营行为,展现了跨时空的经济社会风貌。并且,《史记》有着统一的结构,各篇之间相互牵连,从而形成了有机整体。可以说,一部《史记》也是一篇完整的作品,以宏观视角记录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貌。
第三,司马迁记录生活、反映民生的意识更为自觉。无论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4]361的《诗三百》,还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1756的汉乐府民歌,多是诗人对生活本身有感而发的结果,它们体现了诗人反映民生日用的自发性。而司马迁表现生活,除了源于对生活现象的直接感发以外,还得益于他关注民生的儒家修养和理性自觉。因此在反映民生时,史迁形象并未与反映对象融为一体,而是呈现出高屋建瓴的史学家姿态,以相对独立的立场,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描述了社会生活的实情。
《史记》实录精神的上述特点,也渗透进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中。汉魏六朝动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诗史之作,诗史之作也正因反映了苦难现实,而具有了慷慨使气的精神风力。对此,刘勰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673-674刘勰对魏晋文风的概括,也同样适用于魏晋诗风。其时诗歌慷慨使气的风格,除了丧乱征战的现实渊源和《诗经》、汉乐府的实录传统以外,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史记》实录精神的影响。从史料记载来看,《史记》在汉末文人中流传已广,南北朝更是文人易得的案头之书,这就为《史记》影响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先决条件。因此,无论是接受《史记》影响的客观条件,还是遗留了史迁运笔特点的诗歌文本,都表明汉魏六朝诗歌继承《史记》实录精神的事实,故而李泽厚说“到了魏晋,那种所谓‘慷慨以使气’的文风,也不能说没有司马迁所遗存的影响”[15]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