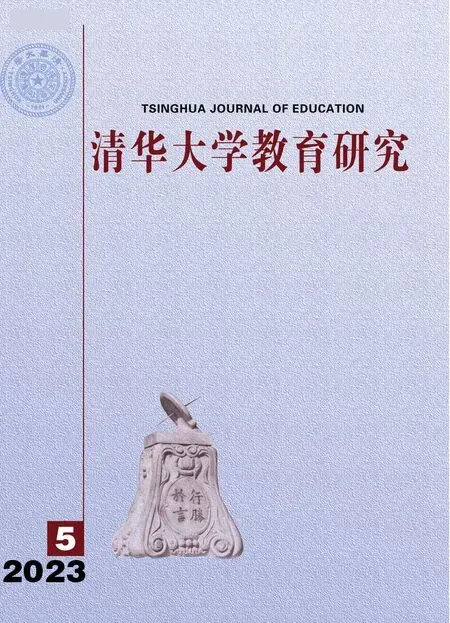英国影响力议程:在政府、高校与学者之间
王 楠 罗珺文 孟祥赛
(1.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2.新疆大学 研究生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3.都柏林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所,爱尔兰;4.外交学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37)
近一个世纪以来,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推动着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硬边界逐渐软化,大学的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包括在宏观层面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微观层面不断强调知识的公共传播等诸多方面。在这种趋势下,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逐步形成了对科研成果“影响力议程(Impact Agenda)”的共识,即不仅强调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停留在学术界的发表和内部交流,还应重视其外部社会价值,使其对经济、文化、公共政策、医疗、环境、教育、公民健康等产生更广泛的积极影响。由此,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也都积极探索“影响力议程”下的科研政策,以及作为科研活动风向标的评估范式的转型,由单纯地关注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转向兼顾其对外部社会辐射的“非学术影响”。比如,加拿大在近几年的科研政策中引入了强化知识流通与成果转移的相关政策,以促进科研的社会影响力;(1)Chubb Jennifer et al.,“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Academy? The Role of Emotion in Response to an Impact Agenda in the UK and Australi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36, no.3(2017):555-568.美国、(2)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STAR METRICS Overview,”https://www.starmetrics.nih.gov/Star/About.荷兰、(3)KNAW et al., Standard Evaluation Protocol 2015-2021, Protocol for Research Assessment in the Netherlands(Amsterdam: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14).澳大利亚(4)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https://www.arc.gov.au/excellence-research-australia.等国家也都在科研评估框架中引入了“非学术影响”评估维度,探索将科研成果的社会贡献作为知识创新活动的导向和资源分配的指挥棒。
在众多他国的实践中,英国作为“影响力议程”这一概念的起源国和先行者,其回应尤其值得关注。英国对科研成果外部影响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议会于1993年发表的白皮书《实现我们的潜力》(5)GOV.UK,“Realising Our Potential: A Strategy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alising-our-potential-a-strategy-for-science-engineering-and-technology.,其中着重讨论了科学技术及科研活动推动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径。此后,英国在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层面,都对推进影响力议程开展了积极探索。2014年,英国在首轮全新的“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评估体系中引入了“(非学术)影响力(Impact of Research Beyond Academia)”评估维度,(6)UK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2014,”https://www.ref.ac.uk/2014/results/intro/.将社会贡献作为界定卓越科研和分配资源的重要依据,将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更加紧密地挂钩,一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希望通过回顾英国政府、高校、学者在影响力议程框架下所作出的改革行动,充分借鉴“先行者”的经验,同时规避以影响力界定卓越科研的做法有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而为更好地构建健康的科研生态体系、完备的科研管理和评估制度等提供建议和参照。
一、政府:结构化的治理框架重构
为了消除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之间的壁垒,促进卓越的科研成果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英国政府对科研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重新搭建了英国科研与创新治理框架。
(一)以价值认同作为治理结构变革的内源性支撑
英国政府于2018年5月对负责高校科研与创新管理的组织机构进行了重组,将原先的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s UK,RCUK)改组为全新的英国研究与创新理事会(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UKRI是在英国2017年最新颁布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法案》的授权下,由政府建立的全新的负责英国研究与创新治理的独立机构,由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提供的科学预算资金支持,由独立的主席和董事会运行,主要负责每年在全英国分配和管理将近70亿英镑的研究与创新经费。UKRI提出将始终保持开放态度,以创新与合作作为工作核心,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如学术界、商界、慈善机构、政府决策者、研究人员、创新创业者、企业家等搭建一个促进多方沟通与融通的平台,(7)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About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https://www.ukri.org/who-we-are/about-uk-research-and-innovation/.并希望通过与研究和创新共同体的合作,实现三个递进式目标:第一,通过聚集人力资源、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诚信体系、实施全球化战略等,创建英国科研与创新体系,产出更多卓越的研究与创新成果,打造良好的科研与创新环境;第二,依托科研创新体系,以卓越的成果和良好的环境作为基础,不断推进人类知识与理解的前沿;第三,也是UKRI最高战略目标,即通过支持个体和组织变得更加健康、多样,具备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创造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8)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Our Vision and Strategy,”https://www.ukri.org/who-we-are/our-vision-and-strategy/.
由此,UKRI所属的科研、创新、监管等各职能部门将科研与创新管理工作置于服务国家需求、社会需要、民生诉求等更广阔的社会责任之下,形成了依托卓越的科研成果创造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价值认同,而这种价值认同也成为其治理结构变革的内源性支撑。
(二)通过机构重组搭建高度协同的治理结构
UKRI通过机构重组搭建了高度协同的治理结构。UKRI整合了全英国科研创新生态谱系下的学术委员会、企业创新部门、资助监管机构。(9)武学超,罗志敏.组织创新与制度优化: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改革新向度及基本逻辑[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3):75-83.首先,UKRI整合了英国原有的七个学术研究委员会,包括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七个学术研究委员会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开展科研活动、进行科研项目的资金资助决策。同时,UKRI容纳了以企业创新为导向的“创新英国(Innovate UK)”,以及主要负责英格兰科研资助与管理工作的英格兰研究委员会(Research England)。(10)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Our Councils,”https://www.ukri.org/councils/.“创新英国”通过建立与企业的密切联系,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实现促进知识应用和助力企业成长的目标;(11)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Innovate UK,”https://www.ukri.org/councils/innovate-uk/.英格兰研究委员会则通过与高等院校合作并为其提供基金资助,为促进高等教育领域多向度的知识交流创造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12)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esearch England,”https://www.ukri.org/councils/research-england/.
UKRI转变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传统科研管理模式,通过机构重组搭建了涵盖学术研究部门、企业创新部门、资助监管机构等多元主体在内的协同治理结构,同时建立健全了各部门之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这大大提升了部门之间协同运行的工作效率,降低了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简化了协作流程,使得各部门工作目标更加聚焦,行动步调更加一致。同时,这有利于更好地发挥UKRI的职能,打通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之间的壁垒,消除大学与企业多向度合作互动的制度障碍,促进院校发展与企业创新交叉融合,从而实现推进卓越科研、促进协同创新、扩大社会影响的多重目标。
(三)通过优化职能配置探索扩大科研影响力的有效路径
高度协同的治理结构为UKRI提供了体制机制的有力保障,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下,UKRI也在优化自身的职能,提升下设职能部门之间协同治理的能力,探索推动科研成果辐射社会影响的有效路径,包括:支持不同的学术委员会之间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创新、知识交换、知识增值活动,促进各学科研究和创新交叉融合、协同发展;鼓励和吸引高校科研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重大技术研发和企业创新活动,加强大学与外部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对各学科领域科研创新活动进行更有力的资助和更完备的监管,始终追求科研创新质量卓越、环境优越、社会经济影响强劲(13)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Our Vision and Strategy,”https://www.ukri.org/who-we-are/our-vision-and-strategy/.的目标。
例如,在资金支持方面,为更有效地扩大科研的影响力辐射范围,UKRI下设的九个委员会都设立了专门的影响力加速基金(Impact Acceleration Funding),并根据学科差异下设不同的子资金,希望为大学和研究人员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灵活度。比如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设立了伙伴关系发展奖励资金、知识转移资金、研究项目后期资助资金等子项目。希望通过提供基金来鼓励研究人员参与知识转移活动,提高知识转移活动的效率,改善研究基地与资助者之间的沟通效果,建立与企业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研究成果商业转化的成功率,增加研究人员在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流动等。(14)Research Strateg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EPSRC Impact Acceleration Account,”https://www.research-strategy.admin.cam.ac.uk/epsrc-impact-acceleration-account.又如,医学研究委员会下设概念置信计划(Confidence in Concept,CiC),其作为面向医学领域的研究转化基金,旨在通过支持处于开发期的可行性研究,加速其从研究到应用的过渡。(15)Office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MRC Confidence in Concept (CiC),”https://otr.medschl.cam.ac.uk/funding/confidence-concept.这些加速基金通过不同的方式运作,一部分拨付至高校,另一部分面向全社会各类研发机构与个人开放申请,并由各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资金管理。
二、高校:全方位的战略推进
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引领下,英国的高校采取了全方位的推进策略来回应影响力议程,积极拓展科研成果的外部社会影响。
(一)成立职能部门,增设专门职位
大学纷纷成立了辅助和支持一线研究人员建立合作网络、开展公众参与、推广研究成果的职能部门,或在原有职能部门中增加和强化推进影响力的新职能,这些部门专门负责在学校层面落实推进科研影响力的战略措施。比如,剑桥大学中主要负责促进影响力的职能部门包括科研战略办公室、战略伙伴关系办公室两个部门,其职能近年来被不断延伸和强化。在巴斯大学,主要负责推动影响力的部门是研究与创新服务中心,(16)University of Bath,“Research &Innovation Services (RIS),”https://www.bath.ac.uk/professional-services/research-innovation-services-ris/.其主要职能是推动院校的科研与创新协同发展,以高质量的研究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各院校还新设立了一些行政管理职位,例如商业伙伴关系负责人、知识转让和伙伴关系促进员、REF影响力协调员等,以协助研究人员与行业中各方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比如,剑桥大学中的不同院系根据学科特点设立了相应的职位:艺术与人文学院设立了社会科学影响促进专员、商业合作协调专员、伙伴关系发展专员,流行病学研究所设立了知识传播协调专员,理工科学院设立了产业合作协调专员、技术转移转化协调专员,生物学院设立了社会参与协调专员、知识传播协调专员等岗位。(17)Research Strateg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Research and Knowledge Transfer Facilitators Contacts,”https://www.research-strategy.admin.cam.ac.uk/impact/research-and-knowledge-transfer-contacts.巴斯大学则在院系中指定了科研副院长专门负责支持和推动本院系的影响力相关工作。(18)University of Bath,“Impact Directors,”https://www.bath.ac.uk/teams/impact-directors/.再如曼彻斯特大学,同样在各院系中设立了知识交换协调员、学术公关协调员等岗位,(19)University of Manchester,“Collaborate,”https://www.manchester.ac.uk/collaborate/.研究人员可以依托这些岗位专员的支持与帮助,花费更少的时间更有效地与行业拓展伙伴关系,以更有利地促成研究的外部影响。
(二)开发工具资源,定期推送共享
为更有力地支持科研人员在影响力方面取得成就,高校纷纷开发了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影响力的工具资源包,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更好地理解和规划研究的预期影响,有效捕捉影响力相关证据,以更加便捷、直观的方式来证明和展现影响,并及时评估影响的成效。这不仅能够减轻研究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将更有效地促成并展现其科研成果的外部影响。
例如,剑桥大学开发和共享了一系列促进影响力的应用工具和指南,定期为研究人员进行推送,主要包括如下几类:第一类,科研影响力计划模板。(20)Research Strateg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Pathways to Impact Planning Tool: Research Impact Planning Template,”https://www.research-strategy.admin.cam.ac.uk/pathwaytoimpact/documents/2-and-9-ImpactPlanningTemplate.xlsx.该模板是协助科研人员计划其科研影响辐射方式的工具,研究人员可以参照模板在设计研究方案的过程中将成果的潜在影响力纳入研究设计。第二类,应用与实践指南。比如共享《学术研究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良好实践和证据管理的国际视角》《研究共同体收集研究影响证据的最佳实践指南》等,这些指南总结了目前在收集、管理和应用影响证据方面的做法,为如何采集影响证据、展示影响效果、利用证据开展内部管理和外部评估等提供了建议和指导。(21)Research Strateg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Evidencing Impact,”https://www.research-strategy.admin.cam.ac.uk/impact/evidencing-impact.通过参考资料,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认识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类型研究所带来的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学习收集影响力证据和展现影响力效果的实践经验。第三类,在线智能技术工具。比如推荐Researchfish等用于跟踪研究过程和捕捉影响力的工具,通过智能技术从网络、外部数据源和研究人员等渠道广泛收集资源,跟踪研究的影响力,并为制定合作战略提供丰富的信息和数据支持。(22)Research Strateg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Evidencing Impact,”https://www.research-strategy.admin.cam.ac.uk/impact/evidencing-impact.
(三)组织模拟评估,开展专业分析
为更好地迎接和准备面向全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卓越评估”框架中全新的“影响力”评估维度,一些大学开展了模拟评估。例如卡迪夫大学在REF2014评估的准备期间(正式评估一年半以前)组织了为期两天的模拟评估,以尽可能相似地演绎真实的影响力评估现场,该次模拟评估依据指南设立了四个不同领域的评估分委员会,邀请了共90名评审者,既包括各领域内的专家评审委员,也包括经过甄选的科研成果终端用户代表。评估对象则是各院系准备提交的真实的影响力案例。评审委员参考REF2014的评估标准和评分范例来对影响力案例进行评审和打分,公开探讨打分依据以及优秀的影响力案例所应具备的条件。与此同时,英国REF的资深研究者沃特迈耶(Watermeyer)博士在模拟现场作为“沉默的观察者”,将评审委员会的讨论过程记录下来并进行了专业分析,认为不同的评审专家对影响力评估标准中“范围”和“意义”两项指标存在不同解读,比如研究成果对本地区产生的外部影响的分值是否低于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影响等。(23)Richard Watermeyer and Adam Hedgecoe,“Selling ‘Impact’: Peer Reviewer Projections of What Is Needed and What Counts in REF Impact Case Studie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31, no.5(2016):651-665.这些专业分析有利于为影响力案例的撰写者和高校的评估组织协调者提供重要参考,从而对评估材料进行修改和润色,使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以评审者更容易理解、接受和赞同的方式表达和呈现出来,同时更好地组织影响力案例的收集和提交工作。卡迪夫大学在REF2014的影响力评估中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模拟评估带来了有效的改进和启示作用。
(四)开展针对性培训,提供实践机会
高校为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博士后和学生们设置了多样化的、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影响力、捕捉影响力、描述影响力以及促进影响力发生的培训课程,并注重将教学研讨、实践参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以实现最佳的培训效果。帝国理工学院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科研影响力策略”工作坊,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在职业发展早期阶段理解科研影响之于不同受众群体的意义,改善与不同受众群体的沟通方式,并将影响力以一种更容易被普通大众理解和赞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明确社会参与将为研究和职业增值。(24)Graduate School, Imperial College London,“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Research Impact,”https://www.imperial.ac.uk/students/academic-support/graduate-school/professional-development/courses-for-doctoral-students/professional-development/research-impact/.再如,剑桥大学的科学与政策中心开展了助推研究者将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的培训,通过研讨会、政府借调和部门实习,为职业生涯初期和中期的研究人员提供机会,加深其对政策制定需求的理解,了解学术研究影响政策决策的路径,并获得在研究和政策的“交叉点”工作的经验。(25)Centre for Science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Helping Researchers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eds of Policy Makers,”http://www.csap.cam.ac.uk/professional-development/.又如,剑桥大学的麦克斯韦中心设立了“影响推动力”计划,旨在帮助研究者评估自己的研究创新理念,并学会将创意推向市场。该计划采用行动学习的方式,凸显结果驱动导向,参与培训的人员需在模拟谈判中展现他们的创业思路,在一些企业家的引领和指导下进行项目开发和落地,可谓是个人和组织创业的催化剂。(26)Maxwell Centr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Impulse Programme,”https://www.maxwell.cam.ac.uk/programmes/impulse-programme.
(五)成立专项基金,设立奖励计划
院校一方面要负责管理和拨付UKRI中各委员会在院校设立的影响力加速基金,同时也独立设立了鼓励影响力的基金和奖励计划。比如,前述所提到的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就在多所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影响力加速基金。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笔资金,各院校分别成立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申请、拨款、审核及各项过程管理工作,并定期向学校研究政策委员会进行汇报,(27)Research Strateg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EPSRC Impact Acceleration Account,”https://www.research-strategy.admin.cam.ac.uk/epsrc-impact-acceleration-account.以保证影响力加速基金的使用效率。各大学也设立了独立的院校影响力促进基金和奖励计划。比如剑桥大学、巴斯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等院校,都设置了大学内部的影响力促进基金,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团队和学者个人提供灵活的资金支持,用于开发创新性的社会参与途径,开展项目推广活动,扩大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第三部门的接触与合作,(28)AH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Arts and Humanities Impact Funding,”https://www.ahssresearch.group.cam.ac.uk/impact/AH-impact-Fund.使研究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积极的外部影响。再如,剑桥大学于2016年设立了副校长奖励计划,旨在认可、鼓励和表彰在科研影响力和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卓越、取得杰出和创新成绩的员工。(29)Research Strateg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Vice-Chancellor’s Awards,”https://www.research-strategy.admin.cam.ac.uk/impact/vice-chancellors-awards.
三、学者:多元化的态度表达
面对影响力议程的政策环境和全新的REF评估形势,一线科研工作者也做出了多元化的态度表达,总体而言分为“拥护者”“质疑者”“中立者”三类。(30)Chubb Jennifer et al.,“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Academy? The Role of Emotion in Response to an Impact Agenda in the UK and Australi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36, no.3(2017):555-568.
(一)拥护者:认同影响力议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拥护者”认同影响力议程的意义,并通过投身社会参与、拓展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等途径积极地树立社会公共形象,履行社会责任。“拥护者”认为影响力议程的推进及由此衍生的影响力评估,为个人的研究带来了更广泛的机会和回报。许多“拥护者”在受访中描述他们对影响力议程的感受时,表达了一系列如热情、快乐、享受、兴奋等积极和肯定的情绪。一方面,“拥护者”认为影响力议程带来的研究范式及评估范式的转型,使其更好地理解了研究成果之于外部社会产生辐射影响的价值和意义,增强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敦促个体在研究中强化科研工作的外部影响,而这也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更加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拥护者”认为影响力评估对于他们的研究机构、团队及个人的学术身份至关重要。影响力评估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公开展示成果和回应公众问责的机会。比如通过REF影响力评估,他们不仅可以向公立资助者和社会大众展现研究人员的付出及所取得的成绩,而且可以向同行展示研究的最新进展。这使得学者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形象得到了更加正面的体现和强化,更好地树立了学者的社会公共角色,同时也使得学者更加认同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31)Chubb Jennifer et al.,“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Academy? The Role of Emotion in Response to an Impact Agenda in the UK and Australi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36, no.3(2017):555-568.当然,不同的学者对学术角色有着不同的认知,对影响力议程最积极的反应很可能来自两部分学者,一部分是有着更强责任感,认为有义务回馈社会的研究者;另一部分则来自那些科研内容(如医药)与终端用户(如医院和病人)之间连接更加紧密的研究者,因为相对而言,他们更容易捕捉和证明研究成果和外部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32)Gemma E.Derrick and Gabrielle N.Samuel,“The Evaluation Scale: Exploring Decisions about Societal Impact in Peer Review Panels,”Minerva 54, no.1(2016):75-97.
(二)质疑者:反对外部审查,呼吁学术自由
“质疑者”认为影响力议程及相应的评估改革打乱了研究人员追求学术理想和学术自由的节奏,对学术生态系统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对影响力的过度追求可能会对科学研究本身造成一定的威胁。有学者表示,影响力评估促使学者不得不审视和调整研究方向以配合产出更现实、可见的影响力成效,这无疑削弱和抑制了不同学者之间多元化的研究兴趣,甚至将淘汰掉那些个人研究兴趣与影响力评估标准不那么一致(比如“冷门”专业)的学者,这可能造成研究领域发展的高度同质化倾向,也将大大损伤学术生态系统多样、自由的特色,以及高等学校对学术自治的追求。(33)Ben R.Martin,“The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and the ‘Impact Agenda’: Are We Creating a Frankenstein Monster?”Research Evaluation 20, no.3(2011):247-254.另一方面,“质疑者”担心未来对影响力的要求不断强化,会导致学术角色的重新定位,这给部分学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担忧和恐慌情绪。比如为了更好地捕捉、跟踪、展现影响力,学者将承担科研工作之外的诸多社会参与、推广工作以及伴随而来的行政事务,这有可能给学者带来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疏离感,以及因额外的工作和全新的社会角色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恐惧感。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就表达了“根深蒂固的担忧”和“挫折感”,他们认为影响力议程降低了学术生涯对他们的吸引力,以至于影响了研究工作和个人职业发展决策。特别是他们当中不太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的学者,将可能因为缺失推广影响力的能力而被同行嘲笑,或选择离开学术界。(34)Chubb Jennifer et al.,“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Academy? The Role of Emotion in Response to an Impact Agenda in the UK and Australi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36, no.3(2017):555-568.同时,“质疑者”指出,当前将影响力作为衡量科研成果质量的标准之一,与日益备受倚重的“审计文化”有关。然而,其过于注重严苛的审核证据,有悖于传统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自由,且并不能真实反映研究成果的质量。尽管“质疑者”也一致认同对公共资金所支持的研究进行审查的做法,但这更应该是学者内心驱动的自我行为,而不是通过外部审查提供一条自我合法化的途径。(35)Richard Watermeyer and Jennifer Chubb,“Evaluating ‘Impact’ in the UK’s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 Liminality, Looseness and New Modalities of Scholarly Distinction,”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4, no.9(2019):1554-1566.显然,现行的评估框架还未建立推动学者自我反思和自我审查的机制。
(三)中立者:做出务实回应,寻求动态平衡
事实上,还有不少学者是介于“拥护者”和“质疑者”之间的“中立者”。他们承认影响力议程的价值和意义,但也表达了与公众问责和不得不配合影响力评估有关的紧张情绪。“中立者”认同并愿意承担推动影响力的责任,但同时对其中具体而复杂的工作表现出一定的焦虑和无奈。(36)Chubb Jennifer et al.,“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Academy? The Role of Emotion in Response to an Impact Agenda in the UK and Australia,”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36, no.3(2017):555-568.影响力评估对他们来说既是机会和资源,也意味着沉重的负担,无论在何种具体的影响力评估框架下,他们都会选择性地去争取对所在科研机构和自身至关重要的外部资源,承担起与科研活动紧密相关的社会责任。但同时他们也畏惧“质疑者”所提出的担忧和挑战,担心因为对影响力的过分追求而失去了对科研本身的控制权和对学者身份的认同感。(37)Ben R.Martin,“The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and the ‘Impact Agenda’: Are We Creating a Frankenstein Monster?”Research Evaluation 20, no.3(2011):247-254.“中立者”是相对而言的灵活主义者,他们对影响力议程的政策环境和具体的评估框架都能给出比较务实的回应,比“拥护者”少了些主动,比“质疑者”少了些抱怨,努力在二者之间追求动态平衡。
四、经验及启示
(一)凝聚共识:搭建协同开放的治理框架,形成推动影响力议程的协同效应
英国对影响力议程给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搭建高度协同开放的科研与创新治理框架,凝聚各方共识,形成了推进影响力议程的协同效应。要实现以科研成果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离不开一线研究人员的意识提升和行动努力,但更需要外部的组织保障与制度优化。UKRI的改革与重组整合了全英国科研创新生态谱系下的学术、创新、监管机构,搭建了各部门高度协同、相互耦合的治理框架,有利于打破学科与学科之间、科学与社会之间进行知识交换与创新合作的壁垒,为科研与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和优越的治理环境。
治理结构的重构也必然带来其功能的重塑。在高度协同开放的治理框架下,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不同层面、不同组织、不同主体之间都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形成了落实影响力议程的合力。学术组织之间进一步拓展交流与合作领域,创新交流与合作形式,更加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资源,开展了更多高质量的跨学科、多学科、超学科的科研活动。高校采取了多元化的战略措施来实现影响力议程中所需要的平台搭建、资源分配和人力协调,同时加强了与企业创新部门的多向度合作,形成了良性互动、交织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以促进科学研究与企业创新交叉融合,加速科研成果向行业转移转化,使研究成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认可,为社会带来切实的改变和影响。而学者个人无论是否支持和拥护影响力议程,REF这一统一的评估体系都推动和促进了他们对科研工作之于外部社会的意义与价值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协同效应在英国落实影响力议程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也为他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照。
(二)多措并举:采取多样化的战略行动,推动影响力导向的知识创新
在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学术研究活动已经超越传统的在学科结构体系和逻辑下所进行的纯粹的知识生产,更加强调跨越学科和学术的边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利用自身的环境、制度、人才优势,采取了多样化的战略措施回应影响力议程,不断推动更高层次的、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知识创新。如上所述,英国高校在价值提升、制度优化、资源分配、人力协调的各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行动回应,包括:在价值层面推动院校和一线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影响力以及科研工作之于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在制度层面,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强化影响力的院校和学院制度;在具体实施策略方面,开发促生影响力的资源工具,帮助学者开展学术公关,建立与社会广泛而紧密的合作网络,协助推广研究成果的外部影响;在保障机制方面,给予学者更灵活的经费和资源支持,以及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分担与协助。这些行动不仅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成效,还将潜移默化地促进英国大学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鼓励大学采取战略行动来推进影响力议程,并非要求大学以一种机械化、程式化的方式去追求短期效益或刻意迎合影响力议程。虽然影响力议程倡导大学有责任为增进社会福祉、消除贫困、保存文化、促进社会正义等作出贡献,但并不等同于狭隘地认为大学知识生产活动应被直接的、短期的社会效益所驱动。相反,影响力导向下的科研活动应定位于为社会作出更长远、可持续的改变与贡献。举例而言,电子芯片的设计制造与更新换代仅仅依靠接近终端市场的电子工程方向的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还需要依赖物理、材料、化学等多个基础学科领域之间开展长期、深入的协作与创新,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需要高校明确长周期的投资回报目标、投入更多的成本,并提高对失败风险的宽容度。因此,大学应始终将推动更高层次的知识创新作为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将科研成果的辐射影响作为一种常态化、内生性的追求,嵌入大学的文化基因。当院校和学者都能够关注和反思研究的社会责任,那么影响力议程将由自上而下的推进,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行动自觉。这将促进大学在不断增进人类知识与理解前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预期之内和预期之外的积极、持久的影响。
(三)尊重差异:共建信任体系与信任机制,为学者保留空间和弹性
通过对英国的考察,发现影响力议程的推进确实带来了科学家之间截然不同的反馈,唤起了一部分学者对科研更广泛的价值的认知和认同,使其主动承担起了研究者的社会责任,但是对于另一部分学者而言,却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比如被认为侵蚀了研究自主权,破坏了学术信任机制,增加了个体的工作压力,(38)Bruce Macfarlane,“The Morphing of Academic Practice: Unbundling and the Rise of the Para-academic,”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65, no.1(2011):59-73.甚至带来了不良的负面情绪。我们应该意识到,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固然重要,但它只是科研价值的一部分,不应该成为决定研究价值的最为核心的标准,也不应该成为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与内容的绝对依据。大学的核心任务始终是“通过无边界的、开放式的探究来扩展人类的理解”。(39)Stefan Collini,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London: Penguin,2012).这种理解连同探究实践本身,是具有内在生成性价值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实现外部目的的手段。虽然这些探究活动有可能同时产生一系列具有工具性价值的结果,在许多领域为社会带来重大利好,但是这些外部影响并不是可以预测和受控的,其中一些益处可能是立竿见影的,而另一些则要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会显现出来。社会不能以追求工具性利益为目标而将大学掏空,甚至以其内在生成价值作为利益交换。
因此,虽然科研成果的经济、社会等辐射影响可以由外部推动、资助或委托,大学也有责任不遗余力地支持影响力的发生,但与此同时,研究工作的主体,即学者个人仍应最大限度地拥有学术自主权。高校应尽量避免影响力议程和评估框架给学术环境的活力、多样性和自由带来阻力,更不应把追求政策效果当成唯一重要的目标。在影响力议程下,大学应该与学者和公众共同建立新的信任体系和信任机制,(40)Tristan McCowan,“Five Perils of the Impact Agenda in Higher Education,”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16, no.2(2018):279-295.为学者的科研工作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为“拥护者”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持,鼓励他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来应对影响力议程;为“质疑者”保留一定的空间与弹性,尊重他们不同的立场,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回避影响力评估;同时,允许“中立者”在影响力“路口”有选择个人发展路径的自由,使信任体系和信任机制成为大学内生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的一种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