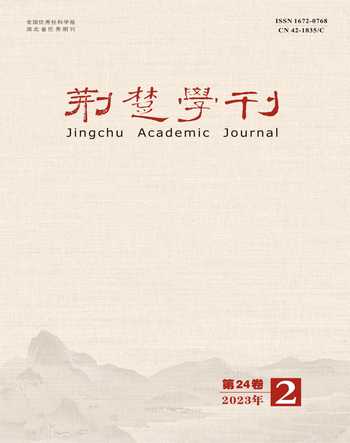近代公共娱乐空间的政治改造
摘要:审视汉口民众乐园的发展变迁,汉口市政府通过体制、空间、演出内容和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政治化的改造,使民众乐园成为其延伸政治力量,传播意识形态,推动社会教育的的重要媒介。民众乐园作为个案诚然有其特殊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政治化改造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民政府对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思想的探索。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公共娱乐空间不仅仅是专供民众的享乐空间,在政府的精心设计下,它还可以是灌输意识形态、培养民众行为的政治空间。从这一点看,对民众乐园的历史梳理无论是对城市空间的价值研究,还是当下对政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化建设,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口;公共空间;城市空间;汉口民众乐园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2-0041-09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个人、家庭和国家公共权威之间的自主性社会领域[ 1 ]。公共领域既不属于私人范畴,又处在国家政治权力架构的边缘,可以说是一个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维持巧妙平衡、居中调和的“中间地带”。而在近代的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一方面彼时根基未稳的国民政府亟需巩固统治,塑造权威,赢得民众认同。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公共空间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成为了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共空间这一“中间地带”自然的成为了政府延伸权力、体现国家意志的“必争之地”。 作为近代武汉最为著名的公共娱乐空间,汉口民众乐园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典型范例。学界关于汉口民众乐园的研究已有不少,特别是胡俊修、钟爱平等学者都将民众乐园纳入到近代城市市民生活的范畴进行了论述,但关于城市空间的政治功能则较少涉及。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报刊文献,重点梳理并探讨近代汉口市政府在主导公共空间话语权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即汉口民众乐园是如何在管理体制、演出内容、空间内部建设以及社会功能四个纬度下的政治化改造中最终成为政府实行政治教化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媒介,进而由点到面的窥探近代国民政府的公共娱乐事业的建设思想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建设。
一、汉口民众乐园的草创
汉口于1861年开埠后快速迈向了城市和商业的现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下,原先作为内陆转运中心的汉口被纳入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成为了全球性的贸易枢纽。此外,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所施行的修建京汉铁路、创办近代工业、兴建新式学堂等种种举措都进一步推动了汉口迅速发展,使其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业中心。商业的繁荣催生出民眾对精神娱乐的需求。在西风东渐下,汉口的娱乐业也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无论是传统的茶馆戏楼,或是新式的酒吧影院。这些满足了各类人群需求,呈现不同文化特色的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的各个区域生根发芽。在中西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汉口民众乐园由此诞生。
1917年,时任汉口稽查处长的刘有财意图仿造“上海大世界”的建筑规模和经营模式,于汉口筹资修建一所可容纳一万两千人的大型娱乐场。娱乐场最初命名为“汉口新世界”,后经多方商议改名为“汉口新市场”。为了筹措资金,刘有财一方面拉拢了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等一众政要,另一方面还联合了汉口华商总会的多位富商代表和买办参与入股,最终凭借军警政商的各界关系,共计筹集本金四十万余元组建了“新市场有限公司”,其下设汉口新市场协利股份有限公司和协兴合记房地产经理处,分别负责新市场的建设经营[ 2 ]。1918年,新市场开始修建,地址位于租界与华界交界之处的后城马路,共分前后两部,前半部分先由协利公司“新盖新市场三层大楼,外加平台和七层塔式屋顶,并大厅及洋楼各一栋”作为新市场的主体建筑。整个建筑呈罗马古典主义风格,以七层圆形塔楼为主楼,两侧为对称的三层“V”字型裙楼,进门处建有圆形喷水池,旁边设一五米高的假山并栽种各类名贵花木,面积约有十五六平方。在其内部各层均设有大厅,四楼有通道可以直达两翼平台,建筑顶端为外嵌“新市场”三个大字的气窗穹顶。穹顶之上设有观景塔亭,底厅电梯可直达于此。后半部分则由协兴公司“在统一街市盖市房七栋,在贤乐巷盖市房十七栋”,并在两部相连之处加盖戏院两所,“一曰大舞台;一曰新舞台”。内部中庭则特邀日本建筑师设计精致园林。整个新市场共计占地面积12187平方米,建筑面积17168平方米。时人感叹其“层楼高耸,气象巍峨,建筑宽宏,规模美丽,洵足以壮此邦人士之观瞻,而园四千六百七十余年之破天荒矣”[ 3 ]。
作为集大成者的新式娱乐中心,新市场兼备了娱乐和商业功能。从弹子房、秋千架、棋牌室、到大花园、动物院、影戏院、游玩场、大戏馆、博物院、特别宴宾室等,其娱乐场所可谓一应俱全,甚为完备,涵盖了各类中西新旧娱乐项目[ 4 ]。此外,在其外部靠近后城马路一侧,还设立了商店、理发店、照相馆、浴池等八十余家各类商业场所,专供人们进行消费。如此规模,可谓“汉上独一无二之游戏场也”。1919年6月1日上午8点,汉口新市场正式开幕,随即轰动一时。当天即售出门票两万余张,其场面“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创汉口空绝之奇观,备吾人娱乐之妙境,武阳夏三镇士女,联袂而来,诚盛极也”[ 5 ]。自此,以一站式、集成式为特征的汉口新市场,很快凭借多元的娱乐文化引领了整个汉口娱乐业的风向,开辟了近代汉口城市娱乐空间的新天地。
二、民众乐园的政治改造
(一)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实践
在近代中国的动荡时局下,民众乐园的发展可谓历尽波折。1926年9月7日,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党认为新市场“在昔实为军阀官僚夫富商大买集货利之所,与国内通商大埠之游戏场,同其性质与社会教育漠然无关”[ 6 ],遂由汉口市教育局牵头于1926年12月将新市场作为逆产收为公有,作为市民集会和工余俱乐的地点。其适逢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广州迁往武汉,新市场遂被命名被“中央人民俱乐部”。俱乐部的管理体制也从原先的经理制变为主任制,俱乐部主任由时任国民党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李之龙兼任。人民俱乐部起初只是作为“一切民众之安乐园”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服务。但在192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委员会举办的临时联席会议指出可凭借“其旧有规模,借艺术之力宣传党义”,遂决定将中央人民俱乐部内部改组为政府宣传机构,隶属于政治部血花剧社。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特以“先烈之血浇灌主义之花”为意亲题“血花世界”四字寄于李之龙,中央人民俱乐部因此又自称“血花世界”。
“在文化娱乐行业实行公有制,源于政府力图控制社会舆论主导权的强烈冲动,特别是在社会剧变时期,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为达成其政治目标,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舆论资源。文化娱乐业因具有与最广大群众直接联系的天然优势,被纳入了国家和政党的视野。”[ 7 ]中央人民俱乐部的成立,客观上催生出新市场作为娱乐空间的公共属性。国民党通过公有制改造,将汉口最大的綜合娱乐中心纳入囊中,其寄希望通过这一公共空间作为传播纽带,一面使自身的政治力量得到延伸渗透至城市各个角落,另一面亦可将自身以“党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辐射输出至整个社会,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从1926年到1930年,民众乐园管理体制的频繁变化,正是国民政府在公有制下的艰难探索与实践。
1.从“委员制”到“协同管理制”
随着1927年宁汉合流,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南京,中央人民俱乐部旋即归由汉口市党部管辖。汉口市党部鉴于中央人民俱乐部“因各种关系,不能如意设施使成一个有组织有主义之人民俱乐部,以合乎革命民众之要求”[ 8 ],遂于1927年8月21日组建改组委员会着手俱乐部的改组事宜。改组后的中央人民俱乐部变主任制为委员制,由黄坚、唐性天、李星亚、苏甲荣、黄恩良五位委员组成中央人民俱乐部委员会负责管理。1927年末,宁汉战争爆发,以新桂系为主力的南京国民政府赢得胜利并控制了武汉,武汉市党务整理委员会遂将“中央人民俱乐部”易名为“武汉人民俱乐部”,并决议重新委派五名委员重组管理委员会。但未曾想“正办理间适政治训练部长江上游办事处呈请军事委员会准由该处派委员五人接收,仍沿前名,未几主其事者发生内哄”,尽管湖北省政府专门抽派二十一人组成监督接收委员会前往俱乐部内调解纠纷,但仍“纠纷益甚”。鉴于此当局只好复改委员制为主任制,于1928年5月将武汉人民俱乐部改名为汉口民乐园,就近交由汉口市公安局监管,委任局长汪以南暂行代管。而后又于1928年9月委任汉口市公安局行政科长冯伯谦专任民乐园总务科科长兼代主任,乐园自此“事权统一,责任乃专,内部情形始有起色”[ 9 ]。1928年10月,汉口市政委员会成立,汪以南以“市政事宜,既有专管机关,自应分别执掌,以清权限”,以及“冬防期间,公安吃紧,难兼筹并顾”为由,呈请汉口市委会统筹各局接收办理[ 10 ]。11月1日,汉口市第一次市政会议决议将民乐园改组为社会局附属机关,以作“社会教育实施之所”,同时命令公安财政二局协助监管。具体来说即公安局负责维持园内秩序,财政局负责收管门票收入,社会局则主要负责乐园经营以及内部组织和艺术宣传。社会局在接收之后委任王绍虞为民乐园主任,并于11月15日派其前往交接全园事务。1929年后,武汉市改称汉口特别市,民乐园遂改名为“汉口特别市民众俱乐部”。
总体上,从1926到1930年的4年间,是民众乐园管理体制的探索时期,民众乐园“协同管理”的实践标志着政府已将对公共娱乐的管理作为一种公共职能纳入到其日常的行政管理之中。但另一方面,社会、财政、公安多部门间权责不清、体制不顺造成的管理混乱也严重影响了民众乐园的健康发展。1929年的《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中收录了一份由汉口市水电公司委托市政府向民众乐园追讨欠款的公函,水电公司指责“民众乐园为民众娱乐机关,亦营业而有收入之场所,所耗商公司供给之水量电度为数甚多,应缴之水电费实为商公司收入大宗,乃竟积年累月延不付费,以致积欠之款为数极钜。”自1929年5月至10月,民乐园所欠水电费在优待条例减免五折的基础上共计为一万三千八百零八元五角。除在六七月间缴费五百元之外,剩余“下欠之款,屡经往索亦延不照付,往返接洽,头绪毫无”。而需要指出的是“该园近来营业极为发达,盈余已积数万并非无款付费者”。可见民乐园之所以“积欠如此之钜,迄不清偿”并非因为财政困难,而是有意为之。水电公司因“近闻该园已由社会局委员接班,当此新旧交接之际,诚恐彼此推诿”,又怕“市面用户群起效尤”,特呈请市委会和公安局“拟恳均会体恤商艰,俯赐令饬”,以期将欠款如数付清,以维商本[ 11 ]。由此可见,民众乐园虽然营业发达,盈利颇丰,但却并没有完善乐园的发展建设,每月的数万盈余不知最终流往何处,其内部管理的混乱可见一斑。
2.从“官办”到“商办”
汉口市政府对民众乐园一系列的体制改造虽然进一步扩大了政府对公共娱乐的掌控,促使其政治功能得到不断加强,但相应的也导致了民众乐园商业功能和娱乐功能的严重退化。早在1928年时任汉口民乐园主任的冯伯谦就预见到这一管理体制带来的弊端,他在《汉口民众乐园征信录》感叹道:“查民乐园(民众乐园)之历史,在军阀时代则为新市场,革命军底定武汉,则为血花世界,为人民俱乐部,其间迭经改组……以致民乐园之性质,淆杂莫分。其为公共娱乐之场所乎?抑为宣传党义之机关乎?或以注重营业等之财政所属之征收局乎?尚难确定!主斯园者,殊却穷于当付也。然任其事者……有主张官办者,有主张招商承办者。盖鉴于官办则开销巨,商办则收入增;官办则宣传为重,营业为轻,其结果必不免于亏累;商办则营业为重,宣传为轻,其结果必不免于背驰。”对此两难之境,他提出了自己主张,即“欲求救济之方,须有平衡之论,官督商办,其为惟一之法门乎?”[ 12 ]冯伯谦寄希望于通过“官督商办”的模式,使民众乐园在政治性、商业性、娱乐性三者中达到平衡,从而修正以往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然而在多重因素的困扰下,民众乐园的经营效益每况愈下,很快就难以为继。1931年,鉴于“公家亏累不堪”,民众乐园遂被改交商人承办。经原新市场的股东们请愿,民众乐园被改名为“兴记新市场”,仍由原新市场股东负责经营。至此,国民政府对其公有制的体制改造宣告失败。武汉沦陷之后,乐园于1939年被汉奸王文明侵占,改名为“明记新市场”。由此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组织管理委员会重新接收,副主任委员郭寄生将其命名为“民众乐园”并一直延续至今。
综上所述,民众乐园管理体制的频繁变动折射出这一时期政府对于公共娱乐事业管理的摇摆不定。因公共娱乐事业的管理具有特殊性,早期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在当时欧美各都市的公共娱乐建设中,虽都“设专官以司其事”,但因“各都市市制各有不同”,故“负娱乐之行政之机关,也各异其名称”。由于国民政府在此之前向无管理娱乐之官制,早期的娱乐场所往往由政府教育机关分管。原中央人民俱乐部委员会委员唐性天对此就指出:“以前教育机关,虽负有指导社会教育之责,增设调查专员,但夷考其实,为政者并没有什么诚意,或是立下一个整个的计划,来建设健全的娱乐场所。充当调查视察者,本人就未必认识艺术为何物,娱乐为何事。徒知填写报告,敷衍塞责,无补于市民娱乐之改进,言之不胜浩叹[ 13 ]。”值得一提的是,民众乐园虽然最终回归商办,但民众乐园在政府主导下多部门兼管的管理模式却成为了国民政府日后构建地方公共娱乐管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即首先必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介入对公共娱乐业的管理,其次由于公共娱乐事业牵涉甚广,必须由多个政府机构齐抓共管。具体来说,在各地政府中往往由社会局负责对公共娱乐场所的登记注册以及经营活动的监督,教育局负责对戏曲、电影等娱乐演出内容的审查、改良以及对娱乐从业人员的登记、考察和改造,公安局则负责维护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秩序和日常治安。1928年汉口市政府组建了戏剧审查委员会,作为首个文化艺术和公共娱乐业的政府专职管理机构,委员会不仅负责有关公共娱乐事业管理事项的制定,执行省市政府的相关指令,还专门负责协调教育局、公安局、社会局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民众乐园的实践中所出现的多部门间权责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也标志着民国地方政府公共文化娱乐管理体系的初步定型。
(二)空间的内部改造
“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14 ]。由于公共空间在意识形态向社会广泛传输时具有天然优势,国民政府寄希望以此为媒介将其政治触手伸向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空间。在对民众乐园管理体制的探索过程中,政府也在不遗余力的推动其空间内部的改造。
1.高举的“三民主义”大旗:遗嘱亭
新市场建成初期内原设有一八角亭名曰“哈哈亭”,亭内布置有凹凸镜数面以供游人娱乐。新市场被充公之后,国民政府将其改为“遗嘱亭”,后又因“亭内每面制遗嘱一道,既无意义,又太笨拙”,遂改为“遗教亭”,总理遗教被摘录于亭中,并采用醒目的“蓝底白字标写,以引起游人注意”[ 15 ]。孙中山及其所倡导“三民主义”作为当时国内民主革命的指导性纲领,毫无疑问的在社会各界都有强烈的号召力。国民党当局一贯以总理遗志和三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一直以来都将“三民主义”视为凝聚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大力宣传,进而达到争取民众支持和服从的目的。早在新市场改组成立中央人民俱乐部之初,国民政府就已提出要“以宣传三民主义,促进民众健康,创造平民艺术,提高民众娱乐为宗旨”的建设纲领[ 16 ]。以期让民众在日常娱乐中被三民主义“教化”,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对国民党的认同感。从这一点看,园内的“遗教亭”除了承担纪念孙中山先生之作用外,更重要的则是将“中山”这一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国家政治符号根植于公共娱乐之中,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政府通过民众乐园这一公共娱乐空间向民众宣传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及三民主义思想,一方面通过灌输中华民国的国家观念从而增强民众对新政府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则能引导民众将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移情到国民政府身上,进而加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2.国耻教育的推广与实践:国耻馆
汉口市政府还在乐园内部设立了国耻馆,以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国耻馆是身兼社会教育功能和特殊政治意义的设施。汉口市政府认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鉴于此,“今欲唤起民众,必须将历次国耻之前因后果灌输人心,庶几映像,一深感奋斯起,此国馆之设立不容或缓”。政府将被近代以来中国在列强强迫下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序其先后,逐条开列,镌于馆之四壁”,此外还将彼时百姓受外国欺凌残害的各类惨案或用油画绘出,悬挂馆内,或专门制作模型摆放于馆内,使“游人身入其境,即生感动,于以发奋自强以雪国耻”[ 17 ]。
事实上,国民政府早在执政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国耻教育的价值所在,在1915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国耻教育首次被纳入中小学启蒙教材,成为彼时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新政府的合法性往往不够稳定,许多老百姓还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要尊重它”[ 18 ],所以推动国耻教育不仅可以激励广大民众雪耻救国,还成为国民政府在早期向社会各界展示权力,赢得认同的重要手段。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梁寒操就曾呼吁:“甲午耻,尤未雪,济南恨,何时灭?国人绝非无此心,所苦的是无此‘力而已”,无论是雪耻也好,救亡也罢,都离不开教育二字。而“中国之不振恰恰在于没有民众的教育,在于没有革命的救国的全国的民众的教育”[ 19 ]。国耻馆正是这一时期国耻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实践,为了发挥其特殊的教育功能,国耻馆大多被设立于如公园、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之内,民众乐园自然也不例外。其往往通过陈列展览国家受辱的相关主题内容,利用视觉感官上的冲击使参观者产生强烈的情绪反映,民众通过实地参观,在所营造的悲痛屈辱的氛围中见证民族苦难,自然有助于强化国耻记忆,进而增强社会公众救国雪耻的决心和信心。更重要的是,国耻馆的存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使民众在这种屈辱感和神圣感之下萌生出对国民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并“最终沉淀为一种城市的集体记忆和市民心理的一部分为每个人所恪守”[ 20 ]。
3.重铸国魂的政治愿景:国技馆
汉口市政府鉴于武术作为我国“国粹”,其“派远流长,精妙无比,实为欧美各国所不及”,民众乐园虽原有五福班、少林会等武术组织,但其性质皆属于卖技表演,对武术的进步发展作用甚小,鉴于此,汉口市政府特在园内新设一国技馆。国技馆中除了置办各种武术器具供大众练习,还定期举办国术训练班,邀请武术专家到园进行指导[ 21 ]。从而鼓励民众练习武术强身健体,“于提倡体育发扬国光不无裨益”外,还能使“国术之发扬光大,以奠党国于永固”[ 22 ]。
“国技为吾国之国粹,神而化之,小足以却病健身,大足以御悔卫国”[ 23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下,中国传统武术不仅被赋予了强健体魄和保家卫国的双重功能,还被赋予了更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武术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视为国粹,肩负起重铸国魂的使命。对国民政府来说,开展武术教育不但是“卫国利器”之本,还是践行三民主义的重要措施。在这种武术救国的思想下,武术教育得以快速进入到国家政治的范畴。1929年和1932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国民体育法》和《国民体育实施方案》,鉴于“国术实为体育活动之一种,不能因其为我国所固有者而予以特殊之地位,以捐弃他合乎科学及教育之体育活动也”[ 24 ],国民政府不但将武术纳入到学校体育课程标准之中,还在全国各省市陆续建设公共体育场及国术馆作为推广社会武术教育提供施教场所。仅在1929年,这类以国术馆、国技馆为代表推广社会武术教育的场所就达到了1142个,民众乐园内的国技馆正是在此背景下设立,成为政府践行社会武术教育、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实体。
4.国货运动的主阵地:国货陈列馆
汉口市政府鉴于“本市国货,销路疲滞,洋货充溢,其影响于工商业之进展”,特在民众乐园内“亭子间五层楼房屋(自二层至六层)”设立国货陈列馆。以期“非但可以起市民观感,尤为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之要点”[ 25 ]。国货陈列馆的设立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推动国货运动的重要举措,自民国成立伊始,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推销国货为主要内容的国货运动日益兴盛。1928年,时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提出了“策励工商、提倡国货”的经济建设方针,不但会同中央各部院专门成立了国货调查委员会,调查国货产销行情,奖励国货生产,还陆续在各省市繁華地段设立国货陈列馆,广泛征集产品,分部陈列,用以比较观摩,进而推动国货的改良发展。民众乐园内的国货陈列馆同全国各地一样,内设总务、出品、审核三股,除了负责国货陈列的相关事宜,还兼具出售和改良国货之责。为了鼓励民众选择国货,馆内专门附设售品部用以出售商品,其“场内货物,均经免税减运。价格自较市上为廉”[ 26 ]。此外,陈列馆还专门“研究仿制外货”,负责为国货商品的改良提供指导。而在各地国货荟萃一堂,相互比较观摩的过程中,不但能让民众近距离的接触商品从而萌生购用之意,还激发了厂家由竞争而生的改良奋发之心。可以说,不论是抵御西方经济侵略,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还是凝聚民族意识,增进民众团结,国货陈列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可谓“国货陈列馆之设置,原为提倡国货。骈罗万货,使国人感奋而激发其爱国精神!比较观摩,而发生竞进改良之兴趣;作永久之宣传,使国人对于国货之重要,家喻户晓,互相勉励,而成乐用国货之习惯,国货陈列馆之于提倡国货实有最大之功动。”[ 27 ]
(三)戏剧的改造
彼时的欧美国家早已意识到戏剧重要的政治功能,故“多以市款建筑戏院,自行办理”,从而让政府可任由支配一市之戏剧,达到“凡所提倡,凡所禁止,均可实现之”的目的[ 28 ]。鉴于其如此重要的政治功能,作为民众乐园内规模最大的支柱性娱乐项目,戏剧毫无疑问成为了政府对娱乐内容改造的首要目标。
1.平民剧社和清吟社
汉口市政府在园内陆续新建了专事楚剧表演的平民剧社。楚剧原为湖北黄孝各县乡之中的乡村土曲,早先被称作花鼓词,因其词调浅俚,表情深刻,不识字的乡民们均能听懂其意,因此作为通俗戏剧在湖北民间广为流传。1926年国民革命军控制湖北后,为使花鼓词符合党义宣传的需要,国民政府便对其内容加以改良后称之为楚剧,因楚剧受众多为城市和乡村的一般平民,剧社因此被命名为平民剧社。由于早先汉口市的各个戏院大多为商民承办,加之政府未深刻认识到戏剧之功效,遂造成汉口市“所演之戏,专事迎合社会幼稚心理卑陋龌龊”,而楚剧因脱胎于乡村土曲,所以这一情况更为严重。为了改良楚剧促使发挥其社会教育的作用,汉口市政府首先将平民剧社所有常演的楚剧剧本汇集专人进行审议,其中“遇有戏名过俗或涉秽亵者,先行更改,继以修饰词句”,其次还面向社会广招戏剧人才编撰剧本,革新淘汰一批旧有落后词调,以达到楚剧“最良之通俗戏剧为目的”[ 29 ]。此外,政府还将园内另一剧社群芳会改名为清吟社。群芳会原为园内校书清唱之所,因取幽雅之意而以群芳为名,后因其名“似嫌狎邪”遂改名为清吟社,和专事楚剧的“平民剧社”不同,清吟社专门负责演唱京汉正戏,剧社内不仅常常聘请程砚秋等戏剧名家来此表演,还组织专人编撰革命戏剧或时事新剧,这些新剧多以党义、国耻等主题为歌词,并谱以新曲由演员在园内循环演唱,以使园内游客在聆音之余有“相当感化”。
2.戏剧训练班
除了对剧社的改革外,汉口市政府还广招各界戏剧人才在民众乐园内新设戏剧训练班,以希望其成为汉口“艺术界之发动机”。戏剧训练班顾名思义即以“实地训练”为主旨培养戏剧人才,其定期面向社会招生,学员多以中小学生为主,并设有严格的选拔考试。在政治教化的需求下,训练班的培训内容不但有传统京剧,还有改良新剧。老师平日不但向学员教授最新的艺术知识,还鼓励学员们进行戏剧的创新。通过考核训练合格的学员,除了日常在园内演出工作外,还定期组成团体外出表演新剧。戏剧训练班的设立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推动了汉口戏剧的传播和发展,也为政府推广革命新剧,传播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支持。
政府对民众乐园内戏剧机构的改造,一方面推动了戏剧的健康发展,重塑了戏剧的公共娱乐价值,在社会教育层面有益于“世道人心”,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主导全市戏剧的标准控制了对内宣传的重要通道,戏剧作为承载政府作政治教化、舆论控制乃至对民众行为的引导的载体,成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公共娱乐建设的重要一环。
(四)社会功能的演进
近代城市娱乐的不断发展为国民政府进行广泛的政治教化和社会动员提供了重要舞台。城市公共娱乐因兼具“政治吸收功能”“价值导向功能”和“利益表达功能”而被政府当局所倚重[ 30 ]。在政府“娱乐艺术化,艺术革命化”的政治改造下,娱乐让位于政治,以民众乐园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开始发生改变,进而成为政府用以灌输意识形态的政治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汉口市政府通过在民众乐园组织举办各类形式的政治活动,在向民众进行政治教化的同时,有意无意间也推动了其空間属性和社会功能的转变。
1.政治讲演
政治讲演是最典型的政治活动,除了本市的政客、学者、社会名流之外,其他如李济深、戴季陶等来汉的国民党大员也都首选民众乐园进行讲演活动。慷慨激昂的演讲可以传递热情、感动和激情,在讲演的过程中,园内数万市民汇集一处,静立聆听,讲台上大人物的“演讲之声反射于耳鼓,训诫之词萦绕于脑际”[ 31 ]。再辅以隆重的仪式、精心布置的会场以及激昂的口号,足以让台下的市民对台上的演讲者产生敬畏,在不经意间认同其宣讲的内容与精神,从而萌生对政府当局的服从与拥护之情。
2.纪念活动
“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举行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往往是教育世人”,通过这些纪念活动,“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 32 ]。在民众乐园所举办的纪念活动中,最多的就是以孙中山为主题的纪念活动。1929年11月12日,孙中山六十三年诞辰纪念大会在民众乐园内盛大举办,当天武汉市“各区党各分部党员及各学校各机关各团体代表等,均相继冒雨到会”,“时至正午十二时,到会者已达三千人以上”,国民党一向擅于利用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其做政治背书,此类大会大都以“继续总理光明伟大的精神”和“完成总理的遗志”为主题,通过纪念孙中山的伟大精神激发民众的敬仰之情,在总理遗志的号召下团结一致,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即“我们的党是总理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的民众都要去拥护党,我们今日的中华民国是总理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民众都要爱护民国,而后总理留下给我们的遗产,才不会失去,那才是今日纪念总理诞辰的意义。[ 33 ]”此外,民众乐园还经常举办追悼牺牲将士和死难同胞的纪念活动。如1928年10月14日在民众乐园内为悲壮殉国的飞行员刘国桢所举办的追悼大会。当天乐园“门首与马路侧门,均悬有素花牌楼”,“花圈约二百余具,陈列灵前,会场内外挽联约千余幅,悬挂殆遍”[ 34 ],现场民众无一不为之动容。英雄人物的牺牲最能唤起大众的同情,政府通过在民众乐园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歌颂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使民众的悲愤情绪和爱国热情油然而生,从而更加自觉的团结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
3.政治互动
公共娱乐空间作为一个公开的、自由的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彼此了解的平台,从而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政治互动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汉口市政府在民政乐园所举办的市政宣传周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范例。从1929年3月24日开始,汉口市政府定期在民众乐园举行市政宣传周。在宣传周活动中,从市长到各局长每天轮流于园内举行演讲报告,一周内依次将汉口的市政建设、财政、公安、社会事业、工务、卫生以及公用事业的施政计划与建设方针向民众公开述职,并征求民众的监督和建议。此外政府还将两百余种与市政有关的图书表册公开陈列以供市民阅览,并专门设立询问处答复市民询问。时任武汉市长的潘宜之在第一次市政宣传周中讲到:“市政府办市政,就如同人家公仆或账房办家事一样,人家公仆账房所办的事,要报告主人使主人明瞭,以便市民可以批评,可以监督,一市的市政,定要政府与市民这样合作,才可以把市政办得好。[ 35 ]”市政宣传周的举办使市民得以亲自参与到市政建设之中,政府与民众在民众乐园中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依赖感,通过给予民众主人翁式的意识,提高了民众自发性的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进而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之中自觉维护国民党的现有统治秩序。
三、结语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曾指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36 ]。”在他看来,公共生活离不开空间这个载体,同样,权力的运行也无法离开空间的基础,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权力运作的工具,权力在空间中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空间,并组织着空间。国民政府对城市空间的政治改造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权力意志,还通过塑造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规范,维护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在空间改造的过程中把原先基于地域、血缘、宗教关系之中的民众认同转变为服从国家权威的政治认同。即“任何空间的存在、生产、重组都必须以维护党的合法性和国家的自主性为前提”[ 37 ],民众乐园这类极具控制和教化意义的公共空间即是如此。
审视民众乐园的发展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如何通过政治化的改造,使民众乐园成为其延伸政治力量,传播意识形态,推动社会教育的的重要媒介。民众乐园自建成伊始,就凭借多元的娱乐文化成为近代汉口最大的文娱商业综合体。而后又因具有公共空间的天然优势,成为了国民政府塑造权威,赢得民众认同的重要媒介,事实上,无论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对民众乐园体制、内部空间、演出内容亦或是社会功能的改造,都可以说是其在探索城市公共娱乐事业建设的缩影。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对民众乐园管理体制的艰难探索与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为之后建立以戏剧审查委员会为主导的地方公共文化的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从内部空间看,民众乐园成为了日后政府改造建设公共空间的范式,类似遗教亭、国耻馆等这一类具有强烈政治导向的设施在中山公园、阅马场、武昌公共体育场等近代汉口著名的公共空间中都有所体现。从演出内容看,政府通过对戏剧的改造控制了对内宣传的重要通道,戏剧作为承载政府作政治教化、舆论控制乃至对民众行为的引导的载体,成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公共娱乐建设的重要一环。从社会功能看,在政府“娱乐艺术化,艺术革命化”的精心设计下,民众乐园的娱乐功能让位于政治功能,成为了汉口市宣传教化的重要场所。“寓教于乐”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公共娱乐空间不仅仅是专供民众的享乐空间,在政府的精心设计下,它还可以是进行政治教化和社会教育的政治空间。从这一点来看,民众乐园的范例无论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研究,乃至当下政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化建设,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社会学研究,1999(3):37-38.
[2]螺隐.汉口将建新市场 模仿上海大世界[N].小时报,1918-07-17.
[3]汉口新市场已落成矣[N].汉口新闻报,1919-05-27.
[4]盛雨时.汉口新市场开幕之先声 期在阴历新年[N],小时报,1919-01-25.
[5]严铁颜.恭祝纪念庆贺节喜[N].汉口新市场日报,1924-06-02.
[6]武汉市社会局.附属机关纪略:汉口民乐园纪略[J].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1929(1):20.
[7]傅才武.民国地方政府管理近代文化娱乐业的探索——以汉口为中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109-114.
[8]血花剧社紧要启事[N].汉口民国日报,1927-03-04.
[9]武汉市公安局.交替市政各机关[J].武汉市政公报,1928,1(1):54.
[10]胡宗铎.训令:武汉市市政委员会训令(十七年十一月三日) 令公安局将民乐园交归社会局接受并分令[J].武汉市政公报,1928,1(1):55.
[11]涂允檀.函公安局为奉市委会令据既济水电公司呈民乐园冯前主任任内积欠该公司水电费事请酌量见复由[J].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1929(1):41-42.
[12] 冯伯谦.汉口民众乐园征信录序二[G]//武汉市文化史志办公室.武汉文化史料(第一辑).1996:35.
[13]唐性天.论汉口市公共娱乐之建设[J].社会,1929(3):83.
[1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2.
[15]武汉市社会局.附属机关纪略:汉口民乐园纪略[J].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1929(1):22.
[16]中央人民俱乐部组织大纲已经市党部通过[N].汉口民国日报,1927-08-25.
[17]武汉市社会局.附属机关纪略:汉口民乐园纪略[J].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1929(1):22.
[18]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
[19]梁寒操.从国耻说到教育的再造[J].再造,1928(8):27-35.
[20]胡俊修,李勇军.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J].甘肃社会科学,2009(1):178-181.
[21]武汉市社会局.附属机关纪略:汉口民乐园纪略[J].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1929(1):23.
[22]中央国术馆举行第一次国考敬告民众书[J].广西教育,1928,1(2):46.
[23]向恺然,唐豪.国技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1923:15-16.
[24]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案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14.
[25]武汉市社会局.筹办国货陈列馆[J].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1928(1):126.
[26]国货近讯湖北省国货展览会开幕[J].国货月刊(上海),1935(2):67.
[27]李平衡.提倡国货运动之回顾与前瞻(四):我所希望于国货陈列馆[J].实业部国货陈列馆三周年纪念特刊,1932:5.
[28]唐性天.论汉口市公共娱乐之建设[J].社会,1929(3):83-87.
[29]武汉市社会局.附属机关纪略:汉口民乐园纪略[J].武汉市社会局局务汇刊,1929(1):21.
[30]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81.
[31]胡俊修,李勇军.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J].甘肃社会科学,2009(1):178-181.
[32]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88-189.
[33]前日武汉各界总理诞辰详志[N].汉口民国日报,1928-11-14.
[34]追悼飞机队长刘国桢 今日在民乐园举行[N].汉口中山日报,1928-10-14.
[35]武汉市政府秘书处.市政宣传周纪盛[J].武汉市政公报,1929(5):102-118.
[36]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4.
[37]朱靜辉,林磊.空间规训与空间治理:国家权力下沉的逻辑阐释[J].公共管理学报,2020,17(3):139-149,175.
[责任编辑:马好义]
收稿日期:2022-04-23
作者简介:谢松晟(1996—),男,河南遂平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