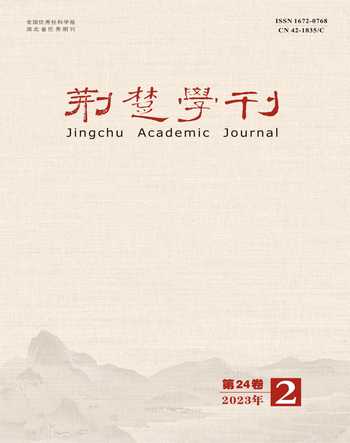汉代西王母神画嘉禾图像研究



摘要:在山东、陕西地区的西王母题材的汉画像石中,存在少数带有嘉禾图像的情况。通过梳理先秦两汉时期有关嘉禾的文献及汉画像石,可以发现,嘉禾并非西王母神话中原本具有的元素,只是在东汉之后逐渐与生长于昆仑的木禾融合、混用,方与西王母神话系统产生联系。在东汉之后的汉画像石中,嘉禾图像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嘉禾与凡人侍者、鸟首神人、羽人等侍者形象共组,充分展现汉代人对长生不死的向往。
关键词:西王母;汉画像石;嘉禾;木禾;长生不乱
中图分类号:K879.4;K234;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2-0087-10
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位神灵,她的形象从诞生之初的“豹尾虎齿”,“蓬发戴胜”,到具有度化升仙、延年益寿、赐子赐福等神力的美丽妇人,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神话系统。而这个神话系统在定型的过程中,不仅兼容了不同时代所赋予它的独特内容,融合了多种原始神话,同时也凭借着其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近年来,学界对于西王母神话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西王母本身,甚至该神话系统中所出现的伴兽、羽人、植株也被发现具有复杂而深厚的文化内蕴(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王母神话系统中,由于植物往往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即便借助现有的传世文献,也很难揭示出这些植物本身被赋予的内涵。因此,本文以汉代西王母神画中的嘉禾图像为研究重点,以这类图像发现较多的山东地区为例,结合此类图像产生的社会背景,探究其艺术规律及内涵。
一、嘉禾与木禾考辨
在西王母神话系统中,胜、兔子、九尾狐等图像,不仅是汉代画像中西王母的重要附属物,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可以作为辨别西王母形象的标志。不同于此类图案,嘉禾并不是西王母神画中普遍存在的附属物,不仅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嘉禾共同存在的例子相对较为少见,甚至在传世文献中,也鲜少能找到西王母与嘉禾直接关联的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嘉禾,昆仑仙境中的另一种植物“木禾”,却屡屡出现在昆仑神话记载中。那么,木禾与嘉禾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对于木禾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西经》( 2 ):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1 ] 294。
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 。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 1 ] 299。
《山海经》中对木禾的记载交代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木禾生长于昆仑山上;其二,文中所言之木禾,与寻常之禾相比,高大异常,甚至有如乔木之态。除此之外,《山海经》不但没有表明木禾与西王母的直接关系,甚至全书也并无有关嘉禾的内容。可见,至少在《海内经》成书的时代,木禾仅仅是昆仑系统的组成部分,尚未与西王母建立联系。
在略晚于《海内经》的《穆天子传》中,也有有关木禾的内容:
庚寅,至于重 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麦,爰有答堇,西膜之所谓木禾,重 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重 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 瑶,琅玕,玪 , ,玗琪, 尾,凡好石之器于是出。[ 2 ] 12
较之《山海经》相关记载,上引文不仅延续《山海经》中木禾长于昆仑之说,且更具体指出木禾生长在“重 氏黑水之阿”。此外,《穆天子传》褪去较多《山海经》赋予木禾的神异色彩,将其还原为黑水之阿的寻常作物。
木禾生长于昆仑墟相关记载,亦見于《淮南子·地形训》,其文曰: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 3 ] 40
值得注意的是,《穆天子传》在记述木禾生长环境时,有“采石之山”一语,而此山正出产“枝斯”、“璿瑰”等玉石。因此,高中正经考证后指出,或许正因为黑水之阿的采石之山出产美玉,所以此山又被写作“旋/琼山”[ 4 ]。由此可知,旋/琼山之禾,亦指木禾。先秦两汉文献也多有此称:
“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吕氏春秋·本味》)[ 5 ] 104
楚苗之食,旋山之饭;捖〔之〕不毁,壹啜而散。(《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反淫》简14)[ 6 ] 94、124
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说文·禾部》引《伊尹》)[ 7 ] 32上
由此可知,木禾在先秦人们的观念中,即是生长于昆仑仙境中的作物,是昆仑神话系统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就木禾的基本内涵而言,尽管所出现的面目不一而足——或是被神化为高大如乔木的神异植物,或是将其置于盛产玉石的西方异境,或是强调其美味,但木禾作为“饭”的意义,基本上是稳定的。之后,随着昆仑山神话系统与西王母神话系统的融合,木禾也就成为了西王母神话中的因素。
反观嘉禾,《穆天子传》已出现相关记载:
天子乃赐赤乌之人□其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宝玉之所在。嘉谷生之,草木硕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树于中国。[ 8 ] 7
除上引文外,文献中与嘉禾有关的记载,多与祥瑞的意义有关,例如: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尚书·微子之命》)[ 9 ] 522-523
王者德至于地,则华频感,嘉禾生。(《孝经·援神契》)[ 10 ] 974
恩及于土,则五谷成,而嘉禾兴。(《春秋繁露·五行顺逆篇》)[ 11 ] 79
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汉书·公孙弘传》)[ 12 ] 2616
臣莽数叩头省户下,白争未见许。今幸赖陛下德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汉书·王莽传》)[ 12 ] 4050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荚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则朱草生,木连理。(《白虎通义》)[ 13 ] 283-285
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刘秀)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嘉禾生,一茎九穗,大于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上曰秀。(《东观汉记》)[ 14 ] 1
从上引文可见,嘉禾被视作祥瑞,由来已久。直至汉代,受到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嘉禾作为瑞应的特性又不断被强调。木禾是以其硕美、美味的特性而不断被赋予神异色彩,而嘉禾则是因为其异本同穗,或一茎九穗的异象而被不断渲染。虽然在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中,也曾提及嘉禾硕美的特点,但是与之后的祥瑞崇拜相比,《穆天子传》中的嘉禾,显然带有原始的植物崇拜的痕迹,进入祥瑞崇拜时期的嘉禾,方才脱离了原始的崇拜印记,开始与国家、社会相联系,具备了政治层面的含义。
然而,嘉禾与木禾并不是两条毫无牵涉的平行线,至迟在东汉中期,嘉禾就已经与木禾融合,进而成为了西王母神话的一部分。如張衡《思玄赋》云:“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抨巫咸以占梦兮,乃贞吉之元符。滋令德于正中兮,含嘉禾以为敷。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居”[ 15 ] 1920,显然已经不区别木禾与嘉禾了。更有甚者,在托名班固的《汉武帝内传》中,通篇不见木禾之称,而“太微嘉禾”则与一众仙草并列,成为西王母世界中的附属物,可见木禾与嘉禾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尽管《汉武帝内传》一般被认为是六朝人所作,然其记载多与东汉相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东汉时期的观念。
实际上,嘉禾与木禾出现融合与混用的情况,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二者本体的相似性。首先论木禾本体。郭璞注《山海经》,称“木禾,谷类也,生黑水之阿,可食。”[ 1 ] 295然其注《穆天子传》时,则指出“木禾,粟类也。长五寻,大五围,见《山海经》云。”[ 2 ] 12显见郭璞将《山海经》中的木禾与《穆天子传》中的野麦互训,默认二者当为一物。但具体到为二者归类时,却又出现粟类与谷类之别。
据《左传·隐公三年》之言,“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杜预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言取者盖芟践之。”孔颖达疏:“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则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传在武氏之上。案经,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则知此是七月,故为今之夏,谓今之五月也。麦熟在夏,而云麦、禾皆未熟者,谓四月之时麦未熟,七月之时禾未熟,二者异时,故言皆也”[ 16 ] 74。可见《左传》中的麦与禾并不能完全等同。故知,禾在先秦时期,虽然有作物总称的用法,但就木禾而言,显然是特指一种作物,所以郭璞以为木禾即野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又《吕氏春秋》将“玄山之禾”与“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并举,也表明木禾非粟、非穄、非秬。
再就木禾名称而言,简单将其归为谷类或粟类也并不妥当。与木禾的命名结构极为相似的,还有《诗经》中的“木瓜”“木桃”“木李”。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曰:“桃之大者为木桃。”[ 17 ]就此来看,似乎木禾之木亦可解释为“大”,结合《山海经》中“长五寻,大五围”的说法,认为木禾即大禾,似无不妥。然而,正如邢公畹先生所指出的,木瓜、木桃、木李之“木”,结合侗傣语的语序来看,并非是指现代汉语中的树木之“木”,而是指果实。[ 18 ]这种用法正如称呼树杞、树桑一样,实际上是上古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大名冠小名的语序,并且“时间越早,它运用的范围越广泛”[ 19 ]。就木禾之称的产生时代来看,木禾之称是符合此一规范的。因此木禾应当是木本禾谷类作物。
其次,就嘉禾本本体而言,前引《穆天子传》中有“嘉谷生之……天子于是取嘉禾以归”之言,可见“嘉禾”即用以指代“嘉谷”。《说文》进一步指出:“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 7 ] 320又指出“粟,嘉谷实也。”[ 7 ] 317由此可知,粟即嘉谷,也就是嘉禾之本体。
综上所述,木禾与嘉禾是全然不同的两种植物,前者是昆仑系统中自始至终都具备的元素,而嘉禾虽然也与昆仑系统存在联系,然其多以祥瑞面目出现,是人间的植物。时至东汉,嘉禾替代了木禾,成为西王母神话中的组成部分。
二、西王母神画中的嘉禾
嘉禾是在东汉时期通过与木禾融合、混用,从而进入西王母神话系统。然而,嘉禾与西王母神话系统的联系,仅靠文献并不能完全解决。幸而汉代画像石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带有嘉禾图像的西王母神画,在山东、陕西、四川均有分布。然而,四川出土的相关图像数量较少,且多数时代较晚、受其他地区风格影响的痕迹明显。而出土于陕西地区的图像,虽然数量可观,但是经李凇先生考证,该地区带有嘉禾的西王母神画明显受到了山东嘉祥样式的影响[ 21 ] 164-171。因此,本文拟以该类图像出现时间较早,且影响较大的山东地区为主,辅之以陕西地区的图像,以分析嘉禾与西王母神话的关系。
(一)嘉禾形态的辨析
就目前可见的汉代西王母画像砖石来看,带有嘉禾图像的情况如表1所列:
对于嘉禾的形态,文献中多有记载:
三本一茎九穗,长于禾一二尺,盖嘉禾也。(《论衡·吉验篇》)[ 22 ] 47
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居。(《思玄赋》)[ 15 ] 1932
是岁嘉禾生,一茎九穗,大于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上曰秀。(《东观汉记》)[ 14 ] 1
嘉禾茎长五尺,三十五穗。(《尚书中候卷下》)[ 10 ] 1203
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茎长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连茎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极也。(《春秋说题》)[ 10 ] 215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对于嘉禾形象的描述具备三个特点:一是较寻常“禾”更高大,二是垂颖,三是多穗。而在汉画像砖石的嘉禾图像中,与文献描述较为相符,且带有榜题者,见于甘肃成县摩岩石刻西狭颂中的《五瑞图》(图1、2)
《五瑞图》中的嘉禾除有左右互生的禾叶外,左侧有四穗,右侧有五穗,共九条谷穗,穗末呈圆弧状,较为粗大,且谷穗下垂的特征尤其明显,是典型谷穗的造型。与之类似的,还有江苏睢宁九女墩画像石中的嘉禾图像(图3)。结合农耕场景中禾的形象(图4、图5)来看,汉画像石中所表现的禾的共同特征,即皆有叶与穗,叶端呈尖形,穗各呈长水滴状、纺锤状或长条状,皆下垂。反观山东、陕西地区汉代西王母画像中的嘉禾图像,显然并不具备明显的叶、穗同构的特征,反倒更趋向于仙草的形象。就此看来,山东、陕北地区的“嘉禾”是否仍能被视作禾呢?
(二)嘉禾图像的分类
目前学界认为西王母神画中的嘉禾图像分为四种:一是其植株表现为长茎两侧各有两簇如须的线条,顶上有一蕾苞,见于嘉祥五老洼第五石(图6)与嘉祥村画像石(图9);二是呈单穗状、无叶的植株形态,见于陕西绥德县军刘家沟画像石(图12)、陕西绥德县四十铺画像石(图13);三是表现为一茎多作三长条物下垂,没有穗的圆线条与粗壮感的植株,此种植株形态最接近西狭颂与农耕图中的禾的形象,见于宋山第四石(图7)与第七石(图8)、以及陕西绥德汉墓门框(图10);四是一短茎左右各一叶对生,顶上有一花苞的植株形态,见于陕西榆林南梁村汉墓门框(图11)。
就以上四种类型的“嘉禾”而言,其形態与仙草的形态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就第一种类型而言,其两侧须状的线条,当是对植株叶子的表现,这种双侧叶子对称分布,中间有花蕾的形态与第四种类型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两种类型的植物图像,虽然被个别学者认为是嘉禾( 5 ),但细究其形态,将其视作灵芝或仙草则更为妥帖。再看图十一中仙人所持之物,该物共分为三股,中间一股最长,呈花苞状,左右两股呈对称分布,与灵芝形象存在一定差异。据王仁湘先生考证,这一莲花形态的植株,应当是一茎三歧灵芝[ 24 ],但就目前所发现的灵芝画像来看,一茎三歧的灵芝多呈树枝状,如四川成都新繁县一号汉墓中玉兔所持灵芝(图14),而图十一中植株的三股结合紧密,状似花朵,并无树枝状形态。因此,王氏的观点尚值得商榷。以陕西定边郝滩汉墓的“西王母宴乐图”(图15)为对照,西王母上方的华盖左右两端装饰着有花苞的仙草,与图十一仙人所持之物极为类似,当是与之相同的植物。另外,西王母座下有一株三茎带菌盖的植物,此当为王仁湘先生所谓一茎三歧灵芝。而上述华盖的红色植物与灵芝一同出现,且形态差异较大,自然不是灵芝一类,故而认定其为仙草更为合适。
第二种类型的嘉禾图像,无疑是直接描绘稷的产物。与汉代典型的嘉禾图像相比,其差异在于前者意在刻画稷的单个谷穗,而后者在于表现稷的整体。与前者相比,后者对稷现实形象的描绘更为真实。因此,这两种表现形式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类型的图像仍有融合仙草形态的痕迹。在山东嘉祥宋山第二石(图16)上层画像石中,玉兔手中所持之物,与捣药兔身旁之物与该类型嘉禾形态极为相似。但宋山第二石中的植物顶端分为两股,呈麦穗状,显然并非谷类植物。又因为汉代西王母画像中的兔子往往具有制作不死药的特质,因此,该植物被玉兔所持,且又生于捣药的杵臼旁,其当为制作不死药的原料。更显著的例子,即在绥德四十铺画像石(图13)中,捣药兔身后神树的枝叶与鸡首人身侍者所持嘉禾,在形态上颇为相似。而《汉乐府·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据此推测,该神树的枝叶应当是不死药的制作原料。而鸡首人身者所持嘉禾,其形态当为谷穗与仙草(或神树枝叶)融合之后的表现。
第三种类型的嘉禾,虽然并不具备穗、叶同构的特征,但是制作者在画面中极力地刻画其末端下垂的特征,此当是对嘉禾垂穗的模仿。而这一类型的嘉禾其穗与叶的区别并不大,尤其在叶的部分明显要比农耕图中禾的叶子更为细长。值得注意的是,《海内十洲记》载:“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 25 ] 277菰的叶子窄而长,但却是如珊瑚状分布,不似谷物的植株。由此可见,第三种类型的嘉禾,在形态上显然兼融了不死草与禾的形态特征。
综上所述,嘉禾在东汉时期与木禾融合、混用之后,不仅继承了木禾性质与功能,而且随着西王母掌管不死药这一观念的盛行,嘉禾在西王母神画中不再具有祥瑞的功能,而是与西王母仙境中的仙草相融合,放大了其“食而长生不死”的特质。
三、手持嘉禾形象的象征意义
上述西王母神画中的嘉禾,均为侍者或羽人手中所持之物。对于这一形象的设定,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侍从向西王母献食的表现。王倩在《〈圣经·旧约〉方位结构》中提出:“旧约时代的希伯来人……将用来连接天地的神山与圣树改造成随处可见的石头与树”,使得石头与树成为上帝与人类交流的媒介[ 29 ] 159。这一说法放在西王母神画中同样适用。嘉禾自东汉之后已被视作生于昆仑的仙物,在墓葬中亦被视作昆仑的象征,即沟通西王母与人类的媒介。本部分将手持嘉禾的人物形象分为凡人侍者、鸡首人身侍者和羽人三种类型,并分别对其进行讨论。
(一)凡人侍者
“在古代的神仙思想里,只有特选的人才能接近神仙,比如周穆王、汉武帝等人,汉初这一观念发生改变,人们开始相信生而为神的特权是不存在的,个体生命经过努力也可以成为神仙。”[ 30 ] 32-33這种神仙观念的转变在西王母神画中的体现就是凡人侍者的出现。这类侍者出现在西王母神画中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山东嘉祥与滕州一带,陕西地区的此类画像明显受到了山东地区的影响。这些侍者往往手持嘉禾、三珠树、便面等侍奉之物,通常为侧身像,或跪拜或站立,见于山东嘉祥五老洼第五石、嘉祥县嘉祥村画像石及嘉祥宋山第七石。
嘉祥五老洼画像石中的侍者共五人(图3),西王母右边两人持嘉禾,左右各有一人持珠树,画面最左侧有一鸡首人身者持板。此五位侍者均呈跪姿,将手中所持嘉禾、珠树向西王母呈递。在宋山第七石(图5)中,东王公左侧有持嘉禾的凡人侍者跪在持杯的马头侍者之后,右侧为一侍者持三珠树( 6 )。值得考究的是,侍者向西王母进献三珠树果实,尚可理解,但侍者所持嘉禾均为植株状,侍者断无令西王母生食谷穗的道理。况且在嘉祥村画像石(图6)中,西王母左右各一凡人侍者持嘉禾,仿佛仪仗一般,显然嘉禾并无食用的迹象。因此,侍者持嘉禾应起到沟通仙界与人间的作用。
凡人侍者由凡人进入仙境的身份使其自然而然具有过渡仙、凡两界的作用,同时又手持作为昆仑象征的嘉禾与珠树,凡与仙的组合不正好构成了一个联通天界与凡间的整体吗?汉代的工匠将西王母仙境浓缩为侍者手中的一株嘉禾或珠树枝,与生者进献的酒浆一道出现在西王母身边,达到祭祀者以酒祭祀王母,以嘉禾沟通逝者与西王母的目的。
(二)鸡首人身侍者
出现鸡首人身者持嘉禾的西王母神画,在山东地区出现了一例,即嘉祥村画像石(图6),其余两例均出自陕西地区,即绥德刘家沟(图9)与四十铺画像石(图10)画像石。鸡首人身形象在西汉末就已经出现在山东地区,而陕北地区出现此类图像则是在东汉早期,当是源自山东地区。其中,嘉祥村与刘家沟二石。在人物配置上极为相似,即均有一乘凤车的男子向西王母处行进。画面中的乘车男子经李凇先生的考定,认为其为墓主死后升天或觐见西王母[ 21 ] 166-167。由此可见,这两块画像石尤其凸显了墓主拜谒西王母的形象,而鸡首人身侍者持嘉禾,沟通墓主与西王母的作用也得到了彰显。
实际上,鸡首人身侍者与嘉禾的组合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人们崇拜太阳金鸡的原始记忆。《艺文类聚》引《春秋说题辞》:“阳出鸡鸣,以类感也。”注曰:“日将出预喜于类,见而鸣也。”[ 31 ] 2348东夷部落崇拜太阳与鸡,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鸡鸣日出的现象使先民对于太阳的崇拜自然被附着在鸡的身上,使鸡成为太阳的世俗化形象。正因如此,鸡被视作阳物,具有驱鬼辟邪的功能,如《荆楚岁时记》引《炼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避瘟气。”又载:“帖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32 ] 5-6此种巫术活动可谓将鸡辟邪的功能彰显得淋漓尽致。汉画像中选择以鸡首人身侍者持嘉禾引渡墓主灵魂,也正是源自于金鸡的此种属性。
而陕西地区的鸡首人身侍者持嘉禾显然受到了东夷部落金鸡崇拜的影响,但并不是简单地承袭山东地区。首先,陕西一带原是秦人的土地,与嘉禾的联系较山东地区更为密切,《说文》云:“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声。一曰秦,禾名。”[ 7 ] 327其次,陕西地区原有的陈宝石鸡的崇拜是该地区鸡首人身侍者产生的直接原因。如牛天伟先生所言:“东夷崇拜的太阳鸟——天鸡,原本是具有报晓功能的雄鸡,后来随着秦人的西迁而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在当地饲养的雌性家禽鸡(食卵为主)的基础上,为求得生存,不得不适应当地盛行的民俗信仰——原始的母(雌)性崇拜,将天鸡改变性别,与羌人的灵石崇拜相融合而创造了雌性石鸡“陈宝”的传说。”[ 33 ]清褚人获《坚瓠集》载:“图经称昆仑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寿。”[ 34 ] 994这一说法可追溯到魏晋时期。东晋王嘉《拾遗记》云:“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35 ] 10由此可见,陕西出现鸟首人身者,与该地区的鸟崇拜有关,而鸟首人身者与嘉禾的组合,则是与神鸟赐寿的传说有关。因此,这一组合当具有长生不死的内涵。
(三)羽人
羽人是汉代画像中长生不死的仙人,多为人形加羽翼的形象。《论衡·无形》曰:“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 22 ] 34羽人持嘉禾者,见于宋山第四石(图4)与陕西绥德汉墓石刻门框(图7)。
羽人是人禽同体的神祇,“带有更多非人的、难以理解的神秘气质”[ 36 ] 106,同时,羽人还有博弈、骑马、飞翔等多种表现形态,可谓连接天上人间的精灵。羽人与嘉禾的组合即是将沟通仙、凡两境的强化。以宋山第四石为例,图中持嘉禾的羽人围绕西王母四周,另有一鸟首神人向西王母献酒。因此说,羽人持嘉禾进献的场景,更像是施展巫术的一种体现,用以形成人间与仙界的交流场。
四、结语
嘉禾并非西王母神话中原本具有的元素,只是在东汉之后逐渐与生长于昆仑的木禾融合、混用,方与西王母神话系统产生联系。在东汉之后的汉画像石中,嘉禾图像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嘉禾与凡人侍者、鸟首神人、羽人等侍者形象共组,充分展现汉代人对长生不死的向往。相关图像主要见于山东地区,以及受山东影响的陕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注释:
(1)目前学界关于汉代西王母图像中相关附件的研究,影响较大者如顾森先生从繁式、简式、象征式三种形式探讨了西王母图式中的胜、九尾狐、龙虎座等图式的象征意义(详参顾森.渴望生命的图式—汉代西王母图像研究之一[C]//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4.);陈履生先生将西王母与东王公视作一对主神,并探究了该类型图像中的底座、奇禽异兽、仙人嘉禾等组合的象征内涵(详参陈履生.神画主神研究[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32-45.);李凇先生将西王母图像志分为核心图像、必要图像、辅助图像与区域图像三类,并分析了西王母图像中的玉兔、九尾狐、蟾蜍等图像(详参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248-270.)。针对西王母图像中单个附件的研究,有关于羽人图像的研究,如贺西林的《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J].文物,2010,07.);关于九尾狐图像的研究,如李炳海《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李炳海.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J].学术月刊,1993,12.);此外还有关于西王母画像中三珠树的研究,如汤池的《释郫县东汉画象西王母图中的三珠树》(汤池.释郫县东汉画象西王母图中的三珠树[J].考古,1986,06.)等。
(2)关于《海内经》成书时间,目前学界众说纷纭,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讨论,直接采用茅盾先生的观点,即《海内外经》至迟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参茅盾.神话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47-150.
(3)李凇指出:昆仑山与西王母本是两个不同的神话系统,并以晋郭璞在《山海经》注释中所引东汉《河图玉版》等,说明昆仑山与西王母的融合体现了东汉以来的观念。详参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34.
(4)目前学界已认定,东王公是作为西王母镜像形象出现的对偶神,因此该画像石中虽无西王母形象,但是笔者以为其属于西王母神话系统,故仍有讨论价值。
(5)如陈履生认为陕西绥德汉墓门框左上的东王公图像包含羽人献嘉禾,榆林南梁村汉墓门框西王母图像有羽人持嘉禾图案。详见陈履生.神画主神研究[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82、83.
(6)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三株(珂案:作“珠”是也)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為树若彗。”又《金石索》指出:“此石画云物神仙之状,上作二神,一男一女,疑为东王公西王母也……右侧一侍者手执一物而三珠,疑即三珠树。”详参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2;[清]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98-99.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穆天子传:卷四[M].郭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刘安.淮南子[M].高诱,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高中正.北大简零札三则[J].历史文献研究,2020(2).
[5]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反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穆天子传:卷二[M].郭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11]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陈立.白虎通义疏证[M].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14]刘珍.东观汉记校注[M].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任昉;述异记[M]//汉魏从书第32册(清同治六年半亩园刊本影印).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
[18]邢公畹.诗经中的木字[J].中国语文,1996(6).
[19]罗琦.《诗经》中的“木”字和“琼”字:兼说上古汉语中的大名冠小名语序[J].贵州文史丛刊,2003(2).
[20]赵晓明,宋秀英,李贵全.薏苡名实考[J].中国农史,1995(2).
[21]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22]王充.论衡[M].张宗祥,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3]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24]王仁湘.汉画芝草小识[J].中华文化画报,2012(4).
[25]东方朔.海内十洲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2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社,1986.
[26]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27]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卷六·陕西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8]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J].文物,1982(5):71-78.
[29]王倩.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研究[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
[30]李虹.死与重生[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31]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2]宗懔.荆楚岁时记[M].姜彦稚,辑校.长沙:岳麓书社,1986.
[33]牛天伟,牛一帆.汉晋时期的“鸡首、牛首人身”神像新解[J].华中国学,2018(2):8-10,27.
[34]褚人获.坚瓠集[M].李梦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5]王嘉.拾遗记[M].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6]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马好义]
收稿日期:2022-04-23
作者简介:郝苗(1997-),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