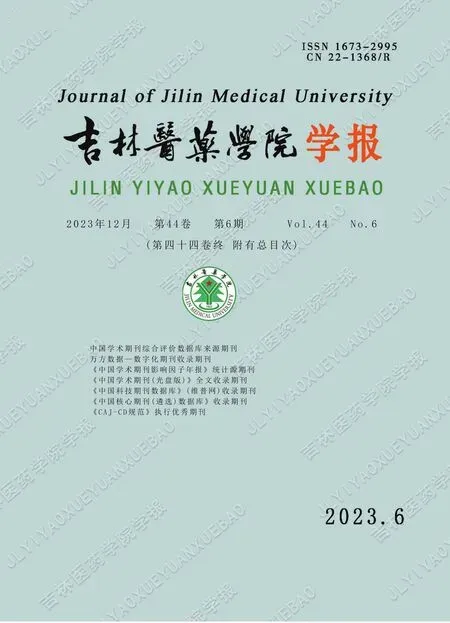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随访15年1例
赵 阳,赵 臣
(1.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五医院,吉林 吉林 132012;2.吉林医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31岁,有乙型肝炎家族史,母亲和舅舅为乙肝后肝硬化患者。自诉1996年其舅舅患乙肝后肝硬化去世,母亲带其(5周岁)体检发现HBsAg阳性、抗-HBe阳性、抗-HBc阳性,肝功、肝脏彩超未见异常,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量(HBV-DNA)未查,因无明显不适,未治疗。2007年高中就读期间因间断轻度乏力就诊,实验室检查HBsAg阳性、抗-HBe阳性、抗-HBc阳性,HBV-DNA 5.9×106copy/mL,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148 U/L,肝脏彩超未见明显异常。给予口服拉米夫定100 mg,1次/d,患者症状逐渐缓解。3个月后ALT正常,HBV-DNA降到3.0×103copy/mL。之后HBV-DNA一直在检测限以下(当时检测限是1.0×103copy/mL),肝功正常。连续治疗1年后,患者不遵医嘱擅自停药。停药后又出现乏力症状,2009年2月复查时发现HBV-DNA 7.8×105copy/mL,ALT 65 U/L,给予肌注重组人干扰素α-2a 300万u,隔日1次,患者症状缓解。2009年5月复查,HBV-DNA降至3.1×103copy/mL,ALT 53 U/L。2009年8月之后多次复查,HBV-DNA一直在检测线(1.0×103copy/mL)以下,肝功正常,疗程72周,2010年8月停药。停药2个月后复查HBV-DNA 3.5×103copy/mL,肝功正常,未治疗。2011年1月复查时发现HBV-DNA 4.5×103IU/mL,ALT 135 U/L,乙肝五项一直没有变化,表现为“小三阳”。口服拉米夫定治疗,HBV-DNA逐渐下降至阴性,ALT下降并保持正常。但治疗12个月后,2012年1月患者又觉乏力,复查 HBV-DNA升至1.25×107IU/mL,ALT 766 U/L,乙肝耐药基因突变检测提示拉米夫定耐药。之后给予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10 mg,1次/d。联合用药以后,HBV-DNA和ALT再次下降。2012年10月,HBV-DNA逐渐降至检测线(5.0×102IU/mL)以下,ALT正常。之后维持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治疗,肝功和乙肝病毒量控制较好。2020年根据《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版)》建议患者把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换成口服富马酸替诺福韦酯,300 mg,1次/d。更换用药后,患者肝功和HBV-DNA一直维持在正常和检测限以下(1.0×102IU/mL)。2022年,经多次检查患者HBV-DNA<20 IU/mL,HBeAg阴性,HBsAg 1400 IU/mL。根据《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版)》推荐意见第17条,结合患者个人意愿,加用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α),每周1次。治疗24周时,HBsAg 900 IU/mL,结合指南停用Peg-IFN-α,继续口服富马酸替诺福韦酯治疗至今。
2 讨 论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我国是CHB高发地区,虽然随着新生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接种的开展,我国HBsAg阳性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CHB依然是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大传染病。本个案的一个特点是患者发病年龄小,有家族史,考虑母婴垂直传播感染。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的年龄是影响感染慢性化最主要的因素[2]。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围产期,婴幼儿感染HBV后易发展为慢性感染,并且此类患儿多数处于免疫耐受状态,病毒不易清除[3]。另有研究认为HBV变异株可能直接造成宫内感染[4],形成免疫逃逸株,从而造成乙肝疫苗免疫阻断失败。因此,对可能由垂直传播感染的患者更应该定期复查,及时治疗,避免疾病进展。本案患者幼年发病,经长达15年的抗病毒治疗,期间经历了《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的多次更新,治疗方案的及时调整,抗病毒治疗药物的新老交替,核苷类药物和干扰素α(IFN-α)的联合应用。但治疗期间患者依从性差,不遵医嘱自行停药,导致HBV变异,病毒学多次反弹,HBV-DNA和ALT反复波动,HBsAg持续高位,难以清除,给患者的身体埋下了隐患。
本个案的第二个特点是患者擅自停用拉米夫定后引起病毒学反弹,产生耐药。拉米夫定是低耐药基因屏障药物,随治疗时间延长,病毒耐药突变的发生率增高[5]。该患者就是在治疗过程中,乙肝病毒发生了变异,对拉米夫定产生了耐药现象。抗病毒治疗过程中随意停药、依从性差导致的耐药成为临床治疗面临不可忽视的问题[6]。患者出现拉米夫定耐药后,改为阿德福韦酯联合拉米夫定口服用药。二者之间无交叉耐药位点且具有互补性[7],联合用于治疗拉米夫定耐药的CHB能有效抑制HBV-DNA复制,降低耐药率,改善患者肝脏功能[8],在本案中起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本个案的第三个特点是患者在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治疗过程中,虽然还没有出现病毒学突破,但是根据《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版)》[9]指导意见及时建议患者更换强效高耐药基因屏障的药物,即富马酸替诺福韦酯。富马酸替诺福韦酯是强效、高耐药基因屏障药物,对拉米夫定耐药、阿德福韦酯耐药以及二药联合耐药等情况都有较高的病毒学应答,且耐受性良好[5,8],患者换药后治疗效果验证了这一结论。
本个案的第四个特点是患者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两次应用了IFN-α。IFN-α能调节人体免疫系统,提高人体HBeAg和抗-HBe转阴率,病毒学反应更持久[10]。长效干扰素(PEG-IFN-α)在HBeAg血清学阴转及HBsAg清除方面更具优势[11]。但IFN-α耐受性低、不良事件发生风险较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临床使用[5]。患者第一次单独应用IFN-α治疗是在患者自行停用拉米夫定出现病毒反弹和肝功波动后,应用IFN-α治疗效果显著,持续治疗72周后停药,停药2个月后出现了病毒学反弹。第二次应用IFN-α是在服用富马酸替诺福韦酯治疗2年后,患者HBV-DNA低于检测线,HBeAg阴性,HBsAg 1400 IU/mL,且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因此根据2022版防治指南推荐意见加用Peg-IFN-α治疗,期望促进HBsAg转阴。但连续治疗24周后HBsAg仍保持在900 IU/mL,结合患者既往治疗史、HBsAg波动情况及2022版指南意见,考虑HBsAg清除可能性低,故停用Peg-IFN-α,继续口服富马酸替诺福韦酯治疗。
总之,HBV容易变异,且HBV-DNA易与患者细胞DNA整合,而目前的抗病毒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病毒复制但不能彻底清除HBV,因此CHB的抗病毒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HBV不易清除,但抗病毒治疗可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肝组织疾病的进展,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